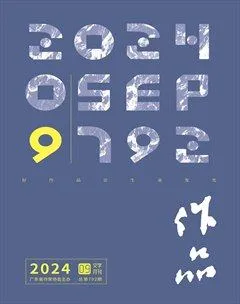一座神秘的城与城里的人(散文)
2024-09-30叶周
1
摩洛哥的马拉喀什(Marrakech)历史上曾经是摩尔人土生土长的地方,经过战争被法国人占领,最后又和平地回到穆斯林人的掌管下。基督教和伊斯兰教在这片红色的土地上自然生长,互为依存。人民在简朴的生活中过着日子,既接受外来文化,同时又珍惜和保存自己的悠久传统文化。
这是一座沙漠边缘的城市,却吸引了远离它的人来到此地,不仅仅到此一游,有些还把这里当作自己长久驻足的居住地,甚至是死后的归属。这座城市为什么有这样的魅力?这个问题始终环绕着我的思绪,当我的脚步踏在那片土地上,走过每一条斑驳的石路,嗅着空气中浓郁的焚香味,我对这座城市之谜越发好奇。
我从卡萨布兰卡坐火车到达马拉喀什火车站,车站的大厅前是一座高大典雅的拱门,门前透明的高大玻璃墙上挂着一面大钟,门外宽敞的空地上铺展着镶着花纹的地砖。第一面留给我的印象,这是一个现代化的城市,广场前的建筑是赭红色的,在蓝天下显得很特别。驱车进入一道环绕着的高高城墙,里面就是麦地那老城(Medina),街巷变得狭窄起来,路面居然都是用石块拼接铺成,可以想象铺设路面时会耗费多少人力和时间,不像铺水泥路或是柏油路那样可以大面积操作。
老城有属于它的气质,车到了一个较为宽敞的路口,下车后民宿的主人已经等在路边,帮我们提着小行李箱转进小巷。小巷里也是石头铺成的路,两边是民居赭红色的高墙,小巷里难得遇见人,可是很干净,欢迎我们的是蹲在路边的各色野猫。猫前加上了野字可能就会给人不好的印象。奇怪的是小巷中的野猫却显得干干净净,且十分文静。一条小巷中总能见到三五只黑猫或灰猫,毛色光亮,面目俊秀,或立或蹲坐于贴墙处,以目光与你交集。可以想见尽管它们宿于巷中室外,却并不缺少食物。猫文化是摩洛哥的一个标志。拐了几道弯到了民宿门前,黑色的木门上面有一排排整齐的金色铆钉。进门后就能见到马拉喀什的民宿典型的格局:中间是一个庭院,上可见天,四周是房间,一共有三层楼,三楼是天台。从住宿体验上来说,民宿中别有洞天,庭院里不可或缺的元素是喷泉、植物和花卉。
马拉喀什作为摩洛哥第二大城市,位于西南部荒漠边缘,天生流着非洲和法国的血。在柏柏尔语(Berber)中,马拉喀什本意是“神之地”的意思。人口约一百万的马拉喀什现为摩洛哥第一大旅游胜地,最早的居民是原住民,在以色列立国前,这里有约二十万犹太人居住。摩洛哥宣布独立以前,这里曾是法国殖民地,法国人便多起来;独立后大部分法国人离开了,却把这座城市当作度假胜地;甚至包括已经移民法国的摩洛哥人,时常还回来度假。
2
被称为继塞万提斯之后西班牙最杰出作家的胡安·戈伊蒂索洛(Juan Goytisolo)称马拉喀什的麦地那为“我的部落”。20世纪70年代,他第一次来到马拉喀什,很快就学会了阿拉伯语,他逐渐听懂了杰马艾夫纳广场上故事叙说者所说的内容,这些内容也影响了他的创作。终于有一天他决定移居马拉喀什,住在离杰马艾夫纳广场(Jemaa el-Fna)不远的街巷中,他在那里住了20年直到逝世。他每天从住处散步到那里与市场上的本地人说话聊天。那里聚集着养蛇人、驯猴的、驯鸟人、说书人、杂技艺人,还有食品摊档的主人。可以说在马拉喀什,只要你真有一技之长都绝不会放过到那里去显摆一下的机会。
令戈伊蒂索洛如此着迷的杰马艾夫纳广场,大约始于公元1050年。“杰马艾夫纳”在阿拉伯语中的意思是“死者的集会”。广场位于麦地那的中心地带,距离皇家离宫不远,附近就是著名的库图比亚清真寺。历史上广场最初是公开处决罪犯的场所,后来成为军队集结的地方,19世纪以前广场边还有一个奴隶交易市场。随着时代的发展,那些都已一去不复返了,现在这里是贸易、社交生活和民俗文化集中的区域。
戈伊蒂索洛曾经为保持广场的原汁原味专门撰写文章。正是在戈伊蒂索洛和一些摩洛哥本土知识分子的倡议下,联合国教科文组织1999年11月创建了名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计划。此前的会议就在马拉喀什举行,主要讨论文化空间的保护问题。正是在这次会议上,人类口头遗产这一文化人类学意义上的新概念得以确定。2003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制定了专门文书:《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非物质文化遗产涵盖传统知识、艺术和技能等内容,制定遗产公约的目的是确保这些内容得到保护和传承。时至今日该公约已得到180个国家批准,目前全球有超过600项遗产入选。1985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已将马拉喀什的麦地那老城列入《世界遗产名录》。而在2001年,被戈伊蒂索洛称为“我的部落”中的街头说书人、耍蛇人、魔术师等一众来自民间的传统文化人集结的这个广场,成为一个原始文化景观,再次被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戈伊蒂索洛曾提起过一个说书前辈索鲁赫(Srouh)的故事,索鲁赫是广场上最著名的说书人之一。20世纪40年代他还是一个男孩时,从农村来城市谋生,可得知马拉喀什找不到工作,就忍饥挨饿以说唱为生。他声音很美,就在广场上唱《古兰经》的诗句,但没有人关注他。他唱了三天,但人们路过时没有在他的帽子里留下一枚硬币。绝望之下他唱了又唱,还是没有人留意他的歌声。一个骑着驴子的柏柏尔农民路过,驴蹄几乎踩在他身上。愤怒的索鲁赫把驴子和骑手都抱在怀里举了起来。他非常强壮,好像没觉得有什么分量。驴子从未遇见那么有力量的人,惊恐地大声嚎叫,叫声引来路人的注意,蜂拥过来看热闹。“白痴!”索鲁赫愤怒地骂道:“你们懒得停下来听真主四天,现在却愿意听驴子的哭声?”随之而来的爆笑声开启了索鲁赫在广场上的流行。饱经岁月的洗涤,他成为广场上中最著名的说书人,摩洛哥的人们会从最遥远的角落来到广场,就是为了听他讲故事,他讲述的故事中或许有你闻所未闻的远古希腊神话。索鲁赫辞世时留下了一个学徒,现在已是一个很老的人,也是广场上能找到的最后几个说书的老人之一。
“失去一个说书人对人类来说比200本畅销书的死亡要严重得多。”戈伊蒂索洛把话说得很重,由此可见他是爱之深,忧之切。
杰马艾夫纳广场获选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曾使戈伊蒂索洛十分兴奋,他写道:“这使我们敏锐地意识到这是地球上唯一一个音乐家、说书人、舞蹈家、杂耍演员和吟游诗人以新的方式表演的地方。一年中的每一天都在大批人群面前展示。广场为我们提供了一种持续的奇观,其中演员和观众之间的区别逐渐消失:如果他愿意,每个人都可以成为其中之一。我们生活在一个信息技术巨头通过将我们的生活封闭在远程控制的隐私黑暗中,而使我们的生活同质化和贫乏的世界中。杰马艾夫纳广场提供的恰恰相反:一个公共空间,通过诗人和说书人创造的幽默、宽容和多样性的混合来促进社会生活。”
对于戈伊蒂索洛来说,存在着两个世界,而且它们之间的差距正变得越来越大。马拉喀什是他热爱的世界——广场上的说书人和各种民间艺人,这个诞生于极端贫困的世界,让他既烦恼又着迷。还有一个是他居住的欧洲发达国家,那里是自由的,儿童不再死于可治愈的疾病,但人际关系却被削弱、被疏离。他的后半生一直在为保持前一个世界而努力。他觉得自己正在为一个不可能的世界而奋斗。“杰马艾夫纳广场提供的恰恰相反:一个公共空间,通过诗人和说书人创造的幽默、宽容和多样性的混合来促进社会生活。”
戈伊蒂索洛回忆道:“我第一次接触口头传统是在马拉喀什的杰马艾夫纳广场,这让我开始思考书面文学的特殊性质,以及这两种表达方式之间的差异。在口头交流中,说话者可以随时参考上下文:换句话说,可以参考听众熟悉的特定情况。在书面文学中,除了前者所写的文本和同一语言社区的成员(通过出生或学习)之外,作者和读者没有任何共同点。口头文学在说话者和听众之间建立了良好的交流,他们都以相似甚至相同的方式体验世界。另外,阅读小说在叙述者和读者之间建立了交流;前者无法验证后者在阅读时是否具备足够的上下文知识来理解文本。”原来如此,他关注的与文学的传承有关,他关注的是口头传统与文学创作的关系。
作者或讲故事的人和细心的听众同时在场——为诗歌和叙事文本提供了一个新的维度,就像乔叟等作家的作品。戈伊蒂索洛在广场上最原始的口传文学中看见了前辈作家作品文体上的特点,他惊叹道:“使一条埋藏的线索将中世纪与二十世纪的先锋派文学联系起来。”
他所称道的15世纪英国作家乔叟创作的《坎特伯雷故事集》是英国印刷史上最早的用双韵诗体写成的故事书,记录了29名前往坎特伯雷的朝圣者晚上聚在酒店中讲的故事。朝圣者中有骑士、僧侣、侍从、商人、匠人、纺织匠、医生、地主、农夫、海员、家庭主妇等。这种典型的民间叙事方式可以追溯到14世纪的意大利作家薄伽丘的影响。薄伽丘的作品《十日谈》对于后世的文学创作影响深远。正如作者的序言中所说:“这本书里讲了一百个故事——或者是讲了一百个‘寓言’,一百篇‘醒世小说’,一百段‘野史’,你们怎么说都成。这些故事都是在瘟疫盛行的一段时间中,由一群有身份的士女——七位小姐、三位青年分十天讲述的。”1348年黑死病在欧洲第二次大流行时,这十名青年男女去一个乡村的别墅避难,为了打消寂寞的生活,他们聚在一起游玩歌唱,每人每天讲一则故事,十天讲了一百则故事,这十名青年中既有王公贵族、骑士僧侣,也有贩夫走卒、市井平民,阶级的不同也使得每个人讲的故事体现了社会的方方面面,这就是《十日谈》的主要内容。薄伽丘和乔叟的作品都具备民间口传文学的特点,也正是因为它们鲜活生动,活生生地扎根在民间和田野当中,所以充满了智慧和幽默,并且在口头传递中不断丰富。
当然在戈伊蒂索洛的年代,薄伽丘和乔叟的文学叙事方式已经淹没在更为丰富的文学表现形式中,可是在杰马艾夫纳广场上的见闻却让他仿如看见了现实生活和文学传统的连接,广场显出了不同寻常的意义。如同看到携带着先人信息的古董仍然以一种鲜活的方式在现实生活中存活,很显然他曾经为薄伽丘和乔叟的作品着迷,忽然又在现实生活中感受到遥远的历史场景,因之而兴奋不已。不过,毕竟这种广场上的文学交流方式产生的文本是粗糙的,没有经过作家精心的构思和文学想象的发挥。但是即便是稍显不够成熟的文学内容,也许正是它所具备的粗糙性引起了戈伊蒂索洛的极大兴趣。显然他在这里看见了文学的源头与现代生活的联系。
而戈伊蒂索洛最为关注的正是与文学密切相关的一个行业——说书人。回到20世纪7O年代,马拉喀什有大约二十名说书人;此外,摩洛哥的所有大城市,以及许多城镇也有讲故事的人。如今人们认为马拉喀什只剩下三四个说书人,整个国家可能只有不到八个,并且都是没有学徒的老人。
3
在同一个城市里,老城与新城相安无事,各自按照自己的性格成长发展。当然说到发展,新城如同年轻人,发展的激素更充分,发展的空间也更广阔。其实这里所谓的新城年纪也不轻了,起码也已经有了百年的历史。从老城进入新城,跨越的不仅仅是建筑格局和街道格局的迥异,更是可以感受到历史和时间的跨越、异族文化的跨越。可是如今它们却和谐地并肩立于城市的两端。
法国画家雅克·马若雷勒(Jacques Majorelle)来到马拉喀什的目的是养病,却没有在居所里静静地安养,反而开始了他在北非和西非的游览。雅克·马若雷勒初来摩洛哥的几年,外国人的旅游受到很多限制,他通过各种渠道才获得了官方的旅游授权,然后和妻子以及一名护卫在非洲多地进行了多次探险。所到之处他都会支起画架进行素描,记录下人们生活的情景。
他身后留下了一千多件作品,其中最引人注目的大多是非洲的景色。雅克·马若雷勒自称是“马拉喀什的画家”,他被壮丽的沙漠风景,被宫殿的建筑,被那些近乎原生态的山区生活和乡村习俗所吸引。在20世纪30年代,他在撒哈拉以南非洲的发现为他带来了审美和创作力的复兴。
我特地找来他的一些画作,在他画笔下,马拉喀什的红色陶土建筑是最常见的背景,红房子像一座座堡垒,高高的墙上开着一个个小孔样的四方窗口,沙漠的风从这里进入;撒哈拉沙漠也染上了红色,牛羊和骆驼组成了沙漠上亮丽的风景;贸易市场前面伸展着探向高空的棕榈树,树下密集的人群或是耕耘,或是交易、载歌载舞。画中的群像总是看不清面目,他把焦点聚集在他们身上披挂的长袍上,女性的有赤橙黄绿青蓝紫,男士的基本以白色为主。
有一幅画中看见了深蓝色的河流,或许被命名为“雅克·马若雷勒蓝”(Le Bleu Majorelle)的灵感就是画中的那一湾河流,深色却又明亮。马若雷勒后来就是用这种以他名字命名的蓝色,把他在花园中居住的建筑和陶瓷陶器涂成蓝色。据说这种蓝色是由撒哈拉沙漠植物提炼,价格非常昂贵。这是画家的一种创造,是属于他的色彩。他还创作了一幅宣传摩洛哥的旅游海报,除了蓝天,就是蓝色的海洋,前景是身披黑、白、红长袍的人和色彩丰富的水果。从这些画作中,我见证了一种说法,雅克·马若雷勒在非洲的土地上画出了他最值得称道的作品。1946年左右,在他的朋友、英国前首相温斯顿·丘吉尔的鼓励下,马若雷勒在伦敦举办了展览。
马拉喀什新城的核心地带是盖利兹(Gueliz)。这是1912年建立的法国区,当时摩洛哥政府与法国签署了一项保护协议。法国陆军将军兼殖民行政长官路利奥泰(Louis Hubert GonzalveLyautey)希望通过保护摩洛哥的文化传统和当地习俗来实现摩洛哥的现代化。这个区域发展迅速,建筑师们借鉴了巴黎的建筑艺术,结合摩洛哥的建筑传统。建筑物必须与老城区一样呈赭红色的基调,主干道的街道宽阔,种有大量树木,几乎每个环岛都有喷泉。如今那里是购物、办公和文化中心,随处可见高级宾馆、办公楼、咖啡店、博物馆。为了感受城市的氛围,我特地坐在街边的咖啡馆里喝了一壶薄荷叶茶。茶壶是银色的,壶壁布满花纹,盖子像一个宝塔。泡开的薄荷叶清翠欲滴,叶片上的经络条丝清晰。茶有薄荷的清香,又有淡淡的甜味。喝着茶看街景是旅途中十分惬意的事。
经过盖利兹,再往北走,进入了一个幽静雅致的别墅区,窄小幽静的街道上高高伸展的棕榈树,建筑都是赭红色的墙,马若雷勒花园就在那个区域。马若雷勒生前非常喜欢旅行,1910 年,他前往埃及和穆斯林世界,东方让他着迷。他在开罗定居了四年。这一地区的色彩、风俗和灯光激发了马若雷勒对非洲的热情。1924年他在马拉喀什购得了一片土地,从此这便成为他终生的项目,他称自己为“园艺家”和“艺术家”,他把对于东方和非洲的热爱通过这个花园的构建和浇灌体现出来,在这个美丽的花园中他建造了他的工作室。
4
花园在马若雷勒生命的后期已开始破败,因为购买植物和维持的花费使他入不敷出,再加上离婚使他经济上受到很大的损失,花园最后不得不对外开放。后来马若雷勒死于一场车祸后,这处房产变得一片混乱。来自巴黎的女装设计师伊夫·圣罗兰(Yves Saint-Laurent)和他的艺术家朋友皮埃尔·贝尔杰(Pierre Berge)购得了这个花园。他们对花园进行了修整,总体上保持了原来的风格。
很显然我所看见的花园中更多留下伊夫·圣罗兰打理的痕迹,现在每天来参观花园的游客络绎不绝。走进花园,扑面而来的是成片青翠欲滴的茂盛竹林。长方形的莲花池占据了花园重要的位置,因为它占地面积大,池水中的莲花开放着,鲜嫩的黄色花瓣簇拥着橘红的花蕊;绿叶上有一只乌龟在栖息,我特别钟情于那只小乌龟,乌龟盛产于亚洲各国,我好奇它的父辈是怎样远渡重洋从东方来到北非?莲花池两边有规则地排列着蓝色和黄色的陶土花盆。在纪录片中曾经看到圣罗兰曾经在这里散步。前半段的花园之旅弥漫着浓浓的东方色彩。当然所经之处走道边的园地里大片种植着非洲热带植物,各种形状的仙人掌、仙人球和热带植物争奇斗艳。通向建筑物的是棕榈树排成行的小道,建筑是绿瓦红房。有一栋马若雷勒居住的屋子被涂成了标志性的蓝色。黄色的窗棂是典型的摩洛哥花纹装饰,铺着深蓝和浅蓝的地砖上排列着鲜黄色和橘色的陶土花盆。啊,色彩都那么鲜艳,有些泛滥了,可是却很养眼。
圣罗兰的挚友贝尔杰记得:“当我们到达马拉喀什时,伊夫和我完全被那里的美丽和魔幻所吸引。我们没想到的是,我们会爱上一个神秘的小花园,花园以亨利·马蒂斯(Henri Matisse)的色彩绘成,隐蔽在竹林中,万籁俱寂,远离喧嚣和风吹。这就是马若雷勒花园。多年后,一个偶然的机会,我们得到了这颗宝石,并着手保存它。”
说起伊夫·圣罗兰的人生经历可谓千回万转曲折又精彩。他是一位来自阿尔及利亚的年轻人,21岁时就被任命为法国国际奢侈品牌迪奥(Dior)的艺术总监。经历了战争和商业诉讼,后来他和搭档皮埃尔·贝尔杰成立了自己的公司,启用YSL作为公司的标志。他们携手把YSL成功打造成一个时尚帝国,从此开始了改变世界女装潮流的划时代勇敢实践。圣罗兰为女性设计燕尾服、短上衣、宽松套装、休闲穿戴;推介女性穿西裤,他的许多女性服装设计为促进性别平等开创了一代新风,也因为这些服装惊世骇俗,曾经引发社会巨大争议。喇叭裤、套头毛衣、无袖汗衫、嬉皮装、长统靴、中性服装、透明装等等,都是他的创造发明。他也善于博采众长,促发灵感,他的服装设计中也吸收了来自摩洛哥、中国、日本和西班牙等文化的元素。不过战争的阴影缠绕了圣罗兰一辈子,他不断地挣扎在抑郁症和酗酒、嗑药折磨中。
或许作为一个时尚娇子,对于镁光灯下的热闹和喧嚣早已疲惫,甚至厌倦。离开了时装季节展销会,圣罗兰就想安静,马若雷勒花园成为他心灵和身体的港湾。他经常在巴黎参加完时装展后回到这座花园,这里属于他自己,没有任何人来打扰他。在一些历史照片中可以看见他身着摩洛哥长袍躺在花园里,或是和他的伴侣皮埃尔·贝尔杰在花园里散步。离开了时尚界喧闹的秀场,回到可以听见风声、鸟叫和树叶唰唰声的宁静院子里,他找到了许多灵感。“多年来,花园都是我源源不断的设计灵感的源泉,我常常梦到那些独一无二的色彩。”作为公认的“色彩大师”,伊夫·圣罗兰把这种发现完全归功于马若雷勒花园。
而在这所谓的独一无二的色彩中,最吸引他的就是“马若雷勒蓝”。那是一种比蓝天更光亮、比海洋更深沉的色彩。在阳光下它带给你舒适的愉悦,在阴影里它并不消沉。对于色彩孜孜以求的圣罗兰从遍布花园独有的“马若雷勒蓝”里不仅获得了精神的放松和愉悦,也获得了创作的灵感。他也把这种色彩应用到了YSL的各种产品中,比如经典的18号蓝色指甲油。
在花园的一隅,我看见一块方正的基石上立着一块粗壮的圆柱石头。下面镌刻着圣罗兰和他的终生好友、事业伙伴也是曾经的伴侣皮埃尔·贝尔杰的名字。他们死后选择一同葬于马若雷勒花园中。
历史上有许多西方作家在摩洛哥旅游、居住,在这片异域色彩浓重的土地上获得灵感,创作出让自己骄傲,又获得世界公认的杰作。美国剧作家田纳西·威廉姆斯在摩洛哥度假时创作了荣获普利策戏剧奖的话剧《热铁皮屋顶上的猫》。摩洛哥曾是他最乌托邦的空间,那里令他充满想象力。曾经创作出反乌托邦经典著作《1984》和《动物农场》的英国作家乔治·奥威尔早年在那里居住,写了小说《上来呼吸空气》。第一位获得普利策奖的女作家、长篇小说《纯真年代》的作者、美国作家伊迪丝·沃顿,在她的著作《在摩洛哥》中写道:“摩洛哥太好奇、太美丽,风景和建筑太丰富,最重要的是太新奇。访问摩洛哥仍然就像翻动一些带有插图的波斯手稿,上面绣满了明亮的形状和微妙的线条。”……美国作家马克·吐温(Mark Twain)在他的游记《无辜者在国外》中描述摩洛哥的城市丹吉尔时,也特别强调那里的异域性,“没有任何东西能让我们想起阳光下的任何其他人或任何其他土地”,这种别处所不曾见到过的“异域风情”使他着迷。
“异域风情”通常是指外国或者国土之外的地域风光与风土人情。人为什么喜欢异域风情?为什么被那种你觉得陌生的,从没见过的,看到以后不知道如何对付的东西吸引?尤其是艺术家们就是希望在自己的作品中创造出别具一格的气象,这种别具一格不仅与别人的作品不一样,而且与自己以往的作品也不同,这才是创新,才是创造,才是一种能使自己满意的成果。而很显然,沙漠边的这座古城中的许多元素,焕发了作家、艺术家们的想象力和创造力。
入夜后的杰马艾夫纳广场人头涌动,这样的景象在疫情后的年代实属不易,时光似乎洗去了过去三年人类对于疫情的创痛记忆,一切又回到了从前。最耀眼的是席地铺开的灯具摊贩,把每一盏灯里的蜡烛都点亮了,在黑暗中远处是灯光辉映下橘红色的清真寺高塔,空中飘散着烧烤摊上的烟雾,前中后景形成了立体感十足的大市场氛围。走着走着肩上如何降落了一只孔雀,原来是养鸟的人来兜售生意。与开屏的孔雀合影一张,自然要给钱了,十迪拉姆约合一美元。商贩们热情地兜售着自己的商品和食物,自然给我们一些压力,生怕他们纠缠不放。不过好在没有发生令人反感的事。我体会到当地人善于讨价还价,但是说好一个价后,他不会欺骗你,而是按照说好的去履行。不仅是小贩们如此,出租车司机也是如此。每一次都需要讲价,没有严格的规范。
21世纪以来,杰马艾夫纳广场也参与了国际电影节和音乐节的活动。届时广场西南部会搭起一个舞台和巨大的屏幕播放电影,举行明星与观众见面会。而在音乐节举行时,在国王的支持下,各种音乐会在舞台上唱响。音乐声和歌手的洪亮嗓音开始笼罩整个空间。
在广场上得到的感觉是毛茸茸生活的原生态。当然作为一个异域的游客,中间隔着语言交流的屏障,我觉得那里更多的是无序和些许的嘈杂,但是依然被那里弥漫着的属于异域的文化氛围吸引。可是我作为游客,却总是希望在原生态的古朴之后,能够感受一种浓缩过提炼过的美和享受吧,了解一个陌生的文化总离不开衣食住行。就在离广场不远的小巷中藏着一家历史悠久的老饭店,历史可追溯至17世纪,房间中的装饰流光溢彩,体现了伊斯兰艺术的高标准。老饭店的环境是一个浓缩的摩洛哥建筑文化的缩影,它的拱门,地上的瓷砖,墙上贴的彩色马赛克,我都曾经在豪华的清真寺以及各种各样的美丽建筑里见过。我面前不远处的喷泉上铺满了鲜红欲滴的花瓣,上面有一盏巨大的吊灯垂下来。
英国前首相温斯顿·丘吉尔曾经是这家老饭店的座上宾。美国电影导演希区柯克不仅被那里的美食陶醉,而且还将餐厅作为他的电影《擒凶记》的外景地之一,在弥漫着浓郁北非风情的餐厅里拍摄了几场戏。在这家老饭店晚餐,不仅可以享受美食,同时还可以近距离观赏摩洛哥特色的歌舞表演。一位男性舞者手里敲着响板,甩动帽子上的花翎,响板的声音据说是模仿手铐脚镣的声音。祖先以前被抓来做奴隶,音乐是对自由的赞美和向往。最别具一格的是舞蹈表演,肚皮舞者披挂着一双荧光灯打亮的蝴蝶翅膀翩然而至,舞姿婀娜。
摩洛哥的招牌菜是塔吉锅,牛羊肉放在一个土红色的陶制锅中,加上蜜枣、花生、果仁或是干柠檬和香草一起炖。我点的羊肉煲口感极佳,羊肉鲜嫩,完全没有膻味,蜜枣等的甜味完全渗进了肉里面,甘甜可口。在饮食系列中,摩洛哥的餐饮最接近东方的美食,与我在美国吃惯的西餐完全不同,完全征服了我的味蕾。
异域风情有时候对于人的影响是很难说明白的,作家与他的部落,画家与蓝色,女装设计师与梦中的色彩,这种联系是怎样建立的?似乎很难用科学实证的方法加以分析证明,捉摸不透,可是却看见了因,看见了果,只是因果之间触摸不到一条清晰有形的连接线。曾经强烈打动马克·吐温的异域的特质,就是我所寻找的谜底,这也是马拉喀什留给我最深的印象。
责编:胡破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