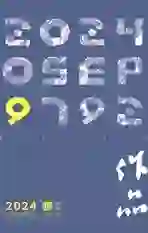不(短篇小说)
2024-09-30王清海
1
一九四〇年,我为寻找一把叫“不”的古剑来到一座高山。山上古树参天,密林中阳光躲躲闪闪,白天断断续续,我在其中失了方向,团团乱转。就在焦急万分的时候,一只小花鹿擦身而过,它与我躬身齐高,黑白分明的眼睛望了我一眼,似有话要说。
我欣喜万分,跟着它奔跑。林中草木葳蕤,深一脚浅一脚跌跌撞撞,它奔跑了一阵后在林中绝望地看着我哀啼了一阵,慌乱转身折返,似是迷了路。
它是属于森林的,怎么会迷路?究竟是迷路后才是该走的路,还是我一直都走错了路?
我闭上眼睛沉思了一阵,暗笑自己懦弱后,便放弃了紧跟小鹿,沿着心中的方向继续走。我心中的方向,就是对古剑的感觉,它就藏在这座深山某一处长满青苔的石缝中。离它越近,我的心就会跳动得越快,我根据心跳的快慢判断着古剑的位置。
几千年来,不停地有剑客寻找它,它存在,但它找不到。我从觉得会是一场徒劳开始,到现在心头乱撞,每一次激烈的撞击都告诉我,寻找“不”是我的宿命,更也许,是“不”的宿命。
找与被找之间,困着我的命。
就在我心跳越来越激烈的时候,我走出了森林,看到一条细小如泉水缓淌的瀑布,瀑布下面竟然站着我的叔父。我问他为什么在这里出现。他说山下土匪横行,很多人受伤了,没有药医治,他是来桐山采药的。我说,叔父,我离家多年才走到这里,是什么药让你走这么远?他说,为武啊,这是桐山,离咱们家不足百里。你应该是顺着山走的,山连着山,山叠着山,你一路又走了回来。
我又走了回来?我顺着叔父的手所指,山形山势,颇为眼熟。没想到少年离家寻“不”,兜兜转转,却回到了原处。
叔父说,我年轻时候来过这里,密林尽头瀑布之下,有大片的金不换,是治疗枪伤刀伤的良药。
我低头,青翠一片,与别处的茂盛相比略显稀薄,正是大片伤科良药金不换。
叔父叹了口气,为武,村里来了很多土匪,祠堂拆了,房子烧了,混战中死了很多人。
瀑布水声不大,我听得到叔父和我急促的呼吸声,呼吸声压住了心跳声,指引我寻找古剑的心跳在这里平稳了。
战祸横起,我也是听到了一些的。我一直对自己说,这些都跟我没关系,我是为“不”而生。每念及此,心都会跳动着指引我古剑的方向,这么些年,从来没有像此刻这样平稳。在呼吸声之下,在山林中寂静,我寻觅不到我要去的方向。
叔父近前来,扇了我两个耳光。
我睁开眼,不解地看着叔父。他说,顾为武,你活着是为了什么?我说,当一名剑客。他说,你为什么要当剑客?除暴安良行侠仗义,我说的可对?我说,对。他说,你连自己的家人都保护不了,找到稀世名剑又有何用?我说,是,没用,可我觉得它已近在咫尺。他说,马上就能拿到吗?我说,不知道。他说,多久能拿到?我说,可能是马上,也可能是三五年,也可能是永远都拿不到。他说,你家人能等得起吗?他们是被土匪杀了还是自己逃到哪里了,他们是在苦苦地等你救,或者盼望能再与你相见,你都不想吗?那你是剑客吗?我说,不是。他说,跟我一起走吧。
我对着莽苍的密林跪下,不,我一定会再回来,我一定会找到你的。密林中隐若有声,我抬眼望去,满眼茂密,但在我眼中是空茫茫一片。我舍弃了多年的追寻,觉得自己在世上忽然不重要了,无足轻重得开始不安,连走动都怕路会嫌弃。
我跟叔父离开瀑布,心跳竟又开始,指引的方向仍是瀑布。我无法回头,我还有重要的事情要做。我跟着叔父走了一座山又走了一座山,走到山脚的时候,面前已是归乡的小路,我的心便只有隐隐的痛。
我收起一直披在身上的槲叶斗篷,摘下斗笠,换上和叔父差不多的青布短褂。叔父叮嘱我一定要藏起常年习武带来的虎气,要蔫头蔫脑,这样能避免引起土匪的注意。
我没有退缩过。我的心也没有再为了那把“不”跳动过。
但我忘了“不”。
我被土匪抓住,被土匪栽进了土里,上身露出大半截,我还能说话。他们叫我投降,多么可笑,我就大声地笑,我的下半身都被栽进土里了,像一棵长势旺盛的庄稼。土匪牵来牛,拉着犁,他们也笑,声音更大,他们大声吆喝牛,牛使劲向前拱,雪亮的犁铧从我身上劈过,我的身体四分五裂。他们的笑声更大,更起劲地吆喝牛,来回犁了几次,又拉来了耙,把我彻底与泥土混在了一起。
在我被犁掉脑袋的时候,我看到了“不”,在深山的石缝中,褪去满身绿锈,长鸣一声,在山中盘旋飞起,树见树断,石见石开,风见风躲,云见云裂。我与它一起飞,腾空而去。
二〇一六年,我的孙子大学教授顾源在五十多岁的时候,开始完成少年时的梦想,写下爷爷顾为武的故事。他总认为顾为武的一生,是一段传奇,有着其他人无法拥有的壮丽。他从京城回到老家,一点一点搜寻顾为武当年的蛛丝马迹。他找到了北水县地方志,看到无名勇士潜入匪寨,被俘,犁毙的记载。
他问,为什么没有名字?地方志办公室的人说,我们也在等,等有了名字,能确定有这件事情,如果再久远些,怕这些没有名字的事情,就会成为不存在的事情。他说,我知道是谁。接待他的说,为什么你知道他是谁?
他讲了从奶奶口中听说的故事。不过他也深知,当事人俱已不在,不拿出证据,无法让人信服。
他想到了那把古剑,家里人反复提到过,爷爷是个剑客,年轻时就在大山深处寻剑,他一定找到了那把古剑,用它来保家卫国。在他死后,古剑下落不明,再没有任何记载或者传闻,对于一把稀世名剑,明显不正常。
他带着几个学生,凭着一些断断续续的口述或者记述,找到了我被犁毙的地方。看着面前的一片茂盛的槲叶树,他脱口而出,我爷爷一定埋在这里?学生问,为什么?他说,你看这片树,长得比别处都更粗壮。
他们在树下挖寻了很多天,他们的仔细,不亚于我当年寻找“不”。不过“不”对于他们来说,只是一把古剑,和很多古剑一样的古剑。不是“不”对于我的独一无二。
他们挖出了一些残碎的骨头,再也没有别的发现,流泪祭拜后,准备把我埋葬在原地。在给我挖造坟墓的时候,他们在泥土中发现了一把锈迹斑斑的断剑,只有剑柄部分,握在手上,感觉轻盈趁手。他们又花了一个月的时间,搜寻了方圆三里,未曾找到剩余部分。
顾源将剑柄小心清洗干净,在放大镜下仔细观看,还是没有找到任何可以证明剑主人身份的东西。我潜入匪寨带的是短刀,那柄短刀在近身肉搏时刀刀见红。
他将断剑带回地方志办,大家都很高兴,虽无法确定,但也无法否定。毕竟在传说中我是剑客,在没有找到证据的时候,他们已经相信了顾源,虽然我在他们搜寻的各种史实中从来没有出现过。他们向顾源表示了感谢,并迅速重新修订了地方史志,将无名勇士换成了我的名字。
顾源开始写顾为武的故事:
我爷爷历尽艰辛,终在深山中找到了古剑,视若至宝,日日带在身边,谁都不能碰触。在见到我奶奶的时候,却解下长剑,躬身递出,娘子,红粉赠佳人宝剑赠英雄,至此乱世,我身无长物,拿不出像样的聘礼,愿将此古剑为聘,还望收下。
我奶本也是习武人家出身,村子被毁,她的家人全部遇难,她随村人躲进深山,他们在与土匪的战斗中相遇。我爷爷看上了我奶奶的如花美貌,我奶奶看上了我爷爷的嫉恶如仇,她高兴地收下长剑,拿出贴身的花手帕,这是奶奶逃跑时唯一带出的贴身物件,上面有她娘亲手绣的鸳鸯,她每每看到上面的密密针脚,就像看到了娘的手在上面挑针引线,娘的心盼她鸳鸯交颈。
我奶将手帕送给我爷爷,我爷爷贴身收好。他们藏在深山洞中,山林风月便是媒证,清泉野果便是喜宴,藨草为席,槲叶为被,我爷爷和我奶奶就成了夫妻。
他们夺回村子的第一仗,就在北水河边。他们嘴里噙一根芦管,从上游入水,慢慢漂浮到匪营,营地建有炮台,探照灯将河面照得亮如白昼,还有几个土匪在水里洗澡,洗的时候,嘴里轻松哼着歌曲。洗澡的人怎么也想不到水里游来的不是鱼,而是刀子。
我爷爷奶奶换上了洗澡人的衣服,轻松地靠近营地,攻占炮台,掉转炮口,隆隆炮声,土匪死伤无数。
此后几个月,我爷爷发现我奶奶有了身孕,便让她躲回山中,自己继续寻找自己的家人。
我从我奶奶那里听来的故事,到此处终止了。我奶奶在山中听到爷爷被犁毙时,我父亲已经满周岁。
我这一生,有幸完成了父亲的心愿,亲手掩埋了爷爷,虽然我不知道是不是他;找到了一把剑,虽然我不确定是不是他的剑。
顾源所说基本属实,我跟刘三姑娘确实是那样相遇相爱,只不过我没有送剑,我见到她时,除了遮体的衣服,就只有槲叶斗篷。我将斗篷送给她,她很高兴。斗篷不能保存太长时间,想必早已被她在不忍中丢弃。我在她心中,应该是个完美的剑客,剑客是要佩剑的。顾源所说的以剑为聘,当是他的杜撰。很多事情到最后总是要被添油加醋的,只要基本的事实没变,就无伤大雅。
我们在一起的那段日子,我记得只跟她提过一次剑。她问我,在山里找剑的日子辛苦吗?我说不辛苦,因为那是我的命。她说那现在辛苦吗?我说不辛苦,因为现在有你,你也是我的命。她就笑了,说,你为什么一定要找那把剑?我说,家里有本古书——《沉潭录》,是元朝人写的,跟着顾家的剑谱一起传下来,里面记载了这把剑,我们家很多人都找过,有的找三年,有的找几天。她说,村子遇袭太突然,东西都没有带出来,剑谱估计在大火中化成灰了。我说,在我脑子里,我会往下传。
我当然没来得及传,这些东西就永远随着我封印在这片土地里。
我相信刘三姑娘会将我的话告诉他,不知道他为何在顾为武的故事里,把这个重要的情节给改掉了。
直到他写完故事,开始一个人进山,从我跟刘三姑娘结婚的盘山开始找,沿着盘山走进桐山,我才明白,他是不想让别人知道世上有这把剑,他还是要找这把剑。
他知道那把断剑不会是传说中的古剑,一把名剑,必然是用了上好的材料,经过了大匠的冶炼,占尽了天时地利人和,斩断了无数兵刃,才会引得一代又一代人寻找,怎会轻易断在那里?
他在山中以杖为马,走走停停,风餐露宿,竟然也转到了我遇见叔父的瀑布。多年不见,瀑布依旧,时间好像静止。顾源对着瀑布仔细打量,并没有停下,转头向别处走去。一只小花鹿从他身边跑过,他跟着跑了几步,然后还是按照自己的方向,一高一低地离开了那里。
他离开桐山后,又寻找了几座山,有些是我当年找过的,有些是我未曾去过的。他找了几座山后,觉得漫无目的又毫无希望,便想起了我当年的说过的那本书——《沉潭录》。
那本书里有这样一段记载:剑成鬼哭猿啸,出剑天地无声,冶惧,遂藏剑于山,名曰“不”,非不可不出,不出。
这本书的作者与顾家祖上关系甚好,多年颠沛流离之后,《沉潭录》也只有顾家一直留存。书名《沉潭录》,书中多为写山水花鸟的诗,不知为何起名《沉潭录》?“不”剑藏于深山,最初的顾家人,专深山古潭,自我认为自己与古剑有心灵感应后,便凭着心跳,独自寻找,才慢慢怀疑,它可能是藏在深山石缝中,不一定是沉潭。
2
二〇一六年,我独自到深山寻找“不”,毫无线索又充满盼望。奶奶不想我爸承袭这样的使命,她甚至觉得顾家的寻找是一种惯性,习惯了一代又一代人找下去。她要在我爸那里终止寻找。
从小到大,我的梦里从没有出现过古剑。在我生长的年代,剑在日常生活里早成了舞蹈道具、墙上的装饰。
我小时候身体不太好,奶奶曾教我练过一套拳法,让我强身健体。奶奶教的时候说过,可惜了顾家的功夫。真正激起我寻找“不”的渴望,是在二〇一五年买房子时,我看中了一套房子,签合同前房产销售一团和气,签了合同后,他脸色骤变,除了不停催要尾款,再看不到笑脸。这样的坑,很多人经历过,五花八门,我就不再一一详述了。
让我生气的是,我随口说了几句合同的不是,一群保安把我抬起扔到大街上,我是教授啊,就这样让斯文扫地?想起祖传的功夫,可是我虽然姓顾,祖上传下的东西,我一点也没有。
我要找到“不”,这是顾家世代寻找的东西。
我正在犯愁的时候,想起了《沉潭录》。顾家相传的应该不是孤本,它的作者,也不会穷尽一生,就只写了一本书。我在全国各地的图书馆里几经搜索,在一本介绍元代诗人的书里,搜到了《沉潭录》的名字,作者遗山先生,曾在盘山一带任过县令。书中还介绍,一九九六年,有人曾在桐山瀑布附近发现一块有字迹的石头,上面有首模糊的诗,经专家考证,作者可能是遗山先生,风蚀雨磨,诗已不能读全,实在辨认不出的字,书中用了□代替:山势巍峨□□图,□□□□影相辉。老僧托钵回来后,独对斜阳补衲衣。
瀑布我是去过的,附近并没有寺庙,怎会有老僧?虽说万物易毁,但是山里的寺庙,经常存在几百几千年,再不济,也会有遗迹,再再不济,也会有传说,但我翻遍北水县志和桐山附近所有县志,皆没有显示桐山瀑布那里有寺庙。所以我就认为,这首诗就算是遗山先生的诗,也是在别处所写。
我的大学同学周敦雨在报社工作,平时在网络上写小说赚外快。我在售房部受辱后,首先想到了周敦雨,他连发三篇报道,引起群情共愤。最后告诉我,地产老板赞助了报社一年的广告。
我要寻古剑的事周敦雨知道,我找到古诗也告诉了他。他说,这首诗莫名其妙出现在荒山野岭,里面定有文章。我说,愿闻其详。他说,前面两句残缺不全,有可能是指桐山,也可能是另外的山,但它出现在桐山瀑布,我们不妨这样认为,遗山先生就是写的桐山。后面两句有寺庙就有僧人,但是僧人一定要住在庙里吗?会不会附近有山洞,僧人住在山洞里?当然,僧人不可能以山洞为家,那这个老僧就是虚写,就是要告诉后人一个位置,斜阳在西,对着斜阳就在东,对着斜阳的地方,就是藏剑的地方,要么是有山洞,要么洞就藏在瀑布下面的潭中。
我说,老同学,你这脑回路,不写网络小说赚钱真是太亏了,你还是找对了职业。他笑,说,顾家祖上,一直没遇到现代这么发达的科技,要查找一个线索,轻而易举,该我们这一代人终结古剑之谜。他还说愿与我一起去桐山瀑布寻找古剑,找到了是我的,他不会要,也不会提出分,他对那剑毫无兴趣,他只对找剑的过程感兴趣。
我是明白的,只要找到剑,或者找到剑的线索,都是他的新闻题材或者小说素材。
一九四〇年,顾为武止步在桐山瀑布,“不”离他,也许一九四〇近在咫尺。
周敦雨分析到这里,声音颤抖,脸色发红,好像不是他在分享我的喜悦,而是我在分享他的喜悦。我当时注意到了这一细节,只是觉得有点激动,好朋友嘛,难得他把我的事情当成自己的事情。等到了桐山瀑布,在幽深的潭边,毫无有剑的迹象,我几次说要离开,他都坚持要寻找的时候,我发现,他对“不”是有执念的。
我说,我爷爷在深山之中寻找多年,毫不犹豫地转身离开,我们也都有比寻找古剑更重要的事,没必要纠结在这潭边。他说,顾源,种种迹象表明,剑就在这潭里,为什么要放弃?绝对不能放弃。我说,这世上,又有什么事是绝对不能放弃的?古剑之所以多年不出,或者因为它本就不属于人间,它有它的归处,我们也有我们的人生,回去吧。他说,可是我们已经快要发现了,补衲衣是什么意思?我现在才体会到,就是人生的残缺不全,找到剑就能补上。我们就活短短几十年,古剑已经存在了成百上千年,我们马上就会死去,可是剑会继续活着,如果我们找到了,我们的生命就在剑上得到了延续,任何一个看到古剑的人,都会想到我们,不被世人遗忘,我们就没有死,这也是一种永恒吧。我说,我们是我们,剑是剑,我们有我们的生存,剑也有剑的归宿,两个是不能合在一起说的。他说,你爷爷的理想是当剑客,不就是想让人和剑合在一起?如果不是为了剑,你又怎么会反复提到你爷爷?你提到了你爷爷,为什么不能再继续寻找剑呢?我生气了,说,这是我家的事,跟你又有什么关系呢?他也生气了,说,剑是天下人的,虽然我承诺找到了是你的,可我是天下人的一分子,我有责任和义务让它重现人间。我说,我爷爷是能在剑前止步的,我们也能。他说,我6f8ed9aa3f18057aac738cd275f135989c506592f0da13eccfaf4850af93ce4e不能,因为我没有找到能让我止步的理由。
周敦雨给我的印象,一直都是成功者。成功者面对一些诱惑,更有拒绝的条件。可是没想到,他竟然将自己困在潭边,不想离开。我又陪了他几日,终于决定自己离开,我放弃了寻找,我宁愿认为在顾为武牺牲地发现的断剑就是“不”。“不”是剑,哪把剑都可以叫“不”。就像顾为武死去了,并不妨碍有人继续叫顾为武。
我也不再翻找资料,我宁愿我自己从来不知道这件事情。
三个月后的一天,新闻报道,桐山瀑布水潭里漂出一具男尸。根据现场遗留的一些物证,警察找到了我。周敦雨的家人做证,我是跟他们通过电话,让他们劝回周敦雨,而他们苦劝不回。周敦雨最终决定入潭寻找,已经入潭多次,终有一次没上来。
这让我深深自责,也许我天长日久的劝阻,对他是能够起到作用的。自责并不能改变事实,我在家中静坐多日,开始写下虚构的小说,希望能完成我的好友周敦雨的未竟之志。
虽然我不确定这是不是他的志向。
3
“不”是我计划铸的最后一把剑。铸完这把剑后,我打算去当官。
当官以后当然还可以铸剑,能找来更好的材料和地点,有更多的人为我忙碌。我还是打算在当官前铸最后一把剑。因为我觉得入仕以后,任何一把剑里都会铸进名利,我不想把名利带进我挚爱的剑里。
我在桐山水边建了铁炉,搭了草庐,雇了数十个壮劳力拉风箱,伐槲树为燃,开始铸剑。之所以选在桐山,是因为铸剑用的铁石在桐山。它属于这里,就该在这里冶炼。剑铸成后准备送给我好友顾成铎,他是辞官归隐的武将,早已看破红尘,“不”送给他,可以显示他的高风亮节,也让他凭借老关系为我在朝中搭条路,让我做个小地方官。
我家祖上以冶剑为生,为无数名人铸了无数名剑,偏就没有人当官,以至于一直默默无闻。十八岁始,我给自己起了名号,遗山先生,意思是遗落深山无人问津。绝非附庸风雅,我不仅会铸剑,琴棋书画样样精通。当然,我也知道,做官要的是谋略。
顾成铎到深山里来看我,我拿出未完成的诗集《沉潭录》请他雅校,他坐在乱石之上,独对斜阳,聚精会神地读。当然,我也知道,他是武将,这些东西他看不懂。但他还是答应为我谋个差事,最好就在附近,这样我们可以多些交往。
我欣然答应。对于我来说,去哪里都行,只要摆脱祖辈的命运。
顾成铎知道“不”是要送给他的,很上心,隔段时间就会进山探看。他围着炉子打转,用慈爱的目光注视。
桐山的这块铁石异常坚硬,难以熔化,我在山中苦炼了七七四十九天,打开看炉中铁石,只是浑身通红,并没有熔化的迹象。这让我坚信会铸出一把旷古名剑。我继续伐木烧燃,又烧了三七二十一天,仍只熔少许。
在铸剑这行里一直有个传说,剑是有灵性的,它不愿意面世时,铁石之类便迟迟不能熔化,或者在剑模中迟迟不肯凝结。在这种时候,有人投入草木,有人投入牲畜,甚至有人自投入炉,为祭为引,才能铸出神剑。
我家几代人铸剑,从没遇到过这种事,便以为传说只是传说。
我寻了许多斩龙草,传说中此草可向铁石传达冶剑师的祈愿。青枝绿叶,投入炉中,炉火熊熊,斩龙草瞬间消失,铁石依然如故。又试了多种植物,依然如故。对仕途的向往,我自然不肯自投入炉,我想到了动物。在铸剑之时,常听后山有呦呦鹿鸣,火越旺,鸣声越大。
面对令我束手无策的铁石,我越发相信,这鹿鸣声就是给我的指引。我就想捕捉一头投入炉中一试。我雇的几个人早厌烦了山中的劳作,只是铸剑不成,他们脱身不得,一听祭鹿或者可行,便去后山,捕得一头鹿来。
是一头小鹿,花白小点,站在我面前,宛如山野中杂开的小花。我伸出手去,它便伸过嘴来,湿软的舌头舔着我在炉火前烤得干裂的手,如同甘霖洒在久旱的土地。
我是知道的,即使投它进去,也只是试一试,未见得铁石就会熔化。可是它的生命,就会消散在炉中。
对着瀑布的水帘沉思了很久,我还是让人把它放了。
熄灭炉火,我在《沉潭录》中乱写了“不”出世时的壮观景象,将祖传的宝剑紫绿和完成的《沉潭录》一起送给顾成铎。我出任县令后,他在山中与好友比剑,不经意间砍断了好友的一把好剑,好友弃剑于槲树之下,甚为不悦。顾成铎就将紫绿送给了他的好朋友,大笑说,一剑易得,一友难求。
两人笑毕,携手下山。身后桐山,风轻云淡。
责编:李京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