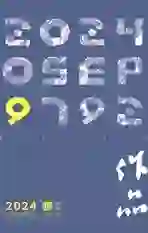世界上最孤独的鲸和一个听觉52赫兹的男人(短篇小说)
2024-09-30徐惠志
在自行车诗社三十周年纪念活动前夕,非亚先生发信息来告诉我,需要我们用方言去读一首自己喜欢的诗,可以是自己的诗,也可以是别人的作品。用原生态的方言,记录一首诗在这个世界上的声音,届时将会在活动现场循环播放。这个想法不知是谁最先提出的。诗社在一次地下摇滚现场用方言朗读过张弓长的诗《一个手里有枪的人应保持谦逊》,观众在台下发出雷鸣般的喝彩。也许是受到那次相当成功的朗读启发吧,我对这个提议十分赞成,并挑好了自己的一首作品。很早的时候,我就发现,我的句子里总会有一种童年期的粤语发音不自觉地冒出,它和普通话有着完全不同的质感,在同一首诗里互动催化,最后变成被写下的样子。我记得,在求学阶段,我和一些同学就特别喜欢用粤语背诵古诗,居然音节铿锵,韵律优美,无不合乎自然。然而,考虑到我的粤语方言有很多朋友也会,比如非亚先生,因此,我决定用闽南话来读诗。由于社会变动,人口迁徙,我生活过的地方杂居着不同乡音的人群,甚至一条河流的两岸就有截然不同的语言,就像南壮北壮发音有差异。闽南话也有许多差别,这是一个福建女人告诉我的。过去,我可以熟练地切换几种方言交谈,骂人,表达日常生活中的喜悦和愤怒,但是,我不得不承认一点,距离我上一次开口说闽南话,已经过去十四年。我的听觉没有问题,但喉咙已经无法正常运转,就像记得旋律却忘了歌词。这让我很痛苦,我把诗发给懂闽南语的朋友读一遍,录下来供我重新练习。后来我们在现场听到了普通话、粤语、壮语、桂柳话、闽南话,还有英语和法语朗读的诗歌。不得不说,这是一次美妙声音的诗歌旅程。但我今年夏天出差广州,对一个朋友说起这件事的时候,他表示赞同,之后却告诉我,第二天可以带我去体验一些更有意思的声音。我当时丝毫没有意识到,“更有意思”的意思竟然致使我回忆起诸多往事,也陷入了一种情绪中难以自拔。
广州之行返程前一天,我的同学陈超勇叫上两个生意伙伴在宝业路的夜宵街作陪。其中一位名字叫作乌兰,是个满洲里人,但只会说几句满语;入乡随俗,能说不算流利的广州话。只是他的反应总是慢半拍,我的意思是说,我们说话之后,他似乎要在心里翻译一遍,才能继续我们的交谈。就在我播放我们的方言读诗后,他奇怪地请我现场用闽南语读一遍。正是在此之后,他提议第二天跟他去看一个展览。陈超勇第二天没有空,所以我们两人结伴而行。
第二天一早我们驱车去了那个地方,乌兰穿了件蓝色的衬衣。车在一个楼盘销售部旁的白色建筑前停住。我以为是美术展览,但乌兰强调说,“这是个声音展览。”
我从未听说声音还可以展出,但我不动声色。乌兰有礼貌地笑了一下,大概他看出了我故作矜持。也许因为疫情期间,来看展览,哦不,来听展览的人不多。展厅空间不大,布置简约,有一些类似乐谱的线条,以及不同颜色组成的弧线,就像乐曲被刻录成线条,转化在磁带或者唱盘上。后来我发现,这些不同的颜色表示了声音的情绪。每个人进入展厅空间以后,都不自觉地放低了声音。而所有从各个地方征集到的声音载体,被存放在同样的格子里,也许暗示所有的声音都是平等的。唯一的差别是,格子疏密不一。于我而言,声音展既熟悉又无比陌生。
整个展览被分成人文与自然两类。人文板块被自然板块呈环形包围之势。另外有几扇独立的门,门后有不同的展厅。每一个声音会有或长或短的文字介绍,也有的标签上空无一字,似乎在等待定义和记录。但每一个被展出的声音都标明了时间和经纬度,仿佛是一个独立的宇宙。我问乌兰,这里有没有你的作品。他有一丝不安在脸上掠过,没有说话。他告诉我,想听什么,就登录扫码,旁边有Bose无线消噪耳机。“尽情地感受一段旅程吧。然后看看你听到了什么。”他说完,就闪身进了一个展厅,消失在一扇蓝色的门后面。
这里的声音五花八门,令人大开耳界。我从人文声音开始,这里居然有一段五分三十秒的声音,记录了俄罗斯袭击乌克兰首都基辅的片段。北京时间2022年2月24日凌晨4点,地处50°30’N,30°28’E,记录者是一名旅乌的留学生。对战争的感受,我只是停留在电影的画面上。飞机的螺旋桨,机翼划开空气,导弹发射,击穿建筑物,然后爆炸。短暂的沉默后,似乎是风在呼啸,接着才听到人的呼喊,哭泣,玻璃破碎,我有一种感觉,就像是一股强大的热风带来了这些声音。从消噪耳机里,甚至可以听见灰尘从空中缓缓降落,覆盖在每个人的肩上,当然,这只是我的想象,而我可能听到了(声音穿过了我),但却无法在相同的频率里被我听见。这一段声音以一声沉闷的枪声(我理解是枪声)戛然而止,就好像一把手枪从枪膛里射出子弹,而这颗子弹到现在还一直在飞行,它和一只愤怒的鸟一样,终生都在飞行,直到击中什么。展厅里开着冷气,我感觉更冷了,摸了摸后脑勺,才意识到自己出了一身冷汗。
还有一段声音,记录了一个锻压厂搬迁后爆破的声音。在文字的介绍里,可能是工厂的老员工,他写道:我在这间厂度过了青春年华,把最好的时光献给了厂。我已经下岗,退休,早已无法操纵机器。这一天,我和工友们一起回来,看着车间大门上方的早已褪色的红色标语,还有五角星,在升腾的烟尘中坍塌。我工作过的地方变成了一具没有生命的巨兽,重重地倒在了地上。这里将会建成住宅区,谁知道什么人会住进去,也许是我的邻居、工友,或者市政人员。锻压厂的爆破,把我心中的一大块空间抽掉了,就像戒烟时被掐掉的空白时间一样,我感觉到了一大片茫然的空白。
天刚亮时的菜市场;中午时分的公共食堂;夜深的街道,有车偶尔飞快地通过;飞机、动车、地铁、公交车车厢,电梯升降的声音;哈啰单车解锁,各种APP支付成功的语音提示;早晨的校园广播,教室里的读书声,眼保健操,第八套广播体操,操场上正在进行的一场球赛,球鞋在木地板上反复剧烈的摩擦,空旷的回音;建筑工地上正在运转的机械声;夜深人静时的医院走廊;一堆气球在婚礼后被几个顽皮的儿童踩爆;以及各种传统节气、婚丧嫁娶、庙会活动,烟花爆竹,吹拉弹唱,大相径庭的人类群居产生的各种情绪的声音。这让我想起童年在乡村时,扫墓的人在清明时节祭祀仪式行将结束时燃放的地炮,火药被塞进金属炮具,撞击充实,等亲人走开几步后,被点燃的地炮炸裂空气,山川土地都在摇晃,旧坟的草尖上的炮仗纸被震落,烟雾歪歪斜斜地随风散去,这时传回来远山的、密林的回声,就像是离开的人收到了纪念的信号,以微弱的音波回复信息。我似乎闻到了火药在我的鼻翼下一掠而过。
有一些特别的单元格,分别记录了不同的人的哭声(16种)、笑声(41种)。相比于人类面部表情,这些哭声和笑声,更具有想象的空间,特别是来自思达公医院产房里的一段婴儿的啼哭,那也许记录了一个诗人的诞生。至于历史上,自然也有许多哭的故事被记载,比如孟姜女哭长城,或者耶稣因为怜悯人而哭泣,又比如有人知道哭是没有用的,所以在葬礼上放声痛哭;还有那些被聘请来哭泣的职业人,真哭也好,假哭也罢,情绪的界限太微妙了,它们从来都不是以分秒计算的,脑电波的传递,形成了眼泪的实质。我无法判断它们(哭声和笑声)产生的原因,是一件坏事,还是好事。有些听起来像是“笑”,却被存放在“哭”那里,有些听起来明明是“哭”,却又被归置在“笑”中,就像八大山人的签名一样,我想,这就是八大的心情,八大签名艺术的声音版。我快速地回忆起我上一次笑是什么时候,我会心一笑。但距离上一次哭泣,似乎已经过去了很久。
还有一些令人遐想万千的呻吟声。这些必须年满十八岁才可以通过扫码申请的声音,记录了人类最为私密的感受。人体似乎变成了各种姿势的发声器官,我从未想过,原来人在欢愉之时还有如此之多的表达方式。也许它们可以作为一种春药,被研发到性功能障碍患者的疗程里面。我有点不好意思,幸而周围的人不多,我想我一定是面红耳赤的。但考虑到我已经35岁,竟然还不能直面自己的欲望,简直令人羞愧。
我悄悄留意了一下,听展的人不多。每人的脸上有不安,有喜悦,有沉思,有恐惧,也有悲伤,不同的面部表情取决于他们听到了什么,发现了什么。这的确是一场听觉的发现之旅。
令人感到奇怪的是,这些声音看不见,却一定程度上让我看见了。就像是在寂静中诞生了声音,声音形成画面再流动成一个故事或片段。类似于一块石头被雕琢出形体,一块泥土被烧制成器物。不同的是,我们需要用耳朵去触摸声音的质感、声音的内容。在我的耳朵植入了这么多声音以后,想要置身事外恐怕是不能的。我回忆起了许多发生在我过往生命里的各种各样的声音,这时我看见乌兰终于从一扇门后出现了,他的心情似乎大好,但又像是悲伤,就像是病刚好那种感觉。
他拍了拍我的肩膀,“伙计,怎么样,没有令你失望吧?”
我笑了,很感激他带我来听这场声音的展览。可是还有这么多我没有听过的声音。他说要离开一下,我又戴上消噪耳机,沉浸在自然的声音里。
一段河流在洪水期带着愤怒和决绝奔赴大海;
一片海域的浪花在凌晨时分一遍又一遍冲上沙滩;
夏天的雨,落在树林里,落在瓦片和青砖上,落在石板,落在铁皮,落在玻璃上,高低错落,这是一段记录某座南方古城的雨,上千年的建筑旁边,是民国建筑,再是新中国成立后的房子,就像时间的音符,使人不由得对时间产生一种信任,也产生遗憾;
闪电,闪电的声音,一次次似乎撕裂天空;
台风,每一次都带着不同的名字,搬运着空气、水,和它可以带走的、摧毁的一切;
猫和狗的叫声;
蜜蜂在花间采蜜,和它们收拢翅膀的声音;
以及蚂蚁的低语(必须把频率调整到对等的音频才能听到);
…………
乌兰回来了,拿出一盒白塔,问我要不要出去抽根烟,我同意了。十点多的太阳把我们晾在一片建筑的阴影之下,我说,这个展览很不错。策展人一定花了很多工夫,乌兰若有所思,他说这需要有相同的频率,恋爱需要频率,生命的诞生和终结也有它们的频率,来自全世界的声音被共同展出,也许提醒着我们,应该对人类有更多的同情心和包容心。
他问我,“你有没有想起些什么?”
我说,“当然有了,我想起了很多小时候的事情。夏天那些聒噪的蝉鸣,我们摘了木奶果,切开果子流出的乳汁用来粘住它们的翅膀。动作要快,一粘住它们的翅膀,它们就再也飞不了了。那些蝉有红色的,有绿色的,非常漂亮。在暮春时节,它们在夜间破土而出,爬到树上蜕壳……
“还有过年时,鱼塘的水干涸了,集体撒网捕鱼,那些鱼在水里扑动,翻滚起朵朵浪花;我小时候经常出去一玩就是半天,饿了就回家吃一点,继续跑出去,直到炊烟从各个地方升起,我的外婆用她拖长的呼喊把我带回家,我闭上眼睛仿佛还能听见外婆的呼喊。还有青蛙和癞蛤蟆,此起彼伏蛙声一片。太多了,它们只存在于我的记忆中,没想到这一天再次复活了。还有1994年,住在母亲的宿舍,晚上听着《粉红色的回忆》这首歌入眠;1998年我第一次看世界杯,半夜睡着了,醒来黑白电视机的沙沙声,一片雪花让我以为下雪就是这种声音。后来我听说大雪压弯竹林,会发出它们断裂的噼啪声。还有情人在身边睡熟时均匀的呼吸……我几乎是不假思索地说了这么多。“太多了。”我说,“也许我应该写一首诗。”乌兰神秘地笑了。他没有再说什么,一支烟抽完,我们又回到了展馆里,在展厅里,我想起了几个人。
午饭的时候,我们点了西餐,边吃边聊。我问乌兰,“你有想起什么吗?很抱歉一直是我在说。”我事后回忆起来,一定是情绪兴奋,所以喋喋不休。第一次坐飞机时,我就是这样,一直说个没完。乌兰说,“不,我想听你说,我喜欢你的故事。那些乡村故事和我的不同,但是我相信童年如果有快乐,那肯定是一样的。”
我犹豫了一下,说起一个故事:
“你有没有这么多年来一直念念不忘的声音?我有一个。徒具声音的形式而没有实质内容。但也许声音已经包含了一切。我的中学阶段住在镇上,每天早上六点有一趟班车发往南宁。距离我去大学报到越来越近,夏天即将过去,我忽然担心那趟班车是不是会正常发车。在此之前,我去车站找司机要了名片。因此,我做了一件事,就是拨打了上面的号码,那是一个座机号,在一阵嘟嘟声后,传来了一声“喂?”我一定是卡住了,停顿半晌,根据声音判断,接电话的是个和我同龄的女生,问,××司机在吗?电话那头说,他出去了。这声音让我呼吸停住了,我无法准确描述她给我的感觉,以至于我们后面又说了什么,又是怎么挂掉了电话,我已经记不起了,又或者我知道我记起来的都是来自我的想象,所以我拒绝相信我的想象,而选择信任她的声音。我想她一定不知道,我是有多么爱慕那通过电话线传递到我这里的音波,而且她和我就住在同一个镇上,也许我们曾经擦肩而过,却毫无知觉。我无数次地回忆,然而声音只能让我想象她很美,也很安静,也许有面包色的皮肤……这是我听过最难忘的声音,我爱上了这个声音。”
乌兰沉吟了一下,说,“请你说慢些。”
“但是我却把卡片弄丢了。后来那趟班车真的取消了,我再也无法联系上她,也就是说,迄今为止,我仅仅听过一次她的声音,就再也无法把她忘怀。至于她长什么样,她过得怎么样,这一切都无从考究。”
“不过后来,又发生了一件事。我们的大学因为扩招,大一时搬到了一所合并的大专院校。天南地北的同学,每天总要拿着电话卡,拨打电话,排遣寂寞,直到电话卡的话费用完,听筒里传来一阵嘟嘟嘟的忙音。有些恶作剧的同学还会到电话超市打女生宿舍的电话取乐。我们住的宿舍过去应该是女生宿舍,因为不时有电话打进来,问某某在吗?得到的回答都是不在。直到有一天下午三点多,我正在等一个电话。突然电话的按键发出了红色的光,响起的铃声在一片寂静中吓了我一跳。我拿起电话,对方是一个女生。等我告诉她,她要找的人不在这里,电话挂了。她的声音似曾相识,让我有怦然心动之感,我想起来了,在上千万音轨上寻找我念念不忘的声音,而刚刚打电话来的女生的声音,和我念念不忘的声音,是如此相似。”
过了半个小时,在那之前我一直陷入一种对过往的沉思当中,直到电话再次响起。是刚才那个女生,她说,“我找到某某了。”
我说,“所以你打电话来是……”
“她们都在打牌,都不陪我玩。”
“我决定不等那个电话了,按照她的地址,见到了这个名字叫作陈灿的女生。我们经历了恋爱、分手、淡忘这些人之常情。”后来我一直在想,也许这只是一个……退而求其次的故事?一个偶然,一个巧合,一个错过。我搅动着我面前的南瓜汤,一圈圈的汤像一张唱片在旋转着。没想到把这个内心故事说出来,会有大病初愈的感觉。
乌兰沉吟半晌,“你刚才问我想起了什么,现在,让我告诉你吧。我是一个没有听觉的人。你的故事,我是通过唇语解读的。我想,那个女生一定很美。”
啊,怪不得,你总是慢我们半拍。他面部的肌肉跳了一下,“我生活在一个没有声音的世界。”
“据我母亲说,我很小就听不到声音了,被过量注射了一种药物导致的。这么多年,她一直生活在内疚当中。她的内疚有时对我来说,更像是一种亲情的维系,一种惩罚。直到有一天,我发现我并非完全失聪。”
“完全,是说听觉偶尔会恢复吗?”
“不是,你刚才有没有留意我躲在一个展厅里?你没有进去,那个展厅叫作Alice,Alice是一头鲸的名字,它是世界上最孤独的鲸。Alice在1989年被人类发现,对于鲸族来说,它就像是一个哑巴,没有亲人,没有朋友,只是在海洋里孤独漫游。它高兴时唱的歌没有同类能够听见,它难过时也无法找到倾诉的对象。原因是它的鲸语频率是52赫兹。而正常的鲸的频率,是15~25赫兹之间。Alice从1992年开始被追踪录音,从来没有在海洋中发现过相同频率的鲸。
“但我意外地发现,我居然能听到Alice的歌唱。多年来,我一直在茫茫人海中寻找我的声音,没想到我是唯一能够不借助频率转换就能听见它心声的人。它的声音被我接收,被我感受。所以,我还不是这个世界上最孤独的人,而Alice,它仍然是,世界上,最孤独的鲸鱼啊。”
他颓然地靠在椅子上,流下了眼泪。比起我的大病初愈,他更像是经历了一场灾难。
责编:周希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