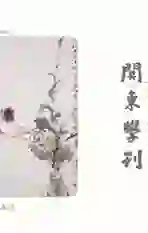萧军集外佚文《笔利谈及其他》辑考
2024-09-29高锐
[摘 要]1940年《笔阵》新1卷第1期刊载有萧军《笔利谈及其他》一文,这篇文章为2008年华夏出版社出版的《萧军全集》所失收,应为萧军集外佚文。《笔利谈及其他》一文写于1940年萧军即将离开成都之时。通过考辨可以发现,这篇文章并非萧军一气呵成之作,而是萧军寄居成都期间,将其对马宗融批评的回应与给王影质小说集所写的序言组合而成的一篇杂文。这篇杂文不仅可为《萧军全集》补遗提供文本依据,而且对于了解抗战期间萧军在成都的思想、交游与创作,完整呈现20世纪40年代四川文坛上的“招标出版”风波亦具有一定的文献史料价值。
[关键词]萧军;《笔利谈及其他》;佚文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延安时期作家回忆录文本整理与研究”(20XZW018);2023年度陕西省出版科学基金项目“延安时期期刊编辑身份认同研究”(23BSC06)。
[作者简介]高锐(1976— ),女,延安大学学术期刊中心副编审(延安 716000)。
萧军不仅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一位著名作家,一位期刊编辑,同时也是中国共产党的紧密追随者。在东北时期,萧军曾协助《国际协报》副刊主编裴馨园编辑副刊;在上海时期,萧军曾参加《海燕》和《作家》月刊的编辑工作;在成都时期,萧军曾为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成都分会会刊《笔阵》杂志编辑,同时还担任《新民报》文艺副刊《新民谈座》主编;延安时期,萧军又参与主编延安《文艺月报》;抗战胜利后,萧军回到东北,在哈尔滨创办了《文化报》。这些报刊都刊载有萧军的作品,且基本上也都收入了《萧军全集》,但仍有个别作品被遗漏。1940年《笔阵》新1卷第1期随感杂谈栏目,就刊载有萧军的一篇杂文。题目为《笔利谈及其他》,该文是萧军1940年3月即将离开成都之前所写的一篇杂文,经笔者核实,该文未被《萧军全集》所收录,应为萧军的一篇集外佚文,现加以辑录释读,并略加考论,以期能为《萧军全集》补遗与萧军研究提供文本参照。
一、《笔利谈及其他》与王影质及其小说序言考辨
《笔利谈及其他》一文刊载于1940年《笔阵》新1卷第1期,作者署名为萧军,文末附记“这是给王影质君小说集的序言”。从文末的附记来看,该文似乎应为萧军写给王影质小说集的序言。但王影质为何人?萧军《笔利谈及其他》一文并未交代。通过查阅萧军成都时期的日记及其与妻子王德芬的通信,可以获知王影质的相关信息。1938年7月间,萧军与妻子王德芬一起前往成都。在成都生活期间,萧军曾与陈翔鹤、顾授昌、李劼人、罗念生、曹葆华、周文等人共同担任《笔阵》杂志编委,同时担任《新民报》文艺副刊《新民谈座》主编,后因感觉“创作的活动常常被各种外力阻害”【萧军:《萧军全集》第18卷,北京:华夏出版社,2008年,第235页。】而于1940年3月7日只身离开成都,前往重庆。在前往重庆途中,萧军致信妻子王德芬,“如果不是王影质君赶到车站代买了票,我是没有希望坐汽车了”。【萧军:《萧军全集》第15卷,北京:华夏出版社,2008年,第110页。】3月30日又一次写信给王德芬,让其收拾行李准备前往重庆,信中交代,成都生活中的“各种家具,如能寄存待你母亲她们来用最好,否则就托王影质君代卖了”。【萧军:《萧军全集》第15卷,北京:华夏出版社,2008年,第120页。】1940年4月5日,王德芬给萧军的回信中也提及,“王影质君也在为我找车,临行他说送我上车和打电报给你,勿念!”【萧军:《萧军全集》第18卷,北京:华夏出版社,2008年,第123页。】萧军4月8日给王德芬的回信中再次叮咛,“事务的事情可多请杨波、王影质帮忙”。【萧军:《萧军全集》第15卷,北京:华夏出版社,2008年,第126页。】显然,从上述萧军夫妇的书信往来中可以看出,王影质与萧军夫妇颇为熟识,是萧军夫妇颇为信任之人,为萧军夫妇在成都时期的生活提供了诸多帮助。另据萧军妻子王德芬回忆,1938年,“7月18日我们到了成都,最初住在旅馆里,一位萧军的读者热心肠的王影质先生,为我们在少城街找到一间房子,第三天我们就搬去安了家。王先生从他自己家里给我们拿来了铺板、支凳,还有锅碗瓢盆,切菜刀、案板,装米的坛子、水缸等日用炊具,应有尽有,解决了我们的大困难”【王德芬:《我和萧军五十年》,北京:中国工人出版社,2008年,第33页。】。从中可见,王影质为萧军的忠实读者。
但经查阅抗战时期四川成都文艺刊物《金箭》月刊可知,王影质,又名王引之、王隐之,曾用穆鹰、吴延等笔名,为抗战时期中华文艺界抗敌分会成都分会会员、成都文艺协会创办的文艺性刊物《金箭》月刊的发行人,先后以影质、穆鹰、吴延等笔名在《金箭》《四川风景》《挥戈》等抗战时期成都出版的文艺刊物上发表了《太仓之粟》《到前线去》《媚浪河在怒吼》《苦行雪山》等短篇小说,以及《池畔》《站在文艺的岗位上来纪念“七七”》《学习这巨人的战斗精神》等散文作品,积极宣传抗战,是抗战时期成都一位致力于抗战宣传的文艺工作者,而非萧军的普通读者。
1940年5月,成都生活书店出版了王影质的短篇小说集《煤矿》,收录了王影质1936年以来创作的《监狱》《煤矿》《太仓之粟》《故乡》《到前线去》《媚浪河在怒吼》《苦行雪山》《野渡》等九篇短篇小说,该短篇小说集的序言题为《皆大欢喜》,署名为萧军。可见,萧军确为王影质的小说集写了序言,这篇序言也为《萧军全集》所遗漏,相关研究者亦未提及,亦属于萧军佚文。但经比对发现,王影质小说集“序言”与《笔利谈及其他》一文颇有差异,王影质小说集《煤矿》序言“皆大欢喜”内容仅为《笔利谈及其他》文章内容的第三部分,其中并未涉及《笔利谈及其他》中“名利谈”与“是非观”两部分内容。这表明,《笔利谈及其他》一文并非王影质小说集序言,由此可知,《笔利谈及其他》文末的附记“这是给王影质君小说集的序言”,应该只是针对文章第三部分“皆大欢喜”而言,而非《笔利谈及其他》全文,但因作者并未在《笔利谈及其他》文末注明仅第三部分“皆大欢喜”为王影质小说集序言,这便容易引发读者的误解,误以为《笔利谈及其他》一文即为王影质小说集“序言”,从而产生误读。从中也可以看出,萧军《笔利谈及其他》一文中有关笔利谈的内容应该另有所指,并非针对王影质小说集而言,因此有必要加以澄清。
二、《笔利谈及其他》与萧军“招标出版”风波考论
如前所述,萧军《笔利谈及其他》一文中“名利谈”与“是非观”两部分并非王影质小说集序言内容,而是另有所指。经查阅相关文献资料可知,《笔利谈及其他》一文中“名利谈”与“是非观”与1940年四川文坛上有关萧军刊载的出版招标“启事”密切相关。1939年12月,萧军在胡风主编的《七月》杂志第4卷第4期刊载了一则《萧军启事》,启事声称:
本人现有文艺作品数部拟招标出版。《侧面》:游记,三部合订约十八万字;《四地文集》:论文,散文,杂文合集,约十七万字;《乌苏里江的西岸》:叙事诗,约两万行;《第三代》:长篇小说,第一第二两部约十六万字,已于某书店出版,现拟收回版权,续写下去,全部约为四十五万字,一九四一年底可完成。
条件:一、凡真正以从事文化事业为目的的书店,或个人均可承印;二、版税最低额为百分之二十,发表费另计之。如双方条件合适,本人已出作品或新作,均可托其出版。至明年三月底止,如不合适,当分别函发。【萧军:《萧军启事》,《七月》1939年第4卷第4期。】
萧军刊发这则招标出版启事的缘由是萧军的长篇小说《第三代》第一部、第二部曾被纳入巴金主编的“新时代小说丛刊”系列丛书,并于1937年2月授权巴金等人创办的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后因版税较低而拟收回版权,重新招标出版。于是,1939年12月,萧军在胡风主编的《七月》杂志第4卷第4期刊载了上述《萧军启事》。《萧军启事》刊出后,当时在重庆北碚复旦大学任教的马宗融看后,于1940年1月14日在重庆《新蜀报》第4版《蜀道》栏目刊发短论《招标出版》,针对《萧军启事》内容发表评论,为友人巴金等人创办的文化生活出版社鸣不平,认为招标“需要有名”,并就名利问题援引鲁迅的话——“张资平式和吕不韦式,我看有些不同,张只为利,吕却为名。名和利当然分不开。但吕氏是为名的成分多一点”【马宗融:《招标出版》,《新蜀报》1940年1月14日,第4版。】,不点名地批评了萧军公开刊发出版招标“萧军启事”之非,认为萧军在文化生活出版社之外,招标出版著作的行为属于背信弃义。
萧军看后,于1月27日作了《文坛春秋录》(第一章),刊载于成都《新民报·新民座谈》第476期予以回应,认为“作品多,有名,而又受了书店委屈的作家们”不应该再委屈下去了!“无论这书店它是有几面关系或是有多少‘帮忙’和‘打手’,至少‘招标出版’的启事是登定了,使‘觉得新奇’的某人,也可以见识一下,省得屁大一点小事就弄得头眩目晕”【萧军:《萧军全集》第11卷,北京:华夏出版社,2008年,第415页。】。之后,马宗融又于1940年2月1日在成都《国民公报》第4版《文群》栏目发表《招标广告与镖旗有灵》一文,指出曾出版过萧军作品的文化生活出版社在抗战期间的艰难处境,“该社一迁广州被炸,再拟迁桂林,又难成事实”,以至于“一个愿意倾家的朋友只好到后方来设法,一个愿意牺牲自己的版税的朋友终于仍回到陷于孤岛形式的上海去独立撑持该社去了”。【马宗融:《招标广告与镖旗有灵》,《国民公报》1940年2月1日,第4版。】倘若作家“对于版税的要求是最低额百分之二十者,发表费还要另计,那么,抱同一目的的出版家,也和作家一样,不吃饭就不能生活,又该怎么要求呢?他之外,还有贩卖商人及其他。‘羊毛出在羊身上’,我们还想有便宜书读吗,呜呼!文化事业!”【马宗融:《招标广告与镖旗有灵》,《国民公报》1940年2月1日,第4版。】同时援引鲁迅生前被人拖欠版税的实例批驳萧军,“鲁迅生前时有被人拖欠版税之事,但他讨索无效,也只好付之从叹。他现在死了,他曾以善意奖掖后进,但每每有人把他的善意当‘灵旗’接受了,我们也就不得不把他当‘镖旗’看。但‘镖旗’作成过人的名,‘名利当然是分不开的’——‘镖旗’有灵,恐怕会想替它的主人出口气,会替它所保的作品的作者获到那‘分不开的’利吧!”【马宗融:《招标广告与镖旗有灵》,《国民公报》1940年2月1日,第4版。】萧军读后又于2月11日撰写了《文坛春秋录》第二章,刊载于成都《新民报·新民谈座》第487期予以回应,文中表示:
鲁迅先生那“付之从叹”的精神,应该声明,即使砍下我的吃饭的家伙,“我绝对”是不想学习的。有拖欠我版税或者稿费的,一定要他结清。不然,无论打官司或是打架或骂街我全来——如果可能。末了,我应该说一声:对于这样的“保镖文章”,一点也不感到:“非常新颖,别致”和“创见”,只是感到一点常常嗅到的“气!”——“呜呼!文化事业!”【萧军:《萧军全集》第11卷,北京:华夏出版社,2008年,第419页。】
之后,2月16日,马宗融在重庆《新蜀报》第4版《蜀道》栏目又发表《从招标自由想到发芽豆》的短文,回应萧军的批评,文章引证鲁迅先生不许人“在嫩苗田里驰马”的说法,指责萧军,“略高两寸苗头”,便“在嫩苗田里俯瞰一切,自居老树了”,就怕只是发芽豆,“顶多不过发芽而已,发了芽就算成熟了”。【马宗融:《从招标自由想到发芽豆》,《新蜀报》1940年2月16日,第4版。】
由上可见,1940年初,萧军与马宗融之间就招标出版“启事”一事进行了几番激烈的论争。从《萧军全集》收录文章来看,萧军有关自己刊登招标“启事”引发的论争中,除了上述刊载于成都《新民报》上的《文坛春秋录》两章外,似乎再没有撰写针对马宗融批评的回应文章。但1940年4月《笔阵》新1卷第1期上刊载的萧军佚文《笔利谈及其他》一文表明,事实上,除了《文坛春秋录》两章之外,萧军还撰写了《笔利谈及其他》一文,就招标出版所涉及的名与利、是与非的问题再次公开回应了马宗融的批评。文章由马宗融援引鲁迅“张资平式和吕不韦式,……张只为利,吕却为名”的话题中的“名与利”说起,以颇为风趣幽默的自嘲笔法既为自己刊登的招标出版“启事”进行辩护,又公开回应了马宗融对招标出版“启事”的指责,并由此衍生出对于是与非的思考。萧军认为,对于“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这一类问题的论争,本质上是因各自立场的不同而生,他借用了施蛰存与鲁迅关于“《庄子》与《文选》”论争中,《致黎烈文先生书——兼示丰之余先生》一文套用的偈语“此亦一是非,彼亦一是非”来说明此类论争问题的实质。
萧军认为,马宗融是以自己之是非他人之是,两者原本就不属于同一是非。在萧军看来,马宗融为友人巴金等人的文化生活出版社辩护之是,实则为非。但从马宗融的角度来看,萧军通过招标出版“启事”争取版税之是,实则为非。显然,从本质上讲,在争取版权这一类问题上,其实论争双方各人有各人的是与非。这也是萧军与马宗融产生分歧,进而公开论争的根本原因,因此导致两人之间的激烈论争。《笔利谈及其他》一文中,萧军公开指责马宗融以己之“是”非他人之“是”,即是非之人。可见,《笔利谈及其他》一文前两部分的“名利谈”与“是非观”实质上是萧军对马宗融批评的又一次公开回应,属于二人论争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但《萧军全集》中该文的缺失,使我们无法窥探到20世纪40年代四川文坛上因萧军“招标出版”引发的这场论争的完整面目。可以说《笔利谈及其他》一文表明,马宗融与萧军之间这场有关“招标出版”的论争,从1940年1月一直持续到4月,最终以萧军在《笔阵》刊发《笔利谈及其他》一文而告终。因此,《笔利谈及其他》一文对于完整再现萧军与马宗融之间的这场论争具有重要的文献史料价值。
三、《笔利谈及其他》与王影质小说“序言”写作时间考论
《笔利谈及其他》一文文末的写作时间标记为“一九四〇·二,四晨于成都”,萧军为王影质小说集《煤矿》所作序言“皆大欢喜”文末标记时间为“一九四〇·三·四晨成都”,两者均为萧军即将离开成都之前所写,但写作时间相差整整一个月。单纯从二者文末标记的写作时间来看,很明显,《笔利谈及其他》一文的写作时间早于王影质短篇小说集《煤矿》序言《皆大欢喜》的写作时间。但从《笔利谈及其他》一文的附记“这是给王影质君小说集的一篇‘序言’”来推论,《笔利谈及其他》一文成文时间似乎又应该晚于王影质小说集序言,因此有必要对王影质小说集序言《皆大欢喜》及包含“序言”的《笔利谈及其他》一文成文时间进行考订。
如前所述,因王影质小说集《煤矿》序言“皆大欢喜”内容仅为《笔利谈及其他》文章的第三部分,且《笔利谈及其他》文末标记写作时间早于王影质小说集序言“皆大欢喜”,因此我们可以推论,萧军可能只是将1940年2月4日写好的《笔利谈及其他》文章的第三部分《皆大欢喜》内容抽取出来作为给王影质小说集的“序言”,但从萧军日记的记载来看,似乎并非如此。经查阅萧军日记,其1940年2月4日的日记,既未明确记载《笔利谈及其他》一文写作情况,也未提及为王影质小说集写序言之事,反倒是1940年3月份日记中,明确记载了给王影质短篇小说集《煤矿》写序言的情形。
据萧军3月4日的日记载:“把王影质的两篇小【据后文可推论,此句应为“把王影质的两篇小说看过了”。】看过了,觉得他那篇《监狱》底起首很有模仿《羊》的痕迹,他要我给他写个序,我还没有决定。”【萧军:《萧军全集》第18卷,北京:华夏出版社,2008年,第240页。】3月5日的日记又写道:“昨天给王影质把序写好了,午间他同一个女学生来,他承认那篇《监狱》是受了我的《羊》而写的。”【萧军:《萧军全集》第15卷,北京:华夏出版社,2008年,第240页。】这两则日记表明,萧军给王影质小说集序言的写作时间应该就是1940年3月4日,这与1940年5月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的王影质短篇小说集《煤矿》序言文末标记的写作时间一致。由此可以推论,至少《笔利谈及其他》一文的第三部分“皆大欢喜”的写作时间应为1940年3月4日,而非2月4日。那么包含着王影质小说集序言《皆大欢喜》内容的《笔利谈及其他》一文文末写作时间为什么会标记为1940年2月4日呢?萧军日记同样可以提供一些线索。
萧军1940年2月4日的日记虽然未明确记载《笔利谈及其他》一文的写作情况,但从其2月4日的日记所记内容来看,与《笔利谈及其他》一文前两部分内容密切相关。据萧军1940年2月4日的日记载:“今天夜间下雨。午间去华西大学闲走。路上我想着将要怎样骂我的敌人的话”,并相应地在2月4日的日记结尾写下了下面的话:
脖子上挂着小铃铎的胡羊们,竟也一代不如一代了,早些还可以做政府保镖,弄个一官半职,如今竟给书店做保镖了,虽然是为了友谊的关系……
如果我能留学法国,现任教授,另外再在某公署挂一名参议,逢年过节,有将军送上车马费或是什么费……千八百元,那末我就不再登广告,使别人呕吐,或是弄得头晕目眩……为了友谊关系,我连版税全可送奉,另外还要加一点股本咧!
——谈“关系”给马宗融。【萧军:《萧军全集》第18卷,北京:华夏出版社,2008年,第224页。】
这则日记表明,2月4日,萧军整日为马宗融对其刊出招标出版“启事”的公开指责与批评所气恼,以至于在闲走的路上都在思考如何“骂自己的敌人”,矛头直指曾经留学法国,时任重庆复旦大学教授的马宗融,并相应地在其日记中写下了“谈‘关系’给马宗融”的话。由此可以推论,2月4日,萧军在思考“如何骂自己的敌人”的同时,也在思考如何公开理性地回应马宗融的批评,因马宗融批评中谈及鲁迅先生“张资平式和吕不韦式”的名利观,因此,萧军便紧承马宗融的话题写下自己关于“名与利”“是与非”的思考,也即《笔利谈及其他》一文的前两部分。故文章结尾落款时间为“一九四〇·二,四晨”。这就意味着,萧军《笔利谈及其他》一文并非一气呵成,而是将2月4日为回应马宗融公开指责而写的“名利谈”与“是非观”两部分内容,与3月4日给王影质小说集所写的序言《皆大欢喜》拼合在一起,以《笔利谈及其他》为题,刊发在4月1日的《笔阵》杂志上,刊发时保留了文章前两部分的写作时间,并在文末加上了“这是给王影质君小说集的一篇‘序言’”的附记。可以说,《笔利谈及其他》一文本质上是萧军与马宗融关于招标出版“启事”论争的一部分,只不过在文末附加了《皆大欢喜》这一“笔利谈”之外的其他内容。
总之,辑录考释萧军《笔利谈及其他》一文不仅对于《萧军全集》补遗及萧军研究具有重要意义,而且对于完整呈现20世纪40年代四川文坛上萧军与马宗融之间围绕“招标出版”展开的论争具有一定的文献史料价值,值得研究者关注。
附录:《笔利谈及其他》
一:名利谈
我既爱名;更爱利,所以每篇文章登出总要署名“萧军”,而每本书的后面,也必要印上著作者就是我。至于那“版权所有”的地方,现在虽然即使贴上印花加盖图章和签字也没效了,但印也还是要印上去的,以存体统。而讨版税要稿费,这又是当然的事了,虽打官司也不惜。这和那些为文化事业而“牺牲版税”,“情愿倾家”的诸君子,当然不能并论。眇小与伟大底区别,大概也就在此。过去我也确是有过一个家,但已倾在了满洲——就是东三省。当然并不是为了“文化事业”——现在,家虽然有一个,即使“倾”起来,数目也决不会可观,不独不能抵xx员,xx顾问或参议等半月“干薪”;连大学教授五个钟点的“束修”——为了高雅故以此代——恐怕也不能相抵!虽然还有一位老婆和一个不足六个月的孩子,似乎可以卖了,但这不独更有动“清议”,中华民国的法律,也要把我送进监牢里去。如今空袭常来,监牢里也并不保险的,虽然可以不愁吃穿,不出房租。所以:还是不“倾”也罢!既然不“倾”,那么“牺牲版税”也可不必了。无论是“……式”也就顾不得那许多。质之:写文章“署名”;登稿拿稿费;做教授领“束修”……以保护“呜呼!文化事业”之马宗融氏,不如以为何如?
二:是非观
我对于“无事【此处疑为作者笔误或原刊排版错误,“事”应为“是”。】非观”之流,是很看不起的,更是“假装”。觉得他已经失去了为人的气概。无论他装得怎样公允,和平,可爱……。
苏联和芬兰交战了,他说:
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我们不能说苏联不好;更不能说芬兰不好。
英法和德国交战了,他说:
英法和德国,本来是没有恶感的,若不是有第三国帮助它——德国——瓜分波兰,他们是不会打起来的。
中国和日本交战了,他说:
“日本就是恨的共产党,中国若没有共产党,他就不会和中国打仗了。”
于是他的结论:
“汪精卫是恨共产党的,所以他去投奔日本。但我们不能说共产党不对,也不能说汪精卫不对。”据他说这结论也是无“是非观”的。
此亦一是非;彼亦一是非,
惟一“无”是非者,才是是非人。
注:此偈语前二句系借用施蛰存君者;后两句算是自撰,但好系鲁迅先生说过了?姑存待证。
三:“皆大欢喜”
诬蔑现实和夸张丑恶,全是不该的,更是做为一个文艺工作者。
监狱,煤矿,这全是存在于人间的东西。它们底存在虽然有地上和地下底不同,而作用却是一个:摧毁人们正常的发展和成长。从这里再接引到“太仓之粟”,我们就不难懂得中国过去的社会,也懂得了世界;不独懂得了人类底现在,也懂得了它底将来。
关于本书作者的技巧,有的地方喜欢用不必要的渲染和“对仗”的地方,我是不同意。但他也懂得,这不完全算为作者的过错,是方块字玩害得我们太深了,是我们“木【此处应为排版错误,“木”应为“本”。】位文化”底功绩。作者是一位勤勉的文艺工作者,不久他就会克服自己创作上的困难和缺点,这是不能作为非难新兴文艺生长者们藉为口实的。
描写光明是对的;但不能被“光明”冲花了眼,以致忘掉了可以障害光明的残墙败垒;描写美丽是对的,而对于毒害和啮食美丽生长底丑恶事物更不能姑宽:这不独是从事文艺工作者过去的任务,也是现在和将来的任务……。
试看一下,在这美丽的雄伟的抗战的光照里,监狱,煤矿,“太仓之粟”的故事等等,它们是怎样存在着的呢?和以前又有了怎样不同了呢?更是最后的一个。这是读者作者们应该深思的一件事:中国底战胜与灭亡的关键,也就在这里了。
自己生活在成都快近二个年,很有一点儿“泥足”的感觉了!最近要到别的地方跑一跑,行前,承本书作者把他的几年来写下的文稿要我代看一看,准备印集起来。我个人曾经有这体验,知道“自己”印书的辛酸,愿意写两句话助助兴,所谓:“皆大欢喜!”是已。
因为行期匆匆,只读了:《监狱》《煤矿》《太仓之粟》之篇。
一九四〇·二,四晨于成都
附记:这是给王影质君小说集的一篇“序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