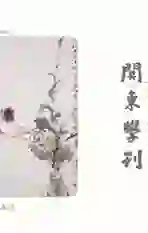王哲甫《中国新文学运动史》的思想来源及其新文学教育实践
2024-09-29李占京
[摘 要]王哲甫的《中国新文学运动史》在新文学史研究和新文学教育研究中备受瞩目,但其思想来源却少有人论及。王哲甫的《中国新文学运动史》思想来源和他的新文学教育经历及实践密不可分。他在铭贤中学时期、燕京大学求学时期所受的新文学教育经历,奠定了部分思想基础;而他在山西两所学校的新文学教学实践,促成了这部著作的诞生。王哲甫和他的《中国新文学运动史》既是新文学教育的产物,又反向哺育了新文学教育与教学。
[关键词]王哲甫;《中国新文学运动史》;新文学教育;铭贤中学;燕京大学
[作者简介]李占京(1986— ),男,文学博士,嘉兴大学平湖师范学院讲师(嘉兴 314001)。
在新文学史著作研究中,王哲甫的《中国新文学运动史》备受学者瞩目。在新文学学科史研究著作中,专家学者们对这部著作展开了深入阐释,对其历史地位也给出了各自的评价。虽然有是否为“第一部新文学史著作”的争议【谢泳认为,陆永恒的《中国新文学概论》“应当是最早完全以新文学为研究对象的著作”(谢泳:《陆永恒〈中国新文学概论〉简介》,《新文学史料》2013年第2期)。付祥喜、宋声泉等人认为第一部新文学史应该是叶荣钟的《中国新文学概观》(宋声泉:《民初作为方法:文学革命新论》,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49页注①;付祥喜:《日据时期台湾人编写的两种“中国新文学史”——蔡孝乾和叶荣钟的〈中国新文学概观〉》,《现代中文学刊》2014年第3期)。本文不讨论该问题。】,但就早期新文学史著而言,王哲甫的《中国新文学运动史》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研究者多关注此书的具体内容及学术史价值,鲜有研究者考察该书的思想来源、新文学教育对王著形成的影响,以及王哲甫对新文学接受及其文学史观的形成过程等问题。
首先,王哲甫既非著名作家亦非长期从事文学研究的专业人员,无论当时还是现在,有关他的研究信息并不多。《中国新文学运动史》出版之前,他没有什么特别引人注意的成果,该书出版之后,他又迅速“消失”,不再出现于学术界。他只在1933年突然拿出一部成系统、有规模的独立的新文学研究著作,接着就离开了文学研究界。他就像一颗流星,在文学研究界突然出现又倏然而逝。人们只能针对他的成果——《中国新文学运动史》的内容展开论述,少有人考察王著的思想来源及产生过程。【相关论述文章可参阅李朝平的《王哲甫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现代中文学刊》2016年第1期)、金鑫的《对新文学知识的再传播:〈中国新文学运动史〉生成论》(《文学与文化》2022年第2期)等。】
其次,学术研究视角限制了研究者的进一步追索。文学史观及内容研究一直处于“正统”地位,而文学史著作与文学教育的关系,通常不为人所注意,少有学者从文学教育的角度切入。
陈平原曾言:“在20世纪中国学界,‘文学史’作为一种‘想象’,其确立以及变形,始终与大学教育(包括20世纪50年代以前的中学教育)密不可分。不只将其作为文学观念和知识体系来描述,更作为一种教育体制来把握,方能理解这100年中国人的‘文学史’建设。”“说到底,体例明晰、叙述井然、结构完整的‘文学史’,主要是为满足学校教育需要而产生的。”【陈平原:《文学史的形成与建构》,南宁:广西教育出版社,1999年,第4—5页。】温儒敏亦言:“但是到了第二个十年,即1928年以后,上述状况就有大的变化,到1930年代初,甚至出现了一个文学史写作的热潮,接连出现数种独立评说新文学的专门文学史。其重要的原因,是当时许多大学都陆续指定开出文学史课程,教员为了授课,就要专门编写各种文学史。据不完全统计,从1917年初到1927年底,十年间出版的中国文学史著作只有8种,而从1928年初到1937年底这第二个十年间出版的中国文学史专著就有67种。这种数量的激增跟1920年代中期以来胡适等人提倡‘整理国故’不无关系,然而更主要的,还是因为许多大学的创办和学科建设的要求。文学史越来越成为现代教育体制所规定的一种知识体系,成为满足学校教育需要的一种时兴的产物。”【温儒敏:《从学科史考察早期几种独立形态的新文学史》,《中国文化研究》2003年第1期。】现代教育体制与文学史著有着互相促进、相互制约的关系。一方面,教师授课需要将文学知识系统地、层次分明地教授给学生,需要将繁杂的文学知识整理成一个体系。现代文学史观念于是被普遍运用到现代教育之中。另一方面,在“大学”这个场域之中,教师受到现代教育规则的制约。准时上课、及时编印讲义等一系列要求导致教师必须不断拿出“成果”,而这些“成果”结集出版之后,便是各种教材与著作。这既是制约,也是督促。不同学者研究成果的汇集、出版,凸显出现代教育体制对文学史写作的制约与促进,同时又反过来促进了文学教育方式及文学知识的接受、传播与经典化。新文学史教材的产生,虽有其特殊性,但也未摆脱这一规律。【最具代表性的例子就是鲁迅在30年代多次表示撰写文学史的想法,最终落空,按照陈平原先生的解释,这其中最主要的原因就是鲁迅离开了大学这个环境。陈平原:《文学史的形成与建构》,南宁:广西教育出版社,1999年,第5页。】
王哲甫的《中国新文学运动史》也是这样的情况。作者在该书《自序》中提及:
去年暑假中,我的平静的生活,忽然起了很大的波浪,使我独自一人跑到沙漠似的太原,心中怀着满腹的郁闷无由发泄。没想到因着这一次的刺激,竟造成我编著这本书的命运。
编著本书的计划,在三年以前我就有过这个意思,但是整天为衣食劳碌的我,少有执笔的工夫,结果只搜集了一些零碎的史料而已。这一年来因担任山西省立教育学院的新文学功课,给我一个很好的机会,得以完成我数年来所计划的工作。【王哲甫:《自序》,《中国新文学运动史》,北京:杰成印书局,1933年,第1页。】
这段文字清晰地展示出这部著作的产生与新文学教育的关系。如果不是教学所需,他撰写文学史著依旧会停留在“想法”的阶段。除了这一点,王哲甫的整个受教育过程、《中国新文学运动史》的产生以及该书所体现出的文学史观,都与新文学教育密切相关。考察《中国新文学运动史》与新文学教育的关系,也能更好地理解1920年底到1933年左右中国新文学教育的部分历史样态。
《中国新文学运动史》有几处值得继续讨论的问题,比如:王哲甫为何给“翻译文学”和“整理国故”设专章?他的左翼思想倾向从何而来?他对新、旧文学的态度是如何形成的?
以上这些问题,是目前关于王哲甫及《中国新文学运动史》的研究未能深入的地方。实际上,王哲甫在中学阶段就已经有这些观点的萌芽,这与铭贤中学的新文学氛围有关。他能够写出这部著作,也是燕京大学新文学教育培养的结果,他就是燕大培养出来的众多新文学教员中的一位。可以说,新文学教育的经历对王哲甫史著的产生有着内在的重要影响。引进新文学教育的角度和新的史料,可以更深入地理解为何王哲甫梳理、评价新文学带有较明显的左翼思想色彩,为何他的新文学史著作要加入“翻译文学”和“整理国故”内容。这是王哲甫著作的特色,也是研究者深入挖掘的线索。
一、王哲甫文学思想的形成与铭贤中学的新文学教育
根据现有资料,王哲甫的部分文学思想与他在铭贤中学接受新文学教育的经历不无关系。他的“五四”启蒙价值观、左翼思想、平民情结的形成,对待翻译文学及“整理国故”的态度,都在此时期打下了基础。
(一)接受“五四”启蒙与新文学教育
翻阅相关史料可知,王哲甫【原名王明道,“哲甫”是他的字,山西孝义人。《铭贤廿周年纪念》中显示他的英文名为“Mr.M.T.Wang”。】1919年入铭贤学校读中学,成为第十五班(即第十五届)学员,同班同学共19人。1923年中学毕业,进入铭贤学校大学预科第八班学习,同班同学16人。1925年由铭贤学校大学预科毕业,同年考入燕京大学国文学系,至此完成了中学阶段的教育。
铭贤中学是一所教会学校,教学质量、升学率当时均居全省前列。【该校由美国欧柏林学院和孔祥熙出资兴办,兼为纪念庚子殉难的传教士们。这些殉难的传教士大多也是欧柏林学院的毕业生。欧柏林学院资金充裕,师资也相对完备,这里的老师很多都是大学毕业生,有过留学经历的也不是少数。见郭学钧:《记太谷铭贤中学的特点兼忆学潮》,《山西文史资料》出版社:《山西文史资料全编·第五卷》,太原:《山西文史资料》编辑部,1998年,第445页。】毕业生大多能考进国内知名的国立大学和教会大学,尤其是北京地区的名校。王哲甫能考进同为教会学校的燕京大学不是偶然的。
铭贤中学的新文学氛围比较浓厚。国文教师多是各大学中文系的毕业生。如白序之、于赓虞是燕京大学国文系毕业生。白序之于1919年入燕京大学读书,文学研究会成员,小说《爱之谜》被收录进“文学研究会丛书”《小说会刊》(民国二十二年),小说集《老处女》被徐志摩编入上海大东书局主编的“新文学丛书”。他于1920年前往铭贤中学教书。【“如1920年聘用北平燕京大学文学系毕业生白序之(北京人)来校讲授高中语文课。”信德俭、温永峰、方亮等编:《学以事人 真知力行:山西铭贤学校办学评述》,北京:中国社会出版社,2010年,第93页。】于赓虞是著名新诗人,有“魔鬼诗人”之称。他于1924年8月进入燕京大学国文系学习,一年后退学。在燕京大学学习期间,他认识了徐志摩、刘梦苇、朱湘、闻一多、焦菊隐等多位新诗人、戏剧家,后经焦菊隐介绍,1927年到山西太谷铭贤学校(即铭贤中学)教书。
铭贤学校的办学成就名声在外。1934年夏,蒋梦麟、潘光旦以及著名新文学家陈衡哲来校参观、讲演。同年11月,蒋介石、宋美龄参观该校,并留下了很好的印象。铭贤中学整体教学质量很高,新文学课程建设也相当出色。该校一方面开设新文学课程,另一方面积极创办文学刊物,丰富校园文化活动,促进了新文学的教学与研习。据贺韶九回忆,该校文科课程开设有“新文学”一课。【“高中系分科教学,文科课程有党义、国文、英文、历史、伦理、法制、心理学、经济学、医学、哲学、文学修辞、新文学、体育等。”贺韶九:《太谷铭贤学校简史》,《山西文史资料》出版社:《山西文史资料全编·第二卷》,太原:《山西文史资料》编辑部,1998年,第917—918页。】
五四运动之后,教育部规定各地中学必须教授语体文,白话文由此在中学教育中大范围普及开来。各地具体实施情况不同,语体文与文言文的比重也不同。铭贤中学的初中一、二年级语体文与古体文的比例约为三比二,初中三年级及高中一年级,语体文言比例大体相等;高中二、三年级语体文言比例约为二比三。用语体文作文的次数也有具体规定。这些教学内容的设定,一方面是教育部的硬性规定,另一方面也与学校对待新文学的态度有关。查相关史料,1930年《铭贤集览》中的《高级中学国语课程表》显示,铭贤中学至少在1930年就开设了“新文学”课程。“新文学”是高中一年级精读课和“文科”组必修科。高中三年级还有“近代文学”“中国文学史大纲”“中国文学源流”“白话文学史”“中国文学变迁史”等课程。【《高级中学国语课程表》,《铭贤集览》,1930年,原文无页码。】该校要求初中生就要读《梁任公学术演讲集》《蔡孑民言行录》《胡适文存》《儒林外史》《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镜花缘》等近现代白话文学作品以及创造社丛书等新文学作品。高中一年级学生要精读章锡琛《新文学概论》、鲁迅译《苦闷的象征》、胡适《论短篇小说》、孙俍工《新诗概论》、孙俍工《戏曲作法讲义》、汪馥泉《戏剧概论》等书。略读部分有:鲁迅的《出了象牙之塔》《热风》《呐喊》《中国小说史略》,郭沫若的《文艺论集》《橄榄》,郁达夫《寒灰集》,张闻天《旅途》,庐隐《曼丽》,欧阳予倩《剧本汇刊》,刘半农译《茶花女》,焦菊隐译《女店主》,田汉《咖啡店之一夜》,等等。这些都是新文学作品、相关译著或理论著作。就新文学教育而言,其范围、种类、篇幅,比之同时期各大学中文系所授,毫不逊色。
铭贤中学校内的文艺活动也很丰富。于赓虞与岳一峰、程志涵及一些爱好文学的同学一起组织了“晨曦社”,出版《晨曦周刊》。此外,还有“海涛社”的《海涛周刊》《半夜钟》,“火花社”的《火花》杂志。文学团体有国学研究会、文艺研究会、语言练习会等,还有新剧表演团等文艺社团,整个学校的课外文艺氛围相当浓郁。
在这样的氛围中,王哲甫对新文学的理解也慢慢加深,逐渐形成一些独立的观点,并撰文发表。《铭贤校刊》即是铭贤中学学生发表文章的理想园地之一,他们可以在校刊上自由地发表文章、阐述自己的观点。
1924年12月1日,王哲甫在《铭贤校刊》第一卷第二期发表《我对于新文学的意见》,署名王明道。在这篇文章中,他说:“我起初对于这新文学,仅以一种浅显的白话文去对待他,并不想他有美妙的色彩,与实用的价值。”“不知不觉的引起我好奇的心来去研究。虽然我的天资迟钝,可是日子长了,倒也领略的不少。新文学的真相,也稍微的了然一些。”【王明道:《我对于新文学的意见》,《铭贤校刊》第1卷第2期,1924年,第36页。】可见,一开始他对新文学并不十分感兴趣。“引起好奇心”,很可能是本校教师的引导、同学校友们的热烈讨论影响的结果。在这个基础上,他由学习白话文慢慢转向新文学阅读。该文提及他常常在图书馆阅读新文学书籍,包括新文学史、新文学选一类的书籍,渐渐对新文学有了更深的认识。他认为新文学有四个特点:新文学相对旧文学而言,浅显易学,是普及教育的利器;新文学有利于促进国语统一;新文学易于了解;新旧文学各有优劣,应当新旧并存。
古来大文豪的著作,至今仍存的缘故,因他有研究的价值。若拿他的一点短处来批判他是死文学,雕刻的,假的,不实用的,便欲用新文(学)来,完全代替他,这岂不是舍本求末自失国粹吗?以我看来这两样各有长处各有短处。新文学活泼明显。其缺点在肤浅。旧文学雄厚深奥,其缺点在拘束。最好新旧并存。让旧文学专门学识者研讨。新文学让求普通智识者讲求。这样一方面可保存数千年的国粹,一方面可以促进新文学的应用。岂不一举两得么?【王明道:《我对于新文学的意见》,《铭贤校刊》第1卷第2期,1924年,第38页。】
无论是之后就读燕京大学,还是工作之后教授新文学史,王哲甫一直保留着“新旧文学并存”的观点,并将之写进了《中国新文学运动史》。在该书第一章,作者即表明:“文学本来没有新旧的区别,新文学这个名词,是民国七八年文学革命运动以后,才常见于书报杂志上的,以前概不多见。新文学的取义,不过是对于昔日传统的旧文学而言,是中国文学上的一种革命运动。然而新文学与旧文学之间,也不容易划出一道鸿沟来,很精确的区分他们。”【王哲甫:《中国新文学运动史》,北京:杰成印书局,1933年,第1页。】文学本无新旧,所谓新旧之别,在王哲甫看来,并不在于语言形式——白话/文言的不同,将它们区别开来的是二者所含的内容本质。文学必须有灵魂,有了灵魂,旧文学便不再是“死文学”;没有灵魂的“新文学”,也不过是报章的补白而已。
与《我对于新文学的意见》同期发表的还有王家驯的文章《语体文的我见》。和王哲甫一样,王家驯对白话文也有个接受过程。他从小受私塾教育,一直到中学,对白话文的理解都不怎么深刻。他在山西国民师范学校最初接触到“五四”所提倡的国语等思想观念,逐渐有所觉醒。“起初我也是抱着怀疑,我肚里就成为新旧挑斗的战场了”,“虽说不明了白话的究竟,也愿做几句”。【王家驯:《语体文的我见》,《铭贤校刊》第1卷第2期,1924年,第40页。】王家驯一年后离开山西国民师范学校,后经过铭贤中学的老师张方谷的教导,“才晓的(得)我已经成了落伍的士族了。并且才懂得白话是必需品了”【王家驯:《语体文的我见》,《铭贤校刊》第1卷第2期,1924年,第40页。】。在文章最后他还热情呼吁:“和我同样落伍的伙伴,你要同语体文作友,快来与我一齐向前奋斗!奋斗!”【王家驯:《语体文的我见》,《铭贤校刊》第1卷第2期,1924年,第42页。】
王家驯、王哲甫一开始并未主动接受白话文和新文学,而是在学校里,在老师的帮助下,逐渐培养出对白话文、新文学的兴趣,后来形成了各自明确的观点。可见,学校新文学教育氛围对王哲甫新文学观念成长的重要性。
白序之拟定的《铭贤中学国文教学的草案(必修科)》显示,铭贤中学国学教学的目的是“人人能用国文自由发表思想”,“引起多数学生研究文学的兴趣及欣赏”。【白序之:《铭贤中学国文教学的草案(必修科)》,《铭贤校刊》第2卷第1期,1925年,第37页。】这样的教学要求,为新文学进入“课堂”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在师生的共同努力下,《铭贤校刊》弥漫着蓬勃的朝气与自由的氛围。中学生们积极思考如何改革社会、讨论女子教育问题、表达对孔子的态度……甚至有学生在《铭贤校刊》上公开反对教育总长章士钊“废除白话文”的教育政策:
白话文是我国近年来文化进步的先导,是将来文化进步的要素,欲统一国语,普及教育,非用白话文不可。自从提倡白话文一直到如今,到处风行,除了几个迂阔古老的人物外,没有不赞成许可的,也没有不用的。现在教长下令禁止,莫非教长以为白话文有害于中国文化吗?那么,但丁和威克列夫都是世界的大罪人了。【李书春:《几句不满意的话》,《铭贤校刊》第2卷第1期,1925年,第1—2页。“威克列夫”应为约翰·威克里夫(John Wyclif),约1330—1384,英国经院神学家,翻译家,基督教改革运动先驱,他的圣经译本使用了大量的英语俗语和方言,使英国人人看得懂圣经,为英国宗教、语言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王哲甫在铭贤中学受到了“五四”启蒙观念的熏陶,在《铭贤校刊》锻炼了写文章的能力,强化了他对白话文、新文学的认识。他在这里奠定了写作《中国新文学运动史》的部分思想基础。
(二)左翼思想、平民情结
通过梳理史料,我们可以在铭贤中学的教育中找到王哲甫左翼倾向的思想来源。《铭贤校刊》第4卷第1期发表了铭贤中学文学教师白序之的《革命的文学》,反映了该校教师对待新文学的态度。白序之认为,人要有自己独立的思考,“唯真正艺术家才配称得起革命家”。【白序之:《革命的文学》,《铭贤校刊》第4卷第1期,1927年,第4页。】面对革命的要求,他认为文学性始终是第一位的。在文章中,白序之引用了郭沫若《艺术家与革命家》与郁达夫《艺术与国家》两篇文章,来说明文学与革命的关系之密切。【白序之:《革命的文学》,《铭贤校刊》第4卷第1期,1927年,第5页。】白序之是新式教师的代表,他倾向于左翼文学革命思想。白序之对铭贤学生有很深的影响:
……白老师受五四爱国运动影响和新文化运动思潮影响,在课堂上大讲五四爱国运动和白话文学的重要性,宣传陈独秀、胡适文集以及《红楼梦》等白话小说,对受到五四爱国运动洗礼的铭贤学校学生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信德俭、温永峰、方亮等编:《学以事人 真知力行:山西铭贤学校办学评述》,北京:中国社会出版社,2010年,第93页。】
据铭贤中学毕业生李有义回忆,他于1926年入校,白序之是他的国文老师。【张江华:《李有义先生访谈录》,揣振宇、华祖根编:《中国民族研究年鉴·2002年卷》,北京:民族出版社,2003年,第427页。】据此推断,白序之至少自1920年一直到1926年均在铭贤中学教书。王哲甫1923年中学毕业,1925年离开铭贤进入燕京大学读书。可以推断,白序之教过王哲甫的可能性非常高。
王哲甫在《中国新文学运动史》中,显露出对左翼文学思想的主观欣赏态度。最突出的,就是他与白序之一样,对革命文学评价甚高,尤其对郭沫若、郁达夫二人,他多次在著作的不同地方不吝盛赞。【此类评价有:“国内的两大文学团体,一是文学研究会……其一是创造社……这两大团体除了郭沫若以外很少有革命的热情。……感受这种革命怒潮最强而最先转变方向的常推创造社郭沫若一流人。”(第70—71页)“像郭氏这样有血性的人,真正是不可多得。”(第103页)“然而他(郭沫若)的超越时代的思想,是无人不承认的。……他是我国的拜伦,他的伟大的反抗的精神,是任何人比不上的。”(第305页)“郭氏……如黑夜中的火炬,使每个青年的读者都为他那烈火般的热情所激动,所熔化。他是天才的作家,同时也是实行的革命家。”(第152页)“总之郁氏在近十年的文坛上,很占重要的位置。许多苦闷的青年,崇拜他若恩师。若只就小说而论,他的成就,尚在郭沫若以上。”(第154页)见王哲甫:《中国新文学运动史》,北京:杰成印书局,1933年。】
在赞美创造社诸人革命的努力之外,王哲甫还以他们为标准来衡量、评价其他文学家。例如,他认为茅盾、巴金等人尚不够普罗文学化,他们二人是小资产阶级的中心:“此外还有所谓小资阶级的文学,是以茅盾及巴金为中心的。他们可说较中间派为前进,意识上较中间派文学为正确,对于普罗文艺也表示同情,却还没有普罗化。”【王哲甫:《中国新文学运动史》,北京:杰成印书局,1933年,第91页。】
“五四”启蒙精神与左翼革命思想、基督教会理念的共同价值取向之一,就是对平民的关怀。这一点在铭贤中学有着突出的表现。
在《铭贤校刊》上,小学一年级的学生可以写《我的家庭》(郭家英)、可以作诗(《果树》陈兴邦)、可以写故事讨论“自由也需有轨”的问题(《自由和轨道》王万春),更能发表《对于胶济铁路的一点感想》(高钟毅),参与讨论时政。在这样的风气中,学生讨论国家前途,有支持无产阶级革命打倒帝国主义的(《无产阶级革命与中国国民革命》张卿云、《怎样打倒帝国主义》郝宝全),也有否定共产主义的(《共产主义不可行于中国》尹致祥)。可以说,文章无禁区,创作很自由。铭贤中学还很注重实践,时常组织学生去学校周边农村,实地帮助农民工作,或做学术调查。在这样的背景下,出现了王哲甫《铭贤学校附近之冬春无雪雨的平民生活》、杨蔚《太谷社会生活的状况》等同情平民疾苦的文章。现实的残酷激发了学生的平民关怀意识,使他们在这所“洋气”的学校里不忘国家人民的艰辛。这也是这所教会学校以“学以事人”为校训的生动体现。【王哲甫在《铭贤学校附近之冬春无雪雨的平民生活》中说:“太谷县本来是本省商业之中心,人烟稠密,居民殷富,不亚通都大邑。可惜近年来因兵燹的影响,受鸦片的流毒,昔年富庶之区,竟变成今日荒凉凄楚,满目萧条的景象了。……他们生活的状况,不时触动我的眼帘,只觉得一般平民的生活,是最可怜的。……河南遭了兵燹的浩劫,流氓丐妇,向这不能自存活的太古沿门乞食,如何能接济生命呢?……再看了这一般饥寒的苦同胞,几乎无泪可挥。民国的国民,眼见的是这样生活,我虽不是□(原文无法辨认——本文作者注)侠,也得写出来,少豁一豁胸中忧愤之气,唉!可怜!”见《铭贤校刊》第2卷第1期,1925年,“调查”栏第3、4页。】
有了同情平民的思想做基础,王哲甫的文学思想就自然倾向于平民文学。他在《中国新文学运动史》中有一段这样的话:
第一平民文学应以普通的文体,写普遍的思想与事实。……普通的男女是大多数,我们也便是其中的一人,所以其事更为普遍,也更为切己。我们不必讲偏重一面的畸形道德,只应讲说人间交互的实行道德。因为真的道德,一定普遍,决不偏枯。……第二,平民文学应以真挚的文体,记真挚的思想与事实,既不坐在上面,自命为才子佳人,又不立在下风,颂扬英雄豪杰。只自认是人类中的一个单体,浑在人类中间,人类的事,便也是我的事。
【王哲甫:《中国新文学运动史》,北京:杰成印书局,1933年,第8页。】
这段话虽然是王哲甫对周作人《平民的文学》一文观点的总结,但也能看出他对待新文学的态度和倾向。他在《中国新文学运动史》第一章“什么是新文学”中梳理了胡适、陈独秀、茅盾、周作人、郭沫若、成仿吾等人的新文学观,很明显看出来,他的“平民文学”观是对陈独秀等人革命文学观的继承和发扬。【王哲甫:《中国新文学运动史》,北京:杰成印书局,1933年,第8页。】
由于“五四”启蒙思想中包孕着平民关怀意识,王哲甫接受整个新文化思潮影响时自然接受了这方面的影响。他的平民文学观是“五四”启蒙价值观、教会服务社会意识、学校思想氛围影响和自身思想综合发展的结果。他的文学思想的形成,离不开铭贤中学新文学教育的影响。
(三)基督教的影响与王哲甫对待翻译文学的态度
铭贤中学这所教会学校对王哲甫的影响,还表现在对其基督教及翻译文学的态度上。铭贤中学的宗教氛围比较浓厚,学生中有布道团、证道团等组织。燕京大学宗教学院与铭贤中学的宗教往来活动也较多。这为铭贤学生入读燕大提供了良好的上升通道,而燕大很多毕业生也选择铭贤中学为服务对象。
白序之和于赓虞都是燕京大学的毕业生,他们大学毕业之后先后来到铭贤中学任教。王哲甫从燕大毕业后也回到母校铭贤中学教过学。暂无证据表明王哲甫皈依基督教,但基督教对王哲甫产生过切实的影响。中学时,他曾以《忏悔》为题,在《铭贤校刊》发文反思自己“灰色的人生观”【王哲甫:《忏悔》,《铭贤校刊》第3卷第2期,无出版日期,该文第2页。】。基督教不但影响了王哲甫,还给了他独特的新文学研究眼光。在《中国新文学运动史》第二章“新文学运动之原因”中,王哲甫将“西洋文化的输入”源头追溯到基督教的传入,注意到了《圣经》的翻译对白话的影响:“自从基督教传入中国,教会学校设立于各地,一方面固然在宣传圣教,另一方面,西洋的学术文化也因之介绍过来不少。”【王哲甫:《中国新文学运动史》,北京:杰成印书局,1933年,第22页。】“基督教圣经的翻译,为要使一般平民都容易明了,所以译文极其明白浅显,可以为白话的模范。”【王哲甫:《中国新文学运动史》,北京:杰成印书局,1933年,第22页。】“当明末欧洲人初来中国的时候,因华语华字难记,便利用罗马字母代替华字,已经伏下改革的动机。”【王哲甫:《中国新文学运动史》,北京:杰成印书局,1933年,第24页。】王哲甫将基督教称为“圣教”,肯定基督教在传播西方文化中的积极作用。这表明,他内心对基督教的接受已达到一定程度。他能注意到传教士对中国文字的改革、圣经翻译对白话的影响以及西方学术文化输入的作用,显示了他认同基督教之后所获得的独特的研究视野。基于宗教的视野,他才能在新文学研究史著中给予翻译文学以重要地位——设立专章。这一点让他与许多同期新文学史家截然不同,也使得他的新文学史著有了独属于自己的韵味。
在《中国新文学运动史》中,他对当时政治、经济等社会形势的观察不乏流行的时代偏见与事实错误。相较对政治、经济等社会形势的独特看法,王哲甫对翻译文学的观察显得相对更为客观。在不涉及社会观察的部分,王哲甫的论断较少左倾,相对中立;在文学研究部分,翻译文学部分更少时代流行话语的痕迹。
《中国新文学运动史》中部分段落充满了“帝国主义”“北洋军阀”“封建社会”“阶级革命”……的流行论调。王哲甫不是革命家,也不是革命文学家,他是一个受过系统学术训练的高校毕业生,也是一个文学研究者,他的这些政治、经济言论与其说是独立观察,不如说是人云亦云。他对近代史实认识不够清晰,有些盲目跟从时髦言论。因此,他的社会观察也很难说得上深刻、专业,这也有损这部文学史著的分量。而一旦回到文学研究部分,他敏锐的文学感受又开始发挥作用,这为他的史著增添了一部分值得保留的历史价值。按照他的社会观察方法,这些资本主义国家是面目“狰狞”的帝国主义,那么中国新文学的源头之一——西方文学的输入岂不是“文化侵略”?传教士们岂不是帝国主义的“走狗”“文化爪牙”?相反,王哲甫并未按照流行的那一套革命语言对待翻译文学。王哲甫在“翻译文学”部分能保持清醒,很可能是基督教强力影响的结果。铭贤、燕大两所教会学校的熏染,让他在内心认同基督教。在此基础上,他才会在充满歧见的时代言论中注意到基督教对近现代中国文学的正面作用。
(四)“整理国故”的执念
王哲甫倾向于新文学,但又不完全否定旧文学。他秉持“重新估定一切价值”的“五四”启蒙精神来研究中外文学,态度相对客观。在对待中国传统文学上,他主张“整理国故”——
新文学运动成功以后,文学家的责任日渐加重,除了介绍外国文学,创作新体作品外,又加了一种整理旧文学的责任。中国的文学,已经有四千余年的历史,有许多不朽的作品,被埋没在乌烟瘴气的烂纸堆里,从不被人注意的,也有许多文学上的争讼,至今没有解决的,所以整理国故的运动,在今日是刻不容缓的事。
【王哲甫:《中国新文学运动史》,北京:杰成印书局,1933年,第281页。】
但是,“整理国故”为何忽然成了“责任”,为何是“刻不容缓的事”?当年胡适提出“整理国故”的口号,就遭到很多人的反对。无论胡适怎样呼吁,对于要求“进步”的青年来说,重回故纸堆无论如何是一种“退步”的表现。况且,王哲甫对郭沫若的评价远在胡适之上,这样的言论在《中国新文学运动史》中并不鲜见。他认为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等文章“有些是很幼稚不适用的”【王哲甫:《中国新文学运动史》,北京:杰成印书局,1933年,第58页。】,胡适的新诗“并不算是成功”【王哲甫:《中国新文学运动史》,北京:杰成印书局,1933年,第100页。】,《尝试集》也“并不见得怎样精采”【王哲甫:《中国新文学运动史》,北京:杰成印书局,1933年,第100页。】。而郭沫若的小说“在表现的技术上,没有多大的成就”【王哲甫:《中国新文学运动史》,北京:杰成印书局,1933年,第152页。】,却成了“天才的作家”【王哲甫:《中国新文学运动史》,北京:杰成印书局,1933年,第152页。】,“他的超越时代的思想,是无人不承认的。……他是我国的拜伦,他的伟大的反抗的精神,是任何人比不上的”【王哲甫:《中国新文学运动史》,北京:杰成印书局,1933年,第305页。】。为何王哲甫接受了胡适的“整理国故”论,反而忽略了郭沫若在《整理国故的评价》里提出的反对意见?
王哲甫受古典文学教育影响较大,他在个人阅读实践中感受到传统文学的价值所在,打下了捍卫传统文学的思想基础。王哲甫很可能受过私塾教育。“五四”运动爆发的时候,王哲甫刚刚进入铭贤读书。【在此之前,王哲甫的学前教育有可能是私塾教育。他的铭贤中学校友王家驯曾经回忆:“那时乡村间的私塾,都请的是些三本书的冬烘先生,只叫念,永不讲。闹得我头昏。现在很觉的读教科书,比那不讲时候,容易记的多。”(王家驯:《语体文的我见》;《铭贤校刊》第1卷第2期,1924年,第39页。)王哲甫比王家驯大两岁,在王哲甫的学前阶段,进私塾读书比入新式学堂的可能大得多。参考其他铭贤中学的学生经历,如李有义1912年出生,1926年考入铭贤中学,7岁左右接受私塾教育。(张江华:《李有义先生访谈录》,揣振宇、华祖根编:《中国民族研究年鉴·2002年卷》,北京:民族出版社,2003年,第427页。)王志均1910年出生,1926年考上铭贤中学,他六岁读的也是私塾,老师是前清举人王敦临。见任立斌:《现代消化生理学的开拓者与奠基人王志均》,《文史月刊》2021年第4期。】铭贤中学的国文教师有两位是前清教师,侯之麟是前清贡生,陈绍德是前清举人。【《本校职教员衔名录》,《铭贤校刊》第1卷第2期,1924年,第30页。】这可是当地最具现代化气息的教会中学。
1925年的《铭贤校刊》第2卷第1期刊登了一篇王哲甫的《本校国学研究会成立记》的报道文章。【王哲甫:《本校国学研究会成立记》,《铭贤校刊》第2卷第1期,1925年。】王哲甫担任国学研究会书记,并由他撰文记录。文末附有各教师讲授科目。侯寿千(即侯之麟),主讲《书经》;徐正之讲《中庸》;李墨斋讲《春秋左传》;王重庭讲《庄子》;燕京大学毕业的白序之讲《诗经》。国学研究会几乎汇集了全校的国文教师,王哲甫能在该会担任书记,说明他对国学还是很认同的。
王哲甫对传统文学有着较深的感情。他在《燕大月刊》上发表过一篇《梦与文学》的文章,历数中外文学中与梦有关的文学作品。文中,他在中国古典文学部分提到了李白、杜甫、陈与义、李后主、苏轼、庄子、金圣叹等作家,以及《西厢记》《长生殿》《红楼梦》等作品,展现出他对中国传统文学各类型作家作品的熟稔与喜爱。与其说他对传统文学怀有深情,不如说他要用五四精神去“重估”古今中外一切文学作品。在价值排序上,“五四”启蒙精神始终在他心中占据主要位置,他认为:“提倡国学使青年对于旧文学也有相当的根柢,本是一件好事情,但是后来发生各种流弊,使青年把许多有用的光阴,都消费在故纸堆中,找不出一点头绪,反把一些世界最新的学术耽误了。”【王哲甫:《中国新文学运动史》,北京:杰成印书局,1933年,第284页。】王哲甫频频“回望”旧文学,并不仅仅是对经典知识的怀恋,而是他要用现代人的眼光,重新梳理已有的知识,为现代青年提供精神资源。铭贤中学的国学研究会成立的宗旨即是“研究国学,介绍近代国学著作藉以整理思想,从新估定价值”。【王哲甫:《本校国学研究会成立记》,《铭贤校刊》第2卷第1期,1925年。】这种对待国学的态度和观点,应该是铭贤中学师生的共识。他将这个态度带进了他的新文学史著中,他对“新文学”的理解也是从这个角度出发的——“我以为文学本没有新旧之别,所谓新文学的‘新’字,乃是重新估定价值的新,不是通常所谓新旧的‘新’。”【王哲甫:《中国新文学运动史》,北京:杰成印书局,1933年,第13页。】由此观之,王哲甫“整理国故”的观念大体上是在铭贤中学形成的。
在铭贤中学的新文学教育与校园文化熏陶下,王哲甫接受了“五四”的启蒙价值观,形成了他对平民始终报以深切关怀的情结,对翻译文学和“整理国故”均有自己的看法,初步建立了自己的新文学观。这些思想均在他的《中国新文学运动史》中有所体现。这为他以后写作《中国新文学运动史》打下了重要的思想认识基础。
二、王哲甫的大学经历与新文学教学实践
1925年,王哲甫从铭贤学校大学预科毕业,同年考入燕京大学国文学系。在燕大的第一年,他向母校铭贤中学校刊投了两篇文章。一篇是《人生》,感叹“现今在北京住久了也觉著没有兴味。人生也不过如此”。【王明道:《人生》,《铭贤校刊》第2卷第2期,1925年。】一篇是《忏悔》,表达对友情的失望与痛苦:“甚么朋友呵!甚么兄弟呵(原文无标点)只不过是互相利用欺人自欺的把戏而已,真正推心置腹的朋友,古今来能有几人?”【王哲甫:《忏悔》,《铭贤校刊》第3卷第2期,无出版日期,该文第3页。】他爱好文艺,思虑敏锐。入学第二年,他逐渐开始在燕京大学刊物上投稿,并参与编辑活动。1927年他担任《燕大月刊》编辑部“比较宗教”编辑员,先后在《燕大月刊》上发表了《梦与文学》《刘伯温评传》等文章。1928年《燕大月刊》全体编辑部成员换届,王哲甫也结束了他在燕大的编辑活动。同年,他从燕京大学国文学系毕业,返回铭贤中学担任国文教师。
王哲甫入学之时,燕京大学已汇集了周作人、冰心、杨振声、熊佛西等一大批新文学家担任教员。他们所开的课,有很多与新文学有关。例如,冰心负责“习作·新文学”组;周作人开设“近代文学”“新文学之背景”课,他在课堂上将新文学家胡适、俞平伯、叶圣陶,还有他的学生冰心,介绍给学生;杨振声的课在中外文学作品的对比阅读中,寻找新文学发展之路。王哲甫进入燕大不久,燕大的课堂已经具备了一定的新文学氛围。
朱以书是王哲甫的同学,林培志比他俩都低一届。他们在燕京大学读书时均参与过《燕大月刊》的编辑工作,是校内新文艺活跃分子。朱以书毕业后在京津各大中学校开设新文学课程,成为戏剧专家;林培志毕业后,回到母校教授“新文艺习作”课。他们用在大学所学的知识为新文学在教育系统中的传播做出了自己的贡献。在这一点上,王哲甫的人生轨迹与朱、林二人相同,他在毕业后也在学校中讲授新文学。王哲甫、朱以书、林培志都是燕京大学培养出的新文学教员。
由于在燕京大学读书的经历,王哲甫和他的老师白序之对冰心评价很高。据李有义回忆,白序之常常将冰心的作品推荐给自己的学生——
我最怀念我的中学语文老师白序之先生,他是燕京大学中文系的毕业生,也是我的恩师谢冰心女士的同学。他的确是一位循循善诱、诲人不倦的好老师,不仅在班上讲课文,还启发学生的思考,常要求学生自己解释课文,训练学生的口才和思维能力。他也介绍一些参考书,要求学生去读,……白序之老师也是把谢冰心作品介绍给我的第一人。谢冰心的《寄小读者》是他借给我看的。【张江华:《李有义先生访谈录》,揣振宇、华祖根编:《中国民族研究年鉴·2002年卷》,北京:民族出版社,2003年,第428页。】
教师们的文学思想势必影响学生。白序之对冰心的推崇,与王哲甫在《中国新文学运动史》中对冰心的高度评价具备一致性:
在中国新文学运动的初期,在文坛最负盛名的女作家,要推谢冰心女士了。她的真挚的心情,丰富的想象,与横溢的天才,曾惊动了万千的读者。她是新文学运动中最早的,最有力,最典型的女诗人,几乎是谁都知道诗。她的诗集虽只有《繁星》、《春水》两个小册子,但她在文坛上已有了不朽的地位。【“几乎是谁都知道诗”有可能是印刷错误,应为“几乎谁都知道她”或“几乎谁都知道她的诗”。王哲甫:《中国新文学运动史》,北京:杰成印书局,1933年,第105页。】
周作人、冰心等人未在《中国新文学运动史》中被戴上与茅盾、巴金一样的“小资产阶级”帽子,反而享受高度评价,这与王哲甫在燕京大学的求学经历不无关系。王哲甫在燕京大学接受了比中学阶段更为系统的新文学知识训练与思维训练。
王哲甫毕业后回到铭贤中学教学,开始了他的新文学教育实践。据《铭贤校刊》记载,王哲甫在铭贤中学被选为《铭贤校刊》文学编辑及编辑主任。【《校刊社职员改选》,《铭贤校刊》第5卷第2期,1928年,第21页。】他还曾担任过铭贤中学的法文教员。【山西省立教育学院编辑委员会编:《山西省立教育学院一览》,山西省立教育学院发行,1934年3月,见“前任职教员一览”“王明道”条。】1930年铭贤中学的“新文学”课可以确定是由王哲甫教授的。正如上文提到的,1930年的铭贤中学《高级中学国语课程表》中,学生要读的书目包括胡适、鲁迅的作品,郭沫若的《文艺论集》《橄榄》,郁达夫的《寒灰集》,张闻天的《旅途》等新文学作品。这与他在《中国新文学运动史》中对胡适、鲁迅及郭沫若、郁达夫等人的推崇完全一致。更巧合的是,王哲甫在《中国新文学运动史》中,同样重点介绍了张闻天的《旅途》。张闻天的《旅途》可能是个“标志”。推崇这部作品的其他新文学教材并不多,由此可以断定铭贤中学的“新文学”课程由他教授。还有一个旁证,王哲甫在《中国新文学运动史》中说:“编著本书的计划,在三年以前我就有过这个意思。”【王哲甫:《自序》,《中国新文学运动史》,北京:杰成印书局,1933年,第1页。】该序文写于1933年7月28日,其所以会在“三年以前”产生著史的想法,很大程度上是因为铭贤中学的这门“新文学”课教学所需。当时,他在铭贤中学教授新文学课程,一边收集材料,一边积累教学经验。这为他以后在短短一年时间之内写出《中国新文学运动史》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正因为有了在铭贤中学教授新文学课程的经验,三年后王哲甫顺利任教于山西省立教育学院。【山西省立教育学院前身为山西省立国民师范学校。山西省立国民师范学校成立于1919年,是山西省为普及全省国民义务教育培养师资所设,也是当时全山西省最好的师范学校之一。1925年国民师范增设高等师范部国文系,1929年高等师范部独立,成为山西省立教育学院。该校在办学上思想自由、新旧并蓄,在动荡不安的时代大潮中,形成了自由而不散漫、朴素奋斗的良好校风。】虽然该校国学氛围浓厚,却对新学兼容并包。因此,王哲甫能够比较顺利前去任教。他对中国传统文学一直抱有“整理国故”“重估一切价值”的想法,也让他得以顺利融入这所学校。该校中文系课程与新文学有关的是“文学研究法”和“新文学研究”。文学研究法课讲述“新旧文学之体制派别与研究之方法”。而新文学研究课则讲述“新文学之起源、特质、个性、形式及趋势,并论其对于国家社会之影响”。【该学院设立文科、教育两科,中国文学、史学、教育三个系。中国文学系四年级设有“新文学研究”课。山西省立教育学院编辑委员会:《山西省立教育学院一览》,山西省立教育学院发行,1933年,第27、29页。】另外还有选读古今名著的“名著选读”。
新的工作环境,“压迫”着王哲甫拼尽全力撰写讲义。他在《中国新文学运动史·自序》中说:“这一年来我的全副精神几乎全用在编讲义上面。每天除了上四小时的功课以外,常是独自伏在书案上不息的工作。在晚上各寄宿舍的灯火已经熄灭,人们都已进入甜蜜的梦乡去了,我还是静默地写作,直到十一点钟才去休息。这样耗心血绞脑汁的工作,的确是太苦了,但我觉着这种生活才是真正有意义的生活,所以并不觉着怎样的困苦。”【王哲甫:《自序》,《中国新文学运动史》,北京:杰成印书局,1933年,第1页。】如此不惧艰苦编写讲义,除了责任感等主观因素,主要还是由于教学所需这个客观压力。三年前就想编著文学史,为何在新的单位工作一年即完成并出版?教育体制的制约是最重要的因素。当时山西省立教育学院的主持者郭象升,就特别重视教师的讲义,尤其是新来教师的讲义,他要重点考察。教师的讲义甚至还要过高年级学生这一关。
郭对老教师总是客客气气,因为绝大部分是自己摸到底细的好朋友;对新来的教师,要从谈话里琢磨他学养的功夫,尤其是他所编写的讲义。高师部讲义分铅印石印两种,高年级学生一看讲义的印刷,就能觉察出这份讲义的分量。这一着他从来没有说过,我亲自听到他面告教务处说,某某讲义定为石印,这不是钱的问题。对于几经修改较成熟的讲义,则列为丛书,由学院付印,如陈晋教授的《尔雅学》。【郝树侯:《山西省立教育学院概况》,《山西文史资料》编辑部编:《山西文史资料全篇·第三卷》,太原:《山西文史资料》编辑部,1998年,第487页。】
山西省立教育学院对教师讲义的重视可见一斑。郝树侯的《山西省立教育学院概况》附录了该校教师从1925年到1936年出版的著作,共计8人15种。其中有4种是该校讲义,王哲甫的《中国新文学运动史》就是其中之一。【该条目后面注明“学院讲义,北平自印”。郝树侯:《山西省立教育学院概况》,《山西文史资料》编辑部编:《山西文史资料全编·第三卷》,太原:《山西文史资料》编辑部,1998年,第492页。】这15种著作中,标明“自印”的只有3种。可见,出版讲义,是该校的一种“风气”,领导重视,同僚努力。即使“自印”,也要尽快印刷出版。
在“讲义”这一点上,山西省立教育学院和铭贤中学有了区别。可想而知,入职该校,王哲甫即面临编写、出版讲义的压力。他自己也意识到了这一点:“这一年来因担任山西省立教育学院的新文学功课,给我一个很好的机会,得以完成我数年来所计划的工作。”【王哲甫:《自序》,《中国新文学运动史》,北京:杰成印书局,1933年,第1页。】工作环境带来的著述压力“迫使”新教师尽快完成讲义的编写、出版工作。
对比“新文学研究”课程说明,《中国新文学运动史》并未完全按照讲课顺序编写。在章节设置和比例分配上,也不够均匀。这部文学史更像是他在教学经验与讲义的基础上加工而成的一本著作。与苏雪林的《新文学研究》、废名的《谈新诗》等新文学教材比起来,《中国新文学运动史》的学术性、著作性相对更强。
教育制度的强大制约内含着对教员的苛刻要求。这种要求包括准时上课,将知识系统地、详略得当地传授给学生,编写讲义,推进学术研究,等等。在这种环境下,并不是每人都能胜任“教员”这份工作。过于浪漫、散漫的文士豪杰,常常难以在讲台上驻留太长时间。能在社会、文学市场上博得响亮名声,却并不一定能做一名合格的教员。有些浑身散发光芒的作家常常在大学里感到压抑和压力,也难以长期在高校任教,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教育体制的这种内在制约。从这个意义上讲,如果没有任教的经历,也就没有《中国新文学运动史》的产生。
三、结束语
王哲甫及其新文学教材《中国新文学运动史》是中国现代新文学教育的产物。在已有的研究成果中,对王哲甫其人其书思想来源的研究相对较少,对他的新文学受教育经历及其新文学教育实践的动态考察也相对缺乏。
王哲甫从小受中国传统文学影响较深。铭贤中学让他逐渐认识到白话文的价值,使他产生了对新文学的兴趣及认同感。铭贤中学的文学教师白序之等人对王哲甫的左翼思想、平民情结等影响深远。他在这所中学受到“五四”启蒙精神、左翼革命思想、基督教会理念的熏陶,并将对平民的关怀带入到《中国新文学运动史》中。他在这部著作中为“翻译文学”设立专章,并且尽力避免使用流行的革命语调评价外国文学,这与铭贤中学、燕京大学浓厚的基督教氛围以及他内心对基督教精神的高度认同有密切关联。他带着“重新估定一切价值”的“五四”启蒙精神“整理国故”,也是在铭贤中学形成的。燕京大学的新文学教育使他对中国新文学有了更深刻、更系统的认识。在他的著作中,对周作人、冰心等人的评价明显中立了很多。《中国新文学运动史》的部分文学思想、内容是王哲甫在铭贤中学、燕京大学读书过程中所奠基、产生的。王哲甫和他的《中国新文学运动史》思想来源,离不开他所受的新文学教育。
王哲甫毕业后在铭贤中学、山西省立教育学院教授新文学课程。从学生到教师的身份转化过程中,诞生了新文学教育的人才和教材。他在铭贤中学教新文学课程的时候,产生了写作新文学著作的想法;在山西省立教育学院,由于“教学”这个具备强制约束力的外在因素,“迫使”他将三年前的想法付诸实践,在极短的时间内,将他一直以来对新文学的认识系统地整理出来,从而产出一部教材式的《中国新文学运动史》。
从动态的角度考察,他的新文学教学经历促进了《中国新文学运动史》的产生,他的《中国新文学运动史》出版之后,又是新文学教育的重要参考资料,成为新文学教育链条上的重要一环,反向哺育了新文学教育与教学。以此为个案,可以窥见我国民国时期新文学教育的知识产生与互动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