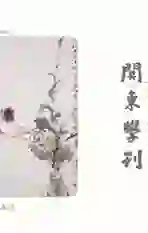跨文化翻译视角下《茶花女》在中国和土耳其的传播与接受
2024-09-29卢梦莎
[摘 要]19世纪末,《茶花女》在中国和土耳其的译作引起了巨大轰动。尽管中国和土耳其在地理位置上相隔甚远,但都在数年内相继翻译了这部作品,并在随后各自创作了本土版本。本文通过对中国译者林纾与土耳其作家米塔特的《茶花女》翻译进行研究,从语言和文化角度分析其在不同语境中的翻译与接受过程,并探讨两位译者对原作的理解与诠释,能够揭示跨文化翻译中文本的再现方式以及其在不同文化价值观下的命运。
[关键词]《茶花女》;林纾;土耳其文学;跨文化翻译
[作者简介]卢梦莎(1993— ),女,复旦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博士研究生(上海 200433)。
引言
在翻译史上有一些文本在被翻译之后,在译入语的社会文化语境中比译出语的社会文化语境中更受欢迎。它们不仅很快就成为时代的热点话题,且在翻译之后的很长时间里,还是会被学者提及并引发进一步的讨论。林纾与王寿昌在1898年【关于译述时间,学界有不同说法,如胡孟玺表示《茶花女》译于1891年,寒光在《林琴南》中说是光绪十九年(1893),高梦旦说是光绪二十五年(1899),阿英在《关于巴黎茶花女遗事》一文中说是在1898年所译的。另外还有黄濬、杨荫与当代学者曾宪辉认为译于1987年。因此林纾翻译《茶花女》的时间应该是1897、1898年左右。】合译的《巴黎茶花女遗事》便是其中绝佳的例子。译本出版之后大受欢迎,受到中国读者的高度评价。林纾之后的不少人也重新翻译了这部小说,陆续出版了三四种新的译本【素隐书屋1899年本,玉情瑶怨馆1901年本,文明书局1903、1906年本。】,与此书相关的演出更是不胜枚举。
几乎在林纾翻译《茶花女》的同一时期,在距离中国十分遥远的一个国度,有另外一位作家也注意到小仲马的《茶花女》,他就是土耳其作家阿合麦特·米塔特【阿合麦特·米塔特(Ahmet Mithat Efendi 1844—1912):土耳其作家、翻译家、报人、出版商。他以在奥斯曼社会中传播现代思想而闻名,被视为奥斯曼文学现代化进程中的关键人物。他的著作通常涉及社会议题,并强调了教育、道德和改革等方面的社会需求。】,米塔特于1880年翻译了《茶花女》,译本一出版即引起巨大反响,获得读者的高度评价。不过,引人瞩目的是,19世纪80年代的奥斯曼帝国(土耳其),与中国一样,也是一个比较保守、对传统文化以及道德价值观高度重视的社会。将小说视为教育百姓的最佳媒介的米塔特,为何觉得这部小说对社会有利?在这种社会背景下,米塔特与林纾为何会选择翻译《茶花女》,其中包含了许多触动当时中国与土耳其社会敏感神经的议题,如“恋爱自由”“妓女”以及“异教”等,这些议题中有许多不符合本土文化的因素。除此之外,翻译《茶花女》之后,两位作家各自创作了类似《茶花女》的作品,即林纾的《柳亭亭》和米塔特的《苦之心》(Mihnetkesan)、《才十七岁》(Henuz On Yedi Yasinda),这些作品同样围绕着男主人公与妓女之间的爱情故事展开。总而言之,本文试图对跨文化翻译中的文本再现以及在文化冲突背景下文本的命运进行比较分析,并展示翻译与创作之间的密切关系。
一、《茶花女》与本土社会的交融与认可
法国浪漫主义小说家、剧作家亚历山大·小仲马,在1848年写作的《茶花女》,虽然不是法国经典作品,小仲马也不是西方一流作家,但无论在中国还是土耳其,经过林纾与米塔特有效的翻译策略,译作都受到两国读者很高的评价。对林纾《巴黎茶花女遗事》所产生的巨大影响力的评论不少,在当时出版的报纸、杂志,以及私人的诗集中,很多人写诗抒发自己的读后感【例如,严复1904年写的一首诗中有“可怜一卷茶花女,断尽支那荡子肠”一句。邱炜萲赞叹林纾说:“以华文之典料,写欧人之性情,曲曲以赴,煞费匠心,好语穿珠,哀感顽艳,读者但见马克之花瑰,亚猛之泪渍,小仲马之文心,冷红生之笔意,一时都活,为之欲叹观止。”又说:“年来忽获《茶花女遗事》,如饥得食,读之数反,泪莹然凝栏干。”包天笑在《钏影楼回忆录》中还把《茶花女》称为“外国的《红楼梦》”。张静庐在《中国小说史大纲》中曾写道:“人情好奇,见异思迁,中国小说,大半叙述才子佳人,千篇一律,不足以餍其好奇之欲望;由是西洋小说便有乘勃兴之机会。自林琴南译法人小仲马所著爱情小说《茶花女遗事》以后,辟小说未有之蹊径,打破才子佳人团圆式之结局。”】。陈平原教授曾也表示,除了福尔摩斯之外,茶花女可以说是在清末民初的语境中知名度最高的外国小说人物之一。【陈平原:《二十世纪中国小说史》第一卷(1897—1916),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第11页。】总而言之,《巴黎茶花女遗事》译本的出版是近代中国文学翻译史上最具影响力的一次活动。与传统的才子佳人小说相比,它“‘令中国读者耳目一新’,‘为中国士人提供了一种新的审美参照系’”【韩洪举:《林译小说研究——兼论林纾自传小说与传奇》,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第138页。】。
《茶花女》在土耳其被翻译后,在土耳其文坛也引起不少人注意。米塔特翻译《茶花女》之后,不少土耳其作家对这部作品进行了重新翻译,并在他们的小说或书信中提到《茶花女》,表达了对主人公遭遇的同情和感动。在土耳其文学界,如同在中国文学界一样,后来创作的许多小说中都可以看到《茶花女》的影子。显而易见,《巴黎茶花女遗事》在当时强烈地打动了中国与土耳其读者的心弦。
纵观原文里包含着不少有悖于传统道德因素的《茶花女》,为何能在比较传统和保守的中国与土耳其社会获得如此高度的接受和赞扬,这在很大程度上与作家所采用的翻译策略有关。从林纾和米塔特的译本来看,他们对原文的翻译和改写显然处于不同的层次。林纾在翻译过程中,对原文进行了一种融入与和谐本土文化以及目标语言的翻译操作,他十分注意本土社会对小说内容的接受程度,尽可能地给中国读者创造了一个“能设想”的玛格丽特形象与容易理解的文本。首先,他对原本中的不熟之物进行了一种“本土化”的改写,如马克乘坐的马车在原本中写为“两匹栗色骏马驾着的蓝色小四轮轿式马车”,而这马车在林纾笔下却成了“油壁车驾二骡”,无法代替的某些不熟之物被直接删掉,如“开司米大披肩”“镶着宽边的绸裙”“厚厚的暖手笼”等中国读者不太熟悉的物品都被林纾删除了。在译本中,删除或改写具体的“不熟悉的事物”,或者马克的外貌细节,是随处可见的,然而本文的主要关注点是跨文化翻译过程中文本再现的问题。因此,从道德角度审视原文的修改才是本文的核心关注点。
众所周知,孔孟之道与程朱理学对林纾的影响比较深刻,因此林纾把纲常名教看得比较重,在他的文本中也经常可以看到“孝”“贞”“忠”“悌”等伦理道德观念。就是这个原因,使得原文中的马克跟林纾翻译出来的马克形象之间有所不同。在原本中马克有不少非道德、非贞节的行为和情节,但这些情节却大部分都被林纾删掉了。由于马克社会身份的特殊,林纾不得不对她进行一种“消去”。林纾对中国社会的倾向和禁忌特别了解,因此他在翻译的过程中采取了将马克“贞洁化”的翻译策略。例如:
你认识一个名字叫玛格丽特·戈蒂埃的女人吗?茶花女吗?就是她。熟悉得很!熟悉得很!他们说这句话的时候,有时脸上还带着那种含意明确的微笑。【[法]亚历山大·小仲马:《茶花女》,王振孙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3年,第27—28页。】(王振孙译)
一日,余问一友人以马克事,友人曰:“即所谓茶花女者乎?我固识之”。余问女之平生如何。友曰:“视他人略聪慧耳”。【[法]亚历山大·小仲马:《巴黎茶花女遗事》,林纾、王寿昌译,杭州:浙江出版集团数字传媒有限公司,2013年,第31页。】(林纾译)
“熟悉得很!熟悉得很”这句话有时会伴随着一个意味深长的微笑发音,而这个微笑让人对其含义毫无疑问。【Alexandre Dumas Fils,Kamelyali Kadin,Ahmet Midhat trans.,Istanbul:Akademik Kitaplar,2015,p.27.本文所引用的米塔特的言论和著作的中文翻译,均为笔者所作。】(米塔特译)
可见,为了维持马克之贞洁形象,林纾将原本中“熟悉得很”一句所表达的含义部分全部进行了删除。与此相比,米塔特则直接翻译了原本中的样子。
又如,亚猛看到马克一个人回家心里很高兴,就自言自语地说:
她一个人回家可能是偶然的,但是这个偶然使我觉得非常幸福。【[法]亚历山大·小仲马:《茶花女》,王振孙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3年,第50页。】
林纾把这句话删除后,直接开始翻译后面的部分,尽管他删掉的只是一句话,但在笔者看来这也是很值得留意的一个细节。因为林纾不希望让读者怀疑马克之贞,或者不希望让读者设想出一些非道德画面,他才有意地把这句删除了。反观米塔特,却把林纾删除的这部分也直接翻译出来了。
当我们看林纾的译本的时候不难发现,他极力把马克和“贞节”连在一起。原本中看不到的“贞”一词,在林纾译本中却屡次三番地出现。比如马克对亚猛说:
我既不是黄花闺女,又不是公爵夫人。我不过今天才认识你,我的行为跟你有什么相干,就算将来有一天我要成为你情人的话,你也该知道,除了你我还有别的情人。【[法]亚历山大·小仲马:《茶花女》,王振孙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3年,第73页。】(王振孙译)
马克曰:“我身非闺秀,而君今日方邂逅我,我何能于未识君前,为君守贞。”【[法]亚历山大·小仲马:《巴黎茶花女遗事》,林纾、王寿昌译,杭州:浙江出版集团数字传媒有限公司,2013年,第56页。】(林纾译)
如上所述,林纾为了维护马克的贞洁形象所下的功夫真令人瞩目。我们从慧云读《巴黎茶花女遗事》后所写的一首诗中,可以看到林纾所下的功夫没有白费:“病中咯血一声声,垂死频呼亚猛名。强起口口犹把笔,写将心事表坚贞。愿不从心伤命薄,几多苦恼有谁知?掷将性命惟拼诬,恨海情波岂尽期!”【慧云:《读〈巴黎茶花女遗事〉》,《国民日日报汇编》1904年第4期。】
在此值得指出的另一点是,林纾不仅仅把丑化马克的部分删掉了,还把亚猛呈现出的不符合中国社会理想中的男性形象的很多细节也删除了。例如,当亚猛在剧院看到马克与伯爵在一起时,感到不高兴,安慰自己说:“G伯爵在玛格丽特的包厢里出现是件极其平常的事。他过去是她的情人。既然我有一个像玛格丽特那样的姑娘做情妇,当然我就应该容忍她的生活习惯。”【[法]亚历山大·小仲马:《茶花女》,王振孙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3年,第93页。】在林纾的翻译中却完全看不到这句话,而且马克对亚猛说的前一句“乖乖地回到你的座位上去,再不要吃什么醋了”也被林纾删除了。另外一个例子是,亚猛说:“我爱的是玛格丽特·戈蒂埃,这就是说在巴黎,我每走一步都可以碰到一个曾经做过她情人的人,或者是即将成为她情人的人。”【[法]亚历山大·小仲马:《茶花女》,王振孙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3年,第124页。】在林纾的译本里,这句话也被删除了。林纾所做的努力不仅仅是为了隐瞒马克的非道德行为,同时也是为了隐瞒亚猛的过度浪漫、不顾男性自尊的行为。毫无疑问,无论林纾多尊重女性,他还是无法超越潜意识里男尊女卑的男权制度。诚然,这也有为中国读者的考虑所在。因为亚猛的很多行为,在比较保守的父权制社会中确实是无法让人接受的,林纾很可能也是担心读者对文本产生反感。同时,观察米塔特的译本可以发现,林纾所改写的部分在米塔特的译本中都保持了原文的直接翻译。
面对文本中的宗教话题,林纾与米塔特又有着不同的处理方式,而这一点是因为中国与土耳其有着不同的社会背景。首先,文本中出现的有关基督教的某些概念,如对上帝与耶稣的赞美与称呼,都被林纾通通删掉了,而在米塔特的译本中,这些内容却全部都被留下了。尽管当时的奥斯曼土耳其社会大部分信仰伊斯兰教,但事实上,基督教里很多关于圣人的概念,在土耳其人看来并不是禁忌话题;恰恰相反,在当地民众眼里,上帝与耶稣都是不可不敬的概念。对米塔特而言,翻译这些宗教话题并没有不符合土耳其本土文化以及民间信仰的一面,因此决定在原本基础上直接翻译。反观林纾的翻译,这些宗教话题对于崇拜孔孟之道的林纾来说,难免会引起心理上的抗拒。假如他照原本翻译了,很可能会引起当地社会的不理解,译出的文本不被社会所理解的危险,是很多译者都不希望看到的结果。
总而言之,从林纾与米塔特对《茶花女》的翻译来看,林纾对原文的改动比米塔特更多,而米塔特则展现了一种更忠于原本的翻译趋势。依笔者之见,产生这一差异的主要原因是他们在翻译《茶花女》时的初衷以及面对的不同社会背景。
首先,从他们翻译《茶花女》的初心来看,在某种程度上来说,林纾是比较随意地决定【关于林纾翻译《茶花女》的原因,有不少人表示其是“为了缓解妻子的去世”带来的痛苦。但张俊才教授在《林纾评传》一书中却表示,林纾在翻译《茶花女》之前,对翻译其实已经有过一定的尝试和准备。他在写给胡孟玺的一封信中,有一句“先母太宜人生时,颇喜纾所译小说,夜中恒听三鼓始寂”。他母亲是1895年去世的,可见他翻译《茶花女》之前对翻译小说已经有所尝试。】翻译这部作品的,而米塔特选择翻译《茶花女》背后是具有其特定目的的。米塔特开始连载《茶花女》之后,在其所创办的报刊《真理之抒发》上发表的一篇著者不明的文章中表示,翻译《茶花女》不是因为小仲马是大仲马的儿子,也不是因为他是法兰西学院的成员,而是因为小说内容所含的寓意才被翻译的。在《茶花女》连载完之后发表的另外一篇文章中再次指出,米塔特介绍小仲马的《茶花女》,旨在教育当时的奥斯曼社会。米塔特对文学以及小说的功能性的考虑,是他在原文的翻译中进行少量改写和删除的主要原因。他将小说看作教育百姓的一种媒介,因此他毕生从地理到科学、从文学到数学、从哲学到经济学如此广泛地涉猎中,翻译与创作出大量的作品。他认为文学应该教育人们、培养美德、激发美丽情怀。但在此需要强调,米塔特虽然提倡文学不应该宣传不良之事,但是在不良之中如果有寓意,为了提醒人们的话也可以写这些题材。这也就是他选择翻译《茶花女》以及没有改动太多的原因。在米塔特的译本中,被林纾删除的小仲马对妓女的同情言辞都得以保留。因为米塔特也特别同情妓女,并希望人人都可以帮助她们抛弃这种生活方式以及融入到社会中。他并没有试图将玛格丽特描绘成一个十分贞洁的女性,其目的只是想要指出妓女所面临的问题。相比之下,林纾更关注译本在中国读者中的接受程度以及本土文化的道德观念。他并没有像米塔特一样希望通过《茶花女》的翻译来教育社会,指出妓女问题,因此林纾对原作的修改也是出人意料的。
米塔特对妓女问题的关注并不是他对某一个特定女性群体的关注的反映。事实上,他是土耳其文学史上最早关注婚姻和女性社会地位问题的作家之一。他与林纾的思想观点之间有不少相似之处,他也主张女性教育的重要性,反对传统的包办婚姻。他在不少小说中讲述婚姻中女性被男性压迫的情景,并对此现象表示不满。他对女性充满同情,常常批评男性在婚姻中的不道德行为,并嘲讽那些要求女性如花似玉却自身无所作为的男性的奇特期望。他在作品中不仅强调女性教育的重要性,同时还把女性的经济独立等同于女性的自由来看。他借助茶花女的经历和感人的故事,揭示了妓女问题和女性在社会中的不幸境遇。显然,他对女性问题的关注远超林纾。在写作过程中,他特别注意所使用的语言表达,从未忽视女性读者的存在。然而,这并不是为了提高小说的销量或吸引更多读者,而是为了强调女性在社会中的地位和存在。他在作品中呼吁读者的时候,经常写到“karilerim”与“kariyelerim”,词根kari的意思是读者,前者的意思是“我的男性读者们“,后者的意思则是“我的女性读者们”。在另外一本书中,米塔特把“人类”这个词特意分开写为“insanoglu”与“insankızı”【“Insan”一词源自阿拉伯语,意指人类或人类群体。“Ogul”最初指的是不分性别的子女,意思是孩子,但后来更多用于表示“男性子嗣”。】。“insanoglu”的意思是人类,但后面的“ogul”词根表示男性,而米塔特自造的“insankızı”后缀的“kız”词根表示女性。由此可见,米塔特对女性的关注以及对男女平等问题的重视,并非仅限于口头上的空谈,而是贯穿于他运用的语言中,真实地反映了他对女性问题的关心和重视。他曾经处在一个“女性并不被视为作家的社会”当中,却坚定地支持土耳其第一位女性作家法特玛·阿里耶(Fatma Aliye Topuz)。他通过翻译、创作以及直接的“支持”来提升当时奥斯曼土耳其女性在社会中的地位和促进其在各个领域的发展。他对女性积极参与社会所做出的贡献是不容忽视的。
然而,《茶花女》正好传达出他所想传达的寓意。玛格丽特并不是自愿成为妓女的,她因为家庭原因最终走上了这条路。同时,她在恋爱过程中所展现出的自我牺牲精神和勇敢放手的性格,也是米塔特认可她的另一个原因。在米塔特看来,玛格丽特虽然是个妓女,但她自从爱上阿尔芒之后,便愿意摒弃所有的坏习惯,而和他过起了一种平静平淡的生活。阿尔芒的父亲在得知他们之间的关系之后,尽管当初曾羞辱玛格丽特,但后来在看到她为阿尔芒所做的自我牺牲之后,也向她道歉了。玛格丽特也履行了她对阿尔芒之父的诺言,离开了阿尔芒,最终心如死灰地死于结核病。【Harika Durgun,“Turkcede La Dame Aux Camelias Tercumeleri ve Hakkinda Yazilanlar”(在土耳其《茶花女》的翻译以及其相关评论),Turkluk Bilimi Arastirmalari,vol.45,2019,pp.82.】总而言之,面对像玛格丽特这样的女性,无论是在中国还是土耳其社会,都会引起人们的敬佩。显然,她的勇气和为爱奋不顾身的精神能够跨越文化和时代的背景,激起人们共同的认同和尊重。
二、追溯《茶花女》的遗迹:从翻译到创作
翻译与创作都是文学手段,现在比较容易分清两者之间的区别,但20世纪人们对翻译与创作的看法与当今社会不大一样。当时且不说普通老百姓,甚至很多士大夫、知识分子都说不清翻译与创作之间的关系。在“著述如云,翻译如雾”【陈平原、夏晓虹:《二十世纪中国小说理论资料(第一卷)1897—1916》,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315页。】的时代,著译往往合而为一,二者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然而,翻译文学往往是构成新文学的重要资源之一,它为文学创作提供主题、题材、表现手法等,从某种程度上来讲,翻译文学推进了文学创作的发展。除此之外,经过翻译,可以给原著在不同国度、不同社会、不同语境当中找到更多传播的机会。而有意思的是,有时候原本经过翻译之后,在目标语言文化中会得到比作品所在的原社会更多读者的认可,并产生更大的影响。
如前所述,林纾与米塔特先后翻译《茶花女》之后,在中国与土耳其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同时,《茶花女》对林纾和米塔特的创作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在他们后来的作品中或多或少可以看到《茶花女》的影子。首先,林纾翻译《茶花女》多年之后,自己也创作了一部书生与妓女之间的爱情故事——《柳亭亭》。这部短篇小说讲述了秦淮名妓柳亭亭与贵族青年姜瑰之间的爱情故事。换言之,《柳亭亭》是林纾心目中拥有美满结局的《茶花女》。与马克相似,柳亭亭也是被逼无奈才走进妓院的,因“父卒家贫”,她被家人“以术鬻于曲院中”。虽然在《茶花女》中亚猛不管马克社会身份仍愿和她在一起,但《柳亭亭》中的姜瑰却因“知一身为承祧主鬯之人”,而“不能娶妓自斩其祀”。此外,与崇尚个人自由、恋爱自由的亚猛相反,姜瑰是个孝子贤孙,担心“老父方严,决不能许”他和柳亭亭的这种关系。从某种程度上来讲,《柳亭亭》可以视为符合中国传统文化、道德价值观念的东方版《茶花女》。通过《柳亭亭》,我们可以看到林纾关于“在中国传统道德文化中如何避免《茶花女》的悲剧结局”的设定。在林纾笔下,姜瑰的父亲不但没有使柳亭亭离开他的儿子,反而亲自找柳亭亭“为吾子订婚约耳”。那在林纾眼里马克与柳亭亭的区别是什么?换言之,导致作为妓女的柳亭亭最终能拥有大团圆结局的原因是什么?首先,林纾在小说的开头就说明柳亭亭之父是名秀才,她“少受庭训,填词书画、皆能得古人遗法”。当姜瑰的父亲听到柳亭亭的名字时,他突然想起柳亭亭的书法和绘画,并问:“尚书公子斋中,有长笺细书,临褚河南真迹,下著柳亭亭者是乎?”“又有便面一方,上作龚半千山水,亦曰亭亭。究一人耶,两人耶?”【林纾:《柳亭亭》,林薇选注:《林纾选集》(小说·卷下),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70页。】姜瑰的父亲得知那些都是柳亭亭之作之后,他很赞赏,并说:“风尘中乃有此隽品!”林纾对柳亭亭这个人物进行了细致的刻画,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读者对柳亭亭的接受与认同。相比于马克勇敢追求爱情的性格,由于当时的中国社会环境容不下这样的性格,因此林纾选择强调更符合本土社会的特质,那就是“才华”。尽管传统文化中有“女子无才便是德”的观念,林纾却常常提倡女性教育的重要性。因此,他笔下的柳亭亭并不只是一个普通的娇美如花的姑娘,而且她字如褚河南、画如龚半千。如此一来,柳亭亭作为妓女的身份,就得到了其工书善画的补偿,转变为一个林纾理想中的女性形象。
林纾首先通过对一个妓女的美丽与才华和温文尔雅的形象的刻画,在读者眼里给柳亭亭奠定了一种初步的合法性。其次,他又通过中国传统文化自古有之的“纳妾”文化来转写《茶花女》的悲惨结局。当姜瑰之父听到儿子与一个妓女之间的关系时,他并不像阿尔芒的父亲那样彻底反对。恰恰相反,他表现得很开明、通达,认为以前古人以妓为偶是一件很常见的事情,儿子与妓女之间的关系并没有什么不道德的,既然“亭亭悦吾子,当为成之”。与此同时,他还不忘记克服时人关于“对妓女不育”问题的焦虑,说“凡妓女不育,皆静脉乱耳。吾精于妇科,治之当得子”。为了避免儿子相思成疾,他直接去柳亭亭家登门拜访,表明来意并约定婚姻。可见,林纾试图一举两得,他一方面让姜父以“让”的传统美德来维护其子与柳亭亭之间的“爱情”,让“父子之情当愈亲”,另一方面通过“纳妾”的方式来让这种爱情合法化。如此的安排,使林纾不再面临像他在翻译《茶花女》时所面临的那种“礼与情”的冲突,促使他成功地塑造出一个“不弃礼又不弃情”的空间。
当我们看土耳其作家米塔特时,会发现小仲马以及《茶花女》对米塔特创作的影响更明显。米塔特在1871年所撰写的短篇小说《苦之心》(Mihnetkesan)是土耳其第一部关注妓女问题的文学作品,因此在土耳其文学中占有比较特殊的位置。小说讲述了男主人公达克贝在青楼认识了一位姑娘之后,最终不仅把她从青楼中救了出来,还跟她结了婚。达克贝是个有学问的手工艺人。因为他喜好寻欢作乐,所以天天都不管不顾地生活,也经常去青楼。有意思的是,米塔特作为讲述故事的人,同时也把自己设定为小说人物之一,即主人公的朋友。有一日,小说人物之一的米塔特在酒店遇见愁苦的达克贝。当米塔特问起原因时,达克贝解释说,他在青楼听到一个十七八岁的女孩被母亲卖入青楼,感到非常怜悯,因此决定救她。此事让他意识到自己过去的生活多么空虚而无意义,他希望米塔特能帮助他与女孩结婚。尽管米塔特最初对婚姻的稳定性存有疑虑,但最终还是决定帮助他们。最终他们的爱情消除了米塔特的质疑,并有了大团圆的结局。小说的结尾部分,与小仲马相同,米塔特也在对妓女表示同情之后,希望“真主”可以引导并帮助那些像达克贝那样把珍贵的人生浪费在这种地方的人。
值得强调的是,小说中的达克贝不是以道德标准来评判妓女,而是从人性的视角去理解她们。他先阐述导致女人进入青楼的各种原因,接着提出应该如何对待这些不幸的女人,并且给出了避免她们沦为妓女的建议。小说的结尾部分,米塔特以作家的身份呼吁社会应该同情这群不幸的女人,并且帮助她们重新融入社会。土耳其当代著名作家唐帕纳尔在《十九世纪土耳其文学史》一书中指出米塔特的《苦之心》为他所在的时代带来了巨大的震动,并认为这部小说在当时的时代语境当中,不再根据传统习俗无条件地谴责卖淫,而是同情妓女并愿意分担她们的痛苦;在他看来,即使这种作品是受外界(西洋小说)影响创作的,它依然具有重要意义。随着《苦之心》的问世,土耳其文学引入了一个新的主题——同情心超越了源自宗教的道德观念。他认为这部作品是在土耳其文学中人性道德的初次觉醒。【Ahmet Hamdi Tanpinar,XIX.Asir Turk Edebiyati Tarihi(十九世纪土耳其文学史),Caglayan Publishing House,Istanbul,1988,p.289—290.】
在米塔特撰写《苦之心》的十年以后,1881年他再次撰写了一部关于妓女问题的长篇小说,名叫《才十七岁》。小说讲述了因为家境贫穷被父母卖给妓院的卡丽由琵的遭遇。小说名为《才十七岁》,是为了强调卡丽由琵被卖到妓院时只有十七岁。米塔特,这位喜欢将自己写进小说的作家,在这部作品中再次出现。男主人公阿合麦德【米塔特的全名是阿合麦德·米塔特,在小说中他以阿合麦德这个名字出现。】和他的朋友葫芦瑟某晚去看戏剧,由于外面下着暴雨且时间已晚,在葫芦瑟的建议下,他们决定在妓院过夜。阿合麦德在妓院认识了卡丽由琵,了解到她的遭遇后感到非常惊讶。原本对妓院和妓女怀有极大敌意的阿合麦德,开始同情和怜悯她们。小说的结尾,阿合麦德帮助卡丽由琵成功脱离妓院,并为她找到了一个好的归宿。
这部小说中充满了对妓女表示同情的言辞。米塔特通过阿合麦德之口,呼吁社会应当友善地对待这些不幸的女性。他对妓女的同情心及希望她们重新融入社会的愿望,与小仲马在《茶花女》中所展现的态度颇为相似。尽管《才十七岁》的主题与《苦之心》有相似之处,但两者之间依然存在显著差异。最为明显的区别在于,《才十七岁》的叙事表现出更为显著的排外倾向。叙述者表示卖淫行为及妓院的出现与西方国家有密切关联。他在小说中写道:“我说我们民族、伊斯兰教或奥斯曼文化中都没有这种恶俗现象,这些都是来自法兰西(西方)的。我说他们那些帽子【作者指的是西方人。】吧!这些帽子出现在哪里,哪里就产生恶俗。”【Ahmet Mithat Efendi:Henuz On Yedi Yasinda(才十七岁),Turkiye Is Bankasi Kultur Yayinlari,2019,p.122.】
值得注意的是,他不仅声称在伊斯兰教中不存在卖淫行为,还强调基督教中也没有。他表示:“我们本地的基督徒以前没有这种不良习惯,自从‘帽子的出现’,这些不良习惯也随之出现……我们本地基督徒中的一部分人在戴上帽子后,开始接受欧洲人的风俗……”他对基督教的强调有其内在用意,意在通过指出基督教的禁忌来提醒生活在奥斯曼土耳其的少数民族。显然,米塔特批判的并非基督教或异族,而是他对现代化过程中所带来的无节制和放纵行为的担忧。
此外,在《苦之心》中不太分明的妓女身份、民族、宗教信息等,在《才十七岁》中却很明显,卡丽由琵和阿赅尼都是少数民族,而且都是非穆斯林。同一个作家在间隔十年所写的两部小说,虽然讲述的都是大同小异的主题,但在后者的写作当中,作家所采取的写作策略很值得我们关注。作家虽然都想强调妓女问题,但与此同时他还特意暴露妓女的民族身份与这一问题的产生根源。从某种程度来讲,这是他应对文化冲突,同时维护自己以及本土文化的一种表现。首先从守护自己的角度来看,作家没有把穆斯林的奥斯曼女性设定为一个妓女形象,这不仅是因为作家自己不愿意这样安排,更大程度上是因为作家担心遭受社会的攻击。他之前曾因为在小说中设定了一些不符合社会道德的人物和行为而受到不少读者的批评和攻击。正如《苦之心》一样,作者本可以在不揭示人物民族身份的情况下叙述这个故事,但为何他选择了暴露其民族信息呢?与林纾相仿,米塔特在其翻译和创作实践中,同样注重维护本土文化的价值观以及国家安全。从时间上来看,米塔特写《苦之心》的1871年是奥斯曼帝国刚进入停滞时期,但还没有很明显地感受到帝国衰落的远景。因此,在作家于1871年写成的《苦之心》中,我们看不到对西方与异族的强调;但在创作《才十七岁》的1881年,人们更明显地感受到了西方对本土文化的危机,以及随着“西方化”现象先在少数民族之中的普及,很多变化都先在异族身上有所表现。一直很支持奥斯曼主义【奥斯曼主义主要主张建立一个多民族、多宗教的多元文化帝国,并在此基础上实现统一。】的米塔特,自然而然地担心这种现象。在某种程度上讲,《才十七岁》或多或少体现了米塔特对现代化的批评。
在文学史研究中,有些学者倾向于因为某些言论或文章而直接给作家贴上某些标签。正如林纾与米塔特,许多生活在“过渡时代”的传统文士在面对现代化所带来的“乱象”时感到恐惧,并表现出“回归”的倾向。尽管林纾曾提倡许多先进的概念,但他在晚年仍然成为“遗老”;米塔特一生致力于教育民众、主张维新,然而在面对彻底推翻帝制的局面时,他也选择了“退步”。在评价他们的作品与言行时,我们不应简单地将他们归类为某某“派”。他们反对和排斥的其实并不是“现代化”本身,或者变革,而是对“不可控制”的转变、文化自我的丧失乃至国家的衰落的担忧。无论是在中国还是土耳其,这种现象都可以视为过渡时代的一种常态,而并不代表他们思想的全貌。时代背景或多或少影响着人们思想的形成,这种因果关系在过渡时代人物身上尤为明显。在接触这些文士的言论和作品时,我们应避免简单和直接的定义,而应该更深入地探究他们言论前后的意图和动机,理解背后的驱动力。
林纾在其作品中试图突出柳亭亭的才华与文雅,而米塔特则更注重刻画卡丽由琵悲惨的命运。从这个角度看,两位作者的创作目的显然影响了他们笔下妓女形象的塑造。林纾创作《柳亭亭》时,中国传统道德文化正面临巨大冲击。他不仅希望创作一部畅销的小说,同时也期望通过塑造一位开明通达、懂得忍让的家长,一个博学的孝子,以及一个多才多艺的女性形象,以唤起人们对传统文化和道德规范的认同。与小仲马或米塔特相比,这群女性的遭遇以及重新融入社会的问题并非林纾关注的重点,他甚至可能从未意识到这些问题的存在。他的目标是通过借用《茶花女》的故事情节,创作出一部可以避免原作悲剧结局的“东方版”的《茶花女》。为此,他着重修饰柳亭亭的形象,强调她的文雅和才华,试图掩盖她的青楼女子之身份,从而提升她的社会地位。与之相反,米塔特的目的在于强调这些女性的困境,帮助她们重新融入社会。他通过翻译《茶花女》和创作《苦之心》《才十七岁》等作品,意在引发更多人的同情与关注。因此,他将小说中的妓女形象描绘得十分可怜和无力,以激起读者的同情心。
说林纾是因受《茶花女》的影响才写青楼女子相关题材的作品,恐怕失之武断。因为林纾翻译《茶花女》之前,中国传统文学中已经有很多杰出的妓女恋爱的故事了,虽然传统中的妓女爱情故事与《茶花女》有所不同,但至少存在这样的题材。与此形成差异的是,米塔特写的《苦之心》是土耳其文学当中的第一部关注妓女问题的小说。米塔特写《苦之心》在1871年,翻译《茶花女》在1880年。虽然看上去是米塔特在翻译《茶花女》之前撰写《苦之心》,但这并不代表他写《苦之心》之前没有读过或者听说过《茶花女》,因为小仲马《茶花女》写于1848,远在米塔特翻译它的32年之前。虽然米塔特是第一个翻译《茶花女》的人,但在1871年,也就是米塔特写《苦之心》当年,在另外一位土耳其作家的作品中曾提到《茶花女》这部作品,并且分享了马克给亚猛写的信。因此,笔者认为在撰写《苦之心》之前,米塔特很可能已经阅读过或听说过小仲马的《茶花女》。
林纾和米塔特的个案为我们揭示了“作家型译者”和“译者型作家”之间的区别。尽管他们都具有双重身份,但某一身份的突出会导致他们在文本的阐释、传达以及翻译效果上产生差异。林纾作为译者型作家,在翻译《茶花女》时,特别注重本土读者对文本的接受程度和易懂性。他翻译《茶花女》的动机并非教育公众或传达特定观点,而是纯粹为了翻译作品。而米塔特作为作家型译者,他的翻译工作始终带有特定的目的。因此,即便翻译的是同一文本和人物,两位译者所呈现的茶花女形象却截然不同。
显然,在跨文化语境下的翻译活动中,两种文化之间的距离越远,译者对文本的修改就越多。为了弥补读者在跨文化知识上的不足,译者可能会对原文进行增补、解释,甚至删减。这种翻译手段是不可避免的,因为如果采用直译,原文很可能会因无法被读者理解而显得晦涩难懂。虽然本论文并不专注于讨论在跨文化翻译中应当如何考虑本土文化与社会背景的影响,但这一现象再次表明,非文本因素对翻译过程以及最终的译文有着极其重要的影响。
结语
上述围绕林纾与土耳其作家米塔特对《茶花女》的翻译以及他们后期的小说创作进行了比较性的探索。尽管学界对林纾的译文与原文之间的异同进行了广泛研究,但这些研究主要集中在翻译美学的视角,探讨译本的本土化过程,或从翻译史与文学发展史的角度分析《巴黎茶花女遗事》对晚清文坛的影响,而且这些研究往往局限于对林纾本人的研究。本论文在此基础上,通过比较林纾与另一位具有相似翻译经历的土耳其作家米塔特的翻译实践,进行了更深入的探讨与比较。因为任何人物或文学作品的真正价值和意义,只有通过比较才能得到更全面的理解。
通过对这一案例的分析,可以清楚地表明,任何翻译都不可避免地受到政治、文化或意识形态等多种因素的影响和制约。因此,将文学翻译简单地视为“语言之间的转换”并期待高度的忠实度,既无用也不恰当。自从20世纪70年代以来,与传统翻译研究相反,将翻译视为一种文化与历史现象的描述性翻译研究受到更多关注。这种翻译研究家通常强调将译文与翻译活动放在目的语言的文化环境之中去研究。描述性翻译研究派的代表人物安德列·勒菲弗尔(Andre Lefevere)在其《〈翻译·历史·文化〉论集》中提出非常重要的观念叫作 “Universe of Discourse”(论域),并认为“译者必须在两个论域之间找到平衡:一个是原作者所属文化中的概念、意识形态、人物和事物构成的整体话语体系,另一个是译者及其读者所接受和熟悉的话语体系”。【[美]Andre,Lefevere,Translation,History,Culture:A Sourcebook,Routledge,1992,p.35.】因此,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偶尔采取本土化策略,或考虑本土文化的接受程度,不仅是不可避免的,也是恰当的。只有将林纾与米塔特的译本置于“以符号转换为手段,意义再生为任务的一项跨文化的交际活动”【许钧:《翻译论》修订本,南京:译林出版社,2014年,第50页。】这一语境中,才能在翻译史上对他们的翻译作品给予应有的评价和价值。
然而,翻译不仅仅是一个语言转换的过程,它同时也是对原文及作者进行深入研究的过程。文学翻译家吕同六在谈及翻译与文学研究的关系时曾表示:“文学翻译离不开文学研究,研究也需要翻译。两者之间的关系是互相促进,相辅相成。……翻译一部文学作品,需要对作家,对另一种语言、另一种文明,有较为深入的理解与研究。”【许钧、吕同六:《尽可能多地保持原作的艺术风貌》,许钧等著:《文学翻译的理论与实践:翻译对话录(增订本)》,南京:译林出版社,2010年,第74页。】然而,在林纾的翻译过程中,他首先未能完成这一关键的第一步,即翻译的最基本步骤。尽管王寿昌的帮助与指引使他能够跳过这一步骤,但无论如何,这与他亲自阅读和深入理解原文本质上仍然有所不同。林纾未能充分做好翻译的前期准备工作,他既没有深入研究原作,也没有亲自阅读和理解原文。同时,他对本土化的过度强调,不可避免地导致译文在某些方面出现“边缘化”的问题。目前,对于林纾翻译的《巴黎茶花女遗事》的研究已有诸多成果,但这些研究多集中于从翻译学角度分析林纾的翻译策略,主要依据“字与字”之间的“忠实度”对译文进行评价。然而,《茶花女》的真正意义是什么?小仲马通过这部小说究竟意图传达什么社会效果?尽管小仲马推崇爱情与恋爱自由,并赞扬玛格丽特的性格,但他最为关心的核心问题仍然是妓女的境遇。他整部小说的核心旨意在于同情这些女性的苦难与不幸,并强调社会应以宽容之心对待她们。林纾的翻译最大的不足之处在于,他在翻译过程中歪曲了原文的意义,违背了原文的精神。在原作中,叙述者不仅频繁表达对妓女的同情,还深入展现了女性的内心世界、男性和社会对她们的看法,以及她们如何看待自己。这些重要议题在林纾的译文中被削弱。此外,原作中也蕴含一定的女性主义色彩。茶花女,作为一名青楼女子,虽身处卖身求生的境地,却展现出某种对男性和男权社会的反抗意识。从另一种角度来看,《茶花女》描绘了一位女性为了追求正派、洁净的生活,毅然放弃了所有的奢华与便利,但却始终无法让她所处的社会相信她已彻底改变的悲剧。作者通过叙事,试图唤起读者对这些女性的同情心。正如他在小说结尾部分所言,讲述玛格丽特的故事是他的一种“责任”,他坚定地表示:“不论在什么地方听到有这种高贵的受苦人在祈求,我都要为她作宣传。”【[法]亚历山大·小仲马:《茶花女》,王振孙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3年,第204页。】
很多人对此可能会觉得可笑,但是我对烟花中人总是无限宽容的,甚至我也不想为这种宽容态度与人争辩。【[法]亚历山大·小仲马:《茶花女》,王振孙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3年,第6页。】(王译)
可怜的女人哪!如果说爱她们是一种过错,那么至少也应该同情她们。……这些残疾逼得那个不幸的受苦的女人发疯,使她无可奈何地看不到善良,听不到上帝的声音,也讲不出爱情、信仰的纯洁的语言。……我之所以要再三强调这一点,因为在那些开始看我这本书的读者中间,恐怕有很多人已经准备把这本书抛开了,生怕这是一本专门为邪恶和淫欲辩护的书……希望这些人别这么想……为什么我们要比基督严厉呢?……不要轻视那些既不是母亲、师妹,又不是女儿、妻子的女人。……在我们行进的道路上,给那些被人间欲望所断送的人留下我们的宽恕吧,也许一种神圣的希望可以拯救他们。【[法]亚历山大·小仲马:《茶花女》,王振孙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3年,第18—20页。】(王译)
从以上引述的段落可以看出,小仲马的原作中充满了类似的言论和呼吁。这些内容不仅可以视为一种宗教赞美的表现,更重要的是反映了小仲马对不幸女性的深切同情与关注。当然,不可忽视小仲马对这一主题的关注与他个人经历的关联,但林纾的译文在某种程度上削弱了原文中的核心议题。他将自己想要突出的文本意义强加于译文中,使得整个文本始终体现他的解读方式,读者也因此按照他的诠释来理解作品,从而使其译作获得了广泛的欢迎。相比之下,米塔特的译本则保留了这些内容,从而保持了原作的核心意义。除了文字上的修改与删减之外,是否成功呈现文本的核心意义,才是评判翻译忠实度的真正标准。然而,这一点常常被研究林纾译作的学界所忽视。
林纾与米塔特在翻译《茶花女》之后各自创作了类似的作品,这在某种程度上是“互文性”的体现。所谓互文性,不仅指文本之间的相似之处,更指其中一者对另一者的影响。因为“任何文本都处在若干文本的交汇处,都是对这些文本的重读、更新、浓缩、移位和深化”【秦海鹰:《互文性理论的缘起与流变》,《外国文学评论》2004年第3期。】。从翻译与创作之间的关系来切入林纾与米塔特的这一个案,也为我们提供了一些新的收获。因为《茶花女》的翻译对林纾与米塔特的创作活动具有一定的影响。然而,通过对两者的翻译及作品进行比较,我们可以看到林纾在《茶花女》的被接受和被认可上的影响超越米塔特,而《茶花女》对米塔特的创作的影响则超越林纾。首先,《茶花女》对林纾创作的影响最多体现在小说题材的选择上。尽管中国传统文学中青楼女子恋爱故事并非罕见的题材,但林纾的《柳亭亭》与《茶花女》从题材的选择以及故事情节的布置上,两者之间的相似性还是显而易见的。此外,作为19世纪浪漫主义的重要文本之一的《茶花女》,从内容来看,对“爱”的推崇是十分突出的;而林纾的《柳亭亭》从某种程度上也是赞颂男女恋爱的文本。与此相比,米塔特的《苦之心》《才十七岁》是土耳其文坛上第一部有关妓女题材的小说。因此,在这一点上小仲马的《茶花女》对米塔特的影响是很大的。
然而,米塔特的创作更能体现《茶花女》影响的主要原因在于,林纾与米塔特在个人审美趋势、价值观以及作家身份上存在差异。《茶花女》恰好完美契合了米塔特所要传达的“意义”,因此无论是在《茶花女》的翻译中,还是在他自己创作的文本中,米塔特都没有歪曲原文的核心意义。他作为一位致力于提升民众意识的作家,在其文学创作中,往往通过小说情节和人物,架起虚构故事与现实生活之间的桥梁,并揭示善恶对立的主题。在一个识字率较低的社会中,他肩负起了教育者的责任,致力于减少公众的误解和偏差。因此,《茶花女》对米塔特的真正吸引力并非源于其浪漫色彩或动人的故事情节,而在于小说整体传达的深层意义,也就是林纾特意歪曲的“意义”。他特别认同小仲马在小说中对妓女的同情以及社会对这些不幸女性的责任感。因此,米塔特的创作,如《苦之心》和《才十七岁》,也都表达了类似的社会关怀和道德反思。
通过“林纾与米塔特”这一案例,我们不仅可以看到跨文化翻译中,文本的再现与在不同文化价值语境下的命运,同时还可以看到尽管本土文化在文本转译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但作者在翻译活动背后的最终目的对其翻译方式和审美趋势的影响往往超越了前者,在很大程度上这也是导致出现两种不同翻译策略以及效果背后的重大原因。显然,《茶花女》的成功不仅归功于原作本身的魅力,还与当时目标语社会的状况与需求密切相关。
总而言之,林纾的《巴黎茶花女遗事》和米塔特的《Kamelyali Kadin》在某种程度上标志着中国与土耳其跟世界文学之间建立初步交流的重要翻译活动。《茶花女》是土耳其文学中首批翻译成土耳其语的小说之一,仅在《鲁滨孙漂流记》《基督山伯爵》等作品之后位列第八部翻译小说。尽管《茶花女》并不是中国文学史上首部翻译小说,但它在中国士人拓展世界文学视野的过程中发挥了关键作用。林纾的《巴黎茶花女遗事》使中国士人认识到,西方也能够创作出类似《红楼梦》般动人的作品,并且“似一颗炸弹炸裂了中国士人‘唯中国有文学’的狭窄地域观念”。【邹振环:《影响中国近代社会的一百种译作》,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94年,第123页。】
众所周知,翻译不仅促进了世界文学的形成,也推动了本土文学的发展。通过这样的比较,我们可以更清晰地理解本土文学作品如何走向世界,以及本土文化和社会如何影响其命运。从世界文学到本土文学,再从本土文学回归世界,这是一种动态循环。《茶花女》虽然并非法国文学中的经典之作,但经过林纾与米塔特的翻译,却成为一部在中国与土耳其社会都产生巨大影响的作品。通过采用不同翻译手段,林纾与米塔特对原作施加了影响,与此同时原作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他们的文学创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