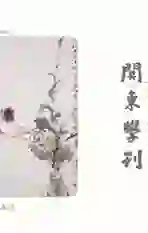爱其子弟之心:朱熹的儿童教育思想新探
2024-09-29向辉梁竹林
[摘 要]“爱其子弟之心”是朱熹儿童教育思想的基石和枢纽。朱熹的这一思想既继承了自先秦至南宋初期历代教育家的论述,也带有宋代的时代特色,更有他个人的童年经验、体验和反思。朱子的儿童教育观不是没有儿童的教育思想,而是饱含着童年印象、经验、记忆的智慧之学,是以经典为基础,关注儿童生存状态,关爱儿童教育成长,呈现出朱子以“爱其子弟之心”为根基的儿童教育理念。
[关键词]朱熹;儿童教育;爱其子弟之心;儿童观
[作者简介]向辉(1980— ),男,教育学博士,国家图书馆国家古籍保护中心研究馆员(北京 100081);梁竹林(1995— ),女,首都师范大学初等教育学院硕士研究生(北京 100089)。
儿童并未游离于古代学者视野之外。经过漫长的历史发展,到朱熹(1130—1200,后世通称朱子)所处的宋代,儿童被重视的程度大大提高。从司马光(1019—1086)的《家范》、吕本中(1084—1145)的《童蒙训》,到朱熹的《小学》《童蒙须知》等,宋代学人系统地表达了关于儿童教育的思考,这些著作均成为后世儿童教育的经典之作。从学前教育发展史来看,朱子的儿童教育经验及其系统的儿童观值得我们关注。【唐淑主编:《学前教育思想史》,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10年,第27—31页。】各种关于儿童的社会事物在宋代纷纷出现,不仅有官方的慈幼局,民间的幼儿药铺、诊所,还有各种专门的小儿书画作品、玩具在市面流通。儿童日渐被社会所关注,儿童的教育也逐渐被教育学家所重视。朱子恰好生活在这个时代,他对儿童、儿童教育及相关问题进行系统思考也就在情理之中。
明代儒学家丘濬(1420—1495)在《学的·道在第八》中,将朱子的“父兄有爱其子弟之心者,当为求明师良友,使之究义理之指归,而习为孝弟驯谨之行,以诚其身而已”【\[明\]丘濬辑:《学的》卷上,国家图书馆藏明刻本(善本书号09956),第59页。蔡衍晃指出,丘濬编《朱子学的》即是阐发朱子学,其中上卷拟朱子《小学》,全书二十篇拟《论语》,是对朱子学道统的重新确认。详见:李焯然:《丘濬评传》,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101—104页。】,“父母爱子之心,未尝少置;人子爱亲之心,亦当跬步不忘”,“人子以父母之心为心,则凡所以守其身者,自不容于不谨矣”【\[明\]丘濬辑:《学的》卷上,国家图书馆藏明刻本(善本书号09956),第56页。】这一说法予以重点揭出,具有经典的意义。从《朱子学的》(即《学的》)一书可知,丘濬所理解的朱子对儿童的思考,是从“父辈—子辈”“父母—人子”“师长—子弟”的关系入手的,通过对“爱其子弟之心”这一儒家哲学的系统分析与讨论,将儿童教育哲学纳入到理学的范畴之中。朱子在一定程度上扭转了“成人—儿童”对立的传统儿童观,从关系的角度重新理解儿童及其教育问题,成为中国传统教育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
朱子以其所历的个人经验、所知的历史记忆和所述的理论系统,构成了新的儿童观,即以“爱其子弟之心”为基石的理学式的儿童哲学。朱子的儿童哲学,论述者颇多,大多集中于道德教育的原理以及教育方法的梳理。【此类研究极多,如王睿、王凌皓《朱熹的道德养成教育思想研究——基于其童蒙教材及读物的分析》,《古籍整理研究学刊》2017年第6期;涂爱荣《朱熹童蒙教育思想及实践探索》,《湖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报》2012年第1期;陈延斌《简论朱熹的儿童道德养成教育思想》,《武陵学刊》2010年第5期;李越、司晓宏《朱熹〈小学〉中的道德教育思想拾粹》,《唐都学刊》1991年第2期。】黄宗智曾说过,“在中国文化和思想中,道德维度的重要性是非常明显的,无论是在儒学传统中,还是在历史上对外来宗教和思想(例如佛教或近代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基督教等)的反应和理解过程中,甚或是对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革命的重新理解中,都很明显”【黄宗智:《道德与法律:中国的过去和现在》,《开放时代》2015年第1期。】。道德主义的思考自然很重要,但教育绝非仅此一端。从朱子哲学的整体出发,我们认为,朱子以理学家的身份来思考儿童哲学时,其根本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是“爱其子弟之心”,其理论的依据为文化经典,其思考的方式是人生经验,最后以爱育主义的理论话语,形成了独具传统特色的朱子儿童教育思想。
一、文化经典的理据
儿童哲学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有其丰富的历史资源,成就了以文化经典为中心的经典主义教育学学理依据。儿童哲学家李普曼(Matthew Lipman)说,儿童哲学“这门课程以生动的故事,而不是课本中干瘪的论述为手段。我们需要描述思维的乐趣,塑造思维者的行为”。“哲学课堂上的热烈的讨论不仅能够增强思维能力,而且能陶冶性格,在这种意义上,儿童哲学跟中国的教育传统不谋而合。此外,在儿童哲学的课堂里的师生关系也颇似中国传统社会中的以提高技艺为宗旨的师徒关系。”【\[美\]李普曼:《哲学探究》,廖伯琴等编译,太原:山西教育出版社,1997年,第2—4页。】按照李普曼的说法,中国传统教育不是为了给学生提供一套概念的体系,也不是为了给学生提供一门具体的实用知识,而是要通过历史、哲学的叙事来提高学生的思维能力,并使之具有诗性的艺术的认知;更为重要的是,通过师生之间的互动,让教育成为一门生活的技艺而不是谋生的手段和工具。就此而言,我们需要对传统的教育哲学进行历史的回溯,以叙事的方式找回曾经长久施行却被我们淡忘了的教育哲学,特别是儿童教育哲学。
儿童,即从幼儿至青年之前的人。儿童是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在前现代社会中,儿童长期被视为成年人的附属物和未完成状态,作为对立项的“成人/儿童”被视为理所当然。即便如此,儿童不管是个体,还是群体,都并未被忽视,在历史的发展中形成了丰富的儿童词汇。查考《四书五经》及《史记》《汉书》等经史典籍可知,我们关于儿童的词汇有童、蒙、稚、幼、子、儿、少、弱、童蒙、童騃、小童、童男女、童子、稚子、孺子、竖子、子弟、小儿、婴儿、幼儿、幼冲、弱龄、少年、垂髫、髫年、丱角、总角、童龇、龆年、未冠、黄口、孩提、志学、青衿等等【王海棻、吴可颖:《古汉语表年龄的语词及其文化背景》,《中国语文》1994年第5期;薛晓平:《对〈古汉语表年龄的语词及其文化背景〉的补充》,《中国语文》1997年第5期;王子今:《秦汉儿童的世界》,北京:中华书局,2018年。中国古代儿童教育著作中儿童的古代词汇情况关注较少,陈汉才:《中国古代幼儿教育史》,广州: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96年;唐淑主编:《学前教育思想史》,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10年;喻本伐:《中国幼儿教育发展史》,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特别是就傅、及学、志学、青衿、采芹等儿童的代称都显示出古人关注儿童及其教育的文化传统。这些词语由文化经典保存下来,成为后世学人思考儿童及其教育问题的历史依据。
自秦汉以来,有史可循的儿童教育与思想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组成部分。文化经典塑造了中华文化传统,依据经典讨论儿童问题是朱熹在内的理学家的特色。文化经典的价值不仅仅在于它记载了过去经验,更在于它能对现实的生活予以切实的指导,如此形成了经典主义。经典主义的思考包括两个层面:首先,依据文化经典对具体问题展开细致的讨论,将经典拆解到具体的事务(实际)语境之中,让经典成为启发提问、解决难题的理论基础;其次,以文化经典的解释形成理学的话语系统,同时又让新的解释回归于经典系统之中,让解释成为经典的阐发性组成部分。众所周知,朱子编辑《四书章句集注》,将《大学》《中庸》《论语》《孟子》合成新的教育经典。在儿童教育方面,他编纂《小学》一书,“其教在于明伦,其要在于敬身,而古人嘉言善行靡不具备,诚果行育德之根柢,齐治均平之权舆也”【\[宋\]朱熹撰,\[明\]陈选集注:《小学集注》,《儒藏(精华编一九七)》,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282页。】(崇祯《御制重刊小学序》)。所谓的嘉言善行就是朱子在《小学》书中对文化经典的引用。《尚书》《诗经》《礼记》《周礼》《论语》《孟子》《中庸》《大学》《春秋左传》《史记》《汉书》《淮南子》《颜氏家训》等诸多文史典籍,以及宋代理学家有关儿童的论述和故事,构成了朱子关于儿童哲学的经典主义话语系统资源。
关于朱子的儿童教育思想,周愚文根据《朱子语类》中论及儿童的部分,以及《小学》等著作归纳出七个方面,分别是:1.强调胎教(优生教育);2.婴孩至成人,不分男女皆须受教(普遍教育);3.儿童阶段以洒扫应对进退为首务(生活教育);4.小学阶段重在教以事,大学阶段教以理(活动教育和哲学教育);5.大学与小学是一事(连续教育);6.立教、明伦及敬身是修身之本(道德教育);7.儿童日常生活应注意衣服冠履、语言步趋、洒扫清洁、读书写字等事宜(规范教育)。在他看来,朱子的儿童教育理念既继承了张载、二程等北宋理学家的观点,又有他本人的发扬和系统化。【周愚文:《宋代儿童的生活与教育》,台北:师大书苑有限公司,1996年,第262—269页。】后来,周氏将上述第七项取消,认定前六项为朱子儿童教育理论要点。他又根据朱子《童蒙须知》指出,这篇有关训蒙方法的专文明确了儿童教育的重点和顺序。【周愚文:《中国教育史纲》,台北:正中书局,2001年,第371页。】除此之外,当代教育学家较为关注朱子《小学》的“道德教训和伦理故事”。【邱椿:《古代教育思想论丛》上册,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5年,第71页。】所谓道德教训,并非纯粹的说理,而是通过对文化经典的话语的再阐释,使之成为儿童教育的哲学资源。诚如邱椿先生(1897—1966)所指出的,《小学》“全书的三纲领:立教、明伦、敬身与《大学》的三纲领:止于善、明德、亲民是一贯的。立教的目标是复性,这也是止于善。敬身是明明德的基础,明伦是亲民的基础。所以小学确是大学的根本”【邱椿:《古代教育思想论丛》上册,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5年,第71页。】。正因为有了经典的根柢,小学才有可能成为大学的根本,因为不论小学、大学,都以文化经典为理据和依托,都指向人性的完善和人生的丰富,以及人格精神的养成。正因为如此,当代学者在讨论儿童哲学教育时,将朱子学在内的儒学传统予以选择性的阐释性的使用,是重新思考传统哲学精神资源的若干可选的路径之一。此亦是经典主义的当代运用,因为朱子的儿童教育著述和其他著作经过历史检验,已然为时代之经典。朱子本人关于儿童教育的观念,除了《小学》《童蒙须知》《朱子语类》以外,在《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以下简称《文集》)中多有论述,此书也是我们考察朱子儿童教育观念的文献依据。
朱子思考儿童教育时,是从“学”(小学—大学)和“教”(教—学)的整体教育来思考的。朱子说:“古者,小学已自暗养成了,到长来,已自在圣贤坯模,只就上面加光饰。”又说:“古人自能食能言,便已教了,一岁有一岁工夫。到二十时,圣人资质已自有十分。大学只出治光彩。”【程水龙:《近思录集校集注集评》,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第938页。】朱子的这般讲述并非特创,而是源自程颢等理学家关于儿童教育的思考。朱子并不认为儿童是成人的未完成KdtxGS5e+sHI/Zwwzhr53WTm/ZPReElCJPaZ/Sfh0PM=状态,也不认为成人是儿童的理想状态,儿童与成人都具有向善的秉性,都具有教育的可塑性,都需要不断接受教育以臻于善与真,但儿童的理解与成年的世界之间存在着差距,所以教法并不能不有所区别。朱子引用程颢的说法来说明此种差距:“伊川程先生曰:‘教人未见意趣,必不乐学。欲且教之歌舞,如古诗《三百篇》,皆古人作之,如《关雎》之类,正家之始,故用之乡人,用之邦国,日使人闻之。此等诗,其言简奥,今人未易晓,别欲作诗,略言教童子洒扫应对事长之节,令朝夕歌之,似当有助’。”【\[宋\]朱熹撰,\[明\]陈选集注:《小学集注》,《儒藏精华编一九七》,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352页。】朱子本人也说:“夫童蒙之学,始于衣服冠履,次及语言步趋,次及洒扫涓洁,次及读书写文字,及有杂细事宜,皆有所当知。”【\[宋\]朱熹撰,朱杰人等主编:《朱子全书》第13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10年,第371页。】由此可知,朱子教育理念中的学的整体,是以经典的传统和儒学的传承为依据的。
早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邱椿教授撰写并发表了《朱熹的教育思想》一文,其中论及朱熹的儿童教育思想与著述。论及朱子儿童教育理论时,邱椿认为朱子的儿童教育思想即小学教育思想。他说:“《近思录》阐明大学的教育原理,《小学》陈述小学的教育原理和实践。后者是从南宋到明末流行最广的小学教科书。”【邱椿:《古代教育思想论丛》上册,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5年,第54页。】清人茅星来(1678—1748)说,《近思录》的第十卷专论教人之法,古代社会中的士大夫除了进入官僚队伍之外,参与教学活动是一大选项,他们“惟有明斯道以淑其徒而已。小学、大学皆有之,亦新民之事也。凡二十一条。朱子曰:‘古人初入小学,止是教之以事,如礼、乐、射、御,及孝、弟、忠、信之事;自十六七岁入大学,然后教之以理,如致知格物,及所以为忠、信、孝、弟者。’”【程水龙:《近思录集校集注集评》,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第932页。】在教学原理上,朱子认为针对成年人的“大学”,与面向儿童的“小学”虽然是一个整体,也不能将其分裂,但在内容和方法上不能不有所侧重。具体而言,其儿童教育的内容包括以下几个部分:(1)小学教育为大学教育服务,小学的对象是具体的事物和行为,大学则是其抽象原理,“具体事物是抽象原理的源泉,所以小学是大学的根本”。(2)从小学到大学,是学习的次第展开过程,从幼学的洒扫应对到大学的明德新民,是循序渐进地展开,“小学是大学的始基,大学是小学的完成”。(3)儿童教育以古今的名言、道理、故事、模范为依据,他编纂的儿童教育教材也就以古代和当代(至宋代)的道德教训和伦理故事为本。【邱椿:《古代教育思想论丛》(上册),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5年,第54—55页。】
显然,朱子的儿童教育思想与方法,值得教育史家予以特别关注,其中最令人印象深刻的就是作为依据的文化经典。经典提供了历史的事例和典故,提供了可供讨论的情节和意象,提供了奇思妙想和意境气象的参考;更重要的是,通过个人的体验,经典成为应对现实的精神滋养。对此,朱子本人有十分明确的说明:“熹儿时侍先君子官中秘书,是时和靖先生(尹焞,1071—1142)实为少监。熹尝于众中望见其道德之容,又得其书而抄之。然幼稚愚蒙,不能识其为何等语也。既长,从先生长者游,受《论语》之说,遍读河南门人之书,然后和靖先生之言,始有以粗得其味。”【\[宋\]朱熹撰、朱傑人等主编:《朱子全书》第23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10年,第2631页。】(《文集》卷五十五《答王德修》)尹焞的《论语解》和《孟子解》已经失传,今有《和靖先生文集》十卷传承。朱子父亲在临安任职的时候,朱子见过尹焞,还抄录了他的著作,大概就是《论语解》之类吧。尹焞给朱子留下了深刻的记忆,最初乃是他父亲带着年少的朱子,在“众中望见”;抄录尹氏书亦当出自朱松的建议。由此可知,朱子的经典主义观念源于他所接受的童年教育。
二、人生经验的反思
如前所述,从日常生活开始的儿童教育,是以儿童的生存状态而展开的教育实践。这种实践,既有文化经典的训示,更有人生经验的洞见。朱智贤指出,在儿童教育方面,从朱子的《小学》一书可见到他的儿童教育观有三个主要的特色:其一,要讲习于幼稚之时,“欲其习与智长,化与心成,而无扦格不胜之患”;其二,要在日常生活中进行,“教人以洒扫、应对、进退之节”;其三,要通过细节化使之成为习惯,“使之即夫一事一物之微,各有以知其义礼所在,而致涵养践履之功也”【朱智贤:《儿童心理学史》,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498—499页。】。朱子的儿童教育充满了道德主义的色彩,更具有人生经验的特征。朱子之所以有如此的认识,与其个人的生涯密切相关。
人生的经验,特别是儿童的经验直接关涉到我们如何看待社会与个人、理想与现实。现代的学术研究已经证明,“早期的人生经验会进入我们的身体,深入我们的行动基因中”【\[美\]帕特南:《我们的孩子》,田雷等译,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7年,第123页。】。成长环境和生活经验不仅对儿童的发育产生直接影响,诸如身体的发育、精神的养成等,都在潜移默化中不断叠加影响力,最终塑造了我们所见到的儿童和成人。在理学家看来,经验的人生给我们带来的不仅是一种对世界的看法、认知和理解,更是一种活生生的体验,只有把我们的经验加以体味、思考和整理,才能够让我们的人生更加丰富。为此,朱子在1187年以“爰辑旧闻,庶觉来者”的编纂思想,从事《小学》一书的编写。他明确儿童教育的根本目标在于要让童蒙(即儿童)“习之于幼稚之时,欲其习与智长,化与心成”。【\[宋\]朱熹撰,\[明\]陈选集注:《小学集注》,《儒藏(精华编一九七)》,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285页。】简单而言,教育不外乎通过对儿童的培养,让人成为一个完善的人,因为唯有完善的人才能有完善的社会,也才有真正的人世间的希望。
朱熹儿童时代的生活经验和记忆对其成年后的教育思想和哲学思想的影响十分明显。从朱子的生平可知,其父朱松和朱子本人都在他们各自的生命旅途中以士大夫自居,对国家的前途命运表达了他们的关切,甚至终身所努力的不过是希望“汉祚中天”,当这一愿望不曾实现时还期待着未来——“明年太岁又涒滩”。朱子和所有宋代人一样,都抱持着一种人生的乐观精神,扬弃了宋以前诗人的悲哀、感伤和哀鸣。【\[日\]吉川幸次郎:《宋元明诗概说 宋诗概说》,李庆等译,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19—21页。吉川氏说:“唐人诗的富于悲哀,这是因为继承了汉魏六朝的诗,其感情的基调,就是视人生为走向死亡、匆忙的颓废过程。……宋诗不同。诗人视人生为漫长的持续,对漫长的人生有多角度的考察和思虑,具有宏观的眼光。……(宋人)诗是平静的,或者是冷静的——至少以此为底色。”(第24—25页)】从朱子《蒙恩许遂休致陈昭远丈以诗见贺已答贺之复赋一首》“阑干苜蓿久空槃”可知,时光荏苒,岁月匆匆,苜蓿槃空,老年时的朱子仍旧抱持着广阔的胸襟和豁达的心态。当他回顾此生时,各种不公正遭遇,并未萎顿他的人生精气神;相反,遭遇激励着、鼓动着奋斗的人生,成为一种不息不屈的生命信念。人生道路何尝一帆风顺,何尝波澜不惊,只要有奋发的精神,有前行的可能,一切皆可无畏,自然也无须叹息。当然,宁静的时光,生活的美好,都值得享受。世事无常,更需要珍惜当下。【\[宋\]朱熹撰,郭齐笺注:《朱熹诗词编年笺注》,成都:巴蜀书社,2000年,第838—839页。】这是朱子的人生经验,也是他的人生信念和童年记忆。
每个人都有他的童年,每个童年都有记忆。童年记忆是人生哲学的基础,童年经验是人生信念的起步。对朱子而言,他的儿童记忆塑造了他的哲学和思想。哲学史家在研究朱子及其学说时,颇为注意朱熹的童年世界。比如朱子哲学研究者陈来叙说其思想时说:“幼年朱熹即勤于思索,5岁开始追寻‘天体是如何,外面是何物’的宇宙课题。8—9岁读到《孟子》‘圣人与我同类’,为成圣的希望激动得‘喜不可言’。”【陈来:《朱子哲学研究》,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0年,第2页。】陈来认为,朱子从14岁丧父开始,他师从诸多学者,最终在40岁完成了哲学思想的基调思考,他的思想至此成熟。哲学史家关心的是宇宙大课题和希圣希贤的道德伦理,而童年的朱子恰好有这样的叙事可以用作他非比寻常的例证。如此,儿童时代的哲学思考对朱子哲学而言,不仅具有开端的启蒙价值,也对我们了解朱子学有着历史的意义,故而朱子学者有意识地使用了朱子童年世界的资料。这种说法对朱子学而言并非特例,比如钱穆(1895—1990)说,朱子回忆他五六岁开始对天体有疑问,“此后格物之学,远从此时已露天倪”,至于好文学、史学、哲学、先秦诸子之学等,皆可以从朱子儿童时代的回忆文字看出线索,童年的启发不可不知;【钱穆:《朱子新学案》第3册,北京:九州出版社,2011年,第44—48页。】陈荣捷(1901—1994)也指出,朱子4岁对宇宙有了兴趣,5岁入学学习,8岁有了学习志向,心向哲理之学。【陈荣捷:《朱熹》,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2年,第1页。】童年时代的朱子有了哲学的向往和兴趣,才有后来走向哲学思考的可能。此后,朱子基本上结束了他短暂的童年时代,开始以成人的身份学习、思考和生活。
教育史家注意到了朱子的童年时代,然而像邱椿所指出的朱子的童年经验是朱子儿童教育观念的重要面向的认识【邱椿:《古代教育思想论丛》上册,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5年,第3—4页。】,往往被学者忽略。不可否认,对古代教育家的儿童教育思想的研究存在着天然的资料限制。对于普遍意义上的“儿童”,难得确切的史料依据,但对于宋元以来的某些人物,比如朱子,我们是有可能通过他们本人的记录来加以研究的,因为他们著述繁富,且保存至今,为我们了解他们的儿童世界以及他们对于儿童的哲学(包括儿童教育哲学)思考提供了第一手的材料。他们的著作不仅留下了他们童年的经验、感受和回忆,也为我们了解他们童年的教育提供了重要的资料。在这方面前人已经做了大量的工作,比如陈荣捷《朱子新探索》一书即有《朱子自述》一章,将《朱子全书》中《朱子语类》《晦庵文集》中有关朱子童年的文字做了较为详细的梳理【陈荣捷:《朱子新探索》,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6—15页。】,为我们进一步的研究提供了可靠的导引。
儿童时期的经验、印象和思考,对人的一生会产生无比强大的影响,这种影响会持续在人的记忆中显现、重现,不仅会触发我们对世界的认识,也会引导我们去行动。全部生活的经验,诸如自我体认、心理与人格的调适,都是“育”字的要义,特别是儿童的教育,“生活的绵延是精神性的,也是唯人所独有的,只有人才需要这种教育,教育教人到如此地步,才是适合人的教育”【贾馥茗:《教育的本质:什么是真正的教育》,北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北京公司,2006年,第205页。】。事实上,中国教育发展至南宋时,以生活为重心的教育观念已经确立且成熟,朱子童年时代所接受的教育2b01891a6906a28763ff3fc3f56baf6c正是此种教育,也给他留下了足够的经验。贾馥茗认为:“我们的教育就必须从幼年开始,小孩刚生下来,无所知也无所能,完全靠成人指导他、教诲他、训练他,因为没有办法,他生活的是人伦社会,不是自然界了,他必须适应人伦社会,将来在这个社会里头,才能够独立生活,要讲自由、独立,要有相当的本事。”【贾馥茗教授教育基金会主编:《教育名家论教育》,北京: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7页。】作为教育史家的贾馥茗之所以有这样的提法,一方面是因为他接受了系统的现代教育学科的学术训练,另一方面也是因为他熟稔中国传统的教育历史和思想,并将这种历史和思想转化为当代的语言。我们回溯朱子儿童教育思想时,也能深切感受到朱子当年对此问题的思考。
回到朱子的生涯可知,朱子的父亲朱松只是当时官僚体制中的左承议郎,从七品而已,生活所迫,劳苦奔波,役形于事,但他并未消沉。小朱熹在童年时代所见识到的正是这样的生活,这样的志向。朱松没有给小朱熹以富足、优渥、无虑的生活环境,也没有给他一个天真、自由、和平的童年记忆,但从朱子晚年回忆童年时,通过对时光流转、人生境遇的描绘,传达了他对童年记忆的怀念和感慨。这些童年记忆不仅包括美好的游戏和乐趣,还包括成长过程中的挫折和磨难,以及对未来梦想和追求的向往。童年的记忆、成人的理想和经典的熏陶共同构成了朱子的内心世界,是他在人生道路上不断前行的动力来源。也正是因为从小接受了这种历史的教育,所以才形成了朱子的童年经验和对历史的感知。他后来编纂《童蒙须知》《小学》等书时,也一再强调历史的重要性,并引用大量历史人物的言行来为儿童的教育提供生动的资源。朱子对于童年的记忆是如此的精确、如此的深刻,以至于在给朋友写完诗篇之后不忘把它郑重其事地记录下来“以示儿辈”。【\[宋\]朱熹撰,郭齐笺注:《朱熹诗词编年笺注》,成都:巴蜀书社,2000年,第839页。】儿童的教育,无非就是给予我们这种经验和记忆。正是因为朱子童年的经验让他养成了一种历史主义,并将其付诸儿童教育之中,但朱子的童年经验毕竟只是一种个体的生活所得,尚不足以成为他的儿童教育思想的支撑。更为关键的是,朱子将他的经验转化为一种理学的话语,形成了一套成熟的儿童教育思想。朱子的童年生活对他本人的成长有着关键的影响。这种影响也有意无意地在他的儿童教育著述之中保存着,因为教育,特别是传统教育,更多地是一种文化的传承和经验的传递。
三、爱育主义的融合
朱子的儿童教育思想不单只有引经据典和个人的生活体验,还有其他的内容,比如前述周愚文及教育史家所归纳的道德规范主义、完整生活主义、人才主义、家庭责任、师长引导等,还有我们可以称之为爱育主义,它同样与朱子的童年生活密不可分。有人问朱子:“父母之于子,有无穷怜爱,欲其聪明,欲其成立,此谓诚心耶?”朱子回答说:“父母爱其子,正也。爱之无穷,而必欲其如何,则邪矣。此天理、人欲之间,正当审决。”【\[宋\]朱熹撰,朱杰人等主编:《朱子全书》第23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10年,第2624页。】(《文集》卷五十五《答熊梦兆》)把父母对儿童的关爱与哲理联系起来思考,这是宋代儿童世界必须予以关注的特点。
关于家庭的教养和师长的教育,朱子的童年印象深刻。首先,在家庭的教育方面,前述历史主义的训练就出自他的父亲朱松。朱子的童年经验不止这一点。在朱子父亲的笔下,儿时的朱子天真烂漫,与一般纯真的儿童无异。朱松《中秋赏月》诗说:“天涯等牢落,世路方艰难。且遵秉烛语,毋为泣河叹。停杯玩飞辙,河汉静不湍。痴儿亦不眠,苦觅蛙兔看。”【\[宋\]朱熹撰,朱杰人等主编:《朱子全书外编》第3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10年,第50页。】(《韦斋集》卷三)和所有的儿童一样,小朱熹在中秋节晚上玩闹于院落、田野,寻找着小动物,而成年的父亲则奔波之暇感叹年华,对烛思往。小朱熹在其他孩童还在继续玩闹游戏的时候,他已经开始了学习时代。朱松有诗记录此情形:“尔去事斋居,操持好在初。故乡无厚业,旧箧有残书。夜寝灯迟灭,晨兴发早梳。诗囊应令满,酒盏固宜疏。漠羁宁似犬,龙化本由鱼。鼎荐缘中实,钟鸣应体虚。洞洞春天发,悠悠白日除。成家全赖汝,逝此莫踌躇。”【\[宋\]朱松:《韦斋集》卷四,清雍正六年(1728)刻本,国家图书馆藏,第14页。】(《韦斋集》卷四《送五二郎读书诗》)朱子父亲对他期待颇高,希望他能尽快进入学习的状态,承担家庭的责任。显然,儿童的年龄和童年的实际并不一致。有些人的童年,是漫长而漫不知省的;有些人则是短暂的灵光。朱子的童年属于后者。天真、纯真、无忧无虑的儿童世界,为诗人所赞颂,童年记忆也成了一种过往的美好回忆。杜甫50岁写的《百忧集行》诗说:“忆年十五心尚孩,健如黄犊走复来。庭前八月梨枣熟,一日上树能千回。”苏轼40岁写的《小儿》诗也说:“小儿不识愁,起坐牵我衣。我欲嗔小儿,老妻劝儿痴。儿痴君更甚,不乐愁何为。还坐愧此言,洗盏当我前。大胜刘伶妇,区区为酒钱。”仇兆鳌说前者是老杜的“少年得意”【\[唐\]杜甫撰,\[清\]仇兆鳌注:《杜诗详注》,北京:中华书局,2015年,第698页。】,査慎行则对东坡该诗不置一词【\[清\]查慎行:《苏诗补注》,南京:凤凰出版社,2013年,第377页。】。不论杜甫还是苏轼或者苏家子,他们的儿童记忆或者儿童观察,更多的是与成年人截然不同的心智、行为和精神,而朱子与此不同。相较于其他思想家和教育家,比如杜甫、苏轼、王阳明等,朱子的童年时光被大幅缩短了。
其次,在师长师范方面。从前贤的记录和研究可知,朱子5岁入学,早期的老师不详;14岁后追随胡宪(1086—1162)等学习儒学,18岁举乡贡,19岁登进士第,这一年就已经成为户主。【木下铁矢注意到,朱子成为户主的时候,是当时记录(《同年小录》)中年纪最小的,其他的绝大部分人是父或祖为户主的时候,朱子已成为一家之主,也需要承担其户主的重任。参见:\[日\]木下铁矢:《朱子:职的哲学》,凌鹏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22年,第19页。】22岁,参加铨试成为泉州同安县主簿。童年时代的老师们给朱子留下了终身的记忆。比如刘彦冲(1101—1147)是朱子在他父亲去世后师从的“三君子”之一。朱子在文章中写道:“熹蚤以童子获侍左右,先生始亦但以举子见期。而熹窃窥观,见其自为,与所以教人者,若不相似,暇日僭有请焉。先生欣然嘉其有志,始为开示为学门户。朝夕诲诱,亹亹不倦。……姑取遗墨聊为一编,而序其本末,以示子孙,且以示诸同志,使于前修景行之懿,知所跂慕。(庆元己未五月)”【\[宋\]朱熹撰,朱杰人等主编:《朱子全书》第24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10年,第3966—3967页。】(《文集》卷八十四《跋家藏刘病翁遗帖》)朱子回忆刘彦冲老师在他儿童时代和少年时代的启蒙教育时,谈到了老师对他的期待,老师希望他能在科举考试上取得成功,期望他能够首先完成这一基本的课业。刘老师并不仅仅提出殷切期望,还用他亲身的示范给朱子带来直接的表率、启示和动力。当朱子晚年回忆此事时,和他想起的父亲的教诲,并无二致。由此可见,童年的朱熹得到了家庭教育和师承教育的双重经验,这也是他终其一生所感念的儿童教育经验。
第三,人的童年生活在社会之中,除了家庭、师长之外,同辈群体的互相学习、相互探讨和嬉笑玩闹等,也对人的成长有着至为重要的影响。朱子也不例外。朱子《题法书》说:“予旧尝好法书,然引笔行墨,辄不能有毫发象似,因遂懒废。今观此帖,益令人不复有余念。今人不及古人,岂独此一事。惟是以往,庶乎其能自强矣。”【\[宋\]朱熹撰,朱杰人等主编:《朱子全书》第24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10年,第3865—3866页。】(《文集》卷八十二)《跋程沙随帖》:“余少尝学书,而病腕弱,不能立笔,遂绝去不复为。”【\[宋\]朱熹撰,朱杰人等主编:《朱子全书》第24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10年,第3961页。】(《文集》卷八十四)这两条记载是朱子谈及他学书法的经验,是他个人的体验。在另一条史料中,他讲述了他对书法的兴趣没有那么大的原因所在。朱子《题曹操帖》说:“余少时曾学此表。时刘共父方学颜书《鹿脯帖》,余以字画古今诮之。共父谓予:‘我所学者,唐之忠臣。公所学者,汉之篡贼尔。’时予默然无以应。今观此谓‘天道祸淫,不终厥命’者,益有感于公父之言云。”【\[宋\]朱熹撰,朱杰人等主编:《朱子全书》第24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10年,第3866页。】(《文集》卷八十二)书法教育在朱子时代是儿童必须接受的课程,但朱子本人并不善于此道,他也未曾将书法作为自身的志业。在他的记忆中,他对书法的把握远不及同辈,所以他觉得写字所重要的,并不见得就是要成为书法家,或者要以那些经典的书法为范,至少对他本人而言是如此。后来,朱子在《童蒙须知》中写道:“凡写字,未问写得工拙如何,且要一笔一画,严正分明,不可潦草。”【\[宋\]朱熹撰,朱杰人等主编:《朱子全书》第13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10年,第374页。】之所以提出这样的要求,显然与朱子童年时代学习书法的经验有着密切的关系。
朱子的父亲朱松曾提及当时某些地方有杀子的陋习,他专门写了一篇《戒杀子文》,其中说道:“自予来闽中,闻闽人不喜多子,以杀为常,未尝不恻然也。……夫人固不可以法胜,而可以理动者。庖宰且可罢,况其天性之爱乎?”【\[宋\]朱熹撰,朱杰人等主编:《朱子全书外编》第3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10年,第240页。】显然,对于儿童的生命,朱松是极为看重的。朱子也继承了他父亲的这种信念。不止如此,他还希望人民保持其爱子弟之心,对儿童教育予以重视。朱子说:“盖闻君子之学,以诚其身,非直为观听之美而已。……今劝谕县之父兄有爱其子弟之心者,其为求明师良友,使之究义理之指归,而习为孝弟驯谨之行,以诚其身而已。”【\[宋\]朱熹撰,朱杰人等主编:《朱子全书》第24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10年,第3568—3569页。】(《文集》卷七十四《补试榜谕》)儿童的教育,从来不是单个人的责任。社会、家庭、家族和学校都负有各自的养育、教养和陪护其健康成长的责任。从小接受了系统教育的朱熹正是根据他的童年记忆和人生经验对其他人提出了建议。朱子说,如果我们存有关爱下一代的信念,我们就当“求明良师友”,培养正常的人格,要让儿童在身心健康的道路上前行,使之社会化得以成功。
朱子正式明确地将“爱其子弟之心”表达出来,这一点极为关键。它是朱子在童年得到的生活经验,也是朱子对儿童教育予以思考的结论,它也构成了朱子儿童教育思想的核心命题,它同样是现代儿童教育的主旨所在。基于“爱其子弟之心”这样的儿童教育理念,朱子编纂了《童蒙须知》《小学》等一系列的儿童教育经典著述,成为后世童蒙教学的典范。如果不能对他本人的儿童经验和他以前的教育历史和思想,以及他那个时代的儿童教育状况有所把握的话,我们就不会对朱子的儿童教育思想有更为切近的把握,得出朱子的儿童哲学是没有儿童的教育哲学这种结论也就不可避免。
社会的希望在于儿童的健康成长,儿童的健康成长则有赖于人的养成。康德说:“人是唯一必须受教育的造物。我们所理解的教育,就是指连同教养在内的保育(养育、维护)、训诫(训育)以及教导。据此,人是顺沿着婴儿、学童和学员成长的。”【\[德\]康德:《康德论教育》,李其龙等译,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17年,第1页。】按照儿童教育哲学家李普曼的设计,儿童的教育是为了塑造、引导和完成儿童的记忆,故而儿童通过哲学的学习要达到这样的目标:(1)提高推理能力;(2)发展创造力;(3)个人的成长和人际交往能力的发展;(4)增进对道德的理解;(5)获取生活经历的意义的能力。【\[美\]李普曼:《教室里的哲学》,张爱琳等编译,太原:山西教育出版社,1997年,第60—84页。】所谓获取生活经历的意义,不是被人给定或者赋予的意义,而是被人自行挖掘出来的意义。这种获取是在教师的带领、引导和促发下,儿童去发现事物之间的联系,寻找不同的选择,考虑不同的可能,创造一种更为公正、客观的判断,促进言行的一致,理解并应对不同的情境。虽然朱子时代没有“儿童教育哲学”这样的课程,但他从小接受了一种人文的教育;经由此种教育而形成的童年的记忆和人文经验,是朱子之所以成为朱子的关键,也是我们了解朱子儿童教育思想的一个面向。在朱子那里,他基于“爱其子弟之心”,通过文化经典的运用和人生经验的思考,以爱育主义的方式,形成了具有典型传统教育哲学思维的儿童观,通过“历传记,接见闻,述嘉言,纪善行”【\[宋\]朱熹撰,\[明\]陈选集注:《小学集注》,《儒藏)(精华编一九七)》,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350页。】的方法呈现了一种立体而非平面、关怀而非强制、重情但不乏理性、重史但要立足现实的理学家的儿童教育观。
结论
征诸经典,求诸前贤,诉诸事实,是教育史学考察的基本方法。回到朱子的儿童世界及其对儿童教育的思考可知,朱子的儿童时代可谓短暂,但他得到了父母之爱,又得到了师长之范,加之他本人的终身努力,最终成为宋代理学的集大成者,也成为中国儿童教育史上的名家。朱子的童年有“爱其子弟之心”的父辈、师长辈,他的儿童生活记忆也就为他后来的儿童教育思想确定了基本的色调,他也以此为基础建构了一种以“爱其子弟之心”为主轴的值得我们关注的传统的儿童教育思想,也是当今儿童教育哲学值得珍视的历史资源。
每一个人都是带着他们的童年经验进入成人世界的,童年的记忆ONdiLNuABklZ9NZHfrqTRLcgeQHwCk3V/e2MIjZxw5Y=塑造了他们的儿童世界和他们思考儿童的方法、理念和视角。朱子的儿童哲学,基于他的童年生活经验,具有鲜明的历史特色;儿童时代的记忆塑造了朱子儿童教育哲学的底色,他的历史主义、示范主义和关爱哲学,都与他本人的经验密切相关。当我们探究朱子的儿童哲学时,需要对童年的朱熹和朱熹的儿童记忆予以关注。
从文化经典和人生经验来看,朱子的教育思想具有三个特点:一方面,朱子以他的哲学生涯创造性地提炼出性理学的宏大体系,构成了程朱理学的多彩画卷;一方面,朱子以他的经学生涯总结性地梳理了古典经学的传统,建构了宋明经学的理论世界;更为重要的是,朱子及其著作在元明清时期以政治权威和学术权威的方式得以延续,有正统思想的地位,直接影响了历史。【黄济:《雪泥鸿爪:新中国教育哲学重建的探索》,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336页。】时至今日,朱子学仍旧为中国的学术市场提供着重要滋养、见解和经验。因此,当儿童教育研究者回顾和反思古代的教育传统和历史教训时,朱子及其著作也必然进入其关注的视野。撰写中国教育史时,朱子及其著作是不得不浓墨重彩的。【王炳照等总主编《中国教育通史》中以“理学教育思想的大成者”来标示朱子的教育哲学贡献。(郭齐家等:《中国教育通史·宋辽金元卷(上)》,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229页)而钱穆则称“朱子为集儒学之大成者”。(钱穆:《朱子学提纲》第3版,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4年,第23页)】事实上,朱子的《朱子家训》《童蒙须知》《近思录》《小学》《论语训蒙口义》等著作中的儿童教育理念和方法被反复地引用、阐释和再阐释,他的“主敬”“童子”“学其事”“童蒙之学”等概念和论断也为儿童教育史家所熟知,还有专书探究其儿童教育哲学思想的。【于述胜:《朱熹与南宋教育思潮》,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19—22页;唐淑主编:《学前教育思想史》,第27—32页;何晓夏主编:《简明中国学前教育史》第3版,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78—81页。】这些讨论构成了中国传统儿童教育学的基本常识,对我们理解朱子和儿童教育有着重要的价值。在此基础上,我们将朱熹的以“爱其子弟之心”为枢纽、中心和基石的儿童教育思想加以重新揭示也就具有了现实的意义和理论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