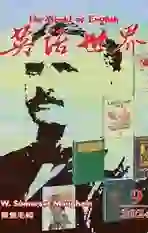论诗歌翻译的“译意”和“译味”
2024-09-04方华文
翻译嘛,无非就是用译文表现原文里的意思,丁是丁、卯是卯,容不得出现差错——这是底线,也是准则。但针对科学技术方面的翻译,这种要求尚可,因为这种翻译的特点是“严谨”,不允许发挥和创造。它“直截了当”,不涉及缥缈的感情或情绪,也正因为如此,便很容易被“机器翻译”所替代。而文学类(包括小说、散文和诗歌等)的翻译则不然,这类作品(以诗歌为最)很含蓄,有时还很深奥,叫你难以捕捉其中的“味道”——人类“多愁善感”的特性使然(宋末诗人文天祥的《过零丁洋》以及英国诗人华兹华斯的《咏水仙》(The Daffodils)就是例子)。翻译时,你需要在原文的字里行间“寻寻觅觅”,就像寻宝人那样,一定要在那里找到作者究竟想说什么(一旦找到,你还得考虑如何翻译出来)。这类翻译十分复杂,对译者要求很高,因为“译意”只是第一步,接下来还得“译味”(也就是表现出隐藏在深处的诗人情怀,这一环节非得用“创造”手段不可)。金岳霖在《知识论》1中指出:“相比较而言,译意是比较简单的,而译味就麻烦得多了。一件作品的‘味’包含种种不同的趣味与情感。要想译味,译者并不是仅仅精通这件作品的语言,以及了解作品的历史根源和作者的情况,便能够做得好的……译意只要求达求信;这不是容易的事,有时还很困难,但这种困难可以说是技术上的困难。译味则不同。译味涉及到再创造的问题。所谓再创造就是‘重行创作’,就是不拘于原来的表达方式,开创出新的方式,以表达原作的意味。译意是一种翻译,而译味虽仍是翻译,却是一种创造性的翻译”。
此处以翻译美国诗人惠特曼的诗集《草叶集》为例。惠特曼的诗歌颂大自然,歌颂民主精神,反对压迫,鼓励自由,曾经对我国的文坛产生过深远影响,如郭沫若的诗歌《天狗》和《心灯》,闻一多的《死水》和《太阳颂》,从中都可以看见他的影子。以下是《草叶集》“纪念林肯总统”一章中的几行原文:
The many-moving sea-tides, and I saw the ships how they sail’d,
And the summer approaching with richness, and the fields all busy with labor,
And the infinite separate houses, how they all went on, each with its meals and minutia of daily usages,
And the streets how their throbbings throbb’d, and the cities pent—lo, then and there,
Falling upon them all and among them all, env3d25d8a1eb5ca113339ea0b79c81678d474dc30def0f2e95b1e8c4ba9f6b252deloping me with the rest,
Appear’d the cloud, appear’d the long black trail,
And I knew death, its thought, and the sacred knowledge of death.
这几行诗既有浓浓的“烟火味”,又有一种不祥之兆(即林肯的遇刺),翻译时显然不能只有其表,而无其“内”,同时还应该注意“押韵”等细节。我的译文如下2,供大家参考(诸位可以逐行对照原文以品其中之“味”):
大海波涛汹涌,看得见轮船在航行,
丰饶的夏天在姗姗而至,田间一片繁忙的情景,
千家万户忙于过小日子,忙于衣食住行,
街道喧嚷沸腾,城市凝结着激情;
看啊,就在这时,出现了乌云的阴影——
长长的、黑黑的阴影,
投在万物之上,罩住了我和一切美景——
我知道那是死亡的阴影,
知道了它的含义——神圣!
以下几行英文诗也是出自“纪念林肯总统”一章:
Over the breast of the spring, the land, amid cities,
Amid lanes and through old woods, where lately the violets peep’d
from the ground, spotting the gray debris,
Amid the grass in the fields each side of the lanes, passing the endless grass,
Passing the yellow-spear’d wheat, every grain from its shroud
in the dark-brown fields uprisen,
Passing the apple-tree blows of white and pink in the orchards,
Carrying a corpse to where it shall rest in the grave,
Night and day journeys a coffin.
这几行诗描写的是民众抬着林肯棺木去安葬的情景,既展示了林肯生前为之奋斗不息的美国壮阔的大地是怎样的美丽,又弥漫着因为林肯的逝世而哀痛的气息。翻译时应该由表及里,采用“创造性”的手法加以展示。我的译文如下:
在春天的怀抱里,行走在大地上和城市里,
经小路穿行于古老的树林里——
(前不久这儿有紫罗兰从地下伸出头窥探,
点缀于灰蒙蒙的枯枝烂叶间,)
走过道路两旁的绿草地——那绿草地一望无际,
经过穗儿金灿灿的麦地——但见深褐色的地里麦粒纷纷露出苞衣,
经过开着红白两色花的苹果园里,
众人抬着一具尸体,要把它放在墓穴里安息,
抬棺木的队伍走啊走,日夜不息。
* 苏州大学外国语学院英语教授,文学翻译家及翻译理论家,已发表翻译作品两千余万字,其中主要包括《西顿动物记》《人鼠之间》《玩偶之家》《莎士比亚十四行诗》《草叶集》《简·爱》《嘉莉妹妹》《雾都孤儿》《双城记》《无名的裘德》《傲慢与偏见》《蝴蝶梦》《儿子与情人》《少年维特之烦恼》《红字》《牛虻》《马丁·伊登》《君主论》《社会契约论》《格列佛游记》《达尔文自传》《富兰克林自传》和《太阳照常升起》。
1金岳霖是我国著名的哲学家,其代表作《知识论》(商务印书馆,2011)讲述了知识的概念,以严密的逻辑思维论述知识体系等内容。
2引自《草叶集》(方华文译,时代文艺出版社出版,20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