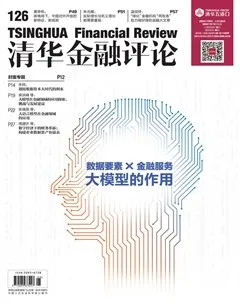剖析中国股市的长期表现
2024-09-03钱军陕晨煜朱蕾


2000—2018年间,国内A股上市的公司股票回报率和净现金流表现低于境外上市的中国公司、发达国家公司和新兴国家公司,且这种表现在大型的A股公司中体现得更加明显。论文《剖析中国股市的长期表现》(Dissecting the Long-Term Performance of the Chinese Stock Market)运用全球上市企业公司层面数据,从理论和实证角度剖析了造成这种局面的主要原因。
中国经济在过去40多年间表现得非常好。1980年,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GDP)约为美国的11%(以不变美元计);而2018年底,中国已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以购买力平价(PPP)计],比美国高23%。如此庞大经济体的惊人增长远远超出了全世界大多数投资者和权威人士的预期。鉴于经济增长明显高于预期,应该预期股市也表现出色。
中国证券市场起步于1990年,上海证券交易所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等两家境内证券交易所(A股市场)相继成立。上市公司的数量持续增长,目前有5000多家公司在这两家交易所上市。按总市值计,A股市场是全球第二大市场,仅次于美国股市。由于中国境内市场的上市要求严格,以及其他原因,大量中国公司在境外上市,主要是在中国香港证券交易所上市,该交易所遵循与美国类似的监管规定,并向全球投资者开放。第二大最受欢迎的境外首次公开募股(IPO)目的地是美国。
尽管中国经济的表现超出预期,但A股市场的上市公司表现相对糟糕,而境外上市的中国公司表现要好得多。在净现金流[利息税项折旧及摊销前利润(EBITDA)-所得税-营运资本变动-按资产比例计算的资本支出]方面,可比(行业和市值)的未上市中国公司表现也明显优于A股公司。这两类可比公司都在中国境内运营,除了上市情况外,制度和经济因素都与A股公司相同。1992—2018年,中国GDP实际增长8倍,远高于其他大型经济体。相比之下,上证综合指数却一直是大型股市中表现较差的指数之一,其表现与日本的日经指数类似(见图1)。
英国帝国理工大学教授富兰克林· 艾伦(Franklin Allen),复旦大学国际金融学院执行院长、金融学教授钱军,上海财经大学金融学院副教授陕晨煜,复旦大学国际金融学院会计学教授朱蕾共同撰写的2024年3月发表在《金融学期刊》(The Journal of Finance )上的论文《剖析中国股市的长期表现》(Dissecting the Long-TermPerformance of the Chinese Stock Market)(以下简称“论文”),运用全球上市企业公司层面数据,主要考察了2000年初至2018年底这一时期中国A股上市公司的股票收益率的相对表现。这一时期中国经济实际增长了4.8倍,远快于包括印度、巴西、日本和美国等其他大型经济体。然而公司层面的跨国回归表明,A股公司的表现却平均每年落后于发达和发展中国家上市公司15.0%,而同期境外上市的中国公司的表现与其他国家的同类上市公司持平或更好。就“买入并持有”的累计收益而言,A股市场的表现在大国集团中是最差的。中国A股市场的累计收益率低于5年期银行存款或3年期和5年期政府债券,股市投资者的实际净收益基本为零。
论文发现,A股上市公司的投资水平(按资产比例计算的资本支出)远高于可比的中国非上市公司及其他发达和发展中经济体的上市公司。但A股公司的净现金流却低于可比的中国和境外公司。这表明A股公司的投资效率低下。此外,A股公司股票收益和会计收益不佳的情况在大盘股(市值最大的30%)中更明显,而小盘股(市值最低的30%)在股票收益和会计收益方面的表现并不比可比公司差。
哪些因素导致A股公司比可比的中国非上市公司和境外上市公司的经营业绩差?为何世界第二大股票市场的长期收益低于境外上市以及发达和新兴市场的上市公司?如何解释A股大盘和小盘股之间的巨大业绩差异?论文从理论和实证角度详细考察了这些问题。
论文首先建立了一个简单的模型,该模型包括无穷期限和风险中性投资者。模型中有两类上市公司,它们具有相同的从其他替代资产计算出的折现率。其中,A股公司现金流增长率相对较低,而海外上市公司现金流增长率相对较高。在模型的第一个版本中,投资者对一系列全市场制度改革(包括治理改善)的可能性抱有相同的观念—当这些改革发生时,A股公司现金流增长率上升到高水平,价值增加。在这些改革发生之前,对这些改革的预期使得A股公司的股价高于实际水平,回报率低于资本成本。因此,初始版本的模型与A股公司相对于海外上市的中国公司具有较低回报这一情况相一致。论文还根据样本期间两组公司的增长数据对模型进行校准,并证明改革后股票收益率和估值“跃升”的可能性是相当大的。
模型的第二个版本是基于投资者行为的—不同投资者对改革可能性持有不同的观点,并面临做空限制。这些设定与Scheinkman和Xiong(2003)以及Simsek(2021)类似。论文展示了这样一种均衡:在该均衡中,只有乐观的投资者才会投资于代表性股票,因为他们相信改革的可能性更高。而现实主义的投资者则对股票的估值低于替代资产,因此只持有后者。与第一版本的情况类似,只要改革没有发生,股票的低回报,正如乐观的投资者定价的那样,将持续存在。
基于这两个模型版本,论文提出了基于公司治理和投资者行为偏差的两个假设来解释A股公司相对于其他组别的较差表现。第一,国内市场的制度特征,包括公司治理的不足,可以解释在股票回报和会计指标方面的相对较差的表现;第二,国内投资者的行为偏差可以解释A股市场的低股票回报。论文对以上假设进行了实证检验。
第一,论文对假设一(制度缺陷说)进行了实证检验。论文的实证检验包括上市审批制度缺陷、上市后业绩“变脸”、退市制度缺陷、公司治理问题。
上市审批制度缺陷。假设一中,上市和退市的制度不完善导致A股市场公司的逆向选择。公司上市须经中国证监会的批准,IPO申请年度前须连续两到三年实现盈利。此外,建立股票市场的目的之一是帮助国有企业通过市场筹集资金来促进国企混改。因此,国有企业、政府支持行业企业,以及与监管联系密切的企业更有可能上市;而私营企业、特别是当前盈利能力不高的新兴和增长型企业,上市难度要大得多。
上市后业绩“变脸”。成功上市的企业,业绩却在IPO后急剧下降。资产回报率(ROA)平均从IPO前的13%降至IPO后的略高于6%,比其他市场上市公司的ROA降幅大。论文还发现,A股大盘股公司在IPO前使用盈余管理,IPO前的盈利暴增程度大于美国公司、其他新兴市场和境外上市的中国公司。A股公司的净现金流也低于匹配的非上市公司。这些结果表明,行业内表现最好的公司未必能进入A股市场;上市公司通过业绩“暴增”来达到IPO标准,但这种表现在IPO后不可持续。
退市制度缺陷。中国公司一旦上市就很少退市,且因上市很困难,上市公司的“壳”是有价值的(参见Liu、Stambaugh和Yuan,2019)。中国公司在连续两年亏损之后,会被贴上“ST”(特别处理)标签,但仍在交易所上市和交易。与从美国退市的公司(包括退市的中国公司)相比,中国的ST公司在ST前5年,业绩[(ROA和股本回报率(ROE)]的下降幅度与美国公司在退市之前相似或更大。这些结果表明,绩差公司未被淘汰,这加剧了A股市场上市公司的逆向选择。
公司治理问题。假设一还表明,在激励和监督公司管理层为所有股东(尤其是小股东)创造价值方面,存在公司治理不善的问题。如上所述,这些公司的投资水平高于其他国家的同行(IPO后),但净现金流更低,表明投资效率低,这可能是公司治理不善的结果。多变量分析表明,A股公司的年度净现金流与资产之比显著低于匹配的中国非上市公司,也低于其他国家上市公司。净现金流低可能与关联交易(related-party transactions,简称RPTs)有关,RPT是文献中表示控股股东侵占公司资源的常用指标。
根据以往文献,论文创建了一个治理指数,包括所有权集中度、内部人所有权和董事会结构[董事会规模和首席执行官(CEO)角色]。论文发现跨国上市公司样本中该指数与(未来)股票和会计收益相关。A股公司样本中,在RPT变量的基础上增加了两个维度——国有股权和内部人“掏空”程度——来创建A股治理指数。发现该治理指数可以解释A股公司的股票收益和会计收益的差异。
第二,论文对投资者行为偏差说进行了检验。论文遵循之前的研究文献(例如Mei、Scheinkman和Xiong,2009;Baker、Wurgle和Yuan,2012;Jia、Wang和Xiong, 2017)构建了市场和公司层面的投资者“情绪”指标,并发现较高的情绪水平与随后较低的股票回报率相关。这个发现在跨国样本和A股样本中均存在。以上结果也与Xiong和Yu(2011)等对投资者行为偏差的第二种假设一致。他们研究了2005—2008年A股认沽权证的价格和交易情况。股价高企使这类权证多数处于深度价外,却仍以远高于内在价值的价格交易,且其收益与标的股票收益不相关。作者得出的结论是,这些价格不能由代表性投资者的理性预期来解释,并强调卖空限制与异质信念推动了权证泡沫。若很多A股投资者不能完全了解监管和改革的制度背景,不能完全了解上市公司内幕活动的目的和影响,但仍对公司的前景保持乐观,则股价将可能高于所有理性人的预期,收益更低。内幕活动包括围绕IPO的盈余管理、公司被ST的过程以及随后的重组、大型项目投资。结果是,发生重大事件和治理不善的公司的股价被高估,导致随后的低收益。
最后,论文将基于公司治理和投资者行为的多因素置于统一框架下进行多因素检验。在跨国和A股样本中,投资者情绪(市场层面)是解释在跨国样本中A股表现不佳的最主要因素,而跨国治理指数和上市后业绩“变脸”也是解释因素。在A股样本中,A股治理指数和投资者情绪(股票层面的换手率)都是解释收益变化的重要因素。此外,A股治理指数还可以解释大小公司间在股票和会计收益上的差异。此外,A股治理指数还可以解释大型和小型公司在股票和会计回报率上的差异。实际上,A股大中小型公司的股票回报差距在样本期后半段明显扩大;两组公司在G-index-A上的差距在2005年至2018年之间也有所扩大。这些结果进一步支持了论文的理论预测,即,公司治理越改善,现金流和股价的增长也越大(进而导致更高的回报率)。
论文的核心目标是,考察能解释A股与境外上市及匹配非上市中国公司,以及发达和新兴市场上市公司之间的绩效差距(以股票收益和会计收益度量)的因素。这些问题的答案应该有助于监管者采取措施提高中国股市的效率和表现。一个发达的股票市场促进了经济中资源的有效配置,允许更好地分担风险,这对于企业严重依赖银行融资的国家来说非常重要。对人口老龄化下有效规划储蓄保障晚年生活也至关重要。最后,一个有效的股票市场应能鼓励创新,促进新兴产业的发展。
论文的研究结果表明,中国证监会应当改革IPO程序,使其朝着市场导向发展,并鼓励私营企业以及来自高增长行业的企业上市。监管机构还应加强对表现不佳企业的退市执行过程。在这方面,中国证监会在2019年启动了一个试点计划,采用了类似中国香港和美国的“注册制”来选取部分技术行业的企业并准许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科创板上市。科创板对表现不佳的企业和涉嫌财务舞弊的企业实施严格的退市程序。这个注册制在2020年扩展到了深圳证券交易所的创业板,2021年扩展到了新设立的北京证券交易所,2023年2月扩展到了包括上海证券交易所和深圳证券交易所主板在内的其他交易板块。尤为重要的是,监管机构需要通过继续鼓励更多机构投资者进入市场来改善投资者结构、消除投资者偏见并通过加强企业治理提高上市企业的投资效率。综合这些措施,可以进一步改善市场中的企业结构和资源配置,并提升所有股东的投资回报,使市场更好地发挥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并促进整体经济的进一步增长。
(钱军为复旦大学国际金融学院执行院长、金融学教授,陕晨煜为上海财经大学金融学院副教授,朱蕾为复旦大学国际金融学院会计学教授。论文《剖析中国股市的长期表现》(Dissecting the Long-Term Performance of the Chinese Stock Market)由英国帝国理工大学教授富兰克林·艾伦(Franklin Allen)与钱军、陕晨煜和朱蕾共同撰写,于2024年3月刊发于《金融学期刊》(The Journal of Finance)。特约编辑/孙世选,责任编辑/丁开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