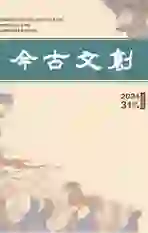熊式一《天桥》自译书写中的中国形象异域建构研究
2024-08-20巩常如
【摘要】《天桥》是一部以现实历史为创作背景的社会讽刺小说,基于先前学者的研究,海外学者主要聚焦于熊式一对戏剧的翻译研究,探讨熊是如何使用翻译策略解决京剧翻译难题,将中国故事移入英语语境中并完整表达,从而形成中国京剧的跨文化传播之路。现有研究主要从不同翻译理论出发探索熊式一笔下的自译范式,从而与同时代不同双语作家的自译策略进行对比。研究发现,鲜有学者将中国形象的建构与自译作品结合进行分析,而本文旨在从此角度出发,提出并研究以下两个问题:一是作者笔下是如何书写清末民初的中国的?二是作者笔下的人物形象或家族形象想要向读者传达什么信息?熊式一在其作品中一直流露出鲜明的民族情感,而这种情感也与人类平等自由的理念相契合。尽管中国与西方的文化差异不太可能短时间内消失,但在坚持主体性的前提下,追求共同点、尊重差异、共享美好的态度,将有助于推动中国和世界的进步与发展。
【关键词】自译研究;形象学;熊式一;《天桥》
【中图分类号】H3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8264(2024)31-0091-04
【DOI】10.20024/j.cnki.CN42-1911/I.2024.31.027
一、引言
作家熊式一出生于20世纪初,一生志在传播中国传统文化,以向西方介绍美好中国为志向,因熊式一以“剧作家”名世,《纽约时报》将其誉为中国的莎士比亚。在尝试戏剧翻译之后,中国戏剧在西方国家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但这并没有突破西方主义的桎梏,中方仍处在中西对立,民族自救而不得的水深火热之中。这些难题的存在激励熊式一《天桥》作品的问世,这一作品向外展示了勤劳、勇敢、正直的中国人形象,向内则激励抗战时期的中国同胞。《天桥》以主人公李大同32年的人生经历为主线,以被排挤的童年为始,再到苦难的青年,最后在动荡的成年时代落下帷幕,他把一生投入到社会变革中最后和国家一起获得重生。本书共十七个章节,篇篇以中国传统诗词或谚语为题,如:“种瓜得瓜,种豆得豆,天网恢恢,疏而不漏”“千算万算,不如老天爷一算”“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射人先射马,擒贼先擒王”等等,作者借用中国典故暗示人物命运走向,同时彰显出作者“让西方了解真正的中国”的决心。
在先前学者研究范围中,大都将熊式一的戏剧翻译列为主要研究对象,京剧承担着传承中国传统文化的重任。对其戏剧翻译《王宝川》进行研究,能够使海内外读者更加了解真实的中国形象。[2]556-570;[4]845-858谈及对 “The bridge of Heave”及其译本的研究,西方学者关注较少;而中方学者主要借助社会翻译学,生态翻译学,接受美学,操纵理论探析熊式一在翻译作品中的翻译策略与方法。由此观之,将《天桥》的自译研究和形象学相结合进行研究还留有空白,本文试图提出并回答两个问题:熊式一是如何通过对《天桥》的自译建构中国形象的?熊式一自译《天桥》对于建构、传播中国形象的意义?
早在20世纪80年代经历文化转向的大潮后,许多翻译界的学者都探讨过形象塑造与文化之间的关系。勒菲弗尔学者谈及翻译与形象研究的关系,他指出:“翻译与目标语文化自我形象之间的微妙关系,指出翻译具有保护和改变目标语文化自我形象的双重功能。”[3]125-127直至21世纪初,Interconnecting Translation Studies and Imagology一书的出版,为之后翻译研究和形象学二者结合奠定了重要基础。[1]8该书以十几位翻译学者最新研究为基础,探讨他者形象与自我形象的核心问题。翻译+fihbIl8Wael12QwJUHqWA==与形象构建密不可分,是一种展示和塑造形象的言语行为。加拿大翻译学者马会娟教授指出,翻译学与国家形象密切相关,文学作品的翻译不仅在国际公共外交中发挥作用,而且对国家形象的塑造至关重要。20世纪40年代,美国政府积极开展一系列美国文学作品的翻译活动,组织国外译者翻译并出版具有代表性的美国文学作品,旨在塑造美国在国际舞台上的正面形象。谈及翻译研究与形象学相结合这一重要性,谭载喜学者指出:翻译作为民族建构与重构的重要手段,不仅对民族语言形成产生影响,并且深深维系着民族凝聚力。[8]自20世纪初的十几年,各大国际出版社都出版了关于翻译研究与形象学相结合的著作,这些著作的数量表明,翻译研究和形象学之间存在着良好的文化交叉基础,这为之后学者将两者结合立论分析提供了肥沃的土壤。
二、自译中的他者话语抵抗
20世纪前后,由于中国自身话语权缺失,在国际中一直处于劣势地位,而中国人的形象也处于西方人的凝视之下,兰姆的《烤猪技艺考原》,萨克斯·罗默撰写的关于傅满洲系列小说,布莱特·哈特的《异教徒中国佬》等作品中露骨地把中国刻画着肮脏低等劣质的形象。熊式一笔下的《天桥》千人千面,一方面用讽刺语气披露清政府统治阶级昏庸;另一方面赞叹救国救民的革命者。作者通过中国人物群像来反抗西方单一的、歧视的、固定的话语侵略,而人物多样性刻画正是重新发掘隐藏在西方霸权话语之下的中国的重要手段,他试图澄清西方的误解,阻止西方对中国的错误叙述,以新的现代视角重构中国人的真正样貌。[6]
本文对源文本进行检索发现,约有260处描写有关外国人的短语或句子,但他们大都以消极词汇出现在中文译本中。例如:作者将李提摩太夫人“the hostess”译为“洋鬼婆”,将传教士“missionaries”译为“洋鬼子的传教士”。在塑造西方形象时,作者分别借吴老太太、莲芬以及李刚之眼看待西方人,无论三人何种身份,何种阶级,无一例外,西洋人都被视为消极的存在。《天桥》中,有关西方人的描述译成中文后都带有“洋鬼子”之名,之所以冠上“鬼子”的名号,是因为他们和鬼一样可怕, 他们的外貌被描画成蓝眼睛红头发满身是毛的猩猩一般,对西洋人的吃穿用度加以魔化。例如:
On the high backs of two chairs a pair of laced pink silk knickers and a corset were displayed in full view.
“Aren’t they lovely”,Mrs.Ma said the host with a smile.[5]207
原来屋子里两把高椅背上,一把挂了一条西式花边内裤,一把挂了一个同式的奶罩儿。
“马师母,这真是你们贵国最美丽的艺术品呀!”吴士可笑道。[9]171
本段描写的是马克劳校长同吴士可一家相互拜访的时候,在马克劳校长家中,吴士可一家看见他们将中国女性私人物品绣花裙和裤子赫然摆在凳子上时,吴士可发出大笑,这让马克劳十分难为情。而当马克劳来参加吴士可女儿莲芬的婚礼时,吴士可将西方人的内衣挂在高椅背上,源文本中用“lovely”描写女士私人物品,这一词并非赞扬,相反极大讽刺了西洋人不注重礼节,刻意摆放私人物品有伤风化。而目标文本中同样保留了讽刺意味的语气,对其称赞“美丽的艺术品”更是用讽刺的语气让西洋人无地自容。中西双方在这场闹剧中都意气用事,以自己之士审度他人,不甘让步。马克劳从而在心底发出中国是一个“疯人院”的感慨,他称参加的是异教邪徒的婚礼。而吴士可鄙夷地看着整日举止端庄的西洋人随意展露自己的私人物品,最后的结果是双方都陷入势不两立的争论中。而这场争论的矛盾点在于双方立足于自己的视角看待他国,不相互了解也不互相尊重,最后演变成互相羞辱的闹剧。
在其他例子中,西洋人被“矮化”也显而易见,例如:
Most of the conservative people thought that to travel in such fantastic contrivances must be highly dangerous.[5]126
“普通一般人都不免思想守旧,认为火轮船是洋鬼子弄的古灵精怪的东西,坐了很危险的。”[9]110
在描写西方发明的火轮船时,作者将源文本中的“fantastic contrivances”译为“古灵精怪的东西”,并将省略的发明主体还原成“洋鬼子”。译者在翻译过程中,保持对中国文化特色和本土意识的敏感度,并尽量保留原文中体现的中国传统价值观和思维模式,这一处理方式为读者展示了中国人对西方嗤之以鼻的态度,无论是多么新奇的发明在中国人眼里不过是“古灵精怪”的玩意罢了。译者通过引入中国本土视角和声音,从而反驳西方话语对中国的片面或刻板印象。在用英语写作时,作者面对读者群是西方读者,对西方人的描写较为保留,而将文本翻译为中文后,面对广大中国读者群,作者用消极话语描写西洋人,重新建构起中国人眼中的他者形象,以确保译文能够真实地反映中国形象。
三、自译中的自我形象建构
《天桥》这一故事发生在清末民初,聚焦描写处在战争时的底层人民,在混乱政治中的奋斗和挣扎的画面,虽然文中刻画了封建迷信的中国形象,但都是通过愉快的诙谐嘲讽语气表达出来。在故事结尾,像封建陋习裹小脚、留辫子、娶妾、贩卖鸦片在辛亥革命后逐渐销声匿迹,这也是辛亥革命取得胜利的一面。熊式一将虚构的故事融于历史事实中讲解目的是:矫正西方主义对中国的刻板印象,虽然历史上的中国人在西方主义视角下被撰写成庸俗、愚昧、无知的形象,但这些形象在作者看来是普遍存在于中西方人身上的,西方没有完美的圣人,中国人也在用双手奋斗奔向崭新的中国。
在《天桥》这部作品中,作家熊式一刻画了典型西式代表和中式代表:李提摩太和李大同,二人在刻画上遣词造句上大不相同,目的是通过对比这两种形象向西方读者展示完整的中国人形象。源文本中,当出现对大同的描写时,总会出现像“brave”“reserved”“generous”这样的正面词汇。李大同这样一个人物,在动荡的战争年代,始终能以善良示人,作者也向读者反映了正面理性进步的中国是存在的。例如:
“Never mind,we’ll have some rice fried with eggs.I like that very much,” Ta Tung said resignedly.[5]262
“不要紧,不要紧!”大同虽然大失所望,也只好赔不是,“对不住,我一提到书,甚么都忘了!饭早已做得了,鸡蛋是现成的。咱们炒两碗蛋炒饭吃算了。反正我喜欢吃蛋炒饭的。”[9]213
大同和莲芬二人在打趣时早已忘记锅炉上的饭,二人刚被强盗打劫,正过着穷困潦倒的生活,一顿饱饭已是奢侈。源文本中用“resignedly”描写大同接受这一遭遇的态度,既不强烈反抗,也不是欣喜若狂只是平淡地顺从,而目标文本中将这一词还原成“虽大失所望,也只好赔不是”。大同在失望的同时,不忘为自己错误道歉,是自己讲了太多才使二人丢失一顿饱餐,此时他作为一个丈夫,为妻子道歉。在经历人生低谷后,不忘自己的职责,没有将自己在革命道路上的逆境牵连于妻子。为此,我们看到了一个敦厚、负责任、老实的中国丈夫形象。作者用英文写作时就从中国人的视角出发,将主人公命名为“Ta Tung,which means Great Harmony”[5]41,翻译时保留“大同”二字。大同二字是古人对于国家社会的最高期盼,同样作者在大同身上也寄予了如此厚望。李大同一生心无旁骛,一心向往革命,充满政治理想,诗性才情。他是超越现实存在的主人公,作者将近代史上一批真实的历史人物身上发生的事情融于李大同身上,既反映出真实的社会现实,又以李大同的革命之路塑造了一个理想的中国。例如:
Gradually,Ta Tung learned to study the map,and was grieved to see that Burma.Annam,and the Liu Chiu Islands,which had all belonged to China,were now taken respectively by Britain, France and Japan.[5]125
大同渐渐地能看地图,看见英国割我缅甸,法国割我安南,日本割我琉球群岛,我中华的版图……渐渐变小了,怎不叫人痛心?[9]109
通过将原文的英文陈述句转换为反问句,熊式一不仅缩小了译者与叙事者之间的文化空间距离,还通过此举调整了自译本的叙事语气,表达了译者因受家国情怀感召而流露出的忧国忧民之情。这种情感的表露发生在国家面临困难之际,凸显了译者的立场和关切,彰显了译者以警语警示国人、救国爱国的紧迫心情。作为译者,熊式一在进行二次创作时对原文和母语进行了二次建构,实现了自身主体性在翻译中的价值体现,并成功地促成了自译本与原文之间的文本对话。
四、自译中的中式形象输出与回归
文中有许多关于中国传统文化的描写,由于其早年的海外游学经历,及其对汉语的熟稔,他能够游刃有余的将中式文化转化为西式表达。在每章的标题上,作者匠心独运,或引经据典,或套用中国传统文化的民间俗语。一方面,面向西方读者时,有助于加深西方读者对中华文化的了解;另一方面,译入中文后,由于适应中文读者习惯,更能有效拉近译者与读者的距离。例如:
The prosperity or the adversity of a nation is the responsibility of every soul of the country.[5]124
天下兴亡,匹夫有责。[9]109
中国的文人墨客总在其文学创作中书写着自己对国家前途命运的牵挂和忧思,熊式一更不例外。以上这句话出自《日知录·正始》,英语的行文中并没有这种表达,而作者将此作为第五章标题,向西方读者群传达出中国人刻在骨子里的风骨士气。在异国他乡的漂泊经历让作者深刻意识到当时弱者与强者共存的尴尬境地。因此,熊式一在自我翻译的过程中,通过主人公李大同的爱国行为,呼吁国人积极认识国家的命运,寻求拯救国家的途径,充分展现了译者对祖国繁荣昌盛、改变国家命运的热切期盼。这种丰富的历史内涵和国家情感突显了译者真挚的爱国之情。
The bridge of Heaven is sometimes the Gateway to Hall.[5]378
上天桥,入地狱。[9]316
在最后的尾声中,作者写到“the bridge of Heaven”和“the Gateway to Hall”这是一组鲜明的对比。翻译时用“上天桥”和“下地狱”能很好地把“Heaven”和“Hal1”的意义进行对比。在西方人的观念里,人的一生是充满原罪与救赎的过程,人的去路将因罪孽不同分为天堂和地狱。Heaven一词在这里有一语双关之效,既与Hall一词对应,指基督教中人们幸福的归属,又指贯穿全文的天桥。李大同则在故事的结尾回到家乡,归于平淡,重修了那座“偷工减料”的天桥,这也暗示着革命远不是终点,这个社会,还需要重新修正传统,天桥连起中国的过去与未来,也连接着西方与中方的对话。
作者刻意在文中将大量的中国文化用英语方式表达,让西方人阅读时,更加贴近中国故事。仅仅用中文书写自己的故事,由于文化壁垒的存在,难以真正对西方读者发声。熊式一将作品中描写中国史实的事件,维新运动、辛亥革命、武昌起义等等,讲给西方读者听,旨在打破二者文化壁垒。西方对中国的看法是片面的,是戴着有色眼镜的,作者用他者话语书写中国故事是带有反抗意味的尝试,向外输出的思想是:尽管西方主义为中国带来了现代性,这并不是恩赐,西方主义不能拯救中国,中国的民族主义已经苏醒,通过自我革新中国正意气盎然。向内:熊式一向中国同胞展示出中国与西方地位是平等的思想,中国人不应妄自菲薄,应用自己的话语与西方强权话语抗衡。
五、结语
中国学者数十年刻苦钻研,笔耕不辍,书写了许多有关中国形象建构的话题。时至今日,中国虽以大国形象出现在国际视野中,但不乏西方主义的他者化凝视,更不必说在清末民初尚处在水深火热,无力自救的中国。而熊式一The Bridge of Heaven的问世,向全世界展示出中国人革命中自强不息,自我革新的精神。该作品自译过程充分展现了译者在叙事创作细节方面自我修缮和自我审读的痕迹,这恰是自译主体“双重身份自我协商对话的结果”[7]。熊式一决心要书写中国真正的历史,恢复中国人的本来面貌,虽然中国人里有智有愚有贤有不肖的,但是这也和世界各国的人一样,中国人是完完全全有理性的动物。熊式一强烈的民族自尊心在此表现得淋漓尽致,在让中国人的形象平等地站立于世界之林的事业中,他的确做出了不可磨灭的功绩。
学者谭载喜提到翻译者和形象塑造的关系时说:“译者参与‘想象’民族或民族形象的最直接方式,就是以翻译为途径,在译作中塑造、建构或重构出符合自身认知与期望的民族形象,以满足个人在民族建构与重构中的诉求。”[8]20熊式一集作者和译者本人身份于一身,向读者们展示了本族文化和西方文化相交融的结晶。作者在使用异语写作时既不自贬,也不刻意迎合他人文化,而是为西方读者构建了一个更真实的中国形象。本文以形象学理论为框架,试分析熊式一自译本中的中国形象塑造,发现形象的塑造不是单一的,《天桥》中虚伪的统治阶级和敢于反抗的革命者相互交织塑造了中国的全貌,一来回应了西方社会对中国的片面认识;二来面对中西方复杂的文化交流,中西方共同处于一个对话平台,在双方的冲突中,互相对照,重新审视自我,从而达到友好交流的目的。
参考文献:
[1]Flynn,P.,Leerssen,J.&L.van Doorslaer. Interconnecting Translation Studies and Imagology[M]. Amsterdam/Philadelphia: John Benjamins,2015.
[2]Huijuan Ma&Xing zhong Guan.On the transcultural rewriting of the Chinese play Wang Baochuan[J].Perspectives,2017,(04):556-570.
[3]Lefevere,A..Translating Literature:Practice and Theory in a Comparative Literature Context[M].London: Routledge,1992.
[4]Qingquan Qiao.The theatrical imagining of diasporic modernity in Shih-IHsiung's Lady Precious Stream[J].Journal of Postcolonial Writing,2020,(6): 845-858.
[5]Hsiung,S.I..The Bridge of Heaven[M].Beijing: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2013.
[6]陈昭晖.熊式一的双语写作与其文化自觉的实现[D].华东师范大学,2017.
[7]李文婕.从《雁南飞》翻译的对话模式看自译活动的动态平衡机制[J].中国翻译,2017,38(03):84-89.
[8]谭载喜.文学翻译中的民族形象重构:“中国叙事”与“文化回译”[J].中国翻译,2018,39(01):17-25+127.
[9]熊式一.天桥[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2012.
[10]宇文刚,高慧,郭静.社会翻译学视阈下英汉自译惯习研究——以熊式一《天桥》汉语自译本为例[J].外语研究,2021,38(05).
[11]孔悦.接受美学视阈下熊式一自译《天桥》中的形象重塑探析[D].西安外国语大学,2020.
作者简介:
巩常如,女,汉族,陕西西安人,西安外国语大学英语语言文学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英国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