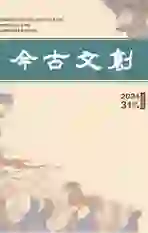民族形象的历史变更与内涵阐释
2024-08-20李冰史妍
【摘要】儿童形象是反映一个地区、国家、时代印记与形象的重要依据,儿童形象的描绘是对时代与现实生活的再现。儿童形象的描绘从古至今也被赋予了不同色彩、形象与内涵。木版年画中儿童形象以图像印记的形式记录着中华文明的发展与变革,呈现出集体意志的审美趋向和文化内涵,是中华文明砥砺前行的缩影与传承。
【关键词】木版年画;儿童形象;民族形象
【中图分类号】J2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8264(2024)31-0085-03
【DOI】10.20024/j.CNKI.CN42-1911/I.2024.31.025
基金项目:本文系重庆市社会科学规划培育项目“百年中国图画书儿童形象谱系研究”(项目编号:2021PY17)研究成果。
年画题材上自古就有“一人、二婴、三山、 四花、五兽、六神佛”之说。年画“中国娃娃”形象塑造,形成了以追求“圆润流转”为主流的造型取向,在封建社会中发挥着“成教化,助人伦”“教化劝诫、祈福纳祥”的重要作用。时移世易,经过明清的延续发展、抗战时期的重要变革、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传承与创新,木版年画儿童形象的概括力彰显着不同时代、社会背景下人们对社会生活的透视力。
一、明清木版年画中儿童形象的审美与内涵
明清是木版年画发展的鼎盛时期,其中“送财童子”“麒麟送子”“子孙万代”“人丁兴旺”“和睦美满”等是大众喜闻乐见的题材。该时期儿童题材木版年画以绘画语言传达着时代背景下的民俗信仰与审美主张。
(一)题材形象:千人一面,祈福纳祥
明清时期木版年画中的儿童形象以宋画婴戏图为基础,以描绘百姓喜闻乐见的富足生活或儿童游乐场景为主,该时期圆润造型的儿童形象已然成为一种共性审美。《说文》说:“圆,全也。”《吕览审时》说:“圆乃丰满也。”在百姓眼中圆即圆满、周全、完备等之意,也是传统思想中以圆为范的典型显示写照,是将圆所蕴含的美好寓意融入艺术创作祈福纳祥、和谐美好愿望的完美呈现。
明清木版年画中儿童形象的发型也颇有讲究。第一种“髫”,孟元老《东京梦华录·序》:“垂髫之童,但习歌舞。”指剃掉头发四周只留中间部分,形似蟠桃,这种发型在民间被称之为“桃子头”。第二种“垂髫”,清戴名世《姚符御诗序》:“符御与余垂髫相识,稍长,各游学四方。”“垂髫”是在“桃子头的基础上再左右两侧各增加一撮获几撮头发,并配以红绳捆扎”。第三种,在儿童头部左右两侧各留一撮头发,或以红绳扎起或形成桃形自然垂落,年纪多为8岁以内儿童,这种发型在民间称之为“羊角辫”,学名“总角”。从儿童不同年龄段的发型可见,在年画中描绘的儿童形象多为8岁以内的儿童形象,例如大家喜闻乐见的《五子夺莲》,其五子均为8岁以下儿童,其中一名留有明朝儿童典型的“圈秃”发型。该时期年画中儿童五官的塑造也以宋画“婴戏图”为基础,以凤眼、翘鼻、小口形象出现。如王树村所说:“短胳臂短腿大脑壳,小鼻大眼没脖子,鼻子眉眼一块儿凑,千万别把骨头露。”[1]呈现出“千人一面”的程式化造型模式。同以五子夺魁为例,明清木版年画中儿童服饰、配饰的选择与宋画相似,多以对襟长衫、右衽长衫、褙子、肚兜等为主要着装,与传统文人画的素雅不同,年画中儿童服饰的刻画多局部或全部绘以吉祥图案,其中以花卉、纹样为主。足部特征的塑造或赤足(足部圆润形式佛手)或配以不同形态的鞋子。在饰品上项圈、长命锁、红绳是木版年画儿童形象塑造中必不可少的元素,长命锁上多有“长命富贵”“福寿绵长”等字样,寓意着儿童健康长寿的美好愿望。
(二)场景塑造:以景寓意,意不在人
木版年画在意境塑造上融合了民间审美与民间喜闻乐见的符号美学,使作品更具乡土气息。以五子婴戏图为基础的木版年画,在人物动态上均以夸张活泼的形态呈现,头或仰或侧,儿童手部动作或手持或争夺的戏剧化场景动态,但在人物塑造上基本没有差别,作品寓意的差异主要体现在儿童周围场景环境的变化。如“榴开百子”描绘的是两个孩童相向而立,构图左右对角上下形成斜角,手持石榴,周围辅以石榴和石榴花,表达期望多子多福的愿望。作品“桃献千年”人物形象、动态、穿着等则与“榴开百子”完全一致,不同的是周围环境营造以寿桃、鲜花装饰,手持物也变成了寿桃。由此可见在年画“婴戏”题材中寓意的营造并非由儿童形象、动态组成,符号化的纹样组合才是表达作品真正内涵的关键。
(三)文化内涵:教化规范,繁衍不息
随着历史发展,年画艺术得到不断发展与传承,这个过程中,艺术与百姓生活不断交融,成为百姓文化交流、审美传播、教化信仰、民俗习惯、社会思想的重要工具和形式。值得探究的是在传统年画中却很少有女孩形象单独呈现,女孩形象往往与仕女形象组合出现,即便有女孩形象也是以配角形象出现。年画中儿童形象的刻画是对“生殖”的渴望追求,是中国封建社会中男权思想的现实体现,是百姓对“多育”“育男”理念的执着,也是这一时期典型的社会心理文化特征。宋代提倡孕“男年十五,女年十三以上,并听婚嫁”的生育政策,为进一步提升生育率“栓娃娃”这种民俗事项应运而生,年画中儿童腰间、发髻上的红绳也是基于“拴娃娃”这种民俗而来。“婴戏”题材的年画在明清盛行,从侧面反映的是当时百姓对“求子”意识的渴望与执着。“年画娃娃”在该时期已然是“育男”“祈福纳祥”的符号。
二、抗战时期年画中儿童形象研究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传统年画艺术在百姓生活中不断发挥宣传爱国思想、传播抗战精神的作用。全国范围内年画艺术创作群体在年画中打下“打日本、救中国”的“烙印”,“为大众、为战斗”[2]成为该时期重要的发展方向之一。该时期木版年画儿童形象的塑造在抗日战争中发挥着积极的宣传作用。同时,“中国娃娃”形象与传统木版年画的创作方向、形象塑造、功能均发生了巨大变革,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称之为新年画[2]。
(一)题材形象:爱国救亡,传承创新
抗日战争时期新思想的涌入,鲁迅先生提出“新年画”运动,也被称为“翻身年画”。该时期木版年画在题材上围绕宣传抗争思想、鼓舞抗战精神、激励国人奋发图强等题材开展艺术创作。“中国娃娃”转而成为手持红缨枪立马战斗的英雄形象。“千人一面”的儿童形象被满脸正气、英勇斗争的小英雄形象所替代,例如1945年的年画门神作品《讲究卫生人兴财旺》,在人物塑造上儿童塑造为短发平头,剑眉怒挑、圆眼怒睁、方形国字脸的形象;服装上借鉴红军蓝灰色配色,吉祥纹样装饰占比也极为简洁,人物形象更为庄重。
女童形象刻画在该时期得以独立呈现,发型以抗日战争中女性红军形象为基础。头部发型以学生头配红色蝴蝶形象呈现,象征着革命与自由。五官刻画上,眉形为弯月细眉,圆眼小鼻小口的严肃形象呈现。在服装上与男童相似均采取红军服装配色,另配以传统云肩,既表现了抗战时期女性儿童保家卫国的英勇身姿,又有儿童应有的可爱整洁,也有传统文化的传承。
(二)场景塑造:思想引领,与时俱进
该期间儿童题材木版年画以现实生活为基础,以思想引领为导向的宣传性新年画场景塑造。场景的塑造可分为如下几类:
第一,抗战题材的塑造。该类场景的塑造多以战马、红缨枪、大红花、麦穗、大刀、鲜花等为背景开展形象塑造。例如:《讲究卫生人兴财旺》场景中心区域塑造的是面部肃然手提红缨枪、背挎大刀、斜跨五角星文件包、手抱麦穗、身披红军配色服装、身跨麒麟瑞兽的小红军形象,画面下部配以五谷、上部以莲花(寓意连连大捷)红色飘带为底、上书人才兴旺讲究卫字体。从场景建构可见,该时期儿童形象塑造是以民族英雄形象为基础开展艺术创作的,作品传达的是红军保家卫国,抗日战争是全民族的战争等思想。
第二,培育新时代儿童题材。该类型题材以儿童教育、教育强国的理念开展场景塑造。例如年画《念好书》中,儿童斜跨五角星书包,手持毛笔、算珠、书信,身着传统印花粗布服装,上方双鱼与铜钱的灯笼,以花草连接灯笼与周边纹样,蝙蝠左右分布,寓意年年有余、富贵吉祥、双福临门。上部配以“念书好,念了书,能算账,能写信”作为画面主题。下方绘以麦穗、玉米、南瓜等各种农作物寓意喜庆丰收,该作品营造出男女平等、儿童是未来的美好场景。
第三,日常生活类。该类型的场景描绘了安居乐业、军民团结、男女平等的美好场景。例如《儿童劳军》场景细节刻画与作品名称相呼应,画面共塑造四个人物形象(两男两女),儿童或戴毛皮棉帽或留“桃子头”或扎双辫。儿童或手持毛笔书写慰问信或肩抗儿童团旗帜或分装慰问品,形象之间相互呼应生动自然。在儿童着装上或传统盘扣棉服或蓝印花布棉服或条纹棉服。场景远处描绘盘长纹样木窗,寓意长长久久、延绵不绝,旁挂带藤葫芦寓意福禄双全、儿孙满堂,下方以劳军箱、牙刷、肥皂、慰问信等表明作品主题。
综上,该时期画面在塑造形象上以现实为基础融合优秀传统文化,体现百姓抗战情结,表达对抗战胜利的期待,是现实世界百姓思想的真实写照与艺术升华。
(三)文化内涵:求同存异,真实写照
抗战期间儿童题材年画本质上是融合了连环画、西方绘画、年画、剪纸等艺术形式的新年画,在思想上表现的是抗争精神、男女平等、丰衣足食、上进变革等,也是抗战精神、抗战思潮以及先进思想不断涌入的具象化表现。首先在表现内容及题材上,抗战期间婴戏题材(不局限于婴戏题材)年画艺术作品,在构成上打破了传统文人绘画对年画艺术的影响,呈现绘画样式的多样性。表现技法上呈现出融合化的特征,使年画艺术在艺术表现上具有更强的综合性。对比传统木版年画,新年画也反映出百姓认知与意识的变迁。首先,女性形象的刻画,在这一时期也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在《儿童劳军》这一作品中明显的女性儿童的刻画无论是从衣着和画面中位置的布局,都与男性儿童是一致的,这种变化实际上是女性站起来的一种现实写照。其次,在画面配饰的变化上,这一时期的婴戏图年画形象刻画,没有了传统木刻年画的雍容华贵场景的做作,也没有了金银首饰的搭配,更没有了繁复纹样服饰的刻画。这种变化是新思想、抗战情绪下艺术家对现实生活中百姓形象的模写,是正视现实、表现现实、激励现实的写实化表现手法。从作品中能够看出抗战期间百姓生活状况的艰苦与奋斗、反抗与团结以及男女平等共同抗敌的思想变化。
三、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年画儿童形象研究
(一)题材形象:破旧迎新,千人千面
新中国的成立带来新思想、新风尚,百废待兴、除旧迎新,新观念、新风尚逐渐塑造着新人民。在这一背景下童题材年画摒弃了传统年画求福纳祥的符号化作用,造就了该时期年画娃娃形象的新气象、新面貌,确立了中国孩子形象。
该时期塑造的是积极向上生活富足的新中国儿童形象,儿童形象采用写实主义技法,人物刻画完全摒弃了宋画影响,以生活的不同角度塑造了全新儿童形象。例如《群英献礼图》(江南春,1961)儿童形象的刻画共六名儿童,男女各3,男孩形象塑造为留平头,五官浓眉大眼,上身着白衬衫系红领巾,下身穿蓝色海军裤,脚穿黑皮鞋手捧鲜花热泪欢呼的形象。女孩头扎双麻花辫系黄色蝴蝶结,五官精致、明眸皓齿,上身穿白色衬衣,下身着粉色连衣裙,脚踩白色皮鞋的形象。彰显新中国儿童精神与物质的满足,塑造了乐观向上、面容俊俏的新时代中国儿童形象。在《做共产主义接班人》(沈家琳,1964)作品中,儿童形象塑造得肃穆庄严,手举红旗,踏正步行进,服装以白、黑、粉、绿四色配以红领巾,以人民英雄纪念碑为背景,塑造出中国儿童坚毅、自信、勇往直前的形象。
总之,该时期作品主要以社会主义建设接班人为题材开展艺术创作,多角度描绘了新中国新气象下的中国儿童形象,在思想引领文化建设上起到了引领时代的作用,包含美好生活、社会主义接班人、劳动教育、互帮互助等题材。
(二)场景塑造:划分时代,融合发展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尤以20世纪50—80年代年画娃娃形象的塑造,随着艺术家纷纷加入,例如刘文西、张碧梧、安茂让、赵幼华、黄妙发等使得该时期年画风格与传统木版年画形象塑造在造型方式和构成上产生了划时代的变化。首先该时期年画风格与传统年画、抗战时期年画在空间构成上的变化表现为由传统散点透视(平面化)转变为焦点透视(空间效果),例如年画作品《丰收》(张清岩,1965)、《红太阳光耀暖万代》(亢佐田)等画面利用焦点透视营造出近大远小、近实远虚的效果,画面更接近水彩的表现效果。在表现技法上该时期年画创作方法既有传统年画制作流程的方法(制版、线板、色板),也有借助年画形式题材利用水粉、水彩等材料进行直接绘制的技法。因此该时期年画的创作方式是融合了西方绘画技术材料的全新年画艺术。在人物塑造上,作品形象的刻画更为深入,无论是服装、面部刻画都利用光影效果使画面呈现出立体效果,同时融入传统年画或水墨人物痕迹。例如《在毛主席身边》(刘文西,1959)画面采用横向大场景构图,画面以焦点透视呈现出空间效果,同时画面中人物面部塑造呈现出油画的立体效果,但在色彩及技法上又以中国画的设色和勾线技法寓意表现。因此该时期的儿童题材年画应该是融合的、包容的,儿童形象是积极的、乐观的,富有时代朝气与韵律。
(三)文化内涵:服务社会,表现希望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国民希望安居乐业,国家迈向繁荣昌盛。年画艺术作为百姓的艺术激发了时代背景下年画艺术服务社会、服务大众、反映美好场景的功能。同时该时期年画艺术男童女童描绘得到均衡表现,也反映着社会现状中男女平等思想的落地生根。艺术家所建构的场景及人物形象刻画,反映了当时百姓的质朴与真诚,每个儿童面部表情的变化也是在生活中挖掘与艺术升华的社会现状体现。因此,该时期年画儿童形象的刻画本质上是社会安定、百姓安居乐业、人民有奋斗目标的客观反映,应该说年画儿童形象刻画拉开了年画艺术从依托民俗迈向描绘美好、表现人民的艺术。
综上,年画艺术在发展过程中是积极的、美好的艺术,在时代变更中年画艺术也在不断演变发挥着自己特殊的艺术魅力。儿童题材年画与其他类型年画艺术不同的是,儿童题材年画因儿童的真与善更能够代表时代的美,也更能够激发人美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与拼搏。
参考文献:
[1]王树村.中国年画史论[M].天津:天津杨柳青画社,1991:250.
[2]张西昌.从“民间文艺”到“人民文艺”——武强新年画的形成及解析[J].美术,2022,(06):26.
[3]吴祖鲲.传统年画及其民间信仰价值[J].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7,(06):115-122.
[4]都晨.木版年画发展中的博弈与互动[D].中央民族大学,2012.
[5]王坤.20世纪中国年画的嬗变[D].天津大学,2014.
作者简介:
李冰,男,汉族,重庆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副教授,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民间美术理论及课程开发研究。
史妍,女,汉族,重庆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副教授,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儿童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