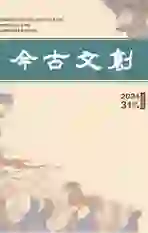论叶昼的心学观
2024-08-20王睿文
【摘要】明代《西游记》刊本中,李卓吾的评本(以下简称“李评本”)是至今保存最为完整的,在《西游记》研究中具有不可磨灭的价值。诸多证据表明该评本是由叶昼假托李贽之名所作,实际点评者为叶昼。《西游记》的主旨贯穿着一条修心的主线,与晚明社会盛行的心学思潮关系密切。叶昼的评语包含多种思想内容,可以通过这些评语分析其心学观的内涵。
【关键词】叶昼;李贽;《西游记》;心学观
【中图分类号】I2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8264(2024)31-0045-04
【DOI】10.20024/j.cnki.CN42-1911/I.2024.31.014
《西游记》是中国神魔小说的代表之作,其幻妄无当,奇幻多姿的风格吸引了无数读者,也由于其中涉及的儒道释种种思想,引发无数争论。有关《西游记》的主旨探究,几百年来一直颇受关注。如今可考西游记刊本中,最早的当为万历二十年(1592年)金陵世德堂梓行的《新刻出像官板大字西游记》,此时正是王阳明的心学思潮繁盛之时,李贽的“童心说”也在当时广受欢迎,从诞生背景来看,《西游记》作为流传于市井间的白话小说,其内容和思想在很大程度上会受到王阳明和李贽等人的心学观念的影响。明清两代的学者对于《西游记》的主旨认识大体相同,形成广泛共识,那便是《西游记》是95/BIJEFmmgZ6loD7xYlECbTn3RceOAO1eh0/3YtjeQ=一部披着神魔外衣,而阐发心性之学的著作。[1]根据学者苏兴的考证,李卓吾评本《西游记》的刊刻时间应最晚不超过崇祯年间[2],这一时期正是商品经济迅速发展,工商业市镇发展和市民阶层逐渐壮大,社会思潮和价值观念发生转变,李评本的评点者便是在这一社会背景之下,吸收王阳明、李贽等人的心学学说的基础上,对《西游记》加以点评的。下面将论证李评本《西游记》的评点者问题。
95/BIJEFmmgZ6loD7xYlECbTn3RceOAO1eh0/3YtjeQ=一、李评本《西游记》评点者为叶昼之证
有关叶昼的生平事迹,历史文献记载不详,只能在寥寥几处得以窥见。钱希言在《戏瑕·赝籍》中有记述:“比来盛行温陵李贽书,则有梁溪人叶阳开名昼者,刻画摹仿,次第勒成,托于温陵之名以行……近年始复大行。于是有李宏父批点《水浒传》《三国志》《西游记》《红拂》《明珠》《玉合》数种传奇, 及《皇明英烈传》,并出叶手,何关于李。”[3]
从这段文字中可以得出一些关键信息,叶昼曾经伪托李贽进行多种书目的评点,这其中包括《西游记》;同时叶昼的身份为屈沉下僚的落魄文人,这些人多愤世嫉俗,对于世间不合理现象进行尖锐的讽刺和批判,也和《西游记》评语中嬉笑怒骂嘲讽世相的思想符合。除了钱希言以外,还有周亮工的《因树屋书影》:“叶文通,名昼,无锡人,多读书,有才情,留心二氏学,故为诡异之行,迹其生平,多似何心隐……当温陵《焚藏书》盛行时,坊间种种借温陵之名以行者,如《四书第一评》《第二评》《水浒传》《琵琶》《拜月》诸评,皆出文通手。”[4]这里面同样可证叶昼曾伪托李贽之名对多种书籍进行评点,并且叶昼其人富有才学,故能在评点中表现出独到的审美眼光和富含哲理的评语,超越此前种种粗制滥造之评,而开创一代品评之先。同时,其中描述叶昼生平多似何心隐,何心隐是阳明“心学”里泰州学派的代表性人物,可见叶昼其人思想也明显受当时的“心学”所感染。钱希言、周亮工均为晚明时人,与叶昼年代相近,且能互相印证,因此其记述应具有较高的可信度。
此外,在具体作品的评点内容中也可见端倪。在《西游记》的评语中,多处可见贬低女性之言语,如在第二十九回总评中,提出“那怪尚不是魔王,这百花羞真是个大魔王”[5]。缘何百花羞便是大魔王,这里的评语缺乏合理的逻辑链条论证,具有较强的主观臆断性质;以及在第五十四回的评语中更是直接谩骂妇女为妖魔:“既是女人矣,缘何不是怪物妖精?”[6]此类对女性的贬低之语在《西游记》全书的评点中可见多处,这与李贽的妇女观相互矛盾。李贽主张男女平等,认为妇女拥有参与政事、追求自由婚姻爱情的权利,是对封建礼教的有力冲击,在当时社会上具有极高的前瞻性。即便李贽的思想在其一生的不同阶段中有所变动,但如此大相径庭恐非出自同一人之手。
如今学界较为公认的观点是《李卓吾先生批评三国志》是叶昼托名所评,其中评语多次引用“梁溪叶仲子”之论,如若李贽评点,自然不会也实无必要频繁出现这样一位“梁溪叶仲子”,因此这极有可能便是真正的评点者,即叶昼。并且相比于李贽的思想与评点,以及此后毛宗岗等人的评点来看,其中评语较为粗浅薄陋,明显非李贽所评。在叶昼的《三国志通俗演义》评语中,也可见他对女性的贬低。如第十九回总评处说:“从来听妇人之言者,再无不坏事者,不独吕布也。凡听妇人之言者,请看吕布这样子,何如?”[7]将吕布的失败归结于妇人之言,而忽视吕布本人有勇无谋,反复无常的个性才是其覆灭的主要原因,仅将其妻劝诫这一侧面因素进行大加渲染,可见叶昼思想存在落后之处,也是李评本《西游记》实为叶昼所评的有力证明。此外,关于对虚伪道学的批判,对秀才等的嘲讽与批判,在两部书的评语中同样随处可见,如在《三国志通俗演义》“曹操割发代首”的故事后面总评处,叶昼评道:“做得来,便是丈夫。可笑彼曹无用道学,口内极说得好听,每一事直推究到安勉真伪,一丝不肯放过;一到利害之际,又仓皇失措,如木偶人矣,不知平时许多理学都往那里去了。真可一大笑也!”[8]嬉笑怒骂之间将虚伪的假道学批判得淋漓尽致,反映出对道学的极端憎恶。因此,从前人记述以及作品具体分析上可知,李评本《西游记》的实际点评者应为叶昼。
二、叶昼的心学观
叶昼生平在历史文献中的记载很少,其本人也并无如“四大奇书”之类的传世经典流传,因此之前有关叶昼的研究也较少。虽然近代以来,学界针对托名李卓吾批评的《三国志通俗演义》《西游记》等作品给予很高关注,但整体而言比较零散,缺乏系统性研究,也较少深入的理论分析。近年来学者何毅的《叶昼小说理论体系》进行了较为全面的论述,是研究叶昼评点和相关思想的重要资料,但在一些具体问题上,尚有可待挖掘拓展的空间。因此,本文以叶昼托名李贽所评的《西游记》中评语为中心,尝试对叶昼的心学观予以论述。
(一)对真性情的“赤子之心”的认同
上文中已阐述了叶昼生活于晚明时期,其思想受王阳明“心学”与李贽的“童心说”影响较深,所以在他托名李贽的评语中,有不少与李贽的思想倾向切合之处,这也是不少研究者认为李贽的评本为其本人的重要因素。李贽曾经阐述其“童心说”:“夫童心者,真心也……若失却童心,便失却真心;失却真心,便失却真人。人而非真,全不复有初矣。”[9]认为无论是文学创作,还是为人处世,都应当保持“童心”,去伪存真,表达个体的真实愿望,主张割断与道学之间的联系。在叶昼所做的《西游记》评语中,多处可见对于道学的厌弃和批判,如第五十七回总评中述道:“天下无一事无假,唐僧、行者、八戒、沙僧、白马,都是假到矣, 又何怪乎道学之假也?”[10]在“真假美猴王”一节里论述假猴王在花果山所变的假的取经团队,以迷乱人心,由“二心”的论述借题发挥至道学上,突出对虚伪道学的批判。类似的论调在夹批和总评处均可见到,叶昼在其他书中的评语也能够反映出类似的思想,如容本《水浒传》第七十三回,有人冒充宋江行奸淫之事,评语中便述道:“宋公明已是假道学了,又有假假道学的,好笑,好笑。”[11]突出对道学的嘲讽态度。
叶昼面对李贽所提倡的“童心”,也就是“赤子之心”,则表示出认同的态度。在《西游记》第一回便有交代,讲到樵夫对孙悟空介绍“灵台方寸山”“斜月三星洞”时,旁评便指出:“灵台方寸,心也。一部《西游》,此是宗旨。”[12]总评中也有论述:“篇中云‘释厄传’。见此书读之可释厄也。若读了《西游》,厄仍不能释,却不辜负了《西游记》么?何以言释厄?只是能解脱便是。”所谓“释厄”,便是求取心灵的解脱,是对《西游记》全书宗旨的阐释。此后又述道:“‘子者,儿男也;系者,婴细也。正合婴儿之本论’即是 《庄子 》‘为婴儿’,《孟子 》‘不失赤子之心’之意。”[13]道即本心,进而一生求取者,不过是修以“赤子之心”罢了。第一回的评点,便可多处见到叶昼对心学的解释,并在整体上表现出明显的认同态度,并在此后的评语中进一步强化。去伪存真,回归本心,这样的感情倾向也与后来金圣叹等人的观点具有一致性。
(二)对修心养性的推崇
叶昼除了认同“赤子之心”,还在其评点内容中表现出修心养性的主张。李评本《西游记》的评语分布较为零散,但在关键之处往往能够慧眼识出。叶昼在评点时多用“着眼”的字样标记出《西游记》文本里有关心性的语句,并指出该处是值得关注之处。
叶昼这样的思想观念与《西游记》一书的主旨相契合,在第十三回,在唐三藏决意西行取经,与众僧临别时,曾言:“心生,种种魔生;心灭,种种魔灭。”[14]叶昼在旁评中注为“宗旨”。在篇末总评中进一步加以强调,指出“一部《西游记》,只是如此,别无些子剩却矣。”[15]在面临即将遭遇的种种磨难,叶昼敏锐地观察到文中所包含的主要思想,加以注评,在表层的故事之下捕捉到暗含的主旨,一切妖魔均是由心而生,只要心怀良善,那么种种妖魔皆可幻灭,表现出修心的意旨。在紧接着的第十四回,孙悟空刚被唐三藏从五行山下解放出来,便将所遇到的六贼“眼看喜、耳听怒、鼻嗅爱、舌尝思、意见欲、身本忧”全部打死,这六贼又何尝不是人的六根,正对应佛家所讲的一心灭六贼。叶昼在旁评注道:“世人心都要杀六贼者,只是没手段。”[16]最后的总评处也说道:“请问今世人还是打死六贼的,还是六贼打死呢?”“‘心猿归正,六贼无踪。’八个字已分明说出,人亦容易明白。”“着眼,着眼,方不枉读了《西游记》也。”[17]叶昼在评语中指出这六贼对于今天世人之弊害,以及今天的世人能否打杀这六贼,而成为清净之主呢?在《西游记》的行文和标题中,不止一次将孙悟空称为“心猿”,实际上其所象征的正是人心。因为人心不足,所以大闹天宫,闯下弥天大祸,所以被镇压五百年。心猿一出,则灭六贼而归正,投入到取经的正道中,也是以此为象征接下来的第十五回中,龙在鹰愁涧化为白马,叶昼也在总评处论道:“心猿归正,意马收缰,此事便有七八分了。着眼着眼。”[18]第十九回悟空收八戒以后,叶昼总评曰:“游戏之中,暗传密谛。学者着意《心经》,方不枉读《西游》一记,辜负了作者婆心。”[19]类似的评语在整部《西游记》中前后均随处可见,可以说修心养性的主张贯穿于叶昼的评点之中,也可见叶昼对于《西游记》的主旨体会深刻,对其中的修心着眼之处均进行一一标注,展现出他对修心养性的认同和推崇。
(三)对个性精神的宣扬
“心学”中的另一个重要主张便是宣扬人的个性精神,影响到小说创作中,便是人物形象塑造的转变,更加重视人的个体情欲,强调个性解放,反对禁欲观念,肯定人情、人欲的合理性。叶昼受其影响,在评点小说时,从心学的观点出发,也可见对个性的宣扬。《西游记》一书塑造最为突出的形象便是孙悟空,他是一只集神性、物性与人性于一身的神猴,既有坚决的抗争精神,也有好胜争强的一面,极富个性色彩。叶昼的评语中也对他给予高度关注,并表现出对其个性的认同。评卷凡例处写道:“批‘猴’处,只因行者顽皮,出人意表,亦思别寻一字以模拟之,终不若本色“猴”字为妙。”[20]此言中既是对孙悟空天性的认同,也表现出对其独有趣味的赞颂,也为后面正文评点中该部分的归结设立前提。在有关孙悟空的评语里,经常可见叶昼的关注。如第二回菩提祖师佯怒离开后,师兄弟们都责怪抱怨孙悟空,而孙悟空的反应是什么呢?“悟空一点儿也不恼,只是满脸陪笑。”叶昼在旁评点道:“老猴聪明。”[21]这里不只是一个“猴”字,而是称赞他聪明,写孙悟空面对师父发怒并没有沮丧,面对众人的指责鄙贱也没有气恼,而是独自参悟了师父要授予他本领的密谛,因此只是陪笑,可谓传神贴切,将这样一个不远万里求仙修道的美猴王的聪慧敏锐形象表现出来,富有超脱常人的大智慧。第三回写孙悟空到龙宫求取兵器,写如意金箍棒能大便大,能小便小时,评点道:“此棒也有些猴气。”[22]将兵器与人的特征相联结,也传达出孙悟空灵活多变,敏捷变通的个性。这样的评点在后面孙悟空被召天庭以后的情节中更为突出,如第四回写孙悟空不满天庭授予他的弼马温之职,而回到花果山,自封“齐天大圣”,叶昼评语写道:“爽快!要做便自家做了,何必在他人喉下取气。”[23]直接对孙悟空这样自行封赏的行为进行称颂,更是点出“何必在他人喉下受气”,体现出对他这种追求自由和自主行为的赞同。如此之评语,全书有关孙悟空的情节中多处可见,能够看出叶昼对这个人物给予很高的热情和评价,也可以反映出他本人对个性精神的宣扬。
除了对孙悟空个人情性评点外,还有通过孙悟空的行为对世态人情的指控,可以窥探叶昼明显的褒贬爱憎之情。如第一回写孙悟空远涉重洋来到南赡部洲求访本领,却见世人都是为名利奔走之徒,更无为身命者之时,感叹“争名夺利几时休?早起迟眠不自由”。叶昼在旁评道:“世人可惜,世人可叹,不及那猴王多矣。”[24]表现出叶昼对世俗名利的鄙薄,一语道破扭曲的价值观,对当时社会中人皆争名逐利的无奈与感叹,反衬出美猴王的独到性情。第二回孙悟空卖弄本领惹怒菩提祖师,祖师将其逐出师门,并告诫他日后闯祸莫要提起自身,孙悟空答道:“决不敢提起师父一字,只说是我自家会的便罢。”叶昼点评:“如今弟子都是如此。”[25]对当时世情中欺师忘祖的风气进行尖锐的讽刺,而后面孙悟空在大闹天宫以后,遵守言语未暴露自己的师父出处,也彰显出其虽性情顽劣,但尊师纯良的本心个性,也蕴含着对社会中忘恩小人的有力批驳与指控。
三、结语
综上所述,李评本《西游记》具有很高的文学价值和理论意义,在中国小说评点史上具有不可磨灭的影响力,标志着《西游记》评点的已达到一定的理论高度,并趋于成熟。[26]叶昼从心学的观点出发,是对当时社会思潮的反映,也是对修心养性和个性精神的凝练与升华。虽然从心学的角度并不能完全阐释《西游记》的内涵,但可以作为一个视角,从文本入手,与明代的世俗人情较为贴近。通过对李评本中相关评语内容的研究分析,可以归纳出叶昼的心学观,对于研究叶昼其人的生平思想具有重要意义,挖掘其中蕴含的深刻哲理bd03f8e038e1d732fb7f804d4d53b6eb,对研究晚明社会思潮也具有积极的影响。
参考文献:
[1]薛梅.心学视野下的《西游记》研究—— 《西游记》与阳明心学之关系研究述评[J].明清小说研究,2009,(02):65-76.
[2]苏兴.谈《李卓吾先生批评西游记》的板刻[J].文献,1986,(01):35-37.
[3]马蹄疾编.水浒资料汇编[M].北京:中华书局,1980:360.
[4](清)周亮工著,朱天曙编校整理.周亮工全集第三卷 因树屋书影[M].南京:凤凰出版社,2008:147.
[5](明)吴承恩著,(明)李卓吾评点,陈宏,杨波校点.李卓吾批评本西游记(上卷)[M].长沙:岳麓书社,2005:229.
[6](明)吴承恩著,(明)李卓吾评点,陈宏,杨波校点.李卓吾批评本西游记(下卷)[M].长沙:岳麓书社,2005:444.
[7]张天星.论《李卓吾先生批评西游记》的评语与李贽思想的矛盾——兼论该评本的评者归属问题[J].江淮论坛,2007,(01):142-147.
[8]黄霖等.中国小说研究史[M].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2:71.
[9](明)李贽.焚书 续焚书[M].北京:中华书局,2009:98.
[10](明)吴承恩著,(明)李卓吾评点,陈宏,杨波校点.李卓吾批评本西游记(下卷)[M].长沙:岳麓书社,2005:474.
[11](元)施耐庵著,(明)李贽评.李卓吾先生批评忠义水浒传(第四卷)[M].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4:193.
[12](明)吴承恩著,(明)李卓吾评点,陈宏,杨波校点.李卓吾批评本西游记(上卷)[M].长沙:岳麓书社,2005:7.
[13](明)吴承恩著,(明)李卓吾评点,陈宏,杨波校点.李卓吾批评本西游记(上卷)[M].长沙:岳麓书社,2005:9.
[14](明)吴承恩著,(明)李卓吾评点,陈宏,杨波校点.李卓吾批评本西游记(上卷)[M].长沙:岳麓书社,2005:95.
[15](明)吴承恩著,(明)李卓吾评点,陈宏,杨波校点.李卓吾批评本西游记(上卷)[M].长沙:岳麓书社,2005:100.
[16](明)吴承恩著,(明)李卓吾评点,陈宏,杨波校点.李卓吾批评本西游记(上卷)[M].长沙:岳麓书社,2005:106.
[17](明)吴承恩著,(明)李卓吾评点,陈宏,杨波校点.李卓吾批评本西游记(上卷)[M].长沙:岳麓书社,2005:109.
[18](明)吴承恩著,(明)李卓吾评点,陈宏,杨波校点.李卓吾批评本西游记(上卷)[M].长沙:岳麓书社,2005:117.
[19](明)吴承恩著,(明)李卓吾评点,陈宏,杨波校点.李卓吾批评本西游记(上卷)[M].长沙:岳麓书社,2005:150.
[20](明)吴承恩著,(明)李卓吾评点,陈宏,杨波校点.李卓吾批评本西游记(上卷)[M].长沙:岳麓书社,2005:2.
[21](明)吴承恩著,(明)李卓吾评点,陈宏,杨波校点.李卓吾批评本西游记(上卷)[M].长沙:岳麓书社,2005:12.
[22](明)吴承恩著,(明)李卓吾评点,陈宏,杨波校点.李卓吾批评本西游记(上卷)[M].长沙:岳麓书社,2005:22.
[23](明)吴承恩著,(明)李卓吾评点,陈宏,杨波校点.李卓吾批评本西游记(上卷)[M].长沙:岳麓书社,2005:29.
[24](明)吴承恩著,(明)李卓吾评点,陈宏,杨波校点.李卓吾批评本西游记(上卷)[M].长沙:岳麓书社,2005:6.
[25](明)吴承恩著,(明)李卓吾评点,陈宏,杨波校点.李卓吾批评本西游记(上卷)[M].长沙:岳麓书社,2005:15.
[26]臧慧远.李评本《西游记》评点的“心学”阐释[J].延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32(03):93-95.
作者简介:
王睿文,男,汉族,黑龙江克山人,东北师范大学在读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文献学、元明清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