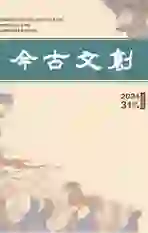中国天鹅处女型民间故事的生态女性主义解读
2024-08-20梁颂宇
【摘要】天鹅处女型故事是在世界各地的民间文学中普遍存在的一类故事,这类故事的母题主要包括飞鸟变形成美貌女子、男子与飞鸟所变的女子成婚、因某种原因男子与女子分离等。在各个历史阶段,我国各民族的民间文学中都留存着数目众多的天鹅处女型故事。本文将从生态女性主义的角度出发,探索中国天鹅处女型民间故事中描绘的两性关系,挖掘和揭示这类民间故事中所表达的人与自然关系的变更,以及社会对女性和人对自然的态度变化。
【关键词】民间故事;天鹅处女型故事;生态女性主义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8264(2024)31-0041-04
【DOI】10.20024/j.CNKI.CN42-1911/I.2024.31.013
一、引言
天鹅处女型故事在世界各国的民间文学中都普遍存在,其主要的情节母题包括飞鸟变形成美貌女子、男子与飞鸟所变的女子成婚、因某种原因男子与女子分离等。在我国,较为详细完整的有书面记载的此类故事最早出现于晋朝郭璞所撰写的《玄中记》以及干宝的《搜神记》:
“……昔豫章男子,见田中有六七女人,不知是鸟,匍匐往,先得其毛衣,取藏之,既往就诸鸟。诸鸟各去就毛衣,衣之飞去。一鸟独不得去,男子取以为妇,生三女。其母后使女问父,知衣在积稻下,得之,衣而飞去。后以衣迎三女,三女儿得衣亦飞去……”[1]3
这个故事尽管只有一百多字,却包含了早期天鹅处女型故事三个主要情节母题:飞鸟变形为女子,凡男收藏羽衣得妻,婚后男子违禁失妻。此类民间故事属于人兽婚类,只是“兽”的形象与人已经十分相近。
中国的天鹅处女型故事经历了四代异文的变迁:第一代异文为人鸟结合;第二代异文添加了凡男藏衣得妻和违禁失妻的情节;第三代异文在第二代异文的基础上添加了丈夫和鸟子寻妻的情节;第四代异文则是让男女主人公化身为王子和公主,并在原来的基础上添加了战争和宫廷斗争等更为繁复的情节。其中第二代异文被认为最具典型性,是此类故事的基本原型,也是被研究最多的对象。
天鹅处女型故事广泛存在于各国各民族的民间文学中,是民间文学中光彩夺目的宝石。众多学者已经对天鹅处女型故事进行了各种分析和研究,包括母题分析、类型归纳、异文分析等。本文将从生态女性主义的角度出发,在分析此类故事所描绘的两性关系的同时,揭示故事中所隐含的人与自然的关系。
二、生态女性主义简介
生态女性主义是生态主义和女性主义这两股思潮的结合,通常认为1974年法国女性主义学者弗郎索瓦·德·埃奥博尼发表的《女性主义或死亡》(Le Feminismeou la Mort)是生态女性主义诞生的标志。生态女性主义认为女性和自然存在着诸多联系和相似之处,将对自然和对女性的压迫联系起来,认为这两种压迫存在着某种联系。“……(生态女性主义)反对父权制世界观和二元式思维统治下的对女性与自然界的压迫,倡导建立一种人与人、人与自然之间的新型关系。”[2]50生态女性主义承认非生命物质拥有和人类一样的平等的地位,认为“万物有灵”,视自然界为有生命的,同时抨击传统的父权制世界观,抨击思维方式的二元式、价值等级观念和统治逻辑,旨在建立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关系。
从生态女性主义的角度看来,人和自然界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是密不可分的。人和自然应成为一个和谐的整体。生态女性主义认为男女两性关系与人类与自然的关系具有共通性,反对把男性和女性对立、人与自然对立的二元式思维,旨在建立人与人之间、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关系。在进行文学评论和文本解读时,生态女性主义关注的是作品中体现的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探寻其中蕴含的隐喻和寓意,发掘其中体现的社会现实。
纵观天鹅处女型民间故事,其情节脉络是建立在男性-女性、人类-异类、人间-天界的二元对立的结构模式基础上的。“这三项对立因素包含了人类发展史上两个最基本的、也是无法回避及消除的矛盾,即人与自然和男性与女性。”[3]45因此从生态女性主义的角度来看,天鹅处女型民间故事表面上是男性和女性之间的故事,其内核却是人与自然的故事。对这类故事进行生态女性主义解读不仅可以发掘故事所体现的男性-女性关系和人-自然关系,揭示其反映的社会现实和历史变迁,还能为此类民间文学的研究提供一个新的研究角度。
三、从生态女性主义角度解析天鹅处女型民间故事
(一)人物角色
天鹅处女型故事中的女性角色通常是由飞鸟或其他动物化为人形的女子。而飞鸟化身为人的这一情节,主要源于远古时期先民们的鸟图腾崇拜。远古时期的先民们崇拜飞鸟,敬畏飞鸟,因此形成了鸟图腾崇拜。而图腾的产生则源于人们对自然的敬畏和崇拜。在之后的天鹅处女型故事中,女主角不仅仅限于飞鸟,而是扩展到狐狸、老虎、猿猴、田螺、青蛙等多种动物。
而女主角的原型通常是当地常见的或被尊崇的动物,例如在傣族的《召树屯》中,女主角是孔雀公主。孔雀不仅是分布于东南亚和我国西南地区的鸟类,更是傣族人民所尊崇的吉祥鸟。在狐狸崇拜文化盛行的山东地区,一则天鹅处女型故事中的女主角原型是狐狸。在江西南昌地区,数目众多的白鹤每年十月至来年三月会在鄱阳湖一带聚集,因此在当地流传的天鹅处女型故事中,女主角的原型是白鹤。河流湖泊众多、雨量丰沛的江浙、两广和福建等地都有“田螺姑娘”或“河蚌精”的民间故事,女主角的原型是当地常见的淡水生物。“‘物’的选择适应当地风土人情和特殊的人文景观,各地各民族选择不同的物来填补自己故事中的‘物人转变’情节。”[1]18女主角原型源自熟悉的自然风物也进一步增强其自身的自然象征属性。从时间上看,鸟类以外的动物原型的出现时间略晚于鸟类原型。
尽管种类不同,故事中的女主角却都是来自自然的、不同于人类的“异类”。“所有的生态女性主义者都相信,人类彼此是相互关联的,人类也是和非人类世界,如动物、植物和静态物质相互关联的。”[4]402相比之下,故事中的男性角色通常都是凡间男子,代表的是人类。天鹅处女型故事在代表自然的女性和代表人类的男性之间展开,实际讲述的是人与自然的故事。
(二)故事发生的环境
天鹅处女型故事中男主角与女主角相遇的场所通常是水边。从最早期的《毛衣女》到后来的《牛郎织女》《白水素女》,在故事中“水”都有着重要的象征意义。在农业社会,水被看成是极其重要但又难以控制的自然元素。一方面,水是生命力和生殖力的象征;另一方面,水又无法捉摸,难以控制的。在我国的文学作品中“水”经常被用来比喻女性,如“女人是水做的”“红颜祸水”等。“水”这一女性化的重要自然元素在我国天鹅处女型故事中频频出现,也暗示着这个故事不仅仅是男性与女性的故事,也是人与自然的故事。
而男女主角相遇的场景也具有明显的地域特点。在流行于高原地区的藏族《普兰飞天故事》中,男女主角相遇的地点是高原湖畔;在以水稻为主要农作物的壮族、瑶族和苗族地区,流行于此的天鹅处女型故事中男女主角相遇的地点是水田旁。
由此可见,先民们在创造这一类故事的时候从周围的自然环境中汲取灵感,将自己熟悉的自然风物和与自己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自然元素融入其中。
(三)故事情节和禁忌母题
早期的天鹅处女型故事主要包括飞鸟化身为人沐浴、凡男窥浴得妻、男子违禁失妻这三个主要情节。其中凡男窥浴得妻通常是男主人公藏匿仙女羽衣以使其不得不留在人间。值得一提的是,流行于壮族地区的《勇敢的黄阿刀》中,凡男得妻的契机并非窥浴藏衣,而是仙女帮忙收割稻子。她们在劳作时将翅膀摘下,放在田坎上,而凡男藏起了一个仙女的翅膀:“收割谷子那天,天上来了七个仙女帮忙……他把最小的那对翅膀放在谷子的上面挑回家。”[5]102
这个故事中的仙女摆脱了被窥视的被动地位,主动参与到农业生产中。然而,无论是窥浴藏衣还是藏起来帮忙的仙女的翅膀,其核心都是获取女主角身上具有超人法力的一部分,让她再也无法回到仙界,变成与男主角无异的凡人。
先民们从最早期的敬畏自然逐渐发展到尝试控制自然,故事中的凡男藏匿仙女羽衣以逼迫仙女留在人间便可看作是先民尝试控制自然的隐喻。而男子最终违禁(在早期故事中通常是让妻子知道羽衣藏匿之所)失妻,便暗示了先民们因违反自然规律,控制自然的尝试失败。而天鹅处女型故事中包含的禁忌母题,则是对这种失败的一个诠释。
早在1929年,赵景深就指出:“天鹅处女的童话是表现禁忌的。”[1]110禁忌来源于早期人类社会在生产力水平低下的情况下,由于敬畏自然而产生的恐惧。早期先民们开始尝试改造和控制自然,但因为生产力水平低下和不了解自然等原因,这类尝试经常以失败告终,天鹅处女型民间故事便是对这种尝试和失败的反映。
(四)故事的发展和演变
随着社会发展,天鹅处女型故事也经历了由简到繁的发展过程。后来的天鹅处女型故事在第二代异文原有的三个主要情节(飞鸟化身为人沐浴、凡男窥浴得妻、男子违禁失妻)的基础上,又增加了凡男(或是男子与其子女)追寻妻子、最终得以团圆的情节,成为第三代异文。而仙女这一角色也发生了较大的改变。早期天鹅处女型故事中的女主角对于在人间生活是不情愿的,所以只要有机会拿到羽衣就毫不犹豫地离开人间。在唐朝和宋朝之后的天鹅处女型故事中,仙女开始留恋人间,不愿离开。这时期的故事通常会有男女主人公幸福生活的描写,这也暗示着人类开始学会与自然和谐相处,与早期故事中凡男提防仙女的关系已有很大不同。
而凡男失妻这一情节,早期故事中通常源于凡男违禁,这时期的故事则通常是因为他人作梗,有时为仙女母家干涉,如著名的《牛郎织女》;有时为奸人作祟,如藏族的《普兰飞天故事》,仙女为妃子和巫师所害;有时为夫家迫害,如傣族的《召树屯》,孔雀公主为男主角的父亲和星象师所害;有时为恶霸强抢,如壮族的《仙女和特苦》,仙女被财主所霸占。
这两大转变不仅体现了男性-女性关系变化和婚姻家庭的变迁,更体现了生产力的发展和人类-自然关系的变化。
四、天鹅处女型故事所反映的社会现实
天鹅处女型故事蕴含着先民们对美好婚姻生活的向往,体现了生产力的发展和人类社会的变迁,揭示了男性-女性关系和人类-自然关系的变化。通过这些天鹅处女型故事可以窥见婚姻家庭结构的变化、生产力的发展以及由此引发的人与人的关系、人与自然的关系的变化。
(一)生产力的发展和婚姻家庭结构的变化
在原始社会,生产方式主要为狩猎和采集,女性主要从事采集工作。相比进行狩猎的男性,她们能获取的物资更为丰富。而盛行于该时期的生殖崇拜也让女性掌握更大的权力。与之相对应,此时的社会形态是母系氏族社会。在早期的天鹅处女型故事中,女主角的仙女身份或超乎凡人的非凡特质反映了这一时期对女性的尊崇。然而,当人类进入农业社会,男性成为主要劳动力,女性屈居次位,母系社会也开始向父系社会转变,婚姻家庭结构也从原来的从妻居变为从夫居。
这一转变也体现在天鹅处女型故事中。从第二代异文开始,故事中的女性几乎没有择偶权。在大多数故事中,女主角都是不情愿嫁与凡间男子的,只是凡男通过某些不甚光彩的手段(藏起仙女的羽衣或翅膀)逼迫女主角与其建立家庭。原本高高在上的仙女已经跌落凡间,她们对婚姻的唯一防抗方式只是在丈夫违禁后离开。
而到了第三代异文,她们离开之后还会被寻回,从中可以看出她们所代表的自然已经进一步被人类所征服。而第三代异文的出现则体现了人类征服自然的信心进一步加强——即使违反自然规律造成改造自然的失败,也有弥补的办法,就如同离开的妻子终究会被寻回。
随着时间的推移,凡男寻妻的情节也逐渐丰富。在为数不少的第三类异文中,阻止男女主角团圆的通常是女主角的娘家,如著名的《牛郎织女》和苗族故事《天女与农夫》。而此类冲突的根源也逐渐从仙母阻挠转化为翁婿之争,有的故事甚至出现了岳丈试图杀害女婿最后被女婿反杀的情节。
翁婿之争体现了夫权和父权对女性的争夺,而且经常以夫权得胜而告终。在这一类故事中,“男子通过自己的行动终于使女子从父权所有过渡到夫权所有。”[6]25然而无论是父权得胜还是夫权占上风,故事中的女性如同任人争夺的自然资源,只是被抢夺的对象,并无任何自主权和话语权。
(二)人与自然关系的变化以及对待女性和自然的态度变化
在中国天鹅处女型故事中,女主角的原型多为鸟类,体现了先民们对鸟类图腾的崇拜之情。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女主角的原型也开始多样化,不仅限于飞鸟,而是扩展到多种动物。这也体现了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人类在改造自然、征服自然的斗争中获得了初步的胜利,自然的神秘面纱已经被揭开,人们对自然的敬畏也开始消退。象征自然的女主角不再如天空中的飞鸟般高不可攀,而是化身为随处可见的自然物,而女性的社会地位也随之发生了变化。原本在母系社会中处于主动地位的女性逐渐屈居次位,最终在父系社会中处于从属地位,成为男性的附属和争夺对象。
和早期的故事比较,后期天鹅处女型故事的男子违禁这一情节也发生了变化。早期的男子违禁行为通常是让仙女得到羽衣而重回天庭,后期的天鹅处女型故事中男子的违禁行为还包括道出妻子的真实身份和出言侮辱妻子。如唐代皇甫氏的《原化记》中就记载了一个男子与老虎所化身的女子结婚的故事,一日男子提起了妻子的真实身份,导致妻子勃然大怒:
……妻怒曰:“某本非人类,偶尔为君所收,有子数人。能不见嫌,敢且同处。今如见耻,岂徒为语耳。还我故衣,从我所适。”[3]45
男子无意间提起妻子的真实身份,实际是凡间男子对妻子“本非人类”一直耿耿于怀的表现,流露出对“异类”妻子的轻蔑。这样的故事还包括《雁姑娘》《蚬姑娘》。江西一带流传的民间故事《田螺壳》中的丈夫不仅对儿子说出妻子的真实身份(田螺变的),还和儿子一起用筷子敲打妻子原来的田螺壳,把人类对“异类”的轻蔑和厌恶表达得淋漓尽致。人类在改造自然和征服自然的斗争中逐渐占了上风,对自然的崇拜和敬畏已经淡化。故事中的男主角通过对“异类”妻子的轻蔑,表达了对自然的轻视。故事中的女主角从原先的“仙”降格为“禽兽异类”。人类可以短时间内和自然和谐相处,“人和异类为了‘故事’的缘故可以暂时组合成一个家庭,但即便在故事里,其间的裂缝也不可能任意弥合。这是人类与整个大自然对话的永恒定理。”[3]47
第三代异文多了凡男寻妻的情节,而阻碍男女主角团圆的力量除了之前提到的岳丈阻挠,还有奸人作梗。这一演变也反映了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人类对待自然的态度也开始发生了分化:一部分人和故事中的男主角一样,希望通过改造自然实现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愿望;而另一部分人则和故事中迫害女主角的人一样,粗暴地对待自然,破坏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关系。
五、结语
天鹅处女型故事是世界各国民间故事中的一块瑰宝,它表达了人们对美好婚姻生活的愿望。其中对两性关系故事的描写之下,暗藏着人与自然关系的隐喻。而此类故事的发展和演变,又体现了人与自然关系的改变。从生态女性主义的角度透视和分析这类故事,厘清此类故事中男性-女性和人类-自然的二元结构脉络,能为此类故事提供一个新的认识角度。美丽的天鹅处女型故事,实际上是一则关于人与自然的寓言。
参考文献:
[1]郭俊红.天鹅处女型故事[M].北京:中国社会出版社,2010.
[2]王立娟,梁华.生态女性主义思想述评[J].辽宁行政学院学报,2006,(05):50-51.
[3]万建中.一场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深刻对话——从禁忌母题角度解读天鹅处女型故事[J].北京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0,(06):42-50.
[4](美)罗斯玛丽·帕特南·童.女性主义思潮导论[M].艾晓明等译.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
[5]黎琳,黎国轴编著.壮族故事荟萃(一)[M].香港:香港天马出版有限公司,2005.
[6]万桂红.男权文化下的“天鹅处女”故事的解读[J].湖北教育学院学报,2006,(07):24-25.
作者简介:
梁颂宇,女,汉族,广东广州人,广西大学外国语学院讲师,研究方向:民间文学译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