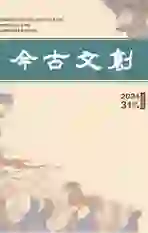鲁迅“精神胜利法”与奈保尔“视而不见”的比较研究
2024-08-20龙航航
【摘要】鲁迅笔下的“精神胜利法”与奈保尔的“视而不见”在封建历史和殖民历史中分别发挥着宗教的功能。“精神胜利法”是阿Q的个人宗教,能够为任何遭受苦难的人提供情感慰藉并恢复心理平衡。同样,奈保尔作品中印度独立后的“视而不见”虽然是一种退缩和盲目的形而上学,导致了象征主义和对西方的盲目模仿,但是“视而不见”也是一种满足自我的哲学,是印度的集体宗教,对自我的维系至关重要。“精神胜利法”和“视而不见”都是典型环境下的典型行为,还是对存在主义之问的艺术再现。
【关键词】鲁迅;阿Q;“精神胜利法”;奈保尔;“视而不见”
【中图分类号】I106.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8264(2024)31-0032-03
【DOI】10.20024/j.CNKI.CN42-1911/I.2024.31.010
一、阿Q式的“精神胜利法”
鲁迅的文学成就是多方面的,但大多数读者都会同意鲁迅最大的文学成就之一是创作了《阿Q正传》,以及提出的“精神胜利法”这一文化概念。《阿Q正传》出版以来,一直是学术界研究的焦点,在国内外都产生了大量的学术研究成果。但时至今日,“精神胜利法”仍然是一个备受争议的话题。谁是阿Q?阿Q是中国农民的化身,还是当时各行各业所有中国人的化身?阿Q的精神胜利法是中国民族性格的阴暗面,还是所有民族性格的阴暗面?精神胜利法是一种短暂的社会现象还是一个持久的生存问题?学者们并不掩饰鲁迅研究中的争议,早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一篇关于阿Q研究的评论就坦诚道:“长期以来,在许多重要问题上一直存在着争议,并没有得到圆满解决或达成一致。”[14][17]张梦阳在进行过系统梳理后,得出的结论是:“《阿Q正传》就像《堂吉诃德》和《哈姆雷特》一样,是一面讽刺世界的镜子。”[18]
阿Q“精神胜利法”的艺术表现展示出了鲁迅深刻的心理洞察力。20世纪80年代以前,以心理学为导向对“精神胜利法”本质的研究还不多见。林汉达于1940年出版的研究报告却开始从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论中汲取灵感,围绕着阿Q的“精神胜利”机制,认为“鲁迅笔下的阿Q是一个虚构人物,也是一个真实的人。可以说,他是一个具有最具体变态心理的典型人物,具有心理学上的防御机制,以应对环境的压迫与内心的挣扎”[4]。林汉达的开创性研究打破了以往对于“精神胜利法”的主要论点,认为阿Q患有变态的心理和病态的人格。事实上,“精神胜利法”并不是精神病患者才拥有的精神状态,也不是变态心理的扭曲结果。要看清“精神胜利法”的深刻内涵,就需要从人的心理机制与环境的关系出发。“精神胜利法”代表了一种复杂的心理应对方式,它与心理学上对“性格”的定义有着相似之处。根据现代的人格和身份理论,奥托·费尼切尔将性格视为将内部需求和外部环境要求协调起来的特有模式[1]。在各种可能的行动中,人类会选择一种能同时满足多方面需求的行为。在满足外部环境需求的同时,也会带来自我需求的满足。将各种要求相互协调的方式形成了特定的人格特征[13]。从人的性格和身份的心理机制角度来研究“精神胜利法”就会发现阿Q的心理状态并没有变态。
阿Q是一个典型的农民,但同时也是一个和其他人一样需要自我保护和自我实现的人。为了自我保护,他需要食物、住所和免受伤害;为了自我实现,他需要爱、尊重和自尊。和其他人一样,他也有自己从生到死的人生轨迹。唯一不同的是,阿Q的存在仍停留在自我保护和自我实现的最底层。事实上,他很难让自己不跌落到最低的层次。尽管他试图改善自己的生存状况,但他从未成功地实现自己的目标。纵观阿Q的日常行为,可以发现他的一生都在为生存而挣扎,唯一能让他忍受这种悲惨生活的方式就是精神上的胜利感。
阿Q应对恶劣环境的奇特策略使得一些学者认为他是一个动物般的人,几乎完全受到动物本能的驱使,没有内在的自我[5],或是“有严重心理问题的流浪农民的典型代表”[15]。这两种观点都只是部分正确。阿Q的病状当然是与他的“精神胜利法”有关,但他对“精神胜利法”的需求并不是一种心理疾病,相反,他的看似变态的行为都是理性计算的结果。它最多可以是一种神经症,而不会达到精神病的程度。事实上,正是“精神胜利法”让阿Q能忍受困境,才不会让一个心理承受能力较弱的人不会走上绝路。从心理学角度上来说,阿Q所谓的“精神胜利”是一种强迫性重复,是一种想象性的解决问题的方法,这种方法给人一种虚假的满足感,使他虽然遭受了巨大的精神痛苦,却觉得自己的存在还能忍受。阿Q并不是生来就有这种强迫性神经症,而是环境迫使他发展出来这种神经质行为。
阿Q的“精神胜利法”是他在各种挫折遭遇中形成的。他屈服于游手好闲,并安慰自己说:“‘我总算被儿子打了,现在的世界真不像样’……于是也心满意足的得胜的走了。”[16]71受到欺辱时阿Q放弃了复仇的攻击性驱动力,因为复仇会导致更大的羞辱和痛苦,同时这也满足了超我对自尊的要求,让自我产生错觉。在另一场争斗中,他人阻止了阿Q的“精神胜利”,强迫他说:“阿Q,这不是儿子打老子,是人打畜生。自己说:‘人打畜生!’”[16]72
在阿Q的性格心理框架中,现实是强大的,他对此无能为力。为了恢复心理平衡,他不得不向现实中的不利力量屈服,牺牲自我。在一个情节中,阿Q在赌桌上赢了很多钱,但却因为赌徒的诡计而输光。他试图用“精神胜利法”来安慰自己,但也无济于事。这一次,无法控制的攻击欲充盈了他的本我,一触即发。最后他采取了一种新的自我安慰方法:
但他立刻转败为胜了。他擎起右手,用力的在自己脸上连打了两个嘴巴,热剌剌的有些痛;打完之后,便心平气和起来,似乎打的是自己,被打的是别一个自己,不久也就仿佛是自己打了别个一般,——虽然还有些热剌剌,——心满意足的得胜的躺下了。[16]74
通过这一新策略,阿Q将压抑在内心深处的愤怒置换到了一个假想的他人身上,从而防止自我失控。
夏志清认为“精神胜利”归根结底是一种自我欺骗。“精神胜利法”是阿Q唯一的安慰方式,支撑着他度过自己悲惨人生的唯一慰藉。马克思曾说,宗教是人民的鸦片。同样地,“精神胜利法”就是阿Q的个人宗教,因为他和大多数中国男性农民一样,不相信任何既定的宗教。作为个人宗教和个人信仰的“精神胜利法”具有超越时间、空间、阶级、性别、国籍和文化的普遍意义,且这种普遍意义的核心在于它能够安抚超我,发挥其宗教功能。
弗洛伊德在对神经强迫症患者行为与宗教信徒仪式之间的相似性进行研究时,得出结论认为,强迫性神经症是个人宗教,而宗教则是强迫性神经症的普遍形式[2]435。阿Q一再用“精神胜利法”来解决自己的问题。这可以被认为是一种强迫性神经症。在论证强迫性神经症和宗教实践之间的相似之处后,弗洛伊德指出了它们之间的不同之处:“宗教仪式的细枝末节都充满了象征意义,而神经症患者的一些细枝末节则显得愚昧无知,毫无意义。在这一方面,强迫性神经症展现出了一种半喜剧半悲剧的形态。”[2]431在其他人看来,阿Q的“精神胜利”是一种变态行为,是一种精神疾病。对阿Q来说,“精神胜利”是他的人格宗教,可以抑制他本能的攻击,抵御无法忍受的挫折和痛苦。
二、印度式的“视而不见”
在少数几位描绘印度独立后的社会思想状态的作家中,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维迪亚达尔·苏拉普拉萨德·奈保尔(V·S·Naipaul)(1932—2018)是一位佼佼者。在印度,奈保尔既是一个局内人,也是一个局外人。奈保尔具有局外人的敏感性,同时作为局内人也具有对印度社会和文化的熟悉程度,因此他能敏锐地观察到印度独立后各地发生的细微变化。
除了外祖父,奈保尔的父辈和母辈在定居特立尼达后没有再返回过印度。他的外祖父则曾两次访问印度,但在第二次访问后没有返回,而是死于胃病。奈保尔认为,与大多数吉尔米提亚人一样,他的外祖父既抛弃了印度,也拒绝了特立尼达。这也是当代许多印度侨民的窘境:他们不想留在印度,也不属于他们的移民国家。他们表现出一种异化的社会人格,一种边缘化的存在。就奈保尔而言,情况更是如此。印度以一种特殊的方式成为奈保尔童年的背景,这是一个“从未被描述过的国家,因此也从未真实存在过……一个悬浮在时间中的国家”。对他来说,这并不是一种损失,反而为他提供了一个优势,即能够对印度和特立尼达进行观察和评论。
1962年奈保尔抵达孟买,接触到真实的印度。在这期间,他不得不在想象中的“印度”背景下,应对真实的印度和印度人。奈保尔对自己的所见所闻感到困惑和愤怒。他对印度人缺乏公民意识感到震惊:随地排便、垃圾成堆、随地吐痰等。他愤怒地写道:“印度人随地大小便。他们大多在铁轨旁大小便,但他们也在海滩上大小便;他们在山上大小便;他们在河岸上大小便;他们在街道上大小便。他们从不找掩体。”[9]77然而,根据奈保尔对印度人看待事物方式的观察,“蹲在地上的印度人”不会在小说或故事中被提及,不会出现在专题片或纪录片中,人们允许将印度美化。事实上,印度人“看不到这些蹲在地上的人,他们甚至会真正地否认他们的存在”[9]78。也就是说,印度人的一个根本缺陷是“无法或不愿看到事物的本来面目”(Theroux xv)。“视而不见”,这是奈保尔对印度方式的描述[8]75-126。
奈保尔所提出的“集体失明”源于“印度人对污染的恐惧”。印度人制定了“细微的规则来保护自己免受一切可以想象的污染”[9]78。奈保尔在印度还观察到了“象征性行动”:植树周(所值树木的70%因缺乏关注而枯死)、反节日周(一个邦在节日到来之间宣布)、儿童节(报纸头版刊登尼赫鲁先生关于儿童问题的正确讲话,而报纸尾版上报道为贫困儿童免费提供的牛奶)、根除疟疾周(帮助用英语在文盲村里的墙上涂写)。奈保尔指出,“象征性行为是印度的诅咒”“东方人心中对待尊严和功能这两个概念,依赖于象征性的行动:这就是危险的、腐朽的实用主义。象征性的服饰、象征性的食物、象征性的崇拜。印度的象征和无为”[9]89。因此,卫生成为一种偶尔为之的仪式,因为得到了大人物的认可,所以是一种美德。劳动被纳入了印度式的象征主义。
奈保尔提出的另一点是殖民主义和帝国统治在近五个世纪中对印度和印度人民的损害。在印度,“视而不见”的自我防御机制不仅无法接触新事物,反而注定要模仿其他地方已经发生的事物。这注定了印度社会总是与时代脱节。
可以说,在面对英国殖民主义时,印度的“视而不见”导致了印度人智力的迟钝,“被俘虏的思想”[7]191。这表现在很多方面,如对外国事物的简单狂热。殖民主义对印度思想的蛊惑导致印度人模仿英国人,更广泛地说是模仿西方人。奈保尔写道:“复杂的舶来思想在经过印度人的感性反驳后,往往会被洗去内容,变得无害。”[10]414殖民统治后的印度选择“看而不看”自己的过去和现在,“印度盲目地吞下了自己的过去”。为了了解过去,印度不得不借用外来的学科,就像外来技术一样,“历史学带着民族主义的尖锐,这些借来的学科仍然是借来的,这些学科让印度人对自己知之甚少”[10]422。将知识寄生在其他文明上是印度文明的一个伤口,需要很长时间才能愈合。奈保尔认为:“印度和英国的相遇是失败的,它在双重幻想中结束。新的自我意识让印度人无法回到过去,但对印度性的珍视和怀念又使他们难以前进。”[9]238
在《黑暗地区》一书中,奈保尔谈到了自己与“印度人的退缩能力”有共同之处,真正看不到显而易见的事物的能力,他认为“这种哲学在很大程度上也是我的哲学”,这种退缩和盲目的形而上学对自我的维系至关重要。奈保尔如此写道:“它使我在英国长期居住的压力下,完全摆脱了国籍和忠诚;它让我满足于做我自己,教我学会保护自己内心深处所有善良和纯洁的东西,使其免受各种原因的侵蚀。”[11]200印度人对其存在和事物的漠视以规避种族凝视,并使得自己能够从有色人种的身体中抽身而退。奈保尔在《抵达之谜》中认为这一盲目避难所就是“……历史,就像宗教,或像宗教的延伸,是一个人对自己的救赎和荣誉的保护”[11]50。
三、结语
作为一种个人宗教,“精神胜利法”的普遍性已经在第三世界国家的学者和作家中得到了证实。在纪念鲁迅逝世20周年的国际会议上,一些第三世界国家的学者和作家就指出,“精神胜利法”在这些国家是一种普遍现象。早在20世纪20年代,罗曼·罗兰在阅读了《阿Q正传》后就指出,法国大革命之前的法国农民就是阿Q式的群体。威廉·莱尔引用莎士比亚的名言指出“既然耻辱和失败是‘肉体所能承受的千百种自然冲击之一’”,那么阿Q的经历和他应对这些经历的方法并不局限于中国。的确如此,阿Q是一种“国际性的普通人”[6]244。
作为一种集体宗教,在不同国家和文化中,“视而不见”也与“精神胜利法”类似的方式反复上演。毕竟,人类在不利环境下需要情感慰藉、鼓舞士气和合理化的勇气。在奈保尔笔下,印度独立后的“视而不见”虽然是一种退缩和盲目的形而上学,导致了象征主义和对西方的盲目模仿,但“视而不见”也是一种满足自我的哲学,是印度的集体宗教,对自我的维系至关重要。因此,“精神胜利法”和“视而不见”都是典型环境下的典型行为,是对存在主义之问的艺术再现。
参考文献:
[1]Fenichel,Otto.The Psychoanalytic Theory of Neurosis[M].New York:W.W.Norton,1945.
[2]Freud,S.The Freud Reader.P.Gay(Ed.)[M].New York:W.W.Norton,1990.
[3]Hsia,C.T.A History of Modern Chinese Fiction[M].Hew Haven,CT:Yale University Press,1961.
[4]Lin,H.Ah Q’s Victory—Psychological Hygiene[J].Chinese-AmericanWeekly,1940,(2):186-191.
[5]Lin,Y.The Crisis of Chinese Consciousness:Radical Antitraditionalism in the May Fourth Era[M].Madison,WI: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1979.
[6]Lyell,W.Lu Hsun’s Vision of Reality[M].Berkeley,CA: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76.
[7]Miłosz C.The Captive Mind.Trans.Jane Zielonko[M].London:Penguin Books,2001/1953.
[8]Naipaul V.S.A Writer’s People:Ways of Looking and Feeling[M].London:Pan Macmillan/Picador,2007.
[9]Naipaul,V.S.An Area of Darkness[M].London: Picador,2002.
[10]Naipaul,V.S.India:A Wounded Civilization[M].London:Penguin Books,1977.
[11]Naipaul,V.S.The Enigma of Arrival[M]. London:Picador,2002.
[12]Theroux P.Introduction:Naipaul’s India[M]. New Delhi:Pan Macmillan India/Picador India,2016.
[13]Waelder,R.The Principle of Multiple Function:Observations on Over-determination[J].PsychoanalyticQuarterly,1936,(5):45–62.
[14]陈金淦.鲁迅研究的历史与现状[M].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1986.
[15]严江.读《阿Q正传》札记[J].鲁迅研究,1983,(4):51-58.
[16]鲁迅.鲁迅全集[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
[17]邵伯周.阿Q正传研究纵横谈[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9.
[18]张梦阳.中国鲁迅学通史(第二册)[M].广州:广东教育出版社,2002.
作者简介:
龙航航,女,上海理工大学外语学院2022级外国语言文学专业在读硕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