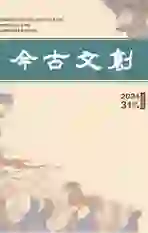论《杜兰葛山庄》母女关系中女儿的自我分化和个体化
2024-08-20王晓
【摘要】《杜兰葛山庄》中的中年女性角色伊迪斯和珍妮佛未能完成与她们各自母亲的分离,因而无法自我分化成完全独立的个体。本文从鲍文家庭系统理论论述了她们自我分化和个体化的失败,使得她们没能向世界展示其独有的特性,成了“无用之人”。女性走向成熟必然会经历失落纯真和建立家庭之外的社会关系的过程。珍妮佛和伊迪斯受困于不健全的母女关系,体现了人们心中那个永远无法长大的、受伤的小女孩,终究无法摆脱少女式的纯真而成长为成熟的女性。
【关键词】自我分化和个体化;母女关系的一体化;失落纯真和社会化
【中图分类号】I56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8264(2024)31-0026-03
【DOI】10.20024/j.cnki.CN42-1911/I.2024.31.008
《杜兰葛山庄》是英国女作家安妮塔·布鲁克纳的作品,于1984年荣获英国文学最高奖项布克奖。小说描写了39岁的浪漫爱情小说女作家伊迪斯逃婚后,来到杜兰葛山庄休假,试图找回自我的故事。伊迪斯通过回忆与现实交错叙事的方式,对山庄中的人物进行了细致的描摹,尤其对被称为山庄失败女性群像的刻画令人印象深刻。
学者们已从女性主义、现代性和后现代性、空间解读、弗洛伊德心理学等不同角度对小说进行解析。本文从鲍文家庭系统理论的角度,分析了小说中的女性角色珍妮佛和伊迪斯与她们各自的母亲关系一体化以及她们个体化失败的成因。本文进一步探讨了女性成熟所必然经历的失落纯真和社会化的过程,并以此来探索她们的成长之路。该小说作为一本女性成长小说,将女性之间,尤其是母女之间复杂而深刻的情感呈现在读者面前。珍妮佛和伊迪斯在通向建立自我主体性的道路上,被以母爱为名的扭曲的母女关系阻抑,她们的个体化受困于融合的、非爱的母女关系,由此导致个体化的失败使她们未能向世界展示她们独特的个性。即使已近中年,她们的身心却始终未能摆脱少女式的纯真,无法进入一个复杂而成熟的成人世界,她们的成长之路还未完成。
一、自我分化、一体化和个体化
(一)龟兔赛跑的隐喻
美国心理学家鲍文认为:“人类所有行为背后的驱动力源自两种相互对抗的生命力量——个体化和一体化之间的相互作用。一种力量使人习惯于遵循自己的内心,变得独立(个体化),另一种力量使人习惯于响应他人的指示,变得有联结(一体化)。自我分化指的是,人们投入和绑定在关系中生命能量的比例之间的差异。分化水平越低,绑定在关系中的能量越多;分化水平越高,个体保留的用于自身功能的能量越多。”[1]60
“每个人都有一种本能的生命力(分化或个体化),这种生命力促使正在发育的孩子,成长为一个具有独立思考、感受和行动能力的人。高度分化的人,也即个性化的人面临他人压力时能够基于理智去坚持自己的信念,而不需要迎合他人的期望。”[1]65
小说中女主角伊迪斯经常提到“这是展现我个性的时候了”[2]30,结果她却总是在退缩和迎合他人的期望中,丧失了自己的独特性。个性意味着独一无二,为自己设定目标和负责,是自我的表达和展示,是将自己与他人区分开来的重要特征,也即个体化。高度个体化的人的自我得到了充分的发展,如果有必要,他在任何时候都可以在群体中成为一个与众不同的人。小说中,伊迪斯和珍妮佛作为39岁的成年女性都展现了较低的个性,伊迪斯性格温顺、缺乏野心,从不对人提要求。她习惯作为陪衬配合他人,是其他人冲突的缓冲国。珍妮佛和母亲形影不离,除了华丽的外表,世人看不到她独特的一面,她一直被认为是母亲的影子,并且是更为逊色的那个。
伊迪斯几次提到龟兔赛跑的寓言,“兔子是什么人呢,她们坚信自己出类拔萃,就没把乌龟当成真正的对手。这就是兔子为什么总赢。兔子在生活中获胜,而在虚构的故事里,从来不会。正是因为现实的生活事实太过残酷,人们才喜欢龟兔赛跑的故事”[2]27。书中寓言里的兔子是能充分展现自己完整个性的人,是高度自我分化和个体化的产物,不被外在环境干扰,朝着明确的目标前进。蒲赛夫人和莫妮卡就是“兔子”类人物的典型代表,她们极端自我,却成功地展示不同于他人的个性。而乌龟顺从传统,是低分化的存在,伊迪斯和珍妮佛更多像是乌龟,她们对人没有要求,习惯配合其他人,甘于面目模糊的附属者的地位。伊迪斯多次表达了身为乌龟的无奈,她渴慕身边活成像兔子一样的女性,充分说明她对展示个体性的向往。
(二)“无用之中年女性”的困境
作者的大部分小说,正如罗伯特·霍斯默指出:“它们都讲述了一个敏感、孤独的中年女人的困境,尽管她敏锐、聪慧,具有强大的学习能力,但却从来没有‘把事情做对’。”[3]《杜兰葛山庄》也不例外,书中的中年女性伊迪斯和詹尼佛展现给读者的就是“从未把事情做对”的失败者,她们始终以边缘人的角色活在社会和各种关系中。
为什么她们聪明努力,却一事无成,始终是局外人呢?这实在是值得深思的问题。伊迪斯写了好几本浪漫爱情小说,虽然有不错的销量,却渐渐脱离时代,连她的经纪人都认为她书中体现的传统浪漫爱情理念已和当代独立女性的需求相悖了。伊迪斯却不想做出改变,并自欺欺人地认为所有女性读者最终还是会被传统的王子公主式的爱情所吸引。表面上是她不想屈从于市场,而实际上她自己创作的初衷是潜意识里迎合母亲因情感失意,沉迷于大团圆的庸俗爱情幻想。在经历了一系列事件之后,她对自己的创作开始产生怀疑,赖以为豪的写作事业实际上也是无用的,受困于母亲的情感操纵。
布鲁克纳小说中对这些“无用之中年女性”作为社会边缘人物的刻画深入人心。书中的女性伊迪斯和詹尼佛,她们看上去潇洒迷人,足够遗世独立,但实质却是在逃避现实。伊迪斯对爱情有不切实际的幻想,没有爱情就不能活,一厢情愿地维持着和有妇之夫大卫的情人关系,在爱情上过着朝不保夕的生活。珍妮佛则整日无所事事,生活没有寄托,沉溺于生活享受,虚度人生。这些都是她们反抗母亲控制,宣示自己独立的叛逆行为,但却缺乏成年人的担当。究其原因是她们没能从和母亲的一体化中分化出来,无法建立主体性,但人与生俱来的独立渴望又让她们以叛逆的姿态无声地反抗母亲。然而她们以为的特立独行,实际上还是落入套,看上去显得清新脱俗,惊世骇俗,实际是故作姿态,这只是为了逃避那些太过真实却无力控制的局面,并非对自我深刻地自省之后采取的行动。她们的努力全部都用来反抗母亲,没有朝着成为一个真正成熟的人努力,因而是无用功。
反倒是伊迪斯看不上的内维尔成了她成长的启蒙导师,指出了真相:“除非你更犀利地审视自己,否则你不会写别的东西。”[2]116这对伊迪斯无疑是深刻一击,内维尔进一步告诉她要以自己为中心,不要把爱情看成人生的全部。她认识到她终究需要把精力用在探索自我和认识自己到底是什么样的人上面,否则她的个性本来就会越来越不被重视,越来越弱,因为那并非真正的个性。
二、母女关系的融合和分离
(一)非爱的母女关系
心理学家弗洛姆指出:“母爱的本质就在于关心孩子的成长,而这便意味着想让孩子离开她。在母爱中,原来融为一体的两个人分离了。母亲不仅必须容忍而且必须希望并支持孩子离开她。只有到了这一阶段,母爱才成为如此困难的事。”[4]荷兰著名心理学家伊基·弗洛伊德认为:“女性如果想要不失去对自己身体的控制,那么她就必须避免两个极端:与母亲共生或疏离。”[5]因此,女儿和家庭尤其是母亲的分离、建立她的个性化和自主性对其健康成长至关重要,而真正爱女儿的母亲会允许并祝福这种分离。
“母女关系并非单纯一位母亲和一位女儿所组成的人际关系,而是由社会性、历史性以及家庭因素共同累积而成的。女儿们看待母亲的方式亦影响着她们性别的自我认同。”[6]蒲赛夫人把长期无法生育的焦虑,投射到来之不易的女儿珍妮佛身上,对女儿极为宠溺,导致母女过渡融合形影相随。蒲赛太太说话的时候,珍妮佛嘴巴微笑的弧度都不变。母女俩的表情几乎一模一样。珍妮佛时刻准备好为保卫母亲而站出来,似乎这是她存在的唯一使命,几乎所有人都认为她们永远不会分离。蒲赛夫人看上去是一个深爱孩子的母亲,但深入探究,这是一种非爱的母女关系。
弗洛姆说:“慈爱的母亲的责任是承担分离的愿望,并且在分离后继续慈爱。”[6]55蒲赛夫人把女儿看成是自己的延伸,阻碍了她成为一个独立的个体,是一种非爱状态。小说中,经常用以下词汇描绘珍妮佛:“孩子气,天真单纯,无忧无虑,表情像窗户一样空洞,像玻璃一样透明。”她大部分消遣就是和母亲购物以及悠闲地度假。而这对一个39岁的女性来说是不可思议的表现,完全缺乏一个成熟的人应有的担当。她本该独当一面,有自己的事业和追求,建立属于自己的社会关系,而不是和母亲缠绕不休,一事无成。
而伊迪斯的母亲则没有一般母亲常有的舐犊温存与无私奉献,反而表现出恐怖女性的阴暗面,以神话学中所谓的死亡之母和坏母亲,带给女儿全方位的毁灭,而女儿则是天使的形象:温顺、听话、无害、乖巧。伊迪斯始终小心翼翼地对待情绪化的母亲,甚至她的写作事业都源自她潜意识里想要讨好母亲。小说中写道:“我可怜的母亲从来没有这样,她只是嘲讽讥笑,大喊大叫。然而,我还是认为她是我可怜的母亲。随着我年龄的增长,我体会到了她的忧伤,她对人生大变的迷惑,还有她的孤独。她生活在一无所知的阴云当中,把她自己的阴云馈赠给了我。”[2]122
《战国策》有言:“父母之爱子,则为之计深远。”母爱的本质是为了分离,而蒲赛夫人和伊迪斯母亲对女儿们的爱,不管是过渡融合的还是邪恶充满控制的,本质上都属于弗洛姆所说的“两人份的自私”。亲子关系在延续生命的本能下,可以作为爱的动力来源,却不能成为控制、主宰的借口。而“我不必成为我母亲一样的人”的信念构成了女儿们自我重造的契机。女英雄之踏上自我追寻的旅程,就是为了离开母亲,害怕变成和母亲一样的人。
(二)女性的失落纯真和社会化过程
然而,人不可能永远活在童年的乐园里抗拒长大,这就像人类走出伊甸园一样,是一种人类在社会化过程中和他人建立关系所共有的失落纯真。珍妮佛和伊迪斯必然要成长,时间已在后面不停地逼促。她们在年龄上都已步入中年,然而在心理和外在行为表现方面却一直缺乏成年人的担当,仍然像处在青春期的少女。
人们赞颂纯真,但纯真难免浅薄,故而丰子恺在缅怀儿童纯真之美,也承认它贫乏低小,写道:“所谓儿童的天国,儿童的乐园,其实贫乏而低小得很,只值得颠倒困疲的浮世苦者的艳羡而已,又何足挂齿?童真之纯美事实上必然也兼具贫乏低小的性质,而往往成为那些社会适应不良的怀乡症候群。”[7]小说中,经常描写珍妮佛和伊迪斯展现的少女般纯真的一面。尽管珍妮佛已经39岁了,她的身体发育良好,但她母亲仍然认为她是个小女孩,珍妮佛也继续表现得像个小女孩。伊迪斯对自己的认知是:“我又不是不谙世事的小女孩,我是严肃认真的女人。”[2]4说明了她心中渴求进入一个成熟的世界,但从第一次婚礼现场逃离的行为,表明了她实质上无法承担婚姻的责任。但在答应内维尔的求婚后,她感觉人生第一次有了成年人的严肃态度,从此以后,她就要进入一个崭新的世界。这表明了伊迪斯一直处在成长和幼稚摇摆不定的状态中,始终没有跨出真正的一步。在又一次拒绝了内维尔的求婚之后,她选择继续与有妇之夫大卫保持情人关系,在这样的关系中可以不用负责,不用给出承诺。她自己也承认她生来就不是为人妻子的料,因而她还是未能建立起真正属于她的社会关系。
个体心理学家阿德勒在《自卑与超越》中指出:“一个人要成为正常而健康的人,就必须通过合作和建设性的姿态将自身融于社会之中,借此获得一种社会意识,即对他人怀有一种社会兴趣。”[8]个体通常与生俱来拥有社会兴趣的潜能,要保证这种固有的潜能在个体后天的生活中被认知并获得充分的发展,儿童时期的母亲便发挥了关键性的重要作用。母亲是儿童最初接触到的,最主要的社会环境,母子关系是以后与他人发生社会关系的雏形。珍妮佛没有自己独立的社交,沉浸于和母亲一体化的世界,对外在世界漠不关心。“这位‘少女’总是跟在妈妈身后,亦步亦趋,显然,只要能陪在妈妈身边,看着她谈笑风生,这位‘少女’对于社交的欲望也就满足了。”[2]204珍妮佛和内维尔的私情,也是夜深人静母亲不在身边悄然进行的,这表明她内心期望摆脱母亲的束缚,但在母亲权威的压迫下,不敢公开行事,只能暗中发展这种扭曲的两性关系。
伊迪斯和珍妮佛仿佛是潜伏在人们心中,那个永远没有长大的、受伤的、寂寞的小女孩。她们因命运被母亲控制而带来的不安,并未随着年龄的增长而化解,而是固守在内心深处的阴暗角落。但失落纯真和建立家庭之外的拟亲缘关系,是人成长过程所要必然经历的过程。
三、结语
珍妮佛和伊迪斯的悲剧,充分展示了过渡融合的非爱的母女关系对女儿们的生理和心理所造成的摧残。小说可谓是失败女性群像的精彩展现,她们失意的原因各种各样,概括起来不外乎是书中大部分女性受困于男性权威的规训,而患上了慢性焦虑。她们言谈举止离不开男人,她们潜意识受到男性权力和意志的影响,甚至包括母女之间的雌竞。母亲们的低分化,在家庭中又传递给了女儿们。小说的结尾,伊迪斯将正在写作的小说手稿收进了箱子里,表明她对自己创作的信念不再盲从,并有了剖析自己内心的勇气,朝着真正的创作性写作的路上前进。
《杜兰葛山庄》可以说是一本女性成长小说,“成长小说展示的是年轻主人公经历了某种切肤之痛的事件之后,或改变了原有的世界观,或改变了自己的性格,或两者兼有;这种改变使她摆脱了童年的天真,并最终把他引向了一个真实而复杂的成人世界”[9]。珍妮佛受困于母女关系的过渡融合,她的成长觉醒之路还未被唤醒,但对自由的渴望已在暗中燃烧。伊迪斯经历了内维尔求婚事件后,开始有了较深刻的存在自觉,这是一种人格成熟的表现,但从她最后回到情人大卫身边的决定来看,她的成长还在路上,任重道远。
参考文献:
[1](美)迈克尔·E·科尔,(美)默里·鲍文.家庭评估[M].王谨一译.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23:60.
[2](英)安妮塔·布鲁克纳.杜兰葛山庄[M].叶肖译.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2016:27.
[3]Hosmer,Robert E,ed:Contemporary British Women Writers:Narrative Strategies[M].New York:St.Martin's Press,1993.
[4](美)艾里希·弗洛姆.爱的艺术[M].刘福堂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8:55.
[5]Iki.Freud.厄勒克特拉vs俄狄浦斯:母女关系的悲剧[M].蔺秀云译.桂林:漓江出版社,2014.
[6]刘惠琴.母女关系的社会建构[J].引用心理学,2000,(06):97-98.
[7]杨牧.丰子恺选集1[M].台北:洪范书店,1984:15.
[8](奥)阿尔弗雷德·阿德勒.自卑与超越[M].黄光国译.北京:作家出版社,1986:43.
[9]Mordecai Marcus,“What is an Initiation Story?”in William Coyle(ed.),The Young Man in American Literature:The Initiation Theme,NY:The Odyssey Press,1969.
作者简介:
王晓,女,江西上饶人,上海中侨职业技术大学,专任教师,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英美近现代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