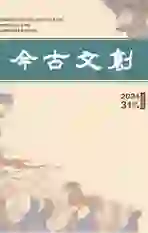《喜福会》中的经验表达与华裔身份重构
2024-08-20肖诗颖
【摘要】美籍华裔作家谭恩美在小说《喜福会》中展现出了四对华裔母女在西方语境夹缝中寻找自我的生存状态。小说里中美文化语境差异所致母女冲突,背后反映出华裔母亲因时空差异形成的文化“失语”。这不仅造成两代华裔女性之间的隔阂疏离,还让二代华裔女性陷入精神失落与自我身份模糊的困境。通过母亲们用“自述”讲述女性经验,在母女之间构成了代际与文化之间的和谐对话,并指导女儿直面生活与婚姻危机。在女性记忆与中国文化精神的传递中,二代华裔以践行中华精神,赓续血脉传承这一方式,完成与母亲的和解,完成对自我文化身份的重构。
【关键词】《喜福会》;女性经验;二代华裔;身份重构
【中图分类号】I7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8264(2024)31-0023-03
【DOI】10.20024/j.cnki.CN42-1911/I.2024.31.007
《喜福会》是美籍华裔作家谭恩美1987年创作的小说,讲述了20世纪50年代移民旧金山的四对中国母女们的故事。四位中国华裔母亲与美国出生的女儿之间的关系面临着互不理解的危机,语境差异让母亲的“爱”不为女儿理解与认同,母亲的女性经验难以言说。小说通过独特的叙事架构与跨越时空的叙事层级,让华裔母亲们用“自述”展现中国语境下独特的女性经验与内在视角,从女性真实生存境况出发,打开华裔母亲这一独特群体的心灵空间,讲述一直“沉默”“失语”的女性经验。谭恩美在小说中对华裔女性经验表达方式的探索为二代华裔女性回归中华文化,重构自我身份提供了一条重要的话语路径。
一、冲突:中美语境差异下母辈经验传递的失败
《喜福会》中塑造的四组母女形象均为在美居住的华裔母女。从文化角度来说,华裔身份她们站在中美两国文化的交叉点上举步维艰;从性别来说,女性身份让她们在以男性为主要话语的美国社会夹缝中生存。母亲与女儿处在同一社会同一家庭,又代表着不同的文化语境,让她们的沟通尤为艰难。吴素云、许安梅、龚琳达和映映·圣克莱尔作为母亲与第一代华裔,她们的成长轨迹深植于中国传统文化背景,心灵成长受到中国语境的深刻影响,即使来到了更都市化的西方环境,心中仍深刻着传统文化的烙印。吴晶妹、许露丝、韦弗莱·龚和丽娜·圣克莱尔作为二代华裔,成长中的文化观念与身份意识更多受西方语境影响,难以对中国文化与中国身份产生深刻的认知与理解,更不用说践行中国文化精神。
当母亲们试图以中国传统的家庭文化(督促或者是炫耀,试图和女儿建立并保持紧密的联系,并像传统家长望女成凤一样,希望让女儿在有保障更优越的物质条件下,完成她们自身未竟的梦想)来链接女儿时,母亲的构想与女儿追求个体自由的思想格格不入。吴晶妹不满母亲对她弹钢琴的期望,这种压抑让她对中国文化产生误解与抵触心理:“我不是你的奴隶,这不是在中国!”在吴晶妹看来,自由翱翔一定比替母亲实现她们的愿望更重要。华裔孩子无法感受到母亲深深的爱,这种不被理解的爱更进一步让她们不理解,也不愿探究母亲身上带有的中国文化经验,于是“喜福会”在吴晶妹眼里只是“有着令(她)脸红的、许多魑魅荒唐的中国陈规习俗的社团”,尽管这些中国元素与中国智慧恰恰是吴素云女性经验的重要构成,亦是她作为中国女性在异国保持自我甚至加强自我的基石。
华裔母亲不合语境的爱还体现在“沉默”上。根据爱德华·霍尔“语义依赖对话背景还是对话语言来传达的成度”把文化大体划分为高背景文化和低背景文化两大类的说法,“沉默”作为其中一种有着丰富意义形式载体,在中国、日本和印度这些东亚高语境国家,具有重要的积极意义。中国传统的日常行为规范将“沉默是金”视为高价值的美德,人们高度赞扬沉默,认为沉默有时比有声语言更具感染力,认为通过沉默能够获得睿智和平静,将它视为磨砺意志的一种行为方式。中国母亲们也将“沉默是金”奉为圭臬,常用沉默传播经验,希望女儿在遇到困难时用沉默让她们学会独立,在意志磨炼中实现自我思考。然而在美国这样的低语境国家,“沉默”失去了价值,甚至丧失了表意功能,“沉默”无法作为经验的传播载体,还可能会造成误解。《二十六道鬼门关》的序言中,母女矛盾源自母亲在“骑车别转过那个拐角,因为那样会摔倒”之后的沉默。母亲沉默的背后是女性日常经验的丰富性与权威性,而在习惯直接表意的女儿眼中,沉默反而在此代表经验的缺失:“你不告诉我就代表你根本不知道!”在意义曲解中,母亲缺乏言说的行为在女儿眼里演变为一种“沉默的暴力”。小说中龚琳达同样以沉默折磨学下棋的女儿,在韦弗莱的叙述中有一段心理描写:“我升到空中,从窗口飞了出去,越飞越高,飘过小巷,飞越一个个屋顶。一阵风将我卷起,推向夜空,直到下面的一切都从我眼前消失,只剩我孤身一人。”平静叙述背后是童年韦弗莱的孤独与迷茫。即使血脉相连,母亲不加言说的教育方式会造成女儿心里的创伤,加速她对母亲所代表的中国文化身份的逃离与怀疑。
二代华裔对中国式教育的排斥与中国文化的否定切断了华裔母亲以家庭身份直接传递经验的渠道,二代华裔无法从生活表象理解母亲,理解中国文化经验。她们面临的困境也十分明显:母亲们无法帮助女儿获得幸福生活;女儿们在男性仍为主要话语的社会面临“失语”的痛苦,在生活与婚姻中没有主见,缺乏抗争精神。谭恩美关注到二代华裔童年至成年后整个成长脉络所面临的代际隔阂与生活危机,在美国现代性背景下面临的孤独无助、自我身份缺失的心灵困境及背后的深层原因。基于此困境如何重建母女间沟通的桥梁?谭恩美通过让华裔母亲在“喜福会”这样一个中西结合的文化空间进行“自述”,让一代华裔女性隐秘的创伤与感性经验得以言说,展露出时代背景下鲜活的女性自我。华裔女儿得以通过记忆讲述了解母亲的另一面向,期望在共鸣中建立起母女沟通理解的桥梁,激活二代华裔的身份重构意识。
二、“自述”:华裔母亲基于叙事策略上的经验表达
谭恩美在小说中运用了独特的叙述策略。小说叙事打破了时空顺序与单一叙述者限制并重新排列。通过将故事深入到了两代每位女性的记忆深处,构成平等对话,母女在此摆脱中西社会中多种因素造成的“失语”,有了独立且平等的自我言说的空间,华裔母亲也获得了传递自己女性经验的契机。
从叙述视角上看,小说中个人篇章符合热奈特《叙述话语》中聚焦模式里内聚焦中的固定式聚焦,即从始至终都从某个单一聚焦的人物观点出发进行对事件的研究。属于某人物的章节就跟随着她的视角与心灵进行书写,充分了解她们的所思所想。通过聚焦华裔母亲的视点,可以看到母亲们并非不苟言笑,她们的情感甚至更为浓烈。许安梅看到女儿婚姻破裂后的痛苦时感同身受,为女儿感到悲愤;江林多看到女儿多年后面临身份重构的困难,心里内疚自责:“我一心想让自己的孩子拥有最佳组合:既适应美国的环境,又保有中国人的品性。可我怎知这两样东西根本无法调和呢?”映映·圣克莱尔为与女儿之间的隔阂深深反思:“我真想对她说:我们双方都迷失了,她和我。”内聚焦视角打破文本的时空限制,母亲们打开自己的记忆,抒发自己的情感,女儿们得以感受华裔母亲真挚的情感与单纯善意的爱,看到它们如潺潺流水般流淌。
从叙述层级上看,交错的主体叙事使母亲与女儿的自我表达构成对话。两代女性在跨越时空的回忆中,得以用成熟理性的眼光审视和反思过去的创伤体验与生活历程,了解曾经严峻的生存状态,以及语境制约下经验传递的有限性。细腻真挚的记忆讲述让女儿们理解母亲行为的必然性与合理性,并发现彼此女性经验背后存在的共性。
基于叙事策略上的经验表达,创伤记忆作为一种特殊的女性经验得以言说。弗洛伊德认为:“一种经验如果在一个短时期内,使心灵受一种最高度的刺激,以致不能用正常的方法谋求适应,从而使心灵的有效能力分配受到永久的扰乱,我们便称这种经验为创伤。”小说中母亲一代基本在童年或青年时期因为社会或家庭原因造成心灵上的创伤,她们希望女儿过上幸福生活,才对女儿格外严格。许安梅的母亲就是传统礼教的受害者,她在家中忍气吞声,因为再婚被赶出家门,被迫远离亲生骨肉,最后绝望服毒而死。许安梅看到母亲的悲剧命运后产生的创伤感能被女儿捕捉,母女关于生活相似的感受在记忆中响起共鸣。
创伤记忆在华裔母女间构建起独特的感性纽带,既让创伤在言说与共同承担中得以抚平,也让母亲意识到文化传承在精神上的重要。映映·圣克莱尔意识到女儿的婚姻面临不平等的危机时,决定打破沉默:“我要用锋利的痛苦刺进女儿坚韧的皮肤,激发她的老虎气质。她就会和我搏斗,因为这是两只老虎的天性,但我一定会赢,把我的精神传递给她。这是母亲爱女儿的方式。”“老虎精神”代表着中国女性独特的反抗精神,在精神的激发中,母女间情感得到升华,两种不同的文明之间最终以一种更加公平的方式完成了精神上的沟通与融合,并导向华裔女儿们精神上的觉醒。
在感性记忆的召唤与理性精神的升华中,华裔女儿觉醒了自己的身份意识。母亲的经历与精神背后所蕴含的中国文化内涵,让她们变得更加坚强,勇于克服生活中的挑战。女儿们深刻领悟过去母亲对她们的关怀和支持,正向的价值思考引导她们进行文化融合与归根的行动。
三、融合:二代华裔基于女性经验指导的身份重构
通过分析母女隔阂与女性经验链接,二代华裔的身份重构的必然性与重要性已浮现。对母辈记忆的追寻让女儿们意识到自己对血缘及中国文化仍保留集体潜意识式的感受与精神内核。在接收中华文化的情感与精神力量后,她们以反抗固有生活显示她们对自身自尊的坚持与女性个体价值的重估。许露丝开始主动反抗自己的畸形婚姻,不再一味地对丈夫妥协而是为自己的利益而呐喊;丽娜·圣克莱尔在承继母亲“老虎精神”后开始不再隐忍,她学会用愤怒向丈夫AA制的生活声讨,追求自己的幸福。她们以行动挣脱代际中延续的女性困境,即使这份反抗的结果尚未可知,但这抗争既是对母亲过去的痛苦经验的体悟,也是她们对待生活的全新态度,是真正理解母亲后身份觉醒的起点。
在二代华裔觉醒后认可中国文化并进行文化身份重构的过程中,谭恩美并未强调人物的反差,性格变换的张力,仍基于每个人物的特点展现每个华裔后代在母辈经验影响与自我选择的过程中,选择与转化中美文化的方式。有的华裔女性从一味排斥一种文化到接受两种文化,但两种文化方式的选择始终保持明显分界。韦弗莱承继了母亲敢于质疑的特质,不让自己完全归于一种文化,将自己变成又中又美的“双面人”,虽并未展现出强大的人物张力,在中国文化与美国文化中反复游离,但作为从小就在西方语境下生长的二代华裔女性,这似乎才是更为自然的发展状态,是实现更好生活的现实选择。谭恩美同样给出了中国读者更喜闻乐见、更欣慰的二代华裔的发展路径——华裔母亲血液里流淌的中国文化最终被女儿重新解码,以二代华裔主动“寻根”的方式,体现对中国文化身份的追寻与回归。吴晶妹以母亲的记忆激活血液中的文化基因,在重新认识母亲的过程中建立起对于中国的印象。当她真切感受到中国土地的存在,文化地理环境与她体内的文化印象发生剧烈的融合反应,母亲传递的文化信息被真正解码:“我们的火车开始从香港进入深圳,霎时,我一阵激动,只觉得额头上汗涔涔的,我的血管突突地跳着,从骨髓深处,我觉得一阵深切的疼痛。我想,妈讲得对,我觉得唯有这时,自己完全变成一个中国人了。”以吴晶妹为代表的二代华裔在对中国文化语境的自觉融入中实现自我的身份重构,将中国的文化特质视为自身基因就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人事物的召唤加速了基因的激活,与双胞胎姐妹的相遇使吴晶妹的血液沸腾,发自内心流露出归属感与快乐:“我终于看到属于我的那一部分中国血液了。呵,这就是我的家,那融化在我血液中的基因,中国的基因,经过这么多年,终于开始沸腾昂起。”吴晶妹对中国的真挚依恋与喜爱,对中国文化特质的双重身份的认知与重构过程,为我们提供了中美文化由矛盾冲突走向融合的过程的可能性。
谭恩美在《喜福会》这一小说中向我们展示二代华裔与母辈、自我以及文化生活和解的过程。她们在沟通与成长中以殊途同归的方式各自完成了对自我身份的体认与重构,这将帮助她们更好地生活,体会与感知幸福。谭恩美同样也为我们提供了海外华裔打破文化隔阂,促进文化交流的新的可能性,小说中多元开放的表现手段背后展现出的尊重包容的文化心态,有利于推动移民群体真正对中国本土文化产生归属感,走进和认识真实的中国,认识真实的自己。
四、结语
谭恩美作为华裔女作家,具有独特的跨语境反思能力。《喜福会》这部小说探讨了华裔家庭关系、女性代际经验和华裔女性文化身份重构之间的联系。作者通过描述几代女性的现实经验,为建立一座跨越中美两国的文化桥梁做出努力。小说聚焦四对母女间的心灵沟通,她们在冲突和妥协中彼此理解,走向新生活的过程,展现出二代华裔女性面对文化焦虑与精神困境中,如何通过文化融合、文化认同的方式帮助自己建立更好的认知体系,更好地生活,展现作者的人文关怀。同时在女性个体记忆的回溯中,大家可以感受到两代女性独特的生活感受与细腻情感,并同样获得源自中国文化深沉而强大的精神力量,拥有与社会进行对话的勇气。这部小说也为全球化的大背景下华裔女性的身份书写提供了参考的文学样本,在平等交流的基础上进行了一次良好的文化沟通实践。
参考文献:
[1]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引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
[2]谭恩美.喜福会[M].田青译.沈阳:春风文艺出版社,1992.
[3]查尔斯·泰勒.自我的根源[M].南京:译林出版社,2001.
[4]Samonvar Larry,Communication Between Cultures.NewYork:Clark Baxter,2001:80.
[5]程爱民,张瑞华.中美文化的冲突与融合:对《喜福会》的文化解读[J].国外文学,2001,(03):86-92.
[6]王丹丹.热奈特的叙事话语理论研究[D].山东大学,2021.
[7]邵韵之.跨文化背景下美国华裔女性“自我”身份的重构——以《喜福会》为例[J].文化创新比较研究,2023,7(19):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