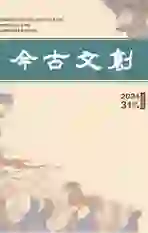天、地、人相融共处
2024-08-20卢应霞
【摘要】《亚鲁王》是贵州麻山苗族地区在丧葬时唱诵的长篇史诗,史诗内容涉及历史、地理、军事、农业等方面。史诗流露出一种宏大且深邃的生命哲学,向我们展示了遵律而行、竞争适应、敬畏自然、生死循环等哲学观点。同时,《亚鲁王》为当前苗族人民的文化认同、麻山地区的发展策略及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团结与发展提供了新思路。
【关键词】生命哲学;《亚鲁王》;三位一体
【中图分类号】I2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8264(2024)31-0013-04
【DOI】10.20024/j.cnki.CN42-1911/I.2024.31.004
一、问题的提出
19世纪末20世纪初期,生命哲学在西方国家逐渐引起主流学术的关注,其试图以人的生命发展过程来解释宇宙世界的生成与发展。西方宇宙观下的生命哲学秉持着鲜明的“灵肉二分”“神人对立”观点。而中国的生命哲学却构建出不同于西方,具有生生之德的天人合一生命哲学,将天、地、人融合成一个体系,生动地体现人在生命活动过程中的主动性。凝聚了无数麻山苗人智慧的创世史诗—— 《亚鲁王》中同样蕴含了丰富的生命哲学,本研究将基于其史实材料,深入挖掘有关生命的创生、适应、敬畏以及死亡的哲学思想,并探讨其对当代的启示与价值。
二、《亚鲁王》中的生命哲学
贵州麻山地区的苗族史诗《亚鲁王》由东郎在丧葬时唱诵,史诗中讲述了麻山苗族人民的创世史、迁徙史、文明史等,内容包罗万象涉及历史、文化、地理、宗教、民俗等内容。苗族人民将史诗《亚鲁王》视为连接上界的中介,他们相信通过亚鲁王的考问,便会回到彼岸世界与先祖共同生活,实现自我的精神超越。史诗从原初生命出发,构建出“嘞冬”世界、天界、地界,将万物与人的生命融汇在同一个大系统中,展现了苗族人民万物同源以及人、神、自然三位一体的万物平等生命哲学。
(一)生命的创生——遵律而行
“天地之德曰生”,天地的生生之德不仅贯穿自然亦贯穿人类社会,“在中国哲学中,既然我们把宇宙看作是根于人的身体的宇宙,看作是人的身体的化身,那么对人的身体何以生成、何以可能的解答其实也就是对宇宙本身何以生成、何以可能的根本解答”[1]。人类的生育观经过几个阶段发展而定型,其分别为自然生人的化生阶段、图腾与女性相结合的感生阶段、男女交媾的性生阶段。中国哲学认为生命的原发生命机制造端于男女的夫妻型伦理,其一阴一阳、相互交感的男女之道逐渐衍生出世间万物。《亚鲁王》也依循这一思路,通过论述人的身体如何生成,逐步上升至自然如何生成,经历了自然生人、男女交媾的阶段,其用大量的篇幅讲述了世间万物的生成,并以大量事例,论证了顺应自然规律、遵循正确生命法则的重要性。
《亚鲁王》史诗一开篇就交代了远古时期的创世过程,麻山苗族先祖经过几代的繁衍创造出“嘞冬”世界、天界、地界三界,而后派遣不同的人对三界进行守卫与万物的创造。等到薄彤出生后造就女人的天,博咚出生后到天外的下方造就男人的地e90f6ad45a12cc6e680c9ca1c3adbb0b286c5e6b910fe1bd5994bbad4e7b0c38。但是他们所造的天地并不和谐,违背了生命之道,天地男女错位导致天不下雨、地不长草。而后觥斗羲又开始造人,“觥斗羲在人头上造角,觥斗羲拿人脚板造趾……他们活着的不会死,他们死去的不再活”[2]33。由于违背生命法则和自然规律,觥斗羲造出的人眼睛竖立,最终致使十二个太阳与月亮同时出现,万物皆亡,世间依旧无半点生气。这种局面直到觥斗羲生董冬穹后才有所改变。“董冬穹造成了母的上半空,董冬穹做出了公的下半空……树木不结果,竹子不拔节。”[2]34“天地交而万物通”男女与天地并举,天地间万物化育,只有经过正确的“男女”交合才能生育出万物。董冬穹吸取错误后又一次造物,经过正确的交合之道大自然才开始孕育生命。天地之大德曰生,天地遵循规律衍生出有生命力的万物,使得世界逐渐多元化。
“天地氤氲,万物化醇,男女构精,万物化生”,董冬穹询问偌、婉后去备下聘礼去娶妻,最终生育七十个女儿、七十个儿子。除了董冬穹造人造物外,《亚鲁王》中关于万物的生发并不局限与此,诺育造人遇不见男人,“诺育哩诺育,你坐的是下面……你爬到上方住,你会娶得丈夫”[2]39“波简磅去和乌利睡,波简磅出怀了……种得好庄稼,繁育了后代”[2]55。《亚鲁王》将空间人性化,一分为二,其上母下公违背了生育之道,使得董冬穹造出的世界不能生育万物。下面没有男人,上面才有男人,男、女、天、地、乾、坤需要处于正确的位置才能进行生命的衍生。《亚鲁王》清晰地展现一幅人类从混沌走向合理秩序的生命起源之图,将男女之交感既“至大无外”地被推广至整个宇宙,又“至小无内”地退返和还原到每一个人。
纵观《亚鲁王》的生命创世,不难看出生命的生成需依据正确的生命法则才得以衍生。在苗族的迁徙过程中亚鲁王依据合适的土地、水文情况进行农业种植;当造成十二个太阳与月亮时将多余的日月射杀,让人们依据正确的日月运行规律有序发展。在重建家园的过程中,亚鲁王的一系列举措都基于特定的逻辑性和规律性而进行。《亚鲁王》向我们展示了生命从何而来,生命怎样生存等问题的清晰脉络,强调人与万物一同被置于自然之中,人们需要遵循规律,发挥生命最大价值,使其不停闪耀。
(二)生命的适应——竞争意识
竞争是生命哲学的核心思想,人们对生命演进进行分析,总结生命规律服务于人们。生命哲学教导人们对生存环境的残酷进行深入认知,同时改善自身去适应和改造世界。[3]在麻山苗族的迁移史、战争史中,我们看见他们为生存所做的一系列活动,看见其“胜者为王,败者为寇”的残酷竞争意识。麻山苗族通过自我的不断努力与奋斗,使得其生命价值与意义充分得到体现。
亚鲁与赛阳、赛霸之间的竞争关系在龙心大战、盐井之战以及哈榕泽邦之战以及运用计谋侵占荷布朵王国中充分展现。在与赛阳、赛霸的斗争过程中,赛阳、赛霸丝毫不顾及与亚鲁之间的兄弟情义,抢夺亚鲁获得的龙心与盐井,也凸显了《亚鲁王》中弱肉强食的竞争思想。在当时的生存环境之下,只有不断进行竞争,才能获取族人生存的资源,同时亚鲁也从竞争中充分展现自己的生命价值与能力,吸引了大批跟随者。
麻山苗族生活环境恶劣,资源较少,无论是和人之间的相处还是与动物之间只有通过不断地竞争才能继续生活下去,只有通过竞争才能保住自己的东西获取新事物。“我不射倒你的熊,那头老熊会咬死我。我不射死你的雄狮,那头雄狮会吞吃我。”[2]74“我们见一头野物,太阳下黑油油的像只黄驹,抬头回望那一瞬,头顶上有花斑像只白面。”[2]104-105“见一头野物长着三只脚,有一只大兽生出三只爪。”[2]135“公龙猛撞亚鲁王船底……公兔撞翻亚鲁王竹筏,三队将瞬间翻入浪底。”[2]154史诗中塑造了熊、雄狮、公龙等比人高大数倍的猛兽形象,从侧面暗示麻山苗人征服自然、获取资源的艰辛。而亚鲁王以及他的军队并未气馁,他们充分相信自我、凭借积极向上的竞争精神和过人谋略,勇敢地同猛兽竞争,在射杀中成熟、壮大,凸显了竞争在征服自然之路上的重要地位。
“它把生命看作是世界的真正基础和唯一实在……认为生命只有克服并超越物质自然的滞碍才能显示其本性和生机。”[4]亚鲁王的生命哲学,在他一次次的战争中、一次次的迁移中充分展现出来,史诗中充分展现了人类进化的曲折性,亚鲁王的祖先们经过多次试错摸索出正确的生育之道,同时正是因为麻山苗人永不言弃的坚强意志,在经过几十次迁徙,在逃亡中不断重建家园,他们越平坝,走山地,闯峡谷,最终定居找到一个自然资源丰富,地势有利的家园——哈叠。在这过程中麻山苗人克服各种障碍,总结规律扩展农业、手工业等的发展,最终获得成功,充分体现了亚鲁王勇于竞争、越战越勇的生命哲学。
(三)生命的敬畏——人与自然的统一
“有天地,然后有万物。”天地万物为一整体,充分体现人、地、天的和谐统一性。史诗中万物皆为神造,出生平等,无高下贵贱之分。苗人对于生命多用类比的形式进行置换,平等地看待宇宙中的任何事物,赋予动物、植物和人一样的生命力,给予自然同等的尊重与敬畏。世界上的一切现象都藏着生命,宇宙万物都是普遍生命流行的产物,将生命与万物贯通,物我混一,生命的起源被置放在多种因素共同作用之下,如《苗族古歌》中认为世间的生物及人类都是沿着从枫树衍生蝴蝶,蝴蝶下蛋,蛋孵化出神灵与生命的衍生逻辑,于是人物同祖,动物、植物等都被看作是有人格意志的事物,并且他们与人类社会一样拥有家族血缘的传承,将人类的生命置放在和动植物生命的同一阶梯,对客体的生命给予高度肯定。这种独特的生命观跨越了不同种类的边界,将自然拟人化,人与万物统一于一个大生命圈,高度显现出苗族群体对生命的敬重,构建出万物和谐的自然图示。
“在麻山苗人的世界里,世间万物都是有生命有灵魂的,山有山魂,树有树魂,各种动物都有灵魂,不能随意触碰,否则会受到罪恶的惩罚。”[5]“牛天,成群的牛渡江而来,大群牛浮水尾随而到……万物跟随来了,万物尾随到了。”[2]221从动物到植物,由于其被赋予了“生命力”,他们被亚鲁王的魅力所吸引一路跟随,人与万物在迁徙过程中逐渐具备同一性与互助性,二者之间相互贯通,有了这些祖宗的帮助,新的家园才得以建立、发展。
他们苗族人群以自身为尺度去理解世间万物,通过探索周遭独特的生活环境去确认自己的自然属性以及同自然的内在统一性。《亚鲁王》认为人生活在自然中,便需要利用自然以获取益处,人与自然共存、共生。在探索自然的过程中,人力是有限的,在此种情况下需要借助外力。史诗中充分借助自然祖宗的力量,“他派祖宗青蛙去察看疆域……派老鹰祖宗察看疆域”,在这里充分利用各个祖宗的能力,以便利对疆域的考察;同时当公雷引发洪水淹没大地,洪水褪去后大地找不到糯谷种,在这种情况下蝴蝶祖宗帮乌利王找到了糯谷种,从而解决了人类的饮食问题,而蝴蝶祖宗也通过此而得以寄生在稻谷上,体现出人与自然的互帮互助,人与自然是一种平等的相互交易关系,构建出人与自然的生命共同体。
在《亚鲁王》中自然界中的动植物被赋予生命并神化,主张人类需要顺应自然规律、尊重自然,否则会酿成大祸导致战争与失败。亚鲁王通过获取龙心被赋予了强大神力,获得了保护族人,守护疆域,使得王室经久不衰的力量,龙心在这里变为一种神授的权利,获得了龙心就获得了神力的庇佑。“七十个王后拿它煮煮不熟,七十个王妃用它烧烤烤不透……七十个王妃用斧砍,铁斧砍不碎。”[2]106“亚鲁哩亚鲁,你第一个来到这里。回去用红布包裹龙心挂上宫梁,他会保住你领地,他会繁盛你疆域。”[2]108亚鲁听取耶婉、耶偌的建议将龙心挂上宫梁后,亚鲁领地被飞舞的雪花铺满,当面临战争时将龙心置于水缸,天地出现惊雷、地动山摇、狂风暴雨等现象,这些现象使亚鲁免除外界的侵扰。龙心在史诗中具有十分强大的力量,它所造成的自然现象是人们无法抵挡的。“你不能带它做生意,你不能拿它赶集。它会给你带来仇恨,它会给你引发战事。”[2]108当赛阳、赛霸知道亚鲁获得龙心后,他们运用阴谋诡计迷惑波丽莎、波丽露将龙心抢夺过去,使得亚鲁与赛阳、赛霸爆发战争,当龙心失去后,亚鲁领地的庇佑全都消失,亚鲁战败,不得不带领族人走上迁徙的道路。
龙心便是自然之力的代表,当有自然之力助力时亚鲁战无不胜,失去后即战败,自然之神和以亚鲁为代表的人类互帮互助,共同创造出亚鲁领地的和谐状况。同时龙心大战中,赛阳、赛霸亦认为得龙心就得益处,“亚鲁得龙心就得七十坝水田,亚鲁有兔心就有七十坡肥土。亚鲁得龙心能占据七十个城堡,亚鲁有兔心就盘踞七十个城池”[2]109。在这里以亚鲁为代表的人,龙心为代表恶神,水田、城堡等代表物,得到龙心即得到下方的物产,也得到上方的庇佑,天、地、人相融,促进亚鲁领地的繁荣发展,形成独特的生命共同体。
(四)“生命”的死亡——循环生命观
在麻山苗人眼中,生命分为肉体与灵魂两部分,肉体消亡后,灵魂就会离开身体回到祖先故地,在祖先故地继续过和人间相同的生活。麻山苗人认为人死后和祖宗一起生活才算幸福生活的开始,于是生命的死亡亦是生命的开始,生命呈现一种循环状态。《亚鲁王》中生生不息的生命循环观混淆了生死之间的界限,亡魂回到祖先故地成为新祖先创造生命,使得世界不断复制。同时史诗中通过与祖宗的对话,寻求魂魄的回归,体现出其希望族群生生不息,世代流传的观念。
生命循环的观点也指导着麻山苗人的日常生活,如史诗中提及“我和大家一起杀牛为你父母送葬,大家和我一起砍马为你父母送行”[2]42。这里的杀牛、砍马仪式在今天依旧能在麻山地区看见,人们通过在葬礼上举行砍马仪式,并唱诵史诗将亡灵超度到祖先的故地,在这里,祖先的故地即东方圣地,东郎作为媒介联结天、地、人,形成天界、地界、祖界三位一体的格局。“亚鲁哩亚鲁,我就要归去祖奶奶那里,谁来为你做菜?波尼桑说,亚鲁哩亚鲁,我就会去往祖爷爷那方。”[2]86“这次我定要叫亚鲁王子归去见祖奶奶,这回我定让亚鲁王子归天见祖爷爷。”[2]91肉身死后灵魂离开肉体,灵魂从世俗社会回归到理想社会,将生命从物质提升到形而上的精神层面,自此人从有限的人生、生命向无限的祖界、祖灵超越而获得永生,这既鲜明地体现了生命循环的哲学观,又表明了人们对生命延续的渴望与追求。
“生者与死者身体之间界限的力量具有重要的连带意涵。”[6]180在《亚鲁王》中同样也存在着生者与死者的关联,以独特的生死观实现生命的循环和对子孙后代、家园疆土的庇佑。
在神话中,死亡并不是生命的最终消逝,而是另一种生命形式的过渡。[7]麻山苗人认为人死后,灵魂离开肉身回到东方圣地继续过着和人间一样的生活,生命侧面来说并没有结束,而是以灵魂的形式继续生活下去,同时死去的人回到东方圣地后成为新的祖宗,创造新的生命,生命继续循环。史诗中认为人死后其尸身会演变为其他的事物,这种理念常见于各民族的神话传说,体现出汉文化与少数民族文化的共通性。“赛扬把亲生儿郎冉郎耶埋在马槐树下……赛扬后悔死了,他拔剑自杀身亡。他也变成十二簇惑,他又变成十二簇眉。”[2]45当赛扬把自己的儿子郎冉郎耶砍死后,他的儿子变为惑与眉等生灵,他自杀后,自己的身体也变成惑与眉等生灵,从肉身转变为生灵实现了生命的延续与循环,也体现出对生命超越的渴望。
三、《亚鲁王》生命哲学的当代价值
(一)有利于苗族人民的文化认同建构以及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团结
在人类社会的发展轨迹中,各民族所拥有的神话故事有着鼓舞精神、维系民族团结、促进本民族文化认同等功能。《亚鲁王》作为苗族口头史诗,具有高度的口碑价值,其在东郎的代代口语相传中,为世人展现了苗族人们的历史轨迹,为苗族人民提供给了民族身份自我认同的仪式支撑。“不少文化群体和部落群体早就开始将其身份认同铭刻在成员的身上。”[6]189在麻山地区的葬礼上,东郎以独特的仪式过程在葬礼上通过“芒就”与唱诵《亚鲁王》为死者灵魂去往东方圣地指路,通过独特的葬礼仪式进行身份认同,形成集体记忆并产生相应的社群反映,促进麻山苗人内部的文化认同。《亚鲁王》从生命的诞生、发展、消亡等各方面展现出苗族祖先的所作所为,为麻山苗人回溯族群记忆展现历史线索,在对历史的回忆中麻山苗人不断加固对首领亚鲁的崇拜感,亚鲁成为麻山苗人共同的精神信仰。通过东郎对《亚鲁王》的不断唱诵,苗族人民进一步掌握自己的来源,增强民族的归属感,强化族群内聚力。
神话是民族的共同意识和精神支柱。[8]在史诗的影响之下,亚鲁成为他们共同的文化信仰,他们将自己视为亚鲁后裔,行亚鲁规定的礼仪,在仪式当中以亚鲁规范家庭中的行为准则,促进家庭的团结与幸福。《亚鲁王》作为地方文化,在对史诗的学习中,麻山苗人不断学习自己的文化,促进苗族人民对植根于本土的身份认同和文化认同的建构。
《亚鲁王》是民族智慧和精神的重要体现,对苗族群众有着巨大的凝心聚力作用,而对其他地区或民族的群众来说,也因其神秘性产生了强大的吸引力。[9]民族间的交流有助于构建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有助于建设各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有助于建立各民族相互嵌入式社会结构,从而达成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根本目标[10],进一步助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强国的建成。各少数民族的英雄史诗以其独有的方式展示了特定群体的生存和发展之道,记录了该群体社会历史发展变迁的延续逻辑,成为反映其生成、发展的历史印记。同时这一类史诗又在最大限度地彰显不同群体之间、群体与自然之间和谐共生,休戚与共的调和逻辑,是天、地、人辩证关系的自然展演。
(二)为麻山地区的发展提供历史参考
麻山地区地理环境相对恶劣,多为喀斯特地貌,当地石漠化较严重,土壤稀薄,耕地较少。在这样的背景之下,麻山地区想要发展就必须因地制宜找到自己的发展之道。在《亚鲁王》中,我们看到亚鲁王在迁徙的过程中充分从土地、水源、安全等自然地理和人文地理等情况来考虑所安邦的寓所,和赛阳、赛霸战争以失败告终后,不得不走上迁徙的道路,在迁徙的过程中亚鲁充分考虑各个地方的自然和人文情况是否有利于族人生存。在《亚鲁王》中这种描述并不少见,从中麻山苗人为我们展示了其因地制宜的思想,族人的生存不仅需要自然亦需要人文,天时与地利需要合一才能更好地促进发展。
人因自然而生,人与自然是一种共存共生的交叉关系,《亚鲁王》全篇为人们展现出的万物有灵思想有助于人们摒弃人类中心主义,重建人与自然的和谐自然观。[11]史诗中无论是人类生命的创生还是动植物生命,都要在遵循规律的大前提下得以发生,如今现代化高度发展,人们对大自然的资源进行了大量开发与利用,在这样的背景下过度的开发使得些许地区自然灾害频发,人与自然是共存亡的一体,我们应该充分秉持《亚鲁王》中人与自然和谐相处、遵律而为的生态观,平等地对待世间的动植物,尊重自然,保护自然。同时麻山地区的发展不应随波逐流地模仿、照搬其他地区的发展模式,应以人为首位,根据不同环境、不同情况实施不同的策略,因地制宜选取最适合人类生存与发展的方法。
参考文献:
[1]张再林.中国古代宇宙论的身体性[J].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04):10-17.
[2]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苗族英雄史诗:亚鲁王[M].北京:中华书局,2022.
[3]龚世雄.生命哲学视域下中国哲学思想研究[J].福建茶叶,2019,41(02):211.
[4]董德福.柏格森生命哲学与中国现代思想界[J].天津社会科学,1996,(01):88-93.
[5]张慧竹.在亚鲁王的庇佑下:麻山苗族的家、家族与村寨[D].贵州大学,2016.
[6]克里斯·希林.身体与社会理论[M].李康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
[7]冉永丽.苗族史诗《亚鲁王》意识特征探析[J].贵州民族研究,2015,36(10):95-99.
[8]萧家成.神话研究的现实意义[J].云南社会科学,2002,(01):44-48.
[9]田晓华.贵州苗族民歌的种类、传承与发展对策[J].遵义师范学院学报,2022,24(05):30-33.
[10]郝亚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视角下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研究[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19,40(03):9-13.
[11]孙秀伟.传统天人合一思想在生态文明建设中的应用[J].遵义师范学院学报,2022,24(01):48-5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