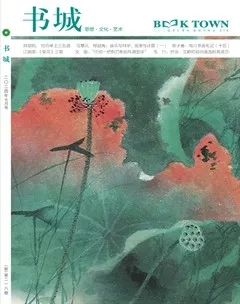电影与非虚构文学如何重构历史
2024-07-18乒乓台
尘埃已在表面落定:马丁·斯科塞斯执导的《花月杀手》获得二○二三年度奥斯卡十项提名,最终颗粒无收,让人大跌眼镜。
故事说的是“美国二十世纪最为黑暗、肮脏的谋杀戏码”:一个世纪前,世界上人均收入最高的奥赛奇印第安族群变成了最容易遭到谋杀的对象,数十起谋杀成为悬案,唯有莫莉一家人的案件水落石出,主犯被绳之以法。
从文本到电影:编剧很懂影帝
电影原著是二○一七年出版的非虚构作品《花月杀手:奥塞奇谋杀案和联邦调查局的诞生》(下文简称《花》),入围了美国国家图书奖决选名单,获得了埃德加·爱伦·坡最佳真实犯罪小说奖。作者大卫·格雷恩(David Grann)是美国非虚构写作领域的标杆性人物,畅销榜上的红人,特别会选吸睛又刺激的题材。他擅长扣人心弦的编年史和犯罪故事,钟爱探险家和杀手的故事,热衷于描写阴谋和背叛,但他书写的故事都是确实发生过的史实。
相比之下,《花》具有格外深远的历史意义,小说一问世就迎来了七位数的翻拍版权竞标,莱昂纳多·迪卡普里奥、乔治·克鲁尼、布拉德·皮特和J·J·艾布拉姆斯等人都曾接触过这个项目。格雷恩从二○一二年夏开始采访和搜集小说素材的工作,“像大多数美国人一样,我在学校时,从未在任何教科书中了解到这些谋杀案的介绍,仿佛这些罪行被从历史中彻底消除了。因此,当我误打误撞发现提及上述谋杀的文献后,便开始着手调查。自此,我便醉心于解决某些悬而未决的问题,以填补联邦调查局侦破工作留下的空白”。
书名已充分表明本书的另一个重点落在“联邦调查局的诞生”上,相比于讲述奥赛奇谋杀案的第一部和第三部,第二部以探员汤姆·怀特为主角,详尽描述了艰辛的办案过程,以及本案大获成功对胡佛创建联邦调查局的意义所在。因为奥赛奇族人深知自身所在的郡县已被白人恶势力全面掌控,无法伸张正义,便在一九二三年要求联邦政府派遣与本州或本郡毫无瓜葛的探员来调查系列谋杀案。怀特直捣虎穴,很快就意识到当地社会的各个阶层、各种官方机构都是共犯,让奥赛奇印第安人的处境更糟糕,无处申冤,一系列投毒致死事件也表明医药系统同样不可信任;白人设定了不公正的监管政策,导致奥赛奇族的财产监护人或执行人大多是当地声名显赫的白人士绅,为这些人侵吞侵占行为提供帮助、打掩护的执法人员、检察官以及法官也属一丘之貉,甚至执法人员本身就是侵占财产的执行人或监护人—堂而皇之地把非法掠夺“合法化”。侦破案件并不难,打破这套规则才难。怀特破案后,绝望地发现,到了庭审阶段,法官竟会找寻、编造各种理由解散陪审团,导致被告凶犯无法被定罪,比如指控布赖恩·伯克哈特谋杀安娜·布朗的案件审理就以陪审团悬而未决宣布告终,白白耗费了怀特和调查局三年多的时间。但对于胡佛来说,只要有一起奥赛奇谋杀案宣告成功侦破,他领导的现代意义上的调查局就有了能炫耀的政绩,足以证明:有一个全国性的、专业性的、技术性的执法力量是多么重要。事实上,此后生发出的不只是联邦调查局和中央情报局,还有对美国政治有重大意义的深层政府(Deep State),这是后话,暂且不表。
怀特的人生故事跌宕起伏。他性格沉稳,心地善良,探此案时大胆启用卧底,办案手法可圈可点。更具戏剧性的是,他在本案了结后主动离职,不再当胡佛的金牌探员,因为他梦寐以求的工作是像父亲那样监管监狱,而本案的两大主犯—欧内斯特·伯克哈特、威廉·黑尔—恰恰被关进了他监管的监狱。“当怀特在不同囚室间巡视时,仿佛是在记忆的坟墓里穿行,因为可以看到曾经在自己生命中出现过的一些人,他们的眼神在铁栏后飘忽张望,他们汗流浃背。他看到了黑尔及拉姆齐,他遇到了艾尔·斯宾塞匪帮的歹徒,他见到了丑闻频出的哈定总统执政期间因为收受贿赂被判入狱的退伍军人事务部前负责人……怀特还遭遇到杀害自己兄长达德利的两名亡命徒。”这一段读来就像一个残酷又隐忍的长镜头,甚至像一个时代的缩影。
怀特的人设非常饱满,在本案之前、之后的故事都值得一读。按理说,据本书改编的电影完全可以把他作为男一号,有充足的正能量,能让人热血澎湃。据说,第一稿就只改编了原著的第二部分。斯科塞斯拿到第一稿剧本后,立刻让莱昂纳多·迪卡普里奥来演怀特。
然而,迪卡普里奥不肯,铁了心要演欧内斯特!于是,编剧写了第二稿,怀特成为两小时后才出场的配角,调查局的故事隐入背景,不再成为重点,但最终得到了原著作者格雷恩的盛赞,因为“忠于历史比忠于原著更重要”。
值得一说的是,该剧编剧是鼎鼎大名的埃里克·罗思(Eric Roth),曾写过《阿甘正传》《慕尼黑》《沙丘》《一个明星的诞生》等名作的剧本。这是一次很有趣的改编,影帝的钦定决定了一个微妙的配角成为主角,也解决了斯科塞斯有过的困惑—汤姆·怀特太像救世主了,会让这部电影显得毫无悬念。怀特是白人,但在这部电影里,白人不应该既是救世主,又是杀人犯。于是,在原著中看似漠然、顺从乃至矛盾的欧内斯特给出了充分的演绎空间。迪卡普里奥显然对自己的演技很有把握,很想演出这个白人身上“平庸的恶”。无奈不少挑剔的观众觉得他这次的演出主要是靠下巴和嘴,表情单一,用力过度。不过,格雷恩忽略了表情管理之类的细节,表扬得一语中的:“我很高兴他们没有拍一些低俗的犯罪片……欧内斯特·伯克哈特确实是更复杂但更关键的人物之一。他不是反社会者。我所做的所有采访和来往信件都清楚表明他对莫莉有真挚的感情。但正如你在电影中看到的:他渐渐深陷其中,成为这些谋杀案的同谋。”
欧内斯特是主犯黑尔的外甥,在原著中的存在感并不算太强,因为原著中的罪案故事是从受害人莫莉写起的,欧内斯特出场仅两页就和她结婚了。但欧内斯特是电影里贯穿主线的主角,故事就是从他退伍后投奔舅舅黑尔开始的,原著中仅以一句带过的学习奥赛奇语的介绍被扩展为黑尔对他的刻意调教—年轻人聆听长辈教诲的时候还会露出憨憨的表情,对黑尔多年来处心积虑谋财害命的内情一无所知。电影在欧内斯特和莫莉相恋、结婚的情节中不疾不徐地展开,但气氛始终紧张,因为很有节奏地穿插了数个印第安人被谋杀的场景,且都以冷血无情的全景镜头展现。我们能在好几对白人和印第安女人的组合中看出阴谋的黑影,但印第安女人们似乎没有对白男们产生警惕,游乐时还会拿各自的男人开玩笑,毕竟,她们是有钱的招婿者,完全没想到白人们会用那些阴险恶毒的招数觊觎自己的财富。正如斯科塞斯在很多采访中强调的,这不是个悬疑故事,任何人都看得出来是白人在谋杀印第安人。
欧内斯特渐渐从舅舅、弟弟和连襟口中得知了越来越多的真相,被派去传话、安排谋杀的时候也显得毫无良知,但电影强调了他和莫莉之间是有真爱的,刻画两人的爱情也在事实上打破了原本历史叙事中的刻板印象和先入为主的偏见,闪现出人性的复杂。尤其当他明白了自己的家人正在一个一个杀死莫莉的家人后,他只能陷入无法自洽的心理矛盾:目睹了瑞塔一家被残酷地炸死后,他露出的惊恐表情并不是虚伪的;当黑尔指责他不以家族利益为先,沉迷于和莫莉的情爱后,他被鞭打时的苦楚也不是装的;为了得到莫莉家族所有的石油开采人头权,黑尔派出内定的医生,在莫莉的胰岛素里下毒,欧内斯特不情不愿地投毒时自己也喝了一口,他的两难也不是演的—但只会出现在以他为主角的电影里。
编剧是懂影帝的,知道要加哪些戏,让这个白人的形象更立体,不让他成为天生的杀人狂,也不是漠然的走狗和帮凶,不是没有良知的恶人。这种人设并非空穴来风,原著中—乃至现实中—欧内斯特在得知爱女病逝后心态崩了,翻供认罪,把自己和舅舅都送进了监狱。事实上,在当时发生的数十起谋杀案中,只有莫莉家人的系列案件得以了结,纯粹是因为欧内斯特选择(或没有选择地)说出实话。他确实是阴谋的执行者,也是受害者。
从受害者到抗争者:给女主加戏
对于没有读过原著、对这段历史毫不知情的观众来说,这部电影的前两个小时并非没有悬念。斯科塞斯所言非虚,但电影并没有展示全知视角,每一方所言所行并非全部真相,因为需要观众担任侦探,自行厘清诸多凶杀案背后的多方勾连,但悬念始终不曾落在“谁是坏人”上,而是落在“谁是好人”上,尤其对于一直苦于没有证据的受害者一方来说,最大的悬念莫过于“我能不能幸存”。
原著的第一部就是基于受害者视角写成的。莫莉一家的女眷接二连三去世,没有人告诉她真相。电影从一开始就展现了莫莉的端庄美丽、可爱聪慧,甚至明知欧内斯特也是“贪婪的土狼”,还是接受了他的求婚。因为她善良,对人性之恶没有黑尔那类人的想象力,观众很容易和她产生共鸣,这在很大程度上归功于莉莉·格莱斯顿(Lily Gladstone)内敛、敏感的表演,演出了爱情和财富带给她的笃定和自信,也演出了目睹亲人惨遭杀害、无处申冤时的悲恸和悲愤。
电影对莫莉的描写符合原著,唯独加了一场重头戏—让莫莉独自去华盛顿请愿,代表整个奥赛奇印第安族向总统求助—这段电影里才有的情节无疑是正面展现了奥赛奇人的反抗,哪怕在某种程度上改写了莫莉的性格,因为在原著中,她在瑞塔夫妇被炸死后非常害怕,乃至闭门不出。
将反抗和顺从同时加于一个被迫归化的印第安女性身上,电影显然期待让女主更出彩,更立体,但电影叙事时空紧凑地聚焦在案件发生前后,因而不得不舍弃前传—女主是怎样成为这样的受害者的?为什么白人必须让莫莉和她的家人们如此惨死?
原著在这一点上做得很好,以莫莉为例,讲述了奥赛奇印第安人是如何一步步被迫接受白人归化的。“一八九四年,七岁的莫莉被父母告知,必须去寄宿制天主教女校就读,如果不这样做,政府就将停发年度津贴,整个家庭就会无米下锅。”印第安专员曾这样说:“必须让印第安人按照白人的方式生活,如果情愿,就来软的;如果不情愿,就来硬的。”就这样,年轻人的语言和思想方式都渐渐不再能够坚持部族传统,再加上石油带来的巨富让他们无所顾忌地享有西方文明的种种奢华,三角钢琴随便买,豪车爆了胎就再买一辆,莫莉的妹妹安娜就是深受这种生活方式腐蚀的印第安年轻女性,酗酒,吸毒,纵情声色。但莫莉不一样,她和母亲莉齐一样恪守传统服饰,遵循传统美德,她总是披着精美的奥赛奇织物披肩,耐心地照料母亲,总能在被迫接受的白人文化和承袭的部落文化之间采取折中、冷静的态度。
就是这样的莫莉,敢于在凶案屡次发生后发表声明:鉴于“犯罪之猖獗”,以及“对于他人之威胁”,她决定对任何提供信息、能将罪魁祸首绳之以法的举报者奖励两千美元现金。此举也招来道貌岸然的威廉·黑尔的附议,还增加了赏金,美其名曰“我们必须立即制止这种血腥的杀戮”。莫莉竟然一直没能看破黑尔的虚情假意,一直和土狼首领相敬如宾,对于她的善良,观众必将痛心。另一方面,黑尔对欧内斯特的洗脑却是直截了当的,谈及莫莉的妹妹罹患“特异类型的消瘦症”、奥赛奇人的寿命不超过五十岁时,黑尔甚至给出了纳粹式的解释:既然这个种族活不长,那不如让我们帮他们早日脱离苦海。悬念必然在观众心中升起:欧内斯特和莫莉真的都相信黑尔的这种说辞、这种做法吗?
当黑尔开始对莫莉投毒,并规划好设立遗嘱,从而将莫莉一家人的人头权揽入自家腰包后,观众对日渐憔悴的莫莉的同情也上升至极点。私家侦探全都铩羽而归,甚至丢了性命,她实在是孤立无援,连身边最亲密的丈夫也无法信任了。怀特所带领的调查局团队拯救了她,同时也摧毁了她对欧内斯特的最后一丝幻想。后来,莫莉和其他奥赛奇人一起努力,终结了腐败不堪的财产监护人制度。
莫莉代表了整个受害者群体,也凝聚了奥赛奇族人的美好和力量。电影中最美的部分都属于她。就连书名也是取自奥塞奇族的成员埃莉斯·帕申 (Elise Paschen)二○○九年写的一首诗—从莫莉·伯克哈特的角度讲述,描述了鲜花盛开的“摧花之月”—“茎蔓较高的花草,如紫露草和黑心菊,偷偷将自己的枝叶伸展开来,肆意截占委身其下的矮小植株理应享用的阳光雨露。这些浮华浪蕊随即凋谢,花瓣散尽,化为春泥。”看似浪漫的书名却有残酷的寓意。
格雷恩用人类学家式的笔法描绘了古老的瓦空大仪式—“奥赛奇人在荒野中搭建起一个舞台,配上了蘑菇形状的金属穹顶,圆形地面周围则是一圈一圈的木制板凳……中心簇拥着用来跟神灵‘瓦空大’交流的一面神鼓,以及几位男性乐师与歌手……无论老幼,都打着绑腿,身着色彩艳丽的饰有缎带的衬衫,膝下还系着若干铜铃,每个舞者均有头饰—大致包括雄鹰的羽毛、豪猪的剑刺以及麋鹿的尾巴—支棱起来后很像莫霍克族(Mohawk)的发髻。……伴着鼓鸣与歌声,这些舞者排成一圈,逆时针方向且舞且走,以纪念地球的转动,脚步拍击地面,铃声叮咚。随着鼓乐节奏与伴唱和声的逐渐加强,舞者们的身体开始略微弯曲,步伐加快,行动精确统一。有人点头,有人振臂,宛若雄鹰。其他人的姿态却好似在警戒或者搜寻着猎物。”电影团队善用影音技巧展现这个族群的美好。当格雷恩到片场观摩时,惊讶地发现剧组完美再现了这个场景,“令我印象深刻的是斯科塞斯和演员们的投入程度以及他们为理解角色和历史所做的大量研究。他们……有点像历史学家,寻找任何能找到的记录、文件,与奥塞奇族的成员交谈……从服装设计到奥塞奇语言的使用,都让我觉得很了不起。奥塞奇人多年来一直致力于复兴并教授他们的语言……电影中有奥赛奇语言专家与演员一起工作”。
特有的电影语言展现了族群神秘的文化传统。莉齐去世前的一幕是超现实的,也是全片色彩最单纯、最艳丽的一幕,她看到祖先们来接她,便带着笑容走向了溪水和草原,如此诗意的死亡信仰对照的却是那么恶毒的谋杀,一切尽在不言中。同样,电影只需一只超现实的猫头鹰入镜,就能充分阐释莫莉危在旦夕的状态。
电影可以展现过往是如何被体验、被演绎的,巨大外力和重大事件又是如何在不同地方具体而微地被感知、被经历的。
重构历史的话语权:
一本书不够,那就再来一部电影
在这部讲述真实历史的电影里,作为一种艺术媒介的电影的长处和短板都很明显。
比如,原著有充沛的空间详述一百多年来白人的掠夺进程,格雷恩的写法很符合非虚构历史作品的设定,开篇就铺陈了历史背景,把奥赛奇印第安人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受到的迫害讲得清清楚楚:奥赛奇人拿到这片富含石油的土地的曲折历史需要追溯到十七世纪,当时,奥赛奇族印第安人主张整个美国中部地区都应当是自己的属地,范围涵盖从今天的密苏里、堪萨斯直到俄克拉荷马一带的广袤地区,并一路向西,延伸至落基山脉。一八○三年,托马斯·杰斐逊总统从法国手里购得路易斯安那,其中就包括了奥赛奇族世代生息的土地。杰斐逊曾对自己的海军部长坦言,奥赛奇族是一个伟大的部落,“我们必须言行得体,因为在人家的一亩三分地,我们的力量弱得可怜”。面对平均身高超过六英尺的奥赛奇族勇士,总统也曾赞叹他们是“我们见过的最精壮的男人”。但仅仅四年后,杰斐逊便迫使奥赛奇人放弃了阿肯色河以及密苏里河之间的大片土地。奥赛奇族头人“别无选择,或者签约割地,或者与国为敌”。随后的二十余年里,奥赛奇族人被迫放弃了世代繁衍生息的约一亿英亩土地,最终在堪萨斯州西南约五十乘一百二十五平方英里的狭小区块内,觅得栖身之所。也就是在那里,开掘出了石油,结果却导致白人监护人在一九二五年前,直接从其奥赛奇族印第安人的账户里夺取了八百万美元之巨的资金。
和许多非虚构作家一样,格雷恩查阅、使用了未公开的资料文档,“包括数千页的联邦调查局档案、大陪审团秘密听证的证言,法庭庭审记录,线人的报告,私家侦探的工作日志,假释、保释记录,私人信笺,以及一位参与破案的侦探与他人联合撰写但尚未公开出版的手稿、日记,奥赛奇部落议会记录、口述史,印第安事务办公室的实地调查记录,国会档案,司法部的内部备忘录及电文,犯罪现场照片,遗嘱及遗言,监护人报告以及谋杀案件中的有罪供述等”。作者好比是自发的考古学者,去挖掘,再重述,打通不同场域间的深层血脉关联,把阶级、种族矛盾和联邦调查局体制联系起来,挑战了主流话语权力。
因为这段历史始终被刻意掩藏,不要说历史文献,就连《花》也被列入俄克拉荷马州教育系统的禁书,不让年轻人知道。在涉及黑历史方面,美国官方的这类做法实属福柯所谓“话语即权力”之典型:作为政治技术的这种“权力”带有类似司法功能的支配力,渗透于社会实践主体之中,难以被人们感知,却又无所不在,管束甚至役使社会实践主体,使其成为“合格”的社会人。
电影不可能拍成科教片,但电影可以作为一种呈现历史的媒介,或者借用娜塔莉·泽蒙·戴维斯的话来说:“电影人不再是历史学家领地中的偷猎者,而是重视历史的艺术家。”(《电影中的奴隶:再现历史真相的影像实验》,姜进译,上海教育出版社2022年)
历史电影可以是关于过往的思想实验。尤其,对于原本隐藏在黑暗中的历史局部而言,电影能极大程度地吸引眼光,鼓励思考和评论,甚至唤起情感,完成传播媒介功能。即便斯科塞斯并不打算拍一部严谨的历史电影,但拍出来的这部剧情片从立场、精神到细节都忠实于非虚构文本展现的史实。斯科塞斯将其最擅长的黑帮题材和美国二十世纪初最骇人听闻的迫害印第安人事件完美结合起来—用将近两小时的篇幅逐一展现白人群体的阴谋罪行,但所有罪犯并非严格从属于帮派,而仅仅是基于贪婪的利益关系达成的松散、随机的组合,只有当事态发展到不可收拾的地步,阴谋团体的始作俑者才会动用家族、共济会、司法体系等组织形式向其成员施压。从传播效应的层面说,这部电影因其耀眼的主创团队、出色的执行力,抵达了更多受众,弥补了一本书之所不能及。
另一方面,书籍多由个体完成,电影却是绝对意义上的团体合作,即便有导演的印记。研究调查工作是由编剧、设计师、服装和道具专家、实景地选择者、选角导演、演员、作曲和编曲等人共同完成、分头执行的,甚至往往在杀青剪辑后遭到制片方的干预。这种创作方式和文本写作有着天壤之别。对于《花》的题材而言,这恰好让上述的扩大效应更具体地、对更多个体产生了影响力。
从文本到电影,众多创意工作者的合作证明了历史需要重构,也可以被重构。对被禁言的黑历史而言,被更多人看到、记住就是一种重构。理解也是一种重构,当影视工作者让我们亲眼看到瓦空大仪式后,我们对瓦空大的理解就能更深一层,深及感官;当莉莉·格莱斯顿把莫莉的喜怒哀乐演绎得如此逼真后,我们对奥赛奇人遭受的暴行也更能感同身受。这些,都是重构过程中的浓墨重彩。电影人的同情不能以倨傲的姿态、煽情的手法,批判也不能以说教的方式。电影语言、场面调度、剪辑节奏都在有意识地呈现主创团队的立场,人物塑造、演员表演在很大程度上展现了人性对于历史事件的潜在推动力,因为历史既是客观的事件,也必然落实于个体的心理。
电影似乎更能让我们领悟历史是叙事。和关注集体动态的历史书不一样,电影必须落实在个体经验中—因为个体是历史的最终承担者。
当然,电影也不能述说一切。媒介本身的局限、戏剧化处理必定会带来不同程度的夸张或缩减。原著的第三部分写的是其他案件的后续,以及这段历史对奥赛奇后代的影响,被命名为“杀戮文化”,内容远远超出了黑尔的罪行,是一种“更深层次、更黑暗的阴谋”,而联邦调查局的局长胡佛却选择了忽视。也许,在这部电影中不给胡佛留太多镜头是正确的。
局长的大名是必须提及的,在结尾。但这个结尾有点出人意料—案件相关人的结局是以精简的舞台剧形式叙述的,唯独莫莉的讣告是斯科塞斯亲自站到镜头前念完的—这让剧情片一下子收束了戏剧性,归结到了真实的历史中。斯科塞斯选择自己出镜,当然不是因为没有好演员能演好,显然是在“敲黑板”“划重点”。这一幕让我们最终确认:他希望完成某种希望,电影是他发力的平台。在他这一生完成的电影里,拍了太多小众群体,拍了太多暴行,拍了太多主流不爱听到的声音,他走出了小意大利区,走进了美国历史更深处的阴影。
所以,尘埃尚未落定,甚至永不落定,只有明面上的奥斯卡奖杯金灿灿的,丝滑地嵌入政治语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