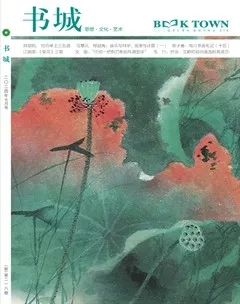乔治·艾略特如何遭遇斯宾诺莎
2024-07-18毛竹
一八四三年,二十四岁的玛丽·安·伊万斯第一次读到斯宾诺莎的作品时,沉寂近两百年的斯宾诺莎哲学在英国正处于被重新发现的风口浪尖上。(按,乔治·艾略特本名玛丽·安妮·伊万斯,直到1856年创作和出版她的第一部小说时,她才采用乔治·艾略特为笔名。22岁时她将自己的名字改为玛丽·安·伊万斯,1851年来到伦敦后改名玛丽安·伊万斯。本文将按照她当时的不同名字来称呼。)按照通行的看法,斯宾诺莎写作的那些“在地狱之中锻造的书籍”本应不会与尼采笔下的“道德主义小女人”乔治·艾略特产生任何关联,然而令人颇感意外的事实却是,在成为小说家乔治·艾略特之前,哲学女青年玛丽安·伊万斯曾经有过一段长期阅读与翻译斯宾诺莎的往事,或者更确切地说,翻译斯宾诺莎的《伦理学》构成了《威斯敏斯特评论》(The Westminster Review)杂志编辑和撰稿人玛丽安·伊万斯投身小说写作之前所做的最后一项长期工作。
这里存在一个有趣的论题。要知道在维多利亚时代,公开谈论与研究被打上“无神论”与“异端邪说”烙印的斯宾诺莎哲学,在某种程度上仍然是一种社会禁忌。那个时代,斯宾诺莎的著作长期以来仅在小范围的智识圈层流传,作为普通中产阶级家庭出身的独立女性玛丽安·伊万斯,为何年纪轻轻就接触到了斯宾诺莎的作品?这个问题涉及斯宾诺莎哲学在英国维多利亚时代的接受史,以及作为英国第一批传播斯宾诺莎学说的知识分子之一的乔治·艾略特在其中所起的作用。
一
众所周知,以“caute”(谨慎)为座右铭的斯宾诺莎在其短暂的一生中仅有一部冠名《依据几何学证明勒内·笛卡尔〈哲学原理〉的第一部分和第二部分》(Renati Descartes prinipiorum Philosophioe pars prima et secunda demonstrata,1663)的作品以实名发表,而其一六七五年完成的《伦理学》(Ethica)曾在出版前被叫停,只在一个有限的小型朋友圈之内传看。一六七七年二月斯宾诺莎去世后,才由其友人编订出版。一六七七年九月四日,斯宾诺莎曾经的熟人、宗教改宗者尼古拉·斯坦诺(Nicolaus Stenonus)向罗马及普世宗教裁判所首席圣部(Supreme Sacred Congregation of the Roman and Universal Inquisition)检举了斯宾诺莎,认为其哲学具有异端危险的倾向,此后斯宾诺莎的作品逐步被梵蒂冈天主教会列入了“禁书名录”(Index Librorum Prohibitorum)。由此很长时间内,人们只能通过斯宾诺莎的敌人为了攻击其思想而转述的只字片语来了解斯宾诺莎的观点,以致斯宾诺莎思想不仅缺乏传布,而且还极易遭到歪曲。
斯宾诺莎的生平遭遇也同样如此,只有两部严重失之偏颇的斯宾诺莎传记是在他死后不久写作的:《斯宾诺莎先生的生平》(La vie de Monsieur Benoît de Spinosa)可能是斯宾诺莎的朋友让·马克西姆廉·卢卡斯(Jean Maximilien Lucas)在一六七八年完成,直到一七一九年才出版;一七○五年,路德宗的德国牧师约翰·柯勒鲁斯(Johannes Colerus)出版了《论耶稣基督从死亡中真正复活,反对斯宾诺莎及其追随者:连同从其遗作和仍然活着的值得信赖的人的口头证词汇编而来的这位哲学家的精确传记》。柯勒鲁斯并不认识斯宾诺莎,他的资料主要来自斯宾诺莎生前最后租住住宅的房东夫妇,他的传记也带着明确反对斯宾诺莎哲学的先入之见。这部传记要比卢卡斯的传记早出版十四年,而卢卡斯的传记出版后旋即遭禁,只有少数几本被允许在特定读者群体中流通,以至于在后世人们眼中,柯勒鲁斯的传记俨然成了关于斯宾诺莎生平的权威版本,而柯勒鲁斯本人甚至似乎从未听说过卢卡斯版传记的存在。
围绕斯宾诺莎哲学的批评之声,自从一六七○年《神学政治论》(Tractatus Theologico-Politicus)以虚构的出版商和错误的出版地点匿名出版之后不久便不绝于耳,这些批评以及当时保守的社会风气,构成了斯宾诺莎生前推迟发表《伦理学》的充足理由。不过斯宾诺莎同时代批评者们的共识之一,就是极为小心地不把斯宾诺莎学说的全貌通过引文的方式呈现给公众,通过这种策略,他们曾经在很长时间内,有效地阻止了斯宾诺莎哲学的传播。可以认为,第一次向公众展示斯宾诺莎学说梗概的著述是,一六九七年由法国胡格诺派学者皮埃尔·贝尔(Pierre Bayle)撰写的《历史和批判辞典》(Dictionnaire historique et critique)中的一个简短而具有高度偏见的词条(尽管这个词条是这部辞典中最长的,但它显然远不足以概述斯宾诺莎),他把斯宾诺莎描述为“一个系统的无神论者”。这种看法在当时是一项极为严重的指控,很长时间内主导着人们对斯宾诺莎哲学的认知。
但皮埃尔·贝尔也是最早将斯宾诺莎作为哲学家的平静而有道德的生平最大范围地展现给读者的写作者之一,从此斯宾诺莎的形象便成了一位“有德性的无神论者”。这显然是一种矛盾修辞法,因为按照通常的理解,无神论者作为最邪恶的魔鬼代言人,往往最不可能具有德性。皮埃尔·贝尔大量采用了柯勒鲁斯传记中,有关斯宾诺莎节俭、平静且从不忤逆世俗道德习俗的例子,展现了作为哲学家的斯宾诺莎在现实生活和政治生活方面的审慎与成熟。据说斯宾诺莎一生中曾经多次有机会接受来自他人提供的年金俸禄和大学教职,但他仍然选择蜗居在海牙的一个租金低廉的小房间,以极低的物质欲望度过了大部分人生。这种有选择地建构出来的斯宾诺莎生平,连同他匿名出版的那些带有玫瑰花纹样的作品一道,在很大程度上暗示出了“Sub-rosa”(玫瑰花下,意为隐匿)的神秘讯息—不但斯宾诺莎的作品充满各种谜团,就连其生平细节,以及其著作的各种版本信息,也全都笼罩在历史的重重迷雾之中。
由此,尽管存在重重禁忌,斯宾诺莎充满矛盾而又令人着迷的思想形象,仍然激发了大量的文学创作。例如最早的地下反宗教文本《论三大骗子》(Traité des trois imposteurs),最初在一七一九年的印刷版本中就曾以《斯宾诺莎的生平与精神》(La Vie et l’esprit de Spinoza)为题发表。这部曾经以多个匿名版本、多次秘密印刷并且流传甚广的小册子分为《斯宾诺莎的生平》和《斯宾诺莎的精神》两部分。《斯宾诺莎的生平》是斯宾诺莎的简短传记,据传作者为让·马克西姆廉·卢卡斯;而《斯宾诺莎的精神》则是一篇非常肤浅且不得要领的散漫论文,显然完全没有表现出斯宾诺莎的精神。此外,由尼古拉·弗莱雷(Nicolas Fréret)创作的《色拉叙布鲁斯给留西坡的信》(Lettre de Thrasybule à Leucippe,1722),据说也深受斯宾诺莎哲学的影响,它使近代早期的无神论成了一个哲学上值得尊敬的传统。
这些只是对斯宾诺莎哲学漫长的接受史的一缕浮光掠影的描述。十八世纪末和十九世纪初德国围绕斯宾诺莎的“泛神论之争”(Pantheismusstreit)为斯宾诺莎的德国接受史投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一七七四年,弗里德里克·雅各比把斯宾诺莎哲学介绍给了他的朋友约翰·沃尔夫冈·冯·歌德,此后历经海涅、莱辛、雅可比、摩西·门德尔松、谢林、诺瓦利斯、施莱尔马赫,以及康德“哥白尼革命”的洗礼,“死狗”(莱辛语)般的斯宾诺莎哲学得以复兴,展现出了完全不同的思想维度。在这场“泛神论之争”中,“无神论者”(atheism)斯宾诺莎摇身一变,成了至少是一位与世无害的“泛神论者”(pantheism)或 “无世界论者”(acosmism)。由此之后,斯宾诺莎不但并非渎神,反而成了诺瓦利斯笔下“醉心于神之人”(Gott-trunckener Mensch,这个术语也成了后世描述斯宾诺莎的思维定式,尽管诺瓦利斯补充说,这个属于斯宾诺莎的神大抵非常乏味)。这段漫长而曲折的斯宾诺莎接受史,构成了哲学青年玛丽安·伊万斯接触斯宾诺莎的史前史。
二
德国斯宾诺莎复兴的余波很快传到了英国。尽管英国剑桥学派长期以来具有批评斯宾诺莎、将斯宾诺莎与本土哲学家霍布斯相提并论的古老传统,但在启蒙时代的英国,斯宾诺莎哲学也随亲德分子的引介得以广泛传播。一七三八年,威廉·沃伯顿(William Warburton)发表了《摩西的神圣立法》(Divine Legislation of Moses),这部作品中斯宾诺莎作为极度不虔诚的幽灵多次出现,威廉·沃伯顿重复了皮埃尔·贝尔和早期剑桥柏拉图主义者对斯宾诺莎无神论的指控,只不过与其他斯宾诺莎批评者们最终实现的结果一样,在批判斯宾诺莎的同时,也传播了斯宾诺莎的声名。
同一时期的珀西·雪莱、塞缪尔·泰勒·柯勒律治和艾尔弗雷德·丁尼生等诗人,也曾打算2c8fb4ada82dbf9c5a5982f959ebf21b在英国尝试斯宾诺莎主义。早在一八一七年,柯勒律治就在他的《文学传记》(Biographia Literaria)中提到过斯宾诺莎,对于柯勒律治来说,斯宾诺莎是通向谢林的一站,谢林哲学中充满了斯宾诺莎主义。威廉·华兹华斯同样如此,他沉醉于自己的本性,以及斯宾诺莎的“醉心于神”。
复兴斯宾诺莎哲学的重任,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杰里米·边沁和詹姆斯·穆勒创办的《威斯敏斯特评论》杂志实现的。一八四三年,乔治·亨利·刘易斯(George Henry Lewes)在大量参考德国哲学和文学文献的基础上写作了一篇题名为《斯宾诺莎的生平与著作》(“Spinoza’s Life and Work”)的文章,第一次试图在英国公众面前为斯宾诺莎辩护。一八五一年,玛丽安·伊万斯开始担任《威斯敏斯特评论》的编辑和撰稿人,日后她将是斯宾诺莎《神学政治论》和《伦理学》的第一位英译者。威廉·海尔·怀特(William Hale White)曾于一八五二年到一八五四年在《威斯敏斯特评论》杂志社工作,十九世纪五十年代他曾与玛丽安·伊万斯一起为出版商约翰·查普曼担任校对,并与她一同寄住在查普曼的房子里,日后他将是批判与引介斯宾诺莎的主要人物,也是《知性改进论》和《伦理学》最早的英译者之一。一八八三年,他翻译的《伦理学》英译本正式出版。一八五五年七月一日,詹姆斯·安东尼·弗劳德(James Anthony Froude)关于斯宾诺莎的生平和哲学的长文发表在《威斯敏斯特评论》上,与此同时,玛丽安·伊万斯正在翻译斯宾诺莎《伦理学》的第四部分,这篇文章标志着英国知识分子日益认识到了斯宾诺莎的重要性。而我们也可以推测,此时担任《威斯敏斯特评论》编辑与撰稿人的玛丽安·伊万斯有可能读到过这篇文章,甚至就文章内容与之交流讨论。
自从一八五三年开始,已婚分居的乔治·亨利·刘易斯正式成为玛丽安·伊万斯公开同居的伴侣,他也是在斯宾诺莎翻译上协助她,并帮她与出版商斡旋的中间人。若我们比照一八四三年,乔治·亨利·刘易斯与玛丽·安·伊万斯之间暂无交织的生命轨迹的话,事情将会变得非常有趣。是年,二十六岁的刘易斯完成了《斯宾诺莎的生平与著作》雄文的写作,尽管这篇作品迄今已经很少被研究者提到,但无可否认他对斯宾诺莎哲学的通盘理解仍是较为准确的;与此同时,二十四岁的玛丽·安·伊万斯则在这年二月致查尔斯·布雷一家的朋友、斯普林希尔学院的神学教授弗朗西斯·瓦茨的一封书信中,首次提到了斯宾诺莎,她说自己没有如期还书,因为自己正沉迷于阅读斯宾诺莎。这两个彼此还并不相识的年轻人,都在以各自不同的方式接触斯宾诺莎的拉丁文本—刘易斯身处伦敦,玛丽·安偏居考文垂。
只不过乔治·亨利·刘易斯与斯宾诺莎的接触则要更早。他在另一篇写于一八六六年的关于斯宾诺莎的文章(“George Eliot’s Spinoza: An Introduction”)中曾回忆说,十九世纪三十年代,他曾与一些业余哲学家定期在一个伦敦小酒吧聚会,“友好地碰撞不同观点”,这群人中的一位德国犹太人买到了一本阐述斯宾诺莎体系的德文研究著作。刘易斯写道:“那时英国读者还看不到关于斯宾诺莎的任何介绍;除了含糊不清的描述或荒谬的曲解,什么都没有。这对我来说更有趣,因为我碰巧渴望了解这个神学上的贱民—毫无疑问,大概因为他是一位被排斥的人,而我当时正遭受社会迫害,这种迫害使所有偏离公认信条的行为变得痛苦,我对所有被抛弃的人都有一种叛逆的同情。”不久后,刘易斯在二手书摊豪掷二十先令,买下了一本斯宾诺莎拉丁语《遗著集》(Opera Posthuma,1677)。他写道,在这个“激动人心的时刻……我把它带回家,就好像它是女先知的叶子”。
至此可见,直到一八四三年,斯宾诺莎的声名对于英国的知识分子圈层而言早已经不再陌生,只是其著述与思想仍处于极少数人涉及的领域。不过从书籍流通的层面上看,刘易斯已经可以在书摊上碰巧购买到一本斯宾诺莎的原著(尽管这种机缘很可能极为难得),青年学者玛丽·安·伊万斯也已经能够较为容易地拜托她的朋友查尔斯·布雷和卡拉·布雷,从柯勒律治曾经的一位医生罗伯特·布拉班特那里辗转借到一部《神学政治论》的拉丁文复本(此时斯宾诺莎作品的英文译本尚未出现)。正如克莱尔·卡莱尔的判断,他们这代英国人已经为迎接斯宾诺莎主义的洗礼做好了准备。
三
此后的故事,我们依然可以从玛丽·安·伊万斯写给朋友的信中得知。一八四九年四月十八日,她“正在翻译斯宾诺莎的《神学政治论》”,她说自己非常渴望从事斯宾诺莎研究;一八五四年十一月八日,在与刘易斯结伴逃离英国社交圈,造访魏玛和柏林期间,玛丽安·伊万斯开始翻译斯宾诺莎的《伦理学》。此后“斯宾诺莎”的名字频繁出现在她的日记中,直至译本在一八五六年冬季最终完成。至此,我们已经来到了青年哲学学者玛丽安·伊万斯成为中年成功小说家乔治·艾略特的分水岭,此后鲜有资料显示,乔治·艾略特再像青年时代那样,继续集中大量时间阅读与研究斯宾诺莎,尽管她小说中的斯宾诺莎主义因素,成了后来既读斯宾诺莎又读乔治·艾略特的极小圈子内津津乐道的话题。
实际上,乔治·艾略特的早期读者极少会将其与斯宾诺莎的异端学说相提并论,道德主义俨然成了乔治·艾略特及其小说挥之不去的经典标签。在其真实身份与性别曝光之前,读者们曾经想象这位总是进行道德说教的作者应该是一位善良的乡村男牧师,因为刘易斯控制了艾略特与读者的评论往来,并且为了保持匿名,刘易斯对外称呼乔治·艾略特为“我的牧师朋友”,对内则拣选不那么刺耳的评论转呈艾略特。《米德尔马契》发表后,刘易斯向出版商布莱克伍德先生讲述了一则笑话:都柏林博览会的开幕式上,有人注意到大主教的眼睛老是盯着帽子里面看,还以为他在虔诚地聆听布道,没想到他是在偷着看《米德尔马契》。
作为身处维多利亚时代的女性,道德困境始终伴随着艾略特的生平和写作,尽管她或许并不是当时意义上的好女人,但她必须表现得像个好女人,这是她的生平与小说的道德困境之所在。同样,对于身处宗教审查时期的斯宾诺莎,尽管他的哲学或许不是传统意义上的虔诚神学,但他也必须表现得像个醉心神学的好哲学家,或者应当被塑造成一位讲究道德的好人,这也是构撰他的生平与哲学的伦理学悖论之所在。
尽管斯宾诺莎的著述因其离经叛道引起轩然大波,但是根据柯勒鲁斯的记载,斯宾诺莎本人却从未试图挑衅公序良俗。斯宾诺莎的女房东曾因自己能否凭借信仰进入天堂而惴惴不安,斯宾诺莎安慰她说:“你信的宗教很好,不必再找另外的宗教,你当然能够得救,只要你真心虔诚地信奉它,你就能过平静安定的生活。”(《斯宾诺莎生平》,收入《斯宾诺莎全集》[第1卷],龚重林、曹忠来、王宏健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21年)同样,在完成费尔巴哈翻译后,玛丽安·伊万斯在一封信中表示自己不会再去挑衅大众关于信仰的情感:“十年前我会反对许多事情,现在的我会觉得自己太无知,道德敏感性太有限,从而无法自信地表示反对:在许多问题上,我过去曾经喜欢表达智力上的差异,现在我喜欢感受情感上的一致。”(The George Eliot Letters)
作为乔治·艾略特的读者,在评论艾略特究竟如何遭遇斯宾诺莎的时候,我们应当总是非常小心。毕竟在一八六五年十月二十八日,在致莎拉·亨内尔的信中,当谈到歌德如何阅读斯宾诺莎的时候,艾略特如此提醒我们:“在我看来,阅读一个人的作品,要比阅读别人对他的评价好得多。尤其是当这个人是一流的,而‘别人’是三流的时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