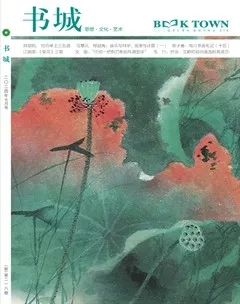批评何为:重审门肯—白璧德之争
2024-07-18杨靖
一九一七年,美国文学批评家H. L. 门肯(H. L. Mencken,1880-1956)在《充当文学破坏力的清教主义》(“Puritanism as a Literary Force”)一文中,将清教主义定义为“一种挥之不去的恐惧”(haunting fear),因为它一直“担心某人会在某个地方享受幸福”。在门肯看来,天然患有“道德洁癖”的清教主义严重束缚了美国文学的自由表达和自我发展,犹如健康肌体上长出的毒瘤,必须加以铲除—这一观点和同时代另一位文学评论家布鲁克斯(Van Wyck Brooks)的主张遥相呼应:后者在《清教徒之酒》(The Wine of the Puritans,1908)中将清教主义视为美国的“文化短板”(cultural shortcomings),并断言唯有根治这一痼疾,方能抵达“美国的成年”(America’s Coming-of-Age)。
日后门肯和布鲁克斯在评价马克·吐温的问题上发生争执:布鲁克斯批评马克·吐温后期向加尔文主义屈服,压抑了他的艺术天才;门肯则坚持马克·吐温是反抗美国清教文学的样板,认为在美国现实主义文学三大家(马克·吐温、亨利·詹姆斯和豪威尔斯)中,马克·吐温革除清教积弊的态度最为坚决,成效最为卓著,对于美国文学的自立与成熟“贡献良多”,堪称美国“民族文学之父”。在此后的文学史中,马克·吐温一跃而为“美国文学中的林肯”,可见门肯之慧眼和判断。一九五○年,著名文论家埃德蒙·威尔逊(Edmund Wilson)宣称,门肯“毫无疑问,是自坡(Poe)以来我们最伟大的文学评论家”;传记作家乔希(S. T. Joshi)在《门肯论美国文学》(H. L. Mencken on American Literature)中,褒赞门肯“在建立美国文学经典方面厥功至伟”,洵非溢美之词。
门肯十岁时偶然读到《哈克贝利·费恩历险记》,从中发现了迥异于欧洲文化传统的“粗犷的个人主义”。这“可能是我一生中最惊人的事件”,正如他后来在《自传》中所说:“马克·吐温多么伟大!他高高在上,与世隔绝,就像复活的拉伯雷(Rabelais),观察着人类的喜剧,嘲笑着人类永恒的欺骗!他对于宗教、政治、艺术、文学、爱国主义、美德等方面的虚假事物有着多么敏锐的洞察力……”更重要的是,马克·吐温“嘲笑他们,但并不经常带有恶意”—这也是门肯终生奉为圭臬的批评家的准则。
门肯对马克·吐温作品中“乡土的市侩气”不无微词,却又称赞他在《哈克贝利·费恩历险记》中抛弃了他一贯沉溺于其中的“狭隘的乡土主义”。照门肯的看法,马克·吐温的文学作品中表现出来的这种“超越美国国界的丰富想象力”恰是他最伟大的地方。此外,作为《美国语言》(The American Language,1919)的作者、语言学家的门肯对马克·吐温式的美国方言大为激赏。与此同时,他更“识别”出马克·吐温作品中蕴含的传承自欧洲文化的“书卷气”:马克·吐温以自己的天才“在丰沃的想象世界自由驰骋,他超然物外,游刃有余地醉心于用喜剧揭示人性的弱点,并对其加以鞭辟入里的尖刻讽刺。所有这些,让人不免联想起那些文艺复兴时期的伟大艺术家”—事实上,门肯不仅将马克·吐温视为愤世嫉俗的拉伯雷(《巨人传》作者),而且将他比作嬉笑怒骂的斯威夫特(《格列佛游记》作者),甚至视之为这两位讽刺作家的合体。马克·吐温反对繁文缛节,针砭宗教伪善,憎恶道德主义—这一切都很符合门肯的文学旨趣,也是门肯对马克·吐温始终赞誉有加的主要原因。
身为《美国信使》(American Mercury)等报刊的文学编辑,门肯以“审稿迅速”(并反馈审稿意见)著称—他破天荒地允许作者“一稿多投”,由是扶植了包括辛克莱·刘易斯、舍伍德·安德森、尤金·奥尼尔、威拉·凯瑟和菲茨杰拉德在内的一众青年作家,其中最为耀眼的是德莱塞。正如早年发现马克·吐温一样,门肯为德莱塞深刻而准确描摹美国社会现实的天才所折服,并为之呐喊欢呼。从一九一一年的《珍妮姑娘》(Jennie Gerhardt)开始,门肯与德莱塞书信往还不断,数量惊人;门肯读过德莱塞众多手稿和校样,并为德莱塞几乎每一部作品撰写评论。门肯在自己主编的《时尚人士》(Smart Set)上发表德莱塞的作品,以此抗议文坛对这位离经叛道作家的打压。尽管德莱塞被称为“文笔拙劣的大作家”(索尔·贝娄语),但门肯却坚信,德莱塞“那丑陋的笨拙和粗犷恰是他令人惊喜的思想稳定性的一部分,他对巨大的文字工程驾轻就熟,对人物性格有着超凡的感受”。此外,门肯还意识到,无论《美国的悲剧》有多少缺陷和不足,“作为一部人类巨著”,它依然“充满了探索和庄重的尊严,有时甚至能够达到真正的悲剧的高度”。
从一定意义上说,正是声望卓著的门肯为初登文坛的德莱塞铺平了道路,并在德莱塞作为小说家的成长过程中一次又一次鼎力相助。当然,这不仅是门肯为德莱塞个人所作的努力—门肯认为,所有的美国评论家都应该为小说家做出同样的努力,因为这是评论家的职责所系。在一九一四年十一月写给《大西洋月刊》编辑埃勒里·塞奇威克(Ellery Sedgwick)的信中,门肯坦言:“德莱塞把关于《巨人》的所有短评都寄给我了,大概总共有一百篇。其中没有哪一篇对他的创作思想作出一点系统性的论述,也没有哪一篇提供了任何建设性的评论。他读了那些评论之后,感到越发糊涂。在我看来,一个这样诚实而有天赋的艺术家应该有权利从他的祖国得到更好的回报。”门肯巨笔如椽—传记作家蒂乔特(Terry Teachout)声称普通读者阅读门肯书评时常体会到“一种秘密放纵”(a secret indulgence)的快感,而当时的新锐作家听说门肯要评论他们的新著时则感到“惊恐万状”—对于建立和巩固德莱塞的文学声望至关重要。
门肯对德莱塞的“英雄主义”气概也极为推崇,后者尽管饱受道德审查官指摘(《嘉莉妹妹》因“有伤风化”被查封,小说家沉寂将近十年;自传体小说《“天才”》被发现“淫秽段落75处,亵渎神明17处”,结果遭封禁长达五年),但仍坚守艺术理想,不做任何妥协。门肯于一九二一年写道,像德莱塞这样的艺术家,“永远不会成为时代的卫道士,他会始终反叛自己所处的时代……他最好的作品永远是在他积极反叛周围的文化氛围之时创作的,并有意识地与那些安然享受这种文化的人势不两立”。无独有偶,一九三○年,第一位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美国作家辛克莱·刘易斯在致辞中也坦承:“没有他(德莱塞)披荆斩棘地开拓的功绩,我怀疑我们中间有哪一位—除非他心甘情愿去坐牢—敢于自由地表现人生、表现生活的美以及人的恐惧。”门肯平生最不能容忍包括清教主义在内的一切正统思想,并始终坚持要敢于冒犯绝大多数人,他在《批评附识》(“Footnote on Criticism”,1922)一文中断言,“只有在激烈斗争的氛围中”成长起来,“文学才能繁荣”。
作为严肃的文学批评家,门肯尽管视德莱塞为马克·吐温的“文学继承人”,但也从不讳言他对德莱塞连篇累牍的废话和漫不经心的文风之反感,并宣称后者“对抽象事物永不满足的胃口”—尤其是“对政治的神学般的热情”—“扼杀了他的艺术”。门肯高度赞扬《嘉莉妹妹》的艺术成就,但对“欲望三部曲” (Trilogy of Desire)—《金融家》《巨人》和《“天才”》持保留意见。他认为其中多“堂吉诃德式的”(quixotically)哲学思辨和无动于衷的细节堆砌(如同左拉一般令人生厌),但大部分人物形象却“像费城做馅饼的女人一样邋遢”。在门肯眼里,德莱塞“幼稚的哲学思考”(puerile philosophizing)和对“崇高正义事业”的追求,导致了他最终的失败—“他的一生就像一头四处寻觅的松露猪(truffle-hunting pig);到后来再也没有写过任何可读的文字。”一九二六年,二人分道扬镳。
门肯力挺德莱塞,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后者遭遇了评论界清教主义的无端攻击(门肯称之为“天真道德主义”[naive moralism]):这些人义正词严地指出,嘉莉妹妹这样先失身(一名推销员)后私奔(同酒店经理)的坏女人,理应受到惩罚—或流落风尘或身陷囹圄,然而在德莱塞笔下,她摇身一变,反倒成为受人追捧的名伶(并将落魄的酒店经理一脚踹开),这“大大超越了普通美国小说的道德界限”(德莱塞也因对嘉莉妹妹的同情收获一枚绰号“嘉莉哥哥”)。在此类文学的道德伦理批评中,最引人注目也最具杀伤力的评论来自哈佛大学法语文学教授欧文·白璧德(Irving Babbitt)。
作为“新人文主义”运动领袖,白璧德倡导阅读古代经典,重拾人类黄金时代的美好回忆,以此涤荡现代人麻木衰朽的心灵。在《文学与美国的大学》(Literature and the American College,1908)一书中,白璧德指出:“有些古代作家和现代少数几个最伟大的作家可以被看成是文学界的恒星。我们完全可以以他们为坐标来确定自己的方向……它们脱离了一切狭隘的地方主义,值得被看成普遍和典型的东西。”正是从这一厚古薄今的立场出发,白璧德将绝大多数现代派文学贬斥为颓废文学:约翰·多斯·帕索斯的名作《曼哈顿中转站》作为“腐蚀现代美国社会的堕落艺术和道德败坏的典型”,被他讥讽为“文学的梦魇”;德莱塞的《美国的悲剧》在他眼中是“真正让人痛苦的作品”,而人们之所以身陷痛苦乃是由于他们“失去了生活的目的和方向”,其言下之意暗示德莱塞本人的创作思想大可疑问。由是,白璧德以“污水池的迸裂”作譬喻,警示美国作家必须恪守“古典人文主义的自律”。
白璧德以学院派文化名人的身份在报刊著文,对美国文学中粗俗(vulgarity)和自我放纵(self-indulgence)的倾向发起征讨,并隐然将矛头指向门肯。在一篇关于辛克莱·刘易斯作品的评论中,白璧德以霍桑小说的“原罪”观作参照,总结刘易斯小说的寓意是告诫美国人不可“背离他们祖先的道德现实主义(moral realism)”—美国人道德水准日益下降,鼓励并“纵容”小说家向传统道德习俗发起挑战的评论家(如门肯)显然难辞其咎。在白璧德看来,由于缺乏古典人文精神和道德关怀,门肯的写作目的并不在于引导而在于“泄愤”。正如白璧德在文中所言:“门肯先生写作的效果是产生傲慢而非谦卑……(他)把自己想象成高高在上的神祇,对无边无际蔓延的‘愚民阶级’鄙夷不屑。”作为法国文学研究专家,白璧德联想到了同样憎恶资产阶级的福楼拜—“他在收集资产阶级愚蠢行为方面表现出的勤奋,堪比门肯先生……可惜如今这一场反对资产阶级的喧闹战争已经到了收益递减的地步”—并预言门肯这一派的批评不久将“宣告破产”。最后,白璧德以福楼拜名言(“通过责骂白痴,一个人就有可能自己变成白痴”)为他的雄文画上了圆满的句号。
这样的战书显然是门肯无法容忍的挑衅,何况刘易斯和早年的德莱塞一样也是他的心头至爱,岂能任凭他人强制阐释、随意曲解?《大街》甫一问世,门肯便发表重磅书评,宣称刘易斯对小镇生活的辛辣讽刺“鞭辟入里,厚重深沉,比伊迪丝·华顿的十几本书更重要”,而与当时占据主流地位的豪威尔斯式粉饰太平、温文尔雅的“乡镇神话”相比,也更为真实可信。一年半后,《巴比特》出版,门肯赞誉它的质量“胜过《大街》两倍”,惊呼它绘制了一幅比他本人想象的“美洲愚民更为凶猛的肖像”—“我相信,我了解巴比特这一类型。二十年来,我一直致力于探索它的特殊性。而刘易斯以绝对的忠诚度描绘了它。”根据传记作家的说法,正是出自门肯之手(single-handedly)的这一系列评论将刘易斯置于“美国文学(乃至世界文学)的版图之上”。
一九一九年,门肯推出《偏见集》首卷(其后数年间陆续推出6卷),猛烈攻击包括白璧德在内的文坛“雅士派”(genteel tradition),不仅尖锐地指出美国知识分子(博士、教授、院士)的软弱性(“渴望精神安逸,怯于熟虑深思”),更指明这一心理疾病的根源在于清教主义—其虚伪的道德观、陈腐的文学理念、狭隘的地方主义等合谋阻碍并遏制了美国文学的“原创性”。
日后文学史家将这一场争论戏称为“书籍之战”(Battle of Books)—以门肯为崇今派,以白璧德为崇古派。白璧德论断“整个现代实验文学,不仅在艺术和文学中,而且在生活中,都因为没有创造新的标准而濒临崩溃”,并讥讽门肯的文学评论近乎“智性的杂耍(intellectual vaudeville),而非严肃的批评”。作为回应,门肯在《偏见集》第二卷起首以《国民文学》(“The National Letters”,1920)为题发表十余篇檄文,猛烈抨击“雅士派”的清教遗风。在《新英格兰的灰烬》(“The Ashes of New England”)一文中,门肯认为,在半个多世纪的时间里,上述崇古派一直在影响和操纵着美国的文学、文化和社会习俗,并以清教领袖的身份审查文学—而他们审查的结论是,现代文学“与我们距离太近,因而不美”,远逊于希腊罗马经典。由此,门肯将白璧德、莫尔等人称为“严肃的文学验尸官”—在他们眼里,“唯有死亡才能为艺术家所犯下的大奸大恶赎罪”。
似乎意犹未尽,门肯又在《孤独的艺术家》(“The Lonesome Artist”)一文中将白璧德等人与臭名昭著的康斯托克(Anthony Comstock) 相提并论—后者强烈反对“有伤风化”的文艺作品,主导了美国历史上喧嚣一时的“禁邮(淫秽书刊)”运动。据统计,该运动以“美国反堕落协会”之名,压制言论和思想自由,累计焚书逾十五吨。门肯将康斯托克贬称为“美国的道德总监”(leader of America’s moral eunuchs),认为他和白璧德等人一样,是美国历史上“充当文学破坏力的清教主义”之化身—他们挥舞道德大棒,扼杀了文学的创新与发展(参见鲁迅《摩罗诗力说》),对二十世纪初的美国知识界造成了无可挽回的恶劣影响。
门肯对清教主义的文学审查官深恶痛绝,认为他们不仅毁了文学创作,也毁了文学批评。什么是真正的文学批评?在《对批评的批评之批评》(“Criticism of Criticism of Criticism”)一文中,门肯提出批评家应该充当文学艺术家和观众(以及读者)之间的“催化剂”—如果观众对一件艺术作品能够产生“自发的敏感”,也就“没有必要进行批评”,然而事实是,观众通常无法洞见艺术的真谛,因此,批评家的职责是“让艺术作品为观众而活。他也让观众为艺术作品而活。这一过程带来理解、欣赏和智慧的享受—而这正是艺术家试图创造的效果”。清教主义批评家谈“性”色变,并不代表他们道德纯洁,更不表示他们人格高尚,恰恰相反,这反证了他们的“孱弱”和虚伪。在门肯看来,与豪威尔斯式“微笑的”现实主义相比,率“性”直言的作家如薇拉·凯瑟、菲兹杰拉德、海明威才代表了美国现实主义文学发展的方向:他们的著作“真正是美国民族主义情绪上升的证明—或许是真正意义上的民族主义的第一道曙光”。
从这个意义上说,门肯“向清教主义开战”的文学批评为二十世纪初保守而倦慵的美国文坛注入了强大的活力。它们开启了文学艺术家代言美国(以及世界)各地中下层民众生活的可能性—而不仅仅是亨利·詹姆斯和伊迪丝·华顿笔下珠光宝气的“纽约-波士顿”上流豪门生活;普通民众可以用浓烈的美国方言表达对性、金钱和地位的正常欲望,而不必含糊其词假装清高。换言之,也正是因为门肯在舆论方面扮演“清道夫”角色—他在一九二二年与摩尔论战的一篇文章中写道:“我的文学理论,就像我的政治理念一样,主要基于一个主要思想,即自由思想……清除地上腐烂的垃圾,驱赶阴魂不散的老妖,帮助艺术家获得自由,是我的职责所系”—使得清教主义对美国文学的负面影响相对减少,现实主义和自然主义文学得以长足进步。德莱塞、菲茨杰拉德、海明威等作家的创作摆脱了外在的束缚和羁绊,更容易表现美国的地方特色和精神风貌,这也为美国文学向现代主义过渡奠定了思想基础。正如传记作家蒂乔特在《怀疑论者:门肯传记》(The Skeptic: A life of H. L. Menken,2002)一书结论中所言,门肯的文学批评是“美国脾性(temper)无与伦比的精确表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