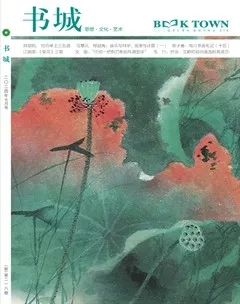“任何一把剃刀都自有其哲学”
2024-07-18文敏
村上春树早已在读者心中建立起那种“村上体”的风格,其独特之处在于他内敛独省的气质,又在于他能让大众接受并产生共鸣,二者并行不悖。据村上春村作品的加拿大英译者泰德·古森说,多伦多书店里被偷走的书,村上春树作品占压倒性多数。村上本人也曾在旧金山报纸上看到过自己的书最容易被人“顺手带走”的报道,这似乎可以视为其读者关联度的一个佐证。村上的作品,没有太多的灵魂分裂和挣扎,没有深渊式绝望,没有无奈之下的撕痛感,没有天才式的疯狂或偏激。所以,他的艺术美感不难消受。在一次访谈中,村上说到从德累斯顿大轰炸中幸存下来的美国作家库尔特·冯内古特去看望濒死的父亲,老人说:“你的小说里,坏人一个也没出现啊!”这让冯内古特当即陷入沉思。村上不禁想道:“那么说来,我的书中也基本没有坏人出现啊!”
我觉得,这些特质尤其集中地表现在村上所有的短篇作品中。一个稳定输出的高产作家,就像“一千零一夜”中那位妃子那样,每晚在枕边讲一个奇思妙构却不致令人夜不成寐的故事,在高潮处戛然止住,抽身离去。这种欲言而止的魅惑,实是亘古弥新,所以,我部分地赞同一位网友的评价:赞美村上春树就像赞美一家品质稳定的连锁店。我爱村上春树就像爱这乏善可陈又稳定可控的现代生活。不过,用村上自己喜欢的语言来说,那就是“任何一把剃刀都自有其哲学”。
一
村上还真的写过一篇名为《山鲁佐德》的短篇小说,收在《没有女人的男人们》那部短篇集里。“她每和羽原做一次爱,都会给他讲一个有趣又玄妙的故事,就像《天方夜谭》中的王妃山鲁佐德一样。当然,和故事中不同,羽原完全没有在天亮时将她杀掉的想法(当然,她也从来没在羽原身边睡到过早晨)。她给羽原讲故事,只是因为她自己想那样做。或许也是想慰藉一下每天只能待在家中的羽原。”读者自始至终不知道这羽原是什么人,为什么被关在这里不能自由行动,由这样一个女人每天来为他做饭、做事及做爱。山鲁佐德这一名字是羽原给她取的,但她的外表却和《天方夜谭》中的美丽王妃完全不沾边,是一个全身开始增生赘肉(就像用油灰填满缝隙一样)的城市家庭妇女,下颌已有几分变厚,眼角的皱纹已难以用护肤品掩饰。但她的确是讲故事高手,每次在枕边将一个个近乎变态的故事徐徐展开,在悬念高潮处突然结束,犹如事了拂衣去的古代传奇。
村上春树曾说:“我觉得写长篇小说是一种挑战,写短篇则是一种乐趣。假如说写长篇犹如开拓一片森林,那么短篇更像是经营一个花园。”迄今为止,他出版了十部短篇集,我个人最喜欢的是《东京奇谭集》《电视人》《没有女人的男人们》。作家王安忆说过,短篇小说就有些像钻石,切割面越多,收进光越多,一是要看材料的纯度,二是看匠人们的手艺如何。也就是说,短篇小说是作家用来炫技的,奇巧的构思与文字只是用来精致地表达一个想法,一段情绪,或是某种发现。有评论家认为村上的短篇胜于长篇。
村上的短篇小说基本属于都市故事,类似张爱玲的“在平常中寻找传奇,在传奇中寻找平常”。主人公们都有某种遗世孑立的特质,对外界与人际关系介于关心与不关心之间。性格温和而隐忍,中庸而平稳,结婚也好独身也罢,有意无意间处于一种仅需面对自我的孤独状态。几乎所有的短篇小说都以第一人称叙述,主人公的最大愿望是与周遭环境保持距离而不起冲突,即使是面对从天而降的突然变故,他/她也不会有过激反应,甚至过于平静淡漠:“啊?居然是这么回事?那,就这样吧。”
有一篇《驾驶我的车》,收在《没有女人的男人们》那个集子里,被改编为长达三小时的电影(西岛秀俊主演),成为村上影响最大的短篇之一。故事中主人公家福与妻子均为中年演员,妻子患病去世,他料理完后事继续自己的生活,仍去剧院登台演出。由于出过交通事故,他被吊销了驾照,那段时间有朋友介绍一位年轻女司机替他代驾。身为演员的家福,生活中却沉默内向,而那个叫渡利的女司机也是非必要不出言。两人毫无交流地过了两个月,然后借契诃夫戏剧《万尼亚舅舅》的台词,在贝多芬弦乐四重奏的背景音乐中慢慢打开了一些话头,一点一点说起家福过世的妻子,每合作一部戏必与搭档上床的隐事,据他所知就有四人。眼下,他正与妻子最后一个出轨对象高槻同台合演,并一次次约请对方喝酒长聊。高槻不知道家福是否探悉他与自己女人的隐事;或者说,家福不知道高槻是否知道自己已经知道,两人都太需要向对方倾吐,从对方那儿探知些什么。他们经常在位于根津美术馆后面巷子里一个不起眼的小酒吧里喝酒。说到柜台上的调酒师,是一个四十岁光景寡言少语的男子。一只灰色的瘦猫,弓作一团睡在墙角装饰架上。爵士乐老唱片在唱机转盘上旋转着。不知为何,他们每回约见都是下雨天。轻柔安静的雨,在流水声中被抹去,听不见了。只是触及皮肤的空气的细微变化,让人感觉似乎在下雨。
这篇小说触动人心的东西很微妙,并非那个在文艺题材中被反复咀嚼的故事,而是对于人本身的一些意外发现。比如,家福发现,世间的饮酒者大致可分为两类:一种人是为了给自己追加一些什么而饮酒;另一种人则是为了从自己身上消除一些什么而买醉。高槻的饮酒方式明显属于后者。他是想消除什么呢?直至某一天,他告诉家福:“如果真要窥看他人,那么只能深深地、直直地逼视自己。我是这么认为的。”这番话,似乎是从高槻身上某个幽深之处浮现出来的。尽管可能仅是一瞬间,但他终究打开了封闭的门扇,听起来是发自内心的无遮无拦的心声,至少那不是演戏。家福不声不响地盯视对方的眼睛。这一次,高槻的眼睛没有避开。两人久久地相互对视。并且在对方的眸子中发现了遥远的恒星般的光点。这是村上春树对孤独和沟通的基本认知态度:“人生基本是孤独的,但同时又能通过孤独这一频道同他人沟通。”“人们总要进入自己一个人的世界,在进得最深的地方就会产生连带感。或者说人们总要深深地向下向内挖洞,一直挖下去,就会在某处同别人连结到一起。”
这样的词语,这样的情景,这样的人物,你会在村上很多作品中见过。“家福”也好,“谷村”也好,“木野”也罢,或是“渡会”“凯锡”,等等。或者可以这样说,村上春树似乎从来只是在描述着某一类人,就是他自己那一类人,“要窥看他人,只能直直地逼视自己”—应该是他自身的经验。所以提到村上春树,读者也许就会想起一张无欲无求、神情淡漠的东亚脸—听着爵士乐,喝着威士忌,以均匀的速度跑步。那样的脸上有无可奈何的失落,有着对失落的平静接受,有温和却孤绝的气场,以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我这人生简直像在橡树顶端的洞穴里头枕核桃昏昏然等待春天来临的松鼠一样安然平淡”。当然,有些作家就是这样让人记住他们的,比如莱蒙托夫让人记住了“当代英雄”们,屠格涅夫则让人想起苦难的“多余人”(诚然他们是更伟大的作家)。可是据说这样的特色正好在一定的审美频道上与许多人发生了共振,成为喜欢他的原因。
二
川端康成的《雪国》中有这样的句子:“穿过县界长长的隧道,便是雪国。夜空下一片白茫茫,火车在信号所前停了下来。”那种空灵、恍惚的气质很川端,所以一直也被认为很日本。到了村上春树笔下,他说雪:“札幌开始下今年第一场雪。雨变成雪,雪又变成雨。在札幌,雪并非那么罗曼蒂克的东西,总的说来像名声不怎么好的坏亲戚。”他也许是最不像日本人的日本作家,他有空灵,更多是灵异:“细看之下,这人瞳仁呈不可思议的颜色。黑中带有茶色,又约略掺进些许蓝,且左右掺的程度不一样,简直就像左右各想其事。手指在膝头不住地动。我产生一种强烈的错觉,以为那十指马上就要离开他的手朝我这边走来。”这一段让人想起什么?是不是很像茨威格《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中的年轻赌徒?村上的短篇小说有许多向欧美经典致敬之作,这一点使他在日本作家中的异质感相当突出。
如村上自己在访谈中所说,他的许多作品中主人公是“中性的”。这个所谓的“中性”,是指人物不能有一个显著的血缘家系背景。这可以被看成是村上对于“家庭”占有相当分量的日本文学传统的背离。他想把他的主角设定成一个个独立的、基本不涉及亲情的个人。在《舞!舞!舞!》中,那对完美男生与完美小姐结合的夫妻,婚后感情非常融洽,只因妻子来自每位成员都被牢牢绑定其中的大家庭,各方面匹配又相爱的两人只好以离婚收场,再以前夫前妻的身份偷偷幽会。村上曾引用自己翻译的雷蒙德·钱德勒的一个句子,每个人都“像灯塔一般孤独”,用来描述一个个选择自由与孤独的都市人。
在《巴黎评论》的访谈中,他对此有过明确解释:
巴黎评论:谁是你的榜样?哪些日本作家对你有影响?
村上:我小的时候,还有少年时期,都没怎么读日本作家的书。我那时想从日本文化中逃脱,我觉得那文化很沉闷,很黏糊。
巴黎评论:但您的父亲不就是教日本文学的老师吗?
村上:没错。所以也是父子关系的较量。而我是直接奔了西方文化:爵士乐,陀思妥耶夫斯基,卡夫卡,雷蒙德·钱德勒。那是我自己的世界,我的太虚幻境。如果我愿意,我可以在书里去圣彼得堡或西好莱坞。那就是小说的力量—你可以去任何地方。现在去美国很容易了,人人可以去世界的任何一个地方,但在1960年代,那几乎不可能。所以我就阅读,听音乐,我就可以去那些地方。这是一种心态,像个梦境。我是个秉性孤独的人。我不喜欢团体,学校,文化圈。在普林斯顿的时候,有一个作家午餐会,我被邀请参加。乔伊斯·卡罗尔·欧茨和托尼·莫里森都在那儿,我紧张极了,什么都吃不下!玛丽·莫里斯也在座,她人特别好,和我年纪差不多,我们可以说成了朋友。但是在日本,我一个作家朋友也没有,因为我就是想保持……距离。
但父与子的传承却属于命中注定—无论你如何反感、抗拒。它成为爱与死并列的文学母题不是没道理的。他的父亲如那个时代许多同龄人一样上过战场,却根本不跟儿子说起战时的经历。晚年在家中设一神龛,天天沉默诵经拜祭良久。村上问父亲:你在为谁诵经?他回答,是为了死在那场战争中的所有人,为了死在战场上的战友和中国人。但是他的父亲从未参与过任何社会活动。村上春树本人在早稻田大学就学时,正是日本的“安保时期”。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学生运动火遍全球,日本也不例外,身为大学生的村上也卷入其中。他回忆当时的自己,一想到示威游行要跟同学们手牵手顿时就觉得毛骨悚然,害怕后退了。这种对有组织的社会运动的冷漠态度,是村上早期作品中典型的人物特征。他后期小说的许多重要的角色,也都经历过那个时代。
翻译与研究村上作品的哈佛大学教授杰伊·鲁宾指出,村上春树的小说里,第一人称的叙事者,英文译作“I”,中文译作“我”,但在日文里边却有不同的称呼方法。日文小说里出现第一人称时,通常采用比较正式的称名,翻译成汉字叫“私”,私人的私。但是村上喜欢用的是“仆”,而“仆”完全是另一个字,代表一种比较平等的非正式的用法。他笔下这个“仆”,就是经历过学运时代的人,他在早期作品里,将其设定为二十多岁、三十岁,是日本那个十年的生活事件见证者、记录者、叙事者。
学运结束,理想幻灭。泡沫经济破灭,强烈地震摧毁城市,邪教团体无差别且残忍地杀害许多无辜的普通人。一时光芒四射的战后神话看上去一个接一个应声崩溃。然后呢?“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必须静静地站起寻求应该存在于某处的新的价值—这就是我们自身的形象。我们必须继续讲述我们自身的故事,其中必须有给我们以温情鼓励的类似moral(道德)那样的东西。”村上后期小说中的人物在漠然状态下反复咀嚼人生的细节,跑步,打球,做手工,听音乐,甚至只是给自己做一日三餐:持久忍耐又温柔,有些类似于日式禅修—屏声静气,专注某事,日复一日,无明无暗。并非要修得什么结果,而是在这种日常专注中探究人生。如深夜静雪般悄无声息存积起来,天亮时豁然另一番天地。几十年来,他自己每天凌晨四点起床,写作五六个小时。下午外出跑步十公里,或者游泳一千五百米,或者两项都做。然后是看看书,听听音乐。晚上九点就上床睡觉。天天如此,没有变化。“无论某个动作看起来多么平凡,坚持足够长的时间,它就会变成一种沉思冥想,甚至是一种哲学。”
自一九八二年开始,三十三岁的村上春树,在开始职业作家生涯之际,也开始了长跑练习。此后,村上在夏威夷的考艾岛、马萨诸塞州的剑桥、希腊马拉松古道都参加过长跑比赛。一九九六年六月二十三日,他在北海道参加了全程一百公里的超级马拉松比赛,从早上一直跑到晚上。在那种跑步状态下,除了耳边的风,他与身外世界几乎隔绝一切联系,这正是他最喜欢的状态。他为此写过一个短篇小说《天天移动的肾形石》,收在《东京奇谭录》中。里面女主角与男生关系密切到任何心里话都可以倾诉,但就是不告知对方自己的职业。后来男生无意中得知,那位漂亮的女士经营着一家高楼幕墙清洁公司,她自己也参与清洗工作,她最喜欢的是不系安全缆绳独自一人走在两座高楼之间的钢缆上唯有风在耳边的那个瞬间。
“任何一把剃刀都自有其哲学”是村上春树最喜欢的格言。没有比这句格言更“村上”了。高中他看到这句话时,立刻被击中心魄,自那以后一直铭刻在脑子里。他认为这句话的关键在于把“剃刀”这一日常的用具与“哲学”发生联接,即便是每天早上的剃须,也有其不可思议的涵义。
三
我说“部分赞成”将村上比喻为品质稳定的高端连锁店,是因为我觉得更值得赞美的是其作品中无以名状的细节部分。普林斯顿大学授予村上荣誉博士时的评语是:村上春树“以文学形式就日常生活的细节做出了不可思议的描写,准确地把握了现代社会生活中的孤独感和不确定性”。所谓“现代社会生活”,在村上笔下即“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想想看,仅就全世界的剃刀品牌与功能而言,就已成为一个巍然帝国,更遑论其他。这是他在所有的写作中竭力自我反省并批判的文化环境,“手握宝马车方向盘,听着舒伯特《冬之旅》,停在青山大街等红绿灯的时间里,我蓦然浮起疑念:这不大像是我的人生,我好像是在某人准备好的场所按某人设计好的模式生活”。但他的生活与小说却常常被标签为“小资”,虽不算太冤枉,也真是个不小的嘲讽。
似乎为了反照这种嘲讽,村上小说中多次出现“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中日本社会“优等生”式人物。他有一篇题为《我们时代的民间传说—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的前期发展史》的短篇小说,收在《电视人》中。描写了一位中学时的同班同学,一位出身、成绩、容貌、性格、运动甚至为人处事无不完美的男生,被他称为“美加净先生”。人到中年后,他与那位同学意外重逢,不出意料,得知对方一路名校名司,然后与一位“美加净小姐”结婚。可是同学口中讲述的人生故事却荒谬反常得令他颇感意外,更意外的是同学最后突兀地说了个一点也不好笑的童话,情节已被他忘光,只记得结尾是:“一切结束后,大王也好喽啰也好全都捧腹大笑。”让他莫名想起在夏威夷看电影《廊桥遗梦》,剧终时场内观众哄堂大笑。“怎么回事呢,这?”
但村上对这样的人物、这样的故事并非全是揶揄,他有怜悯有共情,对于这些唤起了自我意识却又无法挣脱出来的人物,他给足了恻隐之心。
王安忆曾说,日本的短篇小说在她的印象中相当平淡,“大约与日本人敬语体系充满庄严的仪式感,使得叙述过程曲折漫长有关”。但现代主义切入进来之后便大有改观,浅田次郎的短篇小说《铁道员》因高仓健主演的电影而广为人知。作者自言是讲述“发生在你身上……温柔的奇迹”。“温柔的奇迹”真是一个好说法。
很多人都知道村上与父亲关系极差,几十年不见面也不通音讯。在他父亲九十岁的时候,村上自己年届六旬,两人在病榻前有过一番简短的对话,然后终于和解。但村上没有透露父子间当时说了什么。如此,又过了十多年,七十二岁的村上写出了《弃猫—当我谈起父亲时》。他在书中回忆起儿时与父亲一道去海边丢弃一只养了多年的猫的往事。父亲和他将猫放到一个离家挺远的名叫香栌园的海滩上,对猫说了声“再见”,两人便骑车回去了。到家时,少年村上心里还在难受着:“怪可怜的,可是,也没办法啦。”“哗啦”一声拉开玄关的门。没承想,明明是刚刚扔掉的那只猫“喵”地叫着、竖起尾巴亲切地来迎接父子俩了。原来它已经抢在他们前头先回到了家。它是怎么在那么短的时间里跑回来的?毕竟他们是骑自行车直接回家的啊!实在是想不明白。可是晚年的他,却还能清楚地记起那天海岸边的潮声,以及风儿穿过松林带来的清香。他想起,正是那些小事的无穷累积,才让每个人长成如今的模样吧?那些向着广阔大地滴落的无数雨滴,其中寂寂无名的一滴,是确实存在的,也是可被替代的。但这一滴雨水,有着它独一无二的记忆,有它自己的历史,有将这历史传承下去的责任和义务—我们不应忘记这一点。即使它被轻易吞没,失去个体的轮廓,被某一整体取代,因而消失。不,应该说,正因为它会被某一整体取代因而消失,才更值得铭记。
我在家里读完《弃猫》时已近傍晚,凉风从窗外拂来。我放下书打开电脑,一位网友上传了一段钢琴曲视频,Le Mal Du Pays(中文名《思乡》,李斯特钢琴曲《巡礼之年》中的第八段,村上曾以此为书名写过一篇小说)。一对美丽的舞伴在空旷的大厅里相拥起舞,规整,和谐,美得恰到好处。如切如磋,如倾如诉,这音乐如同村上的行文,那些语言和想象的光束,照在生活的前方,让人窥见遥遥的仙境里转瞬即逝的风景,讲述令人难以置信却又确实发生的一桩桩“温柔的奇迹”。
村上曾在《我的职业是小说家》里写道:“假如读者能从我的作品中,感受到一星半点像温泉浴那般深刻的暖意,那可真是令人喜悦的事。”所以,无所谓他是远离川端康成还是近乎夏目漱石,他的写作归属小资文抑或纯文学;无所谓他是否能跻身诺贝尔文学奖殿堂,等等。重要的是,我似乎明白了他的小说带给了我们什么。所以,谢谢村上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