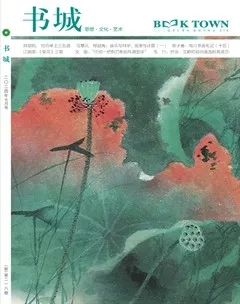当了解苦难变成观看表演
2024-07-18杨吉
面对他人的苦难或伤痛,除了情感共鸣心生恻隐,还该有怎样的行动呼吁或人道援助?这似乎是一个能够清晰回答的简单问题,对很多人来说,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心存善念尽力而为即可;但这也可以是一道可供学理深究的复杂论题,它涉及公众如何观看、怎么思考,以及会产生何种情绪、做出哪些行为。曾有观点开创性地提出,同情需要两个触发条件—距离和围观。距离要适中,太远容易事不关己无动于衷,太近则恐慌不安自求多福;围观即换位,外人通过观看来形成移情,设身处地去感知他人的悲苦,从而激发出或多或少的救济意愿。不过,在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媒体与传播系终身教授莉莉·蔻利拉奇(Lilie Chouliaraki)看来,事情远非这般轻松。
单就距离来说,它是想象力的产物,和实际物理空间中的长度指称并没有直接的、绝对的因果关系。就像人们会关心远在非洲大陆饥民的温饱生计,却未必能关注身边的民众生活。两者相比较,后者无疑是更真实的、可触及的,但经由媒体的议程设定、话语的雕琢形塑、叙事的编排铺陈,人们可能会更关注一个在遥不可及陌生地方的困难人群。早在二○○六年,蔻利拉奇就通过《观看他者之痛》(The Spectatorship of Suffering)一书揭示出,人们的同情心不完全取决于苦难本身,更多时候还在于观看的方式,以及等待被观看的内容表达。此后数年,蔻利拉奇持续对媒介传播与灾难报道的互动关系深入探析,《旁观者:观看他者之痛如何转化为社会团结》(叶晓君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23年;以下简称《旁观者》)一书的问世,标志着她又一个新阶段、新方向和新维度的研究成果。
在《旁观者》这本书中,悖论和困境是一组关键词,也是通往蔻利拉奇思想深处的密钥。她对于借由各路媒介展示的苦难、悲剧,几乎都持省思、怀疑论的立场。这不等于说,她是在断然否定这些实践本身的真实性,而是会注重那些被刻画、烘托、营造出来的基调与意图。因而,那种建立在人道主义传播上的真实呈现与道德号召,在蔻利拉奇这派学者眼里恰恰构成两个“自我矛盾”—在书里,她分别用了“本真性的悖论”和“能动性的悖论”来指称。前者是指“媒介化的苦难可能造成观众的麻木不仁而非调动他们的道德情感”,而后者则是指“慈善捐赠行为被视为在合法化西方与全球南方之间的系统性的不对等关系”。这样的阐述确实有些绕口,事实上,这本书在多数时候都没有给读者提供一种舒适、畅快的阅读体验。但简而言之,就是蔻利拉奇在这些传播中敏锐地捕捉到了一种“反讽式的人道主义”—这一概念借鉴自罗蒂的哲学批判,指的是人们因为对苦难景观的质疑,对于宏大话语的不置可否、无所适从,所以变得同情疲劳,但即便如此,还是愿意去为那些正在受难的人做些事。
尽管蔻利拉奇得出的结论令人不安,但按照她的说法,这正是当前西方世界人道主义传播进入“后现代”的一种现状,也是发展变化的一个结果。她在书中写道:“人道主义理念经历了三个主要转变:人道救援和发展领域的工具化,关于社会团结的宏大叙事的退场,以及传播交流的日益技术化。”很多学者未曾注意其间的变化,当然也不会去梳理它们彼此的交叉和勾连,至于“三者的结合如何影响社会团结的意义”更加鲜有人讨论。本书的价值也正由此体现—它会细致地考察人道主义传播在每个转折节点是如何实践的。进一步说,这也关乎当下乃至今后的人们该如何组织展开道德教育和人道援助。
《旁观者》一书分别梳理了募捐倡议、名人公益、慈善音乐会和灾难新闻报道这四种最常见的人道主义的表现类型,“把它们置于视觉和企业传播、发展研究、新闻研究、文化研究和社会理论等跨学科领域中来研究”。蔻利拉奇这么做的目的,是为了尽可能全面地探讨这四种类型在历史演变中,如何应变出不同的解决策略,以尽力克服所谓本真性和能动性的悖论。
在蔻利拉奇看来,四种类型都高度依赖技术化的行动方案,且内嵌了消费主义的倾向。不论是请愿,还是点击捐款链接,又或是购买各种“腕带”,这些行为都需要通过技术平台或工具;而名人公益或慈善音乐会,需要粉丝来应援;灾难报道,则让新闻当事人面对镜头进行讲述或演示。以上这些行为,似乎是在召唤富有同情心的支持者们,以“消费”的方式进行响应。这种消费,既可以是购买明星的周边产品,也可以是购买灾区的农特产品,更可以是出钱请公益机构购买物资去驰援当地。在蔻利拉奇敏锐的审视下,一场场人道主义活动变成了受难者、观看者、行动者、表演者、消费者等多种角色的混合表演—人们不再把“不幸的他者”视作行动的对象,而是把自我感觉和满足当作首要动力;不太关注导致不幸的根源,反而利用“行善过—心安了—得救赎”的认知逻辑来遮蔽某些扎心的事实和残酷的真相。而这也正是蔻利拉奇着力批评的后人道主义的困境,即“人道主义日益增长的工具化倾向”。
然而,面对这一发展趋势,蔻利拉奇给出的解决方案却让人兴奋不起来。她借鉴了政治学家汉娜·阿伦特的说法,提出了“竞胜式团结”一词,将多元的行动者和团结方案并列放置在显现的空间中,进行对话和竞争。对此,我们大可以把它进一步解释为让弱势者作为独立的行动者参与到苦难的“表演”中,还可以邀请观看者以某种方式参与其中,“身临其境”,进而作出有效的移情和评判。蔻利拉奇自信这种建设性构想能够弥合理想与现实的鸿沟,克服眼下的缺陷和不完美。但这种哈贝马斯式的公共协商,貌似均衡、稳妥,两头不得罪,但一旦涉及落地,就不免陷入纸上谈兵、止步理论的僵局。
但即便是这样,莉莉·蔻利拉奇确实以有趣的、具有说服力的例证说明了,这些后人道主义倾向在现实中是如何被纠偏的,从而使读者相信,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依旧可以尽绵薄之力来改变他人遭受的苦难状况。不得不说,蔻利拉奇在媒介传播与灾难叙事的研究中,写就了一个精致的学术文本,也确立了一种标杆示范。这部作品会不断提醒旁观或参与慈善工作的人,什么该是正确地面对他者悲痛的站位和心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