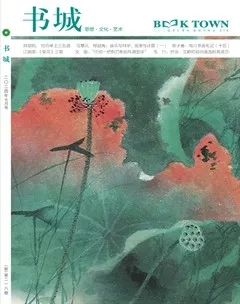月明云淡露华浓
2024-07-18樊愉
“五一”期间奔赴了一趟苏州,为了观看上海昆剧团青年演员演出的经典版《玉簪记》。之前曾在网上看过岳美缇、张静娴二位演出的录像,及其他各团的演出版本。相比之下,唯有上昆这一演出版本的整编堪称绝妙,名之为“经典版”,十分恰当。
如今搬演传统昆剧,推广时最重演员,对文本的解读和剧本沿革的释讲,往往还不如对演员的介绍。殊不知昆曲被纳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绝非仅仅是因为表演,它的历史、文学,包括曲辞、曲牌的艺术价值更为要紧。每逢演出,应为观众多多加强引导欣赏的功能。
《玉簪记》传奇是明代中晚期作家高濂的作品。自问世后,就其曲辞、宾白、场景和人物设定,向来疑议不少。兹举数例:
《玉簪》词多清俊。第以女贞观而扮尼讲经,纰缪甚矣。(明·吕天成《曲品》)
《玉簪》幽欢女贞观中,境无足取。惟着意填词,摘其字句,可以唾玉生香,而意不能贯词……(明·祁彪佳《远山堂曲品》)
《玉簪记》之陈妙常,道姑也,非尼僧也,其白云“姑娘在禅堂打坐”,其曲云“从今孽债染缁衣”;禅堂、缁衣,皆尼僧字面,而用入道家,有是理乎?诸如此类者,不能枚举。(清·李渔《闲情偶记·词曲部·宾白第四》)
此记传唱四百余年矣,顾其中情节颇有可议者。……至于用韵之夹杂,句读之舛误,更无论矣。编制传奇,首重结构,词藻其次也。记中《寄弄》《耽思》诸折,文彩固自可观,而律以韵律,则不可为训,顾能盛传于世,深可异也。(吴梅《曲选》)
以上指摘,多针对“扮尼讲经”。确实,《玉簪记》场景设于女贞观,人物为道姑,此为道家,在传奇本中却有“谈经”“念弥陀”,确属混沌。
大概因为这一缘由,自从十八世纪末的《纳书楹曲谱》起,到二十世纪中叶《春雪阁曲谱》《六也曲谱》《集成曲谱》《与众曲谱》诸曲谱中的《玉簪记》唱演本,对剧情、关目已做了很大的筛减和更名。常以折子戏形式演出的大致有:《茶叙》(原本第十四出《幽情》)、《琴挑》(第十六出《寄弄》)、《问病》(第十七出《耽思》)、《偷诗》(第十九出《词媾》)、《姑阻·失约》(第二十一出《姑阻》)、《催试》(第二十二出《促试》)、《秋江》(第二十三出《追别》)等折。这些唱本都隐去了时代,剔除了无关剧情衍展的事件、人物及情节,如传奇本事中张于湖挑引妙常、王仁求婚与妙常拒婚、及第圆婚等冗杂俗套。
若要捏成“全剧”演出《玉簪记》,整理改编者的立意至关重要。上海昆剧团的演出本剧情简洁为:下第书生潘必正寄居于姑母女贞观中,爱慕年轻道姑陈妙常,以琴曲相挑,倾诉心声。因妙常拒之,潘生相思成疾,观主与妙常前来探视。后来妙常作诗一首,流露真情,被潘生所得,妙常无以分辩,只得私订终身。事后被姑母察觉,逼侄子进京赴试。潘生无奈启程,妙常闻讯追至江边,互诉衷情,誓守前盟。这一版本仅以《琴挑》《问病》《偷诗》《催试》和《秋江》演出。改编者意在让观众听到本剧最为精华的优美之曲,也使演唱者尽展唱曲功力,可谓用心遥深。
现演出的经典版《玉簪记》,以《琴挑》[懒画眉]“月明云淡露华浓”开场。第三支[画眉]“谁家夜月琴三弄”便点出了琴曲《梅花三弄》;第四支[懒画眉]“莫不是为听云水声寒一曲中”,就是指琴曲《潇湘水云》;再加上二支[琴曲]《雉朝飞》和《广寒游》,更似带唱词的浙派琴曲。接下来的[朝元歌]“长清短清,那管人离恨”,点的是嵇康四弄中两首琴曲《长清》《短清》。由四支[懒画眉],加二支[琴曲]和四支[朝元歌],构成了经典的南曲曲牌套曲结构,巧妙地点了六首琴曲名。《琴挑》和《秋江》两折也向来是戏工和清工的最爱,经久传唱。
《偷诗》一折,从[清平乐][猫儿坠]九支曲牌又构成了一组套曲,尽显度曲者经营曲牌的高妙,最后似乎仍觉不过瘾,又以两支[掉角儿序]告终。
此演出版的第四出《催试》,是为了引出下一出《秋江》,仅仅巾生、老旦和丑的几句宾白一带而过作为衔接,交代了下一折的起因,紧接着引出了《秋江》[水红花]。《秋江》一折曲牌的取舍,体现了改编者的巧思。推测改编者首先考虑到演出时长,以期尽快抵达全剧高潮而收尾,所以在二支[红纳袄]之间省略了二支[山歌]。原本接下的套曲有五支曲牌,而只保留了精华的[小桃红]和[五般宜],直接到[尾声]:“夕阳古道催行晚,千愁万恨别离间。暮雨朝云两下单”,全剧告终。
这一演出版本之所以被誉为“经典版”,除了演员的表演,主要应归功于整理改编者,即曲家、剧作家陆兼之先生(1916-1986)。他以曲家的立场来整编《玉簪记》的剧本和唱本,不以陈述故事情节为要,而以昆曲的曲为重,让演员得到最大的发挥,让观众得到最美的享受。
兼之先生是苏州人,自幼浸淫于昆曲,工诗词,擅唱曲。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即调任上海市戏曲学校专职编剧,参与了现代昆剧《琼花》的编写,并参加了昆剧折子戏二百种教材的校注工作。一九七八年上海昆剧团成立后,又被聘为专职编剧,先后编写了《画皮》、《白蛇传》(与顾文芍合作)、《琵琶记》、《蝴蝶梦》、《牡丹亭》(与刘明今合作)、《唐太宗》(与方家骥合作)、《烂柯山》和《玉簪记》等多部昆剧,并整理传统折子戏多种。他还是《振飞曲谱》和《昆曲曲牌及套数范例集》的策划和撰写者之一。
兼之先生还是一位精于铁笔的篆刻家,晚年眇一目,犹奏刀不止,留有《岸铁印存》一卷(“岸铁”是他晚年的号)。他是我的父执。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的先严“笑笑楼”中,每周日都有许多曲家、画家相聚欢谈,兼之先生的身影常常出现。他见我时常会问:“近来阿有啥画册(西洋画)可以借我一观?”我当然应之,随后他会加问一句:“阿要帮倷刻方图章?”我真是喜出望外,旬日后便得到了他带来的一方印,至今宝存。
上昆《玉簪记》演出现场和节目单上,剧本整理者署名至今仍是陆兼之先生,观之深感欣慰,草此文以表纪念。
甲辰立夏后旬日灯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