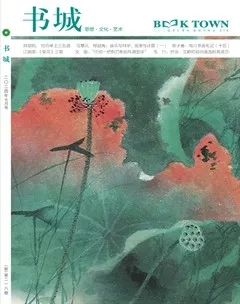梅川书舍札记(十四)
2024-07-18陈子善
译介裴多菲
今年七月,是匈牙利大诗人裴多菲·山陀尔逝世一百七十五周年。早在一九二九年十二月,也即裴多菲逝世八十周年时,鲁迅、郁达夫主编的上海《奔流》第二卷第五期译文专号,也即该刊最后一期,就在头条和二条的显著位置,刊出白莽(殷夫)所译《彼得斐·山陀尔行状》(奥地利奥尔佛雷德·德涅尔作)和《黑面包及其他》(裴多菲诗八篇)以为纪念。鲁迅在该期《编辑后记》中特别说明:
收到第一篇《彼得斐行状》时,很引起我青年时的回忆,因为他是我那时所敬仰的诗人。在满洲政府之下的人,共鸣于反抗俄皇的英雄,也是自然的事。
鲁迅不仅对裴多菲表示一以贯之的“敬仰”,还简要回顾了近代以来中国的裴多菲接受史。其实,周氏兄弟才是裴多菲进入中国的最早介绍者,是裴多菲真正的中国知音:
绍介彼得斐最早的,有半篇译文叫《裴彖飞诗论》,登在二十多年前在日本东京出版的杂志《河南》上,现在大概是消失了。其次,是我的《摩罗诗力说》里也曾说及,后来收在《坟》里面。一直后来,则《沉钟》月刊上有冯至先生的论文;《语丝》上有L. S.的译诗,和这里的诗有两篇相重复。近来孙用先生译了一篇叙事诗《勇敢的约翰》,是十分用力的工作,可惜有一百页之多,《奔流》为篇幅所限,竟容不下,只好另出单行本子了。
这里所说的《裴彖飞诗论》,系匈牙利爱弥耳·籁息著《匈牙利文学史》之第二十七章,正是鲁迅自己所译,刊于一九○八年八月《河南》第七号,署名令飞。据周作人后来回忆,此文的翻译,他也参与了,“经我口译,由鲁迅笔述的”。早半年发表的有名的《摩罗诗力说》中,鲁迅已详述裴多菲生平,并将其与拜伦、雪莱等并列,称颂其“为爱而歌,为国而死”。到了一九二五年一月,鲁迅又在《语丝》周刊第十一期上以L. S.的笔名发表《A. Petofi的诗》,共五首。这是首次较有规模地译介裴多菲的诗,兹录一首《愿我是树,倘使你……》:
愿我是树,倘使你是树的花朵;/你是露,我就愿意成花;/愿我是露罢,倘使你是太阳的一条光线:/我们的存在这就打成一家。/而且,倘使你,姑娘,是高天,/我就愿意是,其中闪烁的一颗星;/然而倘使你,姑娘,是地狱,—/为要和你一处,我宁可永不超生。
裴多菲这首爱情诗,殷夫的译题为《我要变为树……》,译文也照录如下,与鲁迅的译文各得其妙:
我要变为树,假使你是花,/假使我是花,你要变成露,/若是我为露,你为日之光;/我俩同誓约,此生常相顾。
假若你,女郎哟,你是苍天,/我愿变为星星,在空中放光;/假若你,女郎哟,你是地狱—/那我也要沉沦,和你厮傍。
接着就是诗人冯至在一九二六年八月《沉钟》第二期上发表的《Petofi Sandor》和这期《奔流》上经鲁迅审定的殷夫的译介了。孙用译长篇叙事诗《勇敢的约翰》,后于一九三一年十月由上海湖风书局初版,鲁迅也出了大力。到了一九四○年六月,重庆诗时代社又出版了后来成为台湾著名诗人的覃子豪译的《裴多菲诗》,惜现在已鲜为人知。
当然,裴多菲诗中译最有名也流传最广的是鲁迅《为了忘却的记念》中所引的殷夫译《格言》:
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
若为自由故,二者皆可抛!
刘半农译《法国短篇小说集》
五四新文学运动健将刘半农一九二一年留学法国,一九二五年以论文《汉语字声实验录》获法国国家文学博士学位。同年八月回国后,他继续致力于各种著译,所译《法国短篇小说集第一册》即为颇具代表性的一例。
这本法国短篇小说选译本一九二七年六月北京北新书局初版,平装,毛边本,版权页上有蓝印编号,我所有的这本为“第000228号”。此书当时很受欢迎,两个月后即一九二七年八月就再版了,我还见过一本再版本,编号则为“第001216号”。
也许是刘半农的要求,《法国短篇小说集第一册》虽然封面平淡无奇,装帧却极为讲究。扉页为套红的一幅法国油画,上印“刘半农法国短篇小说集第一册 北京中法大学丛书之一 一九二七年北新书局印行”。书中又印有嚣俄(雨果)“登流废崖回望祖国图”,及那法尔(M. Navarre)、服尔德(伏尔泰)、嚣俄和左拉四位作家的头像并签名的黑白照片等五帧插图。全书共收入拉萨尔(A.la Sale)、那法尔、服尔德、底得啰(狄德罗)、嚣俄、弗洛倍尔(福楼拜)、阿雷费(L. Halévy)、左拉、丹梭(L. Tinseau)、阿雷司(A. Allais)等十位法国作家的十四篇短篇小说,时间跨度为十四至十九世纪。其中左拉一人收了三篇,那法尔和服尔德一人两篇,其余均为一人一篇,由此或可见刘半农的偏好。每篇小说前均有一页套红印刷篇名和作者名的辑封,正文开头又印有篇名和作者名,篇名为潇洒的毛笔行书,不知是否出自刘半农之手。整本小说集如此装帧,简直可以用“奢华”两字来形容,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的新文学著译中独一无二。
左拉的三篇短篇为《失业》《猫的天堂》和《爱情的小蓝外套故事》,前两篇又在同年分别出过“法汉对照本”,我以前还专门介绍过《猫的天堂》毛边本。这里不妨引录《爱情的小蓝外套故事》的第一段写景,来领略一下刘半农的译笔:
她,这美貌而红发的女孩子,是十二月中某一天的早晨生产的,正好像是天上下着的雪,慢慢的,处女般的。在空中,有种种的兆象,报告爱情的任务,要由她来完成了。太阳照耀着,玫瑰色的光,映托着白雪;人家屋顶上,有紫丁香的香味和鸟儿的歌声流荡着,好象是春天的光景。
再引录弗洛倍尔《游地狱记》中的一段:
于是我看见了两个巨人。第一个是年老的,弯腰曲背的,皱皮的,瘦的。他把他身体支靠在一根刑杖上。这刑杖的名字叫做“腐败”。又一个是年青的,高傲的,勇猛的。他有“大力神”的身材,诗神的头脑,黄金的臂膊。他把他身体支靠在一根巨大的,已被刑杖打得很坏的棍子上。这棍子的名字叫做“理智”。
有意思的是,此书书末还附有一份《刘半农撰译编校各书》书目,这是留学归国的新文学作家常见的做法。从一九一九年在群益书社出版《中国文法通论》开始,到一九二七年,刘半农已出版了中文的著、校、编、译书共十四种,以及法文著作两种,可谓蔚为大观。书目还预告了正在“编译”“撰述”和“材料搜集中”的书十一种,其中就有《法国短篇小说集第二册》,可惜的是,此书后来未能问世。
最后要补充一句,《法国短篇小说集第一集》还有线装本,是刘半农特别“精印十本”分赠友好的,而今已是可遇而不可求了。
冯雪峰译《流冰》
译诗集《流冰》,署画室译,一九二九年二月上海水沫书店初版。此书为四十八开小毛边本,独具一格,封面图也新潮别致。扉页又印有“今日文库 流冰(新俄诗选)”等字,可知此书为“今日文库”之一种,而书中的译诗均为“新俄”诗人所作。所谓“新俄”者,与“旧俄”相对,是对苏联的简称。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初的文学译著,以“新俄”为书名的比比皆是,如《新俄短篇小说集》《新俄文学的曙光期》《新俄大学生日记》,等等。虽然唐弢在《晦庵书话·新俄诗选之一》中已写过这本小书,但是仍值得再说一说。
翻译《流冰》的画室,是五四初期有名的湖畔诗社诗人、后成为著名左翼文学评论家的冯雪峰的主要笔名,他晚年在致友人的信中是这样回忆《流冰》的:
《流冰》,译诗集。我译过日本升曙梦的《新俄的无产阶级文学》(原名《无产阶级文学的理论与实际》)一书,书中引有不少所谓无产阶级诗人的诗。水沫书店戴望舒把那些引诗取出编成一小集,以其中的一首诗题目为集名,得我同意而出版的。(冯雪峰1974年2月26日致包子衍信,见包子衍《雪峰年谱》,上海文艺出版社1987年7月初版)
水沫书店由刘呐鸥、戴望舒和施蛰存等共同创办。施蛰存在《我们经营过三个书店》中对《流冰》也有过回忆:
水沫书店最早印出的是两本小书:冯雪峰译的苏联诗集《流冰》,我的中篇小说《追》。《追》是我的仿苏联小说,试用粗线条的创作方法,来写无产阶级革命故事。(见施蛰存《沙上的足迹》,辽宁教育出版社1995年3月初版)
画室译《新俄的无产阶级文学》一九二七年三月由北新书局初版,书中有“无产阶级诗人和农民诗人”一章,《流冰》中的译诗显然都选自该章,两年后另出《流冰》单行本,以书中第一首诗即查洛夫作《流冰》为书名。冯雪峰告诉我们,这都应归功于戴望舒。至于施蛰存所说的《流冰》是水沫书店最早印出的小书,严格来讲,略有出入,因为他自己的《追》出版于一九二九年一月,比《流冰》早出版一个月。尽管版权页所示出版日期,未必与真正的出版时间相一致,但如以版权页为准,《追》才是水沫书店真正最早出版的书,《流冰》只能屈居第二。水沫的“今日文库”也只出版了《追》和《流冰》两种,就戛然而止。此外,《流冰》所收的查洛夫、卡思捷夫、基里洛夫等十三位诗人的二十五首诗,并非都是冯雪峰所译,苏汶(杜衡)译了别赛勉斯基的《村野和工厂》和马连霍夫的《十月》,建南(楼适夷)译了别德芮伊的《资本》,都已经在诗末注明。当然,《流冰》主译是冯雪峰。
当时戴望舒和施蛰存受勃兴的左翼文学潮流影响,都以绍介“新俄”文学作品为己任,所以及时推出了这本小巧玲珑的《流冰》。但正如冯雪峰所说,这些“所谓无产阶级诗人”的诗,政治鼓动性固然很强,艺术上有所追7dbf2ab84f2f6a02a2c5fa512362d071求的并不多,下面这首加晋的《春似的歌》似还不错:
秋的莫斯科阴郁着。/空气,行人底脸,/窗底碧眼,/家家底招牌底面也都(阴郁着)。/铁筋沙合土的屋脊底/条条的线,/张在雾中的/电线底毛发都(阴郁着)。/秋的莫斯科阴郁着。/秋的莫斯科……忽然旗儿升举了!/旗儿燃烧着,/地平线是仿佛看不见,/然而春在手中沸腾着。
不要忘了黎烈文
近日得到一通现代作家、翻译家黎烈文(1904-1972)致陈纪滢(1908-1997)的信札。这通共三页的手札,蓝黑钢笔书于“国立台湾大学”的白色信笺上,似乎提醒我们,黎烈文和陈纪滢也是台湾作家。
那就查一下黎烈文一九四六年去台湾后的经历。查阅了手头的数种关于台湾文学的专门辞典,结果令人失望。《台港澳暨海外华文作家辞典》(王景山编,人民文学出版社1992年5月初版,2003年7月修订版)竟然没有黎烈文的条目,陈纪滢也没有。《台湾新文学辞典》(徐迺翔主编,四川人民出版社1989年10月初版)、《台湾港澳与海外华文文学辞典》(陈辽主编,山西教育出版社1990年6月初版)、《台湾文学家辞典》(王晋民编,广西教育出版社1991年7月初版)和《台港澳暨海外华文文学大辞典》(秦牧、饶凡子、潘亚暾主编,花城出版社1998年10月初版)等四种,条目倒都有了,但对黎烈文在台湾的文字生涯均语焉不详。其中最详细的是《台湾文学家辞典》,该书黎烈文条目中写到他在台湾的情形时,也只有一百多字,照录如下:
(黎烈文)1946年春辞职往台湾任《新生报》副社长,同年秋改任“台湾省训练团”高级班国文讲师,1947年应台湾大学文学院之聘任外文系教授,历20余年。主要作品有:杂文《文艺谈片》(1964年,文星书店)、论著《法国文学巡礼》(1973年,志文出版社);另有译作多种。
这么短短的一段话,当然无法概括黎烈文对台湾文学所作的多方面的贡献。黎烈文在大陆时,先主编《申报·自由谈》,影响深远;后致力于法国文学翻译,也成就卓著,所译小说《冰岛渔夫》(罗逖著)、《伊尔的美神》(梅里美著)等,均被誉为一时的佳译。他后到台湾生活了廿六年,除了从事大学教学,仍笔耕不辍,这通新发现的黎烈文致陈纪滢手札就是一个有力的证明,照录如下:
纪滢先生:
前次承 约于八月份前将拙译《法国短篇小说集》编妥寄上,以便年内出书,兹已抽空编妥,另邮挂号寄奉,至希查收。该稿内容如有不妥之处,尚祈不吝指教,俾克改正。该书编排格式,务乞 费神设计,弟无意见。出版手续如签订契约等等,请由邮寄下,当即照办不误。
又前次承约《红与黑》一稿,适穆中南先生亦商请交由《文坛》连载,弟因该稿尚未译完,连载对弟较便,且可逼弟非陆续译完不可,故已决定由《文坛》连载,连载完毕即由该社出版单行本。素知先生与穆先生深交,当不以此介介,惟有负 盛意,终觉歉然,尚希 谅宥为幸。
溽暑未及走访,匆此顺颂
撰安
弟 黎烈文敬上 七.廿八
黎烈文在这通手札中,对陈纪滢说了两件事,一是践约交其已编竣的《法国短篇小说集》书稿,二是说明正在翻译的长篇《红与黑》书稿将先交穆中南创办的《文坛》连载,然后出版单行本,故无法再一稿两用,请其谅宥。已知黎译《红与黑》一九六六年开始在《文坛》连载,那么这通手札写于一九六五年的可能较大。至于这两部书稿何时出版了单行本,暂不明。黎译《红与黑》是继赵瑞蕻、罗玉君译本之后的第三部中译本。以黎烈文在大陆和台湾的文学成就,应该有一本较为详尽的《黎烈文年谱》备查,海峡两岸都不要忘了黎烈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