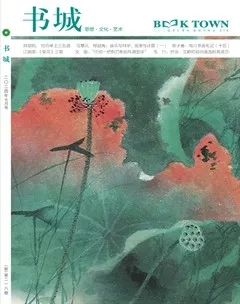缅怀王世襄先生
2024-07-18尚刚
对于王世襄先生的成就,大家早已耳熟能详,这里不必重复。在下面的书面发言里,我只说两点,一个关于先生的著述,一个关于他的待人。
先说著述的严谨科学。
世襄先生博雅,对于古代家具、漆器、竹刻、绘画、铜佛、匏器等,都有研究,都有重大贡献。而他用力最多、成就最高的是明式家具和漆器,这两项研究也最能揭示他著作富含的科学精神。
《明式家具研究》和《髹饰录解说》是先生的名著,两书广受称颂,但书后的索引部分,尚未见他人言及。有心人都会认同,索引大大便利检索,特别有益研究。可惜,在中国的学术出版里,书无索引至今仍是不大不小、又痛又痒的通病,而先生四十年前已经如此作为。真不知为了附录索引,先生花了多少精力,费了多少口舌。或许有人把这归于他毕业于燕京大学,早年接受现代教育。不过,近百年来,受现代教育的学人已经太多,学术著作早就浩如烟海,但是带有索引的著作又有几种?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国美术全集》编撰出版,先生担任《漆器卷》主编,为此,他写作了导论《中国古代漆工艺》。全文五万余字,认知真切,见解深邃,资料全面,求证严谨,原原本本,凿凿有据。若讲中国漆器简史或概论,迄今未见可与之比肩者。这篇导论还出注释二百四十条,说清了所征引古今文献的出处,是当时最完备的漆器研究索引。应当一说的是,那一时期及之前的著述往往忽略注释,倘若在正文中提到议论所本,就会被誉为严谨,甚至不说出处的抄撮蹈袭,都会被今世以合乎那时的学术规范开脱。与先生比较,他们的学术品质、科学精神简直判若云泥。
研究古物,真赝、时代二者,是最先遇到的大问题。尽管传世品往往拥有更高的艺术价值,但常常由于来历不清、时代不明,而科学价值较低。出土物不同,往往具备来历清楚、时代明确的优长,是最可信赖的实物资料。四十年前,考古学还很少关注明清,先生的研究大多时属明清,故其多数著述对考古成果无法征引。可是漆器特殊,有大批的考古发现。先生对早期漆器的研究,主要的实物依据就是甄选出的考古资料。因为现今的文物学家都已关注考古学,故而讨论文物参证考古资料,眼下并不稀奇。不过,但凡稍知学术史,就该了解,先生是最早如此作为的少数学者之一,在他撰著的当年,多数专家还在依傍传世文物循环论证。这无疑显示了先生识见的深远和方法的科学。
再说先生待人的朴厚热诚。
以前,每逢春节我前趋王府拜年。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有一年,我去了,进屋坐定,便听到蝈蝈、蛐蛐叫声清亮,此起彼伏,绕室绵绵,便放眼四处找寻。先生见状,微笑着说:“那是录音。”显然,对这个“发明”,先生颇有得意之色,还有炫耀。我请求借录音带回家转录,或许是怕我搞丢弄坏,先生说:“不用,我录好给你。”次日清晨,我刚起床,电话铃响。先生要我别走,说他一会儿就到。先生居住的方嘉园离我家虽然很近,但我仍无法料到,十分钟后门铃已响。开门,见先生跨在二八自行车的车座上,一脚踏住脚蹬,一脚踩定门前的台阶,车把上斜挂着那只有名的菜筐。见我出来,先从中式棉袄的兜里摸出盒录音带,说:“这个你听。”又从菜筐里掏出个雀巢咖啡礼盒,说:“这个你喝。再见!”言罢,车把一扭,就回家了。进屋,我见那录音带的签纸上写着:“秋虫大合唱”。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先生的力作《明式家具研究》(港版)在大陆发售,价格高昂,相当于我两三个月的收入。我曾向先生抱怨太贵,说读书人根本买不起。说话间,话题岔到别处,当日就没再提这事儿。不料几天后,老人家竟屈驾寒舍,专程送来一部,扉页写着“尚刚同志惠存,王世襄持赠,一九九三年七月”。那天,我们照了合影(这也是我和先生的唯一合影),茶几上就铺着先生的赐书。以后,每有新作出版,先生或其夫人袁老,总电话招我领书。
迁入迪阳公寓后,两位老人特别开心,袁荃猷老人还几次说:“新房子太好了,日坛就是我家后花园。”我曾陪他们到日坛公园散步。三人先在一起,边走边谈,快到公园门口,先生突然加快脚步,将袁老及我甩在身后。见我满脸惶惑,袁老便告诉我:“给你买门票去了。”
王世襄和袁荃猷老人待我极厚,是我格外敬仰的前辈。今天是王老一百一十周年诞辰,由衷感谢三联书店操办这个活动纪念他。我本应奉邀出席,无奈,月前已经应允出差,活动只得请假。但是我愿以书面发言的形式,纪念这位富有科学精神、待人热诚朴厚的前辈。同时,我还特别怀念纯真率直的袁荃猷老人。
二○二四年五月二十五日
本文系作者在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举办的王世襄先生诞辰一百一十周年纪念活动上的书面发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