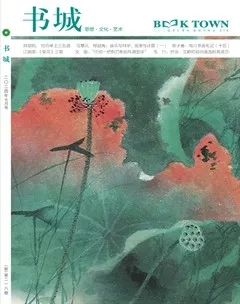米饭与面饼
2024-07-18刘文荣
中国人常说,“民以食为天”,古代中国人和现代中国人一样,以米饭和面饼为主食。
米饭
无论是米饭,还是面饼,都来自谷物。那么,古代中国人食用哪些谷物?《黄帝内经》大概是战国时的一本医书,后成历代医家经典,其中说道:“五谷为养,谓黍、稷、稻、麦、菽,以供养五藏之气。”意思是说,“五谷”,即黍、稷、稻、麦、菽,可以供养“五藏之气”。“五藏”即“五脏六腑”中的“五脏”。可见,这里的“五谷”是主食,吃了可以活命。黍、稷、稻、麦、菽,其中的稻和麦,我们今天比较熟悉,黍、稷、菽又是什么?其实,这三种东西我们并不陌生,黍就是黄米,稷就是小米,菽就是豆。看来,战国时代的中国人吃的主食,和今天没多大区别,也是那么几种。只是,他们的吃法,还有哪种吃得多、哪种吃得少,却和我们大不相同。
《礼记》中则写道:“饭:黍、稷、稻,粱、白黍、黄粱,稰、穛。”和《黄帝内经》所说的“五谷”比较,前面三种是一样的,都是黍、稷、稻,后面说到了粱,却没有了麦和菽。粱,也就是粟,一种上好的稷(小米)。古书中有“膏粱子弟”一说,指的是吃着肥肉和细粮的富家子弟。至于后面的白黍、黄粱,并不是其他谷物,是指上好的黍和粱。至于稰和穛,按照为《礼记》作注的郑玄所说“熟获曰稰,生获曰穛”,即晚熟的谷物称作“稰”,早熟的谷物称作“穛”。也就是强调,无论是晚熟的,还是早熟的,都要用好的。为什么要这么说?因为《礼记》讲的是“礼”,它说到的“饭”,不是平时吃的饭,而是用来祭祀的饭。所以,要用好的黍、稷、稻。至于它为什么不提“五谷”中的麦和菽,那是因为麦和菽在当时很罕见,连诸侯也未必吃得到。
请看《礼记》中的另一段话:“饭之品有黄黍、稷稻、白粱、白黍、黄粱……此诸侯之饭,天子又有麦与菰。”可见,麦和菰在当时弥足珍贵。菰是什么?菰是一种菽,就是茭白的种子,因为长得很小,很像米,所以被称作“菰米”或者“茭米”。
那么,黍、稷、稻在当时又是怎么吃的?主要是蒸来吃的。这可以从一本叫《逸周书》的古书中得到证实:“黄帝作井,始灶,烹谷为粥,蒸谷为饭,燔肉为炙。”这里说,挖井、筑灶始于黄帝,说黄帝开始“烹谷为粥,蒸谷为饭”。“烹”,就是放在水里煮。关于“蒸”,其实,当时的蒸和后来的蒸是不一样的。当时还没有蒸锅和蒸笼,而是用一种叫“甑”的陶器来蒸饭的。至于“燔肉为炙”—“燔”就是烤,“炙”就是熟肉。现在我们要说的是,古代中国人何时开始“烹谷为粥,蒸谷为饭”的。其实,谁也说不清,因为谁也不知道“黄帝”究竟是何时之人,或许根本没有此人,只是“很久iZhb/W3MWnoG1FuE6xdvEg==很久以前”的一个代名词而已。
不过,我们虽然不知道“很久很久以前”是怎样的,却知道后来数百年间,古代中国人就一直“烹谷为粥,蒸谷为饭”。当然,在这期间,“蒸谷为饭”的方法一定是有所改进的,但我们无从得知,因为这期间的古书里没说。
直到东汉以后,西晋有个叫周处的大官,写了一本叫《风土记》的书,其中才写到如何“蒸谷为饭”:“精折米,十取七八,取淅使青,蒸而饭,色乃紫绀。”文中的“米”,是粟米,即小米。那么,什么叫“折米”?折米,就是淘米,去掉米中的杂质。文中说“十取七八”,可见当时的米实在不怎么样,竟然要“折”掉四分之一。“取淅”,即清洗。
周处是做大官的,肯定不会下厨做饭,他这段话说不定是从哪里听来的,而且也太简单了。
不过,北魏期间,贾思勰著的《齐民要术》里面讲到“作粟飧法”,比较详细:
舂米欲细而不碎,碎则浊而不美。舂讫即炊,经宿则涩。淘必宜净,十遍以上弥佳。香浆和暖水浸饙,少时,以手挼,无令有块。复小停,然后壮。凡停饙,冬宜久,夏少时,盖以人意消息之。若不停饙,则饭坚也。投飧时,先调浆,令甜酢适口。下热饭于浆中,尖出便止。宜少时住,勿使挠搅,待其自解散,然后捞盛,飧便滑美。
这段话中,“饙”,意思是蒸,而且是专指蒸饭。“挼”,意思是揉。“复小停,然后壮”,就是再等一等,然后“壮”(猛蒸)。“凡停饙,冬宜久,夏少时,盖以人意消息之”,就是“停”和“饙”的时间,冬天长一点,夏天短一点,看情况而定。“投飧时”就是吃的时候。“浆”就是汤。“尖出”就是(饭从汤中)冒出。“宜少时住”就是最好再等一会儿,等饭粒自行“解散”后,再捞出来吃,吃起来“滑美”。
不知你注意到没有,那时的小米饭,其实是泡饭,而且是甜酸的。在其后的数百年间,古代中国人就是吃这种饭的。所用的谷,主要是黍和稷,即黄米和小米。稻米吃得很少,因为在当时的“中国”(即中原诸国),天气较冷,水源较少,水稻种得很少,产量也不高。
不过,在西汉时还被认为是天子吃的“麦”与“菰”,到了北魏(与东晋同时),好像已变得很平常了。因为我们在《齐民要术》中读到了“作面饭法”和“菰米饭法”。《齐民要术》旨在“齐民”,显然是针对民间的。
魏晋之后,是南北朝。这期间,找不到任何关于“做饭”的记述。我们只能假定,情况没多大变化。于是,就到了唐朝。唐人固然也吃小米饭,偶尔也会吃稻米饭(当然都是蒸来吃的),但他们更喜欢吃“饼”(后文讲到“饼”的时候再作解释)。
唐人喜欢吃“饼”的习俗,无疑会传至宋代。不过,宋代人口比唐代多了许多,而且就是在宋代,汉族人口中有很大一部分人,也就是所谓南方人,是以米饭为主食的。其实,他们本来就是吃米饭的,只是在宋代之前,以吃“饼”为主的北方人一直把他们视为“南蛮”。
很可能,蒸饭变为煮饭,就发生在这一时期。因为很可能,那些南方人本来就是把稻米煮来吃的,从未蒸过,也从未有过“甑”这种陶器。为什么说“很可能”,因为学术界至今无法确定,古代中国人是何时改蒸饭为煮饭的。
如果这事发生在宋代,那么对于南下的中原人来说,放弃蒸饭而接受煮饭,可能经历了很长一段时间。因为到了清朝的乾隆年间,我们仍从袁枚的《随园食单》中读到关于蒸饭和煮饭的议论:
《诗》称:“释之溲溲,蒸之浮浮。”是古人亦吃蒸饭。然终嫌米汁不在饭中。善煮饭者,虽煮如蒸,依旧颗粒分明,入口软糯。
袁枚仍在蒸饭和煮饭之间“彷徨”:蒸,有可能蒸不透;煮,有可能煮烂,要“善煮饭者”,才能“虽煮如蒸”,“颗粒分明”。
我们知道,后来吃米饭的中国人几乎都是煮的,很少蒸。只有某些特殊的米,如糯米,有时会蒸,因为糯米很难煮,稍不慎就烂了。不管怎么说,中国人完全放弃蒸饭,只吃煮饭的历史并不长,就是袁枚所在的乾隆年间,距今也只有二百多年。
说到乾隆,有件事正好在此一说。在乾隆年间,朝廷大力推广种植两种外来作物—红薯和玉米。红薯和玉米原产于美洲,由哥伦布在十六世纪初带回欧洲,再由欧洲传至非洲和亚洲。明朝万历年间,红薯被引入中国。大概情况,就如清朝陈世元在《金薯传习录》一书中所言:
按番薯种出海外吕宋。明万历年间闽人陈振龙贸易其地,得藤苗及栽种之法入中国。值闽中旱饥。振龙子经纶,白于巡抚金学曾,令试为种时大有收获,可充谷食之半。
文中所说“番薯”,即红薯。万历年间,由福建人陈振龙从吕宋(今菲律宾)引入,后陈振龙之子陈经纶,说服巡抚金学曾,令当地人种植,当年所收红薯,竟然“可充谷食之半”(可代替一半谷物)。于是,朝廷开始大力推广。尤其到了乾隆年间,由皇帝下旨,令民众开荒,大量种植红薯。至于玉米,也是明朝时引入的。不过,玉米来自中亚,是经由丝绸之路引进的。最初在广西种植,后经朝廷推广,从乾隆至道光年间,全国二十多个省全都大面积种植了玉米。在许多地方,玉米甚至代替小麦和水稻,成了主食。据说,清朝人口大增,红薯和玉米功不可没。
面 饼
前文说到“饼”,唐人喜欢吃“饼”。为什么要在“饼”字上加引号?因为这个“饼”和我们现在说的饼不一样。现在说的饼,大概就是指烙饼或煎饼,即在铁板上干烙或放点油煎的饼。但是,“饼”字的原义却是指任何用面粉做的食物,也就是说,所有面食都称为“饼”。
最早定义“饼”的古书,是东汉刘熙的《释名》。他在《释名·释饮食》中说:“饼,并也,溲面使合并也。”“溲面”,就是用水和面。从这条解释看,“饼”字最初是个动词,即“并面”,也就是“和面”。后来,不知从何时起,“饼”又不作动词用了,而用作了名词,泛指所有面食。用火烤的面食,叫“烧饼”(这和今天一样);用水煮的面食,叫“汤饼”(参见宋·吴处厚《青箱杂记》:“凡以面为食煮之,皆为汤饼。”今叫“面”或“面条”);用蒸笼蒸的面食,叫“蒸饼”,又叫“笼饼”“炊饼”(今叫“馒头”),如此等等。
其实,“馒头”的叫法几乎和“蒸饼”一样古老。据北宋高乘《事物纪原》一书考证,“馒头”似乎出自东汉末年,还和诸葛亮有关:
诸葛武侯之征孟获,人曰:“蛮地多邪术,须祷于神,假阴兵一以助之。然蛮俗必杀人,以其首祭之,神则向之,为出兵也。”武侯不从,因杂用羊豕之肉,而包之以面,象人头,以祠。神亦向焉,而为出兵。后人由此为“馒头”。
诸葛亮用“馒头”代替人头,最初应叫“蛮头”。里面还包了肉,今天似乎应叫“包子”,若叫“馒头”,北方人会觉得很可笑。但是,古人却是这么叫的,今天的南方人也这么叫。很奇怪,面食源自北方,承袭古称的竟是南方人。
那么,古人何时开始吃“饼”?先来看西晋束皙的《饼赋》,其曰:“《礼》,仲春之月,天子食麦,而朝事之笾,煮麦为麷。《内则》诸馔不说饼。然则虽云食麦,而未有饼。饼之作也,其来近矣。”《礼》就是《礼记》,《内则》是《礼记》中的一篇,其中说到许多食物,即引文中所说的“诸馔”。确实,《内则》没有说到“饼”。这不是遗漏,而是当时还没有“饼”。所以,束皙说“饼之作也,其来近矣”(饼是近来才有的东西)。那么,这个“其来近矣”,究为何时?我们不妨来推断一下。
《礼记》是西汉宣帝时的“博士”戴圣所作,束皙则是西晋时的“尚书郎”。西汉和西晋之间隔着东汉,而在《释名》中说“饼,并也”的刘熙,是东汉建安年间的人。这么看来,“其来近矣”是指东汉?可是,却冒出个西汉成帝时的“大儒”—扬雄,其《方言》曰:“饼,谓之饨,或谓之餦,或谓之馄。”尽管扬雄只注意到“饼”的名称,并未对“饼”做什么解释,但“饼”至少已是当时的“方言”。既然有“言”,肯定有“物”。更何况,他还说,“饼”也称作“饨”,称作“餦”,称作“馄”。这样一来,一下子把刘熙说的“饼,并也”推前了两百多年。也就是说,在汉成帝时,已经有“饼”,而在仅几十年前的汉宣帝时,“博士”戴圣尚不知饼为何物。由此推断,“饼”出现在西汉后期,也就是汉宣帝和汉成帝之间的汉元帝年间。
刘熙距束皙大概只有几十年,而扬雄距束皙却有两百七八十年。两百七八十年,能说“近矣”?看来,西晋时的“尚书郎”束皙,好像并不知道扬雄的《方言》,只看过刘熙的《释名》或东汉许慎的《说文解字》(其中有“释饼”:饼,面糍也),所以,才会说“其来近矣”。
那么,在西汉前期,如《礼记》里说的“天子食麦”,又是怎么回事呢?其实,自上古以来,中国人(中原人)就已“食麦”。为什么不食“饼”?因为,食“饼”需要先把麦粒磨成面粉,然后才能“并面”(和成面团),而要把麦粒磨成面粉,需要磨具,即石磨。然而,在西汉前期,中国人还不会制作石磨。所以,“天子食麦”是把麦粒蒸来吃,即吃麦饭,没有“饼”。
“饼”的出现,表明中国人在西汉后期已学会制作石磨。怎么学会的?有人认为是张骞出使西域,带回西域的石磨后,中国人学会了仿制。但是,算一算时间,似乎不对。张骞出使西域,是在汉武帝时,而“饼”的出现,是在汉元帝年间,两者相距近百年。仿制石磨,需要百年?那也太慢了。
实际情况虽无确切的史料可考,但不难推测:石磨从西域传至中原的时间不是汉武帝时期,而是在汉宣帝年间。至于是怎么传过来的,不知道。
关于“饼”,自扬雄、许慎、刘熙和束皙之后,还有许多人在许多书里谈论(好像关于“饼”的定义历来有争议)。南宋黄朝英在《靖康缃素杂记》里有一段概述:
煮面谓之“汤饼”,其来旧矣。按《后汉书·梁冀传》云:“进鸩,加煮饼。”《世说》载:“何平叔美姿容,面至白。魏文帝疑其傅粉,夏月令食汤饼,汗出,以巾拭之,转皎白也。”又按吴均称:“《饼德》曰:汤饼为最。”又《荆楚岁时记》云:“六月伏日并作汤饼,名为辟恶。”又齐高帝好食水引面,又《唐书·王皇后传》云:“独不念阿忠脱紫半臂,易斗面为生日汤饼耶。”《倦游杂录》乃谓:“今人呼煮面为‘汤饼’,误矣。”《懒真子录》谓:“世之所谓‘长命面’,即汤饼也。”恐亦未当。余谓凡以面为食具者,皆谓之“饼”。故火烧而食者,呼为“烧饼”。水煮而食者,呼为“汤饼”。笼蒸而食者,呼为“蒸饼”。而馒头谓之“笼饼”,宜矣。然张公所论市井有鬻胡饼者,不晓名之所谓,乃易其名为“炉饼”,则又误矣。按《晋书》云:“王长文在市中吃胡饼。”又《肃宗实录》云:“杨国忠自入市衣,袖中盛胡饼。”安可易“胡”为“炉”也。盖胡饼者,以胡人所常食而得名也,故京都人转音呼“胡饼”。
文中说到,称煮面条为“汤饼”不合适,因为“汤饼”是指所有水煮的面食。还说“水煮而食者”,呼为“汤饼”;“笼蒸而食者”,呼为“蒸饼”。这些,我在前文已经说了。值得注意的是,这里说到被人误称为“炉饼”的“胡饼”。
胡饼,“以胡人所常食而得名也”,即汉人对胡人常食之饼的称呼。胡人,即西北异族之总称。胡饼怎么做的?贾思勰《齐民要术》曰:“面一斗,羊肉二斤,葱白一合,豉汁及盐,熬令熟,炙之,面当令起。”
宋朝王谠《唐语林》曰:“时豪家食次,起羊肉一斤,层布于巨饼,隔中以椒、豉,润以酥,入炉迫之,候肉半熟食之。”
注意,按上述两种方法做出来的胡饼,是极品,是最上乘的,虽然那也不过是用葱、椒、豉、盐做配料烘烤而成的羊肉馅饼,但和普通的胡饼相比,已是非常考究。普通胡饼做起来简单得多,只是在面粉里拌上一些油脂,做成厚厚的饼状,然后在上面撒一层芝麻,放到炉中烤熟,即成。就如刘熙《释名》所云:“胡饼,作之大漫冱也,亦言以胡麻着上也。”
“大漫冱”,壮观貌。可见,胡饼很大。芝麻在古代叫“胡麻”,和胡饼一样,也是从胡人那里传入中原的。(参见沈括《梦溪笔谈》:“胡麻直是今油麻,汉使张骞始自大宛得油麻之种,古名胡麻。”)按《齐民要术》的方法,做一次胡饼要用二斤羊肉。按《唐语林》的方法,也要用一斤羊肉。这么大的胡饼,吃的时候显然是要用刀切开的,就像现在街上仍有卖的“羌饼”那样。其实,羌饼也是胡饼,因为羌人是胡人中的一族,羌饼上面也有一层芝麻。稍不同的是,羌饼是烙饼(放在铁板上烙熟的),唐代的胡饼是烧饼(放在火上烤熟的)。
不知何故,就是这种今天看来仅供充饥的胡饼,竟然使古代中国人痴迷了上千年。尤其从东汉到大唐,胡饼每每还是皇家御馔。请看史书里说到的一些事例:“宣帝微时,每买饼,所从卖家辄大售,亦以自怪。”(《汉书》)皇帝买饼吃,还被卖家斩(“辄大售”),真是奇了怪也。不过,这是皇帝落难时(“微时”)。“灵帝好胡饼,京师皆食胡饼。”(《续汉书》)皇帝喜欢吃胡饼,一班臣民跟着吃,以表忠心。“惠帝崩,由食饼也。”(《晋阳秋》)这位皇帝真是搞笑,吃饼吃到驾崩。“永明九年正月,诏太庙四时祭荐宣皇帝,面起饼。”(《齐书》)这位皇帝竟然用饼来祭祖。“贵人御馔,尽供胡食。”(《旧唐书》)大唐宫廷,大吃西餐。“胡食”确是当时的西餐(“西”来的“餐”),尤以胡饼为主。
确实,不仅大唐宫廷“尽供胡食”,大唐臣民也食饼成风。这食饼之风,甚至连外国人也知道。譬如,唐武宗会昌年间,有个叫“圆仁”的日本僧人入长安,亲见京城胡饼盛行。回国后,作《入唐求法巡礼行记》。其中曰:“立春节,赐胡饼,寺粥。时行胡饼,俗家皆然。”立春那天,唐人互赠胡饼(“赐胡饼”),寺庙里施粥(“寺粥”)。“时行胡饼,俗家皆然”,意即人人吃胡饼,除了出家人。
这个日本僧人说得一点不错,唐人确实是把胡饼当作礼物送人的。白居易还曾写过一首题为《寄胡饼与杨万州》的诗:
胡麻饼样学京都,面脆油香新出炉。
寄与饥馋杨大使,尝看得似辅兴无。
杨万州即杨归厚,时任万州刺史,故称“杨万州”。白居易时任忠州刺史,可称“白忠州”。这白忠州为什么要写这首诗呢?因为他做了一次胡饼,而且是照京城里的做法做的,很得意,特地寄给老朋友尝尝。忠州离万州不远,都在四川,所以送饼是可行的。最后一句“尝看得似辅兴无”,是说你看味道是不是很像辅兴坊的胡饼。“辅兴坊”是长安城里最有名的一家饼店。
那时的长安城里,有许多卖饼的胡人,这在读唐传奇时也能体会到。譬如,唐传奇《鬻饼胡》,其开篇曰:“有举人在京城,邻居有鬻饼胡。”“鬻饼胡”即卖饼的胡人。还有唐传奇《任氏》,其中曰:“既行,及里门,门扃未发。门旁有胡人鬻饼之舍,方张灯炽炉。”
虽然传奇故事和胡饼没有直接关系,但作者时不时说到卖饼人,使我们得知,当时长安城里有许多卖饼人—既然有那么多卖饼人,肯定有更多吃饼人。
还有唐传奇《贺知章》,讲贺知章向一个老人求道的故事。其中讲到,贺知章为了请教那个老人,特意奉上自己珍藏的一颗明珠,可没想到:“老人即以明珠付童子,令市饼来。童子以珠易得三十余胡饼,遂延贺。”
用珍贵的明珠去换胡饼,这使贺知章“意甚不快”。然而,这正是老人对他的教诲:要想得道,“当须深山穷谷,勤求致之,非市朝所授也”。这里,胡饼成了“市朝”的代表,可见胡饼在唐人生活中有多重要。
唐之后,胡饼渐渐式微,渐而由蒸饼(馒头)和汤饼(面条)取而代之。这一变化,发生在宋代。到了明清两代,胡饼依然有,但成了“点心”,馒头和面条成了北方中国人的主食。在南方,也有胡饼,但南方人只是偶尔才会尝尝。他们的主食,如前所述,是米饭。
此外,还有两种面食,虽不是主食,不会天天吃,但也经常吃。那就是南方人吃的馄饨和北方人吃的饺子。
其实,馄饨和饺子都是“饼”—汤饼,水煮的面食。还记得扬雄在《方言》中所说吗?“饼,谓之饨,或谓之餦,或谓之馄。”这里,姑且不去管它“餦”是什么,至少我们读到了“饨”和“馄”两个字。只要把次序颠倒一下,就有了“馄饨”。按扬雄的意思,“馄”和“饨”都是“饼”。问题是,这种“饼”是蒸饼,还是汤饼?从我们今天吃的馄饨看,应该是汤饼。那为什么这种汤饼被称作“馄饨”,而最常吃的一种汤饼又被直接称作“面”,我想,区别大概在于馄饨是有馅的,面是没馅的,只有面粉。
那么,“饺子”又是怎么回事?其实,饺子只是形状与馄饨有点不同。馄饨的形状,从西汉到清朝,一直是圆的,很像我们今天吃的汤团,就如清代富察敦崇在《燕京岁时记》中所言:“夫馄饨之形有如鸡卵,颇似天地混沌之象,故于冬至日食之。”可见,到了清朝,馄饨仍是圆的。至于我们今天吃的元宝形馄饨,那是近代才有的一种“变形馄饨”。饺子的形状,是半圆形的,有两个角,所以刚出现的时候叫“角子”。据说,饺子是东汉名医张仲景发明的,他把羊肉、胡椒等剁碎后包在面皮中,然后下水煮,煮熟后就是一剂活血祛寒的良药,称作“祛寒娇耳汤”。也许是为了有别于平时吃的馄饨,他故意把它做成耳朵状,即半圆形的,并取名为“角子”。若真是这样,饺子最初是药,并不是食物。遗憾的是,这些都是后人编的故事,毫无根据。传说张仲景写的那本《伤寒论》里,也没有“祛寒娇耳汤”。
此外,还有一种主食,本应说一说的,但限于篇幅,只能在这儿提一下了。那就是粥。前面所引《逸周书》说:黄帝“烹谷为粥”。后来历朝历代,中国人从未停止喝粥。对许多穷人来说,粥可能还是他们唯一的主食,因为他们拥有的“谷”实在太少,若“蒸谷为饭”,根本吃不饱。当然,历朝历代的达官贵人也喝粥,但他们是为了“养生”。所以,历朝历代的医书和笔记里充斥着各种各样的“养生粥”,譬如“七宝粥”“五味粥”“茯苓粥”“胡麻粥”“羊肚粥”“狗肾粥”,甚至“人乳粥”,形形色色、五花八门,不是说可以延年益寿,就是说可以补肾壮阳。至于到底有没有这样的奇效,那就只有天知道了。
本文选自《古代中国人的生与死》,刘文荣著,文汇出版社即将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