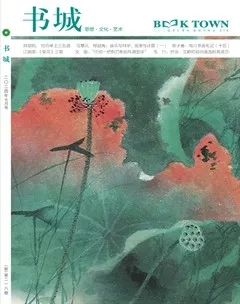《三国志·吴志》札记
2024-07-18李庆西
“据三州虎视天下”
读《三国志》,体察曹、刘、孙三氏各自意业,可见陈寿落笔饶有思虑。写曹氏父子,旨在统率纲维,为王者之道;写刘备,表现其折而不挠,亦一世之雄;唯独孙权,以应变性格与想象力设置主题,由其自擅霸业,自设一种神话困境。三方开国君主中,孙权在位最久,凭览前后三十年(自吴国初建,立“黄武”年号算起),是非成败,断鸿声老。
诚如《吴志·吴主传》“评曰”所言,孙权“屈身忍辱,任才尚计,有勾践之奇”,而另一方面,又是“性多嫌忌,果于杀戮”。他一再改立太子,对谁都不放心。太子党、鲁党两边都不信,连自己的儿子女婿都杀—鲁王孙霸夺储不成,被“赐死”;左将军朱据(适公主鲁育)拥护太子孙和,亦“赐死”。
说到屈身忍辱,孙权跟刘备大不同。刘备早年寄人篱下是自己无立锥之地,有人收留就行。对照《蜀志·先主传》,不难看出,刘备并不擅长折冲樽俎与人周旋(自诩继统汉祀,视别人都是伪僭)。孙权则不然,真正是能屈能伸,从不在一棵树上吊死。有一点不能不说,在三方鼎峙格局中,东吴是唯一对其他两方都下过狠手也曾曲意妥协的一方。比如,对付刘备,孙权是既打又拉。灭关羽定荆州,转身就跟刘备“遣书请和”;之前,赤壁战后刘备领荆州牧,便是“进妹固好”;之后,夷陵大破蜀军,旋而又“遣使请和”。
对曹魏这边,孙权更是虚与委蛇。曹操在世时,孙权就“上书称臣”,还进劝曹操做皇帝。曹丕称帝之后,他便是北面称藩,受封为吴王。但因为不肯拿太子登做质押,暴露其“诚心不款”,魏国发三路大军来攻,孙权赶忙做检讨化解危机。稍早,就在刘备伐吴的节骨眼上,孙权怕曹魏背后捅刀子,遣都尉赵咨出使魏国。《吴主传》记述赵咨回答魏帝问话,以不吝赞美之辞道出孙权几个特点:
魏帝问曰:“吴王何等主也?”[赵]咨对曰:“聪明仁智,雄略之主也。”帝问其状,咨曰:“纳鲁肃与凡品,是其聪也;拔吕蒙于行阵,是其明也;获于禁而不害,是其仁也;取荆州而兵不血刃,是其智也;据三州虎视于天下,是其雄也;屈身于陛下,是其略也。”
送还于禁一事,不过是讨好曹魏的顺手人情,算不上“是其仁也”。其他几点,却非虚言。孙权占有扬、荆、交三个地域辽阔的大州(其实扬、荆二州北部尚属曹魏),“据三州虎视天下”,自是不可小觑的存在。不过,东吴总是很有危机感,佯称“屈身于陛下”,居然将曹丕糊弄过去。孙权这人性格层次太多,其开土拓疆的雄心和想象力亦非别人所能想象。
从谭其骧《中国历史地图集》(第三册)三国全图来看,如果不算人稀地广的西域长史府,吴魏两国地盘庶几相埒。孙权称帝当年曾盘算将辽东公孙渊收归藩属,这事搞砸了,但第二年即出征夷洲(今台湾地区)、亶洲(今日本国),赤乌五年(242)又征珠崖、儋耳(今海南省)。这些跨海开拓虽未见成效,却可见孙权“虎视天下”的目光可真是无远弗届。早在建安十五年(210),他已将交州收入囊中。交州地域不仅包括今之两广,更延至今之越南中部,并将扶南(柬埔寨古国)、林邑(今越南中南部)、堂明(老挝古国)等外藩纳入职贡(见《吴志》孙权、士燮、吕岱诸传)。
“惟尔有神飨之”
孙权登基之前,有一段准备时期,既受封吴王,便自立年号“黄武”。《吴主传》接连记载吴地各处出现祥瑞,如东吴黄武二年(223)“曲阿言甘露降”,四年“皖口言木连理”,五年“苍梧言凤皇见”,八年“夏口、武昌并言黄龙、凤皇见”。八年四月,孙权终于称帝,改黄龙元年(229)。之前魏文帝已驾崩,明帝践阼亦有两载。
跟魏蜀两国不同,陈寿将孙氏建国的合法性完全归结于天命。虽然曹丕、刘备登基时也都是一套君权神授的说法,但是到孙权这儿尤为强调“惟尔有神飨之”。《吴主传》记录作为神谕的祥瑞之物不断出现—嘉禾生、甘露降、赤乌集、黄龙见、神人授书……这些现象预示着天命神明之应,亦是国家话语的重要构成。在孙权及其身后三嗣主采用的十八个年号中,大多取自这类符瑞(如黄龙、嘉禾、赤乌、神风、五凤、甘露、宝鼎、凤皇、天册、天玺、天纪等),似乎一切历史活动都围绕神迹而展开。如,嘉禾改元赤乌,传中作如下说明:
秋八月,武昌言麒麟见。有司奏言,麒麟者太平之应,宜改年号。诏曰:“间者赤乌集于殿前,朕所亲见,若神灵以为嘉祥者,改年宜以赤乌为元。”群臣奏曰:“昔武王伐纣,有赤乌之祥,君臣观之,遂有天下。圣人书策,载述最详者,以为近事既嘉,亲见又明也。”于是改年。
虽然,曹魏之王权建构亦夹杂此类受命符瑞的故事(如青龙见摩陂井),但痴迷程度远不及东吴,而蜀汉则几乎不问天命。读《三国志》诸帝纪传,各自叙事模式实大相径庭,概乎言之,曹魏践行王道之职,蜀汉贯以正邪之论,东吴则悬于天人之际。孙权的国事充满了各种留予后人猜详的隐喻,其生前三立太子,身后是两度废立之局……据于神的想象,大可撇开现实羁绊。孙权死的前一年,派官员迎“神人”王表,神神道道,语焉不详,让人更觉匪夷所思。时谚曰:“国将兴,听于民;国将亡,听于神。”(裴注引孙盛语)其实孙权始终是“听于神”的神谕主义。其后三嗣主将亡不亡,魏禅晋,蜀亦灭,它不死不活撑到最后。
《吴志》卷十八专设吴范、刘惇、赵达三位占候家列传,载录各种卜筮谶应之事。如,孙权初为将军时,吴范预言:“江南有王气,亥子之间有大福庆。”他说的“亥子之间”就是建安二十四年至二十五年,这其间孙权擒关羽、定荆州,受封吴王,吴国始建。又,孙权在豫章时,问灾变之事,刘惇以星躔推算“灾在丹阳”,果然孙权之弟、时为丹阳太守的孙翊被手下人杀害。赵达擅九宫一算之术,亦见“东南有王者气”,早早渡江南来。本传谓:“孙权行师征伐,每令(赵)达有所推步,皆如其言。”在陈寿笔下,东吴历史似有一种神谕的先验逻辑,一切军政大事冥冥之中皆有预设。
当然,孙权本人就是神话的主人公,自有超越魏帝和蜀主的气场和境界。主人公将退场之际,那些符命自然就成了失落的凶兆。《吴主传》记述了那种天崩地裂的惊悚场景—大风卷地,江海涌溢,高陵松柏斯拔,郡城南门飞落……
孙权建国理念
魏、蜀、吴三方建国理念各有不同,简单说分别是代汉、祀汉、去汉。关于三者之意涵,笔者在《建安二十六年》(文津出版社2022年)一书中有专文陈说,可扼述如下:
汉献帝建安二十五年(220),曹丕以禅代方式践祚,结束了汉朝历史。这番以魏代汉的程序颇为复杂,其过程《魏志·文帝纪》未作详述,但裴注引《献帝传》状述其事,连篇累牍皆是新君旧君与诸臣互动的繁文缛节—臣下不断上奏劝进,献帝本人更是一再申明汉祚已终,从虞舜之义说到各地出现之祥瑞,无非说明禅代之事已是天命所归。走禅代程序,不能完全视为权力转移的一种伪饰形式(汉廷早为曹氏挟制,以魏替汉并未真正发生权力转移),而是以这种方式昭示天下,曹氏从刘姓天子手里接过了汉家江山。这不但是作为一种合法性依据,更重要的是它传递了国家让渡的消息,旨在杜绝刘备、孙权以恢复汉室的名义兴兵作乱,尤其是借以褫夺刘备承祧汉祚的资格。
可就在曹丕成为魏文帝的第二年,刘备也赶紧做了皇帝。如果说魏国合法性来自献帝禅让,刘备则以宗室身份“祚于汉家”,这是其血脉带来的根由。他在登基文告中宣示其“率土式望,在备一人”之嗣国资格,并谴责曹丕“载其凶逆,窃居神器”云云。蜀汉虽仅占据汉末十四部州中一个益州,却并非作为割据政权而存在,数十年间始终持有大汉王朝的帝国心态,理所当然认为普天之下皆为其汉家领土。蜀汉自己地盘太小,便以想象和征伐去拓展帝国疆域。征伐是后来诸葛亮、姜维折腾未果的事业,但刘备在想象中已将中原划入自己版图。譬如,其分封诸王便发明了一种“遥领”制度,将封地一概置于境外。《蜀志·先主传》谓,刘备于章武元年(221)分封诸子,立刘永为鲁王,刘理为梁王。作为封地的鲁、梁二郡国都在魏国境内。既是遥领,未能“之国”,也是宣示主权的一种话语方式。后主刘禅不仅将其六子分封到魏国,还跨境遥置封疆府署,作为对臣下的特进奖赐,如魏延、姜维就先后遥领魏地凉州刺史。
相对而言,孙氏立国似乎逮不着实际的合法性。本来,东吴有孙坚从洛阳宫中获得的传国玉玺(《吴志·孙坚传》裴注引韦曜《吴书》),那倒是一件“神器”,只是当初孙策向袁术借兵作为质押,后被徐璆所得致之献帝(《魏志·武帝纪》裴注引《先贤行状》)。可那东西不过是个物件,即使仍在孙权手里又能怎样。
当然,孙权自有说辞,就是直接诉诸天意。东吴建政只比蜀汉晚一年,自立年号“黄武”乃其初建之始。孙权是先称藩,曹丕册封他为吴王,他“先卑而后踞之”,在立国问题上延宕时久,七年后才以吴大帝身份登基。这个策略性过程比较复杂,这里不作详述。总之,代汉、祀汉,都没他的戏码,孙权干脆抛开那个远去的刘汉国家,将自己的政权来由完全归结为天命。登基之日,他在祭天文告中这样说:
汉享国二十有四世,历年四百三十有四,行气数终,禄祚运尽,普天弛绝,率土分崩。孽臣曹丕,遂夺神器;丕子叡,继世作慝,淫名乱制。权生于东南,遭值期运,承乾秉戎,志在平世。奉时行罚,举足为民。群臣将相,州郡百城,执事之人,咸以为天意已去于汉,汉氏已绝祀于天,皇帝位虚,郊祀无主。休徵嘉瑞,前后杂沓,历数在躬,不得不受。权畏天命,不敢不从,谨择元日,登坛燎祭,即皇帝位。惟尔有神飨之,左右有吴,永终天禄。(《吴主传》裴注引《吴录》)
这登基的祭天文告中特意强调:“天意已去于汉,汉氏已绝祀于天!”申言“惟尔有神飨之”,就是要剥离汉业之因缘。
本来,所谓“君权神授”就是一种合法性,但孙权干脆釜底抽薪,直接拉黑了世俗的皇权统绪。可话说回来,原先在他老爸手里的传国玉玺就镌有“受命于天,既寿永昌”的字样,“有神飨之”之说,冥冥之中还是来自“受命于天”的汉家之命。
以行辕为国都
魏蜀吴三方,东吴最具草根性和原生特点。孙氏坚、策父子破虏讨逆,纵横天下,仍扎根于吴会之壤。建安五年孙策薨,孙权接领部曲,是时据有会稽、吴郡、丹阳、豫章、庐陵诸郡。曹操表孙权为讨虏将军,领会稽太守。会稽太守本治山阴,孙权不之郡,却留驻吴县(今苏州),显然为军事便利之计。此后其治所和国都均建于长江沿线,贴近荆州和曹魏地盘,摆出一种咄咄逼人的架势。
建安十三年,孙权自吴迁治京口(今江苏镇江)。其时吴国尚未初建,只是将京口作为大本营。顾祖禹《方舆纪要》介绍说,“汉建安十三年,孙权徙镇于此,筑京城,周三百六十步,于南面西面各开一门,因京岘山为名,号曰京镇”(卷二十五南直七)。按此描述,这是一个不大的城池,更像是军事堡垒。赤壁大战后,刘备雄踞荆州,《先主传》谓:“(孙)权稍畏之,进妹固好。先主至京见权,绸缪恩纪。”京,即京口。刘备诣京见孙权之事,见于《吴志》周瑜、鲁肃、吕范诸传。小说戏曲将此演绎为刘备招亲故事,可发一噱。
京口作为孙权治所只是三四年光景,很快又迁至秣陵(今南京)。《吴主传》谓:“(建安)十六年,(孙)权徙治秣陵。明年,城石头,改秣陵为建业。”秣陵与京口相去不远,此地古称金陵,秦时置县,西汉时一度为小侯国,东吴建都之前算不上什么通都大邑。自孙权到此,更名建业,开启六朝繁华的历史。当然,孙权这时顾不上都城规划与建设,重点是改造临江的石头城,是从军事戍防考虑。故左思《吴都赋》有“戎车盈于石城,戈船掩乎江湖”之语。从建安十六年到二十五年,孙权在建业这九年中,与曹魏在东兴至皖城一线互有攻防,吴军几度推进到合肥均功败垂成,而曹军亦未能突破濡须口(在今安徽无为县)。
建安二十四年,东吴灭关羽,定荆州。翌年曹操薨,曹丕称尊后改元黄初。二年,刘备亦称帝,就在这个历史节点,孙权悍然将都城迁至武昌。《通鉴》胡三省注曰:“既城石头,又城武昌,此吴人保江之根本也。”其实,这不是防御思路,是以行辕为国都。武昌地理位置接近中原,曹魏尚占据荆州北部(襄阳、江夏等七个郡),孙权将国都推至前线,大有进攻意图。但这同时也使自己处于“豺狼交接”的夹缝中。此际东吴虽向魏国称藩,但因拒绝质押太子登的征命,面临三路攻来的危局。孙权一方面临江拒守,一方面“卑辞上书,求自改悔”,施以缓兵之计。
东吴黄龙元年夏四月,孙权即皇帝位,是年九月便将都城迁回建业。在武昌的九年中,东吴巩固了荆州西部,却未能楔入中原,孙权这时感受到国都置于疆畔之弊。比之武昌,建业防御态势较好,至少不会腹背受敌。当然,回迁建业另有一个重要原因,此际孙权的战略思路已转向辽东和海外。
起初,重新作为都城的建业并未大规模兴建宫苑,孙权居住的建业宫还是早年从京口迁来时建造的将军府。至赤乌十年(247)改建时已窳败不堪。这年二月,孙权迁居太子所住的南宫,在将军府原址修建太初宫。从三月开工到翌年三月竣工,正好用时一年。工程如此快速是因为驱使文武百官投入大量义务劳动(曹叡修洛阳宫亦如此),另一个原因是太初宫所用建材系拆之武昌宫的砖瓦木材。孙权声称效仿大禹以“卑宫为美”,其实是因为“军事未已”而未敢过度劳民伤财。
吴大帝之后,孙亮、孙休两位均为弱主,未治都城宫苑。至宝鼎二年(267)末代吴主孙皓开始大兴土木,起昭明宫,面积与太初宫相当,工程仅耗时半年。当然亦驱使官员为劳役,“二千石以下皆自入山督摄伐木”(裴注引《江表传》)。孙皓颇能折腾,可谓“王事靡盬,不遑启处”,在此之前(甘露元年,265)曾迁都武昌,一年后又从武昌迁回建业。这位酒色荒淫的皇帝亦幻想开土拓疆,闻说北方防守空虚,以为徙都武昌可伺机长驱中原,未免作画饼之想。
将国都置于武昌,远离吴会富庶之地,必然有一个大问题,就是物资给养全靠长江下游泝流运输(想来孙权那时亦如此),左丞相陆凯上疏称“扬土百姓,以为患苦”,举童谣谏曰:“宁饮建业水,不食武昌鱼;宁还建业死,不止武昌居。”(《吴志·陆凯传》)孙皓很快就回迁建业,恐怕亦是国力难以支撑如此繁重的物流。吴都在建业与武昌之间来回折腾,反映了孙氏爷孙两辈的战略踌躇。
征伐宗部与山越的长期战争
唐长孺先生早年所作《孙吴建国及汉末江南的宗部与山越》(《魏晋南北朝史论丛》,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5年),论述孙氏建国前后征剿宗部、山越之长期斗争。所谓宗部(又作宗伍),即江南地区以山越(山民)为基础的宗氏武装。这种山野强宗不同于北方士族,亦不同于本地豪门世家,向未濡染儒学教化,又完全处于王权治外,且好武习战,不时与官府发生冲突。陆逊初入孙权帐下,即建言曰:“山寇旧恶,依阻深地,夫腹心未平,难以图远。”(《吴志·陆逊传》)确实,东吴建国须面对攘外安内两大要务:一边与曹操、袁术、刘繇、刘表等各路豪强相抗衡,一边要扫荡其域内大大小小的草莽武装。
自坚、策父子讨伐许昭、祖郎、严白虎开始,孙氏集团一直致力于消灭江南宗部武装。《吴志》载述各地山越之患并及孙吴之征讨行动,见于孙权、太史慈、士燮、孙贲、孙辅、吕蒙、黄盖、韩当、蒋钦、周泰、潘璋、朱治、吕范、骆统、陆逊、贺齐、全琮、吕岱、周魴、钟离牧、潘濬、陆凯、诸葛恪诸传(包括裴注所引诸史)。江南山越草莽分布甚广,尤以丹阳、会稽、东安、鄱阳、海昏、庐陵、武陵等处为盛。如丹阳一地,自孙策以来,数十年间迄未平定。建安中陆逊、贺齐等继而进剿,嘉禾三年(234)诸葛恪领太守,又大举扫荡。诸葛恪此役历时三年,方得平定宗伍使山民归化。
东吴与宗部的战争有一个实际所得,就是掳获山越之民,纳入诸将领的部曲和庄户(所获田客又称“复客”),即所谓“强者为兵,羸者补户”(《陆逊传》)。《吴志》诸传有许多这样的记载。如,黄武七年,全琮领东安太守,以“招诱降附”的手法对付山越,“数年中得万余人”(《全琮传》)。之前,凌统进山征讨,亦以“恩威”诱之,“得精兵万余人”(《凌统传》)。陆逊早年进剿丹阳数地,“得精卒数万人”,嘉禾中破鄱阳等三郡,“料得精兵八千余人”(《陆逊传》)。诸葛恪平丹阳山越,从俘虏中“得甲士四万”,其“自领万人,余分给诸将”(《吴主传》《诸葛恪传》)……从这些实例可以看出,进山征伐所获的人力资源源源不断地补充了东吴的军队和农业人口。
唐先生文中特别指出,讨伐宗部与山越的长期战争,使东吴形成一种独有的领兵制度和复客制度,并由此影响其国家建构。汉末三国时期,各路豪强纠合宗氏乡党起事,其部曲本身多具私兵性质,或称“家部曲”(语出《吴志·顾雍子邵传》裴注引《文士传》)。应该说,这种情形并非东吴特有,曹魏将领中李典、吕虔、许褚等亦自拥部曲,不过他们的私兵只是从乡里带出来的兵勇,亦未是一种普遍现象。而东吴将领的私家部曲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可以世袭,跟他们的庄户田客一样,父子兄弟递相继承。这种制度设计,显然是根据战功实行利益分配。在“君君臣臣”的制度安排中,其将相大臣亦各有自己的实体经济,这就加入了一种类似合伙人的利益关系。
东吴的国家构成更接近汉初的分封体制,孙氏宗亲及异姓将领权益均霑是其特色。
关于北人与南人
汉末群雄破黄巾讨董卓,吴会精英趁势崛起。坚、策父子破虏讨逆,驰驱中原,大量网罗北方人氏,故东吴将相大臣中北人竟不在少数。
检点《吴志》诸传,除去孙氏宗室子嗣,不算孙氏集团之外的刘繇,凡列五十八人(不计各传所附子孙)。其中北人十四,即太史慈(东莱)、张昭(彭城)、周瑜(庐江)、鲁肃(临淮)、程普(右北平)、韩当(辽西)、陈武(庐江)、甘宁(巴郡)、潘璋(东郡)、吕范(汝南)、丁奉(庐江)、赵达(河南)、王蕃(庐江)、楼玄(沛郡)等;还有,避乱江东或交州的北人十五,有士燮(鲁国)、诸葛瑾(琅邪)、步骘(临淮)、张纮(广陵)、严畯(彭城)、程秉(汝南)、薛综(沛郡)、吕蒙(汝南)、徐盛(琅邪)、吕岱(广陵)、是仪(北海)、胡综(汝南)、刘惇(平原)、诸葛恪(琅邪)、濮阳兴(陈留)等。两项合计二十九人,正好占一半。当然,《吴志》立传并不十分允当,这里仅取作一个统计样本,不及其他。
上述北人名单中多为孙氏建国前后的肱股之臣,籍贯分布甚广。东吴虽植根吴会之壤,倒是很具有五湖四海的特点,而反观曹魏和蜀汉集团,却绝无江东人氏。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差异?好像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过去周一良先生有个说法,认为是北人对南人持有偏见,而江东远离中土文化圈,吴人本身亦有自卑情绪(《晋书札记》,见《魏晋南北朝史札记》,中华书局1985年)。周先生说的是西晋王朝如何对待吴人,但西晋承续曹魏而来,魏晋风尚大率相似。不过,这说法似乎简单些,先前长安、洛阳不乏吴会人物,如前汉之朱买臣、严助、郑吉,后汉之王充、严光、魏朗、许靖、朱儁、陆康等,都来自会稽郡(东汉中期之前会稽包括吴郡)。何以三国时期又是另一番情形?这不大好解释。三国人物之地域关联性当有其他因素,或是值得深入讨论的。另如:颍川之于曹魏,荆襄之于蜀汉,似乎都有其特殊意义。
不过,以郡望而论,东吴人物出自吴郡、会稽二郡最多,孙权家族本出富春(今杭州富阳区),汉末三国此地属吴郡,浙水(钱塘江、富春江)以东接壤会稽郡。居于东吴核心地带,吴会大族所受用,亦体现这个政权的原生性。至东吴政权后期,确实南人多居要津。审核《吴志》列传人物,吴郡、会稽二郡先后凡二十二人,吴郡有顾雍、凌统、朱桓、陆逊、陆绩、张温、吾粲、朱据、全琮、周魴、陆凯、孙峻、孙綝、韦曜等十四人,会稽则是阚泽、董袭、虞翻、骆统、贺齐、钟离牧、吴范、贺邵等八人。其中顾、陆、朱、贺等高门大族尤为显贵,对东吴政治影响甚巨。唐长孺《孙吴建国与汉末江南的宗部与山越》文章里借此论证南人对北人的排斥,其中有这样一段话:
在孙吴末期政治上占有特殊地位的便只剩下了南方大族,非土著的北来侨寓即便开国元勋又是汉高门如张昭、周瑜、诸葛瑾之后都倒了霉。鲁肃、吕蒙之后也无著称人物,孙皓时三公之位几乎全是南人,直到晋代江南大族没有一家是孙吴时南来的北人。这个事实说明宗族乡里的结合排斥了这些外来者。
不过,唐先生所谓南方大族排斥外来者的看法,未免臆说。东吴后期南来之北人衰颓不振是事实,但未必是南北地域性攘斥。这里有几个因素不能忽略:
一、东吴北方人氏中最重要的三位元勋都过早夭折,周瑜卒于建安十五年(36岁),鲁肃卒于二十二年(46岁),吕蒙卒于二十五年(42岁),他们都没有活到东吴建国之日。周瑜一子早卒,一子初拜将封侯,后获罪流徙庐陵,为此诸葛瑾、步骘(二者皆北人)联名上疏求情,而朱然、全琮(二者皆南人)“亦俱陈乞”。此子不知何罪,有称“酗淫自恣”,但显然不是南人排斥而构陷。至于张昭二子,因牵入鲁王争储而罹难。诸葛瑾后人亦“倒了霉”,指诸葛恪被孙峻设局诛杀。这些纯是权力斗争,无关乎地域、宗族。
二、君臣相拗,是一大问题,而吴主心目中并无南北厚薄之分。北人张昭反对与辽东公孙渊结盟,孙权不听,此老便称疾不朝。南人陆逊谏阻出师夷洲及朱崖,孙权也不听。位高权重的陆逊但因卷入立储之争,屡遭孙权斥责竟“愤恚致卒”。孙权之后三嗣主时期,大臣得宠或失势亦并无地域因素。
三、鲁王霸与太子孙和争储,形成“二宫构争”之局,撕裂了东吴王室及整个士族集团,此中情形可见《吴主五子传》裴注一则引文:“丞相陆逊、大将军诸葛恪、太常顾谭、骠骑将军朱据、会稽太守滕胤、大都督施绩、尚书丁密等奉札而行,宗事太子。骠骑将军步骘、镇南将军吕岱、大司马全琮、左将军吕据、中书令孙弘等,附鲁王。中外官僚,将军大臣,举国中分。”(引殷基《通语》)显然,太子党与鲁党开撕,并非以南北选边站队。
四、民间的地域歧视和排斥不能说没有(至今陋习仍存),但是在东吴国家政治层面的争斗和倾轧无疑超越了乡闾俗见,事实上不存在“宗族乡里的结合”这种集团势力,没有确凿证据可以认定南方大族挤兑北人。
有趣的是,唯见记载的地域歧视倒是在江南大族之间。《世说新语·政事》有一则记述会稽与吴郡之争衅,实令人发噱。贺邵(贺齐之孙)初任吴郡太守时,闭门不出,吴门大族讥之为“会稽鸡,不能啼”,贺氏即回怼“不可啼,杀吴儿”。于是检察吴郡顾氏、陆氏不法之事,报告朝廷。其时,陆抗(陆逊之子)都督荆江军事,急忙从江陵赶赴建业向孙皓求情,好歹将这麻烦事摆平。说来有些八卦,却偏说南人窝里斗。
作为吴会大族的贺氏、陆氏后来皆不幸遭殃。贺邵犯颜直谏,因被诬告其“谤毁国事”,天册元年(275)被孙皓杀害。陆凯亦有直谏之名,据传还参与万彧等人的废立之谋,其生前孙皓未敢下手,只是“陆抗时为大将,在疆场,故以计容忍”(《陆凯传》)。凤皇三年(274),陆抗一死,陆凯家人就被流徙荒陬海隅。凶顽骄矜的孙皓对南人并不手软。
二○二四年六月五日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