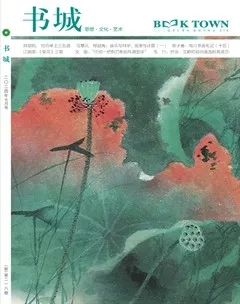《诗经》中的鲤鱼
2024-07-18林卫辉
在《诗经》里,鲂鱼出现次数最多,排第二的就是鲤鱼,虽然次数没有鲂鱼多,但其重要性并不比鲂鱼低,它常与鲂鱼一并出现,比如《陈风·衡门》:
衡门之下,可以栖迟。泌之洋洋,可以乐饥。岂其食鱼,必河之鲂?岂其取妻,必齐之姜?岂其食鱼,必河之鲤?岂其取妻,必宋之子?
这首诗的创作背景,历代学者的观点有较大分歧,不同创作背景对这首诗就有不同的解读,如果把《陈风·衡门》看作一首爱情诗,那么此诗的大意是:夕阳已逝,月上柳梢,一对青年男女悄悄来到城门下密约幽会,一番卿卿我我的甜言蜜语之后,激情促使他们双双相拥,又来到郊外河边,伴着哗哗的泌水,极尽男欢女爱。或许小伙儿被这难忘良宵陶醉,竟发表了一段富有哲理的爱情名言:吃鱼何必一定要黄河中的鲂鱼或鲤鱼?娶妻又何必非齐姜、宋子不可?只要是两情相悦,谁人不可以共度美好韶光?言外之意是,他与眼前的女子情感甚笃,非常满意,希望娶她为妻。
如果把这首诗当成隐者安贫乐道之诗,那么此诗的大意是:一个居住在蓬户柴门的小农或读书人,他一大早打开柴门,面对家门前的洋洋泌水,微微笑着出口成章:哎哟!有此一间柴门陋室,可以栖身避雨,此生足矣!有此一汪洋洋泌水,每天清波潋滟,观此美景,虽腹饥亦以为乐也!难道吃鱼就一定非要吃黄河里的鲂鱼、鲤鱼吗?难道男人娶妻就一定非要娶齐姜、宋子吗?甘愿清贫度日,粗茶淡饭,从从容容,平平淡淡,不求富贵,不求闻达,有一老妻相伴,厮守终生,也不失为人生一大乐趣。
不管如何解释,把吃鲤鱼和鲂鱼与娶齐国、宋国贵族美女为妻相提并论,可见当时鲤鱼与鲂鱼在美食中的地位。
此外,《小雅·鱼丽》有“鱼丽于罶,鰋鲤”。意思是鱼儿钻进竹笼里,那是鲇鱼和鲤鱼。《小雅·六月》是记述周宣王时期尹吉甫北伐玁狁的诗歌,尹吉甫载誉归来,宴请亲朋好友,吃的是“炰鳖脍鲤”,就是蒸鳖和鲤鱼刺身,可见鲤鱼在当时是上档次的美食。《周颂·潜》是周王以鱼献祭于宗庙的乐歌,一口气列出六种鱼,“有鳣有鲔,鲦鲿鰋鲤”,鲤鱼赫然在列。
别看现在鲤鱼普通得很,在《诗经》的时代并不是家喻户晓。许慎在《说文解字》里就把它弄错了,说:“鲤,鱣也。从鱼,里声。”鱣其实是鲟鳇鱼,与鲤鱼差十万八千里。传说中鲤鱼跃龙门后化为龙,古人对此深信不疑,《陶弘景·本草》说:“鲤最为鱼中之主,形既可爱,又能神变,乃至飞越山湖,所以琴高乘之。”唐朝段成式在《酉阳杂俎》说:“道书以鲤多为龙,故不欲食。”《正字通》说:“神农书曰:鲤为鱼王,无大小,脊旁鳞皆三十有六,鳞上有小黑点,文有赤白黄三种。”
鲤鱼是鲤形目鲤科鲤属淡水鱼类,在我国,除西北高原的少数地区外,在各水系均有分布。为什么叫鲤鱼,北宋科学家沈括在《梦溪笔谈》中说:“鲤鱼当胁一行三十六鳞,鳞有黑文如十字,故谓之鲤。文从鱼、里者,三百六十也。”他的意思是鲤鱼的侧线上有三十六片鳞,鳞上有类似十字的黑纹。三十六乘以十,就是三百六十,古时以三百六十步为一里,于是“里”字加个偏旁“鱼”,就成了“鲤”。这个说法对了一半,有一半是过度解读了。以三百六十步为一里,那是隋唐时代以后的事,在《诗经》的年代,是以三百步为一里。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只取其正确的一半将它说清楚了:“鳞有十字文理,故名鲤。”
《诗经》的年代,鲤鱼高级得很。《史记·孔子世家》记载,鲁昭公赐孔子鲤鱼,适其生子,孔子为荣君之赐,便将儿子命名鲤,字伯鱼。到了汉代,鲤鱼就被赋予传书功能,大诗人蔡邕吃过黄河鲤后,留诗曰:“客从远方来,遗我双鲤鱼。呼儿烹鲤鱼,中有尺素书。”
唐代人也很喜欢吃鲤鱼,唐诗的鲤文化相当丰富,以鲤为题的诗歌很多。王维有:“良人玉勒乘骢马,侍女金盘脍鲤鱼。”李白有诗云:“黄河三尺鲤,本在孟津居。点额不成龙,归来伴凡鱼。”岑参的《热海行送崔侍御还京》一诗写道:“侧闻阴山胡儿语,西头热海水如煮。海上众鸟不敢飞,中有鲤鱼长且肥。”李商隐的《板桥晓别》一诗则曰:“水仙欲上鲤鱼去,一夜芙蓉红泪多。”刘禹锡在《洛中送崔司业》中有:“相思望淮水,双鲤不应稀。”
宋人继承唐人的传统,继续大吃鲤鱼,这当中的粉丝还有苏轼。他刚参加工作时以“将仕郎大理寺评事签书节度判官厅公事”至凤翔,遇到年终,想回汴京和父亲、弟弟团聚而不可得,回想故乡岁暮的淳朴风俗,就写了三首诗寄给弟弟苏辙(字子由),回忆小时候在眉州的生活,以抒发思念之情,其中就有“置盘巨鲤横,发笼双兔卧”,想到小时候吃鲤鱼。在凤翔,同年进士章惇来看他,在回长安时路过渼陂,在朋友的庄园里凿冰钓了一尾红鲤鱼,派人送给苏轼。苏轼收到鱼的时候,鱼鳃用紫荇穿着,鱼儿还是活蹦乱跳的。于是他马上洗手下厨,做了一道菜请客人品尝,并且赋诗《渼陂鱼》,诗中说:“携来虽远鬣尚动,烹不待熟指先染。坐客相看为解颜,香粳饱送如填堑。”送鲤鱼来的路虽然遥远,但鱼颔旁小鳍还会动,不等煮熟,他已迫不及待地染指先尝一口了,座中客人看到他这个样子哈哈大笑,大快朵颐地如填沟堑般填饱了肚子。苏轼是真喜欢吃鲤鱼,章惇对苏轼也是真的好,可惜这对才华横溢的朋友后来因政见不同反目成仇,苏轼也因此吃尽了苦头。如何做鲤鱼,苏轼还将此写了下来,他在《煮鱼法》中说:“其法,以鲜鲫鱼或鲤治斫,冷水下,入盐如常法,以菘菜心芼之,仍入浑葱白数茎,不得搅。半熟,入生姜、萝卜汁及酒各少许,三物相等,调匀乃下。临熟,入橘皮线,乃食之。其珍食者自知,不尽谈也。”
鲤鱼的地位下降大概发生在南宋,大宋丢了半壁江山,也丢了最出名的黄河鲤鱼。与黄河鲤鱼相比,南方鲤鱼差得太多,加上当时鱼的品种更加多样,鲤鱼的缺点就显现出来了,比如多刺、有土腥味且肉质粗糙。部分地方的人们又相信鲤鱼是“发物”,这更让鲤鱼的地位一落千丈。
尽管如此,鲤鱼独特的香味也是其他鱼所不具备的,于是形成了这样的一种局面:偌大的中国,一部分地区鲤鱼无人问津,一部分地区的人们却大吃特吃。袁枚虽然是南方人,但也吃鲤鱼,《随园食单》里就有一道鲤鱼做的菜:“糟鲞,冬日用大鲤鱼,腌而干之,入酒糟,置坛中,封口。夏日食之。不可烧酒作泡。用烧酒者,不无辣味。”这道糟腌鲤鱼的诀窍是用酒糟腌,千万不能用烧酒去浸泡。《随园食单补证》载,清末时鲤鱼“一尾须直数千,民家诚未易致耳”。这说明,那个时候北方的鲤鱼并不便宜。
一九四九年,河南名菜“红烧黄河鲤鱼”上了开国第一宴的菜单。今天,鲤鱼早已跌出“四大家鱼”之列,中国人的餐桌已经丰富多彩,有了更多更好的选择,鲤鱼不再那么重要,这是好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