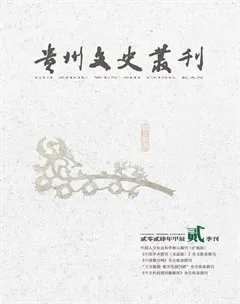论《诗经·小雅·鹤鸣》的主旨及创作手法
2024-07-14张瀚中
张瀚中
摘 要:《鹤鸣》是《诗经》中的名篇,历代诗评家对其关注评论有加,对于《鹤鸣》的主旨,迄今主要有三类观点:一是认为属于劝喻讽刺类,二是认为属于山水写景类,三是认为属于贤者处世类。造成分歧的主要原因在于,历代学者对诗歌意象和文本逻辑的理解不同。笔者查阅相关文献史料,辨析诗歌文本和各家观点,对《鹤鸣》之主旨及创作手法进行分析。
关键词:《诗经》 《鹤鸣》 主旨 辨析
中图分类号:I207.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8705(2024)02-0048-10
《鹤鸣》为《诗经·小雅·鸿雁之什》十篇之一,其诗云:
鹤鸣于九皋,声闻于野。鱼潜在渊,或在于渚。乐彼之园,爰有树檀,其下维萚。它山之石,可以为错。
鹤鸣于九皋,声闻于天。鱼在于渚,或潜在渊。乐彼之园,爰有树檀,其下维榖。它山之石,可以攻玉。1
对于《鹤鸣》一诗,历代文人学者尤其是诗评家对其关注有加,注解颇多;对其使用何种创作手法,也有较多的评论。王夫之称其“全用比体,不道破一句,三百篇中创调也”2。因此,《鹤鸣》一诗给历代读者留下了较多的解释空间。就其诗歌创作方法及诗意而言,历代的学者也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且各持己见。李樗曾言:“至于《鹤鸣》之二章十八句,皆是取兴,殊无一句推序己意,故其诗最为难晓。”3有鉴于此,本文尝试在梳理辨析历代学者观点的基础上,结合诗歌文本,试探其诗旨及创作手法。
一、《鹤鸣》诗旨众说举要
历代学者对《鹤鸣》的诗旨及创作方法的解读,归纳起来,大致可以分为三类观点。
(一)劝喻讽刺类
依据《鹤鸣》劝喻或讽刺对象的不同,这类观点又可以分为三类,即:劝喻周王说、规劝朋友说、讽刺时人说。
1.劝喻周王说。这类观点按劝喻或讽刺的内容又可分为三种:其一,劝喻周宣王求贤说。这个说法出自《毛传》《郑笺》。《毛诗序》云:“诲宣王也。”1《郑笺》更补充说明:“教宣王求贤人之未仕。”2《毛传》亦云:“举贤用滞,则可以治国。”3据此可知,《毛传》《郑笺》均认为,《鹤鸣》有劝喻周宣王求贤之意。该种观点对后世的文人学者影响较大,如宋代的学者范处义、李樗、严缉等,清代的学者陈启源、魏源等,皆支持此种说法。其二,陈善纳诲说。这类观点以宋代的朱熹为代表,他在《诗集传》中云:“此诗之作,不可知其所由,然必陈善纳诲之词也。”4朱熹认为,这首诗不知道因出于何种原因而作,但主要内容是体现“陈善纳诲”之意。朱熹进而认为,《鹤鸣》之首章就说明了“诚之不可掩”“理之无定在”“爱当知其恶”“憎当知其善”等。朱熹还引用了程子之言以解释次章末二句,指《鹤鸣》阐明君子受小人“横逆侵加”则可修省的道理5。在朱熹看来,《鹤鸣》是一首言理诗,作者的主要创作目的是想让人明白处事为人的道理,不因爱憎匿善,以提示人们强化自已的修为。朱熹的说法影响很深,不少学者均认可和采用其观点,如元代的刘瑾、朱公迁,清代的张叙等。另有一些学者虽不完全认同朱熹的观点,但他们的说诗理路与朱熹类似,大多是以自己的理解来阐说诗歌的主旨及创作手法,并将其归类为劝喻周王之作,如宋代的学者戴溪云:“虽所诲者不止一事,大要言事无隐而不彰,安于美者当知其恶,察于逆己者,恶其顺己者可也。”6戴溪认为,《鹤鸣》的确是劝喻周王之作,但劝喻的内容又不止一事,而其表现形式也算言理诗一类。用这种思路去解读《鹤鸣》的学者也不少,包括宋代的苏辙,明代的万时华,清代的张沐、傅恒等,虽然他们对《鹤鸣》在劝喻周王的具体内容方面有不同理解,但是这些学者与朱熹在说诗的理路上是极为相似的,故也可将其归为一类。其三,劝喻讽刺说。不少学者认为,这是一首意在讽刺其时之当权者进用不贤之人的诗,劝喻其不要进用不贤之人。这一观点出自祝敏彻等人的《诗经译注》,他们认为,“乐彼之园,爰有树檀,其下维萚”这三句比喻贤者当居高位,不贤者当居下位,诗人借以讽刺其时之当权者没有选用贤能7。
2.规劝朋友说。此说见清代学者杨名时的《诗经札记》,其云:“《沔水》《鹤鸣》,朋友规劝之诗。”8但历代持此类观点的学者不是很多。
3.讽刺时人说。此说出自清代学者牟庭的《诗切》,其云:“《鹤鸣》,刺时人毁誉不以实也。”9清代学者牟应震则认为,此诗的讽刺对象是当时的大家世族,其《诗问》云:“风世族择宰也。”10历代持此类观点的学者不多。
(二)山水写景类
不少学者认为,《鹤鸣》是一首描写自然风光和园林景观的诗歌,并开历代山水田园诗之先河。如果提及有贤者隐居其中,那也是言外或推测之意。此说出自陈子展的《诗经直解》:“《鹤鸣》,似是一篇《小园赋》,为后世田园山水一派诗之滥觞……诗中所有、如是而已。倘谓有贤者隐居其间,亦止是诗人言外之意,读者推衍之意。”1这种说法的影响也不小,不少学者支持此说,如褚斌杰、高玉海等。
(三)贤者处世类
这类观点按申说重点不同又可分为两种:其一,贤者隐居自乐说。这种观点认为,《鹤鸣》表达的是其时的贤者隐居起来,流连于山水之间,观鹤赏鱼,自娱自乐的生活方式。此说出自宋代王质的《诗总闻》:“泽玩鹤,水玩鱼,言贤者退处自乐也。”2其二,贤者处世之道说。这种观点认为,《鹤鸣》表达的是其时之贤者处世秉持自己品行,不肯与那些不讲道德的人与事同流合污。如清代徐璈的《诗经广诂》云:“盖极言隐处之贤者,怀道蓄德,与世推移,而未尝同流合污也。”3
以上所列,反映了《鹤鸣》作为《诗经·小雅》中的名篇,持续引起历代学者的关注;而不同时代的学者都依据自己的理解,对《鹤鸣》的诗旨及创作方法进行阐释,这也说明《鹤鸣》一诗在后世所产生的影响。
二、《鹤鸣》主旨众说辨析
笔者对历代学者的注解进行了梳理分析,结合查阅相关史料,对其观点进行辨析如下。
其一,劝喻周宣王求贤说。以《毛传》《郑笺》为代表的劝喻周宣王求贤说出现最早,学者多认为其有师承关系,故在历代学者中支持者最多,持此观点者最主要的依据在于“诲宣王”三字。但笔者查阅相关资料,《鹤鸣》是否是周宣王时期的作品,尚无确切的史料支撑,不少学者对此也提出过质疑。如清代学者姚际恒认为:“至于谓宣王之诗,未有以见其必然。”4程俊英也认为,将之作为宣王时代的诗歌不知所据。5虽然也有一些学者尝试联系周宣王时期的历史进行解释,如李樗在《毛诗李黄集解》中云:“宣王之始,固尝任贤使能矣。至期末年,浸不克终,故好贤之心少怠。”6然而,这一说法尚停留在推测层面。因此,在缺少相关史料支撑的情况下,“诲宣王”的说法仍值得商榷。
其二,陈善纳诲说。如前文所述,认同这种观点的学者为数较多,其说诗理路也基本一致,即认为《鹤鸣》是一首言理诗,意在表述事物中蕴含的道理。但这些道理是对何人而讲的,没有定论。有的学者认为是对所有人讲的,有的学者认为是对当时的周王讲的,有的学者认为是对周宣王讲的;有的学者认为只讲了一个道理,有的学者认为是讲了很多道理,但对于具体的内容,则没有列出道明。由于朱熹的观点影响较大,故先作一个梳理分析。陈启源在《毛诗稽古编》中对朱熹的观点持有异议,兹引述如下:第一,篇无统一之旨,不似古人作诗。朱熹“自立新解,分为四意而文义各不相蒙”,但“古人作诗,皆有为而发,语意定有所指”7。第二,对作诗的目的与诗歌内容的解释并不相吻合。朱熹所说的“诚不可掩”“理无定在”等,均为“平居谈理之言”,不能作为“因事纳诲之语”8。第三,对两章末二句的解释差异过大。朱熹以“憎当知其善”解释“它山之石,可以为错”,是谓“不以私怨而蔽人之贤”,又引程氏之言解释“它山之石,可以攻玉”,是谓“君子受小人横逆之加则可修省以成其德”,二者之意迥别。9陈启源的说法亦有其据,尤其“篇无统一之旨”一条,基于这种说诗理路的学者很难避免该问题,如苏辙认为,《鹤鸣》表达了“无物隐而不见”“大者之无所不容”“世未有无用之物”1等,同样如陈启源所言,是“分为四意而文义各不相蒙”,没有统一诗旨。
从相关史料中发现,不仅朱熹个人的观点不被一些后世学者所接受,陈善纳诲说的说诗理路也引起了一些学者的争议。认同这种观点的学者致力于探讨诗中蕴含的道理,原因就在于他们将《鹤鸣》之比兴手法视同《周易》之取象言理,以至于将其作为单纯的言理诗来看待。例如,朱熹引《周易·系辞上》之言,认为此诗之理“引而伸之、触类而长之、天下之理其庶几乎”2。张叙《诗贯》亦云:“此诗如《易》之取象,含蓄无尽,可以类万物之情,可以通天下之理。”3万时华《诗经偶笺》、傅恒《御纂诗义折中》、邹忠胤《诗传阐》等也有类似论述,皆以《易》之取象言理来类比《鹤鸣》之比兴,认为诗歌意象隐喻了某些事理。诚然,《周易》的取象言理与《诗经》的比兴关系密切,正如清代的章学诚所言:“《易》象虽包《六艺》,与《诗》之比兴,尤为表里。”4鲁洪生说:“周人的思维方式尚处在类比联想思维阶段。”5《周易》的取象言理与《诗经》的比兴都是这种类比联想思维下的产物,但它们之间仍有根本差异。钱锺书在《管锥篇》中也提出:“是故《易》之象,义理寄宿之蘧庐也,乐饵以止过客之旅亭也;《诗》之喻,文情归宿之菟裘也,哭斯歌斯、聚骨肉之家室也。”6钱锺书的研究结论是,《周易》通过卦象、卦爻辞等来预测和解释人生、社会,乃至宇宙的变化,一般不反映作者情感,而《诗经》的比兴则寄寓着作者的主观情志,此即《毛诗序》所谓“诗者,志之所之也”7。因此,将《诗经》的比兴视同《周易》的取象言理,以《鹤鸣》为言理诗是否合理,在学者中引起的争议也是比较大的。这也是姚际恒对朱熹观点持不同看法的主要原因,他说:“解此篇最纰缪者,莫过《集传》……以《诗》为言理之书,切合《大》《中》《论语》,立论腐气不堪;此说《诗》之魔也。”8综上所述,通过这种说诗思路来解读诗歌,会产生两个问题:一是学者们将其研究重心全然放在了探寻诗歌可能隐喻的事理上,对诗人自己想表达的情志有所忽略。此即钱锺书所说的“忘言觅词外之意”9。二是不同时期的学者依据自己的理解,通过各自的联想,推测诗歌意象的象征意义,分析诗中可能隐喻的道理,而得出的结论五花八门,难有定论。正如糜文开评价朱熹的观点道:“今释为四个隐喻的比,只是隐约言之的象征手法,让人觉得玄妙而难测,而说诗者也就会流于瞎子摸象,各有所得,各是其是的道路上去。”10从以上观点来看,这些学者认为,这类观点会造成学者在研究诗歌的创作方法上出现许多争议,进而从自己的角度去理解其言外之意,过度地表达说诗者之意,而非探讨作诗者之意。因此,陈善纳诲说仍值得商榷。
其三,劝喻讽刺说。祝敏彻的观点与劝喻宣王求贤说并没有根本冲突,只是说诗的角度不同。前者是反向论述,认为诗人意在讽刺当权者进用不贤之人,并以此提醒君王;后者则从正向论述,强调诗人是在劝喻君王求贤,希望君王广为求贤。细辨之,祝敏彻先生是以“乐彼”三句为《鹤鸣》的落脚点,认为诗人通过这三句诗传达了贤者当居高位,不贤者不应上位的主张,借此讽刺其时之当权者进用不贤之人的事。以此推之,《鹤鸣》一诗至“乐彼”三句就已诗意完整,“它山”二句则显得多馀。但是,末二句不似前七句不露己意,它更为直接地表达了作者希望君王应求贤的主张,是全诗的“诗眼”,起到了卒章显志的作用,不宜被忽略。因此,相对而言,从正面的角度去论述,应当更能切合作者的意图。劝喻讽刺说未必有误,只是理解的方式不同而已。
其四,规劝朋友说。由于杨名时并未详细解说,只能推测其意。观《四库全书总目》,《诗经提要录》之提要称“名时则光地之门人”1,《诗经札记》之提要云:“是编乃其读《诗》所记,大抵以李光地《诗所》为宗。”2据此可知,杨名时是李光地的弟子,其《诗经札记》受李光地《诗所》影响很大。李光地认为,《鹤鸣》表达了“中孚之必应,同心之必合,不待求之而自至”“善人者,不善人之师,不善人者,善人之资,不待远之而自化”等事理,此皆“修身进德之要,而形于论交取友、待人接物之间者”。3杨名时受此影响,故以《鹤鸣》为规劝朋友之诗,规劝内容大抵与李光地所说的“修身进德之要”相似。然而,李光地的说诗思路也是在认为其为言理诗的基础上所得。上文对其争议处已有探讨,兹不赘述。
其五,讽刺时人说。牟庭《诗切·诗小序》有“《鹤鸣》,刺时人毁誉不以实也”一语,但正文佚失《小雅》三十三篇,已无法得知其结论是如何得出。牟应震则认为,鹤、鱼为园林蓄养之物,檀喻园林主人,萚喻其僚属之不材,诗人借以讽刺园林主人(世家大族)不善于用人。4然而,这个说法还是存在一点瑕疵,即牟应震将“乐”解释为“乐主人乐”5,既然僚属不材,主人不善用人,则主人何乐之有?诗意自相矛盾。
其六,山水写景类观点。这类观点主要反映了古代学者与部分近现代学者的分歧。大部分古代学者,如毛公、郑玄、朱熹、何楷、姚际恒等,几乎都认为《鹤鸣》所用手法是“比”或“兴”6,唯清代学者方玉润在其《诗经原始》中点明此诗手法是“赋”,并以“实赋其景”7解释此诗。不过,方玉润并未跳出古代学者说法,基本上认同了郑玄的劝喻宣王求贤说。而当代的一些学者则在“实赋其景”的基础上突破了传统的论诗观点,如陈子展就将《鹤鸣》看作描写园林风景之诗;高玉海还以后世的山水诗与《鹤鸣》作比较,通过挖掘其相似性,认为《鹤鸣》堪称中国山水诗之鼻祖。8
这种观点自有其合理性,为《鹤鸣》一诗的解读与研究提供了新的说诗理路。不过从分析可知,《鹤鸣》的意象具有隐喻意义,诗歌使用的手法是“比”,并不一定是“赋”。原因有二。首先,从背景上看,正如鲁洪生所说:“周人的思维方式尚处在类比联想思维阶段。”9在这种类比联想思维的影响下,“两事物或心与物之间只要存在一丝一毫的相似,不论是‘同形同构,还是‘异质同构……中国古人都可以求同联想,同类相推”10。所以,产生于这一时代的《鹤鸣》不一定是纯粹客观的景物描写。其次,从内容上看,“它山之石,可以为错(攻玉)”这两句不似单纯的景物描写,更像是诗人在陈述其看法,以卒章显志。卒章之志的呈现离不开层层铺垫。因此,诗歌前七句未必只是写景,而很可能有其他意义。
其七,贤者隐居自乐说。王质的《诗总闻》将《鹤鸣》看作描述贤者隐居生活的诗歌。他认为,贤者之所以能“退处自乐”,原因就在于诗中的“檀”“萚”“榖”等物都能成为其生活物资。然而他在解释“榖”时却说:“其穀菜亦可以为茹。”1这是将“榖”误作“穀”。陆德明《音义》曰:“榖,工木反。《说文》云:‘楮也。从木,榖声。非从禾也。”2榖是木名,而穀菜可食,二者不可混同。若依王质“取用何阙?所以为乐也”3的思路,诗中的贤者却恰恰缺乏食物,实难自圆其说。
其八,贤者处世之道说。清代学者徐璈、龚橙都认为此诗反映了隐居的贤者重视德行修为,但他们的论证却不免有些以偏概全。徐璈引《易林》“鹤鸣九皋,避世隐居,抱道守贞,意不相随”以及《荀子》“君子隐而显,微而明,辞让而胜”等论述证明其观点4,但《易林》和《荀子》只对《鹤鸣》首二句进行了解读,并未对全诗作此判断,徐璈却着眼于此,将贤者隐居修身之意扩展至全诗,以致对后文的解读稍显牵强。龚橙《诗本谊》亦引《易林》此语5,同样只着眼于“鹤鸣”二句,仍值得商榷。
辨析上述观点可知,产生分歧的关键在于不同学者对诗歌意象以及诗歌逻辑的理解有所不同;每位学者的看法都各有其理,但难免存在一定的相互矛盾之处,故而引发争议。这也充分说明了《鹤鸣》一诗的主旨“最为难晓”的特点。
三、《鹤鸣》的主旨探析
要探寻《鹤鸣》一诗的主旨,在缺少相关背景史料的情况下,需要从理解诗歌的意象和文本的逻辑着手。《毛传》《郑笺》对诗歌意象的解读大多合理有据,故下面主要结合其中的阐释来探讨《鹤鸣》的诗旨。
(一)“鹤鸣于九皋,声闻于野”
《毛传》云:“言身隐而名著也。”6郑玄解释说:“皋,泽中水溢出所为坎。自外数至九,喻深远也。鹤在中鸣焉,而野闻其鸣声。兴者,喻贤者虽隐居,人咸知之。”7他以“鹤”喻贤人,以“皋”喻贤人隐居之处,“声闻于野”即声名显扬于外。这一说法相对可靠,有两方面可证。
其一,早期的说《诗》者观点基本一致。清代的王先谦在其《诗三家义集疏》中写道:
《后汉·杨震传》“野无《鹤鸣》之士”,《杨赐传》“速征《鹤鸣》之士”,皆指隐士言,二杨皆鲁说。《易林·师之艮》:“鹤鸣九皋,避世隐居。抱道守贞,竟不随时。”《无妄之解》:“鹤鸣九皋,处子失时。”处子即处士,诗言贤者隐居,此齐说。韩诗盖同。8
鲁、齐、韩三家《诗》基本无异义,均认为鹤指贤人隐士。此外,早在四家《诗》之前,荀子就对《鹤鸣》首二句做过类似解读,见《荀子·儒效篇》:“故君子务修其内而让之于外,务积德于身而处之以遵道,如是,则贵名起如日月,天下应之如雷霆。故曰:君子隐而显,微而明,辞让而胜。诗曰:‘鹤鸣于九皋,声闻于天。此之谓也。”1其中,“隐而显,微而明”即《毛传》所谓“身隐而名著”之意。据此可知,荀子同样将鹤看作隐居修身的君子。宋人严粲《诗缉》称毛、郑“必有师承”2,陈启源谓之“说必有本”3,可能就来源于荀子。
其二,‘鹤”的意象在其他先秦文献中也有类似贤人隐士的譬喻。《周易·中孚·九二》云:“鸣鹤在阴,其子和之。我有好爵,吾与尔靡之。”4《周易》多以阳爻居阴位喻人谦退幽居,又以爻居中位喻人坚守正道。九二爻兼具两者,故《周易》有时将处于九二爻情境的人称为“幽人”,即隐居的贤者,如《履·九二》:“履道坦坦,幽人贞吉。”5《归妹·九二》:“眇能视,利幽人之贞。”6《中孚·九二》的“鸣鹤”实为“幽人”之喻,正如孔颖达所说:“处于幽昧而行不失信,则声闻于外,为同类之所应焉。如鹤之鸣于幽远,则为其子所和。”7由此看来,在《周易》爻辞中,“鹤”就曾被用来比喻贤人隐士。因此,《毛传》《郑笺》的说法是有理有据的。
(二)“鱼潜在渊,或在于渚”
《毛传》云:“良鱼在渊,小鱼在渚。”8郑玄则不区分“良鱼”“小鱼”,他说:“此言鱼之性,寒则逃于渊,温则见于渚,喻贤者世乱则隐,治平则出,在时君也。”9二者虽有分歧,但并非根本冲突。支持郑玄观点的学者偏多,如严粲、李樗、何楷等,均认同以鱼的生活环境来比喻贤人进退出处,但《毛传》之意亦通。孔颖达基于《毛传》的解释,认为能够隐遁而处于深渊的“良鱼”喻贤人君子,不能隐遁的“小鱼”喻不贤之人,君王应求得“良鱼”置于朝廷。10不过,清代学者胡承珙在其《毛诗后笺》中辩驳道:“《经》言‘或在者,自是立贤无方之意,故以‘良鱼‘小鱼释之,谓有当求之深者,有当求之浅者。”11按胡氏之意,“良鱼”“小鱼”皆喻贤人,贤人的才能、境况各不相同,君主应不拘一格,广纳贤才。
至于以“鱼”喻贤者,《诗经》中用例不少,就像范处义所说:“诗人尝以嘉鱼喻贤者,以伐檀喻君子,则毛、郑之说不为无据。”12例如,《小雅·南有嘉鱼》:“南有嘉鱼,烝然罩罩。君子有酒,嘉宾式燕以乐。”13此诗以“嘉鱼”之乐兴嘉宾之乐,嘉宾即宴请的贤者,郑玄亦云:“乐得贤者,与共立于朝,相燕乐也。”14又如《小雅·正月》:“鱼在于沼,亦匪克乐。潜虽伏矣,亦孔之炤。忧心惨惨,念国之为虐。”15诗人把鱼比作忧国忧民的贤者。所以,郑玄等人以“鱼”喻贤者的观点确实合理有据。
(三)“乐彼之园,爰有树檀,其下维萚”
《毛传》云:“何乐于彼园之观乎?萚,落也。尚有树檀而下其萚。”1《郑笺》云:“此犹朝廷之尚贤者而下小人。”2即以园喻朝廷,檀树喻贤者,落叶喻小人。檀树喻贤者,后世学者基本无争议。檀木质地坚韧,可以作为造车造船的材料。诗人常因檀为有用之材,将之比作贤人,如《魏风·伐檀》:“坎坎伐檀兮,寘之河之干兮,河水清且涟猗。”3《毛传》云:“伐檀以俟世用,若俟河水清且涟。”4即认为此诗以檀喻贤人君子,谓其不得进仕。
以上三句诗的最大争议在于学者们对“萚”和次章的“榖”理解不同。由于诗歌的重章结构,很多学者对“萚”的理解受到“榖”的影响,故先考察“榖”字。《毛传》训“榖”为“恶木”5,因“恶木”之称,后人多以榖喻小人。《诗经》中被《毛传》直接称“恶木”的,除榖木外,还有樗树。樗树往往被看作无用之材,比如在《庄子·逍遥游》中,惠子评价樗树道:“其大本拥肿而不中绳墨,其小枝卷曲而不中规矩,立之涂,匠者不顾。”6因此,《毛传》可能认为榖也是无用之材,故称其为“恶木”,而有关榖的主要争议就在于此。陆机《毛诗草木鸟兽虫鱼疏》云:“今江南人绩其皮以为布,又捣以为纸,谓之‘榖皮纸,长数丈……其叶初生,可以为茹。”7一些学者据此以为榖木并非无用,故不将其看作小人,如范处义说:“贤之大者,则能任重而致远,如檀有坚美之质,可为轮辐之用。而其小者,则滞于下,如萚之秽杂,亦可以粪其本;如榖之恶木,亦可以绩其皮。”8然而,胡承珙却反驳道:“不知榖之利用乃后世所为,作诗者及毛公时固无所谓‘榖皮纸也。”9胡氏之说颇有依据,后来有学者也多认为植物纤维纸的使用在西汉时才出现。由于年代久远,榖在《诗经》时代有何作用已难知晓,但仍可以通过榖木的一些特点来推测它在诗中的指向。
《说文》云:“楮,榖也,从木,者声。”10郭璞注《山海经》“其状如榖”云:“榖,楮也,皮作纸。璨曰:‘榖,亦名构。名榖者,以其实如榖也。”11楮、构同称为榖,或如清代的王引之所言:“榖、构古同声,故榖一名构。”12而王夫之却认为,楮与构不能混为一谈,他说:“其一乔干疏理,结实似杨梅者,皮粗厚不堪作纸。皮间有汁如漆而白,可用涂金者,构也……其一树小枝弱,条仅如指大,皮可为纸,亦不结实,此则楮也,榖也。”13据《中国植物志》,我国确实有两种构树,一种是高大的乔木,另一种称“楮”,也叫小构树,属于灌木一类14,这与王夫之的描述基本一致。王夫之又云:“构树高数丈,不能托生于檀荫之下。楮小而卑,乔林之下多有之。古无楮纸,而此木叶粗枝细,同于灌莽,故毛公谓之恶木。”15以此来看,王说较为合理,《鹤鸣》中的“榖”应指低矮的小构树,否则不能生长在檀树之下。这种植物之所以被《毛传》称为“恶木”,一方面是因为它叶粗枝细,不似檀木枝干强韧能堪大用;另一方面还在于它具有杂草的性质。《酉阳杂俎》云:“构,谷田久废必生构。”1在周朝时期,《诗经》中就有许多农事诗涉及除杂草之事,杂草也自然成为了人们眼中的恶草,如俗称“狗尾草”的莠,《小雅·正月》:“好言自口,莠言自口。”2《毛传》训“莠”为“丑”3,明代学者季本解释说:“莠,恶也。以莠害嘉谷,故借以为恶。”4因此,《毛传》称“榖”为“恶木”,后人多以之喻小人,这种说法确实较为符合《诗经》那个年代的实际情况。
在赞成《毛传》对“榖”训释的基础上,有少部分学者将首章的“萚”也当作树木而非落叶,如季本说:“萚,木之先落叶者,当指恶木言之,方与下章‘榖字相应。”5王引之甚至认为“‘萚疑当读为‘檡”6,檡即一种树木。诚然,重章结构的诗歌每章更换的字词有一定相似性,但并非所有诗都这么严格。例如,《南有嘉鱼》前二章以“嘉鱼”起兴,第三章以“樛木”起兴,第四章又以“鵻”起兴,三者并非同类物种。大概是一些诗歌产生时间较早,诗人在创作语言使用上还未定型之故,所以这里没必要将“萚”说成树木。
承认“萚”指落叶的学者,又对落叶有不同理解,其一,以郑玄为代表,认为落叶喻小人;其二,以范处义为代表,以落叶喻“贤之小者”7。这两种观点自有其理,却仍值得商榷。一方面,既以檀喻贤者,却又以檀的落叶喻小人或“贤之小者”,有些自相矛盾。另一方面,诗歌前四句谓野有遗贤,“乐彼”三句讲诗人因朝廷中贤人在上而小人在下,或因贤有大小,各堪其用的情况而感到满意,最后二句却又劝在位者求贤。这在逻辑上存在瑕疵,即诗人在朝廷用人没有问题的情况下,因何而劝喻在位者求贤?明代何楷的《诗经世本古义》则提供了另一种思路,他说:“檀之下所见者惟萚,则凋零之甚,而檀亦已槁矣,喻贤者衰谢也。”8何楷认为檀有落叶意味着贤人衰老,这在意象喻义和文本逻辑上都更合理。依何楷之意,“爰有树檀”与“其下维萚(榖)”之间存在转折关系,诗人力图说明虽有贤人在朝,但他们日渐衰老,其下还有小人蠢蠢欲动的情况。如此,全诗内容更连贯,逻辑更清晰,即先讲朝廷之外有遗贤,再说朝廷之内有隐患,强调了求贤的可行性和必要性,这样一来,诗歌末二句劝在位者求贤才显得更为顺理成章。
(四)“它山之石,可以为错”
《毛传》云:“错,石也,可以琢玉。举贤用滞,则可以治国。”9《毛传》认为,诗人以石能琢玉比喻贤者能辅助君王治理国家。这一解读不无道理,《诗经》就常用琢玉来比喻王公贵族要修身进德。例如,《卫风·淇奥》是一首赞美卫武公的诗,诗歌首章借琢磨玉石来形容卫武公的学问、德行不断精进,其云:“有匪君子,如切如磋,如琢如磨。”10又如《大雅·抑》,这是一首劝喻周王之诗,其云:“白圭之玷,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为也。”11“玷”即玉上的斑点、缺损,磨玉意味着改正过失。这是劝周王要修身进德,进用贤者。《鹤鸣》也是同理,以石喻贤者,石能琢玉则喻贤者能帮助君王更好地治理国家。
末二句的争议主要在“它山”二字,郑玄以“它山”喻异国1,而《毛传》并无此意。联系前文,诗歌并未提及本国与异国的问题,只是在说朝廷内外的状况,如果以求得他国贤者作结,则稍显突兀。因此,“它山”应与前文的“皋”“渊”“渚”一样,喻指贤人隐居之处。综上所述,全诗之意已基本明朗,诗人通过讽喻手法,向在位者说明了朝廷外有遗贤、内有隐患的情况下,急切希望君王能求得在野之遗贤,故结尾借“它山之石”申说求贤之用。至于不直言求贤而借诸多意象言之,是典型的“主文谲谏”之法,以达到“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以戒”2的效果。
四、结语
综上所述,《鹤鸣》的主旨应是表达劝喻周王求贤之意。《毛传》对诗中意象的解读基本合理有据。至于《毛诗序》“诲宣王”一说,因史料不足,尚停留在推测层面,还有待商榷。在文本逻辑方面,何楷的解释相较郑玄等人更能使文意连贯,逻辑合理。以朱熹为代表的陈善纳诲说,虽见解独到,各有其理,但他们的说诗理路将《诗经》比兴视同《周易》取象言理,从而对诗人的主观情志有所忽略,出现了不少争议,也还有待深入的研究;以部分现代学者为代表的山水写景类观点,为探讨《鹤鸣》的诗旨提供了新思路,可备作一说;其馀观点各有瑕疵,且争议颇多,还需进一步探讨。
总之,关于《鹤鸣》的诗旨众说纷纭,原因就在于对诗歌意象和文本逻辑的理解不同。孟子曰:“故说《诗》者,不以文害辞,不以辞害志,以意逆志,是为得之。”3要探究诗歌主旨,还需要客观审视文本,以文本之意及其使用的创作手法来一一分析。
On the Theme and Creative Techniques of The Book of Songs, Xiao Ya,He Ming
Abstract:He ming is a famous poem in the Book of Songs, which has received much attention and comment from poetic critics throughout the past ages. There are three main types of views on the main theme of He ming: admonishing or satire; landscape writing; the virtuous people's approach to the world. The main reason for this divergence lies in the different understandings of the imagery and the logic of the poem by scholars over the ages. The author consults the relevant literature and historical materials, whoanalyses the text of the poem and the views of different scholars, and also analyses the main idea and creative techniques of He ming.
Key words:Book of Songs;He Ming;theme;differentiate and analyz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