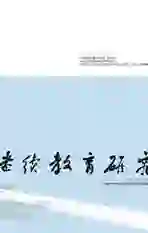数字劳动教育的挑战与治理
2024-07-12李双龙刘守翠
摘要:数字劳动教育是新时代劳动教育在数字空间的拓展,是实现以劳动育人、技术强人为目标的劳动教育新样态。研究发现,数字劳动是资本社会数字经济发展的产物,运用马克思劳动异化理论作为数字劳动异化的重要理论来源,分析数字劳动教育面临的挑战,旨在把握数字技术赋能劳动教育的时代主旋律,促进劳动教育的创新变革。借助数字时代的技术优势,全面挖掘劳动教育的价值意蕴,充分发挥“以人为本”的数字劳动育人目标,注重育人过程中思想性、实践性、社会性的智慧生成,合理把握数字技术与劳动教育学科的高度融合。
关键词:数字劳动;劳动异化;数字劳动教育;数字延伸;智慧生成
中图分类号:G40-01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9-4156(2024)07-0083-07
2022年4月,教育部颁布了《义务教育劳动课程标准(2022年版)》,强调劳动教育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制度的重要内容,是全面发展教育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1]。这对确保我国教育的社会主义方向、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培养和造就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和接班人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2023年2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了《数字中国建设整体布局规划》,该规划提出建设数字中国是数字时代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引擎,是构筑国家竞争新优势的有力支撑。数字技术的创新与发展,不仅创造了巨大的经济价值,而且创建了个体间进行生产、分配、交换、消费的数字空间,人类的劳动环境从传统现实空间转换到现实空间与虚拟空间结合。现实空间中的劳动范畴持续向数字空间转移和延伸,使得劳动在形式、内容、性质上发生巨大变化,拓展劳动的图谱。“在我们这个时代,每一种事物好像都包含有自己的反面”[2]776。在数字技术带来巨大福祉的同时,也应合理看待其带来的挑战。一方面,数字技术赋能劳动教育形式多元、方法多样和空间泛化;另一方面,数字技术发展伴随的劳动异化阻碍劳动教育的发展。基于此,探索数字技术与劳动教育的最佳结合点,有益于发挥数字技术在劳动教育中积极作用的最大化。
" 一、数字劳动的概念及异化
(一)数字劳动的概念
2000年,意大利学者那不勒斯大学蒂齐亚纳·泰拉诺瓦在《免费劳动:为数字经济生产文化》一文中正式提出“数字劳动”概念,文章将“数字劳动”囊括在“免费劳动”的概念中进行初步探索。综合来看,泰拉诺瓦认为,数字劳动是用户在互联网中建立Web站点、修改软件包、阅读并参与邮件列表等活动,它们是渗透在社会诸多领域的免费劳动,这些活动既是自愿的、享受的、无偿的,也是资本剥削的对象[3]。加拿大传播政治经济学家达立斯·斯迈兹(Dallas Smythe)在《传播: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盲点》中阐释了受众商品论,具体而言,大众传播售卖受众,社交媒体售卖“用户信息”,广告商购买“观看时间”,如果节目观看时间为“必要劳动时间”,广告观看则为“剩余时间”[4]。也就是说,媒体通过集合、整理“受众”注意及闲暇,售卖给广告商,实现资本积累。随着计算机、互联网快速发展,福克斯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为基础,分析全球价值链生产方式下各种不同形式的数字劳动国际分工,提出人类的劳动发生变化,完整地呈现了数字劳动的剥削。
随着数字技术渗透到人类社会生活,数字劳动逐渐被国内学者重视,周延云和闫秀荣从劳动和经济的关系,阐释了数字劳动的含义及数字劳动如何创造价值[5]。谢芳芳和燕连福梳理传播政治经济学的受众劳动、自治主义的非物质劳动、传统马克思主义的物质劳动与数字劳动关系,分析数字劳动的内涵及性质[6]。黄再胜基于后结构主义者的文化研究视角、批判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视角、技术决定论的研究视角,认为数字劳动是在网络数字平台运营中鲜被关注却是互联网企业资本增殖不可或缺的各种无偿或低酬劳动[7]。李弦认为,数字劳动是数字劳动者在雇佣或者非雇佣的关系中,通过数字平台所进行的各种有酬或者无酬的“生产性”劳动;从狭义角度来看,数字劳动就是指互联网用户在非雇佣关系中,通过数字平台所进行的各种无酬的“生产性”劳动[8]。
2008年金融危机后,西方学界利用马克思主义理论阐释和发展受众商品论,研究视角从传播学的受众商品转化到数字劳动马克思主义理论批判[9],劳动的范围扩大到整个人类社会。劳动是人类在客观存在的现实空间内进行物质交换过程,包括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三要素”。数字技术形式多元、时间超前、空间泛化的时代特性,为劳动的发展带来前所未有的条件,依据劳动的“三要素”对数字劳动进行分析,辨别传统劳动与数字劳动的关联及差异,从而对数字劳动有清晰的定位。就劳动者来看,根据作用目的的不同,数字劳动的主体分为前台产出数据的一般数字劳动者和后台集合数据的专业数字劳动者。一般数字劳动者在使用数字设备时,通过浏览、点击、消耗等操作,生产了大量的数据信息,互联网专业劳动者将产出的数据鉴别、收集、加工后售卖给广告公司获得收益。个体在网络平台上消耗时间产出的无报酬数据,属于无偿的数字劳动。基于上述,数字劳动没有改变劳动主体,依然是一种有目的地改造对象的活动。在数字技术赋能劳动的过程中,劳动资料由现实空间基于现实存在的物和物的综合体发展到虚拟空间基于数字技术的物和物的综合体,劳动资料变革至新的形式。例如,外卖员的劳动依赖数字平台获取的用户信息,作为商户及客户的派送桥梁。数字技术并没有直接改变外卖员的劳动活动或劳动对象的形态,但是内在地变革了劳动过程。在外卖员送客户所需商品时,实际运输的是外卖员作为劳动力的价值创造,但劳动过程是基于技术平台的支持,不能因劳动样态不变,就排除其为数字劳动的范畴。再如,商家出售商品,消费者购买。劳动形式不同,所属概念不同。商家在现实环境中售卖商品,属于普通劳动。借助数字空间,在网络平台推销商品,吸引消费者注意,然后出售给终端消费者,这属于数字劳动,也称之为有偿的数字劳动。概言之,数字劳动相对于传统劳动,关键特征是劳动过程中运用数字化的劳动资料。劳动对象是没有加工的自然环境中的物质和经过加工的原材料,是劳动得以开展的物质基础和客观条件。在数字劳动中,劳动资料发生变革,劳动对象未必是自然存在的有形物质,也包含新的劳动对象“数据”——无形物质。
就数字劳动外在表现而言,广义的数字劳动是伴随社会发展规律,劳动者将数字技术作为劳动资料进行劳动的过程。狭义的数字劳动是劳动者遵循经济发展规律,以数字技术为劳动工具,以虚拟网络空间为生产领域,以个体认知、情感、能力等内在品质信息为劳动对象,生产直接作用于劳动者的数据商品。就数字劳动资金流转方向而言,一般互联网用户在数字平台输出时间、信息等属于无偿数字劳动,无资本获得但享受数据反馈的便捷与舒适。专业互联网劳动者将一般互联网用户所输出的信息整合,用以售卖,获得资金。从数字劳动剥削与被剥削而言,一般互联网用户属于被剥削者,专业互联网劳动者与市场管理者属于剥削者。
(二)数字劳动的异化
数字劳动作为数字时代新兴的劳动形式,劳动形态发生变革,生产劳动的方式更加先进。虽然数字技术的应用缩短必要劳动时间,但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下,数字劳动仍然是资本获取高额利润的工具,劳动异化依然存在,冲击劳动者的主体地位,加大对劳动者的剥削。
1.数字劳动的劳动主体异化。人之所以能成为人,就是因为人具有意识。在数字空间内,科技公司设计多样的数字产品吸引客户,个体发挥创造性的创造能力被科技公司设计的多样数字产品替代。个体的思维逻辑形成单向的“给与性”,加大了人的机械学习。同样,广告商利用智能个性推荐系统将“取悦”个人的信息进行推荐,个体认为所看到的即真理,从而降低了自己的判断能力与思考能力。弗洛伊德认为,在人的无意识领域中,存在大量的追求快乐和避免痛苦的本能倾向。人的本能更倾向于使自己愉悦的信息。当个体处于身心放空的无意识领域时,在人的本能的倾向下,这时代表不合理的价值观念、劳动认知悄悄潜入我们的大脑中,例如,冠以“爱情”的文化符号、“身份”的名牌效应以及表面的“虚荣满足”。促进了资本滋生,使社会层面普遍存在劳动价值观歪曲,追求财富至上,乐于享受,压抑劳动。智能化的推荐方式只将一部分具有个体倾向的信息进行推荐,导致个体无法在这部分的信息中形成正确的劳动价值观以及行为取向。
2.数字劳动的劳动产品异化。这不仅是对马克思异化劳动的确证,也是对其进行一定程度的延伸,表现对数字文化的批判。个体消耗自身时间创造的源于自身的数据,不属于个体自身,不具有数据的商品权与决定权。简而言之,个体付出的价值并没有控制权,由市场对用户数据整合为商品进行销售,商品作用于哪一方面、哪一产业都由市场与资本决定,而不是由数据产出者决定。一般互联网劳动者属于劳动资料产出者,劳动资料被市场占有,劳动者在终端消耗的劳动价值越多,所受的剥削程度就越强,自身的隐秘性越低,个体就越贫乏。
3.数字劳动的社会关系异化。在数字时代,个体交往环境由“面对面交流”的现实环境转向以网络、数据为中介的互联网虚拟环境,数字技术在提供交往便捷、迅速、远程等前提下,加剧了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异化。传统的人与人交流以情感为导向的交往模式发展为以数字技能为导向。个体的交往方式呈现多样化、智能化、虚拟化,个体交往期间缺少真情流动,导致个体社会性降低、亲密关系弱化、安全感匮乏,人的本质意义降低。
二、劳动教育的数字延伸
劳动作为人的本质特征,必然需要由物理空间向数字空间扩展。人在数字空间中描绘和构建的个体特征和生产关系,呈现了数字劳动的价值,而数字空间中的劳动者对个体本质的保护及劳动价值的维护,都依赖于数字劳动教育的内在价值。
(一)从“劳动-劳动教育”到“数字劳动-数字劳动教育”
发挥教育的主体性,促进个体全面发展,就需要在劳动教育的体系中确立以完善个体本质特征为基本原则,劳动及劳动教育都是其内在价值的延伸,而且劳动是完善个体本质发展的核心。依照劳动教育的本质特征,劳动既是为何实施劳动教育也是如何进行劳动教育的关键因素。劳动不仅是维持人类生存和发展唯一手段,还是劳动教育的目的,这符合我国依靠劳动、崇尚劳动、辛勤劳动、诚实劳动的历史价值。一方面,劳动既是历史发展的重要因素,也是教育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人类历史的起始和发展都源于劳动;另一方面,教育在劳动的过程中通过分析、改善、促进来解决劳动问题。提升以劳树德、以劳增智、以劳强体、以劳育时代新人的综合育人价值,明确劳动的方向。
互联网、人工智能、大数据、区块链等数字技术的融通与发展,促使“劳动-劳动教育”在数字空间中扩展形成了“数字劳动-数字劳动教育”,相比劳动及劳动教育,数字劳动和数字劳动教育的概念外延更小,而且被劳动和劳动教育概念包含,因此数字劳动和数字劳动教育就是劳动和劳动教育的下属概念。“劳动-劳动教育”的逻辑关系可以演绎至“数字劳动-数字劳动教育”。一方面通过数字劳动来实现数字劳动教育的落实;另一方面,通过数字劳动教育来治理数字劳动的异化。纵观数字劳动教育的研究现状可知,数字劳动教育不是数字劳动在教育中的映射,它拥有自己的独特性,进而成为数字劳动异化的治理途径[10]。就数字劳动教育过程而言,Rasskazovao和Alexandrovi认为,传统劳动教育已不适于现代社会发展,劳动教育体系应符合时代需求。数字劳动教育将以现代数字技术为基础,教育过程将通过使用全球教育平台来实施,为学生提供全球互动的机会以及先进的知识和经验[11]。福克斯认为,人的想象力培育及自动化教学将成为未来数字劳动教育的重要特征[12]。巴拉巴诺娃等人从数字技术带来的风险来研究数字劳动教育的治理[13]。
总体上,劳动和劳动教育都归至满足个体美好生活的需要。人作为社会的主体,应该以满足个体需求为核心目标,劳动-劳动教育既是满足人需求的内容,也是满足人需求的方法。不断地追求更高品质的生活是人的自然本性,人需求的永不满足和基本需要的不断提升形成了劳动向前发展的不竭动力,也是劳动向数字空间扩展的根本原因。如果劳动教育没有适应时代的发展就进行数字化转型,那么个体在数字空间的主体地位与生活需求就得不到满足。数字劳动和数字劳动教育共同建立在数字技术基础上,让创造更加美好的生活成为数字劳动教育存在的最终意义。
(二)数字劳动促进劳动教育的必要性
如果说数字技术的更新迭代是劳动教育的外在推动力,那么其内在动因则在于数字劳动教育是劳动教育时代发展的诉求。数字劳动教育的高质量发展在时代性、公平性、高效性、个性化、双互性等方面有着更高的要求,而数字技术能够从多方面赋能劳动教育,从而助力劳动教育实现高质量发展。
数字劳动教育具有鲜明的时代性。人类经历了从农业社会到工业社会、信息社会的时代变迁,即将步入以数字技术为主导的数字时代。劳动教育也从农业社会的耕读结合到工业社会、信息社会的教劳结合。马克思在工业社会的生产方式造就片面的人的背景下,提出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是造就全面发展的人的唯一方法。步入数字时代,劳动教育也以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为目标,但其内容、形式、结构已产生变革。不仅注重单个人的全面发展,知识及数据这一系列的资源已成为全体人民的普遍利益,获取的知识与资源的途径多样化,而且更加注重劳动人民的普遍发展。
相对于传统的劳动教育,数字劳动教育最具优势的价值是为每个学生提供更加公平的学习内容、学习机会、学习条件。我国地域广阔,不同地区注重的劳动文化有差异,不同区域的学校基于地方劳动文化特色,注重的劳动教育内容及方式有差异。数字劳动通过新兴的数字技术打造连接、共享和智能的数字学习场域,个体都具有使用以数字技术搭建的数字空间的知识及资源。在数字赋能下促进信息实施交换,集成真实世界和虚拟世界的信息,形成适需服务的学习支持体系,从而缩小不同地区、不同学校之间在办学条件和教学质量上的差距。
数字劳动丰富社会交往的方式。以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与物联网等为代表的新型数字技术开启了万物互通互联的新时代,深刻变革人类生活的方式,突破人类劳动的边界;数字劳动正是基于高新数字技术的快速发展与融合,重新建构了层次交叉分明、结构合理清晰、复杂多维空间的劳动形态。在技术围绕的数字空间内,劳动主体、劳动资料、劳动对象互联互通,通过新兴通信技术升级,实现各地方劳动文化的互融互合、共融共享的新样态。目前,数字技术的发展速度与日俱增,在前沿技术创新、教育强国建设、相关人才的培养和流动等方面,数字劳动要适应时代需求,与时俱进。
数字劳动教育的个性化特点,可以满足不同学生的发展需要。数字劳动通过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技术设计算法程序,详细分析个体在技术运用和信息处理方面的能力,精准掌握每个个体的学习情况,定位目标。依据不同的认知水平、学习方式、兴趣爱好等有针对性地设计数字劳动学习过程。基于此,对不同学生对数字劳动已有的认知、信息技术运用的能力、学习关注度等进行详细的数据分析,跟踪学习过程,对学生数字劳动知识与能力掌握进行动态评价,并将注意力分配、深度学习程度及时反馈,进而调整教学进度,改进教学策略,实现数字赋能劳动教育的高效。
三、数字劳动教育的挑战
劳动教育是实现人本质的重要途径,如何使个体在运用数字技术的基础上建构劳动知识,体验劳动价值,成为数字劳动育人的逻辑前提和实践基础。数字技术引发的多重劳动异化,揭示了资本主义私有制下数字劳动的剥削逻辑,导致劳动育人的价值危机,冲击数字劳动教育的发展,这对以数字劳动为主题的数字劳动教育提出了新问题和新挑战。
(一)教育者与学习者作为数字劳动教育的主体,对数字技术认识、运用及规避缺乏判断
数字技术推进劳动资料创新,但数字技术内在运行规律支配我们的意识、思想及行为,受教育者极易陷入由算法程序所带来的舒适圈。乔纳森·克拉里在《24/7:晚期资本主义与睡眠的终结》一书中指出,“你随意点开一个网页,你眼睛的浏览、停顿、移动已经对有的地方比别的地方表现出更多的注意力,通通都被每分每秒的分析和量化”[14]。这个过程中,受教育者无须思考,他所想要的就呈现在他的面前。例如,受教育者使用“作业帮”进行课后学习,此程序只需要拍照、搜索、呈现等三个步骤就可看到所查询问题的解决方案,但最后呈现的是“单个解题答案”以及该题的课程视频。这样便捷的学习方式在节省了学习时间的同时,也弱化了受教育者作为学习主体的主动性,使学生陷入一种接受式、单向获得式的学习行为。
数字技术使主动探究学习的受教育者转化为被动算法程序的接受者,数字技术带来了主体性的缺失,角色发生转变。学生作为主体意识以及情感并没有被合理地激发出来,影响了劳动教育的发展。又如,部分教师对数字赋能的劳动课程、劳动教学、劳动教具的使用没有分析及思考,成为数字技术的提线木偶,导致教师逐渐在被技术渗透的教学方式下,产生对算法操作性程序的定式结构及意识形态的认同,弱化个体判断能力。
(二)过度追逐数字劳动而忽视劳动教育的思想性、实践性及社会性[15]
首先,“劳动教育的重要价值就在于将儿童引入他所生活于其中的世界,理解并承担起对这个世界的责任”[16]。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让劳动最光荣、劳动最崇高、劳动最伟大、劳动最美丽蔚然成风。劳动教育直接影响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的劳动精神面貌。在数字时代,受高新技术带来的便捷式影响,学生不愿劳动、不会劳动等思想只增不减。其次,劳动课程作为实践性较强的课程,注重学生的亲身实践、亲身感知。以学生掌握劳动知识、运用劳动能力以及形成劳动品质覆盖到生活劳动、生产劳动、工艺劳动为宗旨,在此过程中不仅是学生的思维得到开发,身体也得到锻炼,但数字劳动教育被窄化为教授数字手段,在具体实践中并不具备很强的操作性。最后,“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2]。劳动是社会关系存在的前提,人既在劳动中形成自己的社会关系,也在劳动中解构并重构自己的社会关系。基于此,劳动教育也表现为一种具有社会性的劳动教育。在数字劳动教育的过程中,所侧重的是使学生掌握数字劳动的知识、技能,是个体获得数字成长的过程,但劳动的本质是社会关系,数字劳动教育的基本目标是促进个体的数字能力,因而弱化团体间情感交流的社会关系。
(三)数字技术与劳动教育的差异性导致数字劳动教育的新挑战
数据成为市场获取资本的对象,在劳动育人的关系中表现为数据与育人的二律背反。市场管理者为获得资本而不断为技术投资,表现为在数字终端采用更加全面的方式大量收集信息,使用更加私密的算法程序整理个人信息数据。直观来看,数据收集的广泛性、整理的精确性以及展现的针对性,势必会对劳动育人产生影响。同时,数字技术的快速发展导致技术与受教育者之间关系的紧张。劳动教育利用模式化的数字程序引导学生的劳动认知、评价学生的劳动行为,单纯的数字进步与数据精进并不能提高育人的本质。受教育者不希望受到数据安排与调控的束缚,不愿意卷入后台不停运作的数据中。
四、数字劳动教育的治理
(一)育人为本:数字劳动教育的目标指向
康德认为,人是社会的主体,都是作为目的自身而实存,不是作为意志随意使用的手段而实存,在一切社会行动中都必须把人视为行动的目的[17]。承认人的主体性,就需要在劳动教育设计时把培养人、促进人发展作为基本考量,因此数字劳动教育的核心是强调以人为本。只有将人置于数字劳动教育的中心,才能沿着正确的方向实现价值。
实现数字劳动教育的价值,在技术赋能上体现个体间的有效互动,呈现生命活力,让技术服务于人,服务于教育。从劳动育人的宗旨出发,数字劳动的目的是为了培养时代新人、促进个体全面发展,包括:秉持热爱劳动和热爱生命的人生态度、尊重他人成果及隐私、提升国民性;培养批判思维和创新思维的能力、基础技术运用的能力和自由探索学习的需求,提升深度学习、劳动智慧;开创多元劳动形式,虚拟和现实共生。这意味着数字劳动教育要有高性能的基础设备、开放的网络环境、资源共享的智能学习平台及虚实结合的学习设备,其目的在于通过高新技术设备赋能劳动育人效果提升。具体而言,虚实结合的劳动环境打破传统时空界限,使学生在时间超前、空间泛化的环境内,丰富学生的意识及头脑,有助于数字劳动的创新方式生成。通过大数据、区块链实现不同学科、不同地域、不同文化的互联,有助于学生基于一方天地,了解多方水土。融合各地域劳动文化,实现课堂与课堂之间的动态联系。数字技术赋能劳动教育的过程,推动了劳动教学模式的变革,学生通过数字技术沉浸在智能空间内,探索劳动方式的创新,研究农作物的生长,参与技术工厂的运作。其根本目的是为了激发学生多方面的劳动思维,提高运用数字技术解决复杂劳动的能力,增强学生的参与意识和社会责任感。
(二)智慧生成:数字劳动教育的价值升华
“若忽视教育数据服务的价值校准与伦理调适,基于智能算法的教育数据服务的价值校准可能会将教育变成一个完全被数据与算法所操控的世界,而传统教育所秉持的人文立场将变得虚无飘渺”[18],因此在数字劳动教育的过程中注重个体数字劳动的思想性、实践性及社会性,从而实现劳动育人的价值导向。
注重数字劳动教育的思想性。一是后台数字开发的工作者的思想,不仅要自身保持着正确的劳动价值观,还要对收集到的不正确内容有高度敏感性。二是以受教育者为核心,提升数字劳动育人新高度。人工智能、区块链、大数据等技术不断扩张,使人们置身于数字技术建构的数据网络背景下,摆正教育主体的数字劳动思想,确保他们能够基于劳动正义的准则有序、规范地参与数字劳动实践,是数字劳动教育得以顺利开展的前提。强化教育者的数字劳动理想、劳动信念、道德观念,使教育者不但具备数字技术的认知与技能,还应具有正确的数字劳动教育价值观念,防止数字劳动成瘾带来的学生思维固化,使教育过程更加科学、更加合理。三是将数字劳动教育从学校领域扩大到社会层面,数字劳动教育应以维护劳动者数据隐私权和商品控制权为基础内容,引导一般互联网用户明辨数字劳动价值观,防止数字市场对劳动者的剥削。
注重数字劳动教育的实践性。培养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相结合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是新时代劳动教育的首要目标,数字技术不断创新劳动新形态,进而赋能劳动教育新方式。数字时代的劳动教育为学生体验多元的劳动形式,应立足多元化的数字空间,结合与学生认知水平相适应的数字技术,设计教学活动。在活动中,数字劳动教育应将指向实践作为指导性原则,加深学生对数字技术改变日常生活意识,科学地认识数字劳动。促进学生的数字劳动素养,积极引导学生参观相关数字行业项目,参与数字劳动实践。同时,在数字空间内切身体验更加直观的数字劳动过程,丰富了劳动的想象力,让学生感受到数字赋能劳动的魅力。
注重数字劳动教育的社会性。具体而言,数字劳动低情感的沟通交流,为学生社会关系的构建带来挑战。换言之,数字技术为学生社会性发展提供更加多元的交流形式、更加广泛的交流范围、更加自由的交流空间。数字劳动空间是一个更加开放的空间,在此学生可自由表达自己的观点,是信息的创造者及接收者。也就是说,在数字生产的实践中,学生具备相比现实空间更加自由的劳动方式。这种基于相对自由劳动之上的劳动,能够为平等社会的理想群体关系创造条件。促进数字技术的民主化转变,进而促使学生的社会性充分发展。
(三)共生价值:技术与学科深度交融
与传统形态的劳动教育相比,数字劳动教育具有创造性,在实施过程中追求劳动形式的多元性、劳动内容的广泛性以及劳动环境的虚拟化。这些特点保障了数字时代在培养适合新型劳动人才方面的育人优势。凡事须有度,物极必反。如果过度追求数字劳动的创造性及简捷性,其育人功能就会弱化、虚化甚至异化。只有加强数字技术赋能劳动教育的统筹和动态调适,才能实现数字技术赋能劳动育人的价值最大化。
1.数字技术赋能劳动教育的实践均衡。从发展历程来看,科学、技术、时代进步对人才的需求,倒逼劳动教育快速发展,使其具有立足实践、追求见解与不断创新的特点。这是数字时代弥补传统劳动教育的重要优势所在,但是劳动教育的主要目的不仅是培养会劳动的劳动者,更重要的是促进人本质的完善,实施育人。数字劳动教育的体系构建与实施都应基于学生的身心特点和现有水平,以有助于学生劳动知识、能力、态度、情感与价值观等数字劳动素养的提升为宗旨,避免把学生异化为追求技术以及劳动机械的实践者。
2.数字技术赋能劳动教育的内容均衡。数字技术的萌发源于社会发展需要。数字技术的快速发展会自然而然地追求和强化劳动教育内容的广泛性,但对于教与育同构的劳动教育而言,过于追求内容的广泛性,会影响学生对实际劳动活动与知识理解的深度,“育人”功能弱化。这样不仅不能体会数字劳动的魅力,还会影响学生的数字劳动素养和对劳动知识系统性、逻辑性的理解和掌握。在数字时代进行劳动教育,要辩证地把控劳动教育的内容,在适度以及广泛的基础上,追求内容的深度。
3.数字技术赋能劳动教育的能力均衡。技术的发展必然促使多种劳动能力创生,但基于个体本身来讲,劳动能力不是每个能力间的平均,而是要根据劳动过程的实际问题,关注劳动内容及其情况,合理均衡。数字劳动并不是反复用肢体去做劳累的工作,更重要的是要对技术的掌握与控制。正如马克思所说:“动物只是按照它所属的那个种的尺度和需要来构造,而人却懂得按照任何一个种的尺度来进行生产。”[2]135个体不应沉沦于数字技术所带来的便捷,而是要根据自身的实际情况在横向知识的基础上纵向深化,挖掘个体的数字技术掌握能力,合理运用数字工具。建设数字网格空间的情感流通场域,在此环境中进行劳动教育,加强个体间情感交流,培养个体运用数字媒介合作交流的能力。
五、结语
随着数字时代人机协同模式更加深入,数字技术在带来优势的同时,在一定程度上也产生一定的危害,但不能因数字技术带来的风险,怀揣着对传统劳动形式的向往,就停止对数字技术的挖掘,这不符合历史发展的规律。传统劳动教育把劳动经验与重复的劳动能力作为学生应该掌握的真理,在教学过程中只以讲授的方式将劳动经验传授给学生,或者是带领学生进行形式化的参观,学生体会不到劳动幸福的价值地位。数字劳动教育是以信息、技术为基础,学生获取劳动知识的渠道多样,教师的经验传授明显不能符合劳动教育的发展,数字技术必将推动劳动理念变革,创新劳动形式更加开放的思维。劳动教育从强调谋生性的具体劳作向强调功能性的数字劳动转变是不争的事实。
参考文献:
[1]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制定.义务教育劳动课程标准(2022年版)[S].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22:1.
[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3]蒂齐亚纳·泰拉诺瓦.免费劳动:为数字经济生产文化[J].杨嵘均,曹秀娟,译.国外社会科学前沿,2023(1):53-69.
[4]盛阳.作为行动的受众商品论——斯迈思《传播: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盲点》的历史性及当代意义[J].新闻记者,2021(3):40-55.
[5]周延云,闫秀荣.数字劳动和卡尔·马克思:数字化时代国外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2-6.
[6]谢芳芳,燕连福.“数字劳动”内涵探析——基于与受众劳动、非物质劳动、物质劳动的关系[J].教学与研究,2017(12):84-92.
[7]黄再胜.数字劳动与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当代阐释[J].湖北经济学院学报,2017(6):5-11.
[8]李弦.数字劳动价值论的理论解析[J].思想理论教育,2022(11):42-48.
[9]孔令全,黄再胜.国内外数字劳动研究——一个基于马克思主义劳动价值论视角的文献综述[J].广东行政学院学报,2017(5):73-80.
[10]肖绍明.数字劳动教育与治理[J].中国德育,2019(2):30-35.
[11]RASSKAZOVAO,ALEXANDROVI.Key competencies in the digital age and transformation of education[J].IOP conference series:materials science and engineering,2020(1):1-9.
[12]FOXS.Mass imagineering:combining human imagination and automated engineering from early education to digital afterlife[J].Technology in society,2017(51):163-171.
[13]BALABANOVAA,PETROVAS,FOMENKOV,et al.Labor potential of youth for the development of ecology in the digital economy[J].E3S web of conferences,2021(258):1-7.
[14]乔纳森·克拉里.24/7:晚期资本主义与睡眠的终结[M].许多,沈清,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5:55.
[15]王豪杰,李怡.数字劳动教育:革新、风险与实践[J].重庆高教研究,2023(2):43-51.
[16]约翰·杜威.学校与社会:明日之学校[M].赵祥麟,任钟印,吴志宏,译.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5:299.
[17]HABERMAS J. The structural transformation of the public sphere:An inquiry into a category of bourgeois society[M].Cambridge:Polity Press,1989:13-22.
[18]赵磊磊,张黎,代蕊华.智能时代教育数据风险治理:实然困境与实践路径[J].湖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报,2021(6):94-102.
Challenges and Governance of Digital Labor Education
Li Shuanglong Liu Shoucui
(College of Educational Sciences, Kashi University, Kashi 844000, China)
Abstract:Digital labor education is the expansion of labor education in the digital space in the new era, and it is a new pattern of labor education aiming at educating people through labor and strengthening people through technology. The research shows that digital labor is the product of the development of digital economy in capital society. With Marx’s labor alienation theory as an important theoretical source of digital labor alienation,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challenges faced by digital labor education, aiming to grasp the theme of the times, that is, digital technology enabling labor education, so as to promote the innovation and reform of labor education. With the technical advantages of the digital age, it is necessary to fully explore the value implication of labor education, giving full play to the goal of “people-oriented” digital labor education, emphasizing the ideological, practical and social wisdom generation in the process of education, and reasonably grasping the high integration of digital technology and labor education disciplines.
Key words:Digital labor; Labor alienation; Digital labor education; Digital extension; Wisdom generat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