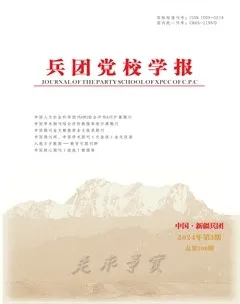加强敦煌文献研究
2024-07-11刘志
[摘要]敦煌文献目录的编纂对于敦煌文化资源的共享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这项研究工作需要多学科领域专家学者的长期积累和交流合作。本文在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这一问题进行探讨。以目录学研究为基础的敦煌写本学研究,一方面要考辨敦煌写本及其写本规格,另一方面要把敦煌写本研究与唐代的历史文化研究结合起来,更加全面地展示敦煌文化的历史画卷。
[关键词]敦煌文献;目录学;写本学;唐代文化;
[中图分类号]G256.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0274(2024)03—0005—07
[作者简介]刘志,男,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敦煌文献、新疆文献、道教历史与文献。
2019年8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敦煌研究院座谈时的讲话》中指出“加强敦煌学研究”“把莫高窟保护好,把敦煌文化传承好,是中华民族为世界文明进步应负的责任。”对于敦煌文化的基础研究,“要通过数字化、信息化等高技术手段,推动流散海外的敦煌遗书等文物的数字化回归,实现敦煌文化艺术资源在全球范围内的数字化共享”。其中敦煌遗书,即敦煌文献,是敦煌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文拟对如何加强敦煌文献研究,推动敦煌文献资源的整合工作做一点探讨。
一、加强敦煌文献目录学研究
众所周知,中国是世界上古籍最多的国家之一,中华文明是世界上唯一未曾间断的文明。敦煌文献作为一个珍贵的文献群体,尤其是对唐代的历史文化研究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充分展现了古代中华民族以自身的文献和文化体系包容吸收世界不同文明的文献和文化的智慧结晶。然而随着1900年藏经洞的发现,敦煌文献除了一部分仍在国内,大部分流散到英国、法国、俄罗斯、日本、德国等国家和地区的公私收藏机构。这样给全面查阅原卷带来了很大的困难。敦煌文献的这种分散状况,使研究者相对集中于研究某种典籍或某一馆藏的典籍,就已付出很大心血,至于再将敦煌文献研究成果与中国古籍研究成果结合起来,则难度更大。同样,不熟悉敦煌文献的古籍研究者也遇到同一类问题。所以在相当一段时期内出现了“敦煌文献研究者与古籍整理研究者的分离”这种状况,其原因关键是“迄今没有一本总目供研究者使用”1,即一部收录全面、分类科学、考证翔实的敦煌文献目录工具书。本文以敦煌文献的影印出版为基础,对敦煌文献目录的编纂略做探讨。
(一)敦煌文献的影印出版
敦煌文献卷帙浩繁,一般认为有6万余件之多。现存敦煌文献分布世界各公私收藏机构,给研究工作带来不小的难度。在20世纪60年代、70年代,敦煌文献的公布主要是通过微缩胶卷,或者是敦煌学者自己拍摄的照片。至20世纪90 年代,各大收藏机构开始以影印图版的形式公布敦煌文献,至今大多数敦煌文献已经通过这种方式公布,主要有:
《英藏敦煌文献(汉文佛经以外部分)》,四川人民出版社1990—2009年出版,全书十五卷,黑白图版。该书公布了英国博物馆东方古物部和英国印度事务部图书馆收藏S.1—S.13677之间的汉文非佛教文书。
方广锠、(英)吴芳思主编《英国国家图书馆藏敦煌遗书》,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2017年出版,50册,黑白图版。前50册收录英国国家图书馆收藏编号S.1—S.2770的敦煌遗书。该书计划收录范围为英国国家图书馆收藏斯坦因中亚探险所获敦煌汉文文献编号Or.8210(S.1—S.14144)的全部敦煌遗书。
《法藏敦煌西域文献》,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2005年出版,34册,黑白图版。该书公布了法国国家图书馆收藏全部敦煌西域文献,编号P.2001—P.6038。
荣新江主编《法国国家图书馆藏敦煌文献》,上海古籍出版社2023年出版,60册,彩色图版。该书公布了法国国家图书馆收藏的敦煌文献P.2001—P.2369,全书预计共160册,公布编号为P.2001—P.6040的敦煌文献。
任继愈主编《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敦煌遗书》,江苏古籍出版社1999—2001年出版,7册,黑白图版。该书公布中国国家图书馆收藏编号BD00001—BD14005的敦煌遗书。
任继愈主编、中国国家图书馆编《国家图书馆藏敦煌遗书》,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05—2012年出版,146册,黑白图版。该书公布了中国国家图书馆收藏编号BD00001—BD16579的敦煌遗书。
(俄)孟列夫、钱伯城主编《俄罗斯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圣彼得堡分所藏敦煌文献》,上海古籍出版社与俄罗斯科学出版社东方文学部1992—2001年联合出版,17册,黑白图版。该书公布了俄罗斯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圣彼得堡分所收藏编号Ф001—Ф366、Дх00001—Дх19092的敦煌文献。
黄永武编《敦煌宝藏》,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81—1986年出版,140册,大部分为黑白图版。该书公布了英藏、法藏、北图藏及散藏的大量敦煌文献和艺术品,其中第1—55册为英国国家图书馆藏编号S.1—S.7599的敦煌文献,第56—110册为北京图书馆藏编号北1—8602的敦煌文献,第111—135册为法国国家图书馆藏编号P.2001—P.3798的敦煌文献,第136、137册为散藏编号散1—散1608的敦煌文献,第138—140册为法藏敦煌文献的精品欣赏(系彩色图版)。图版主要是据已刊布的缩微胶片影印。
除了以图书出版的形式,各主要收藏机构将敦煌文献的扫描照片通过国际敦煌项目(International DunHuang Project)在网上公布。目前各收藏机构发布扫描照片的进度不一,这一形式还不能完全满足研究工作的需要。
(二)敦煌文献索引的编纂
敦煌文献索引工具书,可以为更方便地查找、使用敦煌文献图版提供帮助。
目前已经出版的有,商务印书馆编《敦煌遗书总目索引》,商务印书馆1962年出版;黄永武编《敦煌遗书最新目录》,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86年出版;敦煌研究院编、施萍婷主撰稿《敦煌遗书总目索引新编》,中华书局2000年出版。以上索引工具书都是2000年以前出版,这在当时为研究者提供了很大的方便。但是20多年来,随着各大收藏机构及公私散藏敦煌文献的陆续公布,使得原有索引工具书有大量已经公布的敦煌文献未能编入。目前,随着各主要收藏机构敦煌文献的公布,以此为基础的各馆藏索引也基本出版。所以编纂一部更全面的敦煌文献总索引是必要的,也是可行的。
(三)敦煌文献目录的编纂
敦煌文献研究是一个系统的文化工程,基础研究的关键性成果集中表现在目录学研究,即对书名、卷数、作者、成书年代等问题的考证,并且在此基础上分类著录书目。在敦煌学的早期发展阶段,中国学者就已经率先从事这方面的研究。由于敦煌文献分散于各公私收藏机构,使得馆藏目录的编纂和研究首先提上日程,在这之后丛书目录研究成果出现。
敦煌文献研究的第一部馆藏目录是陈垣编《敦煌劫余录》,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31年出版发行。该书著录了北平图书馆(今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敦煌写卷8679件,按佛教文献、道教文献、摩尼教文献分类著录。
(英)翟林奈编《英国博物馆藏敦煌汉文写本注记目录》,英国博物馆董事会1957 年出版。该书著录斯坦因中亚探险所获敦煌汉文文献,主要收录编号Or.8210中的写本文献S.l-S.6980,以及少量刻本文献等,将英藏敦煌汉文文献分为佛教文献、道教文献、摩尼教文献、世俗文书和印本文献5类进行著录。1
(俄)孟列夫主编《苏联科学院亚洲民族研究所藏敦煌汉文写本注记目录》,2册,莫斯科东方文献出版社1963年、1967年出版。前苏联科学院亚洲民族研究所,即今俄罗斯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圣彼得堡分所。该书收录俄藏文献M1—M2954,按佛教文献、儒道文献、各种文书、非汉文文献等分类著录。
以上馆藏目录编纂时间在20世纪60年代以前,在当时条件下为目录学研究奠定了基础。但是以上馆藏目录所收范围还是部分馆藏敦煌文献,有待于补充完善为全部馆藏目录。再者西方学者对敦煌文献的著录,未能参照唐代文献目录分类,所以未能形成反映唐代历史文化特点的目录体系。
敦煌文献的丛书目录是建立在熟知各馆藏目录和文献的基础上,按丛书自身的目录分类法编纂文献目录。
敦煌文献研究中第一部丛书目录是王重民编著《敦煌古籍叙录》,商务印书馆1958年出版,5卷。该书按经、史、子、集四部分类法著录,敦煌文献主要包括作者在伦敦、巴黎所见,北平图书馆收藏,以及私人收藏的敦煌文献。著录体例,先著录书名、著者姓氏,次著录原收藏号码等有关内容。有关敦煌文献研究论文,酌情收录。韵书、佛经、道经、单篇诗文、金石拓本,不收录。
《敦煌大藏经总目录》,系《敦煌大藏经》的目录册。徐自强、李富华等编《敦煌大藏经》,台北前景出版社、星星出版公司1990年出版,全书六十三册,另有目录册。《敦煌大藏经总目录》按《开元释教录·入藏录》为敦煌佛教文献编目。所收敦煌文献以北京图书馆馆藏为基础,补充了英藏、法藏、国内散藏等内容。方广锠先生对敦煌佛教典籍做过详细的介绍,收录在《敦煌学大辞典》“佛教典籍”辞条中,敦煌文献来源为英国、法国、俄罗斯、中国、德国、日本等国家和地区的公私收藏。
王卡著《敦煌道教文献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出版。该书是在日本学者大渊忍尔编《敦煌道经目录编》(1978年东京福武书店出版,著录道经496件)基础上,进一步收集、整理、考证敦煌道教文献的成果。该书按唐代道经已经形成的三洞四辅分类著录道教文献,另加“道教经目及类书”“相关文书”“失题道经”,共十大类,著录敦煌道教文献170余种,收录英国、法国、俄罗斯、中国四大收藏机构,以及日本、德国等国家和地区的公私收藏机构各类敦煌道教文献达800余件。
此外还有敦煌文献专业目录,例如:马继兴主编《敦煌古医籍考释》2,著录敦煌医药文献70余种;郑炳林著《敦煌地理文书》3,著录地理文书41件;王三庆著《敦煌类书》4,著录敦煌类书43种。耿世民著《敦煌突厥回鹘文书导论》5,著录突厥、回鹘文文献28种。
敦煌文献总目录可看成是各丛书目录和专业目录的合成,其编纂工作时间久而且难度较大。每一件敦煌文献收藏品都需要定名、考证、著录等工作。从敦煌文献公布、索引编纂到各馆藏文献、丛书文献、专业文献目录的编纂,这是几代学人数十年艰辛努力的成果。而将这些成果继承下来,经过系统地考证、分类、编目、著录,汇集成一部敦煌文献总目录,这无疑对敦煌文献以至中国古籍的研究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从上述目录学成果来看,敦煌文献总目录主要包括:
四部书目录。中国古籍的经、史、子、集四部书目录对于敦煌汉文文献应收尽收,对于可以单独编成丛书的佛教文献、道教文献也应在子部说明或存目。按王重民著《敦煌古籍叙录》,子部还包括佛道以外其他汉文宗教文献。敦煌文献中的官私文书,似应归入史部。这些史料对研究敦煌地区的历史、经济、社会、文化具有重要意义。
大藏经目录。在敦煌文献中,佛教文献约占百分之九十,其中汉文佛教文献数量最多。按方广锠先生《敦煌佛教经录辑校》1,以《开元释教录·入藏录》为主要参照,著录敦煌汉文佛教文献,对藏外文献再补充收录。
道教文献目录。中国本土宗教道教的经书体系,在敦煌文献中也有基本的保存。按王卡先生著《敦煌道教文献研究》,以三洞四辅目录体系著录敦煌道教文献,再补充“道教经目及类书”“相关文书”“失题道经”。
古代民族语言文献目录。在敦煌文献中有藏文、回鹘文,于阗文,西夏文,蒙古文、梵文、粟特文、希伯来文等古代民族语言文献。按古代民族语言分类著录有关文献。
总目之后设附录,有专业文献目录索引、作者索引、书名索引等。例如,宗教文献目录索引,包括汉文、藏文、回鹘文、梵文等各种语言宗教文献;再如,敦煌历史文献目录索引,包括敦煌古方志、官私文书等。
敦煌文献总目编纂需要多学科领域的学者加强合作,是一项任务艰巨的研究工作。因为敦煌文献既有精美的写卷,又有大量难以辨识的残片,如何定名、缀合、复原是一项艰辛的古籍整理和研究工程。通过深入细致的整理、研究工作,才能把分散收藏于国内外的敦煌文献,集结成为中华民族的一部大型古籍丛书目录。在此基础上,打造出更多文献学研究的学术精品,建立起敦煌写卷的文献体系,特别是唐代的经籍图书体系,对中国古籍、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和人文学科体系建设,都具有重要意义。
二、加强敦煌文献写本学研究
系统地提出写本学的研究成果有,林聪明著《敦煌文书学》2,荣新江著《敦煌学十八讲》3,张涌泉著《敦煌写本文献学》4,郝春文《敦煌写本学与中国古代写本学》5。本文探讨的写本学是敦煌文献研究发展的一个阶段,确切地说是文献学在目录学成果积累到一定程度时,需要回答有关写本学的问题。敦煌文献在经过著录和考证之后,需要研究的几个基本问题是:同一种文献是由哪几种写本组成的,各种写本有哪些特点,有哪些人物何时何地缮写制作了敦煌写卷。
(一)写本研究的基本内容
敦煌写本研究的基本内容是敦煌写卷的纸张、字体、行款、写卷规格、书写人物、写本年代、缮写制作过程等。
敦煌写卷主要载体是麻纸,还有绢帛等。不同写卷,其纸张形态、尺寸又有不同。再者,敦煌写卷的字体研究,有楷书、行书、草书、篆书等。尤其是楷书真迹,敦煌写卷中多有精品之作,是中国书法艺术的瑰宝,是极为珍贵的艺术文化遗存。楷书是中国古籍缮写的主要正体字之一,唐代则是楷书书法艺术的高峰。同一字体,又有不同的书体,或不同笔迹,可以用来区分写本。敦煌写卷的行款,以17字为标准行款,以此可以发现不同写本行款的变化。以上可以建立起敦煌写卷的基本规格。
写经人物有官方写经人员、宗教人士、经生等。对写经人物的研究,一方面可以研究写卷的书写制作的过程,例如高规格的官方写经,不仅有专人书写,还有专人校对、监制,形成了完备的写经制度。写经人物研究还可以反映唐代的民俗和社会文化。写经多与民俗中的祈福、消灾有关,还有的是宗教人士的经戒传授活动,也有的是为了收藏经书,以至是国家推广经籍、进行文化治理的一项内容。
(二)写本的考辨
在敦煌文献中,特别是抄写数量较多的同一种文献,往往有几个不同写本,甚至是多个本,应加以区分和研究。以敦煌本《太玄真一本际经》(以下简称《本际经》)为例,其留存的写卷有140余件,其中包含了多个写本。仅从写卷题记,就能发现至少有8个写本,分别是:
1.显庆元年(656) 祠部员外李谅监制《本际经》卷四,安徽省博物馆藏皖1-03;
2.仪凤三年(678)女冠郭金基写《本际经》卷二,英国国家图书馆藏,S.3135;
3.长寿二年(693)索道士写《本际经》卷二,上海市图书馆藏,上图078;
4.证圣元年(695)道士氾思庄写《本际经》卷四,法国国家图书馆藏,P.2806;
5.开元二年(714)道士索洞玄写《本际经》卷第二,法国国家图书馆藏,P.2475;
6.未知纪年道士张澄波写《本际经》卷七,天津艺术博物馆藏,津艺116;
7.未知名人士女冠宋妙仙写《本际经》卷五,原罗振玉贞松堂藏本,散0689;
8.未知纪年女冠赵妙虚写《本际经》卷一,俄罗斯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圣彼得堡分所藏,Дх18527。
此外,还有《本际经疏》的写本,即景龙二年(708)神泉观写《本际经疏》卷三,法国国家图书馆藏,P.2361。
在这8个写本中,有纪年最早的是显庆元年(656),最晚的是开元二年(714),前后相距58年,写经人物有官方祠部官员,也有沙州的道士、女冠等。也就是说这8个写本是由不同人物在不同年代独立完成的写本,可以分别进行写本研究,而不应简单归结为一种文献。同时,写本的考辨对校勘学也会产生重要的影响,使校勘的底本和参校本,不是以馆藏编号为基础,而是以不同写本为基础。当然,由于敦煌文献许多是残卷、甚至是碎片,完全区分写本难度较大。
(三)写本研究与唐代历史文化研究相结合
以《道德经》写本研究为例来探讨这一问题。《道德经》又称《老子》《五千文》,是敦煌写卷中的一部重要经典,且有较多的注本和写本。据王卡先生著《敦煌道教文献研究》,敦煌写卷中的《道德经》及注本有:《老子道德经五千文》《老子道德经(白文本)》《老子道德经河上公章句》《老子道德经想尔注》《老子道德经节解》《老子道德经论注》《老子道德经顾欢注(拟)》《玄言新记明老部》《老子道德经开题序诀义疏》《老子道德经李荣注》《老子道德经义疏(佚名)》《唐玄宗老子道德经注》《唐玄宗老子道德经疏》,以上共计13种。1 除《老子道德经想尔注》可能为北朝写本2,大多应为唐代写本。
敦煌写卷中有较多的唐代《道德经》写本,其原因除了《道德经》是道家道教尊奉的重要经典,还有唐代所特有的其时代背景。这就是李唐皇室尊奉老子为远祖,以老子所作《道德经》为唐朝重要经典。李唐皇室尊奉老子为远祖,始于唐高祖李渊。武德元年(618),唐高祖尊奉老子为“帝祖”3,武德三年又称“远祖”4。此后李唐皇室继续尊奉老子为远祖,贞观十一年(637)正月二十五日,唐太宗李世民诏曰:“况朕之本系出自柱下,鼎祚克昌既凭上德之庆,天下大定亦赖无为之功,宜有改张,阐兹真化”5。乾封元年(666)二月己未,唐高宗李治于亳州老君庙,尊奉老子追号曰:“太上玄元皇帝”。6唐高宗还命王公百僚,每岁贡举加试《老子》7。经历武周统治时期之后,唐中宗李显于神龙元年(705)“二月甲寅,复国号,依旧为唐”,“老君依旧为玄元皇帝”,令贡举人“依旧习《老子》”1。唐玄宗李隆基甚至把《道德经》置于儒家六经之上,“我烈祖玄元皇帝,乃发明妙本,汲引生灵,遂述玄经五千言,用救时弊,意高象系,理贯希夷,非百代之能俦,岂六经之所拟。”2唐玄宗《亲试四子举人敕》,即以四子经典(《老子》《庄子》《文子》《列子》)选拔举人,认为《道德经》“可以理国,可以保身,朕欲敦崇其教以左右人也”3。又设崇玄学,置崇玄博士,向学生讲授《道德经》4等。这些举措,使朝廷选拔任用的人才中,许多都精通《道德经》。
唐代前期从京师长安到敦煌,官方和道教都从事《道德经》的抄写和传播,所以敦煌写卷中有不少《道德经》的注本、写本。在这些写本中,具有代表意义的是,唐开元二十三年(735)礼部监制《唐玄宗老子道德经注》、凉州都督府制《老子道德经五千文》,唐景龙三年(709)敦煌县道士经戒传授所用《老子道德经五千文》等。这些敦煌本《道德经》不仅是研究敦煌写卷珍贵的资料,而且对于唐代经籍写本研究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写经人物研究中,关于御制本写经人物,例如敦煌写卷P.3725《唐玄宗老子道德经注》,是唐开元二十三年(735)国子监、礼部缮写校对,最后由礼部尚书李林甫监制的写本。我们发现这是在唐玄宗颁布御注《道德经》背景下的一次写经活动。开元十年唐玄宗开始注解《道德经》,至二十一年完成并向天下诸州进行颁布。当时不仅以写经颁布,而且以石经颁布。敦煌写本与易州、邢州刻本《唐玄宗老子道德经注》,是保存下来的珍贵的实物资料。就写经而言,在开元二十三年礼部监制了御注本的缮写和校对。不久之后,开元二十九年(741)集贤院成立,宰相张说任院士。这是专门进行御本经籍制作的机构,《唐六典》卷九记载,“集贤院所书,皆御本也”。而且李林甫于天宝五年(746年)任职集贤院院士期间,再次监制《唐玄宗道德经注》的缮写和校对。
关于官方写经人物研究,例如敦煌写卷《老子道德经五千文》Дx 0111与Дx 0113两件残纸缀合,背面纸缝钤有“凉州都督府之印”,说明此件是唐代凉州(今甘肃省武威市)都督府颁布的写本。凉州都督府是唐武德至开元年间的军政机构,也是沙州的上级官署,在唐朝诸道中属于陇右道。唐朝有向天下诸道诸州颁布《道德经》文本的举措,据《册府元龟》卷五四记载,唐玄宗于天宝十四年(755)诏令向天下诸道诸州颁布御制《道德经注》《道德经疏》,诸道诸州经过传写,收藏于当地道教宫观之中。5而凉州都督府颁布《老子道德经五千文》当是李唐皇室向天下诸道诸州颁布《道德经》的遗存。
关于道教写经人物研究,例如敦煌写卷P.2347《老子五千文》是敦煌道士经戒传授所用的一个写本,记载了唐中宗景龙三年(709),三洞法师阎履明与敦煌县冲虚观女官清信弟子唐真戒的经戒传授,有《序诀》《老子五千文》《十戒经》以及《盟文》。唐代道教还为朝廷刊定、书写《道德经》,做出这一重要贡献的是上清派宗师司马承祯。开元九年(721)司马承祯奉唐玄宗诏令刊定《道德经》文本为5380字,于长安景龙观三体书写《道德经》,再刻于石柱。
关于民间写经研究,敦煌本《道德经》也有一些抄写规格不标准,字品质量较差的写本,例如S.0792《老子道德经(白文本)》,P.2420《老子道德经(白文本)》。这些写本很可能是民间传写本或学生习字本。唐代特别是开元、天宝年间,是《道德经》在社会上广泛流行的时代。开元廿一年(733),唐玄宗诏令士庶家藏《老子》,每年贡举加老子策。6开元二十九年(741)正月,唐玄宗诏令天下诸州置教学机构崇玄学,学生习读《道德经》,并且要求平民百姓家习此书。
“(开元)二十九年正月诏曰:三皇之时,兆庶淳朴,盖由其上,以道化人。自兹厥后,为政各异。我烈祖玄元皇帝,禀大圣之德,蕴至道之精,著五千文,用矫时弊,可以理国家,超夫象系之表,出彼明言之外。朕有处分,令家习此书。庶乎人用向方,政成不宰,虑兹下士,未达微言,是以重有发明,俾之开悟,期弱丧而知复,宏善贷于无穷。两京及诸州,各置玄元帝(皇)帝庙一所,每年依道法斋醮。兼置崇玄学,于当州县学士数内均融量置,令习《道德经》及《庄子》《文子》《列子》,待习业成后,每年随贡举人例送至省。置助教一人,委所由州长官于诸色人内精加访择补授,仍稍加优奖。”1
所以在敦煌应当有这些缮写习读《道德经》的社会活动。
关于写经规格研究,一般来说,敦煌写经的标准规格是行款17字的黄纸写卷。敦煌本《道德经》,大多也是以此为标准规格。敦煌写卷P.3725《唐玄宗老子道德经注》珍贵之处是保存了御制《道德经注》的写经规格,其写经规格不同于一般敦煌写经。大致来说,经文13字行款,注文17字行款,经注连书13—17字不等。至于用纸,据《旧唐书·经籍志》记载,开元年间,朝廷用纸多是益州麻纸。敦煌写本与文献记载相结合,这可以较为全面地了解御制《道德经注》的主要纸张来源和制作规格。从中国古籍写本的历史发展来看,唐代正处于写卷本书籍的鼎盛时期,这样更加明确了御制《道德经注》历史价值和文本价值。其他《道德经》写本的特点,例如经文赤书注文墨字,经文与注文分行书写,记录经文字数等写经规格也值得进一步研究。
《道德经》在敦煌写卷研究中的价值不仅在于敦煌藏经洞所出经书,而且是研究唐代经籍丛书的重要资料。也就是说,敦煌写卷研究应当放置于唐代历史与文献以至中国历史与文献的学术体系之中。敦煌学以敦煌文献和文物为基础,这是毋庸置疑的,但是不能局限于敦煌地区的历史、文献和文物。敦煌学要以中国历史文化为根脉,以中国与世界文化交流为视野,不断深入地研究敦煌文化。
敦煌学作为一门国际显学,受到国内外众多学者的关注。在敦煌学的发展中,中国学者曾经有过紧迫感,甚至危机感。1970年代末、1980年代初期,在经过10余年发展缓慢,缺少学术交流的情况下,中国学者得以与外国学者展开学术交流,就在这个时期发现了自身学术暂时的落后。当中国学者发现与国外敦煌学学者尤其是日本学者的差距时不禁感叹“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国外”“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日本”。一方面,这里有发现落后的清醒认识是正确的,从而激励中国学者在学术研究中奋起直追。另一方面,若脱离中国历史文化研究的整体,片面认识敦煌学,唯国外学术是为先进的这种思想,甚至出现自卑心理,则是有局限性的。因为在中国学术史上,中国学者对中国历史文化体系的研究和艰辛努力从未停止过。敦煌学的根脉在于中国历史文化体系,而不是脱离于中国历史文化体系的一个学术领域。也就是说,即使在落后、困难的情况下,也应当以文化自信、学术自信的眼光来看待中国学者与国外学者在某些研究领域的差距。从80年代、90年代中国敦煌学的快速发展,也说明了中国学者不仅善于敦煌学专题研究,而且能够把敦煌学置于中国历史文化体系中进行研究。以敦煌道教文献为例,中国学者超过日本学者的关键是在于对道教文献体系即道藏的整体掌握为基础,对敦煌道教文献进行了更为符合道藏特点的综合研究,这是国外学者所难以坚持和做到的。
进入21世纪,中国学者在敦煌学领域已经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习近平总书记《在敦煌研究院座谈时的讲话》指出,“加强敦煌学研究”“敦煌文化属于中国,但敦煌学是属于世界的”。中国学者应当与敦煌学研究领域的各国学者加强合作,共同推进学术研究的深入开展,努力打造精品力作。同时要加强学术交流,讲好敦煌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文明对话和文化交流做出积极的贡献。
责任编辑:杨伟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