穿越贡嘎山遇难事故分析
2024-07-04徐时雨
徐时雨

5月19日,夜色在个人社交平台张贴了一则“寻人启事”,一位来自江苏无锡的户外爱好者小南5月11日从四川康定出发,独自重装穿越贡嘎山期间失联。
5月21日下午,夜色告知《户外探险》,救援队已找到小南,但人已经不幸遇难。
整个5月,贡嘎的春雪未断,一场又一场大雪覆盖来往徒步者的脚印。雪光之下,危险丛生。这是短短一个月内贡嘎穿越线上的第二起遇难事故,也是夜色在这个5月里第二次经历他人的不幸。5月4日,夜色在反穿贡嘎大环线途中时,于日乌且垭口海拔4600米的平台发现了在帐篷中不幸遇难的户外爱好者夏某。
在社交平台,围绕贡嘎大环线遇难事故展开的探讨也不断增多。有人说:“贡嘎大环线的事故9年前我就差点经历。”也有人说:“你一句小小雪山拿下,别人就把命留下。”有人心有余悸,有人已经再次出发在路上。
昨天,贡嘎穿越的路上又下起大雪,一位驴友拄着登山杖在及膝的厚雪中跋涉,她在离垭口还有3公里的地方选择下撤。
对于登山户外运动来说,风险是如影随形的黑影。一场事故的表面背后,也汹涌着巨大的暗流。今天我们反思和探讨一个事故,是为了揭开事故背后更多共同的、本质的东西。
在针对五一贡嘎穿越遇难事故的采访中,多位采访对象都不约而同地称自己那几天在山上的经历与遇难者不无相似,有3位采访对象更是直言道:我自己本身可能就是一个案例。
他们中有独行者,但更多是通过网上AA组队出发,有人在出发3小时后就与队伍走散,一路饱受高反的折磨,“能活着回来还是靠路上碰到的几个老驴友。”他们在慨叹遇难者命运的同时,也在庆幸自己的“劫后余生”。

翻过日乌且垭口
达洛是在4月30日从老榆林去往子梅村,出格西草原往双岔河方向的山坡上遇到遇难者夏某所在队伍的一行5人。双方简单打了一声招呼后,达洛继续行进,他的计划是从上日乌且翻过垭口,去自主攀登那玛峰。但在走出不到10分钟后,他的手机没电了,便回头想去找这组人借用充电宝把手机充上电来看轨迹。夏某慷慨地将自己的充电宝借给了达洛使用。这时天开始下雨,他叫达洛干脆别走了,留下来和他们一起扎营。
达洛对《户外探险》说,通过他的观察,他感觉这支团队“是有问题的,他们并不是太团结”。有个别队友甚至是第一次高原徒步,队员们彼此之间的磨合也不是特别默契。
夏某来自西安,在一起露营的当晚,达洛还开玩笑地对他说“西安强驴多”,并对他提及了3月初在秦岭东梁遇难的驴友。夏某说,东梁是大路,想不通怎么会出事。达洛嘱咐他一定要小心。
次日早上8点钟,达洛收拾好了帐篷,却发现夏某还在帐篷里“磨磨唧唧”没有出来,“不知道在干什么,也没有吃早饭,后来收帐篷时候好像也不太会收。”达洛怀疑可能是他内向的性格使然,并没有说什么,只是帮他把帐篷收完,并留下了一包葡萄糖糖果给他。因为早晨收拾装备时发现一件大羽绒服找不到了,达洛决定先返回康定。“给我的感觉他好像是有点失落,挺想我和他们一起走的。”最后两人互留了联系方式后便告别了。达洛后来仔细回忆,他觉得那天早上夏某的状态就已经不对了,脸色有些黑,行动迟缓,“其实如果我走的时候给他测一遍血氧,给他留下点药,也可能不会这么糟糕。”

夏某所在队伍在5月1日清晨从该营地出发,向上日乌且营地行进,并于5月2日上午10点45分翻过日乌且垭口,在莫溪沟内扎营。据一位队友后来向夜色透露,在翻越垭口前夏某就已经掉队了,这位队友在垭口处并没有看到他。至于掉队时是否有沟通,队友是否通过任何方式试图联系他,我们不得而知,截至发稿,《户外探险》也未能得到遇难者队友对此事的回应。
据一位目击者对夜色说,5月2日晚上9点左右,他在翻越垭口后已经在下方看到了夏某搭起的帐篷。夜色在采访中推断,按照夏某当时状况基本不会在下午翻过垭口,如果下午翻过垭口,他肯定要往前赶,因为4600米平台不是常规营地,而且对于高反的人,有条件肯定降低海拔往下走。所以夜色认为夏某是傍晚从垭口翻下来的,大雪、天黑加上状态不好,就扎营在海拔4600米处,想调整一天。
5月3日早上8点半,户外爱好者“山水”与队友离开上日乌且营地,开始翻越与日乌且垭口线路基本重合的日达曼垭口。他们原本是一支17人队伍,然而和夏某所在的5人队伍一样,他们的队伍联系也并不紧密,翻越垭口的时间和路线都不统一。(其中3人于5月2日下午1点多翻越日乌且垭口,翻过垭口后并未看到夏某扎营的帐篷,这也与夜色对夏某的行程推测吻合)

日乌且垭口海拔4900米,日达曼垭口海拔5025米,之所以选择翻越海拔更高的日达曼垭口,队伍的考虑是,虽然日达曼垭口更高更远,但由于他和其中几位队友状态并不好,很多人处于高反状态,大家想尽快结束这一段,而翻过日达曼垭口下去之后,很快就可以有牧民的摩托车来接他们到玉龙西,商业队也经常选择走后者。但大多数重装徒步者会选择日乌且垭口,翻过垭口后可以在莫溪沟内扎营,其后继续徒步穿越行程。山水队伍中的其中2名队友按照出发时的原计划翻越日乌且垭口,并于5月3日下午2点左右成功翻越垭口。
也正是这样的决策让他们碰到了已经在此扎营一夜的夏某,并看到了他的生前状态。两人路过时看到夏某正在拉开外帐在帐篷里烧水,从他们的观察来看,并不能确定他是否已经失去了行动能力,但烧水时的意识显然是清醒的。两位徒步者并未进一步和夏某打招呼。

“其实那个时候他只要肯去找路过的人,帮他转移下去是没问题的。”山水说。同时,社交平台上几位表示当日也路过了这顶帐篷的徒步者说,路过帐篷时听到帐篷里的呼吸,认为在睡觉,没有打扰。
这一天,5月3日,遇难者所在的队伍已经行至子梅村,这意味着接下来的路线已经有信号。5月4日,这支队伍从巴王海出山,完成贡嘎环线。夜色在面对采访时表示,其中一位队友对他说,他们在出山时曾试图通过微信联系了夏某(他们没有他的电话),但联系不上。目前已无法进一步确认队友是否是在有信号后的第一时间联系队友,但可以确定的是,他们并没有选择报警,也没有扩散消息寻求帮助。
5月3日上午10:30时,正在翻越日达曼垭口的山水与队友行进到了观望勒多曼因峰的最佳观望点,此时天气尚好,而当下午4点到达垭口上时,瞬间开始变天了,山上时而大雾弥漫,他们在雷声轰鸣中翻过垭口,此时天已经开始下雪。大雪持续了一夜。
这个寒冷的夜晚,独自在帐中的夏某究竟面对了什么?我们已无从得知。5月4日上午8点15分,反穿贡嘎大环线途中的夜色,在日乌且垭口下的海拔4600米平台发现这顶三峰橙色帐篷,此时夏某已遇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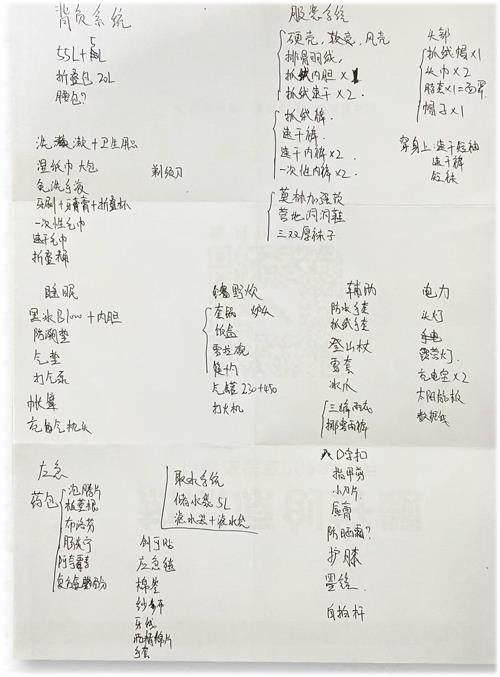
事故分析:最后一根稻草
登顶那玛峰下来后,达洛就听说日乌且出事了,尤其是看到那顶黄色帐篷的照片,他更加觉得不安。两人在双岔河营地互留了联系方式,他的好友申请迟迟没被通过。直到社交平台上曝出遇难者相对详细的信息,达洛终于不得不接受这令人遗憾的事实。
达洛对《户外探险》说,虽然相处时间短暂,但能够感觉到在这支团队里,夏某是最好相处的一位。达洛也觉得或许正是他的实诚的性格,促使他在掉队追不上队友后,依旧在努力追赶。在达洛的观察中,夏某早在4月30日就已出现了高反症状,疲惫赶路的身体加之恐惧焦急感,是否更为加重了他的高反症状?
围绕贡嘎徒步有很多路线,其中贡嘎大环线是比较经典的一条。贡嘎大环线从老榆林水电站出发,经过格西草原、两岔河、下日乌且、上日乌且。这一路可以沿途欣赏田海子雪山、小贡嘎、嘉子峰、日乌且峰等贡嘎周边6000米以上的雪山。从上日乌且出发,翻过日乌且垭口,穿越莫溪沟,翻过玉龙西垭口,到达玉龙西村。其中,从格西草原开始到玉龙西垭口(玉龙西垭口前有一段路有信号),都处于无信号状态。一旦发生高反等险情,呼叫救援很难,而从这里走出去一般都要一两天时间,这对徒步者的身体素质来说要求很高。
有着丰富户外经验的夜色向《户外探险》介绍,他个人认为贡嘎大环属于中高级别的高海拔徒步线,适合有户外长线重装能力,经验丰富,有较好高海拔适应能力的户外爱好者。海拔4900米的日乌且垭口处于贡嘎无人区的中间,也是穿越贡嘎时要翻越的难度最大的垭口。历史上在这里发生的事故也最多。

2008年10月,一名独自穿越贡嘎的户外爱好者,倒在了日乌且垭口下的小溪边,帐篷里还有他没吃的方便面。2016年12月,一位无锡户外爱好者穿越贡嘎途中在日乌且垭口下山到莫溪沟尾营地时遇难。根据现场情况看,遇难者死亡的时间也是在睡觉以后,全身被睡袋包裹,保持着入睡的平躺姿势,面容安详,推断极有可能是由于高海拔缺氧引起的死亡。据当时的报道称,该遇难者生前经常带领队员户外徒步,曾进藏7次,比贡嘎雪山条件更恶劣的地方都去过很多次。
从夏某行前在社交平台发布的内容我们了解到,他为这次出行也做了大量准备,除了装备之外,他还提前了解了高反的成因及如何应对。从他搭建的帐篷及布置来看,夜色认为他具备一定的户外经验。“只是说不是非常丰富,能力不是太强,碰巧又遇到这样的恶劣天气。”但有一点值得注意,这是他的第一次重装,他将这交给了有一定难度的贡嘎大环线。
夜色在该事故发生后对可能存在的原因作了细致的解析,排除了单一发生窒息、失温、一氧化碳中毒、突发疾病的可能,最终他得出的推断是:
5月3日晚上山上的大雪一夜未停,即便天窗打开,因为积雪的原因,帐篷内的氧气也会越来越低,最终导致夏某高反加重而遇难。同时作为第一位发现遇难者并打开帐篷查看的夜色评估,从内帐的痕迹来看,很像肺水肿咯血咳出来的粉红色和白色的泡沫痰凝固体。

而我们也就此事故咨询了中国登山协会高山向导孙涛,他有着近70次高海拔山峰带队攀登经验,并对高原常见风险与野外急救等方面都有深入研究。孙涛评估,从夏某4月29日到5月2日的行进日程来看,突发急性脑水肿和急性肺水肿的可能性并不大。
他分析,首先,夏某完全靠自己的力量穿越了更高的海拔(日乌且垭口海拔4900米),而翻下垭口后,他逐渐走向低海拔,越往下走状态应该越来越好。其次,夏某很合理地搭建了自己的帐篷,如果患有急性高山肺水肿,典型症状是即便在他休息的时候,呼吸也是非常困难的,很难完成弯腰来来回回搭建帐篷的复杂工作。且从搭建起的帐篷形态来看,他应该还拥有非常清晰的判断,否则即便一个风绳没有拉好,帐篷也容易被风掀翻,所以夏某患急性高山脑水肿的可能不是太大。
孙涛分析,压倒夏某的最后一根稻草,导致其死亡的最大原因,很可能是低体温症。低体温症分为急性低体温症与亚急性低体温症,遇难者在当时情况下的发病机制很符合亚急性低体温症:高海拔、低温、低氧的综合环境下对人体能量的需求高,在连续多日的大剂量劳动中,上述几个因素的叠加效应,就很容易诱发亚急性低体温症。
对于夏某来说,连续4天的重装徒步对体能损耗已经非常大,本身的高原反应与开始出现的体能衰竭碰撞到一起,会让他整体表现更差,身体进入恶性循环之中。孙涛推测,低体温症和体能衰竭可能是更大的诱因,此外这些病症也能够诱发其他身体问题,每个人的身体短板都不一样,整个身体系统里哪一个短板崩了,都将是致命的。

作为第一次高海拔重装,夏某的装备总重42斤,出发前,曾有多位户外爱好者在夏某的帖子下留言,认为他的背负过重,建议精简,但他并没有采纳,其中一条留言他这样回复:"其他队友也都是40多斤,希望一切顺利。”
事故发生后,多位户外爱好者对遇难者的装备进行个人分析时也都共同提到了一点:遇难者携带的睡垫可能是最大的问题。山水在采访中表示,在露营时,人体大部分热量是从地面散失的,遇难者携带的充气垫R值仅有1.5,防潮垫基本不起作用,隔热性较差。“当晚又下雪了,加上他本身就有高反,可能是种种因素综合起来的问题。”想到这里山水又说“:他一个人,外面的雪打到帐篷上声音很大,你想想那种恐惧感,随时都觉得自己的帐篷会被压塌。”
但也有很多人认为装备只是风险链中的一环而已,一位博主认为:相比于装备,更大的问题是在于没有安全意识,面对高反没有及时应对和求救。

AA组队,虚假的安全感?
户外爱好者“鹅不食草”从5月5日自老榆林出山后,一直心有余悸,手机有信号时就看到群聊说山上有一人遇难和一人被救援的消息,而5月3日下大雪前,他也是在翻越日乌且垭口路上。
“鹅不食草”入坑徒步仅半年,这次去贡嘎环线是自己的第三次重装,此前他没尝试过高海拔徒步,现在他回想这次徒步也觉得过于冒进,“还是对自己的生命不够负责。”“鹅不食草”说,自己那几天在山上的经历和遇难者也有些相似。在进山后他的身体开始不舒服,但仍在坚持继续走。
5月2日早9点多,在两岔河营地,拼车的队友叫他一起出发,因为前一晚没睡好,他就让他们先走了。因为事先并没有同行计划,他也没具体问队友当天到哪里扎营和后面的计划。接下来的几天行程,“鹅不食草”大部分时间都是独自行进。
5月3日翻越垭口时,他跟在一个陌生驴友后走着,直到五点半时天突然开始下大雪,能见度只能在两米内,前方的背影和地上的脚印都消失了,他又因为看错轨迹走错方向,心中不由生出恐惧。在大雪中跋涉是十分难受的,“鹅不食草”说,自己没法再看清楚前人走过的痕迹,每走一步都得自己开路,雪没到膝盖,直到晚上9点多,他才模模糊糊地找到一处相对平整的地方在大雪中费劲扎好了帐篷。这一夜,同垭口另一侧的遇难者一样,“鹅不食草”也是独自一人窝身在风雪中。

后来“鹅不食草”感慨,他从一开始就希望夏某可以找到有经验的队友,这样他就能安全一点,但后来他想,即便他的队友是经验丰富的,但是没和他走在一起,也是徒劳,这也导致他最后孤立无援。
事故发生后,社交媒体上相关话题的探讨其实一直没有中断。讨论的声音最多就是集中在“约伴”这个话题上。
达洛在谈到队友话题时说道:“他看起来是你的队友,你还觉得很安全,这种假安全其实往往会害你。”也许是和遇难者夏某有过面对面的接触,达洛提到落单的他时,情绪中有着更明显的气愤。“像我之前带队出去,如果到了一个山头,看不见对方,我都会拿对讲机(联系),告诉他我在等高线多少米的地方,我在等你。我觉得像这种(指遇难者所在队伍)隔了两三公里、四五公里,我觉得简直有点难以想象。”
从某种程度来讲,达洛对“组队”是抱悲观态度的,这次在徒步前往那玛峰以及攀登那玛峰的行程中,他都是独行,他说:“当然一个人是很危险的,但我觉得其实不靠谱的队友更不让人放心。”他觉得不应把安全和希望寄托在同伴身上。

关于组队,夜色对《户外探险》说,他个人认为组队成员应当具备独立下撤和独当一面的能力,这既是对团队的负责,更是对自身安全的负责。如果自身能力不够,就要有一个能力强、关系铁的队友相伴,以得到必要的帮助。组队的成员之间应该彼此多交流沟通,及时劝退不合适的成员,同时做好应急预案,以规避风险。同时不建议新人组队高风险线路,应当循序渐进。
对于“组队”,孙涛觉得在不紧密的队伍中,分歧随时可能出现。比如在户外基本安全原则“三新不出行”原则中,如果队伍中存在“新队友”,队员彼此之间对登山户外的价值观认同或许并不一样。面对同一个陡坡,团队中比较有突破精神的队友可能选择继续上,但“躺平”的队友就可能选择不上,此刻因为登山价值观的不同引发的分歧就在山上上演,这样的分歧足以导致小团队分道扬镳。分开后的队伍,力量就会被分解掉,某个队友可能因此落单,一旦因受伤而失去行动能力,就等于完全孤立地被放置山中,失去寻求救援的可能。

查看历年《中国大陆登山户外运动事故报告》,可以发现每年出事故最多的人群依旧是网络约伴人群。孙涛认为这是因为在网络约伴的关系中,大家的责任被默认为是平等的,这种关系在一开始就决定了“我没有豁出命去救你的责任,你也没必要为我付出什么”,在自己也很窘迫的情况下舍己救人,这是一个很高的道德标准。你的选择会是什么?
类似的新闻并不少见。2023年四姑娘山就曾发生一例队友疑似高反、低体温被另一个队友抛弃在山上的事件,同年发生的“勒多曼因山难”,队友消极救援,留下一位大学三年级的年轻生命在雪山上苦等救援,最后绝望地走向了死亡。
或许当我们没处于同样的位置,就没有资格站在道德制高点进行批判,“相信在那样大雪低温的情况下,尤其是连续多日高海拔徒步后,他们每个人都不会像此刻你我坐在办公室里拍着胸脯说‘某某人,你要是怎么了,我会为你付出生命。”孙涛说。

“搭档”一词最初来源于极限登山运动,真正的登山搭档都是将生命系在一条登山绳上。搭档之间的行为有着道义和责任的自我约束。从极限登山到高海拔登山徒步,“搭档”一词也在随着社会大环境而发生变化,更准确来说,是逐渐淡化。随着泛户外的发展和社交工具的扁平化发展,现在的约伴更多是出于便利或经济的需求,例如拼车或拼房。
从“搭档”到“搭子”,曾经生死托付的户外搭档已经走向Z世代交友的语境,在这样的大环境下,每个人在山上给出的答案也就不一样了。
对于进入户外13年的夜色来说,“无兄弟不登山”的精神是渗透在骨血里的。“一起来就一起走,带出来就要把他带回去。”他表示或许是价值观的不同,有人认为完成一条线路更有意义,有人认为如果同伴遇到了什么事情,这个成就也就没有意义了。
回到5月2日,翻过垭口的那一天,遇难者队友发了这样一条朋友圈:“成功翻过垭口的那一刻,真的太为自己自豪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