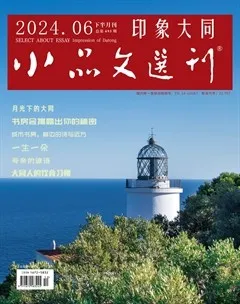谁是《故乡》里的小偷?
2024-06-27胡洪侠
胡洪侠

小时候中学或师范的语文老师讲鲁迅《故乡》,犹如政治老师上思想教育课,大道理满天飞,满堂灌,任由我们昏昏欲睡。他们从来没有讲过,《故乡》的出现标志着鲁迅的文学创作进入了成熟期。也标志着“中国开始了本质意义上的现代化”。这是日本学者藤井省三说的。
在《鲁迅<故乡>阅读史》一书的《引言》中,藤井教授还说,1921年《故乡》发表不久即编入中学国语教科书,1923年收入《呐喊》一书问世,更引起广泛讨论。1949年后,《故乡》又用阶级斗争观点解释,承担起了思想政治教育功能。
《故乡》一百年,读者人数少说也有十几亿了。不同时期的读者,对《故乡》读法大为不同。藤井认为,以此角度观之,《故乡》的文本其实不断被改写,一直在更新。
1927年《故乡》就已译成日文,“获得读者的数量之大异乎寻常”。1957年《故乡》开始进入日本中学国语教科书,到197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之后,日本所有的国语教科书都收入了《故乡》,“就是说,”藤井写道,“《故乡》虽然是外国文学作品,日本人却将其当作‘国民文学对待。”
从“阅读史”角度研究鲁迅作品,是近三十年前藤井先生在鲁迅研究上的方法创新。这一方法不仅要关注小说文本的诞生,还要研究小说问世后的传播、评论与接受。更为重要的是,《鲁迅<故乡>阅读史》分别考察了民国时期、新中国初期和改革开放时期中国语文教材中《故乡》的教学、讲解与争议等情况,并以“事实的文学”与“情感的文学”为分析框架,梳理出了《故乡》在政治潮流中的沉浮轨迹,深具原创性与启发性。
最有趣的纷争焦点是:到底谁把碗碟埋进了草木灰里?闰土,还是“豆腐西施”?
《故乡》相关段落如下:
我和母亲也都有些惘然,于是又提起闰土来。母亲说,那豆腐西施的杨二嫂,自从我家收拾行李以来,本是每日必到的,前天伊在灰堆里,掏出十多个碗碟来,议论之后,便定说是闰土埋着的,他可以在运灰的时候,一齐搬回家里去;杨二嫂发见了这件事,自己很以为功,便拿了那狗气杀(这是我们这里养鸡的器具,木盘上面有着栅栏,内盛食料,鸡可以伸进颈子去啄,狗却不能,只能看着气死),飞也似的跑了,亏伊装着这么高底的小脚,竟跑得这样快。
老屋离我愈远了;故乡的山水也都渐渐远离了我,但我却并不感到怎样的留恋。我只觉得我四面有看不见的高墙,将我隔成孤身,使我非常气闷;那西瓜地上的银项圈的小英雄的影像,我本来十分清楚,现在却忽地模糊了,又使我非常的悲哀。
我忘了学《故乡》课文时老师是怎么讲的了。藤井先生的这本书能够告诉我们:“谁是小偷”的问题颇为复杂,先是1924年10月,诗人朱湘在评论中提出了“闰土=小偷”的看法,之后左翼文学成为主流,朱湘的说法成为禁忌。1949年之前,没有人再追究“谁是小偷”的问题。
1954年,徐中玉教授在评论文章中反对把闰土当作中国农民坚韧性格的代表,又说闰土在灰堆中藏了十多个碗碟,是自私、麻木的农民代表。于是,争论浮出水面,1955年,有人反驳“闰土=小偷”,说硬把这件罪名加在闰土头上,破坏了《故乡》的艺术完整性和思想深刻性。到了1959年,李霁野又写文章说,鲁迅文中并未指明谁是小偷,一定要追问“到底闰土埋了没有”就是钻牛角尖了。
同年北京出版的语文教学参考书也持类似看法:
关于碗碟埋在灰堆里究竟是否闰土干的,学生常常发生疑问。根据原文,作者也不曾肯定地暗示是谁埋的。但有三种理由可以证明不是闰土埋的:(1)前文说:“凡是不必搬走的东西,尽可以送给他,可以听他自己去拣择。”闰土既然拣了那么多东西,再挑几个碗碟也是会被允许的,何必要藏起来;(2)再就作者所创造的闰土的形象来说,他前后的变化虽然很大,但就其品质来说,是完全统一的;(3)再就母亲谈话的口气来说,母亲也是不以为然的。但也不要使学生单只痛恨杨二嫂,应把学生的爱憎从个别人物身上转到整个社会制度上去,因为这种事情在旧社会是常常发生的普遍现象。
可是,钻牛角尖的人从不匮乏。1960年的时候,“杨二嫂=小偷”的声音出现了。1987年的时候,杨二嫂又给恢复了名誉,成了“劳动人民”,而“闰土=小偷”的观点又复活了……
此刻我想,千千万万中学生在《语文》课本上学习的《故乡》、听到的讲解,还是鲁迅的作品吗?《故乡》原本是乌蓬船底的一碗水,一进入教材,就成了封装在玻璃瓶或易拉罐中的饮料,味道变了,瓶子上的标签又变来变去,纵使唤醒鲁迅于九泉之下,请他到课堂上讲解自己的《故乡》,他一定也张口结舌,难免四顾心茫然,感叹道:我竟与自己的小说隔绝到这地步了……
选自“夜书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