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最后600天(十五)
2024-06-26顾保孜
顾保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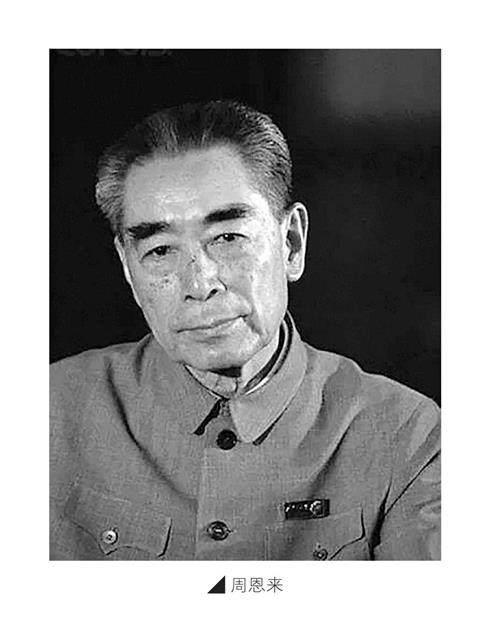


难以回天
周总理病危以来,医疗组多次商定各种应急方案,同警卫及服务人员召开了联席会议,大家明确了一旦进入抢救状态后的分工。
周恩来虽然已有两个多月不能进食,但肠道内仍有自身分泌的液体,还有留下的少许残渣,加之体内恶性肿瘤细胞和各类致病菌迅速地生长繁殖、不停地进行新陈代谢而产生毒素,这些复杂且有害的物质造成肠道麻痹,让本已处在高热状态的周恩来又增加了“肠麻痹”,使得他腹部胀满,疼痛难耐。
为此,在1976年1月5日凌晨,医务人员为生命垂危的周恩来做了最后一次手术,即在左下腹部开一个口子,将肠道里的“残渣余孽”尽量清除出去,但这个手术对于病情没有任何帮助,只是暂时缓解一些身体上的痛苦。
1月7日,周恩来病情继续恶化,气息已变得十分微弱,长时间处于昏迷状态。医疗组成员、护理人员等昼夜守护在病房,随时准备抢救。深夜11时,弥留中的周恩来从昏迷中苏醒。他微睁双眼,认出守在他身边的吴阶平大夫,用微弱的声音说了最后一句话:“我这里没有什么事了。你们还是去照顾别的生病的同志,那里更需要你们……”这时他说话已经不太清楚了,但大家还是听明白了。
周恩来说完这句话,一直睁着眼睛,老是看着门口方向。值班医生就问:总理啊,你有事吗,你还是找大姐?大姐已经走了。
周恩来晃了晃脑袋,意思说没事,不找了。但他就这样睁着眼睛一直到晚上12点也不睡觉。张树迎、高振普等警卫们还以为周恩来病情好转了,都情不自禁高兴起来。可是医生们却紧皱眉头,一点欢喜的情绪都没有。
按照中国民间的说法,这是回光返照。不是好兆头。
事后,大家十分后悔。那天晚上周恩来心神不定,眼睛来回看,一定是在找邓颖超。当时谁也没有意识到这是总理生命的最后一刻,没有想到要把邓颖超喊过去。结果这对经历了半个世纪风雨的革命伴侣没能见上最后一面。
日历翻到了1976年1月8日这一天,正好是农历腊月初八。俗话说“腊八腊八,冻掉下巴”,正是数九寒冬滴水成冰的时节。本是每天上午8点钟医疗组全体人员开交班会,医院里人们常称此为“早会”的时间,这一天7点40分大家已集合在小客厅里,主治医生吴阶平主持了交班会,值夜班的医生和护士详细地报告了周总理夜间的病情、治疗、睡眠状况、醒来次数、有何不适等情况。由于总理的病情已经进入最后关头,每个人都更加细心、紧张。因此除了早会,大家一天要碰头多次,只要发现一点新情况就随时讨论,提出治疗意见与需要注意的事项。
早会后,张佐良走进病室,在心电示波仪旁看了一会儿,没有发现异常变化,再到总理床边,见他仍安静地仰卧在床上,眼睛闭着,脸色灰暗,嘴唇有点青紫,呼吸轻而快,每分钟有三十多次,脉搏虽然有九十多次,但细弱无力。
张大夫觉得情况不太好,当即将情况报告给了心脏病专家与麻醉科专家。他们决定通知所有专家到场,吴阶平等所有医护人员迅速赶到了周总理的身边。这意味着抢救周总理生命的紧张工作即将展开。
这一天正好是高振普值班,因为他以前听医生们说过,人要是不行了,手先发凉,从总理进入病危阶段,他一到总理床边,就习惯性地先摸摸他的手。要是暖和,他的心就踏实一些;要是凉,他会马上喊医生……
8日这天一早,说也奇怪,他摸总理的手并不冷,而且还暖暖的。因为他一夜没合眼了,就准备去休息一会儿,可没有走出三四米,就听见身后的电铃响了。这个电铃在紧急情况下才会使用。高振普一听这电铃声,心想不好,赶紧返回去。这时大夫也都跑了过来,一进病房就赶紧看周恩来的心脏监护器,眼看着快速跳动的光波,由一百四一下就掉到了一百三,几乎就在一分钟之内,心跳频率直接掉落到七十以下。
谢荣教授来到周总理床旁,看到总理的病况,他立刻提出要做气管内插管,并要张佐良向总理报告,征得他的同意。当时张佐良暗想,总理已处在垂危中,神志已经不清楚了,即使清楚,哪还有什么力气向我们表示同意或是反对呢?
张佐良尽管这么想,但还是按专家的要求去做。他弯下身子,将嘴贴近总理右侧耳朵,提高嗓音说:“总理,您的气管被黏稠的痰堵住了,阻碍呼吸,氧气进不去,很危险。谢主任要求马上给您从鼻孔插一根橡皮管进去,把黏痰吸出来,再大量输入氧气,就好了,您同意吗?您如果同意,请您点点头,或者睁一下眼睛。”
张大夫说这话时,满屋子的人都屏着呼吸,凝神注视着周总理的反应。
谁也没有想到,周恩来真的被张大夫叫醒了,他不但睁开了眼睛,还微微地点了一下头,表示同意。
大家的心一下又升腾起来,只要总理心里明白,还有求生欲望,那一定能抢救过来!
谢教授立即将早就拿在手里的橡皮管迅速准确地插进了周总理的右鼻孔,开动吸引器马达吸痰,但只听得橡皮管里的咝咝声,未见到吸出多少痰液。谢荣果断地改用稍粗一点的管子插入气管,又吸了些痰出来后就用手不停地、使劲地捏一个大黑皮球,进行加压吸氧,并进行体外心脏按压,希望用这样的方法挽救总理的生命。
抢救在继续,但是奇迹却没有出现。经过加压吸氧、体外心脏按压后,仍看不到病情有所转机。大家刚升腾起来的希望又一点一点地破灭了。专家们一个个双眉紧锁、神情紧张,看来真的到了药石不医、难以回天的生命终点了。
张佐良一直握着周总理的右手,感觉到总理的脉搏愈来愈细弱,只见心电图示波仪上的曲线波发生了明显变化,从六十一下子到了四十,没过几秒,掉到二十,最后心跳曲线拉成一根直线,一下也不跳动了。
周恩来的脉搏停止了跳动,慢慢地,手臂的皮肤也变凉了……
心电图上画直线后,抢救工作又进行了十多分钟。至此,吴阶平看了下手表,同几位专家交换了一下意见后宣布:抢救工作可以停止了,把那些东西都撤掉,并嘱咐护士把总理的脸擦干净,整理好床铺,用新床单将总理全身覆盖起来……
还没有等到吴阶平说完话,突然有人扯着嗓子,大声呼唤:“总理!总理啊!总理!你醒醒啊——”
这声音把大家压抑很久的悲伤唤醒,悲痛的感情一下子爆发了,整个房间里哭喊声一片,大家边哭边喊:总理,你醒醒啊……
这悲伤的哭声中,邓大姐的哭声格外令人心碎……
她接到通知来到医院时,周恩来已经停止了心跳,尽管还在继续抢救,但那已是无济于事的抢救程序。
这天上午8点,医院一上班,邓颖超就让赵炜给医院打个电话问问情况。8点时总理情况还在正常范围内,于是高振普回复说:还行,一切正常。于是,8点半邓颖超开始吃早饭,她一连几天都是很晚从医院回来,觉得十分疲劳,她对赵炜说,今天我上午先不去了,下午再去。没有想到,邓颖超刚吃完早饭,赵炜就接到高振普从医院打来的电话:总理不行了,正在抢救,快来!赶快来!
赵炜只觉得自己脑袋“嗡”的一声,知道事情严重不妙。她赶紧到邓颖超的屋里,这时邓大姐吃完早饭正在刷牙,她看见赵炜神色紧张,便问怎么了。赵炜一下子想起此时不能加重邓大姐的精神负担,于是她努力装作平静的样子说:“小高打电话,要我们马上到医院去。”
邓颖超因为之前也有过数次被紧急叫去的经历,似乎没有意识到这一次是周恩来生命中的最后一次紧急通知。尽管西花厅距离三〇五医院很近,只要十分钟就可以到,但在车上短暂的时间里,赵炜非常冷静,她觉得应该给邓大姐一点暗示,万一总理抢救不过来,让她有个思想准备。她告诉邓颖超:“刚才打电话来,说情况不好。”
邓颖超扭头望着赵炜,一下子全明白了,一下汽车,就一路小跑奔向病房。
推开病房的门一看,屋里所有的东西全都撤了,只有茶几上大夫进行抢救的机器还在。工作人员都已经站在靠墙的一边哭得上气不接下气,再看拉成一条线的心电图光波,邓颖超知道自己来晚了!她不顾医护人员还在抢救,三步并作两步一下子扑倒在周恩来身上,边哭边喊:“恩来!恩来!我来晚了……”
周恩来好像沉睡一般安详。自此,历经三年半患病的周恩来解脱了所有的痛苦,解除了所有插在他身体上的管子,也结束了将近六百天困卧病榻的苦难岁月。
原本隐忍的哭声顿时成了一片号啕大哭。邓颖超哆嗦着双手摸着周恩来的面颊,轻轻地吻了一下他的额头,无限哀伤地说:“恩来,你走了……”
随后,一床崭新的白色被单将总理覆盖住。
专家、医生、护士和周总理身边的工作人员抽泣着,依依不舍地离开了病床,大家都站到房间边上去,为党和国家领导人向周总理遗体告别腾出空间。
大家担心邓颖超一直这样悲伤,会引起她的心脏病发作,于是几位护士过来将她搀扶到病室隔壁的房间里,先休息一下,以节省体力应对下面更加繁重的后事活动。因为待会儿中央领导人陆续到医院来向周总理遗体致哀与告别时,邓颖超必须亲自守候在旁。
上午11点,中央领导人陆续到齐。邓颖超向在场的中央领导转述了周恩来生前提出的三点要求:一,不保留骨灰;二、后事处理不要特殊,不要超过任何人;三、不要开追悼会,不搞遗体告别。邓颖超说,周恩来的丧事一切由组织决定,她个人没有什么意见和要求。
听完邓颖超的意见,李先念第一个提出反对:不行,不开追悼会不能拿总理来开刀。这样的话我们没法向全体人民交代。李先念的反对立刻得到领导们一致赞同,认为就是改革悼念形式,也不能从总理身上开始改革。
领导们讨论的结果是,不仅追悼会要开,遗体告别也要搞,至于骨灰是否保留,需要经过毛主席批准。
中午11点多,按照事先商定的方案,周总理的遗体被抬到救护车上,被送至北京医院太平间存放。
在中央没有宣布周总理逝世的消息之前,尽管上面强调保密,出动的车辆不多,人们很守纪律,然而,周总理住院一年零七个多月,医疗组、警卫与服务人员等成天忙于工作,围着周总理转,到各单位及医院办事行色匆匆……多少还是让外人看出了苗头。所以,周总理逝世的消息还是迅速传播到了社会上。
剖肝泣血
1976年1月8日中午,周恩来遗体运到北京医院太平间后,医护人员和警卫、秘书兵分两路,分头处理后事。第一路即医护人员要对周恩来的遗体进行解剖,第二路即身边工作人员要去为周恩来准备寿衣与骨灰盒。
遗体解剖,也是周恩来的遗愿。他曾说过,希望他死后,医院要做病理解剖,以利于弄清楚癌症的发展和其死亡原因,为医学事业作最后的贡献。负责遗体解剖的北京医院副院长韩宗琦回忆:
当人们慢慢将被单掀开,露出总理消瘦的面容和腹部的几处手术伤疤的时候,大家的心里都十分难过,当报告各个主要的脏器都有癌瘤转移的时候,有人再也忍不住哭出了声音。
此时医生们犹如剖肝泣血,他们都知道癌症后期,病人一般都是在剧痛煎熬中咽下最后一口气的,可想而知,浑身布满肿瘤的周恩来在生命的最后几个月里忍受着怎样的剜心之痛!
遗体解剖后,接下来就是理发、化妆整容、穿衣等善后工作。
前面已说,北京饭店的朱殿华师傅一直想为住院的周总理理发,都被周总理婉拒了。直到1976年元旦前,他还托人捎来口信说要为总理理一次发,让他干干净净过新年。可周恩来想了想,还是拒绝了朱师傅的好意。他不忍让为他理了二十多年发的老师傅看到自己重病的模样。结果周恩来整整八个月没有理发、刮胡子。而周恩来历史上就是出了名的大胡子,甚至大家曾叫他“胡公”。红军长征时,他曾有过八个月不修理胡须的记录,那时年仅三十六岁的周恩来征战硝烟,配上一脸兜腮长胡,颇有英雄闯荡江湖之豪气。然而此八个月非彼八个月,病魔折磨得只剩下一把骨头的“胡公”,只能任凭头发与胡须蓬乱地生长。唯一能做到的,就是尽量不让熟悉他、爱戴他的人们看见他此般模样。
直到周恩来逝世,朱师傅才接到了去理发的通知。他说什么也不相信这个噩耗,眼前这个“脱了形”的总理他几乎认不出来了。
韩宗琦医生在一边千叮咛万嘱咐:千万千万,多涂肥皂,刀子弄快一点,手法轻一点,千万不要把总理的脸给刮破了任何一点。
可是朱师傅无法接受周总理离世这个现实,他的手颤抖起来,拿着的刮胡刀好似千斤重。他只能让徒弟上手,动手前他嘱咐徒弟:以前,我给总理刮胡子要抹几次肥皂沫,热毛巾闷好几遍,使胡子软和了才能刮下来,现在不能用热毛巾闷了,不然皮肤的颜色会发紫,化妆时去不掉,不好看。这一说不要紧,徒弟的心理压力更大了,加之难度又这样高,徒弟的手哆嗦得不比自己师傅轻多少。徒弟围着周恩来的遗体转了几圈,也是下不了手。
朱师傅看到这种情况后,决定这最后一次为总理整容理发还是由他亲手完成。朱师傅握着一把刮胡刀,望着周总理的遗容,心里好似翻江倒海。他抹了一把眼泪,稳了稳神。以前周总理总是利用理发的短暂时间补充一下睡眠,朱师傅基本都是在总理的鼻鼾声中完成理发工作的。这一次,他望着周恩来沉睡的脸庞,似乎又找回了以前的感觉,他熟练且麻利地修剪头发,再在僵硬了的腮帮上轻轻地刮去胡子……不大一会儿,周恩来的脸上干干净净,没有一处破损。
朱师傅完成了一个高难度的整容任务。他直起腰,望着周总理,眼泪又流了出来,因为他知道,这是他最后一次为总理理发,也是最后一次看到总理的面容。他在打扫地上头发时,特意将一缕灰白的头发悄悄地收了起来,他想保存起来以寄托自己的无限思念。如果这缕头发还在,那应该是周恩来唯一留存在世的身体之物了。
在朱师傅为总理理发时,卫士长张树迎和卫士高振普等人也从西花厅把总理的衣服找来了。当时邓颖超明确地告诉卫士们,不要做新衣服,要选总理平时最喜欢穿的、现有最好的衣服。结果工作人员在周恩来穿过的所有衣服里找来找去,不是太旧就是有补丁,内衣和内裤也几乎没有不打补丁的。最后选了一套周恩来冬天穿的灰色中山装,虽说旧了些,好歹没有补丁;一件布衬衣,也已穿过多年,不过换了领子和袖口。这几件衣服,有的穿了几年,有的甚至穿了十几年。
当他们把衣服选好后请邓颖超认定时,邓颖超含着眼泪点点头说:“这是恩来的作风,平时为他添置一件衣服都很难,他死后咱们还是要尊重他,不要为他浪费钱了,新的旧的都一样,最后一把火都要烧掉的。这样做也许有人会责怪你们,那也是暂时的。”
工作人员把准备好的衣服,用一块使用多年的紫色布包好,送到了北京医院。理发整容后就该穿衣服了。韩宗琦接过包袱,打开一看,顿时就火了,这些衣服竟然没有一件是新的。衬衣太旧了,除领子和袖口还显得白一些,其他地方都已发黄,显然是换过领子和袖口的旧衬衣。于是他问可否换一件,得到的回答是:这是最完整的一件了。
他不禁气愤地冲着周恩来的卫士们喊道:“你们这是什么意思?你们想干什么?怎么拿来这样的衣服?为什么不做新的?……我自己出钱给总理做行不行啊?……你们跟总理那么多年,你们对得起他吗?”
张树迎、高振普等人听着他的这番指责,无话可说。因为他们知道韩宗琦的父辈和周恩来、邓颖超有深厚的交情,从韩宗琦管邓颖超叫“邓姨”,就可见两家关系不同一般。周恩来去世对于韩宗琦来说,也有着失去亲人一般的切肤之痛。
韩宗琦从小就认识邓颖超,他的母亲和邓颖超曾是天津女子师范学堂的同窗好友。在抗战期间,韩宗琦的父亲在重庆开牙科诊所,一家住在重庆,周恩来和邓颖超在重庆八路军办事处忙于国共合作。他们两家同居一地,经常往来,就连韩宗琦父母在上海居住的房子也是周恩来转让给他们居住的,而且这种友谊一直保持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1950年,二十七岁的韩宗琦子承父业,已经是天津医学院附属医院口腔科主任医师了。那时起他开始做周总理的口腔保健医生。由于频频来京出诊,加之他的镶牙技术越来越精湛,中央首长们也随着年纪增大,口腔保健的需求量越来越大,于是他1974年被调到北京医院担任副院长,成为一名为首长服务的口腔专业方面的专家。
这一次,他主动请缨,要求负责周总理的后事。某种意义上这已经不完全是出自一个医生的职责,而是他觉得自己是晚辈,应该尽自己的孝道。事后,邓颖超很感慨,对他说:“我们这辈子没儿没女,想不到恩来倒得了你的济了。”
“得济”,在北方被认为是一种孝道。所以韩宗琦能为世人爱戴和敬仰的周总理做最后的事情——遗体解剖、整容、穿衣、布置灵堂并一直守候在灵前,让他欣慰终生。
其实,韩宗琦的痛也是张树迎、高振普他们这些日夜跟随总理身边,不是亲人胜似亲人的人的痛。韩宗琦的不愿意也是他们的不情愿。正像邓颖超说的那样:这样做也许有人会责怪你们,那也是暂时的。
韩宗琦渐渐平息了火气,他也知道,总理最后连一件新衣服也没有,卫士们心里也很难受,也很不是滋味,冲他们发火也没有用。
后来韩宗琦知道这是邓颖超为尊重周恩来生前节俭的习惯,不得已而为之。他这才无奈地收下了“寿衣”。
穿衣的时候,韩宗琦看见周恩来手腕上那块20世纪50年代生产的“上海牌”国产手表还在嘀嘀嗒嗒地走动着。他含着眼泪将表摘下,一看手表的表带坏了,是用白布带子代替的,表盘也已发黄,只有指针还在顽强地走动着,而且分秒不差……
韩宗琦决定留下这块手表和那枚长方形的“为人民服务”的毛主席像章。他留下手表是想留给人们看那白布表带和已经发黄的表盘,留下像章是想自己作个纪念。如今,这两件文物都陈列在天津周恩来邓颖超纪念馆里。
换完衣服,该最后一项了——化妆。
由于长期遭受疾病的折磨,周恩来已经非常消瘦,眼眶和两颊塌陷得都很厉害。对于总理的整容,邓颖超曾经对韩宗琦专门作过交代:“不要把恩来整理得像擦胭脂抹粉这种,要带一些病容,因为他是病了那么久的一个人。”
夜间11点,经过理发、穿衣、整容及化妆后的周总理遗体被安放到北京医院那间不足一百平方米的房子里,前面没有过道,一扇门直通户外。总理遗体停放在屋子中间,四周放着塑料盆花,紧贴四壁放着几层花圈。除了站立几个守灵人员,所剩空间仅够吊唁者成单行走一小圈了。
这个条件十分简陋并且十分狭小的太平间,将是首都各界人士向周恩来遗体告别的灵堂。
邓颖超来到灵堂,她流着眼泪,满意地点了头。特别是周恩来的遗容,没有上胭脂,只是上了一点点色,看起来虽然带有生病的样子,但神态十分平静,就像安睡一样。
紧接着,西花厅的工作人员与周恩来治丧办公室的同志一起去八宝山革命公墓选购骨灰盒。那里的负责人拿出两种骨灰盒来,一种装饰性的东西较多,价钱较贵;另一种便宜,花色也可以。他们觉得贵的那种显得不太素雅和庄重,便决定依据周总理和邓大姐的喜好买那种便宜的。不想那便宜的当时只剩两个,一个掉了一块漆皮,一个是漆皮完整,但盒盖不太好用,开起来有点费劲。他们想骨灰装进去后是不会经常打开盖的,就选择了漆皮完整但开合不便的骨灰盒。
回来后,张树迎和高振普向邓颖超汇报,并请她过目。邓颖超说:“不用看了,全权委托给你们了。骨灰盒只是一种形式,没必要那么讲究。”
的确如此,骨灰盒对于周恩来来讲可能就用几天,追悼会后,他的骨灰就要撒向天空……所以,谁也无法改变这个结果。
为避免大批亲属来京参加吊唁,邓颖超特意口述了一封电文,告诉外地的亲属们听到总理逝世的消息后不要来京。电文大意是:人已经不在了,亲属来了非但没有什么意义,反而是一笔浪费,还不如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努力工作,这才是对死者的最好纪念。她还交代说,“等我死的时候也不许他们来北京”。就这样,周恩来家乡淮安与其他地方的亲戚们接到电报后,按照邓颖超电报的意思都没有进京吊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