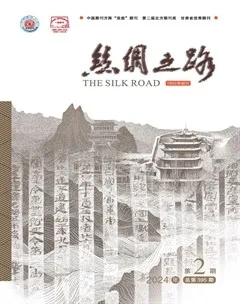敦煌莫高窟洞窟内容调查研究
2024-06-26吕晓菲李燕飞李荣华
吕晓菲 李燕飞 李荣华



[摘要] 1943年,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筹备委员会成立,莫高窟洞窟内容调查工作正式启动。截至1976年,文物研究所初步摸清了莫高窟洞窟的数量和内容,完成了492个洞窟的编号,并开展了石窟档案记录工作。1995年,敦煌研究院完成了北区735个洞窟的编号及洞窟调查工作。通过对1976年之前的洞窟调查档案进行梳理可以发现,莫高窟洞窟内容调查频次很高。莫高窟洞窟内容调查是一个不断完善、循序渐进的过程,包括最初的洞窟编号,之后的考古分期断代、造像和壁画研究,直至形成最后调查成果——《莫高窟石窟档案》。这一成果是对几十年来莫高窟洞窟调查工作的总结,也是落实文物科学保护的重要措施。
[关键词] 敦煌莫高窟; 洞窟调查; 档案资料; 《莫高窟石窟档案》
[中图分类号] K870.6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5-3115(2024)02-0061-10
20世纪初,法国、英国、俄国等国外探险家相继来到莫高窟,对莫高窟文物进行盗掘,期间他们还对洞窟内容进行了调查,这些调查成果的公布引起了外界的广泛关注。1922年,周炳南、高良佐等爱国人士认识到莫高窟的重要性,开始对莫高窟壁画进行调查,但这些调查都是零星的、碎片化的。1944年,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成立,结束了莫高窟无人看管的混乱状态,莫高窟的管理、保护、研究等各项工作得以逐步展开,具体包括清理淹没洞窟的积沙、开展洞窟内容调查等。莫高窟壁画数量庞大、内容丰富,壁画内容的调查比较复杂。1943-1976年,为系统摸清莫高窟洞窟内容,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多次组织人员进行调查。截至1998年,敦煌研究院完成了对莫高窟石窟的总体调查,并将调查结果汇总为《莫高窟石窟档案》。由该调查结果可知,莫高窟有壁画、彩塑的洞窟为492个,壁画面积35678.16平方米[1]。洞窟调查是一个不断认识、不断更新的动态过程,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洞窟内容也经过多次修订,目的在于尽可能准确释读洞窟内容。
自2021年开始,笔者有幸参与了档案资料的整理工作,对莫高窟历年壁画调查进行了系统梳理。早期洞窟调查结果均以手稿形式呈现,记录着莫高窟洞窟的信息和调查的历史过程,也见证了当时的社会状况。这些资料是后世研究的珍贵史料,也是学者们研究莫高窟的第一手资料。
一 、莫高窟洞窟编号情况
洞窟编号是石窟调查研究和档案记录的基础[2]。莫高窟建窟之初,洞窟以窟主姓氏或主尊名号命名,如翟家窟、文殊堂等,大部分洞窟都没有名称。要调查洞窟内容,首先要摸清洞窟数量,现对早期莫高窟编号情况作一回顾。
20世纪初,外国探险队进入莫高窟,为满足洞窟内容调查需要,对莫高窟的建筑、雕像、壁画进行了摄影及测绘等调查工作。1907年,英国人斯坦因编号18个[3];1908年,法国人伯希和编号328个[4]。1922年,敦煌官方编号352个;1935年,高良佐编号207个;1941年,张大千到达莫高窟,因临摹及研究需要,编号309个。
1943年2月,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筹备委员会在兰州召开第二次会议,制定了《敦煌千佛洞安西万佛峡保管办法》,其中第六条规定:“千佛洞及万佛峡所属各洞应逐一编号,并注明所在位置及洞内一切古迹古物之名称、尺寸、大小,附列照片,编制专册,分存教育、内政两部,中央古物保管委员会、甘肃省政府及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5]
1943年3月,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筹备委员会在常书鸿先生带领下在莫高窟展开工作,史岩在张大千的基础上进行学术调查研究。继史岩之后,1944年,李浴又在张大千的基础上增至437个编号[6]。
1947-1948年,鉴于洞窟编号次数多且编号不完善,常书鸿所长带领霍熙亮、李承仙、孙儒僩等对洞窟进行了全面调查编号,这次调查包括洞窟编号和年代记录。洞窟编号起于莫高窟南区北端,按照由北向南、自下而上的顺序逐窟编号,共编号465个,其中南区460个,北区5个(第461-465窟)[7]。
1949-1966年,研究所集全所之力清理莫高窟南区被积沙封堵掩埋的洞窟,完成了南区所有洞窟的清理和调查工作,洞窟编号增至492个,此后一直沿用这次编号。此次调查采用了雕版印刷的调查登记表,不仅登记了研究所编号、张大千编号和伯希和编号,还记录了壁画和塑像的原修年代和重修年代以及洞窟清理出土的时间,如第480窟清理出土于1953年9月20日(图1)。孙儒僩先生设计、制作了纸质窟号标识牌,洞窟首次有了身份标识,至今部分洞窟还保留着纸质窟号标识牌,窟号标识为文物研究所(A)、张大千(C)、伯希和(P)。
1988年6月至1995年11月,彭金章先生主持进行开展莫高窟北区洞窟的考古发掘,首次对北区洞窟进行了编号。北区洞窟按照由南向北、自下而上的顺序编号[8],洞窟编号共计243个(不包括已编第461-465窟)。至此,敦煌研究院完成了莫高窟南北区所有洞窟的编号,并最终确认莫高窟共有735个洞窟。
莫高窟洞窟体量大,不少洞窟中还开凿有一个或多个小窟(龛),虽然部分窟龛无壁画及塑像,但有一定的考古价值。2003年,时任敦煌研究院樊锦诗院长和蔡伟堂先生对敦煌文物研究所漏编的33个窟龛进行了补编。这些窟龛编号用A、B、C标识,如第22窟甬道南壁小窟,编号为第22A窟,这次补编进一步补充与完善了莫高窟窟龛编号[9]。
二 、莫高窟洞窟内容调查
洞窟内容调查是对石窟寺洞窟所包含的造像、壁画、建筑等信息的客观记录。通过调查石窟壁画、造像、题记、发愿文等内容,为之后的石窟档案、石窟保护和研究等工作奠定了基础。
(一)塑像及壁画内容调查
1943年,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筹备委员会的工作人员到达莫高窟,常书鸿组织人员开展莫高窟洞窟内容的调查工作。当时经济条件差,调查形式与内容都比较简单,卡片用黄麻纸制作,规格为12.3厘米×7.4厘米,分壁画调查卡及塑像调查卡(一洞一卡或一洞多卡记录),部分卡片上部打有小圆孔,内容用钢笔、铅笔或毛笔抄录,部分文字有校对修改的痕迹。调查内容包括洞窟年代、造像和壁画情况。壁画按照南壁—北壁—东壁—西壁的顺序依次记录,塑像记录佛龛造像的名号、数量、保存状况,并据此绘制塑像分布草图。这次主要调查了张大千编号洞窟309个,并附伯希和编号(图2):
壁画卡片如下:
第四十二窟 P74 五代
南壁:上部报恩经变、法华经变、西方净土变、弥乐经变、下边女供养16身,经变故事13幅。
北壁:上部思益梵天请问、法华经变、药师经变、天请问。
东壁:维摩诘经变(南文殊、北维摩)。
西壁:劳度叉斗圣,下经变故事十六幅。
窟顶:四角四天王,四方中央说法各一铺,贤劫千佛,藻井图案。
背屏:后为接引菩萨一尊。
窟口:南壁男供养人十六身,顶接引菩萨一尊,一天王。
塑像卡片如下:
第四十二洞 清塑
一弥来佛二弟子,
二弟子前胸和裙子颜色已脱落,
全数完整。
1955年,在之前基础上,文物研究所工作人员对莫高窟洞窟内容展开调查、修订。调查使用细腻白纸手工印制的调查表,尺寸为39厘米×27厘米;具体信息用钢笔填写,一窟一表。调查内容包括洞窟朝代、壁画、塑像、题记四部分。洞窟朝代包括始建和重修时代,壁画按照前室及入口、主室东壁—南壁—西壁—北壁—窟顶—佛龛的顺序记录,塑像记录佛、菩萨的身份,题记摘要记录。调查结果汇编成《莫高窟内容说明(1955年重订)》(图3、图4)。这次调查洞窟480个,与1943年调查相比,内容更加翔实,突出壁画信息,清晰抄录每个壁面内容以及供养人数量,为相关学术研究提供了第一手资料(表1)。
敦煌研究院工作人员在长期临摹、考察、研究过程中,对洞窟内容的认识不断更新和深入。他们认为前期内容调查过于简单,不能客观反映洞窟全貌。为此,1962-1963年,欧阳琳、万庚育、李其琼、霍希亮、孙儒僩等分头调查壁画内容,重新填写洞窟卡片,取得了可喜成果。20世纪60年代,国家处于困难时期,用于记录调查结果的纸张质量大不如前,使用的调查表是在粗糙麻纸上手工绘制的。调查内容如下:洞窟年代(壁画、彩塑、建筑的原修时代及重修年代),建筑,壁画,塑像,洞窟尺寸、面积,地面,窟内各壁面、龛、顶、中心柱等的展开示意图,塑像名称及数量,塑像位置图,题记。调查按建筑、前室、甬道、主室四壁、窟顶、佛龛、供养人题记的顺序展开。为节约纸张及查阅方便,采用双面记录,如第61窟记录卡片38张,第85窟记录卡片22张(表2),第98窟记录卡片44张(图5)。
这次调查带有研究性,考证了经变画所据经文的出处,调查了各壁经变画的名称及题记。本次调查经变画近30种,极大地丰富了莫高窟洞窟内容,如第85窟抄录报恩经变 “孝养品”第二榜书、“论议品”第五榜书、“恶友品”第六榜书、“对治品”第三榜书、“亲近品”第九榜书;“孝养品”第二经文、“对治品”第三经文、“论议品”第五经文、“恶友品”第六经文,“亲近品”第九经文,并注明经文源自《大正新修大藏经》第3卷第128-129页、第132-133页、第139页、第162-163页,仅壁画内容就抄录了14张卡片。这次是最全面、最详细的一次调查,投入人力最多,调查项目也最全。
1964年,史苇湘先生全面复查并著录了调查内容。复查过程也是重新认识的过程,复查有了一些新发现,解决了一些悬而未决的问题,如过去认为第257窟南壁壁画是佛传故事画,这次复查认定其为沙弥守诫自杀故事;第296窟北披故事画一直没有定名,经这次复查认定为微妙比丘尼因缘和福田经变。复查直接用红笔在底稿上修改,之后又由万庚育先生进行复核。本次调查经变增至35种,这些珍贵资料完整保存至今。按照1960年洞窟编号展开调查,调查洞窟492个,最终编撰形成了《洞窟内容记录》(图6、图7),共装订10册(表3)。文字用蓝色钢笔著录,页面整洁,字迹娟秀,为其后编撰《莫高窟内容总录》奠定了基础。
(二)供养人题记调查
20世纪40年代,史岩、史苇湘等对敦煌莫高窟供养人题记进行了调查记录,并出版了《敦煌石窟画像题识》(简略本)。50年代,史苇湘、王去非、万庚育等对《敦煌石窟画像题识》进行了校勘和增补,并于60年代中期整理成书稿,但未能出版。70年代末,贺世哲、孙修身、刘玉权、欧阳琳等再次进行了校勘和增补,贺世哲最后将其整理成书稿[10]。
敦煌研究院藏供养人调查资料有调查卡片、《敦煌莫高窟供养人画像题识校勘记》和《莫高窟石窟档案》。其中以调查卡片中供养人及题名抄录尤为详细,均为逐条逐字抄录,包括游人漫记在内。仅第98窟供养人题记及游人漫题就抄录有27张卡片,均为双面抄录。各时期供养人题记内容对照情况详见统计表(表4)。
万庚育记录手稿《敦煌莫高窟供养人画像题识校勘记》共两册(图8),抄录册分别以稿纸、表格抄录,文中内容均有红笔修改的痕迹。万庚育在手稿中提到,《敦煌莫高窟供养人画像题识》以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20余年积累的资料为基础,并且参照已发表的有关资料,经过多次反复校对和补录而成。根据题识内容和性质,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供养人题记(包括题名、题樑、发愿文、功德记等);另一部分是游人漫题(也称游人题记),初步统计共有1397则。供养人画像题识是以东、南、西、北壁面的顺序进行的,校对时以石窟现存原文为准:凡是校正的文字和新发现的文字,都在文字旁加“Δ”作为标记;文字漫漶不清的以“……”表示;字迹模糊但可以看出其位置的,以“□”表示;文字隐约可见但不能确定的,在其外加框;某字仅存上下或左右一部分的,就在文字外加对三角;缺失的部分保留原状。
万庚育发现题识中最早的纪年是第285窟的西魏大统四年至五年(538-539),最晚的是元代至正十一年(1351)。在历次校对工作中,除校正原有题记外,还新发现了一些被忽略的题记,这些题记为推断石窟艺术时代风格提供了重要线索。比如:
第二八二窟(隋)西龛下发愿文尾题:大业九年七月十五日造讫
第四十一窟(盛唐)北壁画贤劫千佛,西起第六至第七行之间墨书题记:开元十四年五月 十一日讫记
前一条题记为隋代晚期洞窟的划分增添了一个标尺,后一条题记为盛唐时期石窟的划分增添了可靠的依据。
三、莫高窟石窟档案编制
经过对莫高窟多次调查,积累了大量一手资料。不过这些资料比较零散,使用极不方便。为了形成统一、便于查阅的高质量石窟档案,更好地发挥档案的作用,20世纪70年代初,敦煌文物研究所组织开展了《莫高窟石窟档案》编制工作。鉴于当时我国石窟寺没有洞窟档案的先例,因此,选取莫高窟第248、272窟作为编制石窟档案的样本。样本包括十个方面:内容简况及分布示意、残损病害示意图、窟内部分保存现状记录、保护修缮记事、石窟结构剖面图、各壁面实测草图、主要尺寸统计表、壁画临摹品目录、另行套装附件简要说明、摄影资料选编。最终因工程浩大,需要集中文物保护、勘测、临摹等各方面的力量,耗时长难度大,未能付诸实施。
经过多次研究、调整、优化,1976年,敦煌文物研究所制定了一套全面可行的编制办法。石窟档案以窟为单位,分别记录九个方面的内容,包括窟号、壁画塑像的原建时代及重修时代、洞窟位置、洞窟形制、壁画和塑像内容描述、供养人和壁画内容题记、洞窟平剖面示意图、石窟照片资料、洞窟保护工作纪要。1976年至1998年6月,《莫高窟石窟档案》编制完成,一窟一册,共492册,分别记录了莫高窟492个洞窟的内容(图9、图10)。
《莫高窟石窟档案》记录了洞窟建筑、造像、壁画、题记等各方面内容,包括文字描述、测绘图、照片等,记录全面,内容翔实,图文兼备,查找方便,是一部质量高、实用性强的档案资料。《莫高窟石窟档案》的编制,是几十年来莫高窟洞窟调查工作的阶段性成果,标志着莫高窟石窟档案的建立,对莫高窟的保护、研究和弘扬具有重要意义。时至今日,《莫高窟石窟档案》仍然是最全面记录莫高窟的工具书。
对莫高窟进行的若干次内容调查(表5),包括最初的洞窟编号,后来的考古分期断代和内容研究,以及最后的摄影、勘测和现状调查。在调查过程中,学者们不断总结经验,在确认洞窟数量和洞窟内容的基础上,完成了全部735个洞窟的编号和492个洞窟内容的档案记录。《莫高窟石窟档案》的编制,是几十年来莫高窟洞窟调查工作的阶段性成果,标志着莫高窟石窟档案的建立,对莫高窟的保护、研究和弘扬具有重要意义。
同时,工作人员逐渐发现,文物在千百年的发展历程中,会受人为和自然因素影响,不断劣化,并出现各种病害。学者们由此认识到编制石窟档案尤其重要,因为这项工作反过来又促进了文物保护、数字化、美术临摹等各专业的发展。
四、结语
1943-1998年,敦煌研究院(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对莫高窟进行了多次洞窟内容调查,从初期的洞窟编号到中后期洞窟内容记录与建档,由浅至深,涉及面越来越广,内容越来越详细。先后调查了492个洞窟,包括窟号、内容、现状以及摄影图片与测绘图等,积累了大量的基础资料,凝结着前辈们的智慧和汗水。这些资料最终汇总为《莫高窟石窟档案》,既是对前期调查成果的总结,也为后来编撰《敦煌石窟内容总录》奠定了基础。
通过对莫高窟内容进行调查,学者们还取得了一系列丰硕成果,不仅出版了《千佛洞初步踏查记略》《敦煌艺术叙录》《莫高窟内容之调查》《敦煌莫高窟供养人题记》《莫高窟窟前殿堂遗址》等专著,还发表了大量的学术论文。这些成果是敦煌研究院的宝贵财富,也是莫高窟保护、研究、弘扬事业的重要依据,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
[参考文献]
[1]张伯元.浅谈莫高窟石窟档案的编制 [J].敦煌研究,2000,(01):169-170.
[2]蔡伟堂.敦煌莫高窟编号的几处订正[J].敦煌研究,2015,(02):1-3.
[3]樊锦诗.《敦煌石窟全集》考古报告编撰的探索[J].敦煌研究,2013,(03):40-41.
[4]敦煌研究院.敦煌石窟内容总录[M].北京:文物出版社,1996:1-2.
[5]罗华庆,王进玉.敦煌艺术研究所时期制订的石窟保护管理规则[J].敦煌研究,2021,(03):139-141.
[6]敦煌研究院.敦煌石窟内容总录[M].北京:文物出版社,1996:1-2.
[7]孙儒僩.回忆石窟保护工作[J].敦煌研究,2000 (01):24-29.
[8]王建军,胡祯.敦煌莫高窟北区洞窟新编窟号说明——兼谈以往北区洞窟诸家编号[J].敦煌研究,1999,(02):115-116.
[9]樊锦诗,蔡伟堂.关于敦煌莫高窟南区洞窟补编窟号的说明[J].敦煌研究,2007,(02):44-45.
[10]敦煌研究院.坚守大漠 筑梦敦煌——敦煌研究院发展历程[M].兰州:甘肃教育出版社,2020:19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