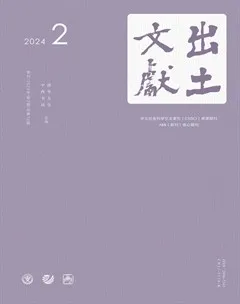桓谭《新论》“邪上”别解
2024-06-25梁睿成
梁睿成



摘 要:通过统计宋本《史记》《汉书》诸《表》单格、单列容字能力,可以发现纸张时代诸《表》的单列很难直接对应两汉时期的单简。当时诸《表》在制作与早期传抄中或采取类似“质日”以及尹湾汉简《延元二年日记》等文献的编排方式,将所有的栏分为多组来书写。与此相应,桓谭《新论》所言“旁行邪上”中的“邪上”,或指这种布局形式下各组间栏与栏的斜向关系。
关键词:《史记》 《汉书》 表 容字量 邪上
战国秦汉出土简帛中最常见的书写方式即通体竖向书写。此外,尚有环绕、分栏等布局形式。诸如《元光元年历谱》等历谱类文献、《为吏之道》等官箴文献、《算表》等数学文献、《占梦书》等占卜文献以及大量的行政文书等均可见分栏现象。而传世文献中,《史记》《汉书》诸《表》是最具代表的分栏文献。
《梁书·刘杳传》载刘杳引桓谭《新论》之语:“太史《三代世表》,旁行邪上,并效周谱。”【姚思廉:《梁书》卷五○《刘杳传》,北京:中华书局,1973年,第716页。】这里提及了两种表类文献的书写形式,一是“旁行”,二是“邪上”(即“斜上”)。“旁行”,学界几无异议,即分栏文献的横向书写、阅读。“邪上”则未得确解。
清人洪饴孙以《世本·姓氏篇》所言“言姓则在上,言氏则在下”即“旁行邪上”;【洪饴孙:《史目表》卷一,清光绪授经堂刻本,第3页。】刘咸炘先生则以“纵横经纬格”为“旁行邪上”。【刘咸炘:《太史公书知意》,黄曙辉编校:《刘咸炘学术论集·史学编(上)》,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48页。】然此二说仅言横纵,忽略了对“邪”(斜)的解释。近年来,学界亦开始重新讨论此问题。黄人二先生认为可能指世系传承所体现的关系,阅读时能见斜上的效果;【黄人二:《古书旁行邪上考》,《战国楚简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第393页。】马彪先生认为指表谱中斜线的图式;【马彪:《战国秦汉简牍中所见“表”及其“旁行邪上”特征》,《山口大学文学会志》第63卷,2013年,第41—58页。】赵益先生认为此体仅存于《三代世表》,是把旁行的部分内容“提行”,形成斜向的布局、阅读方式。【赵益:《〈史记·三代世表〉“斜上”考》,《文献》2012年第4期,第158—162页。】陈伟先生综合前人观点,认为“邪上”指斜向而前的书写和阅读样式,并找到了《三代世表》及《史记》《汉书》其他《表》之中格与格间斜向(含斜上、斜下)关系的例子,并辅以出土秦简为证。【陈伟:《〈史记〉诸表“邪上”新探》,《文史》2019年第1辑,第23—34页。】他将“邪上”用例推广到《三代世表》之外的传世及出土文献,可以说是很有价值的推进。“邪上”松绑了与《三代世表》的对应关系,它也就不再是孤例,而可能是早期分栏类古书中常见的书写体例,其意义也就重要了起来。实际上,《新论》中“并效周谱”也已提示了这点。当然,我们对“邪上”的具体解释还有一些新的看法,不揣浅陋,见教于方家。
一、 重审宋本《史记》《汉书》诸《表》的布局方式
在探讨古书体例时,我们依赖于目前所见的版本,但亦需注意到文献的书写、布局形式可能随时间的推移产生变化,目前所见版本未必完全反映当时的情况。此处可以举一个与分栏文献有关的例子来说明。
清人王绍兰与王谷塍注意到如《汉书·地理志》《续汉书·律历志》《后汉书·马武传》《逸周书·谥法解》《墨经》等传世文献原应采取了分栏的呈现方式,但当时所见的版本已改成了常见的竖向书写。【王绍兰:《汉书地理志校注》卷下“会稽郡”条,二十五史刊行委员会编:《二十五史补编》,北京:中华书局,1995年,第1册,第491页。】以《汉书》为例,《地理志》会稽郡下列有“吴,曲阿,乌伤,毗陵,余暨,阳羡,诸暨,无锡,山阴,丹徒,余姚,娄,上虞,海盐,剡,由拳,大末,乌程,句章,余杭,鄞,钱唐,鄮,富春,冶,回浦”诸地名。【班固:《汉书》卷二八《地理志上》,北京:中华书局,1964年,第1590—1591页。】依今本的书写顺序,则浙东、浙西地名会交错出现。若改为分上下分栏书写,则疆界井然可见(见表1):
以上说法虽是理校,但确有洞见。它提示我们需对目前所见版本留意。在“邪上”这一问题的探讨上,我们也应采取类似的态度。笔者希望从一个前人较少注意的方向来切入探讨,即《表》的栏数、容字与《表》制作的关系。
一个较为正式的文本的制作,往往要考虑承载内容的极限,以合理布局抄写的内容。从出土文献中不难发现一些文本因事先没有算好内容的多少,导致抄写前疏后密,甚至简正面不够,而抄到简背的情况。而表类文献在“布局谋篇”上比非分栏文献复杂,不仅要考虑总字数,还要考虑栏数及每栏容字量,这些往往需要制表前依据手头的史料进行计算。而表类文献出现抄写错误时需要修改,也比非分栏文献麻烦,因此更考验作者或书手的水平。而“邪上”的体例很可能就在表类文献的计算与制作中被使用。
鉴于前文的观点,即“邪上”这一体例并不限于《三代世表》,而《新论》仅是举例而言。因此,我们将考察范围扩大到 《史记》十《表》与《汉书》八《表》。首先,我们对宋本中诸《表》栏数的最大值与容字最大值进行了统计,【《史记》《汉书》均使用“景祐”(旧题)本。此处仅统计《史记》(含补表)、《汉书》原文,不计后世注文。《史记》部分表格的栏数前后会有变化,故分开统计。】结果如下:
从以上统计可看出,《史记》诸《表》中,栏数最多可至27栏,实际单格容字量最多可至74字,实际单列最大容字可达192字。《汉书》诸《表》中,横栏数最多可至20栏,实际单格容字量最多可至68字,实际单列最大容字可达341字。即便不算最高值,《史记》《汉书》诸《表》中单列破100字之例也绝非罕见。其他版本的具体数字可能稍有不同,但不会有本质区别。
以上统计自然是以宋代纸质刻本为基础的,但在《史记》《汉书》的写作年代,简帛才是主要的书写载体,因此需要考虑宋刻本的布局是否可以在简帛上实现。这就涉及前文所说的,文献的书写、布局方式是否会随时间推移而改变的问题。前人对《史记》的书写材料有过一些讨论,有竹简说、木简说、丝帛说,并无定论。【相关综述参见倪豪士:《一个〈史记〉文本问题的讨论和一些关于〈世家〉编写的推测》,陈致主编:《当代西方汉学研究集粹(上古史卷)》,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第434—435页。】我们认为《史记》《汉书》书写材料的讨论,很难得出实证性的结论。除去要考虑司马迁、班固等作者的书写材料外,亦要考虑到《史记》《汉书》的抄本是否一定会遵循作者的书写材料。其实我们能看到一些文本转抄改变书写材料的例子,如清华简《封许之命》当转抄自青铜器,马王堆帛书《战国纵横家书》的祖本当为简本等。【参见程浩:《〈封许之命〉与册命“书”》,《中国典籍与文化》2016年第1期,第4—6页;叶玉华著,黄人二、鲁月媛整理:《论帛书“纵横家”佚文廿七篇的错简、辞例、编制》,《诸子学刊》第4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259—276页。】因此,把《史记》《汉书》的书写材料仅认定为简、帛中的某一种,未必是合理的。帛在内容的呈现上与纸张并没有本质差异,诸《表》的底本或者部分早期抄本确实可以书于帛上,并做到与纸本类似的布局。而较之贵重的帛,简的使用则更为广泛与频繁,当时出现简本的《表》的可能性其实更高,但问题恰恰是该如何用简书写。
目前出土的战国秦汉时期的分栏文献不少栏数在个位,分栏达到十栏以上的,多数为历谱或与日期有关,如《本始四年历谱》《神爵三年历谱》《地节三年历谱》《元光元年历谱》等均为13栏,【历谱资料和形制的搜集可参看王丹凤:《秦汉简帛历谱研究综述》,硕士学位论文,西南大学,2015年,第1—26页;陈侃理:《出土秦汉历书综论》,《简帛研究 二〇一六(秋冬卷)》,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年,第31—58页。】即以月数(十二月加闰月)为栏数。这种栏数无疑和这类文献本身的性质相关,且每栏基本仅书写干支,或外加节气之类,一般单格不会超过五字,大多数为两字。当然,还有以日数分栏之例,如《五凤元年历谱》《居摄元年历谱》等,而里耶秦简中的9—19、9—20等亦以日数分栏,其单格容字仍在五字之内。若拿这些分栏文献与宋本《史记》《汉书》诸《表》相对比,栏数上虽能达到甚至超过,然单格、单列的容字量则远不及后者。
目前出土文献中单简容字量最多的是武威汉简《仪礼》的《服传》乙本,其单简平均容字量约100字出头,最高可达123字,但大多数出土简册的单简容字量或不到其半。程鹏万先生对简册容字量的统计应该是目前最为全面的。【程鹏万:《简牍帛书格式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7年,第231—240页。】笔者将其统计的129篇文献(主要是典籍类)分为3组,以单简平均容字量计,30字及以下的有50篇,31~60字的有71篇,61字及以上的仅4篇(另有4篇未统计);以单简最大容字量计,30字及以下的为32篇,31~60字的为86篇,61字及以上的则为7篇(另有4篇未统计)。其中30字及以下的容字,大多数也是20余字。因此,当时典籍单简的容字量大致在20~60字之间,偶有超过。这与笔者上述统计的纸质刻本上《史记》《汉书》一列动辄过百的情况大有不同,【这里的过百指最大值,笔者前文已提及,表的制作需要考虑容纳的极限。】即便按照武威《服传》乙本(简长50.5厘米)最极限的方式——每简书均书写123字,换算成汉代最长的三尺简,即69厘米来书写,也不过每简168字,离《史记》最高192字以及《汉书》最高341字仍有差距。何况当时日常的抄写很少用到这样的长简。一个侧面的证据是,西北曾出土有《史记·滑稽列传》单简一枚,长约17厘米,宽约0.8厘米,容字31。【此简见罗振玉、王国维编著:《流沙坠简》,北京:中华书局,1993年,第218页。】
程先生统计的主要还是针对一般非分栏文献。如前文所言,分栏文献的布局谋篇要更复杂,加入单格容字量的这一因素后,分栏文献单简的容字则大概率少于非分栏文献。以《史记·高祖功臣侯者年表》为例。该表凡9栏。其中,单列容字最多的是“酇”一列,共192字。该列中9个单格容字量依次为:1;34;24;9;12;33;26;52;1。第8格容字量最大,理论上该简第8格所占空间当最大,然后按字数多少类推各栏的空间。然而实际并不能如此,因为表的设计需要考虑每一栏的最大承载力,故每栏的空间由该栏容字最多的单格决定。“酇”一列总字数虽最多,然9个单格各自的容字未必是各自栏中最多的。如第二栏容字最多的单格在“蒯成”一列,凡63字,第二栏为容纳这63字,就必须按63字的标准来设计空间。而“酇”同列的格仅34字,就会出现有部分空间为照顾“蒯成”一列的单格而浪费。这种空间浪费在其他格中还会出现,故诸《表》并不能像一般的非分栏文献那样,可以满简书写。故前文依《服传》乙本推算的极限容字168字仅能存在于非分栏文献中,分栏文献的容字无疑更低。
最后是列的宽度和容字密度。目前见宋及以后诸《表》均呈现在纸张上,因此单页上表的列高虽是固定的,但列的宽度可以根据该列的实际字数进行相应的调整。
如《史记》宋“景祐”本原书版框高20.8厘米,宽15.1厘米。所有表中单格容字量最多为74字,该单格在《汉兴以来将相名臣年表》“元朔五年”一列的第四栏,该列总字数106字,列宽约为6厘米;前面提到的单列容字量最高的《高祖功臣侯者年表》“酇”一列,其列宽约8厘米。《汉书》“景祐”本原书版框高22厘米,宽15.5厘米。所有表中单格容字量最多为68字,该单格在《百官公卿表》“孝哀建平二年”一列的第四栏,该列总字数为269字,列宽约为7厘米;同表“绥和二年”(“景祐”本误作“一”年)一列为所有表中单列容字量最高者,凡341字,其列约宽4.5厘米。
这种通过在有限空间内密集书写以求达到更多容字量的情况,在秦汉时期也是存在的,如上面提到的武威简《服传》乙本。但编连成册的典籍简大多比较窄,宽度一般不超过1厘米,且基本为单行书写,【文书简中则多见两行书写,且有“两行”这一形制的简。】这就限制了每列的空间延展,灵活性远不如纸张。不过,也有些许双行书写的例子。非分栏文献中,如定县简《论语·尧曰》“不知命”章;分栏文献中,清华简《算表》的部分单格出现了两行小字;汉简历谱的干支与历注也可见两行书写。前不久公布的胡家草场汉墓出土《岁纪》的第二种则更值得注意,【李志芳、蒋鲁敬:《湖北荆州市胡家草场西汉墓M12出土简牍概述》,《考古》2020年第2期,第22—23页。】该篇记秦二世至汉文帝间大事,简长27.5厘米,宽1厘米,年份单行大字,事件字数多者为双行小字,其史料性质和书写方式都与《史记》《汉书》的《表》类似。这种《岁纪》双行小字的书写的形式,或可解决《史记》《汉书》部分单格、单列字数较少表格的空间问题,但诸如《百官公卿表》等大表,两行书写比之纸张的多行书写,仍有较大差距,容字问题依旧存在。当时还有什么办法可以解决窄简容字不足的问题,是我们接下来要讨论的。
二、 秦汉时期“牍”的使用
当时多行书写更多使用“牍”这一形式,【另外还有签牌、觚、封检之类,但不是主要的书写载体,且这几类可书写的内容也较为有限。】典籍类和文书类中均可见。目前牍上字数最多的属文书类,即西汉尹湾汉墓出土的《东海郡吏员簿》(YM6D2),非分栏文献。该牍出土时长约23厘米,宽约7厘米,正面书写21行,反面书写25行,正反两面共书写3
400余字,反面字数较多,约2000字。而分栏的典籍,有周家台秦墓出土的《秦二世元年历谱》(或称“二世元年日”)木牍,阜阳双古堆汉墓出土的《儒家者言》《春秋事语》木牍,尹湾汉墓出土的YM6D9木牍(六甲占雨、博局占)等。
牍的版面较简更宽,可容纳的上限也就更高。其中,容字最多者即《东海郡吏员簿》。若是分栏文献,一般也就数百字。一块牍上书写一篇《表》似乎不太可能。那牍是否会像简那样编连使用呢?若牍可多个编连或与简混编,则可用牍来书写字数较多的列,用简书写字数较少的列,这就解决了诸《表》书写的难题。
对牍是否编连使用的问题,学界也多有讨论,不过多集中于官文书的范畴。首先是秦代的情况。角谷常子女士曾提出里耶简中被认作是编连的简没有三行及以上的。而“单独简”(即所谓牍)依睡虎地秦简《司空律》的规定当“缠”,而非编连使用。【角谷常子:《论里耶秦简的单独简》,《简帛》第8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第168、175页。】史达先生则更明确地指出,单独使用的写本和多件构成的写本应在存储和运输方式上有别,牍(或方、版)单独使用,其保存、运输方式是捆扎,而非简册(多件构成的)的编连。【Thies Staack, Singleand MultiPiece Manuscripts in Early Imperial China:On the Background and Significance of a Terminological Distinction, Early China 51 (2018):pp151.又见《第七届出土文献与法律史研究学术研讨会论文集》,长沙,2017年11月,第17—48页。】而马增荣先生则注意到里耶简92283、165和166三牍有编连痕迹。不过此三牍是分别独立制作的,并不连读,它们先后到达迁陵县,最后存档时被编连,并以“折页”的方式保存。【马增荣:《秦代简牍文书学的个案研究——里耶秦简 92283、165和166 三牍的物质形态、文书构成和传递方式》,《“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91本第3分,2020年,第349—418页。】另,北大秦简“祝辞类”文献中有一篇《祠祝之道》,整理者根据编绳和简牍位置等信息推断,该篇由一支竹牍和六支竹简编连而成。【陈侃理:《北大秦简中的方术书》,《文物》2012年第6期,第93—94页。】但内容上,牍、简并不连读。【田天:《北大藏秦简〈祠祝之道〉初探》,《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2期,第38页。】
以上讨论大致认为牍多单独使用,虽有编连的例子,但内容并不相连。但情况并非一概而论,刘自稳先生指出,在里耶简中以下两种情况下会出现简与牍或者牍与牍的合编,而这些合编册书内容前后相关:(1) 簿籍等材料与附加之公文;(2) 转发公文与原始公文。【刘自稳:《秦代地方行政文书的形态——以里耶秦简为中心》,《文史哲》2022年第5期,第66—70页。】
以上两种情况均出现于文书之中。而文书册书的形成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并非一人一时一地书写好所有的内容后编连而成。因此需要注意不同简、牍的形成时间,亦需注意简册的编连时间。例如作徒簿附加的公文制作是以发文为目的,作徒簿本身的形成无疑早于公文,而各日作徒簿亦非集中一时制作的。【岳麓秦简(伍)《内史仓曹令甲卅》即提到作徒簿的制作流程为“日勶薄(簿)之,上其廷,廷日校案次编,月尽为(最)”。即要求每日记录,每日上交并接受校验,之后再按日期先后编连汇总。】虽然最后的文书形态是一份册书,但各简牍的制作是分离的,编连应在公文书写好之后。原始文书若是作为被退还的文书,则作为本次发出文书的附件而合编,那原始文书与本次文书的制作就是一前一后,其合编就是在本次文书制作完毕后。
明确册书形成的过程,对于我们探讨诸《表》的制作是否也可以采取类似的方案是非常重要的。典籍类简册的书写虽然偶有出现时间差的情况,但这显然不是制度性因素造成的。这次书手个人原因导致简册书写时间出现间隙,下次该书籍的复制就可能一气呵成。但一份作徒簿簿册书的制作,公文的制作不会同步于日作徒簿,而各日徒簿的制作时间也不可能是同时。而典籍中那种先编后写的册书,更不会存在于上面的文书合编之中。此外,文书中被合编的两种材料其性质也不尽相同。上引刘自稳先生文中已经论及二者长度上的差异。
汉代也存在着内容相关的简与牍合编或者牍与牍合编的例子。此处选择两个较有代表性的例子进行列举。首先是睡虎地77号汉墓出土的券与相关的往来文书及其附牒。整理者指出这批文书L组(券)与M组(往来文书与附牒)混编,形成长短参差、宽窄不一、或竹或木的简册,大多可见两道编痕。【陈伟、熊北生:《睡虎地汉简中的券与相关文书》,《文物》2019年第12期,第53页。】但一样要注意各简牍制作的时间和合编时间。同墓所出私人簿籍的N组,也有一个简牍合编的例子(简N5、N6、N30、N31与牍N1),但其簿籍的细目是陆续记入的,【熊北生、陈伟、蔡丹:《湖北云梦睡虎地77号西汉墓出土简牍概述》,《文物》2018年第3期,第46页。】即各简、牍的形成有时间差,编连更是后来的事。而券及相关文书,依整理者所言,已不能复原全部简牍的编连状态,但依简文内容尚能分为若干组。我们以已公布图版的简21—24一组为例进行讨论:
阳武亭受其乡牝狗一。二月甲寅所入。(简21)
阳武亭受其乡牡豚一。四月壬子[所入]。(简22)
远望亭受阳武乡牡豚一。四月壬子所入。(简23)
六年四月乙巳朔乙丑,仓粱人敢言之:乃二月戊申为乡官亭小畜员及给祠用各有数,颇未具。今谨以乡官所入息子未卖者为诣十七牒上,[谒令]亟受如牒署。已受,移右券仓。皆以书言输受月日。余牡狗牝豚亟卖。[它]如前书。敢言之。/四月戊辰,安陆台谓乡官啬夫、署亭校长:听书从事,当相输受,已输受,以书言,勿留。/寄手。各一书。(简24)四月壬申,远望求盗黑以来。/□发。成手。(简24背)
简24(为多行书写的牍)中提到的“今谨以……为诣十七牒上”透露出除此牍之外,同时有17支简记载“乡官所入息子未卖者”,其中就包含目前公布的简21、22、23。而这些细目的牒与简24的公文合编为一组文书。依公布的图版,四枚简牍均有上下两道编痕,下编痕位置大体一致,上编痕位置小有差异。这种与上文秦代所言的情况(1)的类型大体相似,即簿籍与公文的合编。不过此处细目简与文书简的制作与编连,很可能是在一起完成的。四简从字迹看,当为一人所书:
这种情况有两种可能,一是简21—23等内容是从原始簿籍中分别抄来,再接着制作简24的公文,之后编为一份册书;二是整份册书就是一份副本。前者更倾向于实际流通的文书,而后者更倾向于存档的文书。若看作实际流通的文书,则与一般典籍类册书的书写编连方式类似,不存在各简牍制作时空的差异,那是否是诸《表》均会采取这一形式呢?
这里就要谈到被编连二者的性质问题。包括整理者在内,学界多将牒看作一种附属的文书类型。【沈刚:《居延汉简语词汇释》,北京:科学出版社,2008年,第265—266页;李零:《视日、日书和叶书——三种简帛文献的区别和定名》,《文物》2008年第12期,第73—80页;鹰取祐司:《秦汉官文书の基础的研究》,东京:汲古书院,2015年,第544、576页;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简牍研究班编:《汉简语汇:中国古代木简辞典》,东京:岩波书店,2015年,第396页。】牍与牒的编连正是基于“呈文—附件”的关系。而汉代由呈文和细目组成的册书,其呈文多使用木两行,各个细目则用简(札),与此类似。侯旭东先生早已指出,秦汉时期文书的排列顺序大体是细目在前,呈文在后。【侯旭东:《西北所出汉代簿籍册书简的排列与复原——从东汉永元兵物簿说起》,《史学集刊》2014年第1期,第58—73页;侯旭东:《西北出土汉代文书简册的排列与复原》,《简帛》第18辑,上海古籍出版社,2019年,第109—132页。】所以,按当时文书通行的排列方式,字数较多的公文木两行或者牍当编连在字数较少的细目窄简之后。即牍与简的组合方式、编连顺序在汉代的文书制度中并非是随意的。
汉代还有牍与牍内容相关的例子,即谢家桥一号汉墓出土的告地书。考古报告指出208枚简(内容为遣策、分类统计)与3枚牍卷合后于两端各绑两道蒲草,外包蒲草后,在中部绑四道蒲草,在两边各绑一道蒲草,蒲草在端头扭合。【荆州博物馆:《湖北荆州谢家桥一号汉墓发掘简报》,《文物》2009年第4期,第41页。】我们这里主要讨论告地书三枚木牍的情况,其释文如下:
五年十一月癸卯朔庚午,西乡辰敢言之:郎中[五]大夫昌自言母大女子恚死,以衣器、葬具及从者子、妇、偏下妻、奴婢、马牛物、人一牒,牒百九十七枚。昌家复无有所与,有诏令,谒告地下丞以从事。敢言之。(牍1)
十一月庚午,江陵丞虒移地下丞,可令吏以从事。/ 臧手。(牍2)
郎中五大夫昌母、家属当复无有所与。(牍3)【考古报告刊布释文不全,此处释文采刘国胜:《谢家桥一号汉墓〈告地书〉牍的初步考察》,《江汉考古》2009年第3期,第120页。】
汉代告地书的格式基本模仿自秦以来的文书,刘国胜先生已指出前两牍构成告地书的正文,牍3是其附件,而牍1和牍2的内容一般在其他以往所见的告地书中多采取提行书写的格式写在同一块牍上,而此处则分为两牍。两牍之间存在一定关联。不过从文书性质看,牍1所载文书是西乡辰告于江陵丞虒的上行文书,而牍2所载则是江陵丞虒将文书转给地下丞的平行文书。与秦代合编的情况(2)转发公文与原始公文的合编类似。二者本就为两件文书,且从字迹来看,两牍亦不同(见表5):
表5 谢家桥一号汉墓牍1、牍2字迹对比表
二者虽是前后关联的文书,书写、制作时却仍是独立的,在最后下葬时,才与牍3以及附件的200余简一并捆扎保存。捆扎这种形式也不难看出,它本身就不是为日常阅读所准备的。类似的例子还有一些,例如松柏一号墓中的63块牍亦按类捆绑,凡六组(编号为27、28、30、31、34、36)。而另有10支记载标题的细简,依简报的室内平面图,当与36号牍合捆。【荆州博物馆:《湖北荆州纪南松柏汉墓发掘简报》,《文物》2008年第4期,第25、29页。】这些标题简原本各有其归属,但现在却捆在一起,可见其是保存而非使用的状态。
综上所述,秦汉时期虽然存在简、牍合编的例子,但具体来看,则存在多种类型。有内容上无关却编连在一起的,有存放或者归档的时候捆扎在一起的,有各简牍书写、编连存在时空分离的,也有特定文书形式上的编连。而这些方式与一般的典籍制作或者抄写复制方式存在一定差异。因此,笔者认为诸《表》可能不会采取文书中简、牍合编的方式书写。我们只能大体上重构诸《表》在简册上最可能的制作方式以及制作后其抄本的复制方式,而无法做到准确恢复诸《表》的原貌。
三、 分组排列——一种诸《表》早期可能的布局方式
上文笔者提出简册在栏数上虽可看齐宋代的纸质刻本,但在容字量和空间安排的灵活性上却不及后者,这些因素制约了简册上诸《表》的呈现方式。《史记》《汉书》诸《表》当时到底是如何书写和安排的,目前并无诸《表》的出土实物,但笔者希望结合与诸《表》类似的分栏文献的制作情况,作一些推断。
受限于单简的容字能力,当时能采取的一种补救方式即减少单次列出的栏数。宋本册页书能一次看完的栏,在汉代时或需分为若干组来呈现。例如一个10栏的表格,可以分为“5+5”。这种情况集中出现在出土的历书文献中,如岳麓秦简的三种《质日》,周家台秦简《三十四年质日》,北大秦简的《三十一年质日》《三十三年质日》,睡虎地汉简的十种《质日》,尹湾汉简《延元二年日记》等。这些历书均分为两至三组来呈现。简分为六栏,【周家台秦简最后闰月的组次是五栏。】先列偶数月:十月、十二月、二月、四月、六月、八月;偶数月天数的干支列完后,再列奇数月:十一月、正(端)月、三月、五月、七月、九月;若有闰月,则列在最后。如图2。
这种奇、偶相分的历书与一般十二、十三栏的历书在视觉呈现上并不一致,因为存在月数的跳跃。这种设计或许与历法有关。一般而言,大小月是间隔的,各大月的天数一致,各小月天数亦一致。为整齐用简,故将天数一致的月份排在一组。【何晋先生就指出在大、小月相间的一般情况下,所有三百五十四个日干支也正好可以整齐满写在五十九支简上。见氏著:《秦简质日小识》,《出土文献研究》第14辑,上海:中西书局,2015年,第193页。】虽然这种奇、偶分置的方式最为常见,但亦有遵循一般阅读习惯而不用这种方式的例子,如居延出土的天凤六年历书,它按正常月序分置,正月到六月为一组,七月至十二月为第二组。【罗见今、关守义:《〈居延新简——甲渠候官〉六年历谱散简年代考释》,《文史》1999年第1辑,第54—55页。】
这种六栏历书中,部分干支下会另记有文字。既可见岳麓秦简、周家台秦简专记政务的,亦可见北大秦简、尹湾汉简记录建除、节气及私事的。此类文献大都被称作“质日”(自名或拟名),学界对其定名与性质多有讨论。【苏俊林:《关于“质日”简的名称与性质》,《湖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4期,第17—22页;肖从礼:《秦汉简牍“质日”考》,《鲁东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3期,第70—72、82页;李忠林:《岳麓书院藏秦简〈质日〉历朔检讨——兼论竹简日志类记事簿册与历谱之区别》,《历史研究》2012年第1期,第169—170页;工藤元男:《具注历的渊源——“日书”·“视日”·“质日”》,《简帛》第8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第311—336页;何晋:《秦简质日小识》,《出土文献研究》第14辑,上海:中西书局,2015年,第197—198页;史达:《岳麓秦简〈廿七年质日〉所附官吏履历与三卷〈质日〉拥有者的身
份》,《湖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4期,第15—17页;陈侃理:《出土秦汉历书综论》,《简帛研究 二〇一六(秋冬卷)》,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年,第50页;龙仕平:《“质日”释诂》,《简帛研究 二〇一八(春夏卷)》,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8年,第142—152页。】其中,工藤元男先生认为不该把记录政务的历书与记录节气、节日的历书视作同类。笔者认为这种区分现在看来还是有必要的。已有不少研究指出,这些除去干支外尚有其他文字的历书是在制作好的空白历书上记事。【连云港市博物馆等编:《尹湾汉墓简牍》,北京:中华书局,1997年,“前言”,第3页;赵平安:《周家台30号秦墓竹简“秦始皇三十四年历谱”的定名及其性质——谈谈秦汉时期的一种随葬竹书“记”》,
《长沙三国吴简暨百年来简帛发现与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北京:中华书局,2005年,后收入氏著《文字·文献·古史:赵平安自选集》,上海:中西书局,2017年,第209页;谢计豪:《岳麓秦简〈质日〉〈数〉篇书手及相关问题研究》,硕士学位论文,湖南大学,2020年,第10—16页。】据此可认为这种六栏历书本质上是带有日期的空白格套。不同的人依据各自的需求在这类历书上填不同的内容,而不同的内容则产生不同的文本。
何以这种历书要分为多组?其实就是要为记录内容留出空间。若要在27厘米(如岳麓简几份《质日》简长)的简上安排十二或十三个月的内容,如《卅四年质日》第一简就要书写68字加13个墨块,着实困难(虽然在后续简的书写会较为宽裕)。而尹湾汉简《延元二年日记》(简长23厘米)中,后续很多简的记事较为频繁,若以十二栏书写,部分简在容字上亦会出现困难。理论上,当时人完全可以使用更长的二尺简,来达到不分组书写的目的,但实际发现的此类文献大多在20~30厘米之间。即当时人更愿意采用一尺左右的简外加分组书写的方式来制作这类历书。这其实提示我们:在考虑诸《表》制作时,不能单纯看简的容字极限,更要看使用习惯及便利性,诸《表》的作者与抄手的制表法更可能存在于当时表格制作和抄写的平均数而非最高数中。
分组书写的方式伴随着一尺简,反复出现在此类文本中,形成了一种用于解决分栏文献容字困难的方法。而当时亦存在其他一些解决容字难题的方法,如将某简容纳不下的内容,延续到后面的简对应的栏中去书写,这样的例子在出土文献中亦能找到。非分栏文献中,北大简整理者曾提到北大简《仓颉篇》、睡虎地秦简《日书》、周家台秦简均在简首端书写篇题时有跨简书写。【北京大学出土文献研究所编:《北京大学藏西汉竹书(壹)》,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第67页。】李松儒女士亦发现清华简《治政之道》简首端书写的收藏者(或抄写者、作者)的题名亦属类似现象,但为倒书。【李松儒:《清华简〈治政之道〉〈治邦之道〉中的“隐秘文字”及其作用》,《文史》2021年第2辑,第19—21页。】分栏文方面,王化平先生指出郭店简《语丛三》存在一章文字被抄写在两支简上的情况,如简68下栏文字写不下时,就接着写在简69的下栏;清华简《筮法》分栏抄写时常见同一章内容抄写在多简上。【王化平:《简帛古书中的分栏抄写》,《文献》2016年第4期,第149页。】我们还能找到一例,即睡虎地秦简《为吏之道》,其第五栏的“成相辞”、两种魏律以及格言也出现了顺延的情况。而最值得关注的是睡虎地汉简的《质日》,整理者提到在字数较多的栏存在缩减字形,或转书于另栏、另简的现象。【蔡丹、陈伟、熊北生:《睡虎地汉简中的质日简册》,《文物》2018年第3期,第55页。】可见,顺延跨简书写亦能在分组书写的基础上存在,二者可以配套使用。
以质日为代表的分栏文献已经多次应用的解决容字问题的方法,或不限于这些六栏历书,还可能存在于类似事件、日期相经纬的文献中。如司马迁提到他曾读的“谍记”(黄帝以来皆有年数)、“春秋历谱谍”、“秦记”;班固《汉书·艺文志》春秋类则著录有《太古以来年纪》《汉著记》《汉大年纪》等书,历谱类亦录有《帝王诸侯世谱》《古来帝王年谱》等书。今日出土文献的自名中亦有类似名称者,如松柏汉简、印台汉简的《叶书》、【“叶”,李零先生读为“牒”,陈伟先生读为“世”,但二人都认为“叶书”与司马迁所本的世系、谱牒一类文献有关。见李零:《视日、日书和叶书——三种简帛文献的区别和定名》,《文物》2008年第12期,第77页;陈伟:《秦汉简牍〈叶书〉刍议》,《简帛》第10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第88—89页。】胡家草场汉简的《岁纪》,周家台出土的今定名为《三十四年质日》的文献,依墓中所出物疏所列,自名为“记”。【赵平安:《周家台30号秦墓竹简“秦始皇三十四年历谱”的定名及其性质——谈谈秦汉时期的一种随葬竹书“记”》,《长沙三国吴简暨百年来简帛发现与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后收入氏著《文字·文献·古史:赵平安自选集》,第212—215页。】而诸《表》中的年表、月表与填入事件后的历谱其实非常相似,王化平先生亦持类似看法。【王化平:《简帛古书中的分栏抄写》,《文献》2016年第4期,第150页。】徐建委先生对《史记·十二诸侯年表》的研究亦指出该表是先制作好年表的框架,再往表中填入史料,【徐建委:《〈史记〉春秋历史的写作实践与文本结构》,《文学遗产》2020年第1期,第33—34页。】这与六栏历书的制作方式基本相同。诸《表》与记事类历书应该存在一定亲缘关系,诸《表》在史料性,抑或形制上都可能受其影响。司马迁、班固制表时所依据的史表文献大概率也存在容字困难的问题,而这些史表文献用于解决容字问题的方式应该也被司马迁、班固所继承、借鉴。
桓谭《新论》言“太史《三代世表》,旁行邪上,并效周谱”,即明确提到了司马迁制表法借鉴了周谱。如前文所言,前辈学者对此句中的“邪上”作出了多种解释。目前来看,以陈伟先生的观点最为可靠,即栏格的斜向书写或阅读样式(如图3),且这种斜向阅读并不仅存在于《三代世表》中,司马贞在《十二诸侯年表》中的《索隐》也节引了“旁行邪上”的论述。且除《三代世表》外,其他《表》中亦可发现斜向书写(含邪上、邪下)的实例,因《三代世表》处十表之首,故用以概括诸《表》。这是非常具有启发性的意见。【陈伟:《〈史记〉诸表“邪上”新探》,《文史》2019年第1辑,第29页。】
但这种斜向的关系带有一定偶然性,与《新论》中“并效周谱”的说法似有不合。“邪上”(或兼“邪下”)当与“旁行”类似,是一种可“效法”的程式。比之“旁行”的必然出现,单个《表》中可找到斜向关系的格并不多。单格一个个客观排列过去,碰巧临近斜向的格子就产生了相关的内容,这或许并非史家的刻意安排,似难称之为“可效之法”。因为缺乏明显的提示,一般人阅读时也不易发现这种关系,这就降低了其存在的意义。不过,亦有非偶然的例子,即《汉兴以来将相名臣年表》。该表中大量出现提栏倒书现象,倒书文字多涉“节点”,如职官置废或人物的亡卒,而这些文字均会上提一栏书写,则与之相关不提栏的格则必与之产生斜向关系,这可以说是一种程式化的体例。也正因提行和倒书并用,斜向关系才得以彰显,读者亦得以知晓。然此体例并不见于其他九表,可见其特殊。桓谭不举此表,反举《三代世表》,亦证桓谭所说的“并效周谱”的“斜上”并不是类似《汉兴以来将相名臣年表》这样的现象。“邪上”“邪下”若不指单格的斜向书写、阅读关系,那该如何解释?
笔者认为“邪上”(或兼“邪下”)按《新论》原文,一定是指一种可模仿的制表法。而这种制表法作为一般分栏文献均具备的“旁行”制表法的补充,当是为应对一些特殊情况而存在的。而这种特殊情况,可能指的就是容字困难。即表的书写出现容字困难时,即采取“邪上”的方式。
“邪上”不当指表中“格”与“格”的斜向关系,而是“栏”与“栏”的斜向关系。具体而言,即使用分组制表后,不同组之间的栏产生的斜向关系。在这种制表法下产生的斜向关系无疑是稳定的。在质日等六栏历书中,因大小月的关系,大多表现为“邪下”,如十一月与十二月,正月与二月等,若出现闰月,则后九月与九月构成“邪上”。而不遵循大小月的天凤六年历书,其六月与七月亦构成“邪上”。
诸《表》并无所谓整齐大小月用简的需求,更大概率是使用符合视觉观看方式的“邪上”。故《新论》原文即言“邪上”。我们以《三代世表》的八栏部分为例,模拟其形式。
此部分每栏单格最大容字量如下:
前文已述,制表需考虑每栏的极限容字,故理论上需要按单简86字来设计空间。这已经超出一般汉代典籍简的容字上限。若按分组制表的方案,则是用两组四栏的方式来呈现:
如图4所示,帝王世国号至尧属为第一组,舜属至周属为第二组。同组内,各栏内容均遵循“旁行”的方式阅读。但同栏不同组,如帝王世国号与舜属则不构成“旁行”。当第一组的尧属一栏内容完结后,此时转向上接舜属一栏。此时尧属一栏与舜属一栏就构成“邪上”关系。而这两栏产生的“邪上”关系正是基于分组书写的方式形成的。这种方案下,两组单列的理论最大容字量分别为44和42余字,但每栏容字量最大的那些单格并非刚好在同一列上,因此实际单列容字量肯定低于理论值。这样的容字量基本落在当时典籍简正常的容字区间内。汉代20~30厘米的典籍简中,【邢义田先生也曾认为《史记》在当时应当书写在一尺简上。见氏著《汉代简牍的体积、重量和使用——以“中研院”史语所藏居延汉简为例》,《古今纵横》2007年第17期,第74页。】张家山汉简《引书》《盍庐》,银雀山汉简《孙子兵法》、尹湾汉简《神乌赋》等容字均在40字上下。可以说,以这样的文字密度和简长来分组书写《三代世表》是完全没有障碍的,甚至略有富余。
总结
现在我们看到的早期文献基本以宋代及其之后的刻本为基础。而宋代距离先秦秦汉的文献产生时间已相隔太远。而本文主要关注的问题是早期文献在其作者的时代是如何书写和被复制的。
通过统计《史记》《汉书》诸《表》的容字能力,不难发现秦汉时期的简册在容纳诸《表》内容上的困难。而这种困难笔者认为不能使用简(书写内容少的列)、牍(书写内容多的列)合编的方式来解决。因为秦汉文书中的简牍合编所存在的几种方式,均与一般典籍的书写和复制流程不符。
当时用于解决分栏文献容字的方式还有两种:一是将所有的栏拆分成数组来书写。二是该简容纳不下的内容,延续到后面的简对应的栏中去书写,后者可以叠加在前者之上使用。分组制表的方法大量出现在诸如岳麓秦简的三种《质日》,周家台秦简《三十四年质日》,北大秦简的《三十一年质日》《三十三年质日》,睡虎地汉简的10种《质日》、尹湾汉简《延元二年日记》等文献中。使用分组制表的历日文献,在性质和制作方式上均与诸《表》有密切关系。分组制表法亦可为解读桓谭《新论》中的“邪上”提供新视角。
“邪上”是存在于分组类表格中的一种表现栏与栏斜向关系的书写、阅读方式,它是为解决书写分栏文献时遇到的容字困难问题而出现的设计。桓谭看到的《史记》诸《表》的形制是特定时代下的产物,而随着纸张在魏晋以降的流行,作为书写载体的竹木简逐渐退场,由其局限性所导致的容字问题不复存在,在此之上产生的分组制表法亦无需再使用。所有的栏同时在纸张上呈现出来,并一直被后世的版本所继承。
(责任编辑:姜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