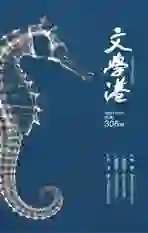漫游者
2024-06-15沙爽
沙爽
一
临近中午,我正在忙碌,一个女生出现在办公室。可能我忙乱中忘记随手关门,她就直接进来了。她说她叫小雨,是C同事的学妹。我说C老师今天在家改几篇稿子,可能不会来编辑部了。她问C的手机号,我未作多想,就告诉了她。
她开始给C打电话,问他能不能过来,一起找个咖啡店坐坐。大约电话那边C说实在走不开,她便说起自己的来意。
“真是恍如隔世,现在好多人都认为我疯了,可能是因为我最近修道修到了一个静心的境界,老感觉有人在呼唤我,我就过来找您了。”
透过电脑屏幕和几摞书刊的缝隙,我看了她一眼。她神色平静,看不出有开玩笑的意思。我想起我的小姑子徐畅。自十六七岁开始,徐畅就成了虔诚的在家居士,甚至一度决意出家为尼。做父母的自然舍不得,遂承诺另备一套砧板锅盘,每餐单独为她做一份素斋。后来她结婚生子,就住在我家隔壁,把近三十平方米的客厅改造成佛堂,量身定制的佛龛占了一整面墙壁,书橱里摆满佛经典籍。有一次她说,前一天晚上,她在小区里看见一位从未见过的老爷子,从我们这幢楼前拐过去,一直向西走,然后就消失不见了。我说:咦,西边不是墙吗,难道那边新开了一道门,咱们还不知道?徐畅说她也奇怪呢,今天早上特意绕过去看了一眼,哪里有门啊。那天表哥和表嫂从沈阳过来赶个婚礼,本来打算在我家住一晚再走,一听徐畅讲的这个事情,表嫂无论如何也不敢住了,逼着表哥连夜开车回家。和徐畅相处了这么多年,我对她讲的这些神神道道的事情早已司空见惯,也懒得去辨个真假。既然每个人的大脑和视觉神经都不相同,那么各人眼中的世界可能也大不一样吧。
但是眼前的这个女生,她的讲述越来越离谱。她说某人的魂魄在她的身体里,又一再强调她的指甲莫名其妙变短了(我不太明白这其中的寓意)。而后她问C有没有事情要她帮忙做,说自己这些年写剧本,也不知都忙了什么,真是恍如隔世。
我也觉得恍如隔世。因为此时我突然记起,三四年以前,我见过她一两次。那时她化着淡妆,虽然有点与年龄不相称的严肃,但总体给人的印象,是成熟和体面的。她是同事N的大学同窗,那次她拿来一摞厚厚的剧本,请同事C帮忙修改。C虽然觉得突兀,但看在N的面上,也只得应承下来。当时我还想,改剧本这样耗时费力的事情,倘若换成是我,大概连个求人的门路也摸不着的。
而今她胖了一圈不止,穿着臃肿的黑外套和过时多年的鞋子,眼前的人与几年前的她,是平行世界里的两个版本。
通话大约持续了半个小时,也许还要更久一些。不知电话那头的C作何感想,至于我,只觉得心跳加速,头皮发紧。要命的是,实习生今天也没有来,整个办公室只我一个人。
终于,她讲完了电话,走过来说要看一下我的手机。没等我反应过来,她已经用我的手机拨出了一个号码,开始与对方通话。
她带来了两部手机。也许,这两个号码都被电话那头的人拉进了黑名单。除此之外,我想不出她需要借用我手机的原因。
我也有两部手机,安装了不同的APP。它们不仅替代了钱包和身份证件,它们甚至可以替代我活下去。
这时同事C发来微信,说此女的精神已不太正常,让我不要与之纠缠,可以推说有急事,尽快锁门离开。
我看了一眼电脑。这个时间,大多数同事已经吃完了午饭。我穿上大衣拎起背包,等着她把电话讲完。
她正在请求电话那头的人放过她。“我想和我对象结婚。”她说。搞不懂这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但我已经没有心情好奇了。我饥肠辘辘,心烦意乱,只盼望她快一点离开。
这通电话如此漫长。我走到她近前,她漠然扫了我一眼,随即扭开脸去,仿佛对一切视而不见。
我不在她的世界里。她也不在我的世界里。但我的手机意外卷入了她混乱的关系网络,而且很有可能,还扮演了一个被人诅咒的角色。
顾不得礼貌了。趁着她说话的间隙,我简短地告知她我有急事,请她换用自己的手机。她仍旧面无表情(据说阿尔茨海默症晚期患者的典型症状便是如此),对着电话那头的人说:你拨个电话到我手机上。对方拒绝了。
天津城这么大,不知她是从哪个区赶过来的,来时的路上,她可能已经用掉了一个小时。差不多整个上午,她奔突在这些无效的沟通里。她试图用电话拓开一条道路,但每条路的前方,都横亘着一道铁壁。
通话终于结束了,她把手机递还给我,却没有要离开的意思。她拿过桌上的一张纸,开始写字,然后对着那几个字陷入了沉思。
几分钟后,她起身走向门口,手里紧紧抓着那两部手机。她的眼神空洞,脚步轻飘,宛如梦游。我提醒她忘了椅子上的背包。黑色人造革背包的提手部位皮质开裂,像两条黑底白斑纹的蛇。
她离开之后,我看了看那页纸,上面写着三个“佛”字,其中一个“亻”的一竖,被描了又描。同事们过来看到这几个字会作何感想?我把纸片折叠起来,扔进了废纸篓。
随后,我知道了她的故事。这些年,她做过编辑和记者,开过花店和服装店,但她的精力和梦想,都投入在剧本创作上。几年前,一个年长她二十岁的男人,声称可以帮她把剧本拍成电影。从那时起,男人在她家蹭吃蹭住,还与她生了两个孩子。生完第一个孩子,她曾经带男人来找我们的同事N,希望她能够帮他找份工作。交谈起来,男人说漏了嘴,N才得知他们已有了孩子。而这些年为了开店创业,她已负债一百万。
整个下午我心绪不宁。直到晚上八点,我测了一下心率,竟然仍高达每分钟九十。
仔细回想,当时挤压在我心头的,倒也并非是恐惧——当我们骤然面对一份被损毁的人生,即使与对方并无多少交集,仍会不由自主地为之惊悸。
211大学毕业,天津本地人。父母分别是教师和会计师。为方便她上班,父母还特意为她在前单位附近买了一套房子——从世俗的角度看,上天往她手里塞了一副好牌。然而从毕业至今,只不过十年,好牌堪堪出尽,眼见得败相尽显……是她不够努力?还是,就像许多人说的,纯粹是输给了运气?
在临睡前的半梦半醒之间,我突然明白,在我与她之间,有某些东西是颠倒的。比如说,于她而言,“生活”更接近一个虚词。当我说到“魂飞魄散”,那只是一个比喻;而她所说的“魂魄”,却是某种实体,是刀锋般锐利的有形之物,足以切入皮肤和骨骼,刺穿那内里的一团团虚无。
二
她的原名很普通,我没有记住。只知道长大之后,她为自己改名叫茉莉。
很小的时候,她就失去了双亲。在养父母家里,另一位养女金吉,成了她的妹妹。或许是因为她的基因远比金吉优秀,无论容貌还是智力,她都明显胜上一筹。养父母的爱,也更多地垂顾在她的身上。及至成年,两姐妹间的落差越发天上地下——她嫁给了富有的商人哈尔,坐拥珠宝与豪宅;而金吉与搬运工奥吉结了婚,虽然无法明言,但有这样的一门亲戚,确实让她暗自感到难堪。
各自安好的日子过了几年,金吉和奥吉突然从旧金山来到纽约度假,并将在此逗留五天。这让茉莉感到压力像山一样大——看来她不得不邀请他们参加她的生日派对了。但一听妹妹妹夫刚在赌场上赢了二十万美金,她顿时来了精神,极力撺掇金吉和奥吉将这笔钱投资于哈尔的生意。哈尔也顺水推舟,承诺会帮他们赚到百分之二十的收益。
金吉夫妇乘出租车游览纽约,在路口等绿灯的间隙,透过车窗,不期然看见了哈尔——他正与美丽的情人在街角激吻道别。
在茉莉的生日派对上,金吉暗示姐姐:“你不觉得那个女人与你丈夫走得太近了吗?”但茉莉说,她相信哈尔,而且那个女人是她最好的朋友。
要不要将真相告诉茉莉?金吉纠结不已,最后她决定隐忍不言。有些事不戳破就不会引爆灾难。“也许茉莉不想知道。她喜欢视而不见。”
然而实际上,金吉撞见的只不过是哈尔的众多情人之一。当茉莉终于发现了丈夫出轨的确凿证据,好友却满脸同情地告诉她,多年来,她是那个唯一被蒙在鼓里的人。苦心维持的幻觉破灭了。失魂落魄的茉莉回到家里,哈尔的一番话又给了她迎头痛击,他说自己已经找到了真爱,决意要开始新的生活。
急怒攻心,茉莉拨通了FBI的电话。这么多年,她对哈尔瞒天过海的伎俩其实早就心知肚明,但一直以来,她宁愿假装视而不见——若非如此,她怎能挥金如土又心安理得?
因诈骗罪服刑的哈尔在狱中自杀,继子丹尼离家出走。所有的财产被罚没拍卖,破产后的茉莉走投无路,只好前往旧金山投奔妹妹金吉。尽管负债累累,她还是选择了头等舱,带着她既往生活的全部遗物:几只私人订制的LV旅行箱。
此时的金吉已经离婚,正与男友车利热恋。住处狭小,茉莉的到来,使得他们的同居计划被迫延后。车利把他的朋友介绍给茉莉,希望她早日从往昔的伤痛中走出来,展开一场新的恋爱。但茉莉哪里瞧得上这些底层男人?她告诉金吉,在纽约时她迫于生计,不得不到鞋店做导购,为那些曾经将她奉为座上宾的女主人量鞋码,那种耻辱感简直让她生不如死。她不屑于护士和收银员之类的职业,想回到大学里重新学习。当年她本可以成为人类学家,却在大学毕业的前一年选择了退学嫁人,如今既无文凭又无专长,想找个好工作谈何容易?
在金吉的建议下,茉莉决定学习装修设计,虽然这类课程学费高昂,但也可以利用电脑自学。就这样,她一边在牙科诊所做接待员,一边去上网课。这些课程实在让她头痛,幸好班里有个热心的学霸女孩。听女孩说她的男友是位律师,茉莉心里一动,问女孩有没有合适的男人介绍给她认识。女孩便邀请她去参加一个派对。在派对上,一位风度翩翩的男子仿佛从天而降,自称是个外交官,正准备竞选议员。茉莉知道,幸运之神再一次向她敞开了大门——不,真正的神是这位外交官,她要踏上他铺展过来的婚姻红毯,重新做回上流社会的贵妇人。
她为自己虚构出清白的身份:装修设计师,外科医生遗孀。在蛛网的这一端,黑寡妇等待着她痴心的情郎。事情的进展正如她所愿:他对他一见钟情,晕头晕脑地撞进网中。他带她到首饰店挑选订婚戒指,不料却碰见金吉的前夫奥吉。奥吉告诉茉莉,为了谋生他即将远走他乡,而这完全是拜她的骗子老公所赐——那二十万美金本可以让他实现开一家搬运公司的梦想,为他和金吉的整个人生带来重大转机,如今这一切皆成泡影。
谎言被拆穿了。她到底虚构了多少过去?她说的哪一句话才是真的?外交官对茉莉彻底失去了信心。
茉莉明白,他不会娶她了。再一次,她感到无法呼吸。未等他将车停稳,她就跳了下去,背包掉在地上,包里的东西散落一地。
她脚步踉跄,像个梦游的人,不知该去往哪里。这不是她的梦境。或许,她是那个漫游仙境的爱丽丝,当兔子和魔法一起消失,她的双脚落回到地面,却发现真实的世界业已遍地荆棘。而所有属于她的梦,都遗落在另一个世界,遗留在那个不知怎样才能重新返回的兔子洞里。她的梦想如明月高悬,而她的力量却如此黯淡卑微,除了疯掉,她再也没有别的办法避开眼前的难堪和痛苦,没有办法让往日重回。
从花团锦簇到支离破碎,电影《蓝色茉莉》的结局令人哀怜。凯特·布兰切特轻度神经质的气质,也与她所饰演的茉莉完美契合。伍迪·艾伦的嘲讽也恰到好处地戳中了大众的笑点:当一个人的欲望与能力无法匹配,他们努力攀附的身姿难免漏洞百出,堪笑堪怜。但是,衣马轻肥,美食笙歌,谁会主动拒绝这样的生活?谁不想好风凭借力,送我上青云——茉莉的悲剧,在于她需要借助的,不是风,是这世界上最不稳定的一种介质:男人。
三
听一个朋友讲她姨母的故事。
这位姨母多年前离了婚,因为她自己名下没有房产,女儿的抚养权判给了前夫。第二次婚姻,她嫁给了一位离异的男人,从此平平淡淡地生活了二十年。
说是平平淡淡,是因为,婚姻的裂痕只隐藏在两个人之间,外人根本无从看见。她没有什么朋友,与亲戚们也一向疏于往来,大抵是觉得这些人情交往浪费时间和金钱。或许她生来内向,抑或很享受这种离群索居的封闭状态。她厨艺不错,家务方面也堪称勤勉,但随着夫妻二人相继退休,鳏居的公公日渐年迈,丈夫决定搬去照料老人的日常起居,她则留在原来的房子里独住。
她第一次发病,是在冬天。凌晨三点,她跑到街上打110报警,声称有人到她家里要杀死她。
或许那并不是第一次。或许此前的种种异常,那做丈夫的始终不曾声张。
警察询问了事由,叫她丈夫来把人接回去。丈夫找妻子的女儿和姐姐商议,三个人都觉得有必要到医院做个检查。医生的诊断是被害妄想症,要家属督促其按时服药,必要时住院治疗。
但是此后,类似的情形又发生了几次。附近有建筑施工,噪声扰民,她曾打电话举报,随后又疑心自己遭到施工方的报复,并认定楼下的几个人正在监视她,家里的水也被投了毒。这样过了两个月,附近的派出所民警都认识她了。可女人始终坚称自己没有病,当然也不肯服药。女儿和姐姐无法全天候守在她身旁,做丈夫的遂提出住院医治,女人坚决不同意。
如此僵持了几个月,做丈夫的下了最后通牒:要么离婚,要么住院。二选其一。
女人不想离婚。她每月的退休金只有三千元多一点,需要丈夫每月资助二千元。而且,离了婚,她住在哪里?女儿刚刚成了家,她不想成为女儿的负担。
听到这里,我心下一惊。设身处地想一想,如果我住着别人的房子,还需要对方每月资助我生活费,而我的存在无法为对方提供任何价值,那么在潜意识里,我恐怕也免不了会生出被害妄想症的吧?
甚至——我恶毒地想——也许正是这位丈夫,暗中制造了种种恐慌?毕竟,就现实利益而言,他存在这个动机。
我不能理解的是,一个连亲友间的正常往来都舍不得花费的人,既不外出旅游,也未豢养宠物,在不需要支付房租的情况下,仅仅是每个月的基本生活费,怎么会需要五千元之多?要知道,在这个城市,应届大学毕业生的平均工资,也不过三千元出头而已。
没有积蓄、入不敷出,整个生存状态如一株寄生的藤,却又没有培育出足够亲密和可供依赖的宿主——这样的人生,也真的是无解的吧?
后来呢?我问。
后来她自己去咨询律师。律师告诉她,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不想离婚,她的病情反倒于她有利。所以,现在她承认自己有病,答应吃药,但坚持不肯住院——她听说过,那意味着可能要接受电击治疗。
我说:有没有想过,她也可以选择离婚,要求对方一次性支付一定数目的赡养费——估计她丈夫也愿意如此。也许她病情的源头,正是这场形同陌路又不得不捆绑在一起的婚姻?说不定,离了婚,她内心的不安和恐惧悉数消散,这病也就不治而愈了呢。
朋友说,姨母最担心的,可能是自己一旦离婚,将来有事就全要依赖女儿,不仅让女儿心理上的负担加重,在经济上,女儿也难以承受,甚至会危及女儿的婚姻。
我说,如果是这样,她和普通的母亲并无二致,有着正常人的情感。而且她思路清晰,能准确地权衡利弊,那么是不是可以大致确认,她的精神并没有迷失?或许,她只是过分敏感,她所感知的世界与他人不同,却无法被周围的人认可和理解。
作家迟子建曾断言,必要的丧失是对想象力的一种保护。当我们面对精神失常者时,“他们的失神和超常状态其实是引起了我们自身的恐慌,他们那不顾一切、彻头彻尾的丧失令我们疑惑不解,所以我们认定他们有病”。而绝大多数疾病的症状,伴随有抑郁、焦虑、暴躁和惊慌,那么我们此时产生的这种恐惧和慌乱,是否也是一种病态呢?既然“正常”是以大众的普通人的行为作为尺度,那么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并没有办法界定所谓的“精神病患者”就是有病的,他们只是游离于寻常思维之外的人,或者说是“精神漫游者”。
当现世中的门扉逐一关闭,他们在虚空的壁垒间找到了一丝缝隙,让自己的魂魄短暂地安身其间——这些出走者、漫游者,或许他们的魂魄太过柔软,因而需要一个更为致密的、坚硬的壳。
在给弟弟提奥的信中,梵高写道:“每个人的心中都有一团火,路过的人只看到了烟。”
而相对于彼此而言,我们,都是那个路过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