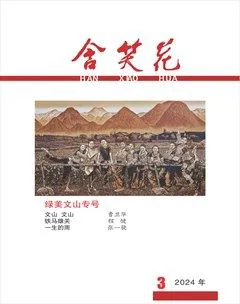拯救一种树
2024-06-12曹卫华
一
广州华南植物园门口满目皆绿,左边草地上矗立着一块扁平的石头,上面刻有郭沫若题写的“华南植物园”五个字。
华南植物园隶属于中科院,是我国重要的植物科学与生态科学研究机构。走进植物园,两排挺拔的大王椰子树矗立在道路两边,一股热带风光特有的烂漫气息扑面而来。园内林木苍翠,绿草如茵,小桥流水,亭台楼榭,分布有许多奇花异树。园区按不同植物种类分为若干个园中园,有国内外引进的热带植物五千多种,是我国植物种质资源保存的重要基地。
为纪念和缅怀植物学家们为科学发展和人类进步做出的贡献,园内还修建了一条科学家雕塑路径,路旁安置了六座中外植物学家的雕像。另外,园中园内,还安置了四位植物学家的雕像,其中就包括刘玉壶。
我这次来,就是专程来瞻仰被称为“华盖木之父”的植物学家刘玉壶雕像的。刘玉壶是中科院院士,世界植物学界著名木兰科专家,曾担任过华南植物园院长。
刘玉壶的雕像坐落在木兰园内,簇拥着雕像的华盖木等木兰科植物枝繁叶荗,郁郁葱葱。阳光有些刺眼,我站在土红色的基座前,凝视着这位宽肩厚臂,脸庞宽大的科学家。阳光下,睿智的微笑凝固在他脸上,他眼睛凹陷,目光炯炯,一头密实的头发,丝丝缕缕,清晰可辨。
1976年,年满六十的刘玉壶准备到广西、云南的原始森林中进行木兰科植物野生种群调查。当时,中国野生木兰科植物的濒危状态令他十分担忧,他预测,如果不及时抢救,大部分野生木兰科植物将会在不久的将来灭绝,那将给地球生态系统带来不可估量的损失。
中国植物资源丰富,占全球十分之一,也是木兰科植物品种最多的国家,主要分布于东南部和西南部。在地质历史上,一些兰科植物起源较晚,1975年,中科院西双版纳热带植物园古生态研究组,在滇南地区景谷县发现了大量树叶化石,化石表面保留了昆虫咬噬的痕迹,这项发现在地质考古生物学上,被称为“第三纪景谷植物群分布区系纪”,是我国少见的生长于3540万年前至2300万年前的植物群,也是唯一没有受到第四纪冰川波及的区系。这是地球历史上最早的关于木兰起源的实证。
木兰科植物多为高大乔木,在维持森林生态平衡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由于姿态美丽、气味芳香、木质坚守,木兰科植物屡屡遭到人类的侵袭。屡遭砍伐,生存环境同时遭到破坏,致使其自身繁衍能力衰退。野生木兰科植物本来已经少之又少,却正以较快的速度在森林中消失,不少种类已处于极度濒危的状态。
那不是一个提倡科学研究的时期,但雨季过后,刘玉壶还是从广州出发了。那时的中国,交通极不发达,乘火车,转汽车,一路考察,他经广西进入云南,已经是半个月后了。植物学的野外调查,是一项极艰苦的工作。翻山越岭,涉水过河,穿越原始森林,吃在山里,住在山里。
刘玉壶来到滇东南地区的文山州西畴县, 在一个叫法斗乡的地方遇到一位护林员,他告诉刘玉壶,这里的原始森林中有一种缎子绿豆树,树干挺拔高大,树皮光滑细腻,树冠高入云端,其枝干上的嫩芽是红色的,而肥厚的叶片却呈深绿色,花挺大,像玉兰花,会结果,果实有大拇指那么大。
刘玉壶十分好奇,作为著名植物学家,他还没听说过缎子绿豆树,他请护林员带他去看看。护林员把刘玉壶带到一座叫草果山的山上,在一片人迹罕至的原始森林中,一棵异常粗壮的树木赫然生长在山坡上。刘玉壶站在山坡下面抬头仰望,这棵树就像一棵巴黎大柱,表面长满苔藓和其他寄生物。树极高,站在山坡下很难看到树冠,刘玉壶又爬到山坡上,再仰头往上看,树冠如巨伞,在蓝天白云下伸展。
两年前,刘玉壶曾经在与云南植物研究所的专家们交流时见过这种树的标本,但是,谁也不知道标本是什么时候留不来的,谁都没见过这种树,谁都不知道这是什么树。在野外发现了这种树,刘玉壶十分兴奋,他知道这次的发现意义非同寻常。他跑前跑后,仔细观察这棵树。植物世界也存在竞争,它们争夺的是生存空间。这棵缎子绿豆树是胜利者,它抢占了阳光充沛的上层空间,以及下面一大片养分充足的土地。
刘玉壶在当地住了下来,护林员带着他,又找到四棵相同的树。
护林员虽然不像刘玉壶那么专业,但在日常工作中,他对每一种植物的观察细致入微。他告诉刘玉壶,缎子绿豆树四季常绿,九月开花,十一月结果,花朵硕大,花色艳丽,散发出一股浓郁的香气,花谢之后,一个花苞里会结三至五颗籽。
刘玉壶认真考察了缎子绿豆树的生存环境,进行了研究,采集了标本,绘制了图片,写了一万多字的资料。
后面找到的四棵树,没有第一棵粗壮高大。刘玉壶猜测,这五棵树应该属于同一母本,那棵大树应该是母株。他相信,偌大的原始森林中一定还会有这种树,他希望能找到另一母本,这样才能保持这种树的生物多样性。这有如大海捞针,刘玉壶忙活了几个月,再也没有收获。为此,他感到深深的忧虑,他预感到,这种珍贵的树已经处在灭绝的边缘。
第二年十一月,刘玉壶又来到法斗乡,他用望远镜在这五棵树上寻找树种,就在那棵大树四十多米高的一根枝条上,他发现了一个籽实包。要想采到这个籽实包绝非易事,刘玉壶想了许多办法,最后跑到西畴县武装部特批了三百发子弹,请部队的神枪手把籽实苞打下来。刘玉壶得到四颗种子,他如获至宝,带着这四颗籽实回到广州,开始人工繁育试验。
二
汉代《西京杂记》卷一中记载有一种树:“终南山有树直上百丈,无枝,上结藂条如车盖,叶一青一赤,望之斑驳如锦绣,长安谓之丹青樹,亦云华盖树。”书中记载的这种树与刘玉壶找到的这种树极为相似,据此,刘玉壶把这种树命名为“华盖木”。
1979年,刘玉壶在中国植物分类学期刊《植物分类学报》上,首次披露了华盖木的存在,揭开了华盖木神秘的面纱,在植物学界石破天惊。
“华盖”一词,在古代有多重意思,首先指的是帝王车辇上的伞盖。晋代崔豹《古今注·舆服》曰:“华盖,黄帝所作也,与蚩尤战于涿鹿之野,常有五色云气,金枝玉叶,止于帝上,有花葩之象,故因而作华盖也。”
后来,“华盖”被引申为达官贵胄车上的伞盖。
“华盖”还是中国古代天文学中的星名,迷信人认为,命中犯了华盖星,运气就不好。星相学家则认为,命中有华盖的人,代表孤傲、孤寂、超然的命象,然而如果性定气坚,且又遇贵人,定是飞黄腾达之兆。《卦辞》说:“华盖星甲木,阳木,主孤高,有科名、文章、威仪,入命身宫,宜僧道不宜凡俗。”
后来的研究证明,华盖木在地球上已经生存了1.4亿年,它记载着地球的成长过程,保存着1.4亿年前的基因,它像一张古老的磁卡,纹理内隐藏着生命起源的奥秘,刻录它一代代繁衍的过程,把1.4亿年来大自然变化的信息传递到今天。
华盖木与恐龙属同一时代,恐龙灭绝了,只在地球上留下一些坚硬的骨骼,一枚枚恐龙蛋化石,华盖木却活着,这对于人类来说是天大的喜讯。
华盖木是中国特有树种,仅存于我国滇东南原始森林中,至今未在其他国家和地区发现过,刘玉壶发现它们时仅有五株,已经极度濒危,后来被列为国家一级保护植物。
滇东南地区位置特殊,第四纪冰川时代,由于地势较低,又有众多高耸着山脉作为屏障,这里形成一个温暖的小气候,使大面积的原始森林及一些古植物保存下来,使许多珍贵的物种在高山及原始森林的庇护下存活至今。
1980年,国际木兰科学术研讨会认定,华盖木为木兰科新属,西畴为华盖木原生地。1992年,华盖木被收入国家珍稀濒危保护植物名录。1999年,华盖木被列为国家一级保护植物。2001年,华盖木被列入《世界自然保护联盟红色名录》,濒危等级为“极危”。
在地球漫长的四十六亿年历史中,地球生物经历了五次生物大灭绝,依次是奥陶纪、二叠纪、三叠纪、白垩纪和第三纪。每一次都给地球生态系统造成了极大的创伤,但是从生物演化的角度来看,也推动了生命不断地变异、适应、进化,最终形成了今天多样而繁盛的生命面貌。人类文明诞生以前,物种的产生与灭绝,受自然规律影响,处于一种较为稳定的状态。当人类在地球上出现,并发展壮大之后,野生动植物的噩梦就开始了,人类攫取大量自然资源维系自身发展,成为除自然力外对大自然破坏最为严重的因素。野生动植物是一个巨大的基因库,一种物种灭绝,这种基因也就消失了,生物的多样性也就在灾难中耗尽。华盖木因木质优良曾经遭遇大量砍伐,其赖以生存的生态环境也遭到严重破坏。
闭上眼睛想想,一棵棵高贵的华盖木哗啦啦倒毙时的情景,是多么令人心疼啊!
1984年,在云南澄江发现的一个古生物化石群,让人们如实看到了地球海洋中最古老的动物原貌,使得人们认识到,自寒武纪生物大爆发时,地球海洋里就生活着众多生态各异的动物,为人们研究早期生命起源、演化提供了宝贵证据,并帮助人们了解了寒武纪生物大爆发中生物演化,以及诱发这种大爆发的原因。
澄江古生物化石群遗址保存的多数是动物化石,而在云南高耸的大山、深险的峡谷、苍茫的原始森林中,除华盖木之外,也还有无数古老的植物遗存,它们都面临着灭绝的危险。这绝不是危言耸听,地球上随时有物种在灭绝,它们中有的可能还未被人类所认识,就从地球上消失了。
珍稀濒危植物是野生植物中最脆弱的群体,一种植物的灭绝不仅意味着其基因、文化和科学价值的丧失,还会引发其生物链中十至三十种其他生物的灭绝,并形成物种灭绝的多米诺骨牌效应,从而打破整个生态系统的稳定。植物专家估计,中国的珍稀濒危植物大概有4000种至4500种,有40种已经灭绝,有3879种高等植物受到灭绝的威胁。近年相继在云南发现的“富民枳”、“巧家五针松”等40多种极小种群的珍稀濒危植物,都是植物界的“活化石”,它们与澄江古动物群化石不同的是,它们都还活着,但已经到了断子绝孙的边缘。
一个物种历经亿万年演变,与人类共存是多么的不容易,但它们的告别悄无声息,这是我们,我们的子孙后代,以及全人类无法弥补的遗憾。近几十年,中国不遗余力地抢救和保护各种珍稀濒危动植物,并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效。
三
1984年,我第一次采访吴征镒是在他的办公室,采访完后他带我来到昆明植物研究所新建的几个专业园去看了看。当时木兰园刚刚建成,园内种有几棵不足一米高的华盖木,他手指着身边的一棵对我说,你别小看了这小树,它的身价无与伦比。
吴征镒是中国植物学界泰斗级的人物,他曾经在西南联大教生物学八年,对云南的生物资源做过细致的调查,并做了两万多种植物标本。20世纪50年代,他参加并领导了中国植物资源考察,开展植物系统分类研究,之后发表和参与发表的植物新分类群1766个,是中国植物学家发现和命名植物最多的一位。正是他改变了过去中国植物主要由外国学者命名的历史。他曾获得过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2011年12月10日,国际小行星中心将第175718号小行星永久命名为“吴征镒星”。
1951年,吴征镒和蔡希陶一起在西双版纳原始森林中考察半年之久,确定了西双版纳作为我国橡胶种植的主要基地之一。1958年,他主动要求从中科院植物研究所调到昆明植物研究所。在他亲自主持下,昆明植物研究所从1983年开始华盖木的“引种栽培、迁地保护”。当时,经费很少,作为院长的吴征镒到处找钱建起了木兰园,引种了华盖木,并成立了专业研究团队。
作为第一代华盖木研究人员,吴征镒曾经多次带团队在野外考察,寻找古代植物遗存。
西畴县那五棵华盖木近亲繁殖,对华盖木的种群繁衍极为不利,会导致华盖木自身的生物多样性损失,植株退化。寻找到另外的华盖木母树,是华盖木人工繁育的关键。
2000年,我到昆明植物園看望吴征镒,84岁的他还在工作,带研究生。当时,吴老给我讲起一件事,由于环境的变化,野生植物种质资源消亡的速度越来越快,吴老心里十分着急。但当时院里经费紧张,吴老向中科院、云南省林业厅、省计委打报告申请经费,希望尽快建立云南野生植物种质资源库,对其中有近期开发价值的野生植物种质资源进行遗传背景的分析研究,提取DNA进行分类保存,在此基础上进行合理开发。但申请了几年,一直没有结果,思前想后,吴老给朱镕基总理写了一封情词恳切的信。
后来,我听说朱镕基总理亲自做了批示,给吴老拨了几千万专项资金。于是,吴老亲自主持,建成了仅次于英国皇家植物园种质资源库的云南野生植物种质资源库。这为今后华盖木以及其他野生植物的种质资源保存、研究、开发提供了保障。
孙卫邦是吴征镒的学生,是昆明植物研究所第二代华盖木研究人员,他始终不相信莽莽苍苍的滇东南原始森林中,就只有刘玉壶发现的那五棵华盖木。2001年,孙卫邦团队开始在适宜华盖木生长的区域进行种质资源野外调查。
群山连绵,林海茫茫,他们穿梭在原始森林中,不断扩大寻找范围,从西畴县找到富宁县、砚山县、麻栗坡县;从文山州找到红河州。偌大的原始森林,要从中找到珍稀的华盖木,就像要从漫无边际的荒原中找到插在草丛里面的绣花针,那得有多难啊!但孙卫邦他们没有放弃。他们发动当地老乡和林场工人帮忙找,为他们提供线索。
很多次,老乡带信给孙卫邦,说找到华盖木了,等孙卫邦兴冲冲地从昆明驱车七八个小时赶去,老乡找到的却不是华盖木。可每次得到消息,孙卫邦都没放弃过。为了让更多人了解华盖木,帮助寻找华盖木,每次野外考察,孙卫邦都会复印一些图片资料带在身上,分发给分布区域周边老乡。这个办法行之有效,老乡们认识了华盖木,提供的信息会准确一些。
对他们帮助最大的,是林场护林员。他们经常巡山,对原始森林中的树木心中有数,正是在他们的帮助下,孙卫邦他们在西畴县法斗乡河麻湾的原始森林中,又找到一棵华盖木。或许别人难以理解,当他们在茫茫原始森林中,站在终于找到的华盖木前,仰望着华盖木在蓝天白云间伸展开来的树冠时,内心是那么激动。梦里寻它千百度啊!他们张开双臂,抱住那棵华盖木,泪流满面。接着,在法斗乡同一片原始森林的另一座山——南昌山中,他们又找到了一棵。找到这两棵华盖木,与刘玉壶发现那五棵华盖木时间相距近30年。
随后,云南加入进来的团队根据华盖木生存的环境条件,把寻找范围扩大到邻近州县,果然相继在文山州马关县,红河州金平县、屏边县又找到四十七棵华盖木。每找到一棵华盖木,就意味着现存华盖木种质资源中又增加了一种不尽相同的基因,增加了一种遗传多样性。
木兰科植物花朵都特别漂亮,华盖木的花朵就像玉兰花,花型大,花瓣肥厚,有粉色、红色、白色、白花红边,像一个个漂亮的小喇叭。但一般情况,三十年左右的树才会开花。孙卫邦在山里找华盖木找了十年,无数次听人描绘华盖木花朵的模样,却还没见过。他交代自然保护区的同志,一旦华盖木开花,立即通知他。头一年,他接到通知赶到那里,只看到几朵枯萎凋零的落花。第二年却又去得早了一点,树枝上挂着的还是花蕾。
华盖木的花都长在几十米高的枝条上,他请当地老乡帮忙,采下几朵花蕾,用白糖兑上清水,把花枝插在水中,一小时左右,花开了。孙卫邦高兴地拿着照相机反复拍。这是人类第一次拍到野生华盖木的花朵,后来孙卫邦还拍到了华盖木的籽实,这些照片绝无仅有,成为华盖木研究的珍贵资料。
四
拯救一种濒危植物,是一个艰辛而又漫长的过程,需要一代甚至几代人共同努力。曾庆文是刘玉壶的学生,是广州华南植物研究所物种多样性保育研究组研究员、硕士生导师,是唯一从种群生物学、繁殖生物学、遗传多样性、种子传播等方面综合研究华盖木保护的科学家。
曾庆文同刘玉壶一样,是一个把事业看得比财富和生命更重的科学家。他的足迹踏遍了广西、云南、贵州的深山密林,每年至少有四个月在原始森林中转悠,采集标本,野外观测。木兰科植物生长的地方,都是高温多雨,花粉多,湿气重,还有瘴气,曾庆文因此落下了病根,不断咳嗽,但他一直挺着,最终促使肺纤维化,整个左肺被切除。术后身体虚弱,可他躺在病床上依然在工作。出院以后,他又毫无顾虑地又投入了大山的怀抱。
曾庆文科研团队的主要研究课题,是华盖木的濒危机理,为挽救这个濒危物种提供理论保障。为了掌握华盖木的种群复壮技术,他曾多次来到西畴县法斗乡原始森林中进行实地研究。2000年,曾庆文申请到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先后进行了观光木、拟单性木兰属的保护生物学与种群复壮实验研究,揭示了观光木、云南拟单性木兰的濒危机理。2005年,曾庆文由广州华南植物园选派,赴英国皇家植物园丘园和爱丁堡植物园进行木兰科植物分类学研究。2010年,曾庆文又申请到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继续对华盖木的种群复壮技术进行研究。为了掌握华盖木的开花、授粉、结果习性,从2011年春季开始,曾庆文带团队奔赴法斗乡,在那棵巨大的华盖木旁边,搭起一个大型竹木观察架,他多次爬上架子,进行传粉生物学野外观测和实验,每次在架子上一待就是四五個小时,甚至七八个小时。
华盖木是一种雌雄同株异花授粉的被子植物,通过观察,曾庆文发现,华盖木的授粉机理非常特殊,华盖木开花时,会有一种甲虫飞到花上,华盖木的花朵会随气温变化开放闭合,花开时,甲虫爬进花蕊,花朵闭合后,甲虫就在花蕊里待着,花又开时,甲虫爬到另一朵花的花蕊里,从而完成授粉。曾庆文还发现,华盖木的传播,多半是由大鸟完成的。芳香的籽实吸引大鸟,大鸟飞来,叼走籽实,飞翔过程中,籽实掉落,在远离母树的地方发芽生长。
2011年3月,曾庆文在法斗乡对140朵华盖木花进行人工授粉,结了九十七个果。遗憾的是,结出的果子成熟后,进行人工育苗,没有一粒出苗。2012年开花时节,曾庆文再次对170朵花实施了人工授粉。九月中旬,他准备到实验基地观察一下,人工授粉后华盖木的挂果情况,找出去年果实不出苗的原因。另外,他准备采摘西畴华盖木标本,与马关、红河采摘的华盖木标本进行DNA检测和鉴定,对比这几个地方野生华盖木基因情况。临出门前,爱人邹婉清一把拉住他,叮嘱他说,都快50岁的人了,这次记得不要再爬树。曾庆文笑呵呵地哄她说,不爬了!不爬了!
9月20日早上八点刚过,太阳就升到了原始森林的上空,温暖的阳光穿过枝叶的缝隙,照射在绿茵茵的草地上,一时间,空气潮湿的原始森林中雾气缥缈。一位护林员带着曾庆文和他的两个学生来到实验基地。曾庆文早把妻子的叮嘱抛在脑后,他利索地和两个学生一起爬到四十余米高的架子上,查看华盖木花朵授粉后的挂果情况,一一对每朵花的变化进行登记。
晴得好好的天气突然变了,一会儿就下起毛毛细雨。中午十二点多,曾庆文和两个学生登记完后,正在下架子准备出去吃饭,他突然发现有两个样本没有登记,就和学生再次爬到架子上。细雨纷纷,山里雾气大。曾庆文为了靠近样本,观察得更仔细一些,便从架子上爬到树枝上,不慎脚下一滑,突然从四十多米高的树上坠落。当护林员刘廷跃和他的学生叶心芬在十多米深的山沟树丛里找到他时,他已面色发青,不省人事。曾庆文被送往医院,但因伤势过重,抢救无效牺牲。
曾庆文的老父亲经商几十年,生意做得大,年纪也大了,他看曾庆文住房条件差,生活拮据,曾几次提出来,让曾庆文退职,接替他的生意。可曾庆文放不下他热爱的事业,每一次都婉拒了。葬礼上,老父亲老泪纵横地感慨道:儿啊,没想到你从事的科研工作会如此危险啊!
五
昆明植物园离我家不远,我有时会一个人到那里走走。园区的规模比以前扩大了不少。
那天早上九点,我如约来到植物园门外,孙卫邦出来,把我带进园区。温暖的阳光照在身上,我们边走边聊,一会就来到了木兰园。这里现有引种培育、迁地保护的华盖木七十七棵,棵棵长得青枝绿叶,郁郁葱葱。这些树引种时间不同,高高矮矮,粗粗细细,参差错落。树龄短的,最矮的不过四五十厘米,不及腰高,树龄长,比较高的已达20米左右。高大一点的树旁边都搭了架子,方便研究人员上去观测。
这些华盖木全是植物园每年派人去野外采集种子培育出来的。为保留人工引种的遗传多样性,他们尽可能采集分布在不同区域的种质资源,这项措施有效保存了野生华盖木70%左右的遗传基因。
孙卫邦是昆明植物园主任,也是中国木兰科植物学权威专家,园里的七十七株华盖木,每一棵的基本情况他都了如指掌。他把我带到最大的一棵树下对我说,2013年3月14日早上我来到木兰园,远远就看见1983年引种栽培的一棵树上,开出一朵白白的花。时隔三十年了,这是我们园引种栽培的华盖木第一次开花。我激动万分,赶紧安排团队成员搭钢架,爬上去拍照、摄像、观察、取样。
我一眼就认出来,这就是当年吴征镒跟我说的,身价无与伦比的那棵树。它的树杆已经有二十厘米左右粗,二十多米高。
孙卫邦继续对我说,木本植物保护周期很长,能够开花、结果,说明我们的迁地保护取得了成效。此后,每隔一两年,园里都会有新的引种植株开花。每到花期临近,我们就在这里白天黑夜蹲守、观察研究,提取一手资料。迁地保护最大的好处,在于方便开展有性繁殖等科学研究,植物园引种的华盖木给这项研究提供了很好的样本。这些年,对华盖木的科学研究不断深入,成果不断增多。过去,学界一直认为大部分木兰科植物种子难以在种子库长期保存,但通过我们多年实验证明,华盖木种子是能够在种子库中以低温及超低温方式长期保存的。我们的科研团队还为木兰科植物开发了一套超低温保存新技术,已在十余种木兰科植物种质资源的保存中应用。我们还与周边林场、研究单位合作,在收集华盖木种源的基础上建设种质圃,进一步开展迁地保护试验。
六
拯救一种濒危植物,首要任务是培养种苗,令植物学家感到苦恼的是,传统的培育方式一年只能做一次。然而,组织培养技术的介入,成几何倍数加快了种苗培育的速度。
孙卫邦的妻子罗桂芬是昆明植物研究所正高级工程师,她用二十多年时间攻克了组织培养快繁技术,为六十余种极小种群野生植物保护提供了技术支持。
孙卫邦一直在想,除了人工引种栽培,是否能采用组织培养快繁技术培育华盖木树苗,加快拯救华盖木的速度。
2010年,孙卫邦把罗桂芬带到木兰园十几米高的华盖木下对她说:你要不要试一下华盖木的组织培养?
罗桂芬先有些犹豫,普通木本植物的组织培养就不太容易,何况这么高大的乔木?看着丈夫期盼的目光,她还是决定试试。
罗桂芬带领团队,开始采用两种方法进行试验,一是让华盖木的种子在试验室里无菌萌发,然后进行组织培养,二是从木兰园生长了二十多年的华盖木上采集顶芽和腋芽实施无性繁殖。开始,两种方法试验都不顺利。第一种方法的难处在于,当时昆明植物园人工种植的华盖木还没开花结果,野外结果的华盖木,树很高,结果量又少,不易采集,而且用作组织培养实验的种子不能长期保存,一年只能尝试一次,一旦失败,只能等待来年。因此,为掌握华盖木种子无菌萌发的技术,罗桂芬足足试验了五年。
第二种方法有一项关键性技术难题有待攻克:多数木本植物在组织培养过程中容易不断产生酚类物质,渗入培养基后导致培养基褐化,种苗随之慢慢死亡。最初,罗桂芬怀疑是芽不够嫩,可哪怕是春天还带着苞片的嫩芽,褐化现象依然存在。
有时,攻克一项科学难题的,仅只是一种简单的方法,而找到这种方法,需要长期的经验积累,以及触类旁通的聪明才智。罗桂芬从其他成功的試验中找到灵感,试着将外植体换瓶位置的次数从一个月换一次改为三天换一次,褐化情况越来越轻。渐渐的,外植体接触的培养基不再褐化,她获得了成功。
两种方法都获得了成功,仅只是完成幼苗培育的第一步。幼苗从组织培养瓶栽种到土壤里,同样不容易。有些幼苗不生根。罗桂芬不断调试激素和培养基的配比,反复试验,对比数据,仔细分析。从2010年到2015年,华盖木组织培养快繁技术实现突破,再到2017年获得第一株组培苗,罗桂芬整整奋斗了七年。
罗桂芬干了三十多年组织培养,她认为华盖木是最难做的。在最艰难的那段时间,罗桂芬几次想放弃,孙卫邦一直鼓劲她,向她强调这项试验的意义。
七
也许人们认为物种灭绝只是生态系统一件微不足道的事,事实上,每一次物种灭绝都会给地球生态系统带来不可逆转的变化。大多数人可能不会联想到气候和物种灭绝之间的关系,实际上它们息息相关。在生态系统中的每个物种都对空气和水的质量及其循环起着关键作用。例如,植物可通过光合作用吸收二氧化碳,从而有助于缓解全球气候变化。然而,由于物种灭绝,植物数量减少,无法充分吸收二氧化碳,导致温室气体排放增加,加速全球气候变化。3.8亿年前,地球正处于泥盆纪晚期,植物已经出现在陆地,当时还没有食草动物,植物处于没有任何天敌的状态,只要环境条件合适,它们就能够大量生长。而植物的生长又导致地球上的碳、氧循环遭受破坏,由于没有足够的生物消耗氧气,导致地球上的氧气含量不断上升,二氧化碳含量不断下降,最终导致地球温度下降,许多无法适应寒冷的生物因此灭绝。这就是地球上第二次物种大灭绝的直接原因。
一些专家研究得出结论,地球正在经历第六次物种大灭绝,今年夏天全球气候暴热,自然灾害频发,似乎印证了这种观点。史前发生的五次物种大灭绝,无论诱因是什么,都是自然现象造成的,都与日照、空气、气候有关。第六次物种大灭绝,原因很可能是人类活动对地球环境的破坏。近年来,随着环境污染和气候变化的加剧,物种灭绝的速度不断加快,每年有近千种物种从地球上消失。全球气候变暖的同时,水源也变得愈发缺乏,这使得物种的生存越来越困难。而这些行将灭绝的物种可能正是人类食物、药物的来源,或者生活必需品、工业产品的原材料。还有,一些对水有净化作用的物種消失后,水质随即下降,加剧了水危机,从而导致了人类生命的损害和环境问题的恶化。而这次的物种大灭绝,影响远比我们的想象更加深远。物种灭绝是指一种生物被连续的自然灾害或人为因素破坏,以至于种群数量逐渐减少,当这种生物种群全部灭绝时,它们就从地球上永远消失了。如果人类不能有效制止第六次生物大灭绝,人类也将在这次生物大灭绝中灭绝。
拯救华盖木以及其他濒危物种,就是拯救地球环境和拯救人类自己,这无疑是一项伟大的事业,不仅只是植物学家在做,一些有生态意识的人们也在做。特别是一些林场职工,他们的方法更直接。他们利用与华盖木朝夕相处的优势,直接从野外生长的母株上采集种子,在适合华盖木生长的大山里,把华盖木幼苗培育出来,他们甚至比专家们动手还早。
朱代清是西畴县小桥沟国家自然保护区一位普通的护林员,他热爱莽莽苍苍的原始森林。从1975年起,他在自然保护区大森林里巡逻,足迹踏遍宽阔的原始森林。朱代清是个有心人,每次巡逻他都细心观察身边的植物,最初看到华盖木,他并不知道这是珍稀植物,他只是觉得奇怪,森林中大多数植物都会连片生长,种群数量巨大,可这种树数量极少,在他负责巡查的法斗乡草果山大面积森林中仅有五棵。这种树花很好看,果实十分稀少,花果长在几十米高的枝条上,成熟的种子,有些还在枝头上就被鸟吃了,有些落到地上很快便被老鼠或其他动物吃了,很难萌发。朱代清想来想去,决定自己培育这种树苗。
为了得到华盖木种子,等到果实成熟,朱代清就找来上树工具,爬到树上采集。种子成熟有前有后,好不容易爬上去,有的种子还没成熟,他便计算着日子,等种子完全成熟了,再爬上去采。一朵华盖木花,会结出五至六颗种子,其中只有一两颗能够发芽。朱代清还有一手绝活,他能从种子极小的重量差别掂量出会发芽的种子。
作为林场职工,朱代清懂得植物育苗技术,经过几次试验,他获得了成功。看着生长出来的幼苗,朱代清高兴极了。由于长期在潮湿的原始森林中工作,朱代清患上严重的风湿病,双腿膝关节肿得厉害,不得不使用拐杖。虽然行动不便,但他坚持每周到苗圃观察幼苗的成长。
这期间,朱代清克服了常人难以想象的困难,他拄着拐杖进山采集标本,研究珍稀植物的生长特点。经过二十多年的精心培育,朱代清培育出华盖木幼苗八百多株,香木莲、滇桐等十六种珍稀植物七万多株,使它们在濒危的绝境中生命得以延续。
朱代清拯救珍稀植物的行动引起了云南省林业科学院、广州华南植物研究所和广西南宁树木园等研究机构的重视,这些机构每年派专家到他的苗圃考察,探索研究朱代清成功的经验。后来,朱代清培育的华盖木被成功移植到广州华南植物研究所、广西南宁树木园等机构,供专家们进行研究。
李友彬就是法斗本地人,他在西畴县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护分局小桥沟管护站任站长多年。按照现在的说法,他就是保护那五棵野生华盖木的第一责任人。按照局里的规定,他每年至少要进保护区原始森林四次,观测和记录那几棵国宝级华盖木的生存状态。可每年,他进山的次数超过规定无数倍。
进原始森林的山路不好走,去年八月李友彬带我去看那棵最大的国宝级的华盖木。我弓着腰,气喘吁吁地跟在他后面。正是雨季,空气潮湿,荒草疯长。李友彬用一根竹棍,不断挥打路上的杂草,勉强开辟出一条路来。
李友彬告诉我,有一年国际木兰科植物大会在广州举办,外国专家们都提出,要看看西畴那几棵野生华盖木,大会主办方就把他们带到西畴来,是李友彬带他们进山的。外国专家们看到这棵珍贵的华盖木,兴奋不已,拍了好多视频、照片。
李友彬还说,2000年以来,华盖木的信息越传越多,有人就打起了它的歪主意,炒作最热的时候,甚至传言,一棵华盖木幼苗,可以换一架直升机。当时,有人从香港来找李友彬,开价18000元一斤收购华盖木种子,被李友彬一口回绝了。当时,李友彬家里就有种子,还有他自己培育的四百多株华盖木幼苗,他把这些都以极低的价格转给了昆明植物园。这些幼苗达到一定苗龄之后,分别被编号、挂牌,移植到回归试验区。
2008年10月16日,几个不法分子进入保护区原始森林,企图盗挖移植到回归试验区的华盖木幼苗,偷运到外地高价出售,被小桥沟林场护林员张奇辉发现,张奇辉不顾自己势单力薄,冲上去制止这些不法分子的违法行为,被不法分子残忍杀害。
当年曾庆文从树上掉下来,是李友彬带人上山把他抬出原始森林的。曾庆文牺牲的第二年,为了纪念他,李友彬带着大伙在另一块山林里,栽种了数十棵由曾庆文人工授粉后培育的幼苗,经过十多年的风风雨雨,这些树苗已经亭亭玉立。
小桥沟国家自然保护区是古老植物的家园,这里森林茂密,物种丰富,是世界上亚热带地区保存较为完整的原始森林。走进这片生机勃勃的原始森林,仿佛走进一个纷繁的植物世界,每一寸土地都充满绿意,我感觉每一脚踩下去,脚下的青草就会流出绿汁。
我终于站在了那棵最大的华盖木前,抬头仰望,华盖如伞,一束束阳光从绿叶间照射下来。在这片神奇的森林中,十多个人牵手围不过来的黄连木、榕树等大树并不少见,但我感觉,眼前这棵树就是“王”, “木兰之王”“、华盖之王”、“森木之王”。
轻轻抚摸这棵沧桑的大树,它冰凉的皮肤使我有一种触电的感觉,我能感受到它古老生命的脉动,能想象得出它顽强的生命所经历的大自然的变化,以及人类文明进程中的种种挑战。
八
车在公路边停下来,我们刚下车,雷连红就迎面走过来,他已经在这里等候我们多时了。雷连红是香坪山林场副场长,香坪山林场建于1951年6月,是新中国成立后云南省建立最早的国有林场之一。为拯救和保护以华盖木为代表的珍稀濒危植物种质资源,1986年,云南省林业科学院、文山州林木种苗站、西畴县香坪山林场联合,在香坪山林场建了一个珍稀濒危树木园。取名为“香坪山林场珍稀树木园”,后更名为“珍稀木兰谷”,这是个木兰科及珍稀濒危树种的迁地栽培基因库。
进入木兰谷,上几级阶梯,一棵直径30厘米左右的华盖木耸立在我面前,树干笔直,枝繁叶茂。这是一棵二十多年树龄的华盖木。木兰园现有相同树龄的人工培育华盖木二十多棵,树龄较小的有千余棵。还有与华盖木伴生的黄连木、白玉兰、云南茶花、滇桐,都是珍稀濒危树种。林下还种植了三七。
从2007年开始,由中科院昆明植物研究所、云南省林科院等单位共同参与的“华盖木回归自然拯救种植行动”正式启动,人工培育的华盖木树苗被移栽回原生地,开展回归试验及示范。
拯救一种树,最后的成功在于它们回归自然后,能恢复在自然环境中的生存繁衍能力,逐步擴大种群数量,保存基因的生物多样牲。“拯救行动”使华盖木生存环境得到恢复,种群扩大。自然保护区先后共培植华盖木树苗三千多株,完成了采种、选种、培育、试验、栽培的回归,并在西畴的原始森林中开始了种群复壮的伟大旅程。
如今,西畴县已有人工培育的华盖木一万五千余株,让人万分欣慰的是,拯救华盖木还带动了各界对其他珍稀濒危植物种质资源的保护。目前,香坪山林场的“珍稀木兰谷”,汇集了来自云南、四川、湖南、浙江、广东、辽宁等地及印尼等国家和地区的热带、亚热带木兰科植物,以及其他珍稀濒危植物一百八十四种。郁郁葱葱的一千五百亩林地,成了名副其实的珍稀濒危树木迁地保育种质“基因库”。香坪山林场育苗站三十多年来,还培育出包括华盖木在内的几十个珍稀濒危植物幼苗一百七十八万多株,它们全都已经回归自然,摆脱了物种灭绝的威胁。
【作者简介】曹卫华,作家、民间文艺家,文学副研究员,曾任某期刊主编。出版(发表)长篇小说《世纪之战》《岁月长河》《风云洗礼》等,中短篇小说集《金船》 ,长篇报告文学《狂飙》,报告文学集《东川记忆》《成就伟业》,散文集《东川飞翔》 ,民族民间文学专著《唱透青山红土情》《永远的歌唱响在历史的天空》等。另有70多篇中短篇小说,200余万字散文、诗歌、报告文学、文学评论、戏剧等发表。主编散文集《跨越》《追求》 获地市级以上奖项20余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