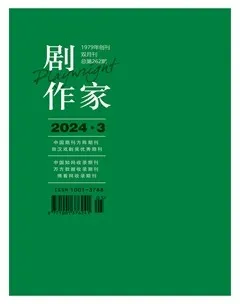论伽森狄哲学对莫里哀喜剧创作的深层影响
2024-06-07陆铭泽
陆铭泽
摘 要:学界过往对莫里哀的研究中,罕有对于莫里哀喜剧与伽森狄哲学之间关系问题的关注。文章首先探赜了法国古典主义文艺理论、笛卡尔唯理主义的本质以及伽森狄对笛卡尔的反驳之要点。随后通过对《伪君子》的细读分析,认为莫里哀虽是法国新古典主义时期的喜剧家,但他的思想却深受伽森狄影响,建立在唯物主义的和伊壁鸠鲁主义的基底上,而与当时的古典主义文艺法则和笛卡尔哲学中唯心化的一面始终保持着距离。他所秉持的“理性”是唯物主义的,其作品中的讽刺矛头指向的也是各种“失常”后的“姿势化”行为、癖性。
關键词:莫里哀喜剧;《伪君子》;古典主义;笛卡尔;伽森狄
自1921年《小说月报》12卷连续刊载了高真常译版的《悭吝人》开始,莫里哀戏剧在国内的译介和研究已有一个多世纪之久,相关成果也颇为丰富。回顾我国的莫里哀研究史,在结出硕果的同时,也由于多方面的原因和局限,导致我们对莫里哀的研究“还受到一些传统的思维定式的限制,未能取得突破性进展”[1]P81。这种思维定式,很大程度上反映在我们仍旧习惯于将莫里哀视作一位具有阿里斯托芬式辛辣讽刺精神的“反封建的优秀战士”[2]P21。而其他诸如“现实主义喜剧家”“人民性”等观点,也都基本与这一固有的定性相互接通。然而近年来有学者指,“莫里哀式喜剧是一个开放性概念”[3]P40,并对于一贯地对莫里哀抱以反封建战斗性立场的看法提出了异议。其言外之意是希望我们注意到莫里哀戏剧创作的多元性、复杂性及其背后的“历史化”因素,即将莫里哀还原到17世纪法国新古典主义的历史语境中去加以公允的考察,而非“去历史化”地将我们遵奉的主流意识形态强加给他,警惕陷入到一种认知上的过于简单、固化的泥潭中去。
笔者认为,在莫里哀传世的三十多部喜剧作品里,很大程度上都受到了同时期著名唯物主义哲学家伽森狄的影响。以此为着眼点,能够更好地探赜莫里哀喜剧背后的复杂性。然而过往学界对这一问题却并未给予足够重视,只有极少数的提及。譬如吴达元指出莫里哀“曾有机会听过唯物主义哲学家伽森狄的讲学,人们以此解释他喜剧中的自由思想”[2]P21,遗憾的是未能继续深入论述。而伽森狄对莫里哀的影响也不仅只体现在其作品中的自由思想问题上。故本文将以伽森狄哲学与莫里哀喜剧之间的内生性关联为着眼点,首先简要梳理分析笛卡尔唯理主义及伽森狄对笛卡尔的反驳诸要点,进而以《伪君子》为范例,在文本精读的过程中发掘伽森狄对莫里哀的深层影响,最终试图就法国古典主义戏剧思想、本质及《伪君子》,乃至整个莫里哀喜剧在这一谱系中的定位、创造性、特殊性等问题做出回答。
一、笛卡尔哲学对古典主义理论的影响及伽森狄对他的反驳
17世纪法国处于一个高度“立法”、服从权威的时期,法国古典主义是与君主制度相伴相生的中央集权产物而布瓦洛的《诗的艺术》便是它的最高法典。在《诗的艺术》中,贯穿始终的主线是“理性”——“要爱理性,让你的一切文章永远只从理性获得价值和光芒”[4]P10。理性也被布瓦洛认为是能够照耀一切的并需要被文艺创作所遵循的永恒、绝对标准。而布瓦洛的理论乃至整个古典主义又都深受笛卡尔哲学的影响。这一影响主要来自两方面:一是笛卡尔的唯心化的唯理主义,二是他的心物二元论。就前者来看,笛卡尔的理性主义延续了柏拉图、斯多噶等人唯心化理性主义传统,认为理性是人人生来便有且均等的“天赋观念”[5]P137、良知良能,它作为“一种普遍的工具,可以使用于任何一种场合”[5]155。人类也应能够在理性的导引下获取知识、迈向真理。他并不认为感性经验是知识的源头活水,只有依据天赋观念来推演的理性才是知识的可靠源头,一切事物也都应放置在理性这一绝对权威性的标尺上进行衡量与修正。笛卡尔对理性的看法也导致古典主义文艺美学中情理冲突中理智的无上重要性、各种金科玉律的制定及对人物道德伦理的严格要求。就后者来看,笛卡尔认为灵肉两分、物质与精神世界二元并存,又在此二者之间安置了上帝进行沟通,这种唯心化的并带有调和与折中色彩的思想构成了当时封建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调和、妥协的思想根基,亦导致新古典主义文艺创作中(主要是戏剧)情理冲突中理性的第一重要性、各种金科玉律和规则的制定及对人物道德伦理的严格要求。
笛卡尔的二元论、我思故我在的哲学命题尽管在对教权统治、宗教神学、禁欲主义的反叛上具有进步性,但其在思想上未能与经院哲学真正分道扬镳。同时期的法国,伽森狄曾对笛卡尔的唯心主义先验论进行过猛烈的批驳。尽管伽森狄对开明君主和君主专制制度同样予以拥护,但是在哲学思想与认识论上却与笛卡尔大不相同。其在《对笛卡尔〈沉思〉的诘难》一书中也对笛卡尔进行了一系列攻讦,并构筑起自己的唯物主义经验论,择要提炼如下。首先,伽森狄并不认可精神本原的看法,一切事物都具有广延性,都是物质性存在,对于笛卡尔著名的“我思故我在”这样的主观唯心命题,伽森狄驳斥道:“当你还在你母亲肚子里的时候,或者刚出来的头几天、头几个月,或头几年,你是否还都记得你想了些什么。”[6]P10由此一来,认识主体就不再是精神实体的东西,而是具有健全思想能力的人。再进一步,伽森狄最终确证认识是心灵对客观实体的反映,二者皆不可缺。其次,在认识论的问题上,伽森狄批驳了笛卡尔的唯心主义天赋观念论及将感觉视作错误的源头的看法:“假如你一切的感官作用都没有了,以至于你什么都没有看见过,物体的什么表面或尖端都没有摸到过,你想你能够在你心里做出三角形的观念或其他任何形状的观念来吗?”[6]P66伽森狄指出感觉源于认识,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存在先后关系,只有事物作用于感官,我们才能进而生成相应的观念。但他在强调感觉经验的同时也肯定了理性的重要性,感性认识有待于上升到理性认识,但后者要依靠前者。此外,伽森狄还发表过《关于伊壁鸠鲁的生、死和快乐学说》《伊壁鸠鲁哲学体系》等著作,汲取了伊壁鸠鲁哲学中的原子论,伊壁鸠鲁式唯物主义也是他反对笛卡尔的有力武器。
如果说笛卡尔的唯理论和二元论构成了古典主义文艺理论的哲学基础,那么这种带有唯心色彩的唯理论在布瓦洛、拉辛、高乃依那里则有着鲜明的显现。但莫里哀的喜剧创作却与古典主义文艺美学原则中唯心化的一面始终保持着一定的隔膜和距离。而与他更为贴近的恰恰正是伽森狄的思想。莫里哀曾与伽森狄有过接触并接受过他的教导。这位带有反叛精神的、将伊壁鸠鲁从禁书中解放而出的唯物论者也由此将他自由、快乐的世界观和唯物主义思想灌注到了莫里哀的心田之中。也正是因为莫里哀与他产生了思想上的缠绕,故而在其本人的喜剧创作中展现出诸多值得我们深思的现象。
二、从《伪君子》看伽森狄对莫里哀创作的影响
我们通过以上对伽森狄个人的哲学思想及其对笛卡尔哲学的诸多反驳要点简练梳理分析后,是为进一步追问、把握莫里哀的头脑里沾染上伽森狄思想的色彩后如何在具体戏剧创作中加以感性显现。接下来将通过对《伪君子》的细致剖解,更为具体地探析莫里哀的喜剧创作与伽森狄思想之间的深层关联性,并对“莫里哀喜剧”这一概念及其与古典主义文艺理论之间的关系做出些许新思考。
1.基于奥尔恭与柏奈尔对笛卡尔唯心哲学的批判
《伪君子》的核心情节是瓦赖尔与玛利亚娜这对青年男女的爱情遇阻而据理反抗,以及众人对答尔丢夫伪善面具的揭穿。莫里哀固然把尖锐讽刺的矛头对准了答尔丢夫这个伪善者,但他之所以能在奥尔恭的家中兴风作浪,根源上离不开奥尔恭和柏奈尔这两根支柱。正是因为奥尔恭将这位戴着伪善面具的宗教骗子请入家中并将他奉为座上宾,再加上他与母亲二人被这位骗子所操控继而近乎偏执地替他辩护,方才成就了答尔丢夫的放肆无边。而奥尔恭何以要为家中引入这么一位“上帝”呢?伯格森曾在《笑》的“性格的滑稽”一章中指出:“喜剧不把我们的注意力导向各种行为,而把它导向各种姿势。”[7]P96如果说悲剧更致力于深入雕琢刻画某个独一无二的丰满个体,那么喜剧则倾向于描绘带有共同性的类型。作品中,奥尔恭将答尔丢夫请进家门甚至对其加以上帝般的崇拜这一行动背后的复杂动机恰恰被莫里哀删削成了“姿势”,观众也在奥尔恭的“愚蠢”中被这位傻乎乎的老者频频逗乐。但这种“姿势”化的处理并不代表奥尔恭的情感不能被加以共情和体验,我们深入到一些具体的场面中,是可以感悟其间的趣味曼妙与意味深长的。
《伪君子》的四幕五场正是我们体会奥尔恭生命情感的重要切口,该场面也是欧米尔当着奥尔恭的面通过其巧设的“计谋”彻底揭穿答尔丢夫的虚伪本性的重要场面,全剧的情势也由此发生转变。可匪夷所思的是,当欧米尔用布好的圈套引得答尔丢夫开始展露其流氓本质时,早已藏在桌下暗中目睹一切的奥尔恭却注视着妻子被不断调戏但迟迟不肯现身制止。莫里哀用其精湛的笔法为欧米尔设置了丰富的戏剧动作来提示观众注意这一点:她不断地把目光望向奥尔恭藏身的地方,又接连不断地通过“咳嗽”这一信号暗示丈夫,直到她找到托词让答尔丢夫出门看看是否有人,奥尔恭方才于第六场中从桌下起身,也受到了妻子的抱怨和对他那固执的宗教迷信的反讽。
欧米尔:怎么?你这么早就出来了?你这不是拿人开心吗!赶快回到桌毯底下去,还没到时候呢;你应该等候到底,索性把事情看个水落石出,不要单单凭信那些揣测之词。
奥尔恭的举动叫人毛骨悚然。按常理来讲,自己的妻子当面被人侵犯、戏弄,稍有不对的苗头丈夫都会第一时间加以保护和制止。奥尔恭之所以在欧米尔连续的催促暗示下都蛰伏不出,不禁叫我们觉得此时的他在注视妻子被调戏的“窥淫”过程中获得了某种扭曲的、带有宣泄妒忌性的“快感”。如若回溯之前的劇情会发现,当这位既“愚”又“迂”的奥尔恭娶进了欧米尔这样年轻貌美的妻子,此番结合反倒给他带来了生命中的某种难言的苦涩:现在的奥尔恭,已逐渐踏进颓老的生命阶段,而在身旁洋溢着青春激情的娇妻与一群活力四射青年人的映衬下,他愈发陷入了一种生命能量疲弱无力的焦虑性困境中。在垂垂老矣的奥尔恭心目中,最重要的早已不再是如何继续追逐功名权利的累积,面对着精力的减损、雄风的散尽、快乐的远去及衰老死亡这一人生的不可逃脱之有限性的步步逼近,其内心所思更多指向的是彼岸世界的天国净土,这种特定生命阶段的内心情境让他急需像答尔丢夫这样的“良心导师”给自己带来清净的宗教抚慰。正如麻文琦教授所言:“奥尔恭这座古老的挂钟,其节奏早已对不上妻子那块只争朝夕的秒表,所以他会渴望深邃的宁静与和平降临他的家庭,于是答尔丢夫才得门而入,而之后的一连串的错误和荒唐,追根溯源,都起源于一个人一生中恐怕躲也躲不过的生命焦虑。”[8]P57
如果说这种带有痛感的生命焦虑让奥尔恭越发虔信宗教并把答尔丢夫奉为了座上宾,那么他对这帮年轻人的妒嫉亦是因此而被不断地强化。再加上他本身的财富雄厚,让如今的他变得越发蛮横专制、愚蠢可笑。正如伽森狄认为,人需遵循“自然”方可收获幸福。莫里哀深刻接受了伽森狄的世界观,在剧中通过年轻人的视角映衬、嘲弄了奥尔恭之专横、冥顽对“自然”的悖逆、毁坏并由此发展到“失常”化的痴愚。
至于奥尔恭的母亲柏奈尔夫人,她的愚蠢和冥顽不亚于儿子。全剧刚开场,因为大伙儿都对答尔丢夫心怀不满,这样的举动让柏奈尔很是不畅,满腹牢骚地开始逐个数落大家身上的臭毛病,唯独对那位“良心导师”抱以无上的崇敬。仅从整部戏的开端部分来看,柏奈尔愚蠢又顽固地对一个骗子加以盲崇便让观众禁不住发笑,这种对众人抱怨不休、对答尔丢夫却虔诚不二的“姿势化”行为也一直延续到了剧末。第五幕三场,柏奈尔再度登场,莫里哀也在此隐晦地将他对笛卡尔的唯心先验论的批判和嘲弄都倾注其间。从情节走势来看,随着前一幕欧米尔的计谋成功,答尔丢夫的虚伪本质已经彻底显露,他在奥尔恭心中的金身形象也陡然间崩塌,唯独家中年纪最长的柏奈尔还被蒙在鼓里,继续坚持着对答尔丢夫的固执辩护。当儿子满腔怒气地将欧米尔被答尔丢夫调戏的事实告诉母亲时,后者的态度意味深长。
奥尔恭:您就别让我着急啦,我的妈。我对您说,那样胆大包天的罪恶是我亲眼看见的。
柏奈尔夫人:人的舌头上有毒,老是要喷出来的,世间的人谁也没法儿躲过。
奥尔恭:您这种说法一点儿道理都没有。是我自己看见的,我说自己看见,就是说我自己的两只眼睛看见的,这叫作亲眼得见;难道必得扒着您的耳朵说上一百遍,像四个人合在一起那么大声嚷嚷才行吗?
柏奈尔夫人:天啊!外表常常是靠不住的,不能老就着我们看得见的来判断事情。
回想起方才答尔丢夫对自己妻子的龌龊之举,看清真相的奥尔恭凭借着自己的“眼见为实”急切地向母亲倾诉着这个骗子的流氓心性。可尽管事已至此,面对奥尔恭振振有力的言辞证据,柏奈尔却决绝地认为一切用眼睛看到的都是难以确信、根本无法判断出事物本质的“洞穴上的幻影”,答尔丢夫作为良心导师的虔诚与向善几乎是固化般不可动摇的存在。但奥尔恭这一次对答尔丢夫的揭发却是建立在肉眼注视到的放荡和邪恶基础上的。面对奥尔恭的心急如焚,柏奈尔在听到这些在她看来并不具有真实性的依据时无动于衷,二人的冷热对比,让我们陡然生疑:为何她会这般顽固不化地恪守己见呢?
其实,柏奈尔正是莫里哀按照笛卡尔唯心主义思想而精心设计的形象。笛卡尔认为理性是与生俱来且绝对权威的,作为一种凭借演绎而获取的真理性的知识,只有通过“天赋观念”的推演方能抵达,与感觉经验和现实实践并无太多关系,因此笛卡尔否认感性认知的可靠性,否认知识的来源是感性经验,唯独认可理性无与伦比的重要性。在奥尔恭给出的切实确证前,柏奈尔无可救药的执拗和我行我素正是笛卡尔这些思想的感性显现,而莫里哀则立足于伽森狄的哲学立场对其做出了嘲弄和批判。如前所述,就认识的源头问题来看,伽森狄认为认识源于感觉:“为了认识一个事物……必须是这个事物把它的形象送到认识的功能里边……官能本身既然不在它自己以外,就不能把它自己的形象送给或传给它自己。”[6]P38只有感官触及了客观事物,认识才能继而产生,也只有先建立起感性认识的基础,才能进一步上升到理性认识。在奥尔恭那里,答尔丢夫凭借高超的伪装技法一度攻克了他的心门,但是在欧米尔以身试险的计谋中,他终于亲眼目睹了这个骗子的下流,感官捕捉的事实让他不得再继续对其抱以任何的幻想。而柏奈尔太太着魔似的冥顽不化,显然是被伽森狄加以诘难的笛卡尔的唯心先验论的化身。从这一人物身上,可以直观地、感性地看出莫里哀受到了伽森狄思想的影响并如何巧妙地将其通过人物形象塑造渗透在自己的喜剧创作中。
2.仆人形象对伽森狄思想的体现
奥尔恭本可以自由地做一个自然人,但他对答尔丢夫机械般的痴迷和愚蠢让自己悖逆常情常态而显得可笑。柏奈尔太太面对儿子通过感性经验获得的实证却几乎无可救药般的冥顽偏执,更是形象地成为笛卡尔唯心主义及天赋观念的感性化身。除此之外,莫里哀还通过仆人形象的成功塑造再次让我们感受到伽森狄哲学对莫里哀的深刻影响。“仆人”是莫里哀喜剧中耀眼的形象群体,他们大多被莫里哀涂抹着源自伽森狄的感觉经验论色彩,并且具有敏锐聪颖的心智和清醒健全的思维,《伪君子》中的桃丽娜便是这样的仆人的典型代表。
桃丽娜是作家安置于作品中的“隐性艺术家”[9]P23,她虽然只是女仆,但浑身却闪耀着智慧的光芒。伽森狄曾对智慧不吝褒赞:“智慧是心灵的一种正确地思考事物和正确地立身处世的素质。”[10]P149这种卓越的素质连同前述伽森狄所提倡的唯物主义世界观都在桃丽娜的身上有着具象的展现。正因为桃丽娜凭借着她的聪慧、机智、冷静、沉着与能动性,尤其是她如“军师”一般对各色人等的心理特质的精准把握、对各种突发情势的判断和对答尔丢夫的坚决抗衡,才使得这个伪君子无法在一度压倒性的态势中让自己的“诡计”得逞。
首先,桃丽娜自始至终都展现出对答尔丢夫的绝对鄙夷并与之决然对立。相比于被答尔丢夫玩弄于股掌之间、直到最后才恍然大悟的奥尔恭与柏奈尔,桃丽娜从最开始便看穿了这个伪君子的虚假面具:“一个素昧生平的人竟忽然做起主人来,一个穷光蛋,来的时候连双鞋子都没有,全身的衣裳顶多值到六十个铜子,现在居然忘了本来面目,居然对什么都要阻挠一下,居然以主人自居起来!”这种对答尔丢夫虚伪本性的把握并非源自于某种理性教条的导引,而是凭借现实经验和直接的生活体验获得的。从对待答尔丢夫的态度来看,达米斯也和桃丽娜一样,同样从一开始都站在反对的立场上,虽然达米斯对他很气愤,但除却情绪上的发泄,实则毫无任何有效的计谋让答尔丢夫的本性在父亲面前尽显无遗。他过激的愤懑和蛮干也让自己在第三幕受到了奥尔恭的驱逐,并助长了父亲的执拗。面对此情此景,桃丽娜则清醒、理智许多,她深知目前的形势是横冲直撞的直接出击扭转不了的,于是一边极力劝阻达米斯收敛起自己“素常的暴躁脾气”来冷静相待、从长计议,同时又忖度着接下来的行事计划。显然相比于达米斯这样的公子哥,身为仆人的桃丽娜更具气定神闲的心态和高明的智慧。
其次,再看玛利亚娜与桃丽娜这组主仆关系。桃丽娜作为侍女,却与小姐玛利亚娜有着非比寻常的友情,玛利亚娜也多次向她提及过自己对瓦赖尔的浓情蜜意。也正是因为这份独特的情感关系,桃丽娜自始至终都在玛利亚娜和瓦赖尔受阻的爱情发展中通过自己的智慧不断地予以援助,为二者穿针引线。就性格层面来看,玛利亚娜作为养尊处优的千金小姐,虽然对自由结合的爱情心向往之,怎奈面对父亲的专横决断往往显得过于隐忍、软弱,除了怨叹之外毫无应对之计,甚至想过一死了之:“我就等着自杀了,倘若他们真要逼迫我。”这些行为典型地出自于玛利亚娜这一类不曾经历过风霜的豪门闺秀身上。这种沉默隐忍的性格,桃丽娜虽深深谙熟于心,但当前的形势已如黑云压城般迫在眉睫,女主人居然想着大不了就自杀而非冷静智取,如此反应也让桃丽娜心生不悦。
桃丽娜:不,不,我什么也不要。我看您是愿意嫁给答尔丢夫先生;我想着了,我实不应该劝您拒绝这门亲事。我何必要打消您这种心愿呢?这门亲事本是挺合适的。答尔丢夫先生吗!哦!哦!提出来这样一个人物還算小吗?当然咯,仔细想来,答尔丢夫先生原不是一个等闲人物,能做他的伴偶,幸福原不算小;大家都已经把光荣堆在他的头上;在他家乡他是个贵族,又长得一表人才;红红的耳朵,亮光堂堂的脸;和这样的一个丈夫过日子,您真是太满意了。
……
玛利亚娜:喂!请你快别说这种话了,你快帮我想个法子反对这门亲事吧!全不用提了,我认输啦,现在我什么都敢干了。
这段对话中,桃丽娜利用女主人最痛恨的答尔丢夫作为切入口而大做文章,通过对他加以接连赞赏的反话方式来“回击”她对大小姐的怒其不争。一方面,在对他人的心思把握上,玛利亚娜远远赶不上桃丽娜的灵敏,很快她便彻底被桃丽娜“拿捏”,但观众只会更加感受到后者的聪明可爱。因为我们知道这只是她撒的小脾气,心底实则一直保持着对女主人爱情走势的关心和支持。另一方面,桃丽娜的反话更起到了事半功倍的效果,她连珠炮弹般地描述玛利亚娜若是嫁给答尔丢夫后的种种画面,无形中对女主人心底的勇气起到了强力的激活作用。霎时间,玛利亚娜如脱胎换骨般质变,决定要坚强地面对这一切,不再退避。
在即将举行婚事之前,桃丽娜明白必须要想尽办法拖延时间,但此时的奥尔恭已经被答尔丢夫蒙骗得走火入魔,但他对宗教信仰的痴狂这一“弱点”却被桃丽娜精准地抓到。于是她再次设计,让玛利亚娜在父亲面前说自己梦到了泥浆、碎镜子、死人等带有凶兆的事物来让奥尔恭延缓时间。此外她还团结来自各方的力量,因为桃丽娜知道此时的奥尔恭几近偏执,需要更多人的合力方可与他的执念加以对垒,所以她及时劝解方才还在吵嘴的玛利亚娜和瓦赖尔,又发动玛利亚娜联络自己的兄长,还指使瓦赖尔寻求更多朋友的帮助……面对答尔丢夫这一最大的阻力,当达米斯被赶走、克雷央特踌躇不前、众人的力量和反击一度陷入瓶颈时,又是桃丽娜现身鼓舞、激活大家,恳请大伙儿:“把咱们的力量联合起来……想法子推翻这个可恶的计划。”往后,当欧米尔太太决定以自己的美色来引诱答尔丢夫步入自己的圈套时,桃丽娜审慎地提醒:“他的头脑是狡猾的,也许不容易叫他上当吧。”此处又彰显了桃丽娜对欧米尔的关心及对极度狡诈的伪君子的警惕之深刻。
总之,作为剧中的“隐形艺术家”,桃丽娜既沉着冷静,又善于审时度势;既睿智聪慧,又对玛利亚娜怀有温热的友谊和爱;既认知清醒,又对每个人的心理有着精细的把握;既不被各种经院教条捆绑,又保持着自然率真的姿态。伽森狄在对笛卡尔关于真理和谬误的看法加以辩驳时说道:“问题并不怎么在于我们是否有能力阻止我们自己犯错误,而是更在于我们是否有能力阻止我们自己坚持错误。”[6]P61如果说奥尔恭本可以选择自由地做人,却最终在追求信仰的歧路上渐行渐远而陷入痴愚,成了此话的反面写照,那么桃丽娜则时刻保持着对可见事物的本质认知的深刻性,依靠清醒的判断和能动性而合理地行事。故正是因为有桃丽娜的存在,才让狡猾的答尔丢夫没能形成压倒性优势,也在双方的斗争中为最终揭穿这个骗子的“假面”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因此,桃丽娜相比于同时代的诸多妇女形象要更加光鲜动人,莫里哀也在她身上注入了丰富的哲思和深邃的情感。
以上通过对《伪君子》中相关人物与场面的分析,能够看出莫里哀对伽森狄唯物主义思想和世界观的接受并将其融化在作品中的各个角落。与这位带有叛逆精神的哲学家的接触,让莫里哀的信念里染上了唯物主义的色彩,也使他的精神国度有了伊壁鸠鲁主义这样的底衬。他在批判答尔丢夫这样伪善的宗教骗子及宗教神学之余,还嘲弄了奥尔恭身上失常的愚蠢,借柏奈尔的形象塑造隐晦批判了笛卡尔式的唯心认识论和经院哲学教条,又将“自然”“智慧”“理智”的虹光赋予了桃丽娜这样的仆人。在莫里哀丰富的喜剧创作阵列中,体现此类思想的佳妙笔触与形象不胜枚举。譬如就仆人形象来看,《冒失鬼》中的马斯加里尔、《丈夫学堂》中的丽赛德、《无病呻吟》中的唐乃特、《司卡班的诡计》中的司卡班等,他们的行为道德准则都建立在伽森狄的哲思上,对否定物质光彩的宗教禁欲主义、悖反“自然”的蛮横贵族与专制家长、枯燥烦闷的经院教条都予以讽刺和戏弄。更何况莫里哀还曾在《唐璜》这样带有悲喜剧意味的作品中塑造出一个玩世不恭、放荡不羁甚至带有些许英雄气概的恶棍,巧舌如簧的唐璜对传统宗教观念的嘲弄和对道德准则的颠覆,一度被当时的保守势力视作具有误导性的激进力量。
那么,这些自由思想的闪光及对唯心主义的嘲弄批判,是否代表莫里哀由此便成为古典主义时期的反主流的“异类”呢?在文章的第一部分,我们曾指出笛卡尔唯心化的唯理主义对法国古典主义文艺美学原则的重要影响。而就理性主义本身来说又有唯心与唯物之别。笛卡尔的唯理主义属于前者,理论上的布瓦洛、沙坡兰,创作上的高乃依、拉辛皆受其熏陶,体现在古典主义悲剧作品中就是:作家往往“把人物投放到一个尴尬的处境中,他的选择成全道义、牺牲自我,故而造就了崇高,引发了感动”[11]P143。这种两难化的极端情境正是出现在当时悲剧中的惯常模式,人物在情理冲突的抉择撕扯中,最终让理性压倒情欲,舞台上由此矗立起一个个诸如熙德、贺拉斯这般忠君爱国的英雄。尽管法国古典主义戏剧对逼真性有着明晰的追求,但这种逼真背后始终离不开对理性的信奉与宣传,可理性在此又并非真正意义上钻研自然现实规律的科学理性,真实自然也要时刻不能背离对君权伦理道德的遵循。因而此时的理性与真正的自然逼真之间产生着矛盾和抵触。由此在沙坡兰看来,倘若一件历史事实不可信,那么它就必须要被按照合乎王权制下伦理要求的标准来进行一次改写,这样的主张显然浸染着浓重的唯心主义色彩。
以此为参照,可以说古典主义的诸多“立法”在莫里哀作品中的存在感实则非常微小。他并未严苛地赋予笔下的人物对君权伦理要求的忠君爱国品质的执着恪守,而更多追求的是某种快活、自然的人生“常态”。但这并不代表莫里哀在当时的主流社会价值观航道上发生了造反性的“越轨”,譬如《伪君子》《唐璜》等作品的结局处理,都表明它们是在“确保政治正确的前提下的讽刺艺术”[3]P39。故莫里哀同样受到了当时“理性”的浸染,但就唯理主义本身来讲,其本身有着唯心与唯物之分。唯心主义的唯理论让布瓦洛、高乃依、拉辛等人醉心于研究宫廷审美趣味并让人物在情理两难的情境中自由选择,最终体现出忠君爱国的崇高英雄气,而唯物主义的唯理论则让拉封丹、莫里哀等人保持着对现实自然的贴近及快乐自由的底色。
立足于此两点,可以认为莫里哀不仅与古典主义的唯心倾向保持着距离,也应注意到他诸多作品中“漂移不定”的讽刺立场和滑稽标准背后实则也有着不变的贯穿线,即“人物的言行是否违反常情、常态、常规。在莫里哀的眼中,只有一种滑稽值得讽刺,即一个个或失常或失位的人”[3]P39。《伪君子》中的奥尔恭、柏奈尔皆是如此。莫里哀从他们身上提炼出的愚昧也构成令人发笑的癖性。至于对答尔丢夫的讽刺,尽管作品曾经一度陷入政治斗争的旋涡,并被认为是对教会的侵犯,但莫里哀并非铁了心要对整个宗教势力宣战,充其量是把批判的棍棒敲打在了一个极其虚伪并不择手段满足个人私欲的骗子身上。
总之,莫里哀在精神信念、世界观上都深受伽森狄的影响,并立足于此,通过诸多失常失位的人物塑造来对经院哲学、唯心主义思想加以无情嘲弄。同时也将伽森狄的诸多哲思和生命态度都赋予了笔下一众类似于桃丽娜这般的“肯定性人物”形象,为人类喜剧艺术增添了耀眼的光辉。除却《伪君子》,在莫里哀其他喜剧著作中,类似的思维体现和匠心设计还有太多,关于莫里哀和伽森狄之间深层关联的议题也值得更加全面深入地研究。
參考文献:
[1]陈惇:《新中国莫里哀戏剧研究60年》,《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3期
[2]吴达元:《莫里哀喜剧选(上册)》,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
[3]麻文琦:《莫里哀式喜剧辨析》,《戏剧文学》,2007年第7期
[4]布瓦洛著,范希衡译:《诗的艺术》,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0年
[5]北京大学哲学系外国哲学史教研室:《十六—十八世纪西欧各国哲学》,北京:商务印书馆,1975年
[6]伽森狄著,庞景仁译:《对笛卡尔〈沉思〉的诘难》,北京:商务印书馆,1983年
[7]伯格森著,徐继增译:《笑》,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4年
[8]麻文琦:《〈伪君子〉的政治性及其“当下化”策略——从立陶宛国家话剧院〈伪君子〉的演出中说开去》,《戏剧与影视评论》,2019年第5期
[9]汪余礼:《双重自审与复象诗学》,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年
[10]侯赛军:《浅谈莫里哀喜剧中的乔装现象》,《时代文学》,2008年第8期
[11]卢暖:《穿越历史的圣女》,北京:人民出版社,2019年
(作者单位:安徽大学艺术学院)
责任编辑 岳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