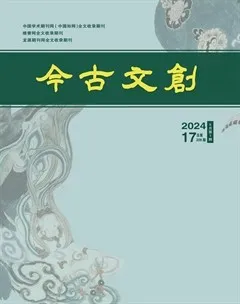聂元松散文中湘西民俗书写的审美特征
2024-06-05姜文臣
【摘要】湘西作家聂元松的散文创作立足于湘西这一片奇崛而神秘的土地,以湘西民俗为主要创作内容,用诗性的笔调对湘西古老民俗进行生动的还原,饱含深情对湘西民俗进行现代性的反思。聂元松散文的民俗书写不仅仅停留于湘西民俗的简单罗列,而是真正实现了民俗与文学的融合,使得散文具有了文化和审美的双重价值。
【关键词】湘西文学;聂元松;《湘西叙事》;《湘西记忆》;民俗书写
【中图分类号】I2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8264(2024)17-0050-03
【DOI】10.20024/j.cnki.CN42-1911/I.2024.17.015
湘西文学自发展伊始,经历了三次浪潮,第一次发生在新中国成立以前,沈从文第一次向世界展示了一个神奇的湘西世界,描摹出一个自然而准乎人性的生命群体,构筑了一个诗性的精神家园;第二次浪潮发生在新中国成立以后至90年代,孙建忠、蔡测海等人紧贴时代脉搏、反映社会变革,开创了湘西现实主义的文学传统;第三次浪潮划分在新世纪,田耳、于怀岸等湘西第三代作家在接续发展中为湘西文学的发展添砖加瓦。第三次浪潮中虽然缺乏传世力作,但是一些富有特色的文学作品仍然根植于湘西大地,与湘西大地血脉相连,续写着沈从文等湘西文学开创者的湘西风格,执着于复活古老的湘西记忆和书写着新时代的湘西叙事,难掩其文学价值和文化意义的光辉。
钟敬文在《民俗学概论》中说:“民俗,即民间风俗,指一个国家或民族中广大民众所创作、享用和传承的生活文化。” ①湘西地区深受巫楚文化的影响,又是土家族、苗族等少数民族的聚居地。巫楚文化和少数民族文化的碰撞、交流中滋养的这片土地,生长着歌谣、传说、舞蹈等异彩纷呈又玄奇鬼魅的民俗资源。从湘西文学第一代作家沈从文开始,就在文学作品中自然本能地融入了湘西民俗。当代湘西作家在湘西自然、文化环境的滋养和前辈作家的影响下,接续对地域文化的书写。
湘西作家聂元松即是不遗余力书写“湘西之书”的代表性作家,她的散文集《湘西叙事》和《湘西记忆》两部作品立足于湘西这一片奇崛的沃土,以湘西民俗为主要展现内容,以散文的文体、行走的方式、诗性的笔调详尽地书写湘西。她选取凤凰、茶峒、王村、酉水等湘西富有代表性的地方作为背景,描写民众生产生活中所产生的民俗事象,并对其形成进行历史性的追溯和深层内蕴的挖掘。从其内容来看,其笔下民俗可分为以下几类:
一是丰富绚烂、渗透着湘西人民智慧和心血的物质生活民俗。如华美精致的苗族银饰,湘西特有的甑子饭、腊肉、菜豆腐、酸萝卜等,鳞次栉比的吊脚楼、古老的石板街、古朴明快的马头墙、精雕细刻的窗根、曲折幽深的宅院等。二是在历史的悠悠岁月中生长出的一些与外界特异的岁时节日民俗。如每年农历的正月初三的为春天祈福的“春会”,土家族“过赶年”等习俗。三是穿越了时间的长河至今仍然在湘西文化的图谱里鲜活生动的湘西民间口头文学。如透露出远古人类文明信息的盘瓠辛女的传说,一唱三叹、详细记述苗族先民迁徙悲壮图景的史诗《鸺巴鸺玛》,与土家织锦结合在一起的“织女歌”等。四是异彩纷呈的民间艺术,如讲述人类起源、民族迁徙、英雄传奇的摆手舞,将音乐与舞蹈完美结合的湘西苗鼓舞,还有璀璨的湘西戏曲和绚丽的湘西织锦艺术等。
聂元松散文中包含了湘西民俗的方方面面,她用自己的脚力、笔力保存古老民俗的来龙去脉,再现了湘西民俗的耀眼神光,追问着湘西民俗的命运走向。本文立足文本细读,结合民俗学的相关方法研究文本,来探寻聂元松散文中民俗与文学文本之间的关系,进而总结其民俗书写的审美特征、发掘其民俗书写的审美价值。
一、第一人称旅人视角的审美蕴含
视角在叙述中的重要地位是不言而喻的,不同的叙述视角会产生不同的效果。聂元松运用第一人称的旅人视角,在散文中,这样的视角“既可捕捉片段的镜头,又能也可以连缀许多镜头把画面串联起来。” ②聂元松带着相机跑遍湘西的山山水水,集中书写仍然存活于湘西民间的物质、精神生活民俗等。十分巧妙地将作者探寻的足迹、文字的记录、和照片的捕捉交织在一起的,在行走的动态中展示着自己所见所闻所认识的湘西世界,产生了独特的审美蕴含。
一方面,旅人眼中所见,民俗著作者之眼光。聂元松返回故乡,以一个寻访者的姿态行走在湘西的山山水水之间,以一支绚烂之笔和一个多彩的镜头为人们展现了湘西世界丰富的民俗画卷。大家在聂元松的文字中很少看到五四时期乡土作家笔下所钟情选取的落后、野蛮的民俗,相反,随处可见的是美好、诗意的民俗事象。作为湘西之子,她对故土有深厚真挚的情感,她眼中所见、笔下所写的民俗,实际上渗透了作者真挚强烈的情感。写到某种民俗的时候,作者总是情不自禁地抒发自己的感慨,或者思接千载、视通万里,将古老民俗的渊源拉到读者面前。大家从聂元松散文中看到的是经过作家主观心灵美化的民俗,其间包含着对湘西民俗深刻的认同和热爱、真诚的保存和守护,以及对民俗不可避免逝去的忧虑和怅然。
另一方面,旅人耳中所闻,民俗更全面而立体。作者在湘西州、吉首市相关领导的支持下,拥有得天独厚的采访便利,她寻访了许多具有代表性的民俗传承人和坚守者,手艺精湛、重义轻利的银匠麻茂庭,在锦中织入了自己的生命的土家织锦传承人刘代娥,痴心不改、老骥伏枥志在千里辰河高腔传承人向荣等等。作者亲闻这些传承人讲述民俗文化及他们与民俗文化的故事。因此,除了第一人称的陈述视角,随着作者的寻访足迹的展开,散文中的人物视角也非常丰富。“所谓人物视角就是散文中出现的人物,可以透过他自己的视角来观物描摹、发言,等等。” ③文章中除了极具作者主观意识的民俗书写以外,在作者与传承人的一问一答之间,第一人称陈述视角和第三人称人物视角相遇合,民俗的古往今来和民俗传承者过去现在的故事交织在一起,使得湘西民俗更加详尽、清晰、立体地呈现在读者的面前,补充了作者第一人称视角对湘西民俗所见、所感的局限性。
二、民俗空间的美学色彩
民俗与文学不能够仅仅停留于被承载与承载的关系之上,民俗不只是被罗列的事象,它在文学文本中还能承担推动情节发展,塑造人物形象,背景的营造、氛围的渲染等等功能性作用。比如“五四”时期一些乡土文学作品中写到水葬、械斗等封建野蛮的陋俗,通过在这些民俗中人们的态度和表现,呈现出愚昧、麻木国民形象;还有沈从文的《边城》中三次写到端午节,不仅将湘西地区端午节的具体场景和民俗风貌浓墨重彩地描写出来了,而且三次端午节也发挥了重要的叙事功能,仿佛串联起翠翠的整個爱情故事。因为是散文作品,所以许多功能性的作用在聂元松的作品中体现得并不鲜明。但本文把聂元松笔下的湘西世界看作一个民俗文化交汇的空间,这一民俗空间无形中发挥着作用,赋予了聂元松散文无可替代的美学色彩。
一是原始朴野、朦胧神秘的地域色彩。巫楚文化和湘西本土原有的土蛮文化的汇合,使得崇神信巫是湘西各少数民族根深蒂固的文化传统,在湘西的许多民俗都是从巫鬼文化中来的。毛古斯的粗犷豪放,梯玛闪现的神光,鼓舞撼天动地的节奏,辰河高腔所包罗的乡土狂欢……许多仍然鲜活存在于湘西人民生活中的民俗背后都隐现着人类童年时期的生产生活的投影,涌动着湘西神秘文化的底蕴,作者的呈现将读者一下拉回原始蒙昧时代中的狂欢氛围中,给作者的文字蒙上了一层神秘、诡异的面纱。
二是自由浪漫、和谐宁静的地域色彩。湘西山环水绕、复杂封闭的自然环境孕育着独特的湘西民俗文化,也成就着特异的文本基调和底色。跟随者聂元松的足迹,一幅风光旖旎、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水墨丹青徐徐展开:九百里酉水滋润着两岸湘西人民的自在生活,也涂抹着丰富的民族画卷,依山而建的村寨、依山傍水的吊脚楼、悠悠的石板街,河谷里回荡着或雄奇粗犷、或舒缓多情的酉水号子,山间荡漾着携带着泥土芬芳的苗家山歌……这些文学景观出现在散文的字里行间,也连同湘西的山山水水、亭台楼阁,一同浸润着聂元松的文字,呈现着自由浪漫、和谐宁静的地域色彩。
民俗渗透在人们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作为地域文化中重要的有机组成部分,反映着特定地域、特定时代的人文风尚和社会面貌。聂元松散文不遗余力地书写湘西民俗,一方面起到了保存和延续湘西民俗的作用,另一方面这一民俗空间也在一定程度上成就了聂元松散文特异的地域色彩。
三、民俗风情与自然人性的审美呈现
湘西文学发展的三次浪潮层次分明、特点各异,但是也具有一定内在的连续性和核心特质的恒常性。湘西文学中,自以启山林的沈从文开始,他“继承和代表的是古代湘楚尊重自然人性、歌颂原始的旺盛生命力、崇尚传统道德境界的浪漫主义文学传统。”潜心构筑了人性的“希腊小庙”,塑造了一大批至真、至善,自然而不悖乎人性的生命形态。《边城》中天真淳朴的翠翠,重利轻义、乐于助人的老船工,乐善好施、通情达理的船总顺顺,《柏子》《龙朱》《虎雏》中一个个充满原始野性、生机勃勃的生命等等。到了湘西文学第三次浪潮的聂元松这里,她的创作深受沈从文所开创的浪漫主义文学传统的化育,将湘西民俗风情的书写与自然人性的描摹紧密结合在一起,也呈现出一些宁静淳朴生活中跃动的美好人性。
一方面,作者书写的湘西传统民俗映射着湘西人的本色与品格。聂元松在展示民俗的同时,试图通过民俗的表象去追寻其背后涌动的深层民族精神、心理特征。费孝通在《乡土中国》写道:“文化是依赖象征体系和个人记忆而维持着的社会共同体验,这样说来,每个人的‘当前,不单包括他个人‘过去的投影,而且是整个民族的‘过去的投影,历史对于个人不是点缀的饰物,而是实用的、不能或缺的生活基础。” ④聂元松从湘西人在艰险的山水环境中创造出来的干栏式建筑“吊脚楼”这一民俗中,发掘到了湘西人民的智慧和勤劳;从摆手舞、毛古斯、梯玛等早期的民俗文化遗存中看到了土家人民高扬的生命意识,自由、雄健的性格和执着的生命追求;从震天的“八合鼓”鼓声中听到了“湘西苗家人灵魂深处自然而质朴的生命本性” ⑤;从历史遗留的点将台、射击场等地名中找寻到了湘西人民勃勃的生命强力和一往无前的进取精神……
“作为人类迈向文明的伴生物和人类生活的永恒伴侣,民俗从人类童年时代即开始构建,历经漫长岁月,在那些大量的具象背后,早已层层叠叠累加着人类心理、情感的积淀,从而成为‘民族精神的标记。” ⑥在聂元松看来,湘西民俗不仅仅是民俗,更是千百年来湘西人民坎坷历史的隐喻,是湘西人民一脉相承的精神、性格的承载,民俗连同民俗背后的隐喻和承载穿越了时间与空间而经年不息、世代相袭。
另一方面,与民俗息息相关的传承人身上看到了自然人性的光辉。聂元松写到的传承人大都经历过动乱岁月的磨洗与历练,都面临着发展艰难的困境,以及传统技艺后继无人的现状。但他们仍然执着追求手艺的精湛,孜孜以求探寻古老民俗和融入当代精神的最好衔接。蓝印花布手艺人刘大炮为人爽朗、刚直,拥有天才的印染绝技和绝佳的创意。碰到真心喜欢自己作品但不宽裕的大学生,刘大炮连卖带送将作品给了远方的顾客。对于想学手艺的外人,他从来都是免费。在唱苗歌的人越来越少,价值越来越高的市场上,丹青苗歌传人陈千钧仍然坚持一天只收100元,平时比赛拿了奖金也是多半请同去的人吃饭了。因为歌艺好,人随和,被大家尊称为“歌王”。梯玛的传承人彭继龙说梯玛不仅要给四里八乡的人治病,还要解决邻里纠纷,他认为“做一个梯玛,首先要做一个好人,只要有人来请,不管有钱没钱,不论地位高低,都要去。”我们从这些执着坚守、讲情谊、重利轻义的传承人身上似乎嗅到一丝熟悉的气息,他们仿佛是《边城》的里老船工、船总顺顺,也是《长河》里的果园主,然而最主要的,他们身上都是隐现着健康、淳朴、自然的湘西文化血脉和人性基因。
四、结语
湘西相对封闭的环境,被时代遗忘的落寞,使得民俗文化的硕果在湘西这片土地上得到良好的呵护并仍然蓬勃鲜活。然而随着时代的变迁,湘西一些古老的民俗在人们生活中退居其后,其重要的文化意义也逐渐消减,聂元松的足迹和笔力却能够返回家乡奇崛的土地,耕耘在湘西民俗的田野,她用丰厚的人文情怀,丰富、详尽的民俗文化知识,打开了一个向世界展示湘西的窗口,对世界认识真正的湘西起到积极作用。并向时代发问:当在物质文明强势入侵的时代,民俗应该走向何处?这是难能可贵的。因此,不仅仅是文章中提到的一个又一个用生命坚守的传承人,实际上,聂元松也用自己的方式守护着湘西的民俗文化。她用散文的方式,保存着湘西民俗的古往今来、制作过程,连同民俗背后的可贵精神一同凝结成文字的琥珀,她的书写必将超越民俗和文学本身而具有经久流传的价值。同时,作者将湘西的民俗画卷和自我的审美情感融为了一体,为我们留下一个历史悠久、风情独特,又注入了时代内涵的新湘西形象,为“文学湘西”“文化湘西”的构筑贡献出散文力量。
总之,聂元松散文中既全面丰富、颇具针对性地描写了湘西民俗,又巧妙地将民俗与文学相融合,用诗意的笔调展现民俗,多彩的民俗又成就着聂元松散文特异的艺术风格,使得聂元松散文的民俗书写兼具了审美和文化的雙重价值和意义而独树一帜。
注释:
①钟敬文:《民俗学概论》,高等教育出版社2010年版,第3页。
②郑明娳:《现代散文理论垫脚石》,广东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75页。
③郑明娳:《现代散文理论垫脚石》,广东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79页。
④费孝通:《乡土中国》,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17页。
⑤聂元松:《湘西记忆》,湖南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189页。
⑥聂元松:《湘西叙事》,湖南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101页。
参考文献:
[1]钟敬文.民俗学概论[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0.
[2]费孝通.乡土中国[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
[3]张永.民俗学与中国现代乡土小说[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10.
[4]聂元松.湘西叙事[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10.
[5]聂元松.湘西记忆[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15.
[6]郑明娳.现代散文理论垫脚石[M].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16.
[7]段建军,李伟.新散文思维[M].北京:商务印书馆, 2006.
[8]乌兰其木格.喧哗中的谛听[M].北京:作家出版社, 2019.
[9]吴正锋,申艳琴.湘西文学的“第三次文学浪潮”[N].湖南日报,2012-12-04(02).
[10]张创弘粹.新世纪以来湘西作家小说创作研究[D].广西大学,2022.
[11]杨倩雯.湘西青年作家群创作特征研究[D].长沙理工大学,2016.
[12]彭文海.继承与探索:湘西青年作家群创作考察[D].吉首大学,2014.
[13]吴正锋.民族民间艺术的坚守与传承——读聂元松《湘西记忆》[J].创作与评论,2015,(16):53-56.
[14]梁瑞郴.用真情诠释山水人文经典——聂元松《湘西叙事》观后[J].民族论坛,2011,(23):62-63.
作者简介:
姜文臣,土家族,湖南湘西人,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现当代多民族作家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