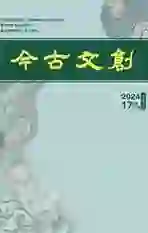莫言小说《红高粱家族》中的生命力之歌
2024-06-05苏悦
苏悦
【摘要】莫言小说《红高粱家族》突破了多年文学为政治服务的模式,以崭新的视角开始对人的本身进行探讨。他的小说充满了对生命力的探索与歌颂,在探索中更接近人的本身。本文将从“性”意识、主要人物性格、无差别叙述这三个维度对小说中生命力的表现进行探究。
【关键词】《红高粱家族》;性;人物性格;无差别叙述;生命力
【中图分类号】I2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8264(2024)17-0027-03
【DOI】10.20024/j.cnki.CN42-1911/I.2024.17.008
随着第一次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的召开,中国文学的发展由现代文学迈向了当代文学的新的历史进程。这里要点明的是,在1976年10月之前,中国文坛的作品无论是小说、诗歌、戏剧还是散文,都不可避免地受到政治环境的影响,都以歌颂光明美好,塑造英雄形象作为当时的文学主流,文学创作呈现一元化态势。但在1976年10月以后,中国文学迎来了新的春天。随着20世纪80年代中国改革的多层次和全方位化,文学发展出现了新态势。此时期的文学摒弃了以前的一元化模式,逐渐向多元化发展。与此同时,文坛兴起了以先锋文学、寻根文学和新写实文学为主的创作潮流。此时期作家的创作不再拘泥于政治环境,在他们创作的过程中,文学的本体性受到了关注,文学观念发生了整体位移,性意识和生命意识开始觉醒。作家莫言创作的《红高粱家族》作为“寻根文学”的代表,深深扎根于乡土,从生活中汲取灵感,生动地为读者谱写了一支生命赞歌。
一、生命力在性狂欢中释放
(一)对传统文学“性”的突破
《红高粱家族》作为莫言早期的代表作,他用极富创新性的魔幻现实主义手法和无差别的超时空叙事手法构建了一个充满野性和原始生命力的“高密东北乡”世界。在这样一片粗犷的、僭越于现代文明之上的红高粱地上,生活着一群似匪非匪的“民族英雄”,小说以“我”的视角描述了“我”爷爷余占鳌率领武装压击日军的同时,与奶奶戴凤莲的爱情故事,他们聚侠气正气匪气与一身,他们烧杀抢掠也报效国家,他们缱绻相爱,奋勇杀敌,离经叛道但充满野性和生命力。生命意识的觉醒和生命的极度张扬是这部小说的突出特征,主要以“性”的形式表现出来。
弗洛伊德认为:性是推动人类进步的一个重要动力。从中国历代的文学作品来看,中国文化中对性的描写十分节制,这种节制性表现为中国文化传统认为裸体如尸体,裸体失去了身体原本的层次感、丰富性和变化性。中国文化通过衣服褶皱和波动来展现身体的奥妙与美丽,而西方文化则以对裸体的描写展示人的美。就算是很长时间被认为是淫书的小说《金瓶梅》,对性的描写十分露骨,但它对性部位并不进行细写。在《红高粱家族》中,莫言对性部位的细节描写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传统认知,呈现出性暴露下鲜活的生命意识。乳房作为哺育的器官,它是否健康蓬勃决定着生命力的能否得以延续。在莫言的文字里,女性的乳房总是那么的健康美丽,丰满挺拔。就是在这样的乳房下才孕育出高密东北乡一个个野性的鲜活的生命。
(二)三场“性”描写
“种种情欲中间,最强有力,直接摇动我们的内部生命的,是爱欲之情。”[3]莫言在小说中着重刻画了三场“性”:余占鳌和戴凤莲在高粱地里野合;余占鳌和恋儿三天三夜的偷情;恋儿被鬼子轮奸。
1.高粱地里的野合
“野合”作为莫言小说中常见的性欲表达,具体表现在奶奶骑着毛驴在高粱地里被余占鳌劫走,发生了性关系。“是他!一阵类似幸福的强烈震颤冲击得奶奶热泪盈眶。”[2]奶奶在得知劫走自己的人竟然是自己颇有好感的轿夫余占鳌之后,喜悦,激动,潜藏了16年情欲猛然炸裂。在此刻得到了真正的释放。“余占鳌粗鲁地撕开我奶奶的胸衣,在他的刚劲动作下,尖刻锐利的痛楚和幸福磨砺着奶奶的神经。”[2]奶奶逐渐在爷爷余占鳌的伟岸雄壮的身躯下沉沦,他们在这种性狂欢中短暂地脱离现实的围困,他们蔑视一切法规,伦理道德。在性欲的放纵中两颗不羁的心灵贴合,爱欲得到满足的同时生命力得以释放。以至于在这种释放中产生了突破封建礼教束缚的真正的爱情。他们之间的爱情如同一团熊熊燃烧的火焰,他们不但在高粱地里共享了激情,更是冲破了社会道德的束缚。
在他们的世界里,爱情无需任何的矫饰,只是纯粹的生命力的宣泄与释放。他们爱情,就如同那高粱酒一般,醇厚而浓烈。他们的每一次接触,无论是九儿在酒坊里酿酒,还是余占鳌在高粱地里劳作,都像是在为这份爱情添加燃料,让爱情的火焰越烧越旺。然而,这份爱情并非只有甜蜜与幸福。当战争的阴影笼罩了他们的家园,他们的爱情也受到了极大的考验。然而,他们并没有向战争屈服,反而更加坚定了对爱情的信仰。他们的爱情如同高粱一般,无论经历多少的风雨与磨难,依然坚韧生长,繁花似锦。在这个残酷的世界中,他们的爱情不仅展示了原始的生命力,更显示出了人性的坚韧与不屈。他们的爱情,就如同那烈日中的红高粱,虽然受尽风雨的摧残,却依旧火热,依旧坚韧。
2.偷情
第二场性描写是余占鳌与二奶奶三天三夜的偷情,在这场性描写中,作者通过恋儿的“四笑”和主动引诱刻画出了一个不羁的、率性的与中国传统女性形象背道而驰的极富生命力的少女形象。“恋儿转回身,用洁白的牙齿咬了一下肥厚的嘴唇,嫣然一笑……”[2]“一笑”[1],此时余占鳌的意思已被恋儿意会,恋儿所做的动作使余占鳌在视觉上受到一定的刺激。“恋儿把嘴角动一下,唇邊上显出两条狡猾的皱纹。”[2]“二笑”[1],在暧昧气氛的来回拉扯中,恋儿的猜测得到了确定,她露出了狡猾的笑容。“恋儿又咬住嘴唇一笑,扭一个屁股,走了。”[2]“三笑”[2]恋儿在余占鳌的语言和犹豫不决的神态中了解了他的顾虑,决定继续引诱,以退为进,扭着屁股走了。余占鳌在视觉上再次受到性刺激。恋儿再次回来,倚靠着门看着爷爷,“恋儿咬着嘴唇,莞尔一笑。”[2]“四笑”[1]最后一次笑,余占鳌经过前面三次性暗示后,他的性欲达到了高潮。恋儿也在最后一次笑的过程中下定了决心。接下来,他们便进行了历时三天三夜的性爱。这场性爱无论是对于余占鳌还是对于恋儿来说都是不忠不义有违伦理的。恋儿背叛了她的主人,余占鳌背叛了他的妻子。但是同时又是合乎人性的,二者的性欲在灵魂与肉体的结合中得以释放,这是一种生命力的绽放。
3.刺刀下崇高的性悲剧
如果说前两场“性”的基础是爱,是灵魂的碰撞,那么第三场“性”则是暴力,悲剧和崇高。恋儿为了救自己的女儿,在哀求反抗无果后主动脱光自己的衣服,冷漠地、蔑视地等待着鬼子的侵犯。莫言用极富张力和感染力的语言描写了一场手无寸铁的中国女性经极力反抗最后仍然在鬼子的刺刀下走向灭亡的悲剧。正如鲁迅先生认为的悲剧就是把生命中有价值的东西撕毁。[4]“二奶奶搂抱着小姑姑……她又有了三个月的身孕……”[2]对于恋儿来说,虽然被戴凤莲赶了出来,但是面对即将到来的新生命,此时的她是甜蜜的。“老太婆不放过,大肚子女人总该放过吧?”[2]恋儿在危机到来之际仍然天真地寄希望于残暴的鬼子身上。殊不知,她的悲剧即将到来。
恋儿在日本鬼子极其残暴的行径中彻底看清了他们就是混蛋,卑劣的畜生。她在绝望中放弃抵抗,之前种种幸福瞬间被撕毁,她唯一渴求的就是日本鬼子能够放过自己的孩子。当然,这种希望在日本鬼子面前无非是痴心妄想,这一刻,母性的光芒在裸体与血水中熠熠生辉,人性中善与恶的对立也尤为凸显。
二、生命力在人物形象中得以具化
山东高密东北乡是莫言笔下的故事世界,这个地方足够奇特:它最美丽也最丑陋;最超脱也最世俗;最能喝也最能爱[2]。莫言用近乎对立的,天马行空的语言搭建着这样一个神奇的世界。在这片土地上,有着大片的红高粱地,在高粱地血色的土壤里埋葬着爷爷,奶奶,刘罗汉大爷的尸骨。在高粱地的上空,飘荡着他们的灵魂。他们有着共同的特征——红高粱般鲜明的性格。
(一)余占鳌形象分析
莫言笔下的英雄人物是丰富的,饱满的,圆润的。他所刻画的英雄区别于传统的英雄形象,爷爷并非名门世家之子,也不是庙堂文治之才。他是一个流亡者,杀人越货者,他是流氓,土匪,无赖……他有种种身份,独独缺了英雄这一种。可在抗日之后,他的身份发生了变化。从一个流氓土匪转为了地方抗日的领导者。即使这样,作者也并未对其进行大肆宣扬夸赞。在作者笔下他依旧粗鲁,自私纵欲:与恋儿偷情,为了给奶奶置办丧礼,他杀人越货,强人棺材,发行纸币剥削百姓……他也同样令人敬畏,余占鳌本性中有正义,有豪爽与侠气。对于强奸了曹玲子的亲叔叔余大牙,他大义灭亲枪毙了余大牙。在战争的硝烟中,余占鳌带领着他的弟兄们,奋勇抗击敌人。在墨水河之战中,传统的主要抗日势力在这场战争中失去了光泽。直到惨烈的战斗结束,国民党军队的冷支队长才现身,还掠走了属于他们的战利品[6]。在战场上,他并不是一个只知道拼杀的武夫,而是一个有着深刻思考和坚定信念的领导者。他知道,他们是在为他们的家园而战,为他们的尊严而战。在目睹奶奶的殒命,兄弟们的惨死和鬼子血洗村子的过程中,余占鳌对生存的迫切渴望,他不甘被人欺凌,受人侮辱和压制。内在的生命力在蓬勃涌动,于是他反抗,更加凶猛。在仇恨和极度的爱国激情的推动下将自己全身心投入到抗战斗争中。
余占鳌的故事,是一个充满激情和生命力的故事。他让我们看到了,生命的力量是无穷的,只要我们勇敢地去追求,去坚守,就一定能够战胜一切困难。他的故事,也让我们看到了,爱情的力量是伟大的,只要我们勇敢地去爱,去付出,就一定能够得到真正的幸福。他的故事,是充满激情和感动的。他用他的经历,告诉了人们生命的意义,告诉了人们爱情的伟大。他让我们看到了一个真正的英雄,一个真正的男子汉。
(二)戴凤莲形象分析
奶奶戴凤莲和中国传统故事中的农村女性一样,命运多舛,受尽苦难。在裹小脚陋习仍存的时空里她有着一双令无数壮汉心潮澎湃的三寸金莲;在父权压迫和封建礼教残害下她无法选择自己的婚姻。但在被极度压抑的十六年里她依旧充满生机,向往自由。她刚烈也敢爱敢恨,她蔑视传统伦理道德。对待爱情和幸福,她大胆追逐,她是个性解放的先驱,妇女独立的典范[2]。当余占鳌把她从驴背上劫下来时,她未曾反抗,甚至为了让他抱得更轻松,她欣然配合。在村民的议论声中,她依然和余占鳌姘居生子,她比同时代女性有更高的追求和更先进的自我意识——坚持做真正的自己,勇敢追求幸福。她与余占鳌一样,也是一位民族英雄。她牺牲在为余占鳌的抗战队伍送拤饼的路上,死在鬼子的机枪下,长眠在那片鲜红明艳的高粱地里。临死前,她发出了一段屈原天问式的对话独白。
“天,你认为我有罪吗?……什么叫贞节?什么叫正道?什么是善良?什么是邪恶?……我爱幸福,我爱力量,我爱美,我的身体是我的,我为自己做主,我不怕罪,不怕罚……”[2]她以竭身之力直问传统伦理道德,在不断追问中发出“我的身体是我的,我为自己做主”[2]的终极呐喊,极大地张扬了一个女性的生命主体意识。
九儿的故事,不仅仅是一个女性的成长故事,更是一个展现人类原始生命力的故事。她的坚韧和勇气,让人们看到了一个不屈不挠的生命,如何在困难和挫折面前,坚定地走下去。她的故事告诉大家,即使面临再大的困难和挑战,只要我们有坚定的信念和对生命的热爱,就一定能够冲破一切束缚,找到真正的自己。九儿的故事中,也蕴含着对封建社会的一种批判。在这个社会中,女性被视为男性的附庸和生育工具,没有任何地位和自由。但是,九儿并没有接受这种命运的安排,而是勇敢地反抗这种不公的命运。她的行动和反抗,为我们揭示了封建社会对女性的束缚和压抑。
(三)刘罗汉形象分析
除了余占鳌和戴凤莲这两位主要人物历来备受学者关注之外,这片土地上还有一个人,刘罗汉,他是劳苦大众的代表,同样也是农民悲剧的典型。刘罗汉原是单家父子酒坊的大伙计,在单家父子死后跟随了爷爷奶奶。抗日战争爆发后,刘罗汉为了保护奶奶,被日本鬼子连同奶奶家的骡子一起抓去修公路。在劳工的过程中,他受到监工多次无故抽打。刘罗汉的心理也从逆来顺受转为反抗逃跑。复仇的紫色火焰的点燃意味着罗汉反抗意识的觉醒。为了救奶奶最喜欢的两头骡子,成功逃脱的罗汉大爷冒险折返,此时的他已经被日本鬼子折磨得不成人样,以至于骡子未能辨别出他来。这在无形之中点燃了罗汉大爷压抑已久的怒火,他认为骡子此时变成了鬼子的走狗。在暴怒下用铲子铲死了两只骡子。忠厚老实了一辈子的罗汉大爷在生命的最后一程中,爆发出了前所未有的生命力。他被身份地位压抑过,在漫长岁月中沉寂过[5]。但在这片高粱地的滋养中孕育形成的豪情侠义之风,在被侵略者侵害之际,在民族存亡之时迸发而出,从而卷起了巨大的生命波涛。
三、无差别叙事下红高粱对生命力的象征
无差别叙事是莫言《红高粱家族》在叙事方式上的一大特色。所谓的无差别即作者在创作时将人,神,动物的世界打通,三者之间相互渗透相互沟通。这种叙事方式在小说中的凸显具体表现为“红高粱”对生命力的象征性。莫言认为动植物都是有生命有灵性的东西,故而“红高粱”这一意象贯穿于整部小说的同时在小说重要的节点上给读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高粱梢头,薄气袅袅,四面八方响着高粱生长的声音。炽目的潮湿阳光在高粱缝隙里交叉扫射。”[2]这是作者对爷爷奶奶在高粱地里野合的描写,此时的红高粱是激情的生命的象征,它随着爷爷奶奶的野合肆意生长,炽目的阳光象征着生命的希望,这是一缕缕圣洁的阳光,照射在爷爷奶奶身上。霎时间,性爱的交融显露出的生机与自然间的生命相遇,显现出生命的光辉。
“在她蒙眬的眼睛里,高粱们奇谲瑰丽,奇形怪状。它们呻吟着,扭曲着,呼号着,缠绕着,时而像魔鬼,时而像亲人。”[2]奶奶临死时,红高粱不复往日的生机活力,变得奇谲诡丽,形状畸形,痛苦呻吟,仿佛在为奶奶即将死亡而悲伤疯狂。高粱的哭泣扭曲象征著生命将亡,而缠绕交织是永恒的象征。在同一片土地上,曾经改变过她的命运,最终她也在此永恒。最终,奶奶的血肉之躯融入了这片土地,美的人、美的事物、美的灵魂在土地中得以永恒。肉体虽死,但她这种为自我而活,为生命而活的精神将永远留存在被高粱滋养的后代子孙的心中。
参考文献:
[1]温瑜.莫言小说《红高粱家族》中性描写的价值[J].长春教育学院学报,2014,30(08):1-2+4.
[2]莫言.红高粱家族[M].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2017.
[3]郁达夫.艺术私见[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
[4]乔淑丽,罗小平,陶敏编.鲁迅箴言全编[M].长春:时代文艺出版社,1993.
[5]师婧昭.从人物生命力角度赏析《红高粱家族》[J]. 语文建设,2017,(26):57-58.
[6]李宝华.生命力的律动与张扬——评长篇小说《红高粱家族》的主题内涵[J].佳木斯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4, (01):57-5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