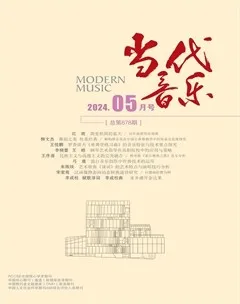“以字行腔”声乐艺术理论在声乐演唱中的运用
2024-06-03王紫云



[摘 要] 讲好中国字是唱好中国歌的关键。著名的声乐教育先驱应尚能先生的声乐艺术理论专著《以字行腔》从其创作伊始至今,对我国声乐艺术发展的指导价值具有深远意义。笔者领会并沿用了应先生著作的核心观点,以中国古诗词现代艺术歌曲《山之高》为例,从歌唱前的准备、说话正音、歌唱行腔、情绪处理多个维度解构了《以字行腔》声乐艺术理论在声乐演唱及教学中的运用,并引申探讨了中国作品演唱中“歌词”第一性的主张。笔者以为:“说话咬字,正音是关键;以字行腔;字正是前提;腔词合一,传情达意是目的”。
[关键词] 应尚能;以字行腔;古诗词艺术歌曲;正音
[中图分类号] J61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7-2233(2024)05-0119-04
一、背景介绍
我国著名的声乐教育家、作曲家应尚能(1902—1973)先生,在其毕生众多的艺术成就中,着力于钻研欧洲传统声乐唱腔如何与我国汉语言结合的问题,简言之“如何用西洋唱法唱好中国歌”。应先生总结了40年的演唱、教学和研究经验,呕心沥血,最终撰写出了对我国声乐艺术发展具有开拓性价值和跨时代意义的宝贵专著《以字行腔》[1]。从该教材的诞生时至今日,其中关于我国汉语拼音的特点、汉字的组成结构以及汉语歌唱咬字发声规律的著述对于我国目前声乐从业者而言,依然具有重要的指导性价值。
(一)《以字行腔》声乐艺术理论内容
应先生《以字行腔》的声乐理论主要从“讲”与“唱”的关系进行论述,包括其一,讲好字是唱好字的前提;其二,在字腹做延长是唱好字的关键内容。具体到该方法论在声乐教学中的运用,主要包括歌唱前的准备、咬字吐字、歌唱发声等内容。正如“以字行腔”方法论传承人冯宝宏(非职业男高音歌唱家)先生于2016年3月在扬州大学音乐学院的声乐专题讲座“推广以字行腔,唱好中国歌曲”中所提到的,《以字行腔》解决的是“美声”唱中国歌曲的咬字问题,“字”是汉字,“腔”是歌声。以中国汉字,行美声之腔。[2]以字行腔是手段,所有的规范最终都是为能够更加科学地演唱作品,传情达意服务的。
(二)中国古诗词现代艺术歌曲《山之高》
《山之高》是由我国著名罗西尼男高音歌唱家石倚洁首唱,青年作曲家王龙根据宋代词人宋玉孃的词《山之高》,古词新编的一首现代艺术歌曲。根据笔者的教学实践和演唱经验,笔者认为遵循并运用“以字行腔”这一艺术发声规律,从心态体态调整、字词正音、诗词诵读到歌唱的咬字吐字(以字行腔、腔从于词)再到词曲的情绪走向把握的演唱处理方法,能够帮助学生更科学、更深刻地演唱这首作品,演唱效果也更加贴合现代中国声乐学习者的艺术审美。
二、歌唱前的准备
(一)心态和体态调整
应先生在其理论中非常强调“身体协调性(心态和体态)”,要求演唱时身体要张弛有度。他说:“咬字对唱是一个关键性的工作,而咬字条件的出现,是从调整全身上下的关系而取得的……唱不仅要用脚,而且还得会用头,连整个身体都要会用。”[3]因此,演唱前,首先要求学生调整心理和身体状态是关键,一般来讲,心理的适度紧张和身体相对放松是演唱时比较理想的状态。心理过于紧张会引起身体的僵硬和不协调,比如:嗓子紧,浑身发抖,无法用气等。而心理过于放松,则演唱者可能会因缺乏演唱激情而导致表演黯然失色,唱者无情,则听者无兴。
保持科学的歌唱体态是确保正确呼吸,从而建立科学发声方法的前提。应尚能先生关于歌唱体态提出了三组关键词“挺胸、收腹、提臀”。在歌唱时,应要求学生厘清这三组动作是建立在各部分协调基础之上的相对概念。挺胸吸气并不是扩胸憋气,歌唱用气时小腹是被动收缩。另外,帕瓦罗蒂也曾言,在演唱高音时,他的臀部是缩紧状态。这一点笔者在教学和练习演唱中也得以反复实践并证实。
(二)咬字吐字正音
“说话的声音是歌唱声音的重要因素,并构成后者的真正支柱。没有正确的说话发声,就没有正确的歌唱”[4]。应先生的理论中,强调了说好字是唱好字的基础和前提这一观点。鉴于此,我国很多音乐类高校专门为声乐学生开设了“正音学”或“歌唱正音”等专业课程。
从近古时期声乐技术偏好正音技术的发展倾向来看,声乐艺术中歌词是具有第一性的,中国声乐作品的歌词正音以普通话为标准。因此,唱歌之前,声乐教师要求学生熟练掌握普通话的发音标准,克服“非普通话”的母语发音习惯尤其重要。以笔者工作地山西为例,山西境域内有中区、西区、北区、南区、东南区、东北区六种不同口音方言。晋南地区的学生时常前后鼻音不分,比如,“粉红(fěn hóng)”时常被误读成“fěi hóng”;晋北学生说话没有“翘舌音”等。由此可见,当我们在进行声乐教学时,尤其在面对声乐初学者时,咬字正音是必不可少的环节。帮助学生正确地发出某些元音,达到字正腔圆的技术后再循序渐进进入“歌唱”,更符合声乐学习规律。正音类课程的目标之一就是要求学生能够标准化地朗诵歌词,并帮助学生建立新的标准化的普通话发声习惯。
那么,具体应该如何说话咬字呢?应先生在其声乐专著《以字行腔》“字的组合”部分重点强调了咬字准确的重要性,包括是否清楚和完整两方面。“所谓清楚是指字音着力点的准确性和母音的腔正;所谓完整是指一个字有几个部分就要交代几个部分”[5]。帮助学生正音,首先可以要求其进行汉语拼音的练习。汉语是单音节语言,一字一音节。每个字音通常包含“声母、韵母、声调”三部分,通常由母音(元音),或者子音(辅音)加母音(元音)进行搭配(如表1),再通过咬字头(辅音声母)、吐字腹(元音韵母)和收字尾(最后一个韵尾因素)一气呵成,形成一个完整的发音闭环,以此实现字音的完整。字音的着力点主要体现在字头(声母:b、p、m、f...z、c、s)的发音上,需要唇、齿、舌、牙、喉等不同发声器官的协调参与。而腔正则要求学生训练元音韵母的发音,按照不同的口形予以引长吐准。
然而,需要明确的是,说话咬字并不完全等同于歌唱中的咬字,说话正音技术也不等同于歌唱正音技术。语言的语音和歌唱的语音在音高、音量、节奏、时值等方面都有显著区别。“歌唱正音是语言的语音在音乐的旋律和节奏规定下使语音形态和语音表意得到有效保持的技术,所以说歌唱正音技术的归属是声乐技术”。[6]笔者认为歌唱语音形态的保持技术是语音表意的先决条件,唱清楚才能达到声乐演唱“传情达意”的最终艺术目的。关于语音形态的保持,应尚能先生在《以字行腔》一书中论述了在讲的基础上延长字(字腹),是把讲转变为唱的关键。歌唱中的字音分字头、介母、字腹和字尾四部分,对应汉语中声母、韵头、韵腹和韵尾四部分(如表1)。近年来,《以字行腔》传承人冯宝宏先生将歌唱当中的咬字归纳为“字头轻巧着力、字腹延长饱满、介母不到半拍、字尾归韵迟短”四项基本原则。
三、声乐作品《山之高》的演唱处理
具体到声乐作品的演唱行腔规范,不同风格的作品有着显著区别和具体要求。民歌演唱咬字更贴近于说话的状态,因此它的字音与我们日常的普通话发音具有较高的一致性,听起来也相对清晰。而欧洲舶来的美声唱法,更适用于演唱外文(比如:意大利语、法语、德语等)作品。如果直接将这一“西洋唱法”原封不动地移植到我国本土声乐作品的演唱中,可能并不恰如其分。笔者以应先生《以字行腔》为理论指导并结合声乐作品《山之高》,从三方面具体分析。
(一)歌唱中的“以字行腔”
演唱声乐作品时,主要以元音(母音)的保持和延长为主,辅音则需要快速过渡。正如我国著名男中音歌唱家廖昌永先生在其声乐讲座中强调的:“歌唱时,字头(辅音/子音)一定要很快的到元音上去……”。以中国古诗词现代艺术歌曲《山之高》为例,歌曲首句“山之高,月出小,月之小,何皎皎”,以“山(shān)”字开头,演唱时字头咬在辅音“sh”上,随着喉位下放迅速过渡到字腹“a”母音进行咬字并延长,最后归韵在字尾“n”,则完成了“山”的发音全过程。“之”(zhī)字整体认读。“高”(gāo)字,辅音字头“g”需要调动舌根参与完成,之后舌肌归位迅速过渡到元音韵腹“a”作较长延留,并在起辅音作用的元音“o”上进行归韵。“月”(yuè)字整体认读,但要注意元音e在韵母ue中要发音变形为英文[e]的发音。“初”(chū),字头咬在辅音“ch”上,并快速过渡到字腹“u”元音进行咬字并延长归韵。“小”(xiǎo),是由字头、介母、字腹、字尾构成的四因素汉字,在元音“a”上做保持延留,其他因素的字头、过渡和收束归韵速度要快。“何”(hé),字头辅音“h”要求舌根参与完成,在元音“e”上延长以保证字音清晰。“皎”(jiǎo)字,字头咬在辅音“j”上,发音规律同“小”。
副歌部分,“我有所思在远道,一日不见兮,我心悄悄”。“我”(wǒ)字是零声母音节,“w”发“u”音,通过介母“u”快速过渡到“o”延时保持。“有”(yǒu)字同样是零声母音节,“y”发“i”音,通过介母“i”快速过渡到“o”延长,并在“u”上归韵。“所”(suǒ)字,字头擦音“s”突破气流阻力快速通过介母“u”,在元音“o”延留归韵。“思”(sī)字整体认读。“在”(zài),字头咬在辅音“z”上,快速过渡到字腹“a”母音保持延时后在“i”归韵。“远”(yuǎn)字整体认读。“道”(dào),字头咬在辅音“d”上,尽快过渡到元音“a”上做保持延留,并在“o”快速归韵。“一”(yī)字是零声母单元音音节,演唱时直接在“i”元音做保留。“日”(rì)字整体认读。“不”(bù)字,字头咬在辅音“b”上,快速过渡到字腹“u”延留归韵。另外,按照我国汉语拼音的使用习惯,有些字在发音时往往会省略字腹或者将字腹变形。比如“见”(jiàn)字的发音。如果按照传统汉字分析方法,其字腹为“a”,实际在发音咬字中需要将其变形为“e”,这一特点是需要歌者格外注意的。“兮”(xī)字,字头咬在辅音“x”上,快速过渡到字腹“i”延留归韵。“心”(xīn)字,前半部分同“xī”的处理,最后要在“n”收字尾。“悄”(qiāo),字头咬在辅音“q”上,其他发音规律同“小”。
另外,在演唱处理《山之高》的咬字行腔时,需要格外注意以下几点:
1.尽管“y”“w”具有拼合音节的功能,却不能担任字头声母。演唱中咬字归韵时,当“y”“w”在字腹前一般被看做介母,并在后方元音字腹做咬字延长,例如:“我”(wǒ)、“有”(yǒu)。
2.当单韵母“i”或“u”独立成音节时,必须在它们的前面分别加上“y”或“w”。此时,“y”或“w”只是拼写规则需要的一种形式,如:“一”(yī)。
3.关于整体认读音节演唱时的咬字吐字规范,应先生的专著里面并未深入涉及。笔者特意请教了《以字行腔》唯一传承人冯宝宏先生。根据冯老师多年来的实践研究经验总结,“y”读音同“i”,当其后出现“ü”时,“y”只是形式装饰。且“ü”见“j/q/x/y”时变“u”,例如:“月”(yuè)、“远”(yuǎn)中“ü”元音的两点省略。因此在咬字归韵时,可将“ü”元音看作介母,重点在其后的uè/uǎn(下划线)字腹咬字。
4.冯先生通过实践经验提议歌唱咬“zi/ci/si/”时,首先通过舌尖前音“z/c/s”(口型韭菜叶的宽度)产生气流之后,咽腔打开迅速发“[?藜]”音。演唱“ri/zhi/chi/shi”舌尖后音时,应该舌尖微翘,产生气流之后,咽腔打开迅速发“[?藜]”音来进行咬字归韵处理,《山之高》中体现在“之、思、日”的咬字处理。
(二)歌唱中的“腔从于词”
汉语区别于其他语言最大的特点是具有“声调”特征,包括阴平(一声)、阳平(二声)、上声(三声)和去声(四声)四种。现代汉语中一声、二声称平声,三声、四声称仄声。在歌曲旋律创作方面,我国民族声乐传统理论保留了“腔从于词”的说法。一般来讲,旋律的曲调声势应尽可能与语音四声字调保持一致,以避免歌者在演唱中出现“倒字”的现象,让听众产生歧义。比如,耳熟能详的《两地曲》中,歌词“你在北国,我在南疆”,字声走向为“低高低高,低高高高”,然而实际演唱旋律却是“低高高高,低高高低”。因此,很容易演唱成“你在背锅,我在南桨”,像这样曲作者更多关注曲调走向而忽略字音声调的例子在中国声乐作品中确有存在。
歌曲写作中,从单个的字来看,阴平(调值为55)的汉字采用的音调比较平直,阳平(调值为35)的汉字音调基本呈上行,上声(调值214)上行(或拐弯儿),而去声(调值51)汉字则多用于下行,而每个字的结合也会产生高低起伏的语气重音。在歌曲《山之高》中,歌词“山之高,月出小”平仄声为“平平平,仄平仄”,其旋律基本符合歌词字声走向(如谱例1)。
“月之小,何皎皎”平仄声为“仄平仄,平仄仄”(高低低,高低低),其中“月之小”旋律走向“2/4 2 3 3(低高高,见谱例2)”似乎并不完全符合单字的应用走势,演唱时的听觉效果更像“约致笑”,容易“倒字”。但这两句中“小”“皎”的音调非常符合其“三声”(拐弯儿)字调特点。接下来“山之高,月出小,月之小,何皎皎”其旋律基本符合单字走向(见谱例3)。需要注意的是“皎皎”二字的连用似乎违背了明代王骥德在《曲律·论曲禁》中关于“禁两上声连用”的词曲写作规范[7]。另外,考虑到“何”是阳平音且常用于上行的特点,许多歌者在实际演唱中在“何”前加入上滑音唱作 。笔者以为这是避免将“何”唱成“hē”的有效的处理方法。类似这样通过加入“滑音”以避免人为“倒字”的方法在前人学者研究中也有迹可循[8]。
“我有所思,在远道,一日不见兮,我心悄悄”平仄声为“仄仄仄平,仄仄仄,平仄平仄平,仄平平平”(见谱例4),字调和旋律音调基本一致,但仍有容易倒字的地方。比如“我有(高低)”其旋律却是上行设计,演唱效果听起来像“我yōu”。上述提到的在“有”前加入上滑音的方法依然可行。另外,歌曲第一遍“在远道”中“远”是上声,一般用在上行(或拐弯儿),此时是逆向的。而第二遍出现时,“远”的旋律“2/4 6 - | 5 6 | 2-”(见谱例5),则更加符合创作规范。“不见”字音走向为“低高”,其旋律为“高低”,亦容易倒字。“我心悄悄”旋律基本符合单字走向。
总体而言,《山之高》全曲字音字调、语势扬抑、旋律曲调大体符合创作规范。尽管存在部分倒字现象,但并不影响全曲的格调和歌曲的内容表达。字声相谐是我国北宋科学家沈括晚年著作《梦溪笔谈》中提到的美学原则,优秀的作品要求字音准确和曲调优美的辩证统一。通过声乐演唱者的演唱,表达歌曲内容内涵是终极目的。
(三)歌唱的情绪倾向
声乐作品中,歌词是音乐的载体,赋予了乐曲具体可感的内容。通过旋律曲调传情,目的是传达歌词内容,是声乐作品的终极目标。歌词的情绪倾向性为歌曲旋律的情绪走向奠定了基调。《山之高》是一首描写玉孃和沈佺的凄美爱情悲歌,凄婉的词义曲调道尽了玉孃的思念。歌词表述含蓄隽永,娓娓道来。词义的情绪性表现由轻声诉说转为感叹、坚定,最后思绪在如梦如幻的落寞中逐渐飘远。因此,此曲调大致走向由水平进行发展为上升式的旋律,最后回落为下降式进行。亦如石倚洁老师感叹说:“第一次听到《山之高》这首作品的小样时……与歌词的匹配度非常高”,喜欢这首作品的朋友们,在演唱这首作品或是类似的古诗词歌曲时,一定要吃透歌词中所表达的意境,文学上的理解是演绎歌曲的前提,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做到歌曲演唱的传情达意,这里恰恰表达的是音乐情绪与词义的匹配问题。
结 语
说话咬字,正音是关键;以字行腔;字正是前提;腔词合一,传情达意是目的。随着美声、民族等唱法的日益交融,声乐教育家、歌唱者也逐渐打破了认知壁垒。不同的唱法植根于不同的语言文化环境,都遵循“以字行腔”的特点是研究共识。传统意大利美声唱法主要是通过a/e/i/o/u五个元音来进行发声训练,这五个因素在我国传统汉语拼音也能找到相应的位置。因此,用美声唱法演唱中国作品亦不冲突。无论使用何种唱法演唱中国作品,技术理应为艺术服务,两者结合表达情感。用正确的技术和贴切的情感表达作品内容是关键,而内容则需要回归到歌词内容“第一性”上来。
参考文献:
[1] 应尚能.以字行腔[M].北京:人民音乐出版社,1981.
[2] 杨殿解.推广《以字行腔》唱好中国歌曲——记“冯宝宏《以字行腔》声乐专题讲座”[J].歌唱艺术,2016(05):57-61.
[3] 应尚能.以字行腔[M].北京:人民音乐出版社,1981:34.
[4] 马腊费奥迪.卡鲁索的发声方法[M].朗毓秀译,北京:人民音乐出版社,2000:79.
[5] 应尚能.以字行腔[M].北京:人民音乐出版社,1981:9.
[6] 张羡声,张蓉,马亚囡.论声乐的正音技术与正音训练[J].当代音乐,2021(09):9-13.
[7][8] 陈树林.歌曲演唱中的倒字与音乐教育[J].中国音乐教育,2010(05):9-11.
(责任编辑:韩莹莹)
[收稿日期] 2023-12-28
[作者简介] 王紫云(1991— ),女,博士,山西传媒学院讲师。(晋中 0306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