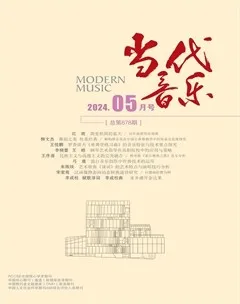我国地方志中音乐史料的价值与开发
2024-06-03张沐
张沐
[摘 要] 地方志又称为地志、地记等,主要记录了我国各个地区的文化习俗、自然风貌以及社会发展现状。地方志为历史学者研究音乐史料创造了便捷条件。鉴于此,本文以我国少数民族地方音乐、清朝时期广西地区地方音乐以及汉唐时期的潇湘音乐作为研究对象,对其中记载的音乐史料展开分析和研究,并对史料中蕴藏的价值进行深入挖掘,以供参考和借鉴。
[关键词] 中国地方志;少数民族;音乐史料
[中图分类号] J60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7-2233(2024)05-0192-03
我国地方志记载经元、明、清三代,发展较为稳定。地方志中的内容繁多,为后世研究我国不同区域的风俗民情提供了史料依据,同时地方志中记载的社会风俗和文化风俗也对现有的文化价值开发提供了参考和借鉴。
一、地方志中音乐史料的区域性溯源
地方志是我国古籍著述中较为重要的一个分支,在我国历朝历代的文化古籍中占有较高比重。作为能够管窥各地文化、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的区域性古籍类别,据不完全统计,目前保存下载的地方志大约有8000多种,共计10000多卷,时间跨度自宋元至今均有著述。如此大体量的著述,在我国历史上除正史著述外,成为具有系统性、功能性、区域性的代表性古籍之一。其中丰富的史料内容,为研究各时期区域文化发展提供了大量史料。史料是研究历史的基础,以音乐史研究为例,针对音乐史料进行研究的过程中,需要参考各类历史资料。我国发展历程较长,拥有的史料典籍众多,正所谓史料均收,记载完全。然而从历史层面分析,一些史书在记载历史的过程中,往往会出现记载断层的现象,部分史料内容还会出现缺失和记载不完全等现象。
我国大多数史料以正史为主,其记载的内容主要集中在经济发达地区,而偏远地区往往被忽略,同时音乐类史料也以宫廷雅乐为主,未能全方位展现我国古代区域音乐文化。地方志以记载地方历史为核心,具有较强的综合性,又被称为“博物之书”,其地域性非常显著。主要记录了特定时期、特定年份以及特定地区的社会、文化、经济等各方面内容。地方志只记载本地区的事情,由于各地的自然环境、人文政治、地区风俗等方面均存在较大差异,且编纂人员对于区域性特征的重点论述,使得地方志记述时主观性较强。也就是说,从正史能够了解史料的详细面貌,而从地方志则能感受到强烈的区域风格。对于那些涉及全国的事件,地方志只详记和本地区有关的部分,其地区性特点,成为研究区域音乐史料的重要组成部分。
地方志以外的地方文献,大多各自有一个侧重面:有的记历史,有的记现状,有的记地理,有的记人物,有的记政治经济,有的记文化艺术,有的只记一时一事。只有地方志,它的记述以最近一段时期(一般是几十年)的现实状况为主,同时要兼叙历史沿革,无论天文地理、名胜古迹、资源物产、民族、宗教、风俗以及政治措施、军政机构、典章制度、经济状况、文化科学、著名人物、重大事件以至方言俗语、金石碑刻、天灾人祸、故事传说等,只要和这个地区有关,统统属于它的记述范围。也就是说,任何地区自古以来均有音乐形式和内容的存在情况,而针对地方志中音乐史料的研究,则会对特定历史时期和特定区域的音乐记述情况有详尽且真实的纪录,如《(光绪)山东通志》卷一一○至一一三为“典礼志”,其中详细记录历次典礼的经过和仪式,包括举行仪式用什么器具,用什么乐器等等,同时也记载其他各种官方的和民间的礼仪。这些记载不仅能够窥探地区音乐文化发展历程,还能从其他方面思考音乐文化流变的缘由。
其中地方志音乐史料中又包含了当地的礼俗祭祀、婚丧嫁娶、乐器乐谱等内容。自从地方志有所记载以来,对地方志进行撰修编撰,成了相关史料记载人员的重要工作内容之一。民族音乐集成具有的“音乐的地方志”性质,其所包含和表现的内容题材方面是十分丰富的。[1]因此通过对地方志史料的有效研究和深入调研分析,不仅可以挖掘其中蕴藏的优秀文化,同时还可以更好地研究地方发展历史。
地方志史料的资料搜集、编撰以及推广应用多由官方完成,因此很多地方志又被称为官书,这也从侧面体现了地方志的重要性。记载地方志的过程中,必须真实地反映当时的史实,还原事物的原貌。[2]在本文中,笔者以区域地方志中音乐史为核心,对其中蕴藏的各类乐器、乐谱、音乐现象展开深入研究,同时也对完善我国地方志音乐史料记载提供对应的借鉴依据。
二、地方志中有关少数民族
音乐史料的分布情况
在我国传统地方志中,主要针对一些较为官方的音乐进行记载,而针对少数民族音乐史的记载内容较少,导致该现象出现的核心原因有二:一是我国古代深受儒家思想文化影响,二是传统汉族文化中心论因素影响。同时由于我国幅员辽阔,在地方志记载的过程中,可能会对部分地区的史料进行零星记载,而这些记载内容也主要以祭祀风俗和艺文志有关。
综合来看,在我国地方志中比较典型的少数民族音乐史料包含以下几类。
(一)清朝《西域图志》中的音乐志
《西域图志》中所载的音乐志,记录了我国边疆地区——新疆的主要日常活动。著述过程中,对于古时西域地区的风貌和知识,除记录清朝时期特征外,还将官方正史与考证材料融入其中,可以更好地帮助大众了解古时西域的相关知识,同时也对一些讹传和野史进行了更正,有极高的学术研究价值。在《西域图志》中曾记载:“回部”和“准噶尔部”专设音乐子目,又将音乐子目分设为乐器、乐谱等各个分项条目。其中的“准格尔部”中,对乐谱和乐器进行细分,还记述了圆布什尔、伊奇尔呼尔、雅托噶、特木尔呼尔等传统乐器的演奏方法;“回部”则记录了哈尔扎克、喇巴卜、巴拉曼等少数民族运用传统乐器演奏的方法与行为,同时还兼述乐舞表演形式。这些对于边疆地区少数民族乐器、乐舞、乐歌的记载,可以更好地帮助现代人了解到我国古代少数民族地区民族音乐的整体发展历程,将其完整、真实、形象地呈现在大众眼前。为音乐史研究学者研究我国少数民族地区传统音乐提供了重要的历史资料。
(二)《云南志蛮夷风俗》中的音乐记述
我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少数民族众多,尤其是在我国的西南地区,少数民族数量人口众多,通过对我国边疆地区地方志的深入研究,可知古代不少学者对我国西南边陲地区的蛮夷风俗进行了分析。以《云南志蛮夷风俗》为例,该地方志中就记载了我国西南边陲地区的民族风貌,充分展示了古代中国文化的包容性和有机性。《云南志蛮夷风俗》共计10卷,涉及的内容主要介绍了云南地区的风俗地貌、婚丧嫁娶、音乐、舞蹈等。通过深入研究《云南志蛮夷风俗》中的相关内容可知,虽然其介绍的篇幅集中在蛮夷风俗这一方面,针对音乐内容记载较少,但是仍能直观地了解到我国古代少数民族地区的音乐活动。
(三)《广西通志》中的音乐记载
雍正时期的《广西通志》中共分为128卷,主要内容有政治、经济、历史、蛮夷文化、艺文、音乐等。蛮夷地区主要介绍安南以及诸蛮部落。在《广西通志》中主要的介绍区域集中在广西区域,同时还对广西周围的少数民族历史风俗进行了记录,对广西当地各个民族的分布情况进行了详细记载,具有极高的地方志研究价值。在《广西通志》的风俗篇中,和音乐相关的介绍内容共有6段,可以真实地向读者反映我国古代少数民族对音乐的喜爱程度。少数民族音乐类型多以婚丧嫁娶为主,不同少数民族地区受经济繁荣程度影响,其风俗和礼仪存在一定的差异。[3]在《广西通志》的诸蛮篇中,对我国广西地区少数民族的历史资料进行了着重阐述,其中有关音乐的研究内容共计有117段,该地方志中详细描述了瑶族男女对歌的场面。瑶族男女通过对歌来互相抒发爱慕之情,是一项非常热闹的民俗活动,该对歌风俗一直沿袭至今,被很好地传承下来,是广西当地非常具有代表性的民间音乐活动。同时《广西通志》中还对当地少数民族的日常生活内容进行了记载,而唱歌内容始终穿插于其中。纵观苗族、瑶族、侗族这类少数民族的发展历程,可知音乐文化史在其历史发展中占有较大比例。音乐多用于祭祀、生产等日常活动,不仅可以满足精神需求,同时还渗透于少数民族群众的日常生活领域。《广西通志》在雍正初年时期曾被删改,其中包含一些少数民族音乐相关内容,对研究我国古代少数民族音乐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男女对歌活动自古已有。少数民族的音乐往往和民俗活动相互融合,其中最为常见的是以唱歌的形式来表达和传递情感。在地方志中记载了大量苗族男女唱歌习惯的内容。通过研究地方志内容,可以深入了解广西少数民族地区群众当时的生活轨迹和风俗,男女通过这类民俗活动可以尽情放歌,享受唱歌的乐趣。
三、地方志中少数民族音乐史料
的研究价值分析
张舜徽先生曾这样说过:“宋代学者气象博大,学术途径至广,治学方法至密,举凡清代朴学家所矜为条理缜密、义据湛深的整理旧学的方式与方法,悉不能超越宋代学者治学的范围,并且每门学问的讲求,都已由宋代学者创辟了途径,准备了条件。宋代学者这种功绩,应该在中国学术史上大书特书,而不容忽视或湮没的。” 宋元祐年间的郑兴裔在《广陵志序》中就明确提出:“郡之有志,犹国之有史,所以察民风,验土俗,使前有所稽,后有所鉴,甚重典也。余奉简书,自庐移守兹土,表章先哲,利赖兆民,日求康治,而文献无征,心窍悼焉。”宋代方志的作者,开始注重方志对社会所起的作用,强调要有补于风教,有益于政事。也就是说,宋人对方志的新认识,并逐渐赋予它新的使命,提出新的要求。自此,地方志发展与正史著作发展并驾齐驱,且成为正史著作中部分内容地域特色的补充部分。
于音乐来说,地方志中所留存下的民歌民谣,岁时风俗,乃是广大人民在共同生活和与自然界做斗争的经验总结。如乾隆二十五年(1760)重修的《乌青镇志》中《风俗》篇有关岁时风俗的记载中,所载“签大桔于柏枝上,著之谓百事大吉。昆弟交戚过从饮椒酒,子弟鸣钲击鼓以相娱乐,三日为小年朝。”便是对于节日用乐的考证。又如《淳祐临安志》卷六《学校》篇所附郡守陈襄的《劝学文》载:“必将风之以德行道艺之术,使人陶成君子之器,而以兴治美俗也”。对当时文化艺术培训的理论体系建设具有时代性的价值。
近代著名学者俞樾(1821—1907)所修之《镇海县志》,《学校》一门所载不仅对于学宫历次兴废重建的过程都有详尽的记载,各个书院、社学、义学建立原委、规模都作记述外,对学宫的“祭器”“乐器”“舞器”“斋戒”“执事”等,以及祭仪、行礼、奏乐、唱舞的各个节奏动作都详细罗列。事实都说明,各种方志的学校门类,是研究我国教育史的很好的园地。还应当指出,方志记载学校,甚至还影响到史学的发展。众所周知,正史中从未立过学校志,唐代杜佑所作《通典》,虽然是专讲典章制度,但也仅在《选举典》中讲到学校。到了宋末元初,马端临作《文献通考》,在方志记载学校的启示下,搜集了大量资料,在《文献通考》中专立了《学校考》这个新的门类。这充分证明学科之间相互渗透,互相影响的作用,且能够通过对于学校门类的记述,了解学校对于音乐人才培养的政策和措施,此乃一举多得之功。
通过对中国地方志中有关音乐史料的研究,为我国音乐史发展提供了更加丰富的史实材料。史书以记载国家大事和重要人物为主,而地方志者则主要记载地方发展历程、地方民俗、音乐、文化等重点内容,对完善我国的音乐文献记录体系具有重要的意义。同时也为学者研究我国音乐史提供途径。“社会的形态所提供的社会环境对音乐的发生、发展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由于它的影响,一定社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规则都反映在不同形式和规模的音乐行为里”[4]。因此,深入研究地方志中的少数民族音乐文献,可发现很多文献中涉及的内容,以风俗节日、典礼、祭祀生产活动为主,包括人文、自然、地理等诸多内容。通过深入分析地方志编撰情况可知,其编纂工作具有详略得当的特点,主要由史学者进行记载,同时多数内容来自民间,是对当时地方风貌和生活的真实记录。不仅可以更好地帮助现代人了解古人生活,同时也具有较强的可信度和真实性。
结 语
综上所述,地方志是对我国古代地方历史风俗文化进行记载编撰的主要史实文献,也是我国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不仅涉及前朝后世的历史发展情况,同时也包含了各式各类的古人生活风貌,为后代学者研究提供了丰富的资料。史料的查找与发现十分不易,是一项十分重要而艰巨的工作。对大量的历史信息进行梳理、提炼也是耗费学者精力的繁重工作。[5]地方志具有内容翔实记载,名目繁多等优势,同时也可以为后人研究地方的发展提供一定的参考和借鉴。针对地方音乐进行研究,笔者上文中所写的内容仅仅是非常少的一部分,对史料的整理和研究并非一件简单的事情。在收集地方志史料的过程中,因地方志史料并非为专业史官所编撰,容易受客观因素的限制和影响。同时在研究方面,受笔者自身研究能力的限制,可能会对史料的整体应用性产生负面影响。如果仅仅是借助史料来研究历史,则难以从宏观层面对音乐文化进行统一系统性的呈现,但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只有不断地积累,才能更好地为研究中国音乐史添砖加瓦。
参考文献:
[1] 冯光钰,王民基.音乐的地方志地方的音乐志——试论编辑五种民族音乐集成的意义和方法[J].中国音乐,1985(03):5.
[2] 刘莎,颜家碧.地方志与区域音乐史研究——以清代广西地方志中的音乐史料研究为例[J].黄河之声,2022(12):62-64.
[3] 翟书艺.中国地方志中少数民族音乐史料的价值分析[J].当代音乐,2020(10):72-74.
[4] 洛秦.音乐的构成:音乐在科学、历史和文化中的解读[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224.
[5] 秦雪峰.中国近现代音乐史著述中的史料探究——评《曾泽霖志忞考》的史料学贡献[J].音乐生活, 2023(02):4.
(责任编辑:韩莹莹)
[收稿日期] 2024-01-05
[作者简介] 张 沐(1992— ),男,博士,江苏第二师范学院音乐学院讲师。(南京 2100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