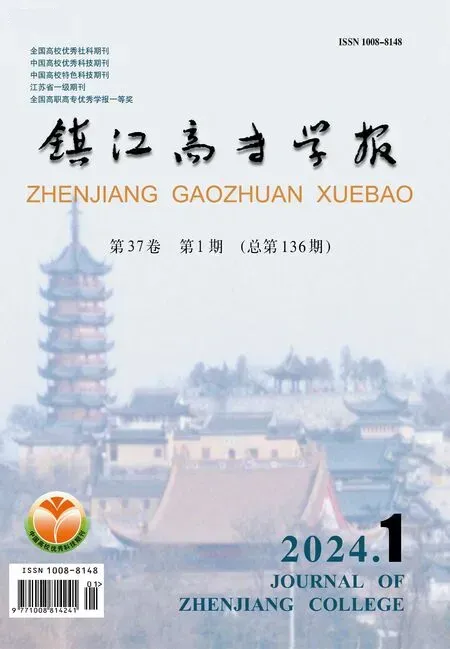论《同情者》中的双向模拟与身份认同困境
2024-06-01王佳希
王佳希
(浙江大学 外国语学院,浙江 杭州 310058)
《同情者》是美籍越南裔作家阮清越于2015年发表的处女作,2016年获得普利策小说奖。小说讲述了双面间谍“我”在越战期间及战后潜伏于美国的经历。故事伊始,“我”便称“我是个双面人,还是个有两套思想的人”[1]1,“我”的两套思想正是源于殖民“模拟”。“模拟”一词来源于法国精神分析学家雅克·拉康,原指动物将肤色变得与环境类似以保护自己,是生物本能的求生之道。当代著名后殖民理论家霍米·巴巴创造性地借用“模拟”这一概念来描述殖民者与被殖民者之间的关系:殖民者对殖民地进行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统治,被殖民者在不知不觉中接受和模仿宗主国的价值观念和行为准则;与此同时,被殖民者与殖民者之间不断产生延异、差别、超越,被殖民者“一方面吸收、‘挪用’一切有用的东西来完善自我,另一方面戏拟、拒绝、不服从、摈弃被模拟者,从而在近似中产生威慑的力量”[2]200。因此,“模拟是对殖民话语的复制,但复制出来的并不是与原体完全一样的复制品,而是‘像却不是’(like but not quite)的一种他者”[2]200-201。
《同情者》中美、法两国在越南推行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和政治体制,法越混血儿“我”即是在这一背景下成为“模拟人”。“我”自幼被天主教思想浸染,长大后被送往美国接受高等教育,甚至将英文学到母语水平。主人公在模拟殖民者价值观念的过程中发现,不论美国还是法国,都是打着“拯救落后文明”的旗号行剥削越南之实,因此主动抵抗殖民话语的控制。正如巴巴指出的,“殖民权力也不是绝对的权威和强势,被殖民者也不是完全被动的受害者,在他们的关系中,存在着某种模模糊糊的矛盾状态,而通过不断的文化商讨和交流,总会产生某种对抗和抵制的可能性”[3]100。正是在这样一个控制与抵抗的双向模拟过程中,“我”脱离了纯粹的越南文化,又无法完全接受美国或法国文化,只能徘徊在两种意识形态之间,饱受殖民主义带来的身份认同焦虑。值得一提的是,在《同情者》结尾处经历磨难的主人公没有自暴自弃,而是成为了一个真正的“同情者”,在关怀其他受难者的过程中找寻到了生命的价值与意义。笔者借助霍米·巴巴的后殖民理论,分析小说中殖民者的模拟控制手段与被殖民者的模拟抵抗策略,探讨作家对被殖民者走出身份认同困境的思考,这既有助于读者更好地了解殖民主义的运作机制,也能深入挖掘小说关怀被殖民者的人文价值。
1 美、法殖民者的模拟控制
越南曾分别经历了法国和美国的殖民话语统治。传播宗主国价值观、改造越南本土文化是美法两国主要的模拟控制手段。早在16世纪末、17世纪初,西方殖民主义者就以传教士和商人身份来到越南[4]90,他们从教育、文化等各方面,企图通过“模拟”策略向越南渗透资本主义国家的价值观念。清华大学教授、后殖民理论研究专家生安峰指出,殖民统治的重要手段之一就是让被殖民者模仿宗主国的文化、建制、价值等,以达到控制其民众的目的[3]106。《同情者》中“我”的父亲就是一位来自法国的天主教神父,与一位越南本地女子生下了“我”。在“我”儿时,每当“父亲给他教区的孩子们传经布道时,母亲叫我非听不可,从他那里,我了解了《圣经》、天父的历史、高卢祖先的故事、天主教教义”[1]239。越南的本土宗教是“和好教”和“高台教”,东方的佛教也在越南产生过重大影响[5]94,随着西方传教士不断增加,天主教思想在越南被广泛传播,本土宗教的影响力被大大削弱。宗教信仰是人类精神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法国早期传教士将天主教思想传播到越南,实则是对越南人进行文化渗透,为殖民入侵作准备,传教士是后来殖民者的探路人,在西方殖民者眼中“传教士教育是世俗化教育模式的直接先驱与典范,对后殖民教育环境产生了强有力的、充满见地的影响”[6]。在传教士的教育下,被动模拟的越南人会对宗主国产生感激和依赖之情,“我”的母亲就是如此。母亲是越南人,因家中贫困上不起学,来自法国的传教士父亲教母亲识字算数。母亲曾说“他总是对我很好,我很想报答他”[1]241,因此年少无知的母亲生下了“我”,并且认为“是天主送你来到这个世界,不然绝不会让你父亲和我之间有那事的”[1]242。在被动模拟中,许多越南人接受了宗主国的宗教思想,并在很多方面逐渐丧失了自我。显然,宗主国对殖民者的控制策略发挥了效果。
1885年越南彻底沦为法国的殖民地后,殖民者除了借助教育实施精神控制,也从国家治理层面进行了更直接的管控。《同情者》中处处可见法国殖民的影子。“我”曾在西贡工作居住,这里不少街道名称被法国人改为法语名,如“诺罗敦大道、夏斯卢·罗巴大街、阿尔贡码头大街”[1]23。法国人在西贡建立运动休闲总会,总是摆出一副傲慢新贵的派头,对越南侍者颐指气使。此外,法国殖民者还对越南少数民族进行粗暴划分,用“蒙塔格纳德人”(在法语中是“山地居民”之意)统称越南几十个居于山地但风俗语言皆有差异的民族。主人公“我”曾对此质疑道:“你们把这些人统称为蒙塔格纳德人,我就想知道,是在说布鲁族、侬族,还是岱依族呢?”[1]158巴巴曾指出“自由主义在西方公然声称其平等主义的计划,可是当面对阶级和性属差异时,却又显得极为暧昧模糊”[7]49,法国人一边宣扬自由、平等、进步的文化,一边又用种族差异思想治理越南。在他们眼中,不论什么民族,越南人只有一个身份,那就是“被殖民者”。越南人因此成为被剥夺差异性的“他者”。
法国于1954年战败,在《日内瓦协议》上签字停战,从越南撤退,然而美国却悍然宣布不受协议约束,并大力扶持南越亲美势力,向越南派驻美国士兵,最多时达50万[4]93。由于此时北越由越南共产党领导,美国不能直接实行殖民控制,只能在与北越作战的同时拉拢南越亲资本主义派。因此相较于法国殖民者,美帝国主义者对越南的殖民模拟策略更加隐蔽。
首先,美国为发动侵略战争编造了貌似合理且高尚的原由,即所谓的从落后的文明中拯救越南人民,为他们带来自由与民主。在谈及越战时,《同情者》中专门研究亚洲的美国学者赫德博士认为“美国总是抱着美好意愿,希望天下人均享自由与独立”[1]300。以“我”的上级将军为代表的南越军人对美国言听计从,认为美国人会兑现承诺,帮助他们清除“祸患”,怎料到美国战败,美国国内反战厌战情绪高涨,美国最后只能一逃了之,留下一片残局。
其次,除了将战争合理化,美国实现霸权的另一个武器是文化殖民。“我”在美国接受了大学教育,谙熟美国的俚语与社交文化,英文说得甚至比普通美国人要好。南越战败后,“我”被安排跟随将军逃亡美国。接到这一任务时,“我”对好友敏坦白其实自己原本就想去美国的,因为那里有“超市和超级高速公路,有超音速喷气飞机和超人,有超级航母和超级碗”[1]33。此时的“我”对美国生活充满了向往。主人公到达美国后受邀成为一部讲述越战的好莱坞大片的文化指导。导演将影片的主角设计为一个受过哈佛大学的高等教育、家境良好的美国军人,为了拯救落后的越南甘愿走上战场。而影片中的越南人则被设计成“爱死了救他们的美国兵”[1]185。除了咿咿呀呀求救的叫声,这些越南人角色没有别的台词,他们的存在只为突出美国士兵的救世主形象。美国通过充满种族主义想象的象征文化对越南进行精神殖民,使得被殖民者对美国产生精神上的崇拜。
推崇“美国梦”也是美国文化殖民的模拟策略之一。美国为战后逃至美国的越南难民营造了一个绚丽的“美国梦”。加州奥兰治县的一位议员在参加一对越南难民的婚礼时宣称:“这是对移民到美国的人作出的承诺!这是你们实现美国梦的承诺!美国是爱国者家园,一直以来义不容辞地帮助弱小者。”[1]140议员这番话,让在场的越南人“个个激动不已,自始至终,喝彩声鼓掌声不断”[1]141,沉浸在美国为他们勾勒的虚幻“美国梦”中。
如果说法国的殖民方式属于一种实践与发现,那么美国则属于巴巴指出的另一方面的殖民,即“它是一个梦想,一个意象,一种幻境、神话、迷恋和需要”[8]135。在美、法两国“实践”和“梦想”的模拟策略控制下,千千万万越南人和“我”一样对西方文化产生了依赖与崇拜,在不自觉中向往着殖民者为其创造的自由神话。
2 越南被殖民者的模拟抵抗
研究殖民问题的另一重要理论家萨义德将殖民者与被殖民者之间的关系描述为二元对立,即一种压迫与被压迫、控制与被动模拟的关系。巴巴却对此提出质疑,他认为殖民关系的复杂程度远非二元对立可以描述,他认为“在萨义德那里,殖民力量是完全为殖民者拥有的,这在历史和理论上都过于简单化了,萨义德的东方主义是殖民理论意向性和单一性的统一,这种统一也使得殖民发声被统一了”[9]。巴巴批判的是萨义德将殖民者置于权力结构权威地位的行为,这使得被殖民者只能扮演受压迫的角色,如此,殖民话语内部就不存在逻辑问题,而被殖民者也没有抵抗的余地。在萨义德这里,殖民过程本身“是一个完整的工程,反对殖民主义则需要从外部进行干预”[3]110。巴巴致力于研究的不是反殖民主义的外部干预,而是殖民话语固有的罅隙。在巴巴看来,殖民逻辑本身是矛盾的,它既肯定差异又排斥差异。巴巴认为“在二者之间不仅存在着对立,同时也存在着非常复杂、非常密切的心理联系,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关系”[8]136。因此“模拟”不仅是殖民者的控制策略,也是被殖民者的抵抗策略,其抵抗的力量正是源自殖民话语的逻辑漏洞。殖民者一方面企图用自己的文明将被殖民者同化,抹杀他们的差异性,另一方面,为了维持自己主人的地位,又不得不令他们与自己保持一定的差异。倘若二者的差异真的不复存在,殖民者也就无法确保自己的优势地位。因此,模拟不是对文化的同等复制,而是一种戏仿,是一种“反讽似的妥协”[8]140,这一点在《同情者》中也得到了很好的体现。
故事中的双面间谍“我”不是被当作普通越南民众教化,而是成为殖民者的代言人、一个模拟的典范。“我”从小接受传教士父亲的教育、被送往美国上大学,这些都是为了将“我”培养成肤色上是越南人、思想上却是西方的模拟人,作为最接近宗主国要求的被殖民者架起殖民者与当地民众间的桥梁。讽刺的是,主人公并没有成为一个与西方侵略者拥有相同价值观的人,而是逐渐发现殖民话语内部的矛盾,自觉与殖民者保持了距离。小时候,母亲总将父亲施舍给她的法国零食当作礼物,而“我”却总是保持清醒,知道这是父亲的“诱饵”,明白一个神父给女孩“礼物”是何企图。因此,尽管经常受神父训诫,“我”却对父亲讲的那一套天主教思想嗤之以鼻。在中学时,“我”认识了好友敏,一起接触了共产主义思想,从而两人从天主教信仰转向共产主义信仰。在将军身边卧底后,“我”与敏每周在一座教堂接头,“我俩单膝跪地,貌似虔诚,但其实是无神论者,不信天主只信共产主义。因此我俩礼拜,煞是滑稽”[1]30。“我”的信仰变化正是对殖民话语的一种“戏仿”,可见,模拟无法成为殖民国家对被殖民者的绝对控制手段,相反,反而是其殖民控制中的一道裂缝[3]106。主人公不仅没有成为殖民者想要的模拟“代言人”,反而生成了与殖民者绝对相异之处。
主人公虽然在中学时就脱离了法国天主教的思想控制,然而对美国描绘的自由民主的文化仍然抱有幻想与期待。越战后,被迫流亡美国的“我”终于看清了美国殖民话语的漏洞。“我”在西方学院的东方研究系谋得一份文员的工作,系主任鼓励“我”多培养自己身上的美国特质来平衡东方性格,并且告诉“我”任何人生活在美国的土地上,没准哪天就能当上总统,这与种族没有任何关系。初来乍到的“我”听闻系主任这番话颇为激动,然而“我”追求美国梦的幻想很快被现实打碎。在担任好莱坞大片文化指导时,负责与“我”联系的导演助理对“我”极其不尊重,甚至不用名字或人称代词称呼“我”。“我”终于明白即使说着一口完美英语、精通美国文化,作为一名亚裔,“我”在白人眼里仍然“名声不好”。因此“我”开始质疑美国式平等。在影片开始拍摄后,“我”认为导演一味突出美国士兵的英勇,不给越南人台词并不符合战场事实,提出意见后,却被导演恶语相向,“你拍过几部片子,一部没有……,谢谢你教我怎么拍片,立刻从我这里滚蛋”[1]158。好莱坞的经历让“我”彻底看清了美国在文化建构过程中如何抹杀他者,从而让美国例外于战争和殖民的罪恶。 “我”在发现这一点后不禁讽刺道:“我同情起天真的法国人。他们的信条是,若要利用一国,需实地考察该国。好莱坞效率高出许多:它要利用一国,仅靠想象即可。”[1]159在美后期,“我”已经看透美国的文化控制策略,并且试图证明其片面性。为了帮将军筹集反攻越南的资金,“我”结识了华盛顿智库常驻学者赫德博士,他在研究亚洲人的著作中,将越南人粗暴地分为两类,一类是读马克思著作的激进分子,他们不在美国争取的范围内,一类是大力推崇美国的越南年轻人,博士指出这类年轻人是美国需要培养的对象。“我”在听到这番论调时,颇为不满,“他没视我为一本厚书,只当我是一页纸,一张上面的内容易读易懂的纸”[1]291-292。而“我”则通过与赫德博士辩论证明越南人有思想、有差异,不是一个平面的、随随便便就能研究透彻的对象。
至此,“我”已对美、法两国的殖民话语都产生了抵抗,明白了他们不过是在自身例外的基础上说教被殖民的越南人,使其产生认同感,然而“面对被殖民者的模仿时,又以本体劣等性思想保持与被殖民者的距离,从而维持其霸权”[10]。于是,模拟成为了巴巴所说的“对控制过程的策略性逆转,……被歧视者的注视转回,投向权力的眼睛”[11]160。殖民话语在殖民者的文明语境中或许能保持其统一的表象,但是到了被殖民者的语境中,其矛盾本质必然会暴露。殖民话语不断延异,最终使殖民双方都落入一种暧昧不明的身份状态。
3 后殖民身份认同困境
巴巴的“模拟”概念使我们得以管窥殖民权力关系的罅隙。同时,巴巴还致力于研究模拟策略导致的复杂身份认同。在研究殖民身份时,巴巴大量借用了拉康精神分析学的概念,他指出,殖民认同产生于“自恋与侵凌”“隐喻与换喻”相结合而运作的复杂过程[9]。巴巴认为在殖民中存在认同的原型,如“两面三刀的亚洲人”,又如《同情者》中“对美国感恩戴德的越南人”与“超级英雄式的美国人”,他借用拉康的“自恋与侵凌”和“隐喻与换喻”两组概念正是为了说明殖民原型如何影响身份认同。因此,有必要先对拉康精神分析中这两组重要概念作一个说明。拉康认为主体的自我意识起源于“镜子阶段”,即对镜像中他者的误认,从此主体便在自我基础上开始异化,进入象征秩序阶段[12]60。拉康镜像理论的重要启示在于主体无法认识真正的自己,永远只能借助他者来建构自我;而主体对他者的认识同样也是不真实的,总是借助自我认识他人,由此引发了“自恋与侵凌”,它们构成了镜像阶段主体矛盾人格的基础。因此,主体对他人的认知很大程度上是自我的投射,并且这种“自恋”总是伴随着对外界客体的侵犯。巴巴用这一点解释了殖民者建构原型的根本动机,即隐含在原型背后的殖民者对自己的自恋式认同。此外,由于被殖民者也需要借助他者来认识自我,于是这种原型不仅得到了殖民者的认同,也同样也受到被殖民者的承认。
需要注意的是,原型并不是真实存在,它不过是对现实的掩盖。这一点,巴巴借用了拉康的“隐喻与换喻”来解释。拉康认为,主体的无意识欲望想要躲过规则的筛查进入意识,必须通过一系列的“包装”,即隐喻和换喻:隐喻就是用一个能指代替另一个相似的能指,而换喻则是用一个能指表达另一个有邻近关系的能指[13]436-439。隐喻和换喻给了能指“自治权”[14]52,让他们能自由地表达各种无意识欲望。拉康认为能指优于所指,因为意义产生于能指链的移动,而“在能指之下,所指不断迁移”[13]433,也即是说意义处于不断的延异中。在此基础上巴巴认为殖民话语中的原型与无意识欲望相似,也是通过“隐喻与换喻”来运作,即“作为隐喻,它通过原型的在场,而遮掩了现实的缺席;作为换喻,它又以似是而非之物将可见的缺席者记录下来”[15]46,并且使得原型的意义处于不断延异中。巴巴揭示了殖民身份认同的矛盾性和不确定性,其实殖民者与被殖民者都处于身份认同的幻象中,所认同的不过是经过隐喻和换喻包装的原型罢了。随着模拟的进一步加深,尽管被殖民者可能发现殖民话语中的漏洞,其人格的分裂与异化却是木已成舟,主体也成为了精神分析中所说的神经官能症患者。尽管双向模拟使得被殖民者的抵抗成为可能,但在这个过程中,侵凌性殖民话语对被殖民者造成的人格分裂与异化将是不可避免。
在《同情者》中,哪怕抗法战争、越战都已结束,后殖民的身份困境仍然如幽灵般困扰着“我”。主人公已经脱离自己的种族,带上了“白面具”,却又发现这只是殖民者将殖民行径合法化的把戏,最终无论是在哪一种文化里都无法找到认同感。在美国,“我”发现,只要谈及种族,“一个人不属于此种族就属于彼种族,没有一半一半之说。要么是白种人,要么不是白种人”[1]151,根本没有接纳双面人的余地。同样地,“我”在越南也无法寻得身份认同。再次回到越南时,“我”与越共的一位指挥官在思想上产生分歧,指挥官认为“我”沾染了小资产阶级气息,有精英思想和西方习性,并强调“我们就是百分之百越南人。你也必须努力变成百分之百越南人”[1]368。圆满确定的认同感,对主体来说显得格外重要,身份认同包含的固有侵凌性使得主体不会接纳比自己优越的他人,也不能容忍将自己视为理想自我的他人;尽管他非常珍惜自己的生命,但为了获得确定不移、完满自足的自我意识,他甚至不惜以生命为代价去斗争[12]73。从词源上来说,身份认同identity起源于拉丁词 identitas,它有两个基本意义:第一个意思是表示绝对的同一性:这个与那个是相同的;第二个意思是表示自身独特性的概念,它假定(人和物)在时间中具有持续性和自身统一性[16]。因此,不论在越南还是美国,身份认同都需要是纯粹的、百分之百的,而因为模拟人格异化明显的“我”最后必然成为两种文化的他者。
“我”所面临的后殖民困境——身份认同的不断延异,提醒我们被殖民者的心理异常复杂,不是某一种理论可以一言以蔽之。从拉康和巴巴的论述中,我们似乎已经看到了主体人格分裂的必然性,后现代主义更是认为“根本就不存在什么身份。不,身份从来就不是给定的、被接受的或获得的,只有身份认同无终止的和不确定的幻想过程是永存的”[17]27。面对似乎永远不可求得的自我统一性,被殖民者究竟有何出路呢?实际上《同情者》的结尾部分的伦理倾向已经回答了这个问题。“我”在受尽越共折磨后,终于在好友敏的帮助下,与众多难民一起登上了逃离越南的船。再次离开越南前,“我”意识到双面人的痛苦经历教会自己“永远同情最最被轻贱的人,……内心的罗盘,受我们的经历这个磁场的引导,无论发生什么,将指向受苦难者”[1]437。我们不知道主人公即将去向何方,但可以明确的是,他在经历磨难后走出了身份困境的迷宫,不再纠结自己属于哪种意识形态,而是转向走向永远为更弱势的他者发声的伦理道路上。淡化对自我统一的追寻,在为他者发声的过程中找到自我存在的意义,这不是正是抵抗自我认同侵凌本质的最佳选择吗?这与巴巴致力推广的世界主义,有异曲同工之妙。在巴巴眼里,世界主义就是将“他性”的存在含纳进自己的日常生活和语言实践,从而建立一种能够应对种族多样性的、具有包容性的世界主义文化[3]143。在巴巴这里,世界主义早已不仅是一种观念,而是一种生存的伦理,这也是《同情者》为后殖民语境中的身份认同困境提供的启示。
4 结束语
《同情者》向读者展现了模拟策略的双向性及其给被殖民者带来的身份困扰。一方面,美国、法国通过模拟策略对越南实施制度和文化等各方面的控制,使被殖民者对其产生依赖与认同。另一方面,模拟不是单向的控制,被殖民者也能借助模拟对抗宗主国的霸权。“我”在深度模拟中发现了美、法两国不过是以拯救越南为借口,将战争与殖民合理化。主人公也通过给好莱坞电影提意见等方式反抗殖民话语。被殖民者在模拟中成为双面人,既脱离了原文化,又被拒斥于宗主国文化之外,饱受身份认同的困扰。揭露困境的同时,《同情者》并没有以悲观论调结束,而是在结尾借“我”之口呼吁,无论经历了何种困境,都要对受苦难者永保同情,在为他者发声的过程中找到自我的意义。这是《同情者》中展现的生存伦理,也是巴巴所期待的世界主义,对解决后殖民者身份困境有着积极的指导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