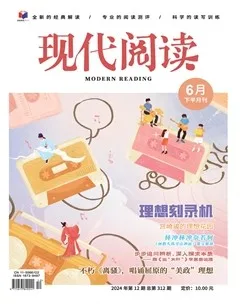论述类文本
2024-05-24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1~5题。
留白,中国文人的艺术“自留地”(节选)
◎ 宋 羽
偶然读到白居易的《暮江吟》,竟被一句“可怜九月初三夜”感动到了,说不出什么原因,只觉得触碰到了中国文人特有的艺术“自留地”的边缘。
九月初三,不是节日,不是节气,似乎也不是什么特别的日子。这个日子在白居易的诗里,似乎处于被忽视的位置—人们想象着“一道残阳铺水中,半江瑟瑟半江红”的景致,回味着“露似珍珠月似弓”的灵动, 甚至琢磨着“可怜”二字里透露出的爱怜、 珍惜之情,至于“九月初三夜”,无足轻重的日子罢了,谁会在意它呢?
它偏偏几乎占据了整一行诗,以看似“无意义”的状态构成了一首七绝的四分之一。如果说《暮江吟》是一幅画,那么“九月初三夜”就是这幅画的留白,一片“无意义”的空白,为天地之间的山水留出了可供呼吸的空气,这种空白,就是物质与精神流动的空间,也是中国文人呼吸艺术气息的一片安静之地。
诗需要意犹未尽,画也需要余味无穷,而文字和笔墨未曾触及的地方,就是留白。
留白作为一种艺术表现形式,渗透在传统中国文人的日常生活和审美中。镂空的花窗、镂空的回廊,连太湖石也一定要以瘦、漏、皱、透为美,让人在石头的空隙间感受光线和空气的流动。这是一种延续性的美,它让人的感官跳出了客观事物的束缚,进入了精神世界,进入了情感世界。留白,留下的是想象,而美,一旦进入想象的空间,就有了无限可能。
我相信古人对时空的概念必有他们独到的理解,远近高低,既是诗歌,也是绘画和书法。看明代徐渭的写意花鸟,仿佛在看飘零的人生—墨葡萄在风中狂舞。风在哪里?风在留白处,这些飘忽不定的风,在葡萄的反衬下跃然于观者眼前。再看宋代米芾、唐代张旭的狂草, 锋利的狼毫将怪诞狂妄铺陈开来,笔断意连,无墨之笔反倒更加变幻莫测,扣人心弦。
中国的文人自古就生活在矛盾之中,他们渴望坐看南山、采菊饮酒,过着与世无争的日子,但又舍不得“货与帝王家”带来的荣耀,他们读书、求学,满腹经纶只求考取一个功名。功名是什么?功名与理想无关,与诗无关,与人的存在无关,可它偏偏攫住了无数人的胳膊,让人挣扎不得。迫于生计,他们在人生画卷上描绘了太多寻常人眼中“有意义”的图像,可越是如此,就越需要一些留白,越需要在一些“无意义”的艺术形式里呼吸真性情的空气。于是九月初三的夜晚就成了永恒的艺术,成了无穷的遐想和怀念。
将留白艺术发挥到极致的当属元末明初画家倪瓒。倪瓒的留白是为水域和天空准备的,他用寥寥数笔勾勒出山的轮廓,然后留下一片干干净净的白色,几乎不事墨色—将观者带进倪瓒的美学空间的,不是山,恰是水天处的空白。在倪瓒笔下,山只是陪衬,水和天才是主体,虚实和主次的关系在倪瓒的空间维度里发生了巨大反转。所以《渔庄秋霁图》也好,《秋亭嘉树图》也罢,倪瓒笔下的山水总透着点点寒意,大片的留白给即将南下的冷空气腾出了呼啸而过的空间—凉意在呼吸间浸透肺腑,最终化作无限的寂寞。
这样的意境, 明代张岱在随笔《湖心亭看雪》中也有相似的表现:“雾凇沆砀,天与云,山与水,上下一白,惟长堤一痕,湖心亭一点,与余舟一芥、舟中人两三粒而已。”这是文学领域虚实和主次关系的反差,同样通过视觉上的留白手法来实现,不同的是,倪瓒的留白更为干净和彻底,他的画面是无人之境,是无我之境—他不是画中风景的参与者,甚至连旁观者的身份都不需要。
倪瓒和赵孟頫、黄公望、王蒙并称为“元四家”,他们在创作上讲究空隙和苍润之美,明朗通透的枯笔山水宣告了文人画标准画风的形成。回看整个元朝,东方传统文化和艺术几乎都处于一种被排斥压抑的状态,散落于民间,像一片无人看管的荒野,各种植物竞相生长,诗歌、散曲、话本小说、书法、绘画、杂剧,都由着自己的性子肆意兴衰。来自草原的统治者更愿意将目光投向遥远的美索不达米亚甚至欧罗巴,他们醉心于马背上的征服,让儒家士大夫从庙堂走向乡野,使得权贵气息、士大夫气息与平民气息相遇,这是先前两宋画院里拥有官员身份的宫廷画师无法想象的。 有元一代,士人沦落为文人,绘画中的匠气充盈了文人气、书卷气,因而元朝统治者对文化艺术的漠视意外推动了文人画的发展。
其实绘画里的东西,诗歌里也有,你读“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这是白描,可偌大的画卷上还有大片留白,你想知道空白处到底是山上的风景还是山下的农家生活,可诗人却说“已忘言”,他说得那么洒脱又真挚,让你分不清他是真的忘却了, 还是故意使性子不说。不说,反而比说了更让人心安。许多人生,因为“不说”变得简单和真挚了,就像许多诗歌,因为留白变得朴素和平易近人了。这样的人生和诗歌都让人感动。
好的艺术形式都会在空间和时间上留下一些空白,喜怒哀乐就在这空白里。
空白是什么?是无限延伸的外延,是语言无法描摹的内心最柔软的地方,留下一些空白,也是为了在下一次蓦然相遇时激起情感深处的波澜和感动。比如南朝陶弘景看山,说“岭上多白云,只可自怡悦,不堪持赠君”。山上究竟有多少妙处?他也是只看在眼里,绝不说破—你若急切地想知道,何不亲自上山一见?
(来源:《文汇报》2023年10月5日7版,有改动)
1.下列对材料中相关内容的理解和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
A.人们读《暮江吟》,容易忽视九月初三这个似乎并不特别的日子,而重视“一道残阳铺水中,半江瑟瑟半江红”的景致。
B.在日常生活中,镂空的花窗和回廊所呈现出来的留白之美,让人的感官跳出客观事物的束缚,进入精神和情感世界。
C.倪瓒的《秋亭嘉树图》中,山只是陪衬,水天处的空白引导观者进入他的美学空间,虚实和主次的关系发生了反转。
D.倪瓒在绘画中的留白比张岱在《湖心亭看雪》中的留白更为干净和彻底,这说明留白在绘画领域比在文学领域更深刻。
2.根据材料内容,下列说法中不正确的一项是( )
A.中国的文人想要在一些“无意义”的艺术形式里呼吸真性情的空气,但又为生计所迫,不得不去追求功名,因此一直生活在矛盾中。
B.“九月初三夜”成了永恒的艺术,成了无穷的遐想和怀念,可能是因为白居易在他的人生画卷上描绘了太多寻常人眼中“有意义”的图像。
C.在元朝,统治者醉心于马背上的征服而漠视文化艺术,客观上使儒家士大夫从庙堂走向乡野,意外推动了文人画的发展。
D.我们想知道“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空白处究竟隐藏着什么,诗人却说“已忘言”,“不说”使诗歌因此变得朴素和平易近人。
3.下列选项中,对留白手法解说错误的一项是( )
A.马致远《天净沙·秋思》中“夕阳西下, 断肠人在天涯”, 描绘的是“夕阳”和“人”,却让读者感受到羁旅异乡的作者无尽的落寞与思念。
B.姜夔的《扬州慢·淮左名都》中“念桥边红药,年年知为谁生”,留下大片空白,引领读者去品味、思索那年年盛开的红芍药花背后所隐藏的无限悲怆。
C.岑参《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中“山回路转不见君,雪山空留马行处”,以马的足印写惆怅惜别之情,给读者留下丰富的想象空间。
D.李清照《如梦令》中“试问卷帘人,却道海棠依旧”,“试问”一句问得自然,空出所问内容;“却道”一句答得认真,空出侍女的细心。
4.作者为什么认为留白是中国文人的艺术“自留地”?请根据文本概括分析。
5.请结合材料主要观点,对《琵琶行》中“东船西舫悄无言,唯见江心秋月白”作简要
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