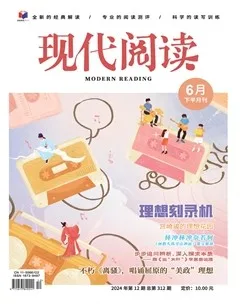皮普:在“远大前程”中找寻自我
2024-05-24邹恒羽

狄更斯是一个世纪里,我所曾见到过的唯一的一个天才。
——[俄]列夫·托尔斯泰
导读
在19世纪的英国文坛上,批判现实主义作家查尔斯·狄更斯是一颗闪耀的明星,他关注英国底层民众的生活,笔端始终丰盈着人道主义的光辉。狄更斯晚年的重要作品《远大前程》创作于1860至1861年,故事围绕心怀“上流绅士”梦想的乡野孤儿皮普突然获得一笔神秘的资助展开,这部作品被美国作家约翰·欧文评价为“英语语言中最杰出、结构最为完美的小说”。主人公皮普拥有怎样的“远大”理想,他又是否成长为自己想象中的模样,成功奔赴“远大前程”?本期“名著赏析”,让我们透过角色跌宕起伏的人生经历,探索皮普自我追寻和成长的心路历程。
皮普的自我追寻之路
少年皮普之烦恼
我真想做个上流绅士啊。
少年皮普受姐姐、姐夫照料,在温和善良的姐夫乔的影响下,他不失天真的本性,会为自己偷拿家里的锉刀和食物给逃犯马格威奇而自责,虽然衣食贫乏,但生活平静。
皮普心态的转变,发生在他被带到萨蒂斯庄园,结识古怪的女贵族哈维沙姆和她的养女埃斯特拉后。
“瞧这孩子,他竟把‘内夫’叫作‘杰克’!”第一局牌还没有打完,埃斯特拉轻蔑地说,“瞧他的手多么粗糙!他穿的鞋多么笨重!”
…………
以前,我从来没有为这些事操过心,现在却烦恼起来,觉得自己这方面实在粗俗……要是乔当年受到了较为高尚的教育,那我也就不会这么没有教养了。(第八章)
“埃斯特拉”在古语中本意为“星星”,狄更斯赋予她这个名字,也借用星星的象征意义暗示了角色的身份、性格乃至命运。一身光芒的埃斯特拉从“黑暗的走道”中登场,“好像一颗明星”,瞬间击中了皮普的心。然而埃斯特拉也像星星一样可望而不可即,这一点在第七章皮普的主观感受中也有所暗示:“……抬头望着这一大片闪闪烁烁的繁星,却得不到一丁点儿援助或怜悯,那该多么难受啊!”美丽却高傲冷漠的埃斯特拉对皮普的1b0ae88be5dfd9975b78a38a20414864奚落,让皮普受到了物质和精神的双重打击—满身珠光宝气的她让皮普羞愧于自己粗糙的手和笨重的鞋,进而对当时上流社会的生活产生向往;贵族们对纸牌的特别称呼也使皮普觉得自己缺乏学识教养,甚至对乔产生忘恩负义的念头。
等我成了你的学徒,乔啊,那该多么开心啊。请相信我一片真心。皮普上。(第七章)
“比迪,”我急躁地嚷道,“我现在这样一点儿也不快活。我对这种行当,这种生活实在感到厌烦。从我当上学徒以后,我一直没有喜欢过这种行当、这种生活……”(第十七章)
“……我要做一个上流绅士,就是为了她。”(第十七章)
在此之前,皮普最大的愿望就是做一个像乔那样的铁匠,此时他却向启蒙老师兼好友比迪透露自己不喜欢铁匠学徒的工作和生活。在他心中,对埃斯特拉的爱慕与自尊心的受损是同时出现的,对现状的不满与对未来的想象也是相伴而生的。对埃斯特拉的爱慕点燃了皮普心中名为“期望”的火苗,最初的“远大前程”愿望应运而生。
技法指引
《远大前程》将第一人称视角细分为“经验自我”与“叙述自我”的双重视角,前者是正在经历事件的“事中我”,即天真单纯的少年皮普;后者是回顾往事的“事后我”,即冷静客观的中年皮普。小说开篇以中年皮普的口吻介绍了自己年少时的身份和人际关系,便于读者了解背景;少年皮普的讲述则迅速将读者带入“我”的内心世界,跟随主角的视角,深度沉浸其中,从而引发共情。
课堂实践:在你学过的课文或课外看过的文学作品中,有哪部作品同样采用了双重视角?请对此简要分析。
答案提示:鲁迅《阿长与〈山海经〉》、史铁生《秋天的怀念》、张岱《湖心亭看雪》……
参考答案:高中语文选择性必修上册节选了狄更斯的另一篇小说《大卫·科波菲尔》,这篇小说同样运用了双重视角。课文选段采用第一人称视角,讲述“我”当童工的经历和与房东米考伯夫妇的交往。选段从成年大卫“叙述自我”的视角开始,“即使是现在”“在我十岁那年”“当年”等用语带有明显的回忆性质。此时的他肯定知道第六段登场的“陌生人”就是米考伯先生,狄更斯却立刻切换到儿童大卫“经验自我”的视角,以设下悬念的方式引导读者跟随“我”的所见所感逐步认识米考伯先生,从而强化这一人物形象的塑造。
皮普人生的大起大落
大起:梦想成真
我在这个世上那么渺小无知,外界的一切却那么神秘广大……
皮普想提高社会地位的愿望与日俱增。他将省下的钱用于求知,也幻想过从铁匠学徒出师后,女贵族哈维沙姆会助他飞黄腾达。好运随即从天而降—他收到一笔神秘资助,能让他摆脱铁匠学徒的身份,前往大城市伦敦接受上流绅士的教育,将来继承一大笔财产。
从今往后,再也见不到这些潮湿的洼地,再也见不到这一道道堤坝和闸门,再也见不到吃草的牛群了——这些呆头呆脑的牲口这天似乎也显出一副较为恭敬的神气,还转过头来,盯着我这个即将继承大笔财产的人尽可能地看了好半天——别了,我童年时代单调乏味的朋友们,我这就要奔向伦敦,奔向美好的前程;到了那里,我就不会再干铁匠的活儿,不会再和你们常聚了!(第十九章)
皮普沉浸在关于“远大前程”的幻梦中,丢失了宝贵的本性。奥地利作家茨威格曾言:“所有命运馈赠的礼物,都已在暗中标好了价格。”纵观皮普的前半生,他的物质“前程”越是远大美好,道德品质就越是堕落沉沦。启程前的皮普心中尚存良知和善意,对离开亲人抱有不舍、羞愧之念;而来到伦敦的他则越发势利,在浮华的社会环境中,拜金思想迅速滋生,他开始铺张浪费、债台高筑。乔满心欢喜地来伦敦见皮普,后者却并不十分高兴:一方面,他担心乔不合上流社会礼仪的举止被他的伦敦朋友看见后,自己会受到嘲笑和轻视,因而不愿再见这个“穷亲戚”;另一方面,乔的淳朴热诚反衬出自己的虚荣势利,彼此之间与其说是身份地位差距大,不如说是品性差距大。乔也感到极不适应,两人之间出现了无形的隔阂,曾经的“老朋友”变为客气疏远的“先生”,这与鲁迅《故乡》中闰土那声恭恭敬敬的“老爷”有着异曲同工之妙。
大落:黄粱梦醒
我搭乘的那条航船已经在礁石上撞得粉碎。
“……你不像我,你心里毫无准备。不过你一点儿也没想到会是我培养你的吧?”(第三十九章)
资助者的真实身份是全书最大的悬念。狄更斯有意安排哈维沙姆给皮普酬劳、她对皮普的转运毫不意外等情节,同时“误导”了主人公和读者。此时的皮普不会想到,这笔神秘资助竟然来自童年时自己曾救助过的逃犯马格威奇。后者逃到海外赚了大钱,认为偿还皮普一饭之恩的最好方式就是资助他进入上流社会。马格威奇冒着生命危险潜逃回来看望他,得知真相的皮普如梦初醒、懊悔万分—
唉,要是他始终没来找我,那该多好!要是他当年就让我一辈子留在那个铁匠铺里,尽管日子过得很不满意,可是总比现在快活!(第三十九章)
皮普受到的打击来自多个方面:自己收到的资助金并不“干净”,竟然来自一个逃犯的施舍,马格威奇一旦被捕,财产就会被没收,目前拥有的“上流绅士”生活将化为泡影,自己也可能遭受牵连,这令皮普感到后悔。同时,既然资助并非来自他猜想中的哈维沙姆,皮普意识到这位女贵族并没有打算把埃斯特拉许配给他,他对爱情的幻想随之破灭。他觉得对不起乔和比迪,“没脸回去”,甚至开始想念曾经贫穷但拥有亲情、友情的平凡生活—而这正是他此前想要竭力摆脱的。
皮普对“远大前程”的憧憬和梦想的破灭,流露出狄更斯对当时英国上流社会视金钱、地位至上的价值观的批判。
同频联动
乍富后的皮普心态失衡,价值观和道德标准发生变化。这令你想起哪些文学作品中的角色?
示例:吴敬梓《儒林外史》中的匡超人。
皮普的自我救赎
我从前所说的那场痴心的美梦早已完全消失了,完全消失了!
法国文艺理论家丹纳将狄更斯的小说归结为“行善和爱”,“好人有好报”的朴素因果观也使其作品站上了道德的高度。从高处跌落的皮普迷途知返,找回了善良的本性。他原谅了哈维沙姆,并在烈火中冒着生命危险拯救她;明知得不到财产,他仍关心和帮助狱中的马格威奇,让其最后的日子过得平静而安详。
“……你,”她(埃斯特拉)接着说,声音里充满了使一个漂泊在外的人感动的关切之情,“你还住在国外吧?”
“还住在国外。”
“肯定过得不错吧?”
“埋头苦干,好过得衣食无忧,所以——对,是过得不错!”(第五十九章)
狄更斯为本性回归后的皮普安排了一条崭新的道路:皮普落魄潦倒、大病一场时,乔及时赶来照顾他并为其还债;他劝说哈维沙姆资助好友赫伯特的事业,负债后投奔好友,努力打拼,最终还清债务并成为公司合伙人。通过奋斗完成自我救赎的皮普多年后回到家乡,乔和比迪对他不计前嫌,他也在萨蒂斯庄园的废墟上与埃斯特拉重逢,二人重归于好的小说结尾极富童话色彩,也表明了狄更斯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对人性之爱的宣扬。
在社会学领域,人的异化是指自然、社会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对人本质的改变和扭曲,具体到本书中,即“远大前程”改变了皮普的本性。成为“上流绅士”的愿望源于皮普对埃斯特拉的爱慕和对荣华富贵的向往,这虽然受到了哈维沙姆、埃斯特拉的影响,但真正从根本上促成这一愿望的还是马格威奇的资助举动。与乔一样,马格威奇扮演了类似皮普父亲的角色,他希望皮普能成为“人上人”,替自己实现“远大前程”。从某种意义上说,马格威奇改变了皮普的价值观,试图通过“孩子”实现自己的愿望,这是皮普异化的原因之一。讽刺的是,当皮普拥有马格威奇眼中的“远大前程”时,他并未成为真正的上流绅士;之后金钱地位的丧失、“远大前程”的破灭,反而让皮普从黄粱美梦中醒来,为其迈向光明前途、追寻真正的“远大前程”铺平了道路。
意象里的“远大前程”
皮普对“远大前程”的追寻贯穿全书,狄更斯也在小说中设置了隐晦含蓄的意象群,形成对现实生活的真实写照,在刻画人物的同时深化主题。
消散的雾
皮普的一生仿若在雾中摸索,“雾”虚无缥缈,给人朦胧迷茫之感,雾中之物的轮廓若隐若现,映照出他想象中的“远大前程”。前往伦敦前的皮普憧憬着“上流绅士”生活,对前途充满信心和期待,“完全陷在未来好运的迷雾中”,对家人朋友的留恋之情如朝雾般“早已在一片肃穆的气氛中散尽”。经过十多年的风雨沧桑,重回家乡的皮普找回了弥足珍贵的亲情、友情,埃斯特拉也不再高傲冷漠。“走出废墟的时候,夜晚的雾气也正在消散”,他不再为名利的幻象所迷惑,找到了人生真正的“远大前程”。
庄园与铁匠铺
女贵族哈维沙姆的庄园名字“萨蒂斯”意为“知足”,“凡是拥有这座宅子的人,都会心满意足”,然而生锈的铁栅、漆黑的走廊、荒废的酒厂却透露出古旧、阴暗、破败的气息;乔的铁匠铺尽管简陋,但始终燃着温暖的炉火。对庄园的向往象征着皮普对“上流绅士”生活的追求,回到铁匠铺则体现了他自我救赎的决心。二者象征着两种生活方式和前途命运,折射出狄更斯使世人看清“美德与其说居住在宫廷大厦,不如说居住在穷街陋巷”的创作目的。
服 饰
皮普与埃斯特拉初见时,服饰直观地彰显了两人的身份地位差异,埃斯特拉的轻蔑也激发出皮普想当“上流绅士”的愿望。奔赴伦敦前的皮普穿上新衣却感到不太称心,“这样照了大约有半个小时,才觉得比较顺眼一点儿”,对新衣的别扭感表明皮普对自己新晋“上流绅士”身份的不适应,也暗示了所谓的“远大前程”并不是皮普人生真正的归宿。
(引文来源:人民文学出版社《远大前程》,主万、叶尊译,有改动)
微写作:成长手书
在成长过程中,你有过怎样的梦想,是否想象过未来的自己将在某个领域大展身手?随着年龄的增长和思想的成熟,儿时为自己规划的“远大前程”是否有所变化?
请参照《远大前程》里中年皮普的叙事口吻,身处当下,以“回顾过去”的视角编写一份“自我成长手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