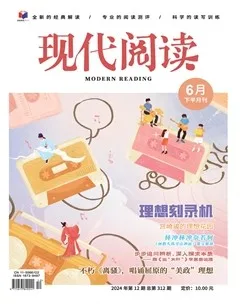不仅是为了那块砖头
2024-05-24张敏
我是一个渺小的人,渺小的人有一个渺小的理想。
为着这个渺小的理想,我奋斗了22年……
1962年秋天的一个下午,我和几个十七八岁的战友,在营房后边的砖瓦窑上谈起了个人的理想。热血沸腾之余,我们把自己的名字写在一块砖头上,向上苍发了誓,然后把砖头砸得粉碎—谁要是说话不算数,下场就和这砖头一样!
有两个战友说的理想是下决心存钱。有一个战友要拉二胡,说将来最起码要在千人以上的晚会上为大家演奏……轮到我时,我说我要当文学家!要写一个电影剧本,要在银幕上看到以我个人的名字编的剧,然后再写十篇小说,全要用铅字印出来。
这里面,数我的理想最“伟大”。当那块砖头被砸碎时,我的心跳得很厉害。
如今,22年过去了。几位战友再次相遇,谈起那场“砸砖立誓”的事,他们的理想都实现了。
这其中,唯我最苦。那次砸砖起誓之后,我便一心写电影剧本了。我的工作是在远离村镇的青海高原的荒滩上看管犯人。这里没有新华书店,也没有图书馆。我手头只有一本《电影文学》杂志,反复看了几十遍,便开始写题为《岳飞》的电影。不久,我收到了八一电影制片厂编辑寄来的信,告诉我《岳飞》已有人写过了,并让我从生活出发,写一写自己身边的事情。我把这封盖有公章的信像圣旨一样看了一遍又一遍。
后来,我想办法托人买书,用三匹马从四十公里外的邮电所驮回了一米高的六叠子杂志。我把这些书全部藏在床下边,抽出能够抽出的全部时间,每天看三本,把自己认为好的剧本、好的评论撕下来,另装成册。
一个星期天的早晨,有人叫我去接电话。临走前,我交代一个同屋的战友不要翻我的东西,他答应了。赶我回来后一看,头都气昏了。他把我好不容易才整理在一起的剧本呀,评论呀,全都翻乱了。他并不懂文学,只是在里面找美人头像。我一看,气不打一处来,便大声喝道:
“不让你乱翻,你这是干什么?”
“翻了怎么样?”
“你再敢翻一下?!”
他满不在乎,顺手拨了一下,那些单页便飘了一地。我眼睛红了,和他厮打了起来。只听见“妈呀”一声,他倒在地上了。
…………
据说当时最轻的处分是要打发我回家的。团政治处主任在会上说,这个战士要学习,将来想当作家,这不是坏事。过去我们没有过问这件事,干部们有责任。把他留下吧,给他点条件,说不定坏事可以变成好事呢。
团里要求我必须给战友道歉,求得他的原谅。我遵照执行,买了礼物,到卫生队去看他。一见到他,我哭了,他也哭了。他说:“张老兵,我再也不翻你那些宝贝了,你再不要这样打我了。”我真是后悔极了。
之后,连里腾出来一个洋芋窖,支了一个床板,每月到司务长那里领三斤煤油,发给我一盏马灯,允许我早起晚睡,到洋芋窖里看书。这件事传到师里。师宣传科每年给我参加一期创作学习班的机会。我写了七个电影剧本,虽然一个也没有被采用,但是许多制片厂都说我的剧本有点苗头。我为师团演出队写了许多节目,演出了,还得了奖。
1968年我退伍了,被分配到一家化工厂当了工人。这时的我,没有写出一个被采用的电影剧本来,也没有发表过一篇小说。我的名字一次也没有变成铅字。
1974年春天,区上请了一个作家,给全区的业余作者讲课,我也弄到了一张票。去得迟了些,小礼堂已经坐满了。守门的一位老兄看了看我的模样说:
“这里面是讲课,不演电影。听课的都是作者,你是作者吗?”
“我,我写过电影剧本,写过七个。”
“放映了吗?”
“没有。”
“发表过作品吗?一首诗也行。”
“没有。”
“那不算作者。写过电影剧本的人多得很,没有拍,屁都不顶!作者是见过铅字的,你连铅字都没有见过,算什么作者?”
我看着他的宽边眼镜,咽了一口唾沫。
“请你记住,十年后,我给你讲课!”说完这句话,我返身就走。
第二年的夏天,有几位作家在我厂深入生活。有一天,我们到街上闲走,来到一家茶馆喝茶。闲聊时,见那茶馆全是用报纸糊着墙壁。他们说,找找看,能不能从报纸上找到自己的文章。
我站在旁边一动不动。而他们都找见了自己的文章。羞愧呵!
那天晚上,我写了一篇散文《献给母亲》,第二天又写了一篇《蚕女》。我的小木箱里,已经有十几斤“作品”了,如今又添了两篇。
1977年冬天的一天,我在路上碰见了作家丁树荣同志,他告诉我要实行稿费制了。我当晚拿出了《献给母亲》和《蚕女》,久久徘徊在邮电大楼的门前。
一个多月后,我收到了《解放军文艺》杂志的来信。信上说,两篇均好,都准备采用。
15年了,我将要看到希望的曙光了。15年,漫长的15年,我看着我变成铅字的名字,喝了三杯酒,流了两行泪。
有了开头,就不能让它断了。1984年,我改编了作家张贤亮的长篇小说《男人的风格》,由西安电影制片厂开拍。不过,改编者有三个人。我的理想是写一个只有我一个人名字的电影。写不出来,我仍然可能“粉身碎骨”。
我是一个渺小的人,渺小的人有一个渺小的理想。
为着这个渺小的理想,我奋斗了22年;为着这个渺小的理想,我怕还要继续奋斗22年吧?
(来源:《读者》1985年5期,有改动)
技法课堂
复沓使感情浓郁
所谓复沓,也称重章叠句,指字句结构在反复中略有变化,可表达强烈的思想感情。文章开头重复提及“渺小的人”“渺小的理想”,将作者执着于理想的浓烈情感与语言上的循环往复相结合,产生了令人动容的艺术效果。结尾处再次使用复沓手法,语句上的重叠和文章结构上的首尾呼应使文章的内容、形式与情感达到了高度统一,“坚守理想”的信念被渲染得愈发鲜明。
时间节点的作用
文章采用线性叙事,从1962年作者“砸砖立誓”树立写作理想开始,以明确的时间节点为标记,如“1968年”“1974年春天”等,一步步推进叙事。这些时间节点对应着作者与不同人的交集——在他朝着理想前行的路上,有给他造成麻烦的战友,有大力支持他的部队干部,有嘲笑他的守门老兄……这些时间节点围绕着“追求理想”的主题,将跌宕的情节紧凑地连结在一起,使叙事更加连贯,更容易激发读者的情感共鸣。同时,作者在漫长的22年后仍然对这些时间节点记忆犹新,侧面体现了作者对理想的坚定不移与执着追求。
阅读思考
当代诗人陈先发认为“世界上所有的美,都需要高度的专注和漫长的淬炼”。他在复旦大学2018级本科新生开学典礼上讲到:“在高度信息化的生存中,人本身如何不会沦为一种快速消费品……在时代的屏幕上转瞬即逝的文字,越是浅陋粗鄙,就越需要有人能以‘坐得十年冷板凳’的勇气,舍弃眼前之利、萤火之光,创造出能昭示一个时代良心和品质的精神产品,穿透这个时代流传下去……越是有人不再确信什么,觉得‘爱’‘理想’‘信仰’都成了过时的、陈旧而虚张的概念,就越是需要另一群人把这些词高高地举在头顶。”结合文章,谈谈你对这段话的理解。
(答案提示:可以抓住“理想”与“时间”两个关键点,从“专注”“淬炼”“坚守”“勇气”等方面进行分析,强调无论身处怎样的时代,都应坚守理想并朝着理想努力前行。言之有理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