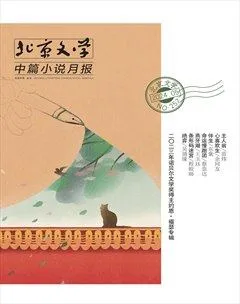无声的语言
2024-05-23约恩·福瑟作叶紫
〔挪威〕约恩·福瑟 作 叶紫 译
那是我念初中的时候,事情发生得毫无预兆。老师让我当堂朗读。不知何故,一股突如其来的恐惧把我压倒、制服了。我好像消失到恐惧里了,恐惧成了我的所有。我站起来,跑出了教室。
我注意到老师和同学们都瞪大了眼睛,看着我冲出了教室。
后来,我解释说,自己表现异常,是因为得跑去上厕所。从听我说话的人脸上看得出来,他们不相信我的说法。他们大概觉得我疯了,或者说,是在发疯的路上。
这种对朗读的恐惧一直跟随着我。随着时间推移,我终于鼓足了勇气跟老师说,我太害怕朗读了,请老师不要叫我当众朗读;有的老师信我,就不再点我,有的老师则觉得我可能是在搞什么恶作劇。
这份经历让我明白了一些与人相关的重要东西。
也明白了其他很多东西。
是的,很可能就是这些东西让我今天能站在这里,向在座的观众朗读讲稿。此时,我几乎感受不到恐惧。
我明白了什么?
当时的情况几乎让人觉得:恐惧夺走了我的语言,而我,可以说,得把它拿回来。要拿回来,就不能遵照别人的条件,只能用我自己的方式。
我写出了自己的文本、短诗、短篇小说。
我发现这么做给了我一种安全感,给了我和恐惧相反的体验。
某种意义上,我在自身内部找到了一个只属于自己的地方,从那个地方,我能写出只属于自己的东西。
现在,差不多五十年过去,我仍会安坐着写作——我仍会从自身内部那个私密的地方写作;关于那地方,老实说,除了它确实存在外,我知道得不多。
挪威诗人奥拉夫·哈·豪格〔奥·哈·豪格(1908—1994),挪威园艺学家,翻译家,诗人。〕写过一首诗,把写作行为比作小孩子的经历:在森林里搭起树叶小屋,爬进去,点起蜡烛,坐在黑暗的秋夜里,感受着这份安全。
我觉得这也非常形象地描绘了写作行为带给我的体验。现在如此——五十年前也是如此。
我明白的不止于此;我明白了,至少对自己来说,口语和书面语之间,或者说口语和文学语言之间,存在很大的差异。
口语常常是独白式的信息传达,表示某事某物应该这样或那样,它也可以是修辞型的信息传达,意在劝说或说服。
文学语言绝不是这样——它从不示知;它注重含意,而非传达,它有自己的存在。
在这个意义上,好的写作显然有别于各种类型的说教——无论是宗教性、政治性,还是其他什么性质的说教。
对朗读的恐惧让我进入了孤独状态——写作者或多或少都处于这种生活状态——从那以后,我一直待在那儿。
我写了很多东西,包括散文和戏剧。
当然,戏剧的突出特征在于它是书面的话语——其中有对白、有交谈,时常有尝试言说的努力,也许还有某种形式的独白——戏剧始终是个想象的宇宙,属于某种东西的一部分:这种东西虽不示知,但自成一体,自为地存在着。
说到散文,米哈伊尔·巴赫金言之有理;他认为,散文这种表达模式,或者说这种讲述行为本身,包含两种声音。
简单来说:说话者、写作者的声音,以及被说到、写到的人的声音。这两种声音常常融入彼此,以至于无法分辨。
它们变成了一种书写成文的双重声音——不用说,这也是那书写成文的宇宙的一部分,是它的内部逻辑。
可以说,我写下的每一部作品,都有自己的虚构宇宙,自己的世界。我的每一部戏剧、每一部小说,都有着各自的新世界。
但一首好诗(因为我也写过不少诗)同时也是它自己的宇宙——主要和它自身发生关联。于是,读诗的人能进入那个宇宙,也就是那首诗——是的,它更像是心意的交融,而非信息的传示。
事实上,我写的所有东西大概都是这样。
有一点是肯定的:我写作,绝不像有人说的,是为了表达自我,相反,我是为了出离自我。
最后我成了剧作家——是的;对此,我能说些什么?
以前,我写小说和诗,无意写剧本,但后来我还是写了剧本,因为当时有个公共资金赞助的项目旨在鼓励挪威新剧的创作,拨给了我这个穷作家一笔可观的经费,要我为一部剧写一个开场,结果我竟写下了一整部剧——这就是我的第一部也是迄今为止演出最多的剧作:《有人将至》。
虽然这是我第一次写剧本,但它却成为我整个写作生涯里最大的惊喜。在之前的散文和诗歌中,我都试图用常见的口语写出那些通常无法用文字言说的东西。是的,没错。我试图表达无法言说的东西;这也是诺贝尔奖颁给我的原因。
曲解雅克·德里达的一句名言来说:生活中最重要的东西无法说出来,只能写下来。(德里达的原话是:“最重要的是,不能说出来的东西,不能任其沉默,而要写下来。”)
于是,我试着用文字传达无声的话语。
写剧本时,我可以使用无声的话语,无声的人物,方式全然不同于我在散文和诗歌中采用的方式。我只需写下“停顿”一词,便有无声的话语出现。在我的剧作里,“停顿”这个词无疑是最重要也最常用的词——长停顿、短停顿,或者仅仅是停顿。
在这些停顿里,或意涵丰富,或意蕴贫乏。可能有的东西无法言说;有的东西不想被言说,只有什么都不说才是对它最好的言说。
然而,我可以肯定的是,通过这些停顿说得最多的,便是“无声”本身。
在我的散文里,所有重复都和我剧作中的停顿有着相似的功能。或许,这就是本人的看法:剧本里有无声的话语,小说里书写成文的语言背后也有无声的语言;我要写出好的文学作品,这种无声的话语也必须得到表达;比如,在《七部曲》里——举个简单、具体的例子来说——正是这种无声的语言说道,第一个阿斯勒和另一个阿斯勒很可能是同一个人,这整部长约一千两百页的小说或许仅仅是对某个被萃取出来的当下时刻的书面表达。
但无声的说辞或无声的语言多半是由作品整体发出。小说也好,剧本也好,戏剧制作也好,重要的都不是部分,而是整体,而整体也必须体现在每个细节当中——或许,我可以斗胆谈谈整体的精魂,一种可以说既从近处也从远处说话的精魂。
如果你足够仔细地听,会听到什么?
你会听到无声。
就像人们说的,只有在无声中,你才能听到上帝的声音。
或许吧。
现在,回归现实,我想谈谈我在戏剧创作中的另一所得。如我所说,写作是孤独的职业,而孤独是好事,只要——就像奥拉夫·哈·豪格在另一首诗里说的——只要回通他人的路依然畅通。
我第一次看见我写的东西在舞台上演出时,牢牢抓住我的,正是与孤独截然相反的关系;也就是相伴共享,是的,通过分享艺术来创造艺术——这带给我一种非凡的幸福感与安全感。
从那时起,这份洞见一直跟随着我,而且我相信,也正因有了这份洞见,我并不仅仅是抱着平和的心性在坚持写戏,即便自己的剧作上演后效果不好,我也能感到一种幸福。
戏剧行当其实蕴含大规模的倾听行为——导演必须主动倾听文本,或至少有义务倾听文本,一如演员倾听文本、倾听彼此、倾听导演,一如观众倾听整场演出。
对我来说,写作行为就是倾听:写作时,我从不提前准备,也从不规划什么,我凭着倾听来前进。
所以,如果要我来给这种写作找一个喻体,那这个喻体必定是倾听。
如此一来,几乎不言而喻的是,写作会让人想起音乐。我曾全心全意投入音乐,但十几岁的某个阶段,我可以说直接转向了写作。事实上,我彻底不再演奏音乐,也不再聆听音乐,而是开始动笔写作;在写作过程中,我试着创造出一些与我演奏音乐时的体验类似的东西。当时我就是这么做的——现在依然如此。
还有一点,也许有点奇怪,就是我写作时,总会有这样一刻,我感到自己的文本已经写好,在外面的某个地方,不在自身内部,我只需在文本消失前把它写下来。
有时我可以照写,不做任何改动,而其他时候,我不得不通过重写来寻找那个文本,不断裁剪、修订,小心翼翼地努力让已经写好的文本呈现出来。
我原本无意为剧院写作,最后却把大约十五年的时间全用在剧本上了。我写的这些剧本甚至搬上了舞台,是的,随着时间推移,它们在很多国家多次上演。
我至今难以置信。
生活真的不大可信。
此刻,我就无法相信自己正站在这里,试着就荣获诺贝尔文学奖,就何为写作说些还算靠谱的话。
据本人的理解,我之所以获奖,既与剧作有关,也与散文有关。
许多年里,我几乎只写剧本,然后,我突然有种感觉,真的写够了,是的,不止够了,还多了,于是我决定停止剧本写作。
但写作已成为习惯,一种我活着就没法放下的习惯——或许就像玛格丽特·杜拉斯一样,你说它是病都行——于是,我决定回到它开始的地方,写散文,写其他类型的作品,就像我以剧作家身份首次亮相前的大约十年时间里那样。
这就是过去这十年到十五年里我一直在做的事情。重新开始严肃的散文创作时,我不确定自己还能不能写下去。我先写了《三部曲》——这部小说被授予北欧理事会文学奖时,我体会到这是巨大的肯定,说明就散文来说,我也还是能拿出点像样的东西。
然后我写了《七部曲》。
在这部小说的写作过程中,我经历了自己作为写作者所能经历的一些最幸福的时刻;比如,在一个阿斯勒发现另一个阿斯勒躺在雪地里,于是救了他一命的时候。再比如这个时刻:故事结尾,第一个阿斯勒,也就是故事的主角,和他最要好的也是唯一的朋友艾斯莱克一起乘一艘小船,一艘旧渔船,踏上自己最后的旅程,去和艾斯莱克的妹妹一块儿过圣诞节。
原本我没有把这部小说写长的计划,但它几乎自行写了下去,变成了一部很长的小说,有很多部分,我写得无比流畅,一切都显得顺理成章。
我觉得那就是我最接近所谓幸福的时刻。
整个《七部曲》都包含了关于我其他不少作品的记忆,但呈现的角度不同。整部小说没有一个句号,这不是刻意发明的。我就是这么写下来的,从头到尾,如顺流而下,不需要句号。
我曾在一次采访里说,写作是一种祷告。看到这话刊登出来,我觉得尴尬。但后来我读到,弗朗兹·卡夫卡也说过一样的话,才聊感安慰。所以,或许——还是有点道理?
我最早出版的书都获评甚低,但我不打算听评论家说了什么;我该相信自己,是的,坚持写作就好。如果不这么做,可能四十年前,第一部小说《红,黑》面世后,我就停下了笔。
后来,我得到的多半是好评,甚至开始获奖——于是,我觉得继续以同样的逻辑写作是很重要的,我向来不听差评,也不会让成功影响到自己,我会坚定地继续写作,牢牢地坚守、坚持以往的创作。
我想,这就是我一直在做的事,我真的相信,在获得诺贝尔奖以后,我要做的事也不会有变。
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消息公布后,我收到了很多电子邮件和祝贺,不用说,我非常高兴;大多数问候都很简洁、欢快,也有人写道,他们开心到尖叫,还有人说他们感动到落泪。我真的深受触动。
我的作品写到很多起自杀。多到我不愿去想。我一直担心,这么一来,我或许推动了自杀的正当化。所以,最让我触动的是,有人坦承地写道,我的写作简直救了他们的命。
也许可以说,我始终明白,写作能挽救生命,它或许还救过我自己的命。如果我的写作有助于挽救他人的生命,我會感受到无上的幸福。
感谢瑞典学院授予我诺贝尔文学奖。
感谢你,上帝。
原刊责编 叶丽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