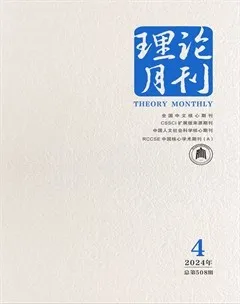论建党前后和大革命时期列宁主义在中国的传播
2024-05-22蔡凯文王刚
蔡凯文 王刚
[摘 要] 列宁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是马克思主义的中国传播史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应当给予必要的關注。建党前后和大革命时期列宁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并非历史的偶然,而是当时国内外诸多因素“合力”作用的结果。建党前后和大革命时期列宁主义在中国传播的内容主要集中在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帝国主义理论、新经济政策理论、民族和殖民地理论等。建党前后和大革命时期列宁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为中国先进知识分子认识、选择和接受马克思主义提供了桥梁,推动了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及其对中国革命基本问题的探索。
[关键词] 列宁主义;十月革命;无产阶级专政;帝国主义理论
[DOI编号] 10.14180/j.cnki.1004-0544.2024.04.004
[中图分类号] A821; K2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4-0544(2024)04-0031-12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两个结合研究”(22AZD003);江苏省高校哲学社会科学一般研究项目“整合资源构建高校实践育人共同体研究”(2023SJSZ0110)。
作者简介:蔡凯文(1993—),男,南京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王刚(1968—),男,南京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列宁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是一个值得深入研究的问题。长期以来,学界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研究主要侧重于马克思、恩格斯学说的传播,而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对列宁主义在中国传播的历史事实的挖掘和考察。事实上,建党前后和大革命时期列宁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对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推广以及中国革命进程的推进起了巨大作用。深入探究建党前后和大革命时期列宁主义在中国传播的时代背景、主要内容与历史影响等,对弥补当前列宁主义的中国传播史研究的不足,进一步丰富马克思主义的中国传播史研究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
一、建党前后和大革命时期列宁主义在中国传播的时代背景
建党前后和大革命时期列宁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并非历史的偶然,而是当时国内外诸多因素“合力”作用的结果。从国内环境看,这是近代中国救亡图存运动反映到理性世界的必然结果;从国际趋势看,俄国十月革命和西方的动荡局面从正反两个方面引发了中国思想界的新转向。
(一)社会改造语境下的主义崛起、社团兴起与刊物盛行
从新文化运动到五四时期,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关注的主题经历了一个从政治关怀、文化革新再到社会改造的转变过程。如傅斯年所言:“五四运动过后,中国的社会趋向改变了……以后是社会改造运动的时代。”1改造社会时代的来临,造就了主义崛起、组织兴起和刊物盛行的局面。其中埋藏着一条逻辑线索:谋求社会的根本改造就必须“先有一个共同趋向的理想、主义”2,从而放弃个人单兵作战,转而聚集在一面共同的旗帜下;这种聚集就催生出有组织、有方向、有纪律的团体,而这样的团体又会寻求刊物,将其作为宣传主义的舆论阵地。主义、组织、刊物由此形成一个同频共振、彼此关联的系统,为列宁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奠定了基础。
1.主义崛起为列宁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提供了思想空间。新文化运动在破除儒家思想和礼教秩序的同时,引入了各式各样的主义。这就给当时的人们提供了一个分析、比较、选择的机会,诸多主义在这一过程中起起落落,列宁主义异军突起,成为社会改造问题的最优解。毛泽东在1920年3月时表示,当时流行的诸多主义和学说“都还没有得到一个比较明了的概念”3。不过在同年7月,他就觉察到,在中国与世界其他国家“尚没有新文化”之时,却有“一枝新文化小花,发现在北冰洋岸的俄罗斯”4。两个月后,毛泽东最终得出结论:“俄国的旗子变成了红色,完全是世界主义的平民天下”5,俄国革命的胜利完全是因“有主义(布尔什维克主义——引者注)”6。
2.社团兴起为列宁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提供了组织载体。中国先进知识分子认识到:社会改造绝不是一两个人的力量所能够实现的,有必要进一步集合起来,成立一个集体化的组织,共同寻找出路。于是,五四前后各种类型的社团如雨后春笋般在中国涌现,“团体化运动”7由此兴起。社会改造要以社团为组织基础,而主义又是社会改造的灵丹妙药,所以主义与社团密不可分、相互联系。社团是传播主义的生力军,增强了主义的传播力量,扩大了主义的影响范围。这些进步社团聚集了一大批先进知识分子,进而形成了一种群体效应,为列宁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做出了突出贡献。
3.刊物盛行为列宁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提供了舆论阵地。五四时期不仅呈现出各种主义相互竞争和各类社团大量涌现的生动局面,也出现了一股刊物热潮,中国报刊事业发展迎来了一个黄金时期。这一时期的期刊发行量十分可观,以影响较大的杂志为例,《新青年》至1917年的年发行量达16000份,《改造》每期也能发行5000份,《每周评论》仅在北京一个地方就能发行50000多份8。据统计,“五四时期出版发行的153种期刊中,有65种刊载有关苏维埃俄国的论文、评论和其他作品,总共835篇”9。对此盛况,杨昌济满心欢喜:“新出之报章杂志,新译新著之书籍,新组织之团体,逐日增加,于是有新思想之传播,新生活之实现,此诚大可欣幸之事也。”10主义的传播、信仰的传递主要以刊物为舞台和阵地,许多青年通过阅读进步刊物而接受了先进思想和社会政治动员,相继走上革命道路,进一步扩大了列宁主义的受众范围。
(二)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的形成
五四时期存在着“大批的赞成俄国革命的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1,他们具备以往传统知识分子所不曾有过的新特点、新优势,并自觉担负起传播列宁主义的战斗任务,发挥着先锋和主力军的作用。
1.这批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群体是忧国忧民、追求真理的趋新求变者。为了实现“挽救危难的中國,解放痛苦的人民”2的目标,他们勇于探索创新,敢于否定自我,努力学习和吸收西方的新式学问与思想,且绝大多数人都受过良好的教育或有过留学经历。除了有强烈的爱国情怀、丰富的知识储备,更为重要的是,他们富有“重估一切价值”的批判精神,热切探索救国救民真理的坚定意志以及比较鉴别复杂、多元社会思潮的能力。面对当时社会盛行的“教育救国、科学救国、实业救国、佛教救国、基督教救国”等林林总总的救国论调,他们愈发对“究竟什么才是拯救国家、民族和社会的正确道路”3而感到困惑与迷茫。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改变了这种局面,为他们提供了新的视角与选择。于是他们决定“应用俄国式的方法去达到改造中国与世界”4的目的,开始秉持列宁主义,确立起坚定的共产主义信仰。
2.这批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群体是主张到民间去、同工农群众相结合的躬行实践者。他们从来不是空谈理论的书斋学者,而是于实处用力,追求知行合一的行动派。在他们看来,列宁主义作为落后国家与民族开展无产阶级革命的理论,如果只停留在知识分子和革命家的头脑中,未被广大工农群众所掌握,未同中国的工农运动发生联系,便无法产生任何实际效用。正如毛泽东所说:“知识分子如果不和工农民众相结合,则将一事无成。”5于是,他们广泛深入工人和农民群体,担负起教育工农、引导工农、组织工农的实际工作。在这一过程中,他们通过浅显易懂的语言、形象生动的实例,诠释了列宁主义的经典观点与核心概念,显著提高了工农群众的理论水平和阶级觉悟。
3.这批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群体是重视宣传喉舌、把握舆论主动的传媒工作者。比如,李大钊、陈独秀是《新青年》《每周评论》的主要负责人;周恩来曾担任《天津学生联合会报》的主编;恽代英曾经是武汉《学生周刊》的主要撰稿人;李汉俊是《星期评论》《新青年》的编辑,又与陈独秀创办了《劳动界》;李达是《共产党》月刊和人民出版社的负责人;邵力子是上海《民国日报》副刊《觉悟》的创办者;瞿秋白主编了《新社会》;毛泽东与蔡和森创办了《湘江评论》;邓中夏创办了《先驱》半月刊;高君宇先后任北京大学《学生周刊》和《向导》的编辑;陈潭秋、黄负生、李季、袁振英、沈泽民、包惠僧等或是报刊的记者、编辑,或是特邀撰稿人6。这些既是媒体人又是革命者的先进知识分子通过报刊等媒介,打开了传播列宁主义的新局面。
(三)十月革命的现实感召
在十月革命前,中国先进知识分子一直把学习的目光投向西方,密切关注着西方世界的政治动态,并在西方种种新思潮和新学说之间寻觅。可这些西方学说,要么由于理论本身的缺陷而“容易流为空谈”7,要么就是在理论上说得通,却在实践中行不通,最终“在中国人民的心目中,一齐破了产”8,打破了只要学西方就能救中国的迷梦。既然向西方学习的取经之路走到了尽头,就必须另辟蹊径来救治苦难的中国,引领中国人民走向光明未来。这个时候,十月革命一声炮响,让陷入“不知前途怎生是好”1的迷惘中的中国人看到了转机。他们认为,俄国与中国地理相近、国情相似,中国接下来只需要照着俄国所走的道路坚持走下去,就能改变国家衰弱不振的状况。正如许德珩所说:“十月革命以后,我们有了一个模糊的方向。”2吴玉章说:“我了解到我们北方邻国已经建立了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建立了一个劳农政府,伟大的俄国人民已经摆脱了剥削制度,获得了真正的自由解放。从前我在法国接触了社会主义各种思想流派,深深为社会主义理想所吸引。今天这个理想居然在一个大国内开始实现了,心中感到无限兴奋和鼓舞。”3刘少奇指出,十月革命的胜利“把全世界想要革命但又没有找到出路的人都惊醒了。特别是在中国,我们那时感到了亡国灭种的危险,但又不晓得朝那里跑,这一下就有办法了”4。这种实际可行的模式鼓舞了无所适从、迷茫不定的中国知识分子,使中国向何处去的时代之问有了得到解答的希望。
找到了一个成功范例,明晰了未来文明的方向,中国的先进知识分子自然要探寻这背后的主义,列宁主义就在这样的历史机缘下进入中国人民的视野。透过十月革命,中国先进知识分子看到了列宁主义在指导革命运动的过程中所爆发出的实践伟力。他们意识到,革命行动的实际影响远非理论宣传文章所能企及,已被事实证明的理论具备其他理论所不可比拟的震撼人心、启迪人心、征服人心的力量。列宁主义由此被中国先进知识分子视为一种“真权威”“真信仰”,他们开始认识到中国的现在和未来都有清晰的方向和道路,有现成的蓝图可供遵循。更重要的是,他们从列宁主义中“找到了一种能迅速转变为革命实践的行动世界观”5。因此,列宁主义很快就成为中国先进知识分子精神上的归宿和行为上的指针。
(四)巴黎和会后中国人民“六个月的乐观的幻灭”
1918年11月,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协约国的胜利而结束。中国虽没有出兵却派出过一些劳工,这种不战而胜的结果对于自近代以来屡战屡败的中国人民来说,像是一种从天而降的意外之喜。近代以来,中国将首次以战胜国身份出席巴黎和会。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社会各界都对巴黎和会充满幻想与期待,希望通过巴黎和会恢复中国的主权和独立,扭转中国在国际上屈辱与悲惨的地位。
从1918年11月到1919年4月的这六个月间,“学生们真是激动得要发疯了”,各种“名流们也勤于讲演”6。如北大校长蔡元培与一些社会名流在天安门讲演时,称赞威尔逊的“十四点”标志着“武断主义的末日”,开辟了“平民主义的新纪元”7。有媒体发表文章说:“美总统之意以为欧洲此次大战为人道而战,亦不啻为惩罚强权而战,故于战后企图永久之和平,而其第一义即欲取消从前强者对于弱者一切苛酷之条约,我国亦世界孱国之一,美总统以为固当扶持。”8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同样极力赞颂威尔逊,对其抱有极大的热情与信任。陈独秀称赞威尔逊“光明正大”,不愧为当今“世界上第一个好人”9。与此同时,北京不少学生还跑到东交民巷的美国使馆门前高呼:“大美国万岁!威大总统万岁!”1
正当人们对公正及和平翘首以待时,原本被寄予厚望的巴黎和会却上演了一出分赃的丑剧。在巴黎和会上,列强不仅无视中国人民提出的正义要求,还将德国在山东的权益悉数转交给日本。残酷的现实无情地粉碎了人们对公理与正义的幻想,中国人民痛苦、愤怒到了极点。许德珩说:“大家眼巴巴地企望着巴黎和会能够给我们一个‘公理战胜,哪晓得奢望的结果是失望。”2在胡适看来,“正因为有了那六个月的乐观与奢望,所以那四五月间的大失望能引起有热力的反动”3。这表明巴黎和会的外交失败将中国人民一下子从幻梦中拉回现实,给中国人民带来了从天上落到地下的巨大心理反差。可以说,假如没有之前如此之大的奢望与期盼,那么后来的失败、绝望和痛苦之感也就不会如此深刻。陈独秀在得知中国外交失败的消息时,直呼威尔逊为“威大炮”,愤懑地说“什么公理,什么永久和平,什么威尔逊总统十四条宣言,都成了一文不值的空话”4。
巴黎和会上希望的破灭,强烈刺激着中国人民特别是中国先进知识分子的神经。他们在沉痛中反思,在反思中觉醒。他们深切认识到,中国依然处在不平等的强权世界里,标榜公理、正义、平等的威尔逊政府与其他帝国主义列强并无区别。弱国无外交,依赖美国、迷信威尔逊来改变中国的现状根本不可能。与之相较,中国人民认为,俄国在“世界外交史上树立了未曾有的模范”5,列宁在国人心目中的地位迅速上升。张东荪敏锐预见了这一新趋向,认为“威尔逊在世界上就是好像克伦斯基在俄国”,如果“威尔逊主义失败”,“必定有世界的列宁出来”6。这在当时社会的民意调查中也能得到印证。1923年12月,北京大学进行了一场民意测验,投票选举世界第一伟人。列宁得了227票,位居第一;而威尔逊仅得了51票,位居第二7。由此可见,巴黎和会后,列宁取代威尔逊,成为中国人民心中的楷模,接受和传播列宁主义成为中国社会的新风尚。
(五)苏俄政府对华宣言的影响
1919年7月和1920年9月,苏俄政府在中国南北对峙、政局不稳以及巴黎和会外交失败、任人宰割之际两次发布了对华宣言,突然宣布要废除沙俄同中国缔结的不平等条约,取消沙俄政府在华的一切特权,放弃庚子赔款的俄国部分,并提出要同中国重新订立条约以保持友好的外交关系,为中国的民族解放斗争提供援助。
这种崭新的姿态使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对俄国的印象发生了一百八十度大转弯,激发了他们研究列宁主义的热情。正如蔣梦麟所说,俄国在对华宣言中一再宣布,“准备把北满的中东铁路归还中国,并且希望中国能够顺利扫除军阀,驱除侵略中国的帝国主义”,其后果之一“就是为苏俄式的共产主义在中国铺了一条路”8。美国学者石约翰也指出,苏俄对华宣言有助于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传播,“由于新苏联与西方国家和日本的东亚政策不同,对五四一代人来说这种联系就特别生动,因为正当后者在凡尔赛会议上欺骗中国时,布尔什维克的行为却完全不同”9。
苏俄政府的对华宣言表明,苏俄政府不仅渴望在平等基础上同中国建立外交关系,愿意为中国被奴役、被压迫的境况仗义执言,而且准备付诸实践。长期饱受帝国主义压迫与剥削的国人在获悉宣言内容后,无不感到欢喜。工人、学生、商人等组成的各种社会团体纷纷向苏俄的善意之举表示欢迎、表达感谢,由此引发了一股“友俄狂潮”。譬如,中华实业协会致电苏俄政府称:“此项伟大壮举,非仅为世界七千年历史第一次创见;抑且足以扫清旧世界国际间一般罪恶,开辟现世界全体民族互助宏基。”1工人团体尤其欢欣鼓舞,认为苏俄政府“是为世界人类谋真正的自由平等底幸福”,“全俄底农民、工人和红卫兵,是世界上最可亲爱的人类”,表示愿与俄国人民“立在那人道正义底旗帜下面,一齐努力,除那特殊的阶级,实现那世界的大同”2。随着苏俄对华宣言通过各种渠道在中国传播开来,社会舆论逐渐将宣言与苏俄推崇的社会革命、列宁主义联系起来。如基督教救国会在给苏俄的复电中指出,苏俄对华宣言是“根据其立国之根本主义”3。彭璜也明确指出,在苏俄对华宣言中“的确看出他的主义是反对强权,提倡人道,主张民族自治,不惜牺牲最少数人,以来收回最大多数固有的幸福。要创造一个大同世界,创造一个永远和平的世界。这就是他们的通牒中传播给我们中国人的一个主义,使我们永远不会忘记”4。陈炯明在致列宁的电文里说:“劳农政府致中国人民的宣言已传至中国,全国人民充满感激之情”,“我更坚信布尔什维主义定将造福于人类,我愿尽全力将布尔什维主义原则传播到全世界”5。对华宣言所展现的苏俄的全新形象与正义担当,进一步扩大了十月革命的影响力,增强了列宁主义的说服力,促使中国先进知识分子转向师俄、友俄、联俄。中国思想界开始接受和认同苏俄的主义,对此表现出极大的学习和研究热情。由此,中国出现了一个“列宁时刻”6,对列宁主义在中国的传播起着重要作用。
二、建党前后和大革命时期列宁主义在中国传播的主要内容
列宁主义中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帝国主义理论、新经济政策理论、民族和殖民地理论等,为变革中国社会提供了切实可行的方法和策略,因此受到中国先进知识分子的欢迎,在中国广泛传播。
(一)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传播
列宁主义的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对中国先进知识分子而言,极具穿透力和影响力。他们纷纷撰文阐释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强调这一理论对于改造中国的重要性。蔡和森批驳了无产阶级专政就是“以暴易暴”的错误认知,指出无产阶级专政是“由资本主义变到共产主义过渡时代一个必不可少的办法,等到共产主义的社会组织世界组织完成了,阶级没有了,于是政权与国家一律取消”7。新民也阐释了他对列宁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认识,直言无产阶级专政是列宁主义的要义之一,是由资本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社会的必经过程。它不仅是对抗资产阶级的武器,而且是改造社会经济的杠杆,而苏维埃制度就是建立无产阶级专政最适当的形式8。任卓宣在《我们对于十月革命应有底认识》中说:“无产阶级专政,是用以压迫大资本家和大地主(农工兵之敌人)而建设社会主义(代表工农兵利益而谋全社会之解放的)底工具。”9任弼时指出:列宁主义认为“无产阶级专政是无产阶级革命真正成功的工具,是资本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的历程中必然的历史产物,是消灭资产阶级反动势力建立社会主义基础的武器……这就是列宁主义根本要义的第一点”1。赵世炎也指出:“专政是为指挥革命的进程,防止反革命的骚动,运用国家的政权,过渡到社会主义之路。”2
(二)帝国主义理论的传播
帝国主义理论是列宁对其所处时代的资本主义发展新特点新现象的总结,深刻揭露了帝国主义的本质及其罪行,直接激励了中国先进知识分子举起反对帝国主义的旗帜。
列宁的《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以下简称“《最高阶段》”)是全面阐释帝国主义理论的著作。1920年11月7日,《共产党》第1期集中介绍了列宁19本重要著作,其中就以《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末日》为书名,向国人介绍了这部著作。《最高阶段》的最早中译文,发表在1924年5月12日至30日《民国日报·觉悟》杂志的“名著”栏目上,题为《帝国主义》。该文节译了《最高阶段》的第1—6节,译者为李春蕃。1925年2月,该文又以单行本的形式面世,书名为《帝国主义浅说》。该文指出,生产与资本的高度集中形成的垄断,是帝国主义的根本特性,其表现形式是由商品输出向资本输出转变,其结果是帝国主义通过经济掠夺和武力手段瓜分世界市场。该文尽管没有包含后四章,但仍然向国人清晰阐释了帝国主义的定义、形成及其基本特征。值得一提的是,一峰(张若茗)根据列宁的《最高阶段》,撰写了《帝国主义浅说》一文,论述了帝国主义的定义、性质及发展3。斯大林的《列宁主义概论》也在1927年被译为中文,该书指出,列宁之所以叫帝国主义为“垂死的资本主义”,是因為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矛盾发展到极端的界限,过了这界限,革命就开始了。这些矛盾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劳动和资本中间的矛盾”;二是“各派财政团体和各派帝国主义列强中间为争夺原料产地争夺别人领土而起斗争的矛盾”;三是“少数统治的‘文明民族和几万万殖民地弱小民族人民中间的矛盾”4。这些文本对传播列宁的帝国主义理论起到了推动作用,使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对帝国主义的认识实现了从感性到理性的跃升。
瞿秋白详细介绍了列宁的帝国主义理论,指出:“列强资本主义国家内财政资本统治一切社会生活;纸币及一切有价证券的发行,已至于总握全社会的金融;输出资本到国外弱小国家内,经营实业或放兑国债,以攫取当地的原料,遂成为帝国主义的根源之一……”5帝国主义国家的发展极不平均,“于是各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明争暗斗非常剧烈,除了诉之于武力之外,绝无其他恢复均势之可能”,“因此,帝国主义之下,战争必不能免;而欧美无产阶级革命与东方之弱小民族革命要相联结,而成反帝国主义的统一战线”6。王懋廷在黄埔军校讲授关于帝国主义课程时,为讲课需要,参考《最高阶段》编写了题为《帝国主义大纲》的政治讲义。讲义内容涉及“帝国主义之内容”“帝国主义之历史的发展”“帝国主义之崩溃”7。萧楚女的《帝国主义讲授大纲》分析了帝国主义的由来及其性质,着重分析了帝国主义的未来。他认为,资本主义的弊端及反帝联合战线,决定了帝国主义必将走向灭亡的命运8。
(三)新经济政策理论的传播
1921年后,列宁领导苏维埃俄国放弃直接过渡到共产主义的“战时共产主义”政策,改为实行“迂回”过渡的新经济政策。国内外一些别有用心的人对苏俄实行的新经济政策抱有很深的偏见,甚至进行了许多恶意的宣传,攻击苏联实行新经济政策意味着放弃了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认为“俄国革命失败了”,俄国已“倒退到资本主义”,新生的苏维埃制度就要消亡了。为了回击这些错误认识,让人们了解新经济政策的实质与科学性,以及实行新经济政策的必要性,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广泛关注并大力宣传了列宁主义的新经济政策理论。
寰澄在《苏俄十月革命后八年来奋斗的经过》一文中指出,“以唯物史观的眼光去观察,新经济政策,是工业落后的国家,物质条件中必然的产物”。十月革命后的俄国,不仅工业基础十分落后,而且经过长时期战争,国家的财富消耗殆尽。在这样的情况下,俄国没有可用于恢复工业的资本,因此也就丧失了仅凭自身发展工业的可能性,而实行新经济政策可以借外国资本来发展俄国工业。寰澄由此得出结论:“新经济政策,是社会革命的一种手段,是社会革命过程中所必由之路!而一般疯狂的帝国主义者以及不懂得俄国内幕的人,说俄国的新经济政策,是俄国革命之失败,回复到资本主义社会。这完全闭着眼睛说瞎话!”1任卓宣也指出,苏俄通过十月革命打倒了内外敌人,这是成功的第一步,而后面临的最主要的问题就是发展生产。列宁“在这个时代,定出了一条非常宽大平坦的到社会主义之路——新经济政策,新经济政策不是目的而是手段”。自新经济政策实行以来,“不仅经济发展,政权更是非常巩固”。因此,“新经济政策不是对资本主义让步的形式,而是对资本主义建设的方法;不是社会主义失败的证明,而是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2。
瞿秋白目睹了苏俄实施新经济政策后所实现的经济恢复与发展,因而对列宁的新经济政策理论十分重视。他深入阐释了实行新经济政策的历史必然性和意义,指出苏俄的新经济政策本质上是国家资本主义的经济形式,具有过渡性质。苏俄实行这种过渡性的经济形式,是由苏俄现实的政治基础和经济基础所决定的。一方面,由于大工业基础的缺乏,俄国的无产阶级力量极其有限,占人口多数的是小生产者。要团结小生产者、壮大无产阶级的力量,就必须实施新经济政策,将其当作调节国家和农民利益关系、增进工农联盟的政治手段。另一方面,俄国小生产占主导地位,大工业极不发达,社会主义国家缺乏必要的经济基础。必须通过新经济政策尽快地发展大工业,克服私人资本的局限,并与国际资本交换,利用国际资本加速发展生产力3。任弼时进一步阐述了新经济政策对落后国家在革命成功后走向社会主义的意义。军事共产主义政策“难适用于工业不发达的一切国家——即工业发达国家在革命后第一时期内亦不能完全采用——因之使工业及农场的生产力不能发展。所以终于采用能适合各国无产阶级革命后所需要的新经济政策以代之”4。
(四)民族和殖民地理论的传播
民族和殖民地理论是列宁主义基本理论的核心之一,是中国共产党制定战略、策略的基本理论依据,对中国革命具有特殊的意义,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因此,对列宁民族和殖民地理论的介绍,也就成为建党前后和大革命时期列宁主义在中国传播的重要内容。正如《向导》所说:“在中国,民族问题无疑是革命中最重要的问题之一。马克思主义对于民族问题本有特色的革命的见解,自列宁以后尤形成整个的理论。”5
1920年7月至8月,共产国际二大制定的《关于民族与殖民地问题决议》《关于民族和殖民地问题的补充提纲》等,标志着列宁民族和殖民地理论的正式创立。不久,共产国际二大和列宁民族和殖民地理论的相关文本就在中国问世。如1921年《共产党》月刊刊登了沈雁冰翻译的《加入第三国际大会的条件》、沈泽民翻译的《资本主义世界和共产党的世界联盟——第三国际共产党第二次大会的宣言》这两份共产国际二大的文件。1922年1月,《先驱》杂志发表了“G.S.”翻译的《第三国际对民族问题和殖民地问题所采的原则》,文章摘译了列宁《民族和殖民地问题提纲初稿》的第1至第5部分的内容。译文虽短且有的地方翻译得并不十分准确、通顺,但它让中国人初步了解到列宁民族和殖民地理论的一些基本内容。同年4月,人民出版社出版了由沈泽民翻译的《第三国际议案及宣言》一书,其中包括《关于民族和殖民地问题决议》和《关于民族和殖民地问题的补充提纲》两份文件的全部内容。总的来看,对列宁民族和殖民地理论在中国传播与介绍,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1.世界分为压迫民族和被压迫民族,其中被压迫民族占绝大多数,它们应当联合起来。硕夫援引列宁在1920年第三国际第二次大会中的论断:帝国主义“使世界上一方面为一大批被压迫的民族,另一方面为很少数的,但极富强的压迫的民族,全地球上約十二万五千万的大多人口都归为被压迫的民族”。“这种压迫民族与被压迫民族之区分是有大的意义的,因为他一方面指示每个世界革命者应该注意到先进国的工人阶级与经济落后国的被压迫民众之反帝国主义的联合战线;另一方面又指示殖民地或半殖民地被压迫的人民所应依附的营垒。”1瞿秋白指出,列宁“将全世界分成两个敌对的营垒:少数先进国家的压迫者剥削者,大多数殖民地和弱小民族的被压迫者被剥削者。因此,各殖民地及弱小民族反对帝国主义的革命运动日益兴起”2。
2.殖民地半殖民地的革命运动已经突破地区的狭隘限制,成为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一部分。林根指出:“列宁主义的最大特点而且于东方民族有最大关系的,就是‘将西方的资本主义的国家的社会革命和东方的殖民地的国家的国民革命联结起来,以打倒国际帝国主义,实现‘世界革命的主张。”3陈独秀说:“殖民地半殖民地之国民革命,形式上虽是一国的革命,事实上是世界的革命之一部分,而且是重大的一部分。”4郑超麟指出,列宁“把民族解放运动和无产阶级革命联合起来,以为民族的不平等是资本主义社会种种不平等中之一种,真正的民族解放必须无产阶级革命成功,但西方无产阶级革命的成功也需要殖民地弱小民族反帝国主义之解放运动的赞助,民族殖民地问题是无产阶级革命总问题中的一部分”5。李达指出:被压迫民族解放运动,“是世界革命最重要的枢纽……决不是孤立的单独的问题”6。
3.民族自决是民族解放运动基本原则。所谓民族自决,指的就是“政治自决即国家独立、建立民族国家”7。如果没有彻底的民族自决,那么民族问题就无法得到完全解决。新青年社出版的《列宁主义概论》指出:“列宁主义扩大民族自决权的定义,解释这是殖民地弱小国家被压迫的民族要求有完全分立的权利,是各民族有独立国家存在的权利。因此,就不能够解释民族自决权就是民族自治,并拿来赞成兼并政策。民族自决的原则,在帝国主义战争时社会爱国派手中,无疑是欺骗民众运动的工具,从此就变成揭破一切帝国主义贪欲和社会爱国派狡计的工具,变成根据国际主义精神作群众政治教育的工具了。”8任弼时也在《列宁主义的要义》中指出:“列宁主义扩张了民族自决的观念,以民族自决权为被压迫国家与殖民地的民族之完全分立权,换言之,为各民族有权设立自己的国家,保有政治与文化上的完全的独立。”1
三、建党前后和大革命时期列宁主义在中国传播的历史影响
建党前后和大革命时期列宁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为中国先进知识分子认识、接受和选择马克思主义提供了桥梁,推动了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及其对中国革命基本问题的探索。
(一)为中国先进知识分子认识、接受和选择马克思主义提供了桥梁
毛泽东曾说:“中国人找到马克思主义,是经过俄国人介绍的……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2这句话正确说明了中国人民选择和接受马克思主义同苏俄之间的内在联系:十月革命所唤起的俄国社会的希望,同中国人民一次次奋斗失败后的绝望形成了鲜明的对照;鲜明的对照带来了巨大的落差,巨大的落差又引发了走向深处的思索;这种深思最终使中国人民接受了马克思主义这一崭新的理论武器,中国革命的面貌为之一新。这种马克思主义,是俄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即列宁主义。中国人民是通过列宁主义认识、选择和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列宁主义一国胜利理论及其实践更加符合当时中国的国情。
在十月革命前,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就已经在中国介绍马克思主义,也尝试用马克思主义的一些观点来分析和阐释中国社会问题。依照当时传入的马克思主义观点,社会主义革命只能在一切或多个资本主义充分发展的欧美国家同时发生,并陆续取得胜利(“同时胜利论”)。而在当时的中国先进知识分子看来,按照这种逻辑,中国的资本主义发展还不充分,不具备进行社会主义的条件。因此,他们也就没有接受和进一步钻研马克思主义。列宁根据对新历史时代特点的研究,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的内容,并进一步将“同时胜利论”改造为“一国胜利论”,也就是社会主义有可能在一个或数个国家率先取得成功。在“一国胜利论”的指引下,十月革命取得了胜利,苏维埃政权在各方面都还十分困难的情况下站稳了脚跟。这就为中国人民选择和接受马克思主义提供了一个重要的历史机遇,启发了一些先进知识分子向俄国学习,通过进行社会主义革命来改造经济社会同样落后的中国。梁启超认为:“俄国过激派政府居然成立,居然过了两年……从前多数人嘲笑的空理想却已结结实实成为一种制度。将来历史价值,最少也不在法国大革命之下。”3陈独秀指出:“此时我们中国不但有讲社会主义底可能,而且有急于讲社会主义底必要。”4李达在对社会主义运动的各种手段进行了分析后,得出结论:“俄国是农业国,中国也是农业国,将来中国的革命运动,或者有采用劳农主义的直接行动的可能性。”5从这些言论中,我们可以清晰看出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对列宁主义及其实践的认可。
(二)促进了中国共产党的成立
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是十月革命对中国影响的最集中的体现,也是中国先进知识分子自觉运用和践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直接结果。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受到了列宁主义的鼓舞。依照列宁的观点,必须建立作为无产阶级的先锋队的共产党,否则革命是不能成功的。所谓的“无产阶级先锋队”,表明党区别于无产阶级的其他群众组织(如工会),必须以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思想,由无产阶级中的优秀分子所组成。列宁尤其强调先进的革命理论对党的发展的重要作用,指出:“没有革命理论,就不会有坚强的社会党,因为革命理论能使一切社会党人团结起来,他们从革命理论中能取得一切信念,他们能运用革命理论来确定斗争方法和活动方式”1,“只有以先进理论为指南的党,才能实现先进战士的作用”2。自发的工人运动不能真正产生洞悉本阶级前途命运的无产阶级意识,因此无产阶级政党的任务就是把社会主义意识灌输到自发的工人运动中去,把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结合起来,赋予工人运动以社会主义性质。列宁说:“给我们一个革命家组织,我们就能把俄国翻转过来!”3由此引出的是无产阶级阶级意识的产生和灌输问题,以及马克思主义理论与革命实践的关系问题。
除此之外,列宁还主张共产党应将民主集中制作为组织原则,只有这样才能形成一个有组织的整体,从而保持无产阶级的领导地位。后来,列宁又把这个组织原则进一步推广到共产国际,指出:“加入共产国际的党,应该是按照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建立起来的。”4一方面,列宁主义鼓舞了中国先进知识分子以俄为师,建立“和俄一致的党”。陈独秀就指出:要造就无产阶级强大的组织力和战斗力,“非有一个强大的共产党做无产阶级底先锋队与指导者不可”5。另一方面,列宁主义还指明了在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建立无产阶级政党的路径与方法,推动了中国共产党的成立。1921年的中共一大就鲜明体现了中国共产党是“依照苏联共产党的榜样建立起来和发展起来的一个党”6,遵循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全体党员组成了一个具有统一意志、统一行动和统一纪律的战斗整体。因此,中国共产党从一开始就是深受列宁主义的建党学说和建党原则的影响而建立的,这就使中国共产党“在思想上和组织上都没有受到欧洲社会民主党第二国际的影响”7。
(三)推动了中共二大对中国革命问题的探索
1922年1月,共产国际在莫斯科召开了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中国共产党除了派张太雷参加大会的筹备工作外,还派遣代表与国民党等组织组成中国代表团参加这次国际会议。1922年7月召开的中共二大,贯彻落实了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的精神,运用列宁主义的基本观点,全面剖析了近代以来中国社会政治经济的状况,认识到“中国一切重要的政治经济,没有不是受他们(帝国主义国家——引者注)操纵的”。除了对帝国主义侵略本质的认识,中共二大宣言还指出,在中国封建军阀“一方受外国资本帝国主义者的利用唆使,一方为自己的利益把中国割据得破碎不全”8。因此,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是中国革命最危险的敌人,是中国革命的主要对象。外国资本主义为了自己的发展和利益,扶持封建军阀,阻碍了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因此中国的资产阶级仍然有革命的要求,具有革命性。而在帝国主义、封建势力的压迫与剥削下,无产阶级同样需要参加民主革命运动。无产阶级不但要团结穷苦农民,而且要和资产阶级结成对敌的联合战线。而在这个联合战线中,“无产阶级……固然应该联合民主派,援助民主派”9,却不能投降和附属于民主派。因为民主革命胜利后,“无产阶级不过得着一些自由与权利,还是不能完全解放”10,只是实现了革命的第一步。无产阶级必须要继续对付资产阶级,与农民联合起来,为实现无产阶级专政而奋斗。在对列宁关于民族和殖民地理论深入理解和对中国国情认识的基础上,中共二大明确将反帝反封建作为中国民主革命的主要任务,制定了党的最高纲领和最低纲领。
对于中国共产党从一大到二大的成长与进步,马林提及了陈独秀在中共三大致闭幕词时的一段话:“党在第一次代表大会时还没有纲领,甚至没有规章,党的要求——无产阶级专政——悬在半空,到第二次代表大会时就脚踏实地了,有了规章,找到了与中国实际的联系并决定了党要走的道路。”①“脚踏实地”四个字充分凸显了中共二大在党的历史发展中的重要地位,也有力说明了中共二大探索中国革命问题所取得的代表性成果的重要意义。列宁主义在这个过程中起到了重要作用。
四、结语
建党前后和大革命时期,列宁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始终与中国的本土实境相呼应、与时代相作用。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基于自身的价值取向和革命的现实需要,广泛传播列宁主义体系中的核心内容,为中国革命运动提供了理论依据和實践经验的双重指导,使中国人民找到了摆脱被动挨打的困境的科学理论。在列宁主义的影响下,中国共产党宣告成立并逐步走向成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思想探索和行动实践开始发轫,翻开了中国历史的崭新一页。回望和审视建党前后和大革命时期列宁主义在中国传播的历史面相,有助于我们深刻理解为何当各种主义在中国竞相争鸣时,其他主义大多流行一时却很快湮灭,而唯有马克思主义展现出蓬勃生命力,实现从一种学说到社会主流意识形态的历史性跨越。
责任编辑 罗雨泽
On the Dissemination of Leninism in China before and after the Founding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and during the First Revolutionary Civil War Period
Cai Kaiwen Wang Gang
[Abstract] The dissemination of Leninism in China is an indispensable and important part of the history of the dissemination of Marxism in China, which should be given necessary attention. The spread of Leninism in China before and after the founding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and during the First Revolutionary Civil War Period was not a historical coincidence but the result of the combined effect of domestic and foreign factors at that time. The dissemination of Leninism in China during these periods mainly focused on theories of dictatorship of the proletariat, imperialism, new economic policy, and national colonialism. The spread of Leninism in China before and after the founding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and during the First Revolutionary Civil War Period provided a bridge for Chinese advanced intellectuals to understand, choose and accept Marxism, and promoted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and the exploration of basic issues of the Chinese revolution.
[Keywords] Leninism; the October Revolution; dictatorship of the proletariat; imperialism theory
1张允侯等:《五四时期的社团》(二),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9年,第97页。
2《李大钊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49页。
3《毛泽东早期文稿(1912.6—1920.11)》,长沙:湖南出版社,1990年,第474页。
4张允侯等:《五四时期的社团》(一),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9年,第44页。
5《毛泽东早期文稿(1912.6—1920.11)》,长沙:湖南出版社,1990年,第504页。
6《毛泽东早期文稿(1912.6—1920.11)》,长沙:湖南出版社,1990年,第508页。
7王汎森:《思想是生活的一种方式:中国近代思想史的再思考》,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8年,第92页。
8白冰:《中国知识界对1917年俄国革命的认知与反应》,《湖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2期。
9孙成本:《俄罗斯文化1000年》,北京:东方出版社,1995年,第327页。
10杨昌济:《达化斋日记》,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194页。
1《毛泽东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699—700页。
2《新民学会资料》,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393页。
3《黄克诚自述》,北京:人民出版社,2019年,第15页。
4《新民学会资料》,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147页。
5《毛泽东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559页。
6田子渝、蔡丽、徐方平等:《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初期传播史(1918—1922)》,北京:学习出版社,2012年,第33页。
7张允侯等:《五四时期的社团》(二),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9年,第345页。
8《毛泽东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471页。
1《梁启超游记》,北京:东方出版社,2006年,第20页。
2张允侯等:《五四时期的社团》(二),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9年,第37页。
3《五四运动回忆录》(上),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年,第59页。
4《刘少奇论党的建设》,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1年,第507页。
5萧秋、吉胜、冯雷等:《国外学者评中国共产党》,北京:中国华侨出版社,1992年,第60页。
6《五四运动回忆录》(续),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年,第52页。
7蔡元培:《黑暗与光明的消长》,《北京大学日刊》1918年11月27日,第3版。
8《欧战和会与我国关系》,《申报》1918年11月22日,第6版。
9《陈独秀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343页。
1李季:《我的生平》,上海:亚东图书馆,1933年,第184页。
2《五四运动回忆录》(续),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年,第51页。
3《胡适文集》第11卷,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578页。
4《陈独秀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461页。
5《商界总会答覆俄牒》,《民国日报》1920年,4月14日,第10版。
6张东荪:《中国问题与世界革命》,《时事新报》1919年5月10日,第1张第1版。
7朱务善:《本校二十五周年纪念日之“民意测量”》,《北京大学日刊》1924年3月5日,第2版。
8蒋梦麟:《西潮与新潮》,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134页。
9石约翰:《中国革命的历史透视》,王国良译,上海:东方出版中心,1998年,第189页。
1《中共党史参考资料》(一),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166页。
2《中共党史参考资料》(一),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164页。
3《基督教救国会征求答复俄牒同意函》,《申报》1920年4月20日,第11版。
4《新民学会资料》,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358页。
5《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0—1925)》第2卷,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20年,第91—92页。
6周月峰:《“列宁时刻”:苏俄第一次对华宣言的传入与五四后思想界的转变》,《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5期。
7《蔡和森文集》(上),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76页。
8新民:《列宁主义与中山主义》,《武汉评论》第37期,1926年1月21日。
9卓宣:《我们对于十月革命应有底认识》,《人民周刊》第30期,1926年11月7日。
1任弼时:《列宁主义的要义》,《中国青年》第3卷第63、64合期,1925年1月31日。
2趙世炎:《列宁的生平与教训》,《政治生活》1925年1月18日,第2版。
3一峰:《帝国主义浅说》,《中国青年》第2卷第46期,1924年9月27日。
4康文龙:《列宁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史料长编(1917—1927)》(下),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19年,第2006页。
5《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论编》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31页。
6《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论编》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32页。
7王懋廷:《帝国主义大纲》,中国国民党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政治部1926年发行。
8《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资料选编》,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133—136页。
1寰澄:《苏俄十月革命后八年来奋斗的经过》,《武汉评论》第28期,1925年11月7日。
2卓宣:《我们对于十月革命应有底认识》,《人民周刊》第30期,1926年11月7日。
3《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论编》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596页。
4任弼时:《苏俄经济政治状况》,《中国青年》第3卷第52期,1924年11月8日。
5《出版预告》,《向导》第188期,1927年2月16日。
1硕夫:《殖民地被压迫人民所应纪念的列宁》,《向导》第99期,1925年1月21日。
2《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论编》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31页。
3林根:《介绍“少年国际”杂志》,《中国青年》第3卷第51期,1924年11月1日。
4《陈独秀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502页。
5郑超麟:《十月革命、列宁主义和弱小民族的解放运动》,《向导》第135期,1925年11月7日。
6《李达全集》第6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38—39页。
7《列宁全集》第2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231页。
8康文龙:《列宁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史料长编(1917—1927)》(下),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19年,第2032页。
1任弼时:《列宁主义的要义》,《中国青年》第3卷第63、64合期,1925年1月31日。
2《毛泽东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470页。
3《梁启超游记》,北京:东方出版社,2006年,第32页。
4《陈独秀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127页。
5《李达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389页。
1《列宁全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161页。
2《列宁全集》第6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24页。
3《列宁全集》第6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121页。
4《列宁全集》第39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205页。
5《陈独秀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265页。
6《毛泽东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357页。
7《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18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454页。
8《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1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128页。
9《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1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139页。
10《建黨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1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132页。
1李玉贞、杜魏华:《马林与第一次国共合作》,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1989年,第24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