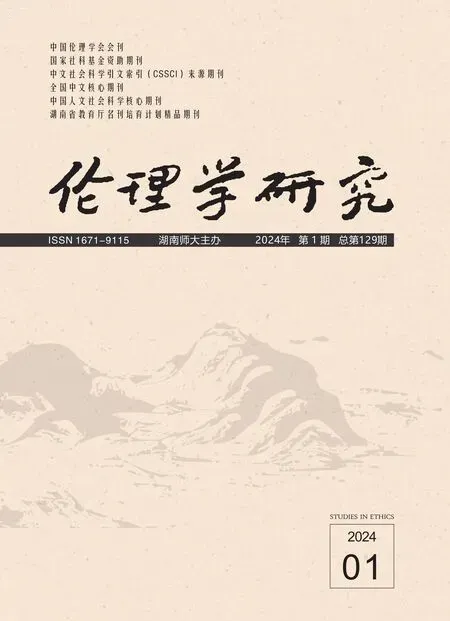毛泽东“无产阶级的革命的功利主义”思想的源头与实践
2024-05-21苗贵山
苗贵山
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130 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青年时代,毛泽东同志就以‘自信人生二百年,会当水击三千里’的壮志豪情,立下拯救民族于危难的远大志向,投身救国救民的伟大事业。为了找到中国的出路,毛泽东同志‘向大本大源处探讨’,在反复比较和鉴别中,毅然选择了马克思列宁主义,选择了为实现共产主义而奋斗的崇高理想,从此一生追寻,矢志不移。毛泽东同志的一生是为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而不懈奋斗的一生……在几十年艰难而辉煌的战斗生涯中,毛泽东同志为中华民族、中国人民建立了不可磨灭的历史功勋,作出了光耀千秋的历史贡献。”[1]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一方面赞颂了毛泽东在青年时期就已胸怀拯救民族于危难的远大志向,另一方面也肯定了青年毛泽东把这一远大志向与坚定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共产主义崇高理想的信念相结合,在中国革命与建设的历史进程中作出了光耀千秋的历史贡献。
毛泽东作出的光耀千秋的历史贡献首先体现在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贡献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毛泽东同志带领人民开创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没有革命的理论,就没有革命的实践。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具有普遍适用性,只有同各国实际相结合才能显示出强大的真理力量。”[1]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进行艰苦卓绝的伟大抗日战争的关键时刻,为夺取最后胜利,毛泽东坚持不懈地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的实际以及国内外优秀文化相结合,在1942 年5 月召开的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明确提出了“无产阶级的革命的功利主义”思想。毛泽东指出,中国人民的解放需要文武两个战线、两个军队的相互结合,军事战线需要“拿枪的军队”,文化战线需要“文化的军队”。针对“文化的军队”中出现的文艺工作者的立场、态度、工作对象、怎样工作、怎样学习等问题,毛泽东明确指出中心问题或基本问题是为群众的问题和如何为群众的问题,也就是“文艺为什么人”与“文艺如何为人”的问题。对于“文艺为什么人”的问题,毛泽东指出,我们的文学艺术都是为人民大众的,为工农兵而创作,为工农兵所利用。对于“文艺如何为人”的问题,毛泽东指出,文艺工作者是在深入群众并在向群众学习的过程中对群众进行文艺的普及与提高。在回答了上述基本问题后,毛泽东随即提出如下问题:“我们的这种态度是不是功利主义的?”[2](864)对此,毛泽东紧接着讲道,唯物主义者并不一般地反对功利主义,而是反对封建阶级、资产阶级以及小资产阶级的功利主义,以及口头上反对功利主义、实际上是最自私最短视的功利主义的伪善者。由此,毛泽东明确地作出如下论断:“我们是无产阶级的革命的功利主义者,我们是以占全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最广大群众的目前利益和将来利益的统一为出发点,所以我们是以最广和最远为目标的革命功利主义者,而不是只看到局部和目前的狭隘的功利主义者。”[2](864)毛泽东的这一论断,蕴含着丰富的“无产阶级的革命的功利主义”思想,这一思想基本内涵如下:
首先,解决的是“文艺为什么人”与“文艺如何为人”的问题,也就是文艺必须是中国无产阶级及其政党——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文艺工作者为工农兵等人民大众的利益服务的,这是立场问题。这种服务必须是在坚持群众路线中对人民大众进行文艺的普及与提高的,这是方法问题。其次,文艺工作的立场与方法问题同样也适用于革命工作,即是说,中国人民的解放不仅需要“文化军队”,而且需要“拿枪的军队”,革命工作也须是中国无产阶级及其政党——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军队,在坚持群众路线中为了工农大众的利益而对敌进行军事斗争,共产党人作为无产阶级的革命的功利主义者必须是为了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最大利益而斗争的,在斗争中必须坚持最广大人民群众的目前利益和长远利益、局部利益与整体利益的辩证统一。最后,无产阶级的革命的功利主义是与封建阶级、资产阶级以及小资产阶级的功利主义有着本质区别的,前者主张的是共产党人为人民大众的普遍利益而奋斗,后者主张的是剥削阶级的或个体的功利主义。中国共产党人的一切言论行动必须是以合乎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最大利益,为最广大人民群众所拥护为最高标准的。
毛泽东“无产阶级的革命的功利主义”思想既有其丰富的理论源头,也有其轰轰烈烈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实践遵循。本文对此加以详细探讨,以期对我们从整体上把握这一思想有所裨益。
一
毛泽东提出的“无产阶级的革命的功利主义”思想,肇端于他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求学时研读颇深的19 世纪德国人包尔生在改造边沁、密尔的功利主义基础上所倡导的目的论的个体自我实现论。
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求学期间,青年毛泽东在1917 年8 月23 日致亦师亦友的黎锦熙的信中指出:“当今之世,宜有大气量人,从哲学、伦理学入手,改造哲学,改造伦理学,根本上变换全国之思想。此如大纛一张,万夫走集;雷电一震,阴曀皆开,则沛乎不可御矣。”[3](73)唯有如此,方能不盲从模仿他人思想而求得真理,以此作为言行准则并有目的地做事,在变换全国之思想的基础上达到“改造中国与世界”(新民学会的宗旨)的目的。青年毛泽东研读颇深的中西方哲学与伦理学,首推陆九渊、王阳明的“心学”,以及19 世纪德国人包尔生在《伦理学体系》中所倡导的目的论的个体自我实现论。对这两者的改造与融通使得青年毛泽东在思想上养成了以致力于“改造中国与世界”为目的的一种特殊的“豪杰之士”的个性自我实现论。青年毛泽东于1917 年下半年撰写的作文《心之力》就是这种“豪杰之士”个性自我实现论的精华体现,极受恩师杨昌济赞赏,并被打了满分。他以“宇宙即我心,我心即宇宙”为开篇,认为世界、宇宙乃至万物皆为思维心力所驱使,但彼时国民心力沉疴羸弱,蛮夷恶敌肆意分割吞并华夏,万民为奴,国资殆尽。因此,若欲救民治国须要自强国民心力,倡导新学,新学不兴则御敌难成。《心之力》是毛泽东受谭嗣同的“心力”说的直接启发,并在阅读了由蔡元培根据19 世纪德国人包尔生的《伦理学体系》的第二篇内容从日文转译成文言文的《伦理学原理》后而撰写的。《伦理学原理》约10 万字,杨昌济教授把它作为教材来讲授。青年毛泽东在1917 年下半年对《伦理学原理》作了12100 字的评注,这足以说明包尔生所倡导的目的论的个体自我实现论对其影响至深。
包尔生在《伦理学体系》中既对以康德为代表的理性的形式主义的义务论与以边沁、密尔为代表的经验的功利主义的目的论进行了区别,又对二者进行改造并作了调和。具体地讲,一方面,包尔生把道德上对善与恶进行区别的理论归结为目的论与形式论,“前者根据行为类型和意志行为对行为者及周围人的生活自然产生的效果来说明善恶的区别,把倾向于保存和推进人的幸福的行为称作善的,倾向于扰乱和毁灭人的幸福的行为称作恶的。另一方面,形式论的伦理学则坚持善恶的概念标志着一种意志的绝对性质而无需涉及行动或行为类型的效果;这种绝对性质不可能得到进一步的解释,而是必须把它作为一个事实来接受”[4](231-232)。对此,青年毛泽东在批注中明确地指出:“善恶之区别以何为标准——一说只论动机,一说兼论效果。”[3](118)形式论就是动机论,目的论就是效果论。对于动机与效果的关系,毛泽东从文艺批评的角度进行了辩证唯物主义的阐释,明确指出文艺批评对于践行抗日与团结群众有好坏之分,“这里所说的好坏,究竟是看动机(主观愿望),还是看效果(社会实践)呢?唯心论者是强调动机否认效果的,机械唯物论者是强调效果否认动机的,我们和这两者相反,我们是辩证唯物主义的动机和效果的统一论者。为大众的动机和被大众欢迎的效果,是分不开的,必须使二者统一起来。”[2](868)而动机和效果统一的基础就是实践,社会实践及其效果是检验主观愿望或动机的标准。
另一方面,包尔生在汲取亚里士多德哲学中关于事物存在的目的因与动力因等“四因说”的基础上,对边沁、密尔的快乐主义的功利主义学说与康德的形式至善论进行了改造并作了调和,把功利主义的目的论与追求精神力量完美行动的自我实现论结合起来,提出了目的论的自我实现论。包尔生“用‘目的论’一词来代替‘功利主义’”,与此同时,“创造了自我实现论这一个词,以使我的观点与快乐主义形成鲜明的对照——亦即意志的目的不在感情,而在行动”[4](233)。他讲道:“我的观点可以表示为目的论的自我实现论。这样我们的原则就是:倾向于实现意志的最高目标——它可以被称之为幸福(福祉)的行为类型和意志是善的。我在此所说的幸福是指我们存在的完善和生命的完美运动。”[4](232)因此,“一个完善的人生即一个人的所有身体的和精神的能力都在其中得到充分发展和锻炼的生活,它是个人的至善”[4](24)。由此我们看出,包尔生把康德的形式至善论赋以人活生生的自我实现的生活,从而使其与功利主义的幸福论相融合。对于包尔生的关于完善的人生的主张,青年毛泽东把它表述为:“人类之目的,在实现自我而已,实现自我者,即充分发达吾人身体及精神的能力至于最高之谓。”[3](218)当读到包尔生批评康德夸大了义务意识在生活中的作用,用对道德律的尊重来取代自然的冲动,从而强调“义务的感情可能防止了世界上许多恶的产生,但美好和善良的东西却不是从义务的感情萌生的,而是从心灵的生气勃勃的冲动中萌生的”[4](23)的主张的时候,青年毛泽东极为认同、欣赏并批注道:“豪杰之士发展其所得于天之本性,伸展其本性中至伟至大之力,因以成其为豪杰焉……大凡英雄豪杰之行其自己也,发其动力,奋发踔厉,一往无前……泡尔生所谓大人君子非能以义务感情实现,由活泼之地感情冲动而陶铸之,岂不然哉,岂不然哉!”[3](193-194)此时,青年毛泽东的“豪杰之士”个性自我实现论初露端倪。
进一步讲,包尔生的个体自我实现的至善论汲取了边沁与密尔的功利主义中个体幸福与社会幸福相统一的思想,强调个人自我实现的至善是与推进他人的幸福或完善相统一的。他讲道:“一个人的行为在道德上是善的是当它倾向于推进行为者和他周围人的幸福或完善的时候,是当它伴有义务意识的时候。而另一方面,当它缺少善性的这两个特征时,或只缺少其中一个时,它在道德上就是应受谴责的……我们称一个人为善的,是当他对自己生命的塑造符合人的完善的理想、同时推进他周围人的幸福的时候。我们称一个人为恶的,是当他既无心愿也无能力为自己或他人做任何事情、相反却扰乱和损害他周围人的时候。”[4](258)这样一来,在包尔生那里,作为目的论的“幸福”概念与作为形式论的“至善”概念在自我的意志精神的完美实现的行动中得到了统一,个体在实现自我完善的同时推进他人幸福的生活是幸福的,无论是在行为上还是在意志上都是善的,它伴随着快乐,包含着快乐,但不等于快乐。这就与边沁、密尔的功利主义的快乐主义明显地区分开来。对此,青年毛泽东认为,这是包尔生主义的真面目。因此,当包尔生批评那种认为目的论的道德哲学不可能解释自我牺牲的论点,而盛赞罗马传说中的执政官雷古拉斯为了公共幸福的目的勇敢地率骑兵与高卢人作战而牺牲个人利益的榜样作用时,青年毛泽东批注道:“正鹄论,自昔学者恒称为功利论,以其较量行为之效果也……欲求某种效果,必行含有某种效果之行为,故杀身成仁之事,正鹄论之伦理学亦尊贵也。”[3](131)当包尔生继而指出“每一种真正的牺牲同时也是自我保存,即保存理想的自我”时,青年毛泽东又批注道:“此语甚精。观此语始知泡氏亦以个人主义为基础,此个人主义乃为精神的,可谓之精神之个人主义。个人有无上之价值,百般之价值依个人而存,使无个人(或个体)则无宇宙,故谓个人之价值大于宇宙之价值可也。故凡有压抑个人、违背个性者,罪莫大焉。”[3](131-132)青年毛泽东汲取了包尔生(这里,青年毛泽东简称包尔生为“泡氏”,亦泡尔生)的精神个人主义的精髓,并把它与现实主义并称为自己伦理观的两个主义。如此,“吾内而思维、外而行事,皆达正鹄”[3](180)。
必须指出的是,包尔生的精神个人主义不是纯粹的利己主义,或者说不是个体功利主义,也不是绝对的社会功利主义,而是强调个体精神的自我实现,而个体精神在自我实现的同时社会整体的生活也得到完善。青年毛泽东在阅读包尔生有关道德生活中个体自身的道德行为(德性)对个体来讲既是目的又是手段,以及个体的道德行为(德性)对道德整体来讲既是目的又是手段,亦即个体的德性对于个人和社会的完善生活的不可缺少等论述时批注道:“正鹄。此义极精,可谓伦理学一大发明。”[3](135)受其影响,青年毛泽东在哲学与伦理学观上主张在功利论(目的论)基础之上建立一种特殊的具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舍生取义”基因的、能够把个人和社会的完善生活统一起来的“豪杰之士”个性自我实现论。
青年毛泽东的“豪杰之士”个性自我实现论随即在社会实践中得到了践行,并且在与马克思主义发生的精神碰撞中,逐步转换成为了工农大众的解放而组织成为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并进行不懈奋斗的无产阶级的革命的功利主义的思想。早在1919 年7 月14 日《湘江评论》创刊宣言中,青年毛泽东就明确提出:“自文艺复兴,思想解放,‘人类应如何生活?’成了一个绝大的问题。从这个问题,加以研究,就得了‘应该那样生活’‘不应该这样生活’的结论。一些学者倡之,大多民众和之,就成功或将要成功许多方面的改革。”[3](270)在他看来,吃饭问题是人类生活的最大问题,为此就要在民众联合(平民主义)这一最强力量的基础上通过强权来打倒各种少数阶级专制的强权。1920 年春,青年毛泽东率湖南驱张请愿团到北京,继续践行他的“豪杰之士”个性自我实现论。在北京期间,他阅读了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考茨基的《阶级斗争》、柯卡普的《社会主义史》三本书,认为马克思主义对历史的解释是正确的,开始受到共产主义的启发并趋赴之。他在3 月14 日致同学周世钊的信中就讲到要在长沙创造一种新生活,办自修大学,组织“工读互助团”,过共产的生活,并且认为“俄国是世界第一个文明国……我们要组织一个游俄队”[3](429)。根据毛泽东在延安与斯诺的谈话,可知他于1920 年夏天起就确立了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这一点在他于1920 年11 月25 日致同学罗章龙的信中也得到了印证。他讲道:“我想我们学会,不可徒然做人的聚集,感情的结合,要变为主义的结合才好。主义譬如一面旗子,旗子立起了,大家才有所指望,才知所趋赴。”[3](498)这里,青年毛泽东所讲的“主义”就是马克思主义的共产主义,并以其为“指望”而趋赴之。由此,青年毛泽东开启了他在中国革命实践中把“豪杰之士”个性自我实现论与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革命价值观相结合,从而开启中国共产党人的“无产阶级的革命的功利主义”思想形成的新起点与新征程。中国共产党成立后,许许多多的中国共产党人为了人民大众的普遍利益与幸福而矢志不渝地奋斗牺牲的英雄气概,在大革命、国内革命战争、抗日战争时期得到了轰轰烈烈的迸发。所有这些为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明确提出“无产阶级的革命的功利主义”思想奠定了人生观、价值观、实践观的基础。
二
毛泽东提出的“无产阶级的革命的功利主义”思想,熏陶于中国共产党人把贯穿于《共产党宣言》的共产党人在无产阶级革命运动中为工人阶级的最近利益和长远利益而奋斗的无产阶级价值观同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实践相结合的历史进程。
毛泽东阅读超过百遍的《共产党宣言》对其把青年时期的“豪杰之士”个性自我实现论与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革命价值观结合,进而形成中国共产党人的“无产阶级的革命的功利主义”思想影响最深。《共产党宣言》作为马克思主义的“小百科全书”,以阶级斗争作为考察人类历史发展的主线,以资产阶级生产方式所导致的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尖锐矛盾及其发展趋势为内容,对无产阶级革命价值观的思想精髓进行了明确的阐释。其一,无产阶级革命有着与资产阶级革命根本不同的性质,表现为“过去的一切运动都是少数人的,或者为少数人谋利益的运动。无产阶级的运动是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的运动”[5](411)。为此,无产者必须组织形成阶级及其政党去反对资产阶级的政治与经济统治,消灭资产阶级所有制。“共产主义革命就是同传统的所有制关系实行最彻底的决裂;毫不奇怪,它在自己的发展进程中要同传统的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5](421)其二,马克思、恩格斯强调无产阶级革命运动必须随时随地依据当时的条件来进行,并把无产阶级革命的原则性与灵活性相结合,“共产党人为工人阶级的最近的目的和利益而斗争,但是他们在当前的运动中同时代表运动的未来”[5](434)。其三,无产阶级革命的目标,是通过无产阶级革命,废除资产阶级私有制这一阶级对立的条件,建立起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的自由人的联合体。这三个方面集中体现了包括无产阶级革命的性质、领导力量、革命策略与革命目标在内的马克思主义无产阶级价值观的核心内容。
毛泽东把《共产党宣言》所主张的无产阶级价值观运用到中国革命实践中,逐渐形成了符合中国革命实际的以中国革命的领导力量与依靠力量、中国革命的性质与道路、中国革命的策略与革命眼前目标和长远目标为内容的中国革命的理论,从而为他提出“无产阶级的革命的功利主义”思想奠定了理论基础。就中国革命的领导力量与依靠力量来讲,毛泽东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中指出:“一切勾结帝国主义的军阀、官僚、买办阶级、大地主阶级以及附属于他们的一部分反动知识界,是我们的敌人。工业无产阶级是我们革命的领导力量。一切半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是我们最接近的朋友。那动摇不定的中产阶级,其右翼可能是我们的敌人,其左翼可能是我们的朋友——但我们要时常提防他们,不要让他们扰乱了我们的阵线。”[6](9)就中国革命的性质与道路来讲,毛泽东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井冈山的斗争》对此有较为具体的论述:“中国现时确实还是处在资产阶级民权革命的阶段。中国彻底的民权主义革命的纲领,包括对外推翻帝国主义,求得彻底的民族解放;对内肃清买办阶级的在城市的势力,完成土地革命,消灭乡村的封建关系,推翻军阀政府。必定要经过这样的民权主义革命,方能造成过渡到社会主义的真正基础。”[6](77)这是毛泽东对中国革命性质最早作出的既遵循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又符合中国实际的认识,这为后来毛泽东提出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奠定了理论基础。就中国革命的策略与革命眼前目标和长远目标来讲,毛泽东在《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中,批判了党内那种认为中国民族资产阶级不可能和中国工农联合抗日的错误观点,指出在革命的形势改变的情况下,革命的策略与领导方式也必须改变,党的基本的策略任务是建立广泛的民族革命统一战线,中国革命在当时依然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性质的革命,不是无产阶级社会主义性质的革命,革命的动力是工人、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在总结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经验的《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毛泽东明确指出,中国革命战争都是中国无产阶级及其政党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在全国人民面前,表示了自己是人民的朋友,每一天都是为了保护人民的利益,为了人民的自由解放,站在革命战争的最前线”[6](184)。在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时期的任务》中明确指出,中日民族矛盾成为主要矛盾,国内矛盾降到次要的地位与服从方面,为了和平、民主和抗战,为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共产党、国民党、全国人民,应当共同一致为民族独立、民权自由、民生幸福这三大目标而奋斗”[6](259)。虽然这三大目标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性质的,但是每一个共产党员应当明白认识到,“重新整顿三民主义的精神,在对外争取独立解放的民族主义、对内实现民主自由的民权主义和增进人民幸福的民生主义之下,两党重新合作,并领导人民坚决地实行起来,是完全适合于中国革命的历史要求,而应为每一个共产党员所明白认识的。共产党人决不抛弃其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理想,他们将经过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阶段而达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阶段”[6](259)。毛泽东的上述主张,为他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提出“无产阶级的革命的功利主义”思想的论断奠定了符合中国革命实际的理论前提。
三
毛泽东提出的“无产阶级的革命的功利主义”思想,启示于列宁的“文艺为千千万万劳动人民服务”以及鲁迅的“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的无产阶级革命文艺思想。
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专门对列宁与鲁迅的文艺思想作了肯定,指出他们的文艺立场坚持的是文艺是为人民大众而不是为地主阶级与资产阶级等剥削者压迫者服务的,与此同时,强调文艺的基础不是抽象的人性论,不是抽象的“爱”的呓语,而是具体的且有着阶级性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文艺工作,是从具体的无产阶级的人性论出发的,是为人民大众利益服务的。因此,文艺就有一个如何与新的时代的群众相结合的问题。在《党的组织和党的出版物》中,列宁阐明了“文艺为千千万万劳动人民服务”的文艺思想,指出自由的写作,“不是私利贪欲,也不是名誉地位,而是社会主义思想和对劳动人民的同情……不是为饱食终日的贵妇人服务,不是为百无聊赖、胖得发愁的‘一万个上层分子’服务,而是为千千万万劳动人民,为这些国家的精华、国家的力量、国家的未来服务。这将是自由的写作,它要用社会主义无产阶级的经验和生气勃勃的工作去丰富人类革命思想的最新成就,它要使过去的经验(从原始空想的社会主义发展而成的科学社会主义)和现在的经验(工人同志们当前的斗争)之间经常发生相互作用”[7](666-667)。列宁的“文艺为千千万万劳动人民服务”的思想,不仅为毛泽东提出“无产阶级的革命的功利主义”思想奠定了“文艺为什么人”的无产阶级革命立场,而且也给毛泽东提出革命与文艺工作“为人民服务”这一中国共产党的宗旨以直接的启示。在1944 年10 月对陕甘宁边区文教工作者所作的《文化工作中的统一战线》的讲演中,毛泽东明确指出:“我们的文化是人民的文化,文化工作者必须有为人民服务的高度的热忱,必须联系群众,而不要脱离群众。要联系群众,就要按照群众的需要和自愿。一切为群众的工作都要从群众的需要出发,而不是从任何良好的个人愿望出发。”[2](1012)
对于鲁迅的文艺思想,毛泽东以鲁迅的两句诗——“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来加以称赞,指出这两句诗应该成为共产党领导文艺工作的座右铭。对于鲁迅的这两句诗,毛泽东站在无产阶级革命文艺的立场上专门进行了解释:“‘千夫’在这里就是说敌人,对于无论什么凶恶的敌人我们决不屈服。‘孺子’在这里就是说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一切共产党员,一切革命家,一切革命的文艺工作者,都应该学鲁迅的榜样,做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的‘牛’,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知识分子要和群众结合,要为群众服务,需要一个互相认识的过程。这个过程可能而且一定会发生许多痛苦,许多磨擦,但是只要大家有决心,这些要求是能够达到的。”[2](877)鲁迅在给左翼作家联盟的意见中曾说:“联合战线是以有共同目的为必要条件的……我们战线不能统一,就证明我们的目的不能一致,或者只为了小团体,或者还其实只为了个人。如果目的都在工农大众,那当然战线也就统一了。”[8](182)“杂文时代”的鲁迅以犀利批判与辛辣讽刺闻名,他是真正站在人民的立场上来说话的,强调文艺对人生改良与社会变革的“不用之用”的积极作用。正如毛泽东所指出的,即使是对人民的缺点的批评,鲁迅也是怀着保护人民、教育人民的满腔热情来说话的。值得指出的是,鲁迅的文艺思想深受俄国马克思主义者普列汉诺夫的以唯物史观为基础的文艺思想影响,反对那种摆脱阶级的利害、为艺术而艺术的观点,强调文艺的阶级性以及革命文学与战斗文学的阶级利害的功利性倾向。在为普列汉诺夫的《文艺论》而作的“译本序”中,鲁迅指出,蒲力汗诺夫(普列汉诺夫)“用丰富的实证和严正的论理,以究明有用对象的生产(劳动),先于艺术生产这一个唯物史观的根本底命题。详言之,即蒲力汗诺夫之所究明,是社会人之看事物和现象,最初是从功利底观点的,到后来才移到审美底观点去。在一切人类所以为美的东西,就是于他有用——于为生存而和自然以及别的社会人生的斗争上有着意义的东西。功用由理性而被认识,但美则凭直感底能力而被认识。享乐着美的时候,虽然几乎并不想到功用,但可由科学底分析而被发见。所以美底享乐的特殊性,即在那直接性,然而美底愉乐的根柢里,倘不伏着功用,那事物也就不见得美了。并非人为美而存在,乃是美为人而存在。——这结论,便是蒲力汗诺夫将唯心史观者所深恶痛绝的社会、种族、阶级的功利主义底见解,引入艺术里去了”[8](202-203)。
四
毛泽东提出的“无产阶级的革命的功利主义”思想,践行在中国共产党以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最大利益为最高标准的革命行动中。
正如马克思所言,任何真正的哲学作为自己时代精神的精华,必然会同自己时代的现实世界接触并相互作用。毛泽东的“无产阶级的革命的功利主义”思想作为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时代精神的精华,有其轰轰烈烈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为中国人民的解放而奋斗、牺牲和创造的革命实践遵循原则,概括地讲,就是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中所强调的“中国共产党人的一切言论行动必须以合乎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最大利益,为最广大人民群众所拥护为最高标准”[2](1096)。毛泽东的这一主张,鲜明地体现了边沁、密尔的功利主义主张的个人利益最大化与最大多数人的利益最大化的思想。青年毛泽东对边沁、密尔的功利主义理论的把握,不仅在其对包尔生的《伦理学原理》的评注中得到了集中的展现,而且在对其恩师杨昌济所著但彼时尚未出版的《西洋伦理学史》的整整七本的抄录中有了更为清晰的认知。《西洋伦理学史》的第三篇“近世伦理学”的第五章“英国之功利说(其一)”与第四篇“十九世纪以后之伦理说”的第四章“英国之功利说(其二)”,以及杨昌济本人所撰写的《西洋伦理学述评》对公众的快乐主义即功利主义的述评,对功利主义作了明确的论述,这使得青年毛泽东对功利主义理论印象深刻。杨昌济讲道:“公众的快乐主义,一曰功利主义,又曰功利说。此主义以最大快乐为判断行为之标准;最大快乐者,自快乐减去苦痛残余之快乐之最大量之谓也。由享受快乐者之为自己,或他人,或社会,或一般人类,而快乐主义生种种之区别:有标榜自己之最大快乐者谓之个人的快乐主义,古代希腊之伊壁鸠鲁,近世英国之霍布斯等所主张者是也;有以他人最大之快乐为目的者谓之利他主义,法国孔特之所倡者是也;以社会或一般人类或有情生类之最大快乐为行为之目的,则谓之公众的快乐主义,在十九世纪之初期配列,边沁,穆勒等之所倡者是也。”[9](211)杨昌济对边沁与穆勒(密尔)的功利主义学说作了略述,指出快乐与苦痛是主宰人类的主权者,道德上的善与恶的区分就是以快乐与苦痛为标准,产生快乐的行为就是善,产生苦痛的行为就是恶。“是故道德的行为,不在于致己一身之快乐,而在于致社会公众之快乐;人生究竟之目的,乃最多数之最大幸福也。”[9](211)
杨昌济所讲的功利主义“人生之目的乃最多数之最大幸福”的主张,对毛泽东提出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最大利益是中国共产党人一切言论行动的最高标准产生了直接影响。在中国革命的具体的历史的实践中,毛泽东把这一中国共产党人一切言论行动的最高标准确定为为现在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而奋斗与为将来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而奋斗的这两个前后相继但又不能“毕其功于一役”的目标。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中指出:“只有经过民主主义,才能达到社会主义,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天经地义。而在中国,为民主主义奋斗的时间还是长期的。没有一个新民主主义的联合统一的国家,没有新民主主义的国家经济的发展,没有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和合作经济的发展,没有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即新民主主义文化的发展,没有几万万人民的个性的解放和个性的发展,一句话,没有一个由共产党领导的新式的资产阶级性质的彻底的民主革命,要想在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废墟上建立起社会主义社会来,那只是完全的空想。”[2](1060)毛泽东进一步指出,共产党人不怕而且提倡本国的资本主义在一定条件下的发展,因为与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对中国人民的压迫相比,本国的资本主义发展是进步的且是不可避免的,“它不但有利于资产阶级,同时也有利于无产阶级,或者说更有利于无产阶级……我们共产党人根据自己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明确地知道,在中国的条件下,在新民主主义的国家制度下,除了国家自己的经济、劳动人民的个体经济和合作经济之外,一定要让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在不操纵国民生计的范围内获得发展的便利,才能有益于社会的向前发展。”[2](1060-1061)基于此,毛泽东把中国共产党人一切言论行动的最高标准具体化为生产力标准。他说:“中国一切政党的政策及其实践在中国人民所表现的作用的好坏、大小,归根到底,看它对于中国人民的生产力的发展是否有帮助及其帮助之大小,看它是束缚生产力的,还是解放生产力的。消灭日本侵略者,实行土地改革,解放农民,发展现代工业,建立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和富强的新中国,只有这一切,才能使中国社会生产力获得解放,才是中国人民所欢迎的。”[2](1079)在这里,毛泽东提出的生产力标准,不是泛指一般的生产力,而是指具体的新民主主义时期的生产力,即为着中国人民的利益而发展的生产力。“中国人民”的概念是同新民主主义时期生产力发展的主体力量相对应的,对此,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中指出,在新民主主义时期,社会生产力的解放和发展同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最大利益是一致的,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都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的主体力量,社会生产力只有在实现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最大利益的基础上才能得到解放和发展,而“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最大利益”的思想是以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为前提的。
“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最大利益”这一中国共产党人一切言论行动的最高标准,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国内革命战争、抗日战争与解放战争中得到了具体的展现。概括地讲,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大革命运动展现了中国共产党为人民和民族的最高利益不惜赴汤蹈火的宁死不屈的革命意志和大无畏的自我牺牲精神。中国共产党开展的根据地的土地革命就是要让广大农民翻身得解放,就是为人民的根本利益而斗争。中国共产党作为全民族抗日战争的中流砥柱,为着全民族的利益,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领导人民与人民军队宁死不屈、血战到底,支撑起中华民族救亡图存的希望。中国共产党领导解放战争,推翻了帝国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封建主义在中国的统治,建立了独立、自由、民主的新中国,人民从此成为新中国、新社会的主人,为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幸福、民族复兴开辟了广阔的道路。正是在践行这一中国共产党人一切言论行动的最高标准而进行的伟大革命进程中,毛泽东的“无产阶级的革命的功利主义”思想所蕴含的中国共产党“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意识得到了充分彰显。在《论联合政府》中,毛泽东在谈到人民战争中共产党领导的军队时指出:“这个军队之所以有力量,是因为所有参加这个军队的人,都具有自觉的纪律;他们不是为着少数人的或狭隘集团的私利,而是为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为着全民族的利益,而结合,而战斗的。紧紧地和中国人民站在一起,全心全意地为中国人民服务,就是这个军队的唯一宗旨。”[2](1039)“为人民服务”作为中国共产党与人民军队的宗旨,不仅体现了每一个中国共产党人在兢兢业业地为人民大众利益而自我牺牲的革命奋斗中淬炼而成的个体的伦理意识,而且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在轰轰烈烈的为人民大众利益而奋斗创造的革命事业中所凝聚成的政治共同体的伦理精神。早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所著的《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中,毛泽东就专门对红四军党内存在的报复主义、小团体主义、享乐主义等各种个人主义的非无产阶级思想作了批评,指出个人主义“完全从个人观点出发,不知有阶级的利益和整个党的利益”,“只注意自己小团体的利益,不注意整体的利益”,“到大城市不是为了去工作,而是为了去享乐”,“这是一种削弱组织、削弱战斗力的销蚀剂”[6](92)。毛泽东对各种个人主义的非无产阶级思想的批评,就已鲜明体现出中国共产党人应有的伦理意识与伦理精神。在中国革命的实践中,毛泽东把中国共产党人应有的伦理意识与伦理精神进一步发展为他在《论联合政府》中讲到的三个原则:一是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的原则;二是密切联系群众的原则;三是向人民负责与向党负责相统一的原则。“我们共产党人区别于其他任何政党的又一个显著的标志,就是和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取得最密切的联系。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一刻也不脱离群众;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而不是从个人或小集团利益出发;向人民负责和向党的领导机关负责的一致性;这些就是我们的出发点。共产党人必须随时准备坚持真理,因为任何真理都是符合于人民利益的;共产党人必须随时准备修正错误,因为任何错误都是不符合于人民利益的。”[2](1094-1095)毛泽东的“无产阶级的革命的功利主义”思想是真理,因为它符合人民的利益,并在中国革命与建设的实践中得到了丰富的检验。